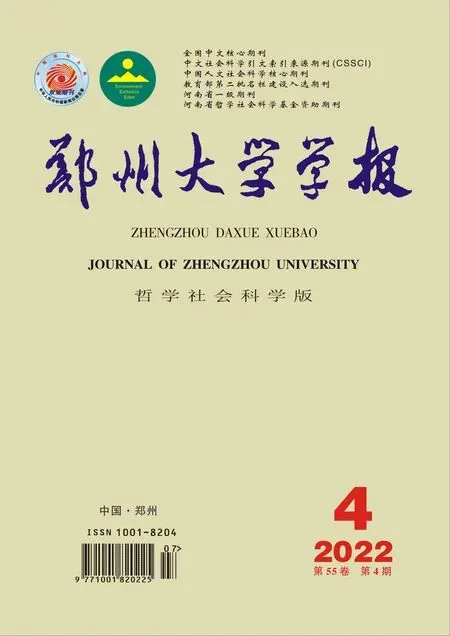民国慈善义演的政治与社会意义
——以《顺天时报》和天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李爱勇 李文姬
(1.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475000;2.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450000)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慈善史研究过程中涉足义演这一新的领域,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清末民初的义务戏已经具有慈善公益性、社会网络性和民间主体性特点。寓善于乐的都市慈善义演,包容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歧见,融入了知识精英的国民塑造,更促进了演艺界等社群的身份认同。具有义演性质的游艺会甚至成了“娱乐救国”的重要公共空间(1)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岳鹏星:《清末民初义务戏的属性》,《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郭常英、岳鹏星:《寓善于乐:清末都市中的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岳鹏星、郭常英:《晚清都市空间中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以慈善义演为视点》,《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李爱勇:《娱乐如何救国:近代游艺会“公共空间”的形塑》,《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近代中国的慈善和义演活动,多与中国政治局面和社会形态密切相关,但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比较缺乏。作为近代中国演艺活动的主要传媒,近代报刊对慈善或义演具有重要的传播与促进作用。但是,不同的报刊又有着很大的区别。晚清民国期间在中国华北地区发行的北京《顺天时报》和天津《大公报》,有着发行量较大、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深刻的共同点,但在办刊背景、政治立场和社会关注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他们对民国义演的报道有着较丰富和复杂的内容呈现。故此,本文以这两报为考察对象,研究民国时期义演具有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分析演艺界人士因此发生了怎样的近代转变,揭示报纸在近代中国所展现的影响力。
一、动员社会和民众:民国义演的政治意义
近代中国面临重大的变局,知识精英呼吁培养新的国民意识以塑造新的民族国家。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思想大解放之后,中国每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必然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参与,属于社会活动的义演也因此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首先,义演为近代中国民众间接参与各种爱国运动提供了展现民族大义的舞台,推动了爱国运动的广泛发展。1912年4月,在黄兴通电倡议创办国民捐以抵制外债之后,“保国即保家,保家即保身”的爱国热潮迅速在全国形成。当时的社会各界在这种热潮的推动下开始积极组织义演,他们通过倡导募捐来表达热烈拥护并积极参与国民捐的意愿。当年6月,天津的高陈作新女士联合同志在丹桂茶园演义务戏两晚,将“所得戏资全数充作国民捐”[1]。7月,河北关下绅民张兆瑞诸君倡议并组织在普乐茶园演唱义务戏数日,也是将“所得戏资全数充作国民捐”。9月,中华民国生计总会为自筹经费“在三庆园演唱夜戏六日”[2],但自救仍不忘救国,以“两日充作国民捐款”[3]。这次国民捐运动中社会各界所组织的义演活动在抵制借用外债、维护经济主权方面所表现出的政治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从1916年10月开始,天津法租界试图进一步扩张所引发的市民抗议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作老西开事件。次月,天津正乐育化会全体以“天津绅商为老西开争地一案,爱国热诚,至堪钦佩。惟经费所关,应须辅助”,乃“联合同志,情愿稍效绵薄,……约集京、津男女著名艺员,假大舞台,合演上好戏剧。所得戏资,全数助充争地案之经费,聊尽爱国之微忱”[4]。租界非法扩张因天津人民极力反对而失败,其中也有艺界同仁在义演的舞台上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赎回胶济铁路是中国1922年2月在华盛顿会议上与日本签署条约确定“债券赎路”后的一次救国运动。次月,北京高师学生因“赎回胶济铁路,需款在即”,便“排演《卖国贼》一剧”在第一舞台演出,“鼓励国人之爱国心”,将“所入之款,完全作为赎路之用”[5]。4月,天津青年会则为此组织演戏、跳舞、游艺大会,“来宾约六百余人”[6]。这次赎路运动开创了近代中国以外交手段收回铁路路权的先河。这时的社会义演则成了各界筹集赎路款、扩大赎路运动影响的重要手段,并在实际上产生了积极作用。
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近代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是时,“全国群起而抵抗强权,拥护公理,已成为中华民族对外的一种有力的表示”[7]。在《大公报》所做的17次相关义演报道中,义演的组织者有新新戏院、东天仙舞台、权乐茶园、爱人义务电影院、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新学书院、工商大学、安徽怀远含美学校以及天津各界联合会、沪案后援会等。这些义演极具政治意义,组织者演戏筹款多“以为外交运动上之经济的援助”[8],而非简单的经济援助。义演宣传要么是“救济沪上罢业同胞”[9],要么自称“京中梨园全体热心同胞”[10],表现了明确的爱国情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热河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接连不断,相关义演也随之日益频繁。艺界名角尚小云和广东音乐会分别在天津北洋戏院和春和戏院演出义务戏,以所得票款援助“一·二八”事变中的十九路军。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时,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两次举行音乐会,将票款悉数拨充前方将士之用。坤角金友琴偕赵少云在开明戏院“演唱义务戏二日,筹款慰劳前方将士”[11]。战争造成大批的伤兵和难民,为了救济他们,南开高中毕业班举行音乐会,开滦矿务总局俱乐部演剧,公艺国剧社组织义务戏,均用所得票资救助战地灾民、伤兵和医院。
在绥远抗战时,各种援助和慰劳抗战的义演此起彼伏,媒体报道也最多。1936年11月和12月,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天津分会举行音乐大会,天津平报社长刘赈风发起演剧,北宁路局国剧社演剧,天津各校学生举行游艺大会,北平天升电影院举行慰劳游艺会,梅兰芳自发演援绥义务戏两场,北平报界全体同仁发起演慰劳义务戏,南开学校举行募款音乐演奏大会,均为援助和慰劳绥远抗战。他们呼吁“站在后方的全国国民,都应当努力来援助正在寒天雪地的民族英雄们。我们援助的方法,最好的当然是捐款了”,“此种筹款运动,实为我津人士捐款爱国一好机会”[12]。绥远抗战能取得重大胜利,离不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此起彼伏的义演和相关的媒体报道。
其次,义演是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表达政治愿望和塑造政治形象的重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政治的进步。参加义演的群体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1912年5月,李怀霜等人发动自由党的党员特约天津“商学各界著名皮簧专家牺牲色相登台奏技,所得剧资全数充作救国捐”[13]。6月,直隶国民捐总事务所也“约请商学界热心志士演唱义务夜戏,……除开销正当经费外尽数充作国民捐”[14]。绥远抗战时,安徽省蚌埠大戏院、移风剧社演出两场义务戏,将收入汇寄绥远。其他类似义演,如蚌埠联谊社游艺募捐大会,也是由蚌埠县党部领导举行。
在1926年5月到8月的南口大战中获得胜利的直系在控制北京后,决定于8月28、29两日在第一舞台演义务夜戏以抚恤灾民,并要求北京全体名演员加入。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等召集同业在梨园公会开会,“一致赞成,同业一律加入,概尽义务,共成善举”[15]。戏票则由警察厅仓促在27日交由二十区警署向各住户劝售。《顺天时报》对这两天的义务戏进行了十三次报道,其中包括五篇名为《第一舞台之义务夜戏庆贺战胜抚恤灾民》(9月2日、3日、4日、5日、6日,署名听花)和三篇名为《庆胜恤灾义务戏评》(9月2日、3日、4日,署名泽公)的戏评。其评论称“冯军倡赤化,各省蔓延,非但流毒于中国,抑得传染于全球。联军诸将领,不忍人民陷斯危劫,大举挞伐,誓行扫灭。义师所至,国军望风而逃”[16]。名义上的恤灾义务戏被抹上了浓重的庆胜意味和政治色彩。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借革命外交之机挑起了中东路事件,其背后实际上获得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鼎力支持。这其中就包括南京政府的地方部门积极组织各种慰劳东北防俄将士的义务戏。1929年11月,北平市党部慰劳东北将士筹备会联席会议讨论演戏筹款。会议推定各成员所属部门与梨园公会进行严正的交涉称:“演戏筹款,慰劳防俄将士,事属为国酬劳,较总商会与梨园公会合办之义务戏有轻重缓急之分,应令其尽先为贵会表演。”[17]但因“时局急促,市面萧寂,剧场营业,尤属不振,入不偿出”,联合部门与梨园公会的交涉并不顺利,筹备会又多次开会,商讨“在不妨艺员生活之范围以内,解决一切,举行义举。以期慰劳将士之热诚”[18]。12月3日,各界慰劳防俄将士筹备会第八次联席会解决了款项分配问题,“十成之五,专供慰劳东北将士之用,以壮士气;总商会拟定十成之三五,系为偿还前次给养之垫款,以清拖欠;梨园公益会,拟定十成之一五,系为本年底赈给困苦同业,以度年关”[19]。
民国期间的各界名流通过对艺界名角的追捧,既赋予了他们明确的政治标签作用,又扩大了政治力量在社会中的影响。1934年2月22日,梅兰芳由南京到上海义演前,褚民谊陪同他拜谒中山陵,孔祥熙设午宴欢送,班禅以其艺术盖世、热心公益特赠哈达、金佛各一[20]。1936年9月2日,梅兰芳由上海飞往北平,到机场候迎的人有梨园公会全体执监委、尚小云和马连良等艺界名角、国剧学会齐如山、新华银行经理曹少璋、北平市政府专员吉世安等二百余人[21]。一个月后,梅兰芳又应天津中国大戏院之聘赴天津义演[22]。梅兰芳当时已是全国的艺界大王,其所得到的政治礼遇是其义演政治意义的显现。
再次,义演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民间社会组织和人员的政治影响。1923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及当时中国对日本的赈灾和相关义演不单单是慈善活动,相关报道已上升到国际政治的高度。地震发生后,《顺天时报》倡议对日赈灾义演,呼吁“吾中国有同种同文之谊,急起提倡赈济,责无旁贷。……凡艺界均有助赈之义务”[23]。该报有关中国赈济日灾义演的政治性长篇大论,对情境的煽情描绘远远多于对事实本身的报道,这显然与其日本背景有着莫大的关系。当时的《大公报》对此也进行了关注,并且认为“梅兰芳因前曾一渡东京,颇为日本朝野人士所优遇,故对于此次日灾亦拟有特别贡献”[24]。可见,中国当时的对日赈灾义演上升到政治层面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作为一种民间社会组织,中国的帮会与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近代更是重视培养与普通民众的关系。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时,江南一带大量难民纷纷逃往上海避难。据《申报》1924年11月至1925年1月的大量报道,张啸林、杜月笙、黄金荣等帮会大佬积极组织演艺界进行了多次联合演剧助赈。作为上海十分活跃的著名票友,杜月笙更是在江浙难民赈灾义演中亲自登台出演了《黄天霸拜山》。与他关系十分密切的梅兰芳,每到上海几乎都会拜会他,二人还合演过《四郎探母》[25](P224-228)。这种情况并不是当时的个例,近代中国的帮会不少都经营娱乐业,娱乐业的竟秀与赈灾很多也都有帮会背景。由此看来,帮会组织及其成员通过义演,在医治战争创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实现了自身从社会向政治的跨界流动。
二、匹夫之责:义演的社会意义
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民国时期参与义演的各社会群体也发挥着十分主动的作用,在义演的舞台上展示了自我形象。艺界通过舞台义演增强了其社会共同体意识,显示了义演活动的社会意义。
首先,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义演有组织者、表演者、场地提供者、剧本写作者等各种社会群体,义演是他们展示自我形象和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舞台。民国初年的国民捐运动开始后,中国社会的各个群体都积极参与到义演筹捐之中,展示了积极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我形象。1912年5月,天津天仙茶园掌柜孙成兴及名优汪笑侬等演唱义务戏,将所得茶资全数捐作国民捐,“藉尽国民之天职”[26]。视参加国民捐为应尽之义务者还有杨小菴、毛朗舟及李剑颖等大批地方名伶。前述河北关下绅民张兆瑞等组织义演支援国民捐,更是普通民众通过义演展现形象的例子。
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组织义演成为各界发挥社会功能医治战争创伤的重要方法。1924年10月,河南禹县惨遭屠城以后又遭遇兵灾,“旅津豫人,因闻梅兰芳将在皇宫电影园献技”,便积极“约其演义务剧,为禹县灾民筹款”,“闻名伶杨小楼、陈德霖等向称热心公益,亦经该同乡聘请”[27]。1925年底,中国北方的直系、奉系、直鲁联军联合进攻倾向于国民革命的西北军。次年1月,京师绅商临时救济会,邀集在京著名艺员,在第一舞台演唱义务夜戏,以救济战后灾民。世界红十字会曾在北京设妇孺收容所六处,慈善家沈秀水等多人于1926年7月,邀集富连成全班并马连良等人在明星电影院演唱义务夜戏,以所收票价补助收容所费用。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援助战地军士和赈济流亡难民的义演,展现出了义演参与者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形象。1932年12月,天津电报局国剧研究社称“溯自上年国难发生以来,敝局同人即废止一切娱乐,敝社亦于是时停演。迄今年又二月,国难演进未已,本不应再事笙歌。袛以顾念难胞□□流难,痛苦万状。坐视有所不忍,挽救又苦无方”,特定于12日“在春和演冬赈义务戏”[28]。1933年1月,天津“光明、明星两戏院鉴于榆关失陷,难民群集平津,……开映救济战地被难同胞特别早场。所有收入,扫数捐助”;平安电影院也“举行义务电影特场,……售票所得完全拨交报馆、救济战地被难同胞”[29]。之后,天津市天宫电影院、新新电影公司等纷纷开演特场,收捐救助战地被难同胞。当时的义演组织者多认为,“社会上多数人,均能存此心念,躬行实践。此即健全的社会,亦即救国之根本办法”[30]。
其次,以音乐人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灌注到剧目之中,其他参与者则积极组织义演,将这种共同的责任与使命展示给观众。1928年的济南惨案发生不久,国立音乐学院的师生创作了《国难歌》《国民革命歌》《五三国耻歌》《国耻》《反日运动歌》《忍耐!》等一大批痛斥日本侵略者暴行、表达激愤之情和抗敌决心的歌曲。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呼吁称,“同胞们,务须留心,这里的歌词,不是风华雪月、才子佳人,是我们的悲壮的叫喊;同胞们,务须留心,这里的曲谱,不是娱乐,不是游戏,是作战的武器”[31]。在这里,一个将音乐创作视为爱国表演舞台甚至是抗战杀敌战场的知识分子群体形象已经跃然于纸上。
社会各界通过义演活动展示反映自己责任与使命的剧目,与民国创建同时发轫,与重大事件始终相伴。1912年6月,北洋高等女学堂召开国民捐游艺会时,参与者先后唱国歌和劝捐歌、进行爱国演说以及表演惊醒和竞争游戏,都是在向广大民众宣传他们所想表达的深层蕴意。当有了赎回胶济铁路的机会后,北京男女高师的师生便于1922年3月组织“游艺大会,排演《卖国贼》一剧,以鼓励国人之爱国心。……所入之款,完全作为赎路之用”[5]。1933年6月,喜峰口战役开始后,战区难民纷纷逃津避难,天津光明大戏院两次放映电影,筹款救济难民,影片为《血战余生》和《战地二孤女》等。7月12日,天津春和大戏院公演了余亦的《丰年》、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张季纯的《二伤兵》和田汉的《梅雨》。义演向观众展现的不仅是剧目内容本身,还表达了组织者关注中国局势的赤子之心和国民之情。
因为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义演中的不少作品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认同。1925年8月,天津国民同志会沪案后援会组织了义务戏,其剧目《亡国痛史》《华工血泪》和《五卅惨案》等内容“原起来于我们现在国家,实有极大助力,很可以启发各界爱国思想。最好者为《五卅惨案》,因此事始末真相,这般演员全是由上海亲眼看来的,并还有亲身经历者。一经开演,较比旁处演的一定要真确详实”[32]。《战地二孤女》讲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少女凌文娟、陈荔英流落关内,同时爱上年轻医生叶剑波,“一二八”事变后,又一起抛弃儿女私情参加义勇军和救护队的故事。二人“初则因战祸天涯相逢,继则因爱情而相嫉恨,终则因国家而下大牺牲”的情形被演的“异常逼真”,“使人有悠然不尽之思”[33]。1936年11月,南开校友筹款援绥与赈济贫民的演出剧目有李子玉之《花子拾金》,“李君拾得金子时,即说:‘穷人发财,如同受罪,我干脆捐助绥东吧!’临时抓词,恰得其当,无怪乎满堂报以彩声”[34]。义务戏的组织者和演出者都十分用心,所以能深深打动观众。
“五四”前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责任与使命的体认,已经超越了思想解放的范围,浸成了担当中国社会精神领袖的理想与抱负,不仅准备充当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而且开始与国民革命的实践相联系,在指导民众中更发挥了独到和重要的作用。其他社会群体对中国社会同样十分关心,他们尽心尽力地组织各种义演,展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并且获得了十分广泛的认同。
再次,在发起组织和参与义演的过程中,演艺界和其他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了一个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命运共同体,而不再仅仅是之前那种在社会底层卖艺和谋生的芸芸大众。1923年9月的日本大地震期间,中国演艺界人士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有“昔岁东渡,备览物华、地主之情”的梅兰芳寄书《顺天时报》,表示“欲发起全国艺界国际助赈大会,而以京师同人,首为提倡……组织会务,演剧筹款,陆续尽数拨汇,以啁灾区暨我华被难侨民”[35]。随后,他约请报界多人及杨小楼、龚云甫等20多位同仁讨论,最终决定演戏筹款以恤日灾。当时的舆论认为,“自北京而上海、汉口、天津诸埠,凡艺界均有助赈之义务”,并盛赞“梅兰芳凡事不落人后,毅然发起全国艺界国际助赈大会,热心提倡,所见甚大。婉华之知识高超,洵不愧为剧界之首领也”[23]。第二年,梅兰芳又赴日慰问演出,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大义。
演艺界的国内共同体形象,则是近代知识分子为救国家而积极倡导塑造的具有“匹夫之责”的国民。1925年6月,天津华商新新戏院同仁声明:“自沪案发生,举国共愤;凡属同胞,无不力争。本院同人,亦国民一分子。……(故)开演援沪义务电影两场。所收入票资,悉数拨交沪上总商会,援助失业工人。”[36]天津艺曲社全体社员等演艺筹款援助沪案罢工同胞时,虽“自知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仍“略表寸心,聊尽匹夫之责”[37]。当时,“程艳秋、贯大元、郭仲衡、侯喜瑞等,前在上海,目击沪潮惨状,恻隐发心,本拟发起演剧,藉资救恤。奈因归期已迫,未及举行”,回京后便“假鲜鱼口华乐园,演义务戏一晚,以遂素愿”[38]。
民国初起,国民身份在普通民众的意识中,已经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时人称,“现在改革政体实行共和,无论何等社会非具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不为功”[39]。1912年7月,天津警界也声明,“警界同人等亦均系国民一分子,窃愿步各界之后尘,聊尽救国之义务”,所以“约请各大戏园男女诸名角合演义务戏,除去艺园开销外,全数充作国民捐”。受此影响,天津丹桂茶园“前后台掌柜及各大戏园男女诸名角,大发热心情,愿于初四日早晚再加演一天,以尽义务”[40]。普通民众在共同体塑造中所发挥的规模效应,从下面一例即可一窥盛况。1923年9月,济南艺界在商埠公园举办筹赈日灾游艺大会,放映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摄东京大火影片,……各界仕女既得游览之娱,又得慈善之实,……公园前车马水龙,道路堵塞,园内人山人海,几无立足之地”[41]。由于普通民众与政治运动的复杂关系,近代中国的一些爱国运动使得当时中国的外交与内政联成一体,国内各方力量形成了全国一致对外的局面,执政府因此也不得不顺从民意。
三、媒体聚焦:义演的舆论引导作用
报纸是近代中国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新兴媒体,它在传播新闻消息、表达社情民意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舆论作用。近代中国的报纸,由于主办者背景不同,政治立场多有差别,其宣传报道在新闻选择和舆论制造方面也往往具有十分明显的差别。民国时期的义演因与各种重大事件密切联系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报道义演活动的各大报纸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舆论影响力。作为民国期间华北地区发行量较大、影响十分深远的大报,《顺天时报》和《大公报》展现了不同角色的作用。
对于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确立场的《大公报》来说,民国时期义演活动的舆论意义在于,它为《大公报》塑造不偏不倚的理性民族主义形象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重要的内容。前述国民捐运动、老西开事件、胶济赎路运动、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榆关抗战、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重大事件,都是民国义演的重要历史背景。新闻嗅觉和政治意识敏锐的《大公报》对相关义演进行了大量报道,而且保持了相对冷静、客观的态度,即使在报道赈济日灾义演时也能秉持中立、公正的立场。同时,在相关报道中,《大公报》还多次发表评论,其中不乏鼓舞国人、激发爱国热情的呼吁。
在介绍援助上海五卅运动的义务戏时,《大公报》给予五卅运动积极评价,实际上也有助于提升义演的社会影响力。报道认为,“英人一再擅杀同胞,举国共愤。上海工人毅然罢工,不为所用,以作外交声援。忠勇不□,极堪钦敬”[42]。“沪上罢工达三十万,为国人之先锋,制英日之死命,奋勇牺牲。□□衣食而不顾,力谋接济,实我同胞之责任。”[43]从1925年6月12日至8月2日,《大公报》对艺界援助沪案义演的报道几乎与五卅运动相始终,这里自然有义演的举行与五卅运动相始终的蕴意。在报道与五卅运动相关的义演时,《大公报》评论说,五卅运动“倘再失败,中国前途真不堪问矣”[44]。关注义演实为关注运动,而关注运动实为《大公报》与中国命运密不可分的重要表达。
在1933年5月报道春和演义务戏接济长城抗战后方医院时,《大公报》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军队在长城抗战中“与敌血战数十日,不愧为壮烈之牺牲,为民族而奋斗。杀敌致果,举世惊震,造成光荣之史页,与十九路军互相辉映。故其战事情况,极为吾人所欲知”[45]。
对于《大公报》在“九一八”事变后所表现出的理性民族主义立场,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大公报》在思考和处理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时,不偏不倚,避免情绪化和非理性化;它既反对“与日一战”(即对日宣战),但也不赞成不抵抗政策,主张在自卫的前提下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它认识到国联作用有限,但也不反对利用国联和国际舆论进行外交斗争[46]。就当时实际情况来看,其立场和主张无疑是最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一种理性选择。
作为清末日本外务省出资在北京创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对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义演报道,是其借机渗透、干政中国的一条秘密途径。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对于《顺天时报》的性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日本方面在评价《顺天时报》时说,它巧妙地从内容到形式等方面抓住了中国人的心理,使得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它是外国人经营的报纸[47]。正因为如此,《顺天时报》才能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特务活动的秘密基地。巴黎和会期间,它对日本在中国山东问题上观点和态度的报道,可以说是日本吞并山东“野心”的全纪录。在报道“济南惨案”时,它更是歪曲事实真相,完全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和代言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爱国民众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运动,最终迫使这份由日本官方暗中支持、充当日本侵略中国舆论先锋的报纸停刊。
《顺天时报》对和日本有关且有助于提高日本形象或有益于日本的义演,进行十分肯定和赞许性的报道,可以追溯到清末新政时期其对中国有关维新和强种的义务的认同。1907年2月,在赵子奇、田际云等发动演戏集资赈捐时,该报《女子出洋》剧本有“女界中,既然有,我甄维新;必定要,发宏愿,普救柔魂。到东洋,勤考察,输入文明;回国来,立女学,教习自任”[48]等语。9月,田际云等为救灾和戒烟筹款演义务戏时,《顺天时报》在详细报道时言“救灾是爱群,戒烟是强种,这都是预备立宪上的要点,不可不记出。令我中国人要实行爱群强种主义的看看”[49]。当时中国戊戌维新已然失败,清末新政徒有其名,这种报道显而易见是意图引导中国的政治舆论。
在日本关东大地震时,《顺天时报》积极报道和评论中国艺界的各种筹款赈灾义演。它对顺利举行的义演毫不吝惜多次盛赞,而对稍有意外的义演则多加责难。如1923年9月,京师男艺人在第一舞台联合演唱赈济日灾义务夜戏,该报评论人辻听花称赞:“该舞台上,必呈剧界罕睹之伟观。而扶桑数十万之灾黎,暨一般国民,可以感激中国剧界之大义举矣。”[50]同年10月2日,辻听花发现赈济日灾义演“发表之伶界通启中,不揭小翠花之名。且昨、今披露之剧目中,亦无该伶之戏码”后,“骇异非常,极引为憾事”,称“翠花所以不演义务戏者,似大有秘幕在”,“该戏办事人中之某伶(暂秘其名),因自己所管戏园营业问题(问题内容今不发表),大怨翠花。遂排斥他议,由艺员名单中,剔除翠花……某伶所为,蔑公谋私,可谓咄咄怪事矣”[51]。7日,署名“萍水”者再次发文批评义务戏发起人杨小楼、梅兰芳,指责他们“对罗致名伶则大有区别。与其厚者,或平素仰其鼻息,则邀之;反之,则不理”[52]。
对于无关日本形象或利益的义务戏,《顺天时报》几乎都是记述事实本身,或仅对几乎都是传统剧目的表演本身进行评论,绝少称赞义务戏的举办。1917年10月对京兆水灾义务夜戏的报道评论说:“呜呼!国步艰难日逼一日。政客大老攘利争权无所底止。比较诸剧界艺员协同一致义务演剧以赈灾黎者,殊有天渊之别”[53]。1923年4月,它将坤角斌艳亲王碧云霞、文艳亲王金少梅、雪艳亲王琴雪芳比为孙文、段祺瑞、张作霖,并称“三伟人名望素著,牺牲色相,与女同胞谋幸福,胜彼扰乱国家阴谋叵测者多矣”[54]。其中指桑骂槐的用意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对《顺天时报》和《大公报》义演的报道进行比较,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它们对义演舆论意义的运用,及其在近代中国政治问题和社会义演中扮演的角色。国民捐运动、老西开事件、胶济赎路运动、五卅运动(含省港大罢工)等事件,有助于激发国民意识并推动民众参与政治与社会变革,社会各界为了声援这些运动而组织和参与各种各样的义演,《大公报》对此都进行了尽量详细的报道,并给予了较为积极正面的评价,甚至还借此机会表达了自己关心中国政治和推动社会义演的心声。对于1925年的五卅运动,《顺天时报》的报道不同于《大公报》的极力正面评价和高度赞扬:其一,所报道的义务戏均演传统剧目。其二,在报道义务戏缘由时虽也称“沪案发生,天下嚣然。全国各界人士莫不投袂奋起,慷慨悲愤”,但目的是“欲公正解决,以维人道”,这个人道是“剧界中人,亦奋然义勇,恻隐为心,以期尽国民义务”[9]。7月29日,该报唯一一次报道津门绅商热心爱国,却是完全抄袭了《大公报》三天前的新闻稿。其三,与前述报道日本赈灾尽量刊登义务戏举办者通启不同,在报道旅京粤人梁士诒等为粤案筹款募捐发出通启时却没有刊登具有广告性质的《通启》[55]。对1926年南口大战后直系张宗昌强力推进为期两天的慈善义演,《顺天时报》则做了大量报道且不乏对国民军的污蔑之词。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顺天时报》在报道中认为,中东路事件起因于“苏俄肆焰,东北边防告急”[19]。在中国东北边防军已于11月战败的情况下,它仍报道援军义演,并以爱国为幌子大肆鼓动中国民众反苏,“所有驰名中外之名伶梅兰芳、杨小楼、程艳秋、王又宸、郝寿臣、荀慧生、尚小云等均行登场,表演颇极卖力”[56]。“作战以来,瞬经数月。以三省之师抵全俄兵力,自不免少有顿挫。而各将士仍勇悍直前,愤不欲生。其忠心耿耿,不禁令人钦佩。北平各界,鉴于各将士爱国热枕,历尽冰天雪地之苦,共起慰劳,商同著名艺员演戏筹款”[5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公报》对中东路事件劳军义务戏仅在11月5日、13日、14日发了3篇报道,且只是报道事实,没有发表评论。
总之,在多次以政治事件为背景的义演上,《大公报》详细报道的,《顺天时报》多采取回避的态度,甚至一言不发。反之,《大公报》表示审慎和理性态度的,《顺天时报》便大肆渲染。多次报道以五卅运动为背景的义演,也并不能说明《顺天时报》有什么特别。因为它的报道讲的是剧界“以期尽国民义务”,而非中国民众的“爱国”。五卅运动的导火索虽与日本有关,但在爆发和席卷全国后反英的成分要更多,该报报道更多的是为了表现关注姿态。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推动了近代中国义演的发展和转型。演艺界人士在义演中用国民意识和爱国精神推动政治与社会的演进,同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进行自我的塑造。近代中国各群体的民族认同是维系相关活动和作用的主线和主题,义演并非是一种独善其身的社会活动,而是与近代中国有紧密联系的文化现象。在这种独特的现象中,作为义演核心的演艺界人士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在用国民意识和爱国精神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与演进的同时,也在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在此基础上塑造自己崭新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