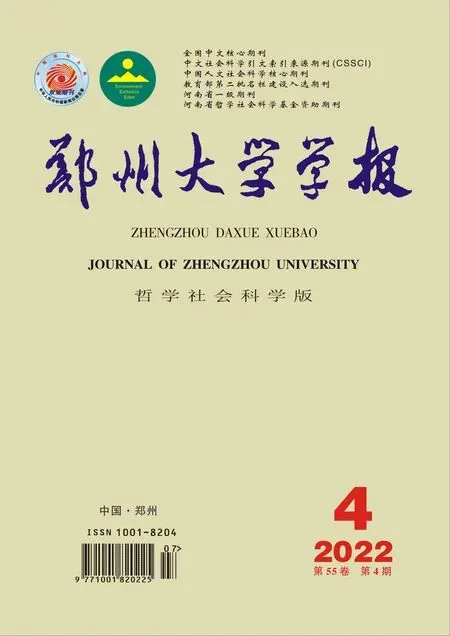民间眼光:虚构、非虚构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李 萱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无论是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的当代文学创作的“民间文化形态”,还是文学在创作过程中对本然存在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创造性转化,“民间文化形态”都“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1](P12)。这种“比较真实的”“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是基于“民间眼光”的文化表达。从整个社会文化形态的角度出发,“民间眼光”和基于“民间眼光”呈现出的民间生活,是“民间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中国文学创作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展示出了较多种类型的“民间文化形态”,例如城市民间、乡村民间等,这些民间的美学展现,都离不开“民间眼光”这一最根本的民间文化形态。由于女性视角与日常生活和民间话语的贴近,当代女性写作天然地对“民间眼光”以及“民间眼光”下女性的生存状态有着独特的认知,先后探索了平民化书写、底层女性书写和非虚构写作等基于“民间眼光”的各种表达方式。
一、以“民间眼光”进入平民世界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在文坛的“新写实小说”就是以“民间眼光”为核心的文学创作形态。1989年第3期的《钟山》杂志开设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提出了“新写实小说”的名称,认为“新写实小说”“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面对现实、直面人生”[2]。“新”主要是指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的塑造,“新写实小说”更加注重表现生活的“纯态事实”,以“一种相对‘客观’的创作态度”“以近似冷漠的叙述态度来掩藏作者的主观倾向性”“以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利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1](P307)。这种“未经权利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就是“民间眼光”下的真实的普通生活,也是平民视角下的普通的日常生活。有学者曾总结过“新写实小说”平民意识表现的三个方面:直面生活的平民生存关怀;民间立场的平民价值取向;大众话语体系下的平民意识表达[3]。这三个方面都是在“民间眼光”这一“民间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创作的具体表现层面。对于“新写实小说”的创作者而言,“民间眼光”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回归“纯态事实”的重要方法和文化资源。
以“民间眼光”进入平民世界,这些作家们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人间烟火味。池莉的《烦恼人生》刻画了一个普通小市民“从半夜开始”的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一天:赶轮渡,跑月票,挤食堂,上菜场,孩子跌伤,老婆怨忿,住房拆迁,奖金泡汤……一个武汉小市民的种种生活烦恼和读者们的生活烦恼重叠在一起,激起了读者们的共鸣,也成为一代人抹不去的时代记忆。虽然刘震云等男作家也在进行“新写实小说”创作,但是女作家的“新写实小说”在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烦恼的时候,也多了不少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温情描写。《烦恼人生》写的是印家厚的故事,但是通过印家厚的心理活动,我们看到了他背后的女人的生存状态和两性之间的惺惺相惜、互相支撑:“印家厚头也不回,大步流星汇入了滚滚的人流之中。他背后不长眼睛,但却知道,那排破旧老朽的平房窗户前,有个烫了鸡窝般发式的女人,她披了件衣服,没穿袜子,趿着鞋,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她在目送他们父子。这就是他的老婆。你遗憾老婆为什么不鲜亮一点吗?然而这世界上就只她一个人在送你和等你回来。”“烫了鸡窝般发式的女人”“没穿袜子,趿着鞋,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这是对平凡女性日常生活状态的描写,同时也是对普通夫妻粗糙生活状态的描写,虽然“不鲜亮”、不浪漫,但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他们“达观而质朴”,互相支撑着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池莉在《也算一封回信》中曾经说过:“举目看看中国大地上的人流吧,绝大多数是‘印家厚’这样的普通人,我也是。用‘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的信条来面对烦恼,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从许许多多的人身上我看到了这种性格,因此我赞美了它。”[4]戴锦华在《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一文中也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她们亦比他人更为固执地执着于她们事实上并不从属的‘庸常之辈’和‘小市民’的热情、书写与认可。它不仅出自在想象、写作、虚构中的对‘想象的社区’的获取,而且是被放逐者朝向放逐者的认同,是对某种新的、悬浮的、无根的文化、历史的弃置,和对一个古远而朴素的历史的皈依”,她们“以一个弱小而绝抉的背弃者的身份,在不期然间记录了一个变迁的时代与变迁中的话语”[5]。尽管池莉一再宣称“我也是”“‘印家厚’这样的普通人”,但事实上,池莉等新写实小说家“并不从属于‘庸常之辈’和‘小市民’”,他(她)们是知识分子,而“民间眼光”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她)们进入这块“想象的社区”的法宝,以虚构性创作“记录了一个变迁的时代与变迁中的话语”。
二、基于“民间眼光”的女性底层书写
21世纪以来,“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和事”的“底层文学”成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6]。这里的“底层”主要指的是“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7](P48-49),这与“新写实小说”指向的“平民”或普通人是有区别的,更为关注处于民间底层的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在底层文学创作中,既有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关注和书写,例如林白的《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也涌现出不少来自“底层”作者的自我发声,其中较多是女性作者,例如郑小琼、范雨素等。
郑小琼来自四川南充的一个小村庄,中专毕业,在东莞打工。她自己本身处于社会的底层,也见过底层世界的冷暖与悲欢,闲暇之余,用诗歌来书写社会底层残酷的生活状态:不分昼夜超负荷的工作、恶劣的工作环境、打工者的焦虑、女工们的孤独和命运……她的诗歌都来自她切实的打工体验,来自她作为女性的对生活和女性生存状态的敏感。诗歌《流水线》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在流水线上不分昼夜工作着的“打工仔”们,他们没有姓名,没有梦想,像一条条“在打工的河流中”挣扎着的“鱼”,只能听命于工业时代自己的“命运”:“在流动的人与流动的产品间穿行着/她们是鱼,不分昼夜地拉动着/订单,利润,GDP,青春,眺望,美梦/拉动着工业时代的繁荣/流水线的响声中,从此她们更为孤单地活着/她们,或者他们,互相流动,却彼此陌生/在水中,她们的生活不断呛水,剩下手中的螺纹,塑料片/铁钉,胶水,咳嗽的肺,辛劳的躯体,在打工的河流中/流动……在它小小的流动间/我看见流动的命运/在南方的城市低头写下工业时代的绝句或者乐府。”
郑小琼的诗更为关注的是“女工”这个群体,“她们”在打工族中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心酸和痛苦。《女工记》是郑小琼2012年出版的诗集,她“用七年时间的追踪和思考,感同身受地记下女工们的欢笑与眼泪、快乐与悲伤、希望和绝望”[8],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关于女性、劳动与资本的交响诗”。在《关于〈女工记〉》这首以诗的形式呈现的《女工记》的创作谈中,郑小琼讲述了她创作《女工记》时复杂的情感:“有时候,我会忘记台下的学生与朋友,我只想和这位/曾经的工友聊天,或者正如你说的那样,在讲着一个/中国女工的命运,我不知道我眼里的湿润是回忆着昔日的友人/还是为一群中国女工的命运,在这些薄薄的书页里/也许我习惯自言自语的力量,如同我习惯在流水线的/沉默的力量,习惯面对生活的洪流的力量,沉默与忍耐/在这工业时代,在这群中国女工的命运里,似乎是唯一/注释,有时想想她们面对的工伤职业病未来/还有爱情希望梦想,以及她们讲述的婚姻童年乡愁/这一切我是那样的熟悉,它们潜伏在流水线上/也潜伏在她们瘦小的身体里,有贫困,有挣扎/有虚弱,也有沉默,有理想,也有美好,喜悦/她们有着的一切,将构成中国的工业时代/也将成为工业的见证,在这些瘦瘦的诗句间存在。”
郑小琼在关于《女工记》的访谈中曾经说过:“我想写的只是关于女工的记录,用最真实最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女工的人生。”[8]记录“她们面对的工伤职业病未来”,记录她们的“爱情希望梦想”“婚姻童年乡愁”,记录“潜伏在她们瘦小的身体里”的“贫困”“挣扎”“虚弱”“沉默”还有“喜悦”[8]。这种“最真实最原生态的方式”就来源于最真实最原生态的“民间眼光”,郑小琼天然拥有这样的“民间眼光”,所以才“更愿倾听那些默默无闻者的声音”,愿意“选择用工友的名字来作为一首诗歌的标题”,愿意呈现“一个个具体的女工个体的命运,而不是群体的样本化的面孔或公共化的面孔”[8],愿意把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的一个个鲜活女工的生活、故事、压抑、愤懑、沉默等,都传达出来。
郑小琼这种天然的、真实的、原生态的“民间眼光”来自于她“打工者”的身份和经历:“我跟本身在打工的写作者的立场更相同一些,而与非打工者的作者在写作打工题材时的立场与观点差异较大。比如有人关注的是农民工在城市赚到钱回家了,或者中国农民进城等问题,而我关注的是农民工进城遇到了哪些问题,哪些方面需要引起关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等等。”[8]也正是因为这种天然的“民间眼光”,使得郑小琼敏锐地发现了“写作者的立场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结论与倾向也完全不一样”,她自身更愿意以一个“女工”的身份去“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具体不同的人在面临现实时所呈现的或无力、或奋斗、或成功、或失败的事实”[8]。作为女工,她天然地去关注这些女工不同于男性打工者的更为辛酸的人生经历和悲惨遭际,同时,作为打工者,她也天然地去思考进城的打工者内心深处“没有进城”的判断和错位的人生感受。在她“瘦瘦的诗句间”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打工者特别是女工们所经历和遭遇的一切,这“将构成中国的工业时代”“也将成为工业的见证”。
2017年,通过自媒体亮相的范雨素拓展了底层女性“民间”书写的边界和方式。范雨素初中毕业,“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带着两个女儿在北京做“育儿嫂”。虽然都是打工人,但是“育儿嫂”的工作却只有女性在做,文学中不乏“保姆”的身影,缺少的却是“保姆”的发声。范雨素的文字却不仅仅是在诉说“育儿嫂”的艰辛,她只是平静地讲述了“我”、母亲、大哥、女儿、皮村工友等底层人们的普通生活,虽然“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但是她并没有通过写作进行悲惨的渲染,而是不断地传达“不如意”中的乐观、坚强和知足。这是一种更贴近当代中国普通大众生活的“民间眼光”,以致《我是范雨素》等文章在网络上持续刷屏,得到了“我们都是范雨素”的共鸣。
三、“民间眼光”与非虚构写作的立场
《人民文学》自2010年第2期起开设了“非虚构”专栏,又于2011年第6期起开设了“非虚构小说”专栏。与此同时,很多文学刊物如《中国作家》《钟山》等都开始设立与非虚构相关的栏目,在文学界掀起了一股“非虚构”热潮。
《人民文学》在开设“非虚构”专栏时曾坦率地表明:“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9]此后,很多学者都对“非虚构”“非虚构写作”“非虚构文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洪治纲认为:“‘非虚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作家面对历史或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它以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在直面现实或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呈现出创作主体的在场性、亲历性和反思性等叙事特征。”[10]冯骥才则认为“非虚构”“成了一个大袋子,所有虚构性创作之外的传统写作都涌了进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散文、传记和自传、口述史、新闻写作、人类学访谈等等”,而实际上“非虚构文学不等于非虚构写作”,非虚构文学“要达到优秀的虚构文学的高度,就需要文学的力量与价值,就要关注文学的思想、人物、细节、语言”[11]。尽管关于什么是“非虚构”“非虚构文学”没有统一的界定,但“非虚构写作”的“在场性”“亲历性”“真实性”“介入性”以及“以创造性的方式呈现精确事实”[12]的写作方式,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而这种“在场性”“亲历性”的文学创造性表达,即是“民间眼光”在文学创作中的又一次创造性转化形式。
真实性与文学性是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一体两翼,“民间眼光”是融合真实性和文学性的重要途径,是造就非虚构文学创作呈现出“民间文化形态”的重要文化资源。有学者将目前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分为两大类:“一是个人性的非虚构写作,二是社会性的非虚构写作”,“第一种写作类型偏重于以个体真实的经历、经验作为写作资源”,“第二种社会性的非虚构写作,具有强烈的当下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此类写作格外关注群体性事件、有话题度的事件、时代性的事件,并以此类社会事实为写作内容,意在发现深层的社会问题或探寻一个时代的本质真相”[13]。无论哪种类型的非虚构写作,都需要作者的“民间眼光”。
梁鸿在《中囯在梁庄》的前言中将这种“民间眼光”称为“整体性的眼光”:“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性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让村庄的过去与现在、它的变与不变、它所经历的欢乐、所遭受的痛苦、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14](PⅩ)这里的“整体性的眼光”和“我的眼睛”实际上就是民间文化形态所自带的“民间眼光”,缺少了这种“见证”“呈现”式的“民间眼光”,非虚构写作的“在场性”“亲历性”很难得到保证。
《中国在梁庄》发表于2010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是当代文坛非虚构写作的“扛鼎之作”。梁鸿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对于“梁庄”的非虚构写作,需要借助“民间眼光”来完成,她自己在小说的前言中也谈到这一点:“与其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的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14](PⅫ)“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是以“民间眼光”来“重新感受”这片土地,以“民间眼光”做“一个文学者的纪实”,“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14](PⅫ)。
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眼光”,梁鸿的非虚构写作是有“归乡者对故乡”的“判断”的:“这个女儿无法将眼前的村庄和记忆中的村庄并置在一起,无法安之若素,无法不加判断地展示梁庄。所以,在这部作品里,尽管梁庄人也在发声,但分贝最高、最具感染力的还是作家本人的声音,她的判断、好恶与悲悯情怀都强有力地引导着读者。”[15]也就是说,作者客观上要求自己要以“民间眼光”来观察、感受自己的故乡,主观上却又不断地以“知识分子”的眼光来进行评判和思考,这导致作者的“民间眼光”不再是展示故乡的“纯态事实”的“民间眼光”,而是展示出一个“知识分子”归乡者感受正在变化着的故乡的“民间眼光”。
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民间眼光”,前者暂时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将自己归位为普通人,回归普通的日常生活,以“零度叙事”的方式展示普通人的悲欢喜乐;后者保留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将“知识分子眼光”和家乡人的“民间眼光”融为一体,将非虚构的“真实性”和文学的“文学性”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不同类型的非虚构写作:“民间眼光”是进入“村庄”、理解“村庄”的途径,而“知识分子眼光”是思考“村庄”、审视“村庄”的方式,二者的融合,表现为一种知识分子“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这一过程“亲历性”的非虚构写作。
在这场一个知识分子“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的“亲历性”的非虚构写作中,梁鸿既展示了自己作为一个博士、教授的文学素养和社会观察能力,同时也将自己作为女性的天然的敏感和敏锐展露无遗,更为关注农村“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留守儿童”的现象。但她并没有刻意地突出对女性的特别关注,而是在纯然的“民间眼光”的浸润中,整体性地呈现了当代中国农村的衰败和变化,在这种整体性的“眼光”中,男女老少、土地、房屋、河流都在她的视野之内,整体性地得以呈现。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女性文学创作,是一种既有女性视角又没有特别突出女性视角的文学创作,在更开阔的视野之下,表现了对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所有存在的悲悯之情。
梁鸿的非虚构写作展示出了女性文学创作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虽然梁鸿曾经反思过《中国在梁庄》的写作方法:“尽管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中,我告诫自己要避免以自己的知识体系凌驾于村庄生命和生活之上,并因此采用了人物自述和方言的方式,以减少自己的干扰,但是,最终也并没有完成。我注意到,我总是不自觉地在模拟一种情感并模仿鲁迅的叙述方式,似乎只有在这样一种叙事中,我才能够自然地去面对村庄。”[16](P86)但她“知识分子眼光”和“民间眼光”融合的写作方式,仍然是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探索。
乔叶的《拆楼记》则展示了女性文学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性。《拆楼记》发表于2011年第9、10期的《人民文学》,是《盖楼记》(《人民文学》2011年第6期)的姊妹篇,也是当代“非虚构写作”的重要作品。《拆楼记》所聚焦的村庄是山阳市张庄村,现属于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张庄村是“我”姐姐的婆家所在地,小说以张庄村为依托讲述了“我”帮姐姐盖房又利用政府拆迁补偿的机会赚钱的故事。与《中国在梁庄》不同,乔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拆楼记》中并没有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我有意克制着自己的道德立场,为此甚至在文本中故意模糊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作品中的‘我’,连工作单位都没有明确地指认。‘我’最明确的叙述身份就是一个乡村之根还没有死的逃离者,一个农夫的妹妹。更坦白地说,我怕自己像个很有道德立场的知识分子。而那种所谓的道德立场,不是冷眼旁观,就是高高在上。其实我也曾试图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但我很快发现我做不到,我站不稳。不仅仅是因为我的乡村之根还没有死,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农妇的妹妹,更重要的是,我一向从心底里厌恶和拒绝那种冷眼旁观和高高在上。我不喜欢那种干净。我干净不了。我无法那么干净。我对自己说:那就和姐姐他们混在一起吧,尽管混在一起让我很不舒服,我也不可能舒服,但我只能把自己投身到姐姐他们中间,投身到他们的泥流里。然后再去说别的。……我尽量客观地裸露我所看到的事实,还有事实中的我自己。其他的,就交由读者。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立场吗?”[17](P249)
这是一种立场,是乔叶在进行“非虚构写作”时所选择的特有的立场——隐去知识分子的身份,隐去道德的评判,作为“一个乡村之根还没有死的逃离者,一个农夫的妹妹”的身份,“投身到”“盖楼”“拆楼”的过程中去,并在对这个过程的参与中,呈现出“我所看到的事实”和“事实中的自己”。乔叶确实作为“一个农妇的妹妹”的身份参与了张庄拆楼事件,以往的“非虚构写作”倾向于把自己看到、听到、调查到的事件清晰地传递出来,“我”是“看”的主体、“听”的主体、“记录”的主体、“思考”的主体,但不是“参与”的主体。在《拆楼记》中,乔叶选择把“我”作为一个“参与”的主体呈现,而不仅仅是“呈现”的主体。
如果说“非虚构写作”是作家想要呈现的“事实”的“舞台”的话,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是“知识分子眼光”和“民间眼光”相融合的呈现,“知识分子眼光”是舞台上方的灯光,“民间眼光”是舞台上的灯光,二者融合,将舞台上的人和事清楚地呈现。乔叶则是将自己沉浸于“民间眼光”之中,沉浸于生活的“此处”,将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暴露”在文学之中。梁鸿的“知识分子眼光”隔断了“民间眼光”烛照下的“看”“听”“记录”主体背后的“阴影”部分,只呈现舞台上的光景,乔叶则将自我、他人、事实全部沉浸于“民间眼光”之中,在参与具体事件的过程中,将“事实”360度的整体呈现。她让读者“看到灯光之下和灯光之外,看到前台和后台,看到白天和夜晚,看到那些拆迁和被拆迁的人们,他们真实的、赤裸裸的动机、利益和情感,不是对着记者、对着麦克风所说的,而是他们正在做的”[18](P4)。从这个意义上说,乔叶的“非虚构写作”探索了“文学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一种“更全面的感受形式和思想形式”,“尽可能忠直地回到全面的人生和经验”[18](P3-4),回到既有阳光也有黑夜、既有美好也有残酷、既有善良也有残忍的生活“此处”,尽管这“此处”“如此赤裸清晰,令我们羞愧不安”[18](P2)。为此,李敬泽在给《拆楼记》所写的序言中说:“凡是惧怕注视自身的人,不要打开此书。/凡在此处‘安居’而乐不思蜀的人,不要打开此书。/凡戴着言词和公论的盔甲,永不卸下的人,不要打开此书。/凡坚信世上只有黑白二事的人,不要打开此书。”[18](P2)这种令人“惧怕”“羞愧不安”“赤裸清晰”的东西,来自于乔叶在小说中的“特定身份以及相随而来的局限和偏见”,她站在人物该站的地方,“以自剖其心的态度,见证了她的所见和所知”,她坦露了她对身边的人的“爱”,坦露了她的“失望”,包括对自己的“失望”[18](P6)。
有意思的是,在乔叶对身边的人和自己的“爱”和“失望”中,书写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姐妹”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中,“姐妹”关系是常见的主题之一。在中国民间故事中,“两姐妹”的故事比较常见,“渗透着传统社会对女性人格的评价以及女子以夫为尚的价值标准”,其中充斥着“姐姐对妹妹的欺骗和残杀”“妹妹对姐姐的咒骂和报复”,“既体现了女性因为社会不公所导致的过分倚重婚姻的狭隘乃至很大程度上的人性扭曲,也隐然蕴含着女性自私、妒忌、狠毒等评价意向”[19]。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书写中,也经常出现对女性“姐妹情谊”的书写,这些女性一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因为某种共同的生活经历而相遇并相互帮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女性同性爱恋关系。而在《拆楼记》中,乔叶呈现了一种更为复杂却又更为客观真实的姐妹关系,一个离开家乡十多年的知识分子妹妹,和一个仍然留在家乡的农妇姐姐,二者之间的互相惦记、牵挂,还有无法避免的相处时的“小心翼翼”“不舒服”甚至“厌弃”。这样的姐妹关系过于真实,在乔叶的另一篇小说《月牙泉》中也曾经出现过,这是乔叶在“民间眼光”的烛照下对自我的发现,对当代社会不可避免的一种新型家庭关系的发现,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她对自我内心深处“阴暗”面的发现,这是乔叶“非虚构写作”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