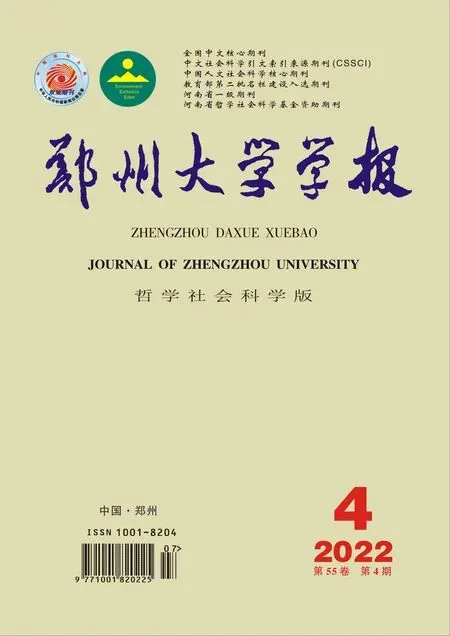丝绸之路视阈下西方“异托邦”营造的“中国风”
张婧楠 崔荣荣
(1.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江苏 无锡214122;2.浙江理工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西方“中国风”作为一种以视觉文化为主的16-18世纪艺术潮流,反映了当时西方文化面貌及对中国的“异托邦”营造。早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与文化传播使中国文化与艺术向西方各国输出,并从外销品的文化输入逐步转型为西方各国对于中国风格的仿制,形成了西方艺术家的“异托邦”“中国风”。米歇尔·福柯在《其他的空间》中将“异托邦”解释为:“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所、有效的场所,它们被书写入社会体制自身内,它们是一种反位所的场所,是被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场所中,真实的位所,所有能在文化内发现的其他真实的位所被同时表征出来,被抗议并且被颠倒……我称之为异托邦。”[1]这种“异托邦”营造的“中国风”从西方仿制的瓷器上经历了由模仿、提取到重塑的跨文化融合过程。瓷器带动的“异托邦”营造的“中国风”在18世纪成为全盛期,洛可可艺术家通过对前期文献与游记插图的提取与再创造形成了新的“异托邦”“中国风”。以华托、布歇与皮勒蒙为主的艺术家通过对中国元素与基于西方社会体系的逻辑重构与虚构,形成了具有特殊中西方文化融合的洛可可“中国风”。这些在西方艺术中自成一体的洛可可“中国风”画作与设计图案同时出现在纺织品上。受16-18世纪西方多文化环境影响,纺织品设计师从节庆与话剧的多文化场景并置中潜移默化影响纺织品设计。由于需要适应工业生产、服装和家具装饰要求,纺织品从设计图册与画作的单一性整体画幅演变为多元素、多文化、多艺术风格的并置形式。丝绸之路文化传播所带来的西方“异托邦”营造的“中国风”是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生产生活方式的虚构解读,在艺术史上的影响是划时代的。西方从引入“中国风”元素用于装饰设计再到对中国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异托邦”营造,是中国艺术文化的一次国际化进程。从经济全球化与现代生活方式角度思考西方“异托邦”营造的“中国风”现象,对现代艺术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16-18世纪西方“中国风”的兴起与传播
“Faconde la Chine”(中国式)字样最早出现在路易十四的财产目录中,此后法语称“中国风”为“Chinois”与“Chinoiserie”。《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其释意为:“指17-18世纪流行于室内、家具、陶瓷、纺织品和园林设计领域的一种西方风格,是欧洲对中国风格的想象性诠释。”[2]西方对于“中国风”的认知与接触最早是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随着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艺术传播,西方逐渐从中国文化的吸收,转化演变为“中国风”的输出,构建起了自我营造的“异托邦”“中国风”。
据史料记载,西汉开辟陆上丝绸之路同期,就已有南海至印度洋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汉书·地理志》中曾记载:“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可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二月余,有黄志国。”[3]16世纪后,西班牙为维系殖民统治开辟了中拉海上丝绸之路。葡萄牙与西班牙通过殖民统治侵占了摩鹿加岛(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并于正德六年攻占了满剌加(马六甲)。继西、葡两国之后,16世纪末荷兰殖民者入侵爪哇[4],这些殖民者通过开辟的大帆船航线连接了亚洲和拉丁美洲。明中叶后,中国蚕丝生产大幅增长,蚕丝业的繁荣带动了整个丝织品的贸易,且商品价格相对于欧洲较为低廉。据记载,自1571年漳州与马尼拉贸易开始后的30年里,约有630艘中国帆船从漳州港驶向马尼拉[5]。中国出口贸易兴起后,中国的瓷器、漆器、家具、纺织品、丝绸等大量艺术品输入欧洲,西方以“想象房间里哪一样精致的东西不是来自中国的”[6]来描述中国外销品的畅销度。这些贸易输入文化及国外游学者对于“中国风”的描述,使得通过丝绸之路输出的艺术风格在欧洲盛行。
国外游学者的人文传播最早为马可波罗于1271-1295年在亚洲的游历。16世纪末期,奥古斯丁教团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萨多在1584年随西班牙使团进京,对中国的建筑、地方官府宅邸等作出了精细的文字描述:“所有这些宅子内部都白得像牛奶,像抛过光的纸。地板上铺的是正方形的石材,宽而光滑;他们的房顶用的是上好的木材,制作细致,漆画精美,看起来像是锦缎,或者呈现金色。”[7]1644年荷兰向清朝派遣出使团,其中的荷兰画家约翰·尼尔霍夫根据访问中国的经历出版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出访大清国记闻》,其中绘制的三百余幅插图为西方了解17世纪的中国提供了直观的图像资料。1721年出版的欧洲第一部描绘中国建筑的著作《建筑简史》中就使用了约翰·尼尔霍夫的插图。而后的1735年,杜赫德所著的《中华帝国地理、历史等详解》中也增加了对于中国设计的描述。法国学者格林在1776年描述中国为:“中华帝国已成为我们时代特别关注、着重研究的课题……在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上,其统治最为开明长久,其道德最为高尚、美好,其法律、政策、艺术、工业同样如此,堪为世界各国的楷模。”[8](P248)欧洲“中国风”设计文化的传播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以中国生产的外销产品所传递的艺术风格与造物思想进行“异托邦”营造;二是对国外游学者或传道士16-18世纪中国游记中的插图及描述性艺术风格进行借鉴与想象。
二、从外销品至“异托邦”营造
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向西方国家输入了大量纺织、瓷器等具有典型中国工艺美术的外销品,外销品所携带的东方文化在西方各个国家掀起了“中国风”潮流,贵族与上流社会均以“中国风”装饰风格的工艺品作为家居或摆件,从而凸显其贵族身份。例如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给我倒杯茶》中写道:“艾兰小姐,为我倒杯茶吧,用精美的中国瓷杯。”[9]而荷兰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的第四任妻子露易丝·德·科利尼在海牙的努儿登堡宫中就有一件专门展示她的285件瓷器的房间[10](P171)。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与海上贸易禁令,外销品供应紧张,使得中国外销品在欧洲更加珍贵。据《明实录》记载:“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11]因禁海令,西方国家开始着手自主研发“中国风”。这种西方自主研发仿制中国外销品的艺术风格、装饰手法与情景画作就产生了“异托邦”营造,这正是西方国家通过外销工艺品来揣测、窥探与西方社会体系截然不同的他国文化、场景与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他们通过对这种有限元素与事实存在的物品、场景、人物的“研究与模仿”,从而形成了属于西方的“异托邦”的“中国风”。这些“中国风”社会样式主要存在于瓷器、画作与纺织品中。
(一)从临摹提取至创新——西方瓷器中的“中国风”
中国外销瓷器历史可追溯至唐、五代时期,至宋元时达到鼎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瓷器外销,欧洲各国开始研究极具东方美学与装饰艺术的外销艺术品。其中以“克拉克瓷器”为主的装饰风格盛行于16-17世纪的欧洲。克拉克名称源自16世纪葡萄牙货船,澳门称之为“加佬瓷”,现泛指16-17世纪销售至欧洲的瓷器[12]。1644年正值中国明末战乱,1656年清代颁布禁海令后随即颁布迁界令,导致中国外销瓷器从货源处被阻断。欧洲开始把对中国外销品的需求转移至日本与欧洲各国仿制的东方瓷器。路易十四时期皇家制瓷中心“塞芙尔”常使用人物、背景及各种中国元素进行瓷器设计。荷兰画家威廉·卡尔夫、弗朗索瓦·德伯特和朱理安·凡·斯垂克的油画中也常出现中国瓷器,瓷器中的图案也常为情景式“中国风”图案。这种由描绘中国场景与人物或东方风格花卉的瓷器主要由16-18世纪的意大利美第奇瓷器工作室、德国梅森制造厂、弗兰肯塔尔瓷器厂、圣克卢厂和法国塞弗里斯制造厂的制作品为主,主要为人物场景造型类的瓷器摆件与器皿类瓷器。
1.以青花形式为表象的欧洲风格
随着16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以瓷器为主的外销品贸易航线逐步在欧洲传播。以青花形式为主的瓷器风格广受欧洲贵族的追捧,并形成了“中国青花风”潮流。工匠开始用不透明的白色锡釉来覆盖器物的所有表面,并在锡釉和蓝色纹饰之上覆盖一层透明釉,这就使得蓝色钴料更加光滑,陶器表面有一定的层次和光滑度,从而获得一种模仿青花瓷表面更好的效果[13]。现存的欧洲本土制作的中国青花风格的瓷器以美第奇瓷器较为多见。
美第奇瓷器工厂建于15世纪60年代末期,为弗朗西斯科·德美第奇所建立,最初的目的就是模仿中国青花瓷[14](P694)。随着中国进口瓷器被欧洲王室贵族收藏家追捧,美第奇工厂成为第一个尝试在欧洲生产这种高级瓷器的工厂。该工厂经过大约十年的实验,能够制造出软瓷器。虽然所谓的美第奇瓷器缺少中国制作的硬浆瓷的成分,但美第奇陶艺家能够制作出带有钴装饰的精美白色陶瓷体,这代表了当时欧洲制瓷业的进步与发展。从现存的美第奇瓷器中可看出该工厂的制陶师们一直在尝试新的装饰形式与风格类型[15](P235)。从收集的样本可看出大部分瓷器被涂成了钴蓝色,部分纹样中存在蜿蜒藤蔓与风格化的花卉,部分瓷器纹样中出现用钴蓝色绘制的穿着欧洲古典服饰的人物形象。这些瓷器的整体色彩灵感来自中国青花瓷的钴蓝色装饰[14](P694)。瓷器图案元素中的卷轴、开花的树枝也源自中国瓷器,类似的带花的叶子藤蔓是宣德(1426-1435)和正德(1506-1521)时期青花瓷器上最常见的图案之一[16](P122)。
路易十四时期,由于外销品的传播,法国人开始推崇中国青花风格,这一时期的“软青花瓷”图案设计与中国的外销品瓷器如出一辙,属于初步的“仿制”阶段。随着“仿制”与制瓷技术的逐步成熟,法国人不再满足于模仿与山寨,开始在青花风格的基础上进行“软青花瓷”的本土化与创新。例如,陶瓷工厂的匠人开始将金银器的装饰手法应用于法国本土瓷器上,即将法国特有的图案、动物、人物融入中国青花风格的瓷器上。这种创新形式的软瓷器被当时的市场所接受和追捧,与中国青花瓷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后续这种以青花形式为表象的欧洲风格瓷器延续至今。
中国青花瓷器风格启发了美第奇与圣克卢工厂的画师,其中部分瓷器中的欧洲人物形象表明,他们对于瓷器的预期目标不是对特定装饰方案的一味复制,而是研发创新型装饰符号,其设计范式是允许基于不同来源的图案混合,即以西方艺术为基础和内涵,以中国青花形式为表象所形成的创新形式。福柯在《词与物》中用“厄斯泰纳的例子”将并置属性解释为:“所列举项目的共同场所和空间是存在的,他们有一个确保他们可靠性和统一性发生的真实空间和基础。”中国外销品在国外场景的出现为后期的并置创新提供了真实空间与基础,这种青花形式的欧洲风格也符合福柯所提出的“异托邦”概念中的并置性。
2.简化中国元素与创新再造
1710年德国德累斯顿设立皇家瓷窑,迁至梅森地区后生产出了许多“中国风”瓷器向全欧洲销售,部分瓷器上常使用中国外销品瓷器上的元素与装饰手法。18世纪初,德国梅森瓷器厂开始对于“中国风”瓷器的仿制与创新[17]。从初期对于“中国风”瓷器的装饰风格的直接临摹,到中期对“中国风”装饰元素的拆分重组,再到后期使用中国元素的直接创新,梅森瓷器重新诠释出了属于欧洲的“中国风”符号。
在现存于18世纪的瓷器样本中,这种对于中国元素的简化与创新再造以人物场景居多。梅森瓷器厂所生产的瓷器中的人物场景大部分以这种西方绘画风格的中国元素装饰手法为主,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以金色与红棕瓷器画色系为主;二是在整体画面上体现为平面化场景;三是在装饰形式上以“异托邦”形式的中国元素和形象为主,而非真实中国场景画像生产。
梅森瓷器中的“中国风”场景色彩均以红棕色系为主,金色为点缀或者常出现在缘饰处。这种早期红绘式的单色画面与同时期瓷器装饰画颜料的获得局限性相关[18],而对于梅森瓷器出现的“异托邦”形式的“中国风”,首先与1720年约翰·格利高里·赫洛尔特的倡导有关。其时,赫洛尔特在塞缪尔·史托茨的邀请下在梅森瓷器工厂负责装饰工作。其次是梅森瓷器厂的资助者奥古斯特二世对于“中国风”的追捧[19]。例如大都会博物馆现存的1730年梅森瓷器厂所生产的餐盘,其中人物场景使用中国人物的形象与花卉瓷瓶描述了三个不同的东方虚拟场景,其中的主要场景中的人物身穿清朝风格服饰,人物刻画风格属于欧洲写实风格。虽以“中国风”为主要元素,但五官与神态、描绘的造型属于外在的单一形式,延续了欧洲艺术中文艺复兴绘画风格的“真”,与中国绘画中的“写神”存在较大差异。该餐盘的边缘使用中国航海上的帆船场景,西方装饰元素为缘饰进行结合与创新,区间的空隙中插入了简化的花卉盆景。瓷盘的着色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瓷器较为单一,多使用红色、褐色与少量绿色为主要彩绘色彩,边缘处使用欧洲当时成熟的描金工艺作为点缀,使瓷盘整体上呈现出奢华感。
由于当时欧洲对于“中国风”的追捧,梅森瓷器厂的工匠并未亲历中国,对于中国人物的塑造与绘画多是根据欧洲当时有关的文字描述与传入欧洲的中国人物形象画,中国人物造型大多数属于工匠们根据文字记载的艺术再创造[20]。这些场景中的器物、花鸟、盆景、人物服饰与帆船都使用了典型的中国元素,但是相关的颜色、装饰、人物五官仍然是欧洲艺术风格,这是欧化方式对中国场景的再展现,也体现了18世纪欧洲基于现实中国元素的场景“异托邦”营造。梅森瓷器厂对于中国元素的简化与创造体现了跨文化接受从直接形式转为间接形式、由被动接受转为自主构建的过程。梅森瓷器中的东方场景表面是匠人及艺术家对于中国的理解,实际上是呈现了当时欧洲社会人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及精神状态,只不过借用了中国元素和场景来表达精神层面的革新追求以及借异体文化来刺激自身文化的变迁。
3.西方场景的中国形象营造
17世纪上半叶开始,欧洲王室成员和贵族喜爱在家中设置中国瓷器陈列室或中国瓷器家居,以丰富的装饰艺术手法来表达东方艺术。德化白瓷在这期间被欧洲工厂重新绘制了金属或者彩绘装饰,以达到富丽堂皇的效果。受这种趋势的影响,部分工厂开始生产这种瓷器雕塑人物,例如圣克卢工厂、梅森瓷器厂与切尔西工厂。这种西方场景下的中国形象营造也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异托邦”式的“中国风”手法。根据现存像本分析,此类手法出现在各式瓷器雕塑上,多为单独东方人物的雕塑描绘,雕塑人物集中出现在1730-1760年间。
在样本中较为典型的为圣克卢工厂生产的雕塑人物,该工厂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实用器皿上,但也制造了花瓶与雕塑,尤其是在工厂最初的几十年。圣克卢工厂的大部分生产规模都很小,鼻烟壶、刀柄、百花香、杯子和碟子等物品似乎占工厂产量的相当大比例。瓷雕考验了工厂能力的技术和艺术极限,在工厂的前七八年历史中,制作的雕塑作品相对较少。这组人物瓷器雕塑对中国人物形象的刻画带有明显的西方风格。雕塑的人物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力与动感,且在其他的人物雕塑中属于复杂造型。该组瓷器雕塑的男性形象穿着的长袍与宽边尖顶高帽是欧洲人对于东方男性人物的标志性帽子,而且作为中国形象因突出的胡须得到了加强。女性形象所戴的头饰,不是通常与来自这些国家的女性联系在一起的头盔,而是唤起了对希腊女神雅典娜的描绘中头盔类型的简化版本。她的“东方”特质似乎完全来自她的图案长袍,并与更明显的中国男性搭配。两位人物所穿的长袍并非直接来自中国或日本模特,而是在其图案和调色板中唤起了东方设计词汇,这与日本出口瓷器上的工艺相似[21]。
克勒尔·勒·科尔贝尔认为,18 世纪早期在中国福建省德化生产的白瓷人物是圣克卢生产的第一批人物的灵感来源[22]。这些早期的圣克卢雕塑出现在18世纪的前三十年,描绘的是中国人物,其特点是造型简单,细节极少,没有任何彩绘装饰。这些人物描绘的是穿着中国风格服装的欧洲演员,而这些人物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巴黎流行以中国为主题的戏剧活动的缘故。这两个类别的大多数圣克劳雕像常被安装在镀金青铜中,有时用作时钟或烛台的组件,或简单配有镀金青铜底座,以提高其作为装饰物的华贵地位。
(二)从元素融合至虚构——西方画作中的洛可可“中国风”
继工艺美术品后,西方绘画中所存在的“异托邦”现象主要存在于洛可可艺术风格中,这也是16-17世纪欧洲一直痴迷于由旅行家、贸易品、欧洲国家所掠夺来的战利品中所展现出的“中国风”。这些所谓“中国风”设计分别体现出巴洛克与洛可可艺术的特点。欧洲“中国风”的时尚流行在18世纪中叶达到顶峰,其中以华托、弗朗索瓦·布歇以及皮勒蒙作品为主。
华托是欧洲中国风绘画的开拓者之一,他赋予了欧洲画作从宏大场景或主题向小场景或私人场景的画风转变。华托的画作多是身着中国服饰与手持中国器物的欧洲人,对于“中国风”的描绘大部分展现出的都是对中国的向往与憧憬。华托“中国风”建构的主要依据是赴华传教士的素描作品以及文献插图,但形式特点是在“中国风”画作上留有欧式印记。这不单纯是用欧式画法展现中国主题,而是带有时代审美理想的痕迹。画面空间的三维构图及人和物的三维造型清楚地映现出欧式画法,画面周围的装饰手法依旧延续典型的洛可可风格装饰纹样[23]。华托作为早期“中国风”的艺术家,其艺术手法还停留在较为生硬的探索阶段,将西方人所看到的中国元素直接照搬进西方场景中,并未将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更好地结合。
弗朗索瓦·布歇较华托更进一步的是将东方服饰和装饰与18世纪的洛可可风格融合在画作中。相比华托较为生硬的照搬,布歇塑造的中国人物更加贴合真实,且能够和谐地融合洛可可风格,这要归功于其本人对于中国的特别关注。巴黎艺术品经销商埃尔·雷米在1771年出版的销售目录中记录了布歇丰富的中国收藏品,包括71幅绘画、93件漆器、39件人物雕塑、20件铜器及16件银器,更多的是陶瓷制品,且包含各式各样的中国日常生活器具,如茶叶罐、灯笼、扇子、伞、中式乐器与中式服饰品等,这也解释了布歇对于中国形象的想象大部分局限在他对这些中国藏品的理解上[24]。布歇在1742年的《中国皇帝用膳》画作中选取了从中国皇帝至底层市民三个不同阶层角色的日常生活场景作为主题,构建起了西方人对于东方封建社会的立体理想式的政治图景,描绘了一种既保留了中国封建阶级的传统形式,同时描绘了洛可可中的浪漫主义,与法国当时繁文缛节的宫廷条规截然相反。布歇的创作手法继承了华托对中国图式与器物的真实性要素,同时有针对性地选取主题与元素进行创作,最后重新赋予整体画面洛可可氛围与意境。这种氛围和意境非原图所有,而是其形式和精神在挪用中形成了所在文化语境中的一种重生[25]。
皮勒蒙被普遍认为是洛可可“中国风”领域华托和布歇的继承人。他在后期成为该流派的主要代表,是该时代装饰艺术中产出较多的艺术家。在其艺术生涯中,他的中国风格作品出版了53部,其中包括358幅版画。例如皮勒蒙所作的《中国装饰新书》在欧洲广为流传。皮勒蒙在1778年被玛丽·安托瓦内特提名为宫廷画家,他在与英国制造商工厂的接触中发现,英国与法国存在着对“中国风”的追捧潮流,中国的外销品价格昂贵且无法满足民众需求,随即开始对中国风格进行仿制[26]。但皮勒蒙的仿制是基于洛可可艺术基础上的“中国风”西方艺术再创作,所有画作中的中国元素均源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文献图像记载以及中国外销品,他本人从未到达过中国。
皮勒蒙的作品中充满着洛可可的浪漫主义与想象力,如1790年画作中展现出的排列整齐的花朵或豆荚形成奇异的图案,完全没有明显的韵律或理由,花朵和叶子组成的形状完全无视物理学规则与经验,中国人从栖息的梯子上或宝塔上钓鱼,梯子从最脆弱的花瓣上升起。威廉·埃文斯认为皮勒蒙的作品“每件事都是经过精心安排,是经过设计的”[27](P312)。
皮勒蒙认为这种异国情调的中国风格主题代表了高度个人化的想象力。让·雅各布称皮勒蒙是“法国洛可可中式风格的诙谐元素”,并详细阐述为:“他的中式风格夸大了洛可可与东方风格的纤细与脆弱,居住在其中的人类是充满幻想的生物。”[28]相较于布歇的基于真实性中国形象的手法,皮勒蒙艺术手法更加夸张与异想。他的画作中甚至不再基于现实场景与现实世界的定律,而是仅提取了真实的中国形象和元素,重新构建了带有中国元素的非常规建筑与花卉。皮勒蒙将洛可可艺术风格中带有的荒诞感与个人想象力发挥至极致,即通过现实元素与个人内心憧憬重新构建起“异托邦”“中国风”洛可可图像。
在洛可可统治时期,中国艺术品本质上的装饰性是美术和应用艺术的理想选择。由于中国在同时期的海禁、战争等原因很难接纳外国使团,大部分的艺术家所根据、参照的资料仅限于约翰·尼奥霍夫的游记插图和外销品实物。故西方艺术家对中国艺术的解释符合中国社会阶级分层的现实图案与西方文化审美,逐渐成为一个通过片段资料所描述的独特镜像,像是一个从实际世界中解脱出来的充满审美愉悦的伪东方场景的欢乐世界。这其中充满了穿着考究、与现实符合的小人物,每个人物身上有各式各样的追求。这也是福柯所强调的:这些场所是外在于所有的场所的,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局部化的。因为这些场所全然不同于他们所反映和所言及的所有位所。
(三)场景与元素的杂糅并置——西方纺织品中的“中国风”
纺织品贸易伴随着丝绸之路将中国工艺美术与各项技术传播至西方各个国家。公元3至7世纪,欧洲纺织品纹样受到东方很大影响,其中包括中国、阿拉伯、印度提花或印花织物。10世纪以后,意大利开始纺织中国丝绸。13世纪欧洲开始流行“鞑靼丝绸”的中国丝织物及仿制品。14世纪后意大利出现“自由风格”纺织品艺术,其常取材于中国神话中的龙、凤和麒麟等非自然物[29]。16世纪后,西班牙为维系殖民统治,开辟了中拉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开辟了连接亚洲和拉美大陆的大帆船贸易航线。贸易商品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当时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华的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进口商品的成本很高,因此仿制商品成为满足广大公众需求的“合理解决方案”。在这种追捧东方文化的时代潮流下,约翰·尼奥霍夫的《联合省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大鞑靼王朝、阿姆斯特丹1668和伦敦1669的插画》成为18世纪艺术家、画师对于中国文化初步认识的视觉模型来源[30],而通过这本文献资料所描绘出的“异托邦”镜像在更多情境下是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文化的混合体[8],在这种情境下所生产出的纺织品纹样也较多为这种文化混合体。
在18世纪前,纺织品工艺常采用提花面料用作连衣裙或家居面料,而18世纪后,随着面料印花技术的革新,“中国风”常出现在印花面料上。1714年丝绸和印花面料的进口被禁止,使得东方纺织品无法运输过去,从而倒逼欧洲本土丝绸行业的生产。纺织品类目中的中国风格常与其他元素与花卉进行混合排列,装饰性的镶嵌画、地毯、壁纸、服饰上均可看到17-18世纪的“中国风”元素。1752年前后,弗朗西斯·尼克松在爱尔兰德鲁姆孔德拉印刷厂的在纺织品上引入铜版印刷技术,解决了传统印刷木块无法达到的图案精致度,改革了传统印花纺织品的外观,让纺织品大图案可以使用单色[31]。随后西方各国都出现了新的印刷设备,克里斯托弗·菲利普·奥伯坎普于1760年在巴黎茹伊昂若萨区附近建立了一家纺织厂和印刷厂,旨在生产符合宫廷要求的织物。奥伯坎普采用了这种铜版印刷技术,且任命法国著名洛可可艺术家让·巴蒂斯特·休特为首席设计师[32](P119-163)。这使得“中国风”画作开始频繁出现在纺织品上,且以元素混合这种适应于工业生产的排布方式为主要表现形式。
纺织品类目中的中国风格常与其他元素与花卉进行混合排列,例如皮勒蒙在1770年的花型手稿场景中的亭台轩榭、人物服饰均为中式,花卉植物或一些装饰纹样则采用印度或欧洲风格,这种以著名艺术家设计稿为蓝本的混合模式组成了整幅纺织品花型,这种混合风格共同构成“中国风”。“中国风”的形成除了受文献与游记插图的影响外,也与流行于意大利的节庆表演和戏剧表演有关。18世纪初期意大利的节庆等盛大场面常出现中国表演人员,例如1716年的奥古斯特大帝访问威尼斯时迎接队伍是一艘插满阳伞的中式舢板,上面满载中国舞蹈演员与乐师。在图中经常表现出以佛的胜利或中国皇帝出巡为主题盛装游行。1769年在克罗尔诺为庆祝帕玛公爵的婚礼举办的盛典上,日本、爪哇与中国的马戏团纷至沓来。以歌剧著称的威尼斯在1753年也流行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与拥有鞑靼式场景的话剧《图兰朵》[33]。这些同时期在不同国家流行元素的混杂也影响了艺术家们的创作,导致在面料上常出现不同国家不同场景的杂糅混合。此外,以“中国风”建筑为主体图案的原因也是18世纪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建筑的狂热。1755年《行家》中曾记载:“中式风格在占据着花园、房屋和家居后,即将入侵我们的教堂,不妨想象一下,一座中式墓碑,上面雕刻着游龙、吊钟、宝塔和汉字,会是何等的优雅别致。”[8]例如收藏于里昂和巴黎西那列庄园中的1770年皮勒蒙所绘制的纺织品花型手稿和生产出的纺织品,这些样本的共同特点除了适应工业化生产的构图以外,都是以真实的中国建筑与人物凸显“中国风”特点,杂糅元素常以欧式花卉玫瑰花、向日葵、康乃馨或欧式藤蔓等装饰纹样为主,其他元素则常出现东南亚特点的棕榈树或带有希腊特点的装饰性陶罐纹样。
三、“异托邦”视阈下的西方“中国风”
米歇尔·福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的《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中首次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福柯对博尔赫斯作品中引用中国对于动物品种的分类——属于皇帝的、传说中的、自由走动的、驯服的数不清的、狂躁不安的等等[34],认为这种分类方式突破了西方语法所能解释的范畴,这促使他开始思考秩序与文化构建的问题。他认为“异托邦”创造出的虚拟空间虽然是不真实的,却能够准确地将真实的空间反映出来,且通过真实空间所缔造出来的空间与我们本身存在的周围空间一样有秩序,像是对原有空间的复制补充。“异托邦”强调的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但是场景或者事件是虚构甚至是内心的憧憬映射。“异托邦”的创造是在世界的真实存在的空间文化中进行的,且是虚拟不连续的,这种形式的存在也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共存现象。西方“中国风”现象在“异托邦”概念下将很多没有联系的空间和场地合并成一个真实的场景,这种“异托邦”营造是基于受碎片化中国元素影响的西方艺术家与工匠通过其对西方社会的现实与对东方社会的憧憬所虚拟出来的场景化衍生品。这种“异托邦”营造分别是西方对于东方艺术的社会补偿营造和西方对于东方艺术的并置营造。
(一)西方“中国风”的社会补偿营造
在同一社会体系或不同社会体系中,不同时代所处的每一个相对不变的社会就是一个“异托邦”,因为从另一个社会体系的角度看,这个社会所发生作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从“中国风”角度来讲,西方角度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异托邦”。每个“异托邦”都针对某个社会内部文化的“同时性”,指从某一历史时期视阈下语言现象具有的历时性或共时性的特点。福柯在讲“异托邦”属性时用“镜子”比喻:“镜子使得我们在看到我们自己时,意识到我所占据空间的真实性。”[35]镜子连接了现实与虚幻,西方对于东方艺术的畅想也同样使得“中国风”艺术具有连接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功能。这种基于现实的虚幻场景使得艺术家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于内心精神的诉求或憧憬,是对社会现实空间的补偿。
对福柯而言,中国就是“异托邦”,因为西方“中国风”是以特殊的艺术手法反映出西方或者欧洲哲学运作的逻辑,并不是完全虚拟的,且中国是一个完全真实的空间。例如布歇在其1742年《中国狩猎》画作中“中国形象”符号元素实现的文化转型,就提取了中国文化中的欢愉特征,表达了欧洲人对于淡泊宁静的中国生活的向往,是欧洲人理想中的景致。
(二)西方“中国风”的时空并置营造
福柯对“异托邦”第三原理的解释是:以为有能力在一个真实的场所并置几个无法比较的位所,每一个单独的真实位置或场所并立安排几个似乎并不相容的空间或场所,这种场景在西方的东方艺术中常出现在纺织品和陶瓷图案上。福柯在《激进的美学锋芒》中举例:戏剧舞台上同时存在或连续表演不同时空的场景,这些场景是相互隔离或相互外在的[35]。这对应了在18世纪的意大利狂欢节的场景与追求,通过利用每年的狂欢节来满足他们对东方华丽服饰的追捧。在18世纪早期的狂欢节舞台上,舞台演员通过圆筒尖顶帽与色彩艳丽的长袍加上一双脚尖上翘的鞋子来描绘中国形象。同时期出现的还有日本形象的马戏团等表演场景。这种现实中的多文化并置也催生了艺术家们对于艺术品的多元素混合的追求,把多个国家文化同时出现在同一块面料上或同一幅画作中。
除了在空间上的并置营造,在时间上也出现了并置营造,福柯称为“异托时”。与对“异托邦”的理解相对应,这个词应该理解为在表面上同样真实的时间顺序中,还存在着至少两个“相异的时间或历史”。福柯指出,与时间连接的“异托邦”还有其他的形式,比如与传统节日连接的盛会。各个民族的节日总是与某种庆典联系在一起,这些庆典发生的场所往往是一个闹哄哄的嘈杂混乱的地方,是专门供人们欢乐的场所,这情形每年发生一次或几次,呈现多样的文化场景——陈列、展览、卖弄、标榜各种不同的商品,还有摔跤的、变戏法的、说书的。人们发明一种新的时间“异托邦”——通常是一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原始村落,生活在当代都市的游客与当地土著人混杂一起,时间的暂时性与永久性混杂在一起,过节一样的日子与日常生活混杂在一起,就像是把时间重叠起来,每一道褶皱都是重新发现一种时间。换句话说,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并不只是存在一种时间。这种不同空间的并置、不同时间的并置常出现在西方“中国风”中,福柯利用“波斯地毯”与“花园”来描述这种并置属性[1]。例如在18世纪末期的纺织品花型中,东南亚的代表元素棕榈树与希腊神话风格元素和中国形象元素会同时出现在整幅画面中。这种跨文化、跨时空的甚至异想的并置都是源自于西方对于中国的“异托邦”营造。
(三)“异托邦”营造的“中国风”的形成,彰显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16-18世纪欧洲“中国风”的出现与形成,展现了中国符号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输出,在艺术史、哲学史上形成了特殊的“异托邦”现象。“异托邦”营造的“中国风”现象为国家形象建构和文化输出提供了历史借鉴。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的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36]“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37]西方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异托邦”营造,彰显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也反映出中华文明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活力以及对世界的引力。16-18世纪西方“中国风”的研究为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找到了又一有力的历史注脚。
西方“中国风”是在丝绸之路“东风西渐”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一个重要历史文化现象,是历史上东西文化交融、文明互鉴中产生的重要文化成果。“异托邦”营造的“中国风”现象再一次证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当前,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明冲突”,但这并不能否定文明对话是全球文明发展的主要趋势。世界文明是多元的,文明之间的对话历来是人类文明创造和谐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机制,这种机制也完全可以从世界文明发展中汲取营养。我们只有坚定文化自觉,把握历史主动,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好中国道路,贡献出中国智慧。
此外,从建构现代艺术设计学科发展来讲,西方“异托邦”营造的“中国风”在艺术交流史中所蕴藏的价值必然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一个时代的风格是时代文化的象征与社会的缩影,新时代艺术设计、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播都是新时代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组成,也是当下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直接体现。激活历史是当代人的责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用当代设计学的丰富内涵讲给西方听,而且要用活化的历史语言讲给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向世界展现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