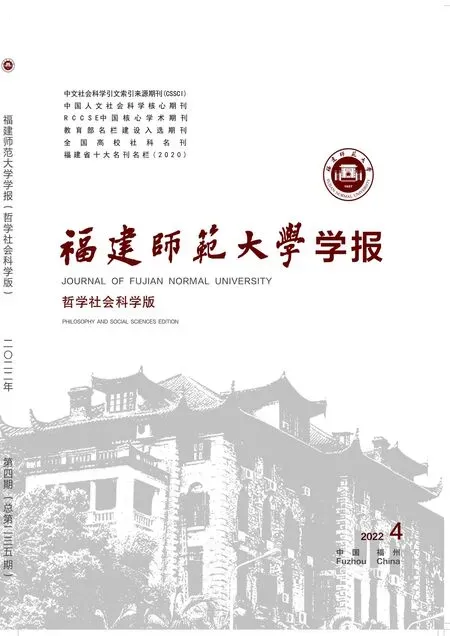由古学、博学、考据学走向经世致用实学
——王世贞与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转向
许在元, 许建平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3)
关于明清学术思潮的转型,学界一般认为明代中后期是王阳明心学的时代,至清初则转为经世致用的实学。事实上思想的发展既非单线的,也非平面的,而是多线多层面的交织发展。“世人但知清代古学昌明是明儒空腹高心的反动,而不知晚明学者已经为清儒做了些准备工作。”(1)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单是这个准备工作,就涉及文学、史学、经学、宗教学等多学科和古学、博学、考据学、致用之实学的多层内涵和发展线索。它们究竟是怎样相互交织而演变过来的,是一个不小的历史课题。自20世纪以来,人们分别从各自学科进行微观、宏观研究,取得不小的实绩。然往往很难摆脱学科限制,言史者不及诗文,讲哲学的不及音韵,言考证者无关思想,各言所知而偏于一隅,很难综合。要突破学科界线局囿,有效方法当属由点切入,以小见大而知全。“点”指时代潮流转换期的集合型、枢纽式人物。集合型指一人兼备众学,集多学科知识于一身,观一人而知多学科发展面貌。枢纽式指处于历史转型的当口,且为一代学术转型的推动者。如陈献章、王阳明、王世贞、方以智、顾炎武等。对这类人物认识的偏差、失真,会直接影响其研究成果的真实性。譬如嘉、万时期文人眼中主盟文坛的王世贞,与《列朝诗集》《明史文苑传》中的王世贞,悬殊天壤,判若两人,真伪掺杂。再加上王氏著述千百卷,能通读其书者少,而人云亦云者多,故而对其研究需更全面而真实,(2)有的学术著作,因对王世贞著述了解不够全面,撰写时或只提其名较少涉及内容,或所言笼统、模糊,如有的学术史、思想史;或仅论及王世贞常见单行本内容,如有的文学批评史;有的提及王世贞只袭前人旧说,观点片面乃至错误,如有的文学史等。总之,难以展现全面而真实的王世贞,也难以将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转型进一步说清楚,这正是笔者写此文的原因。方可窥见他所展示的历史全貌。对于这样一位集合型、枢纽式人物,若以其为切入点作多视角多学科的发掘分析,或许会带来一些曾为遮蔽的新发现和新认知。
一、王世贞与明代古学、博学思潮
(一)由古学之盛到博学之兴
明代博学始于中期的文学复古运动。嵇文甫说:“大概明朝中叶以后,学者渐渐厌弃烂熟的宋人格套,争出手眼,自标新异。于是乎一方面表现为心学运动,另一方面表现为古学运动。”(3)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56页。朱希祖言:“当李梦阳、何景明之辈倡言复古也, 规模秦汉, 使学者无读唐以后书;非是则诋为宋学。李攀龙、王世贞辈继之, 其风弥盛。然欲作秦汉之文, 必先读古书, 欲读古书, 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学兴焉。”(4)朱希祖:《清代通史序》,见萧一山:《清代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页。前后七子就是在复古中走向博览群书的,他们大多为青年进士,才殊纵横,又以复古相号召,如李梦阳、李攀龙等,而尤以王世贞最为显赫。
王世贞是明代嘉靖后期至万历初期(5)指王世贞中进士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至他去世的万历十八年(1590)的43年,此前为杨慎,此后为焦竑、钱谦益等。博学者的代表。他的博学实绩表现有四。其一,富藏、广览、强记、博识,为一时之冠。王世贞藏书数万卷,胡应麟言:“王长公小酉馆在弇州园凉风堂后,藏书凡三万卷。二典不与,购藏经阁储焉。尔雅楼藏宋庋书,皆绝精。”(6)(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明万历刻本,第39页。他自言:“余生平所购《周易》《礼经》《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二千卷,皆宋本精绝。”(7)(明)王世贞:《又前后汉书后》,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九,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5974页。过目成诵,通贯经、史、子、两藏,博综典籍,谙习掌故,在诸子中难有比肩者。《四库全书总目》云:“博宗典籍、谙习掌故,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8)(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集部,清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刻本,第2945页。王锡爵云:“以异才博学,横绝一世……海内之豪俊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学,直千古可废也。”(9)⑩ (明)王锡爵:《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世贞神道碑》,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四十五刑部二,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枟曼山馆刻本,第7044、7055页。“盖集十代之成,而总四子萃者,非公其谁!”(10)(明)焦竑:《弇州山人续稿选叙》,见(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选》,明刻本。
其二,著述丰博,为古人之最。王锡爵言:“古今著述之富,公为第一。”(11)⑩ (明)王锡爵:《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世贞神道碑》,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四十五刑部二,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枟曼山馆刻本,第7044、7055页。《四库全书总目》曰:“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12)《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七卷》,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清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刻本,第13494-13495页。著述种类183种,2672卷,除去内容重复、馆员误记和讬名之作外,尚有1000多卷。王世贞是明代著名的批评家,批评领域涵盖文学、史学、经学、子学、道学、佛学、文字、书画、古玩、民俗学等。(13)其批评文字,不仅见于《读书后》《札记》《艺苑卮言》《弇山堂别集》《凤洲笔苑》《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王氏书苑》《王氏画苑》《古今法书苑》《宛委余编》《觚不觚录》等,还见于数以千计的序跋、论说文和书牍中(仅书牍就1148篇)。
其三,文学创作以体全、量大、学博而雄居天下。诗、文、词、赋、曲、稗、说、评八种文体,无不创作,且诗文等文体内的诸体式也多染笔,诗体12种,7055首(14)这7055首,仅指《四部稿》《续稿》二书而言,《凤洲笔记》《续稿附》和佚诗不包含在内。。文体44种,10000余篇,以全而多雄居天下(15)从体式全和数量大而言,此前少有比肩者。今仅举诗、文两大类以说明之:诗体有拟古乐府451首,五言古体902首,七言古体407首,五言律诗1253首,五言排律156首,七言律诗1678首,七言排律24首,五言绝句628首,六言绝句100首,七言绝句1391首,四言古诗11首,杂体43首。共计7055首。文体包括:序、书序、寿序、表序、记,纪行、志、传、墓志铭、墓表、神道碑、墓碑、墓志铭、碑、行状、述、颂赞、像赞、铭、诔、哀辞、祭文、奏疏、史论、论、辨、说、杂记、议、读书后、杂著、策、书牍、杂文、墨迹跋、碑刻跋、墨刻跋、画跋、佛经画跋、杂文跋、札记、短长、表、考,总共约10000多篇(有些无法计量如《札记》、诸表、戏曲、小说、《艺苑卮言》等,以可计量卷数的每卷平均篇数计,总数在11300多篇)。类之全,量之大,古今能与之比肩者不多。王世懋云:“诗家集大成,千古惟子美,今则吾兄王司马云,上下千载,纵横万里,其斯一人而已。” ((明)王世懋:《沧州三会记》,见(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七十六,明万历刻本,第3466页)王锡爵:“泱泱乎球钟畅、鸟兽舞、宫商鸣、草木动,譬之观海,惟是汪洋浩渺,天水相含之为巨观。”((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一《弇州山人续稿序》,明万历刻本)。可视为此前文学体式创作的集大成者。且有些文体式样、文体观对明末清初多有影响,如传记体的奇事化,书牍的小品化(16)陈晨在分析《尺牍清裁》所选明人的部分作品时发现,王世贞对以书牍表现性灵自由与生活情趣化的浓厚兴趣:“考察王世贞对当代书牍创作的把握……往往可见出其与时代‘言情,言真,张扬个性,表现欲望与性灵’等文学思潮间的积极互动。”参见陈晨:《王世贞与明代书牍总集》,《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14页。,诗歌叙事的《世说》笔法等。胡应麟评“以一人奄古今制作而有之”(17)(明)胡应麟:《弇州先生四部稿序》,见《少室山房笔丛》卷八十一序九首,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485页。。《明书》云:“明之文章至李何而古,至攀龙、道昆而精,至世贞而大。”(18)(清)傅维麟:《明书》卷一百四十七文学传三,光绪五至十八年定州王氏钱德堂刻三十二年汇印《畿辅丛书》本,第6611页。
其四,前后七子派文论的集大成者。人们通常说诗歌理论至清代而集大成,而清代的诗学诸说细究其来源,多来自明代,且未超越明人诗学的范围。王世贞的诗学吸收前期特别是承严羽一脉诗学观、集七子派之大成且有新变:以“捃拾宜博”补“师匠宜高”之狭;复古而求新,对模拟的扬弃、超越;以“性灵”为文学之源的性灵观;意由情生、法随意转、情法合一的情法观; 融性灵、诗法、境界为一体、强调“天会”“至境”“神韵”的格调说。自古以来诗歌创作的几大关系问题:主体与诗(性灵)、客体与主体(神韵)、传统与诗(格调、肌理)皆包容于其诗论的体系之中,形成了以情欲为源,抒情写意为归,以法度范式为体,以学养为粮,以才气思为翼、格调韵境为品,以自然为美的文学思想体系。中国诗学体系至王世贞已大体完成。(19)许建平、许在元:《王世贞在明末清初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价值与地位重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79页。
王世贞对古今诗文的鉴赏、批评,常为明清两代学者所引用,如钱谦益《列朝诗集》、王士禛《带经堂集》等。清人毛先舒言:“古人善论文章者曹丕、陆机、钟嵘、刘勰……王世贞、胡应麟,此诸家最著,中间刘勰、余、王(王世贞),持论尤精确可遵,余子不无得失。”(20)(清)毛先舒:《诗辩坻》,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1页。世贞广览博识、著述之富、创作体全量大以及七子派文论之集大成,皆体现出其博学的实绩。
王世贞身为嘉万时期“异才博学、横绝一时”的文坛领袖,(21)王世贞自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不久与李攀龙结为诗社,成为文坛盟主,时称李王。隆庆四年,李攀龙去世后,独掌文坛二十年,前后主盟文坛四十年,成为明代文坛影响最大的领袖之一。以倡古学与博学搅动一个时代风气。《明史·文苑传》云:“自古文人享隆名,主风雅,领袖人伦,未有若世贞之盛者也。”(22)(清)王鸿绪:《明史稿》卷二百六十八《文苑传》,清雍正元年敬慎堂刻本,第10911页。王锡爵拟之以王阳明:“一时士人风尚,大类王伯安讲学之际,而公之变俗有加焉。”(23)(明)王锡爵:《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世贞神道碑》,见(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四十五刑部二,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枟曼山馆刻本,第7044页。其后,受王世贞影响的一批博学名家、文坛领袖蜂起。诸如王世贞的忘年交、列入“末五子”的胡应麟;作《国朝献征录》大量收入王世贞传记、墓碑、行状的焦竑;受王世贞《奇事述》《异典述》《盛事述》特别是《觚不觚录》直接影响而创作《万历野获编》的沈德符;少年即熟读王世贞《四部稿》《续稿》,且能“谙数行墨”(24)(清)钱谦益说:“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闇记其行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十七《题徐季白诗卷后》,《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第1843页)又言:“仆少壮失学,熟烂空同、弇山之书。”((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九,下册第1359页)的钱谦益;与王世贞世家通好、视《艺苑卮言》为“品隲极当”(25)(清)王士禛《渔洋诗话》:“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而不喜皇甫汸《解颐新话》、谢榛《诗说》,又云:弇州《艺苑卮言》品隲极当。”见《王士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4757页。而引用多达101次(26)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建国依据《中国基本古籍库》文献,统计出这101次引用分别是:《池北偶谈》7次;《带经堂集》17次;《分甘余话》4次 ;《感旧集》8次;《古夫于亭杂录》4次;《花草蒙拾》2次 ;《居易录》14次;《香祖笔记》12次;《渔洋诗话》2次,《带经堂诗话》31次。的清初王渔洋等。他们不断创造文史诸领域的佳绩,遂推进明代至清初博学之风的勃兴。
(二)明清博学走向:博而杂而奇至博而专而精
清人的博学总体不及明人,因明人局束少,世运正盛,思想浪漫,时学压抑久,才高博学者往往令士子引领仰观,故博学成风。然开博学风气者有一共同特点:以博闻强记显其长,著书多凭记忆。嘉靖前期的杨慎如此,嘉靖后期的王世贞亦如是。王世贞虽书可观者富,却以强记、博全显赫于天下,观其数百卷的《四部稿》《续稿》也多恁记忆而成。博览博记博识为其长,而精细则未必,虽说王世贞比杨慎更精细些,(27)于慎行云:“新都(杨慎)博而不核,弇州核而不精。”意为王世贞由杨慎不核而到核,前进了一步。见(清)于慎行:《谷山笔尘》,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但因误记而造成的讹误在所难免。这一点曾遭到后承继者的批评,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以王世贞三述(《盛事述》《奇事述》《异典述》)为学习标杆,同时也指出所记遗漏十余条。如:
弇州所记解元、状元凡九人。而宣德庚戌科状元林震,则本省解元,其会试又第二,而《盛事述》遗之,仅见于《科试考》矣。
又解元会元,弇州所记十一人。而永乐二年甲申科,有吉水刘子钦者,以先一年癸未江西第一,会试复冠多士。弇州亦不之载。(2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六《三试三名内》,清道光七年刻同治八年补修本,第408页。
此后,经胡应麟、张萱、沈德符、谈迁、钱谦益、潘柽章、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章学诚的发展后,进一步由明代的博而杂(或广而疏),走向清代的专而精。嵇文甫说:“自杨慎以下那班古学家,并不像乾、嘉诸老那样朴实头上下功夫,而都是才殊纵横,带些浪漫色彩的。他们都是大刀阔斧,而不是细针密线。他们虽不免驳杂,但古学复兴的机运毕竟打开了。”(29)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56页。朱一清说:“康熙时,儒术最盛,半皆前明遗老。乾、嘉以后,精深或过之,博大则不逮也。”(30)(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第 150 页。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31)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观堂集林(外二种)》卷第二十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74页。因国初“学者多胜国遗老”,故“国初之学”实乃“明末之学”也,即明末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顾颉刚说得更明确:明人的优点“或者还在‘博’上……他们的广而疏和清代学者的窄而精,或者有互相调剂的需要。”(32)(明)陈继儒:《新刻弇州读书后序》,见(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读书后》,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2页。笔者以为,明清学术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明代以“史”为主而辅以“经”,清代则以“经”为纲,以史为纬。二是明代特别是中晚期著述相对自由,不像清代康、乾时期有那么多的文字狱,“他们读书的态度并不严正,什么书都要读。因此他们受正统思想的束缚较轻,敢于发议论,敢于作伪,又敢于辨伪”。(33)顾颉刚:《四部正讹序》,见(明)胡应麟《四部正讹》,上海:朴社,1929年,第3页。而正是这种自由的氛围,形成了另一个特点——尚奇。可以王世贞的《奇事述》《异典述》《盛事述》为代表,而《宛委余编》《首辅传》《昙阳大师传》《皇明名臣婉琰录》《凤洲笔苑》以及《弇山堂别集》中的《巡幸考》《中官考》等,都具“逐奇”之趣,从而形成“以奇显真”的倾向。而清代则更倾向于以“求是”“求真”为归。故而总体说来,明代嘉靖始至清代康、乾时期的学术风气,由博而杂而奇,走向了博而专而精。从而改变了“明心见性”“束书不观”的空疏之学,走向了博学和考据的实学。
二、《弇山堂别集》与明清史学考证风气
王世贞自少年便立志写一部《明史》,在国史、家史、野史三史合一的史体观指导下,长期从事史料的收集撰述,著述达数百卷。(34)王世贞的史学著作有《弇山堂别集》100卷,《弇州史料》100卷,《皇明名臣琬琰录》100卷(现存32卷本,实际卷帙相当于100卷),《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8卷,《凤洲笔苑》8卷,《觚不觚录》1卷,《历史古镜》30卷。还有有序无书的《天言汇录》10卷,《少阳丛谈》20卷,《野史汇》100卷。他承绪并纠补杨慎,推进明末清初史学考据风气的兴盛。王世贞尤以考证典章制度之细、掌握家史资料之广和纠正《明实录》之误的考证见长。王世贞之前长于考证者为杨慎,其著作《丹铅录》盛行海内外。然因书中之瑕疵,也致攻击四起。《四库全书总目》云:“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录》诸书,不免瑕瑜并见,真伪具陈。又晚谪永昌,无书可检,惟凭记忆,未免多疏。”(3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九子部《正杨》提要,清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刻本,第9230页。王世贞与杨慎皆为博学,然杨慎“晚谪永昌,无书可检”,王世贞虽与杨慎一样写书全凭记忆,然身边有大量藏书,为其考证提供了可翻阅的丰富文献。他对杨慎的正误得失较为清楚,《艺苑卮言》云:“杨工于证经而疏于解经,博于稗史而忽于正史,详于诗事而不得诗旨,精于字学而拙于字法,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凡有援据不妨墨守,稍涉评击未尽输攻。”(36)(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九《艺苑卮言》卷六,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6777页。所以他纠补杨慎之误缺,有自觉的意识与明确的目的性。
(一)《史乘考误》(37) 说明:《史乘考误》是《弇山堂别集》中的11卷。开《明实录》考证先河
王世贞以考据见长的著作是《史乘考误》十一卷,这是第一部对《明实录》错误加以系统考证纠误之作,也是较早的开史学考据风气之先的力作。(38)杨绪敏认为:“首开史学考信风气的是王世贞,他的考据代表作《史乘考误》11 卷,是明代首部对当代史史料进行考证的著作。”见杨绪敏:《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的兴起及其成就与缺失》,《安徽史学》2009年第4期,第10页。该书对明代嘉隆以前的92种史书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考订。据孙卫国先生统计,征论次数达306次,几部最为重要的私修史书,如《宪章录》《吾学编》《皇明通纪》《鸿猷录》征论得尤为详细。《史乘考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纠正《明实录》中历代帝王实录中的错误,并加以补正,数量多达一百四十七处(39)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7页。,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考索《太宗实录》曲笔背后隐藏的杀戮功臣的真相,精细如发,多所发现,且有些具有规律性,如“例凡暴卒者,俱赐自裁者也”,“谬、冯二人尚于卒下立传,而傅颖公、王定远仅于封爵下立传,则二公之祸当尤惨也”。(40)(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8页。《四库全书总目》云,“世贞承世家文献,熟悉朝章,复能博览群书,多识于前言往行,故其所述颇为详洽”“皆能辨析精覈,有裨考证”。(4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一《弇山堂别集》,清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刻本,第4305页。特别是关于建文帝出亡、鸡鸣山功臣庙、朱祖亮之死、李文忠之死、廖永忠之死以及在《旧丞相府志》中对胡惟庸案等的考证,成为清代史家考证的基础和重点问题,成为清人修明史者的主要依据,且开启了后代考辨《实录》的先河。焦竑《国朝献征录》、张萱《西园闻见录》、谈迁《国榷》、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及《国初群雄事略》、潘柽章《国史考异》等则是《史乘考误》的继续,“可以说王世贞是嘉、万以前明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而他开创了对明代史料的考辨,为钱谦益、潘柽章所继承和弘扬,也为清修《明史》和《四库全书总目》所吸收和采纳”。(42)⑦ 孙卫国:《王世贞明史学的影响》,《王世贞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255页。后人的考证在继承中也有进一步辩证、纠误、补阙,深化了相关的研究。如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中批评王世贞将元初的“纽璘”与文宗时的太监“纽憐”混为一人,“王元美谓《元史·纽璘传》不载此事,则误以为一人矣”。又批评王世贞《庚午元日日食诗》记错了日食时间,“元美以一代文献自命,不应差误乃尔”。(43)(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跋〈宛委余编〉》,清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家塾重刻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本,第1118页。事实上,杨慎、王世贞等明人“自忴强记,失于检照,往往有此病”。(44)(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一《跋〈弇州四部稿〉》,清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家塾重刻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本,第1149页。钱谦益、潘柽章对《明实录》的有些考证比王世贞更精细。如关于廖永忠之死,王世贞依据两个证据, 一是洪武十年(1378)朱元璋戒谕勋臣之《诏令》、二是永乐年间纪纲《狱辞》断定:廖永忠是僣用逾制而得罪被诛。钱谦益持相同意见,只是关于被诛的原因,钱谦益依据洪武二十九年(1396)宁王朱权奉欶撰的《通鉴博论》,认为“虽为僣侈犯上,实以沉韩林儿之故也”。(45)(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一百三,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明崇祯十六年矍式耜刻本,第4312页。潘柽章质疑若为沉韩林儿事,为何当时未诛,“而隐忍数年,信任不衰”?考出“盖因党比杨宪耳”,(46)(明)潘柽章:《国史考异》卷一《高皇帝上》,清光绪间吴县潘氏刻功顺堂丛书本,第74页。即杨宪为宰相时,廖永忠与之相攀比事。钱谦益与潘柽章都肯定王世贞的廖永忠被赐死之说,并想在此基础上力求有更新的进展,考证虽更细了,但不一定比王世贞说得更可靠。而清人修《明史》最终采用了王世贞的说法:“(洪武)八年三月,坐僣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年五十三。”(47)(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廖永忠传》,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第5677页。孙卫国先生指出,钱、潘之考证“继承了王世贞的考证风格”“凡王世贞对《太祖实录》考订的问题,钱谦益、潘柽章皆作重点,进行细致的论述考订”。(48)⑦ 孙卫国:《王世贞明史学的影响》,《王世贞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255页。然就对《明实录》考证的范围之广而言,未有超过王世贞者。王世贞实开明代史学考证特别是《明实录》考证之先河。
(二)“三史互证”(49) “三史互证”是指《弇山堂别集》中考体的考证方法。的史料考据法
撰写明史在当时存在两大困难。首先是明代官史的史料难凭。明代史官制存在两大缺陷:史官多兼职且分工不明;保证所写史料真实的起居注官,大多时间被罢置,使明史修撰无真史料根基。多仅以《实录》为史,而《实录》“仅纪邸报所列,至大臣小传,仅书平生官爵,即有褒贬,往往失实”。(5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焚通纪》,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第1853页。造成《实录》难据,形成明代官史弱。官史弱给野史兴盛以机会,明代野史发达,野史记事细、征是非是其长,而主观臆断,易失真是其短。家史不免于溢美而失真,然记宗阀、官绩是其长。对此,王世贞提出三史互证的史料考证方法:
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51)许建平、郑利华主编:《王世贞全集·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72-473页。
王世贞因得“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熟悉朝章”,而补官史之弱;自幼好访“朝家典故与阀阅琬琰之详”,(52)(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小序》,见许建平、郑利华主编《王世贞全集·弇山堂别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页。撰《琬琰录》之书,丰富官史;广搜野史异闻而撰《野史录》百卷,补野史不足;努力纠补明史撰写史料不足的问题。王世贞留下的史学著述是在“三史”兼收并用的原则下完成的。《弇山堂别集》一百卷,有帝系、帝历、帝统表、郡王宗系表、公侯伯等职官表,考证《明实录》所载历代帝王事正误的《史乘考误》,以及对诏令、谥法、命将、赏功、科举、兵制等明朝政体制度的考证。也有兼及国事、家事,带有掌故史料性质的《盛典述》《异典述》《奇事述》,具备了撰写一部明史的框架和必需的核心史料。《弇州史料》一百卷,以《别集》为基础,采《四部稿》《续稿》中传纪之文,增加了明代世家和纪传的内容以及带有家史、野史性质的碑、志、题、跋、志、赞、疏、策等“得之生色者”二十二卷而丰富之,使明史结构更完备。《天言汇录》十卷,纪明代自太祖至肃宗皇帝的诏敕、训饬之书。《皇明名臣琬琰录》一百卷,为纪明代名相、重臣、家史之书。《少阳丛谈》二十卷,乃笔谈朝廷得失之书。《明野史汇》一百卷,为明朝之街谈巷议的笔记、野史,是撰写明史不可少的参照史料。可谓史料齐备,卷帙浩瀚,达四百余卷,“是非不谬,证据独精”,(53)(明)杨鹤龄:《弇州史料序》,见(明)王世贞《弇州史料》,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第9页。这在明代史家中较为少见。
(三)《弇山堂别集》与创朝家典章制度考述体
王世贞考证的最大价值是史学中最见功夫的典章制度及其变迁的考证,如《弇山堂别集》中的《亲征考》《巡幸考》《亲王禄赐考》《兵制考市马考》(以上为各一卷)、《命将考》二卷、《赏赉考》二卷、《赏功考》三卷、《野史家乘考误》三卷、《科试考》四卷、《诏令考》四卷、《谥法考》六卷、《中官考》十一卷和《史乘考误》十一卷,(54)(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一百卷,明万历刻本。形成史料学中的“考体”。(55)“考体”由诏令杂体发展而来,源之于《史记》中的“书志”,在记录制度条文时,也记录事实,并对其进行相关的考证。王世贞在《诏令杂考序》中提出:“自高帝以后,书檄之类不登诏令,及不可以入史传者,录以备考。”此为王世贞首创。《四库全书总目》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然其间,如《史乘考误》及诸侯王、百官表,亲征、命将、谥法、兵制、市马、中官诸考,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证。
可见《四库全书》的编纂官,将关于明代典章制度的上述考证,与《史乘考误》等视,即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所创造的史学中的“考体”,得到了清代学者的认可。这种对明代典章制度的系统考证,不仅在史学体式上为首见,而且明代史学界对一朝典章制度的系统检验也是由王世贞所首创的,并得到了清代史学家的赞赏、继承。邵晋涵《南江书录》云:
先是明人撰集故事者,或仅志一朝,或只举一事,闻见未周,事迹未备;郑晓《吾学编》、邓元锡《明书》、薛应旂《宪章录》、何乔远《名山藏》,始有志于正史,汇累朝之诏诰与夫名臣言行之见于州郡志乘、诸家文集,汇萃成书。然晓等未尝得见《实录》,凡夫碑铭志状之虚辞、说部流传之讹舛及年月先后、爵位迁除之乖互,皆懵然未辨,毁誉失真,编排无法,识者病之。至王世贞《史料》,始据实录,以考证诸家之失,于类记之自相矛盾者、小说之凿空无据者、私家著述之附会缘饰者,连叙于篇,以资考订。(56)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足见王世贞对明朝史学、特别是典章制度的考证,廓清了此前明史料的诸多讹误,于《明史》史料整理功莫大焉。
三、王世贞思想演进:由求实尚用到经世致用
王世贞由复古走向博学,又在史学考证中走向实学,而在儒释道批评的思想表现,以致用为归宿。王世贞是位批评家,他在批评儒释道思想和历史人物过程中,始终坚持是否有利于社会之用的评价标准。
(一)致用观的经学批评
王世贞一生最崇敬者当为孔子,他接纳孔子内外兼修的人生观,强调“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不可缺”。(57)(明)王世贞:《读中庸》,见《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四,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176页。认定“古之欲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58)(明)王世贞:《读大学》,见《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四,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170页。于是,“格物”为其始,修身为本,终于用——治其国。所以“致用”是王世贞思想的终极目的,也是他检验、评价一切思想、学术的尺度。
王世贞同样从是否“济于事”的观念出发,对孟子以后儒学多所批评。“治安之于事也,原道之于理也,孟氏之后无伍矣。”(65)⑩ (明)王世贞:《札记内篇》,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6334、6369页。“由濂洛而前,其学博而粗,其旨浅,然其人材大,其就实。由濂洛而后,其学精而纯,其旨深,然其人材纤,其就虚。”(66)⑩ (明)王世贞:《札记内篇》,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6334、6369页。北宋之前的理学虽粗浅,却实,其后理学虽精深,却虚。即从便于用的尺度,肯定汉代经学,否定宋代理学, 认为宋儒不及汉儒。“吾尚谓汉之儒多援经以饰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经。援经以饰事有达而诬者,然而于事济也。推事以就经有迩而当者,然而于事不必济也。其济为隽不疑,而其诬至于刘歆之佐王莽,噫,可鉴也!”(67)(明)王世贞:《读白虎通》,见《弇州山人读书后》卷五,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208页。对宋代朱熹,特别是其《四书注》批评尤为深切,言朱注《大学》:“勇于表章而不精于订定。”“今杂置‘知止’及‘物有本末’诸条于首章,以‘致知’‘格物’之解阙而妄以腐庸之长语补之……何舛也!”“‘至知在格物’之章,何阙释乎!”(68)(明)王世贞:《读大学》,见《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四,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172页。至于《中庸》:“第朱子解,则天下有大本而无达道矣。至致中和,分天地位、万物育,又分戒惧、谨独,支离割强,大失子思本意。”(69)(明)王世贞:《读中庸》,见《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四,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175页。批评明代道学走向虚妄,不仅于世无补益,且失去性理之学的根本。“尊德,性也,主静也。致良知也,随处体认天理也。体仁也,其欲标名而自尊一也。善用之皆可以成君子,不善用之皆可以成小人。”(70)⑤⑨⑩ (明)王世贞:《札记内篇》,见《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6370、6371、6448、6338页。而事实上,王世贞认为不善用者多。“今之谈道者,吾惑焉。有鲜于学而遮者,有拙于辞而逃者,有败于政而遗者,有鹜于名而趣者,有縻于爵而趣者,欲有所为而趣者,是陋儒之粉饰而贪夫之渊也。”(71)⑤⑨⑩ (明)王世贞:《札记内篇》,见《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6370、6371、6448、6338页。王阳明也自在王世贞批评之例,或言其不知圣言之全,或批评其认知有不到位之处,或言其论理过于琐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不可缺,只在‘之’字上体认分晓耳。朱子之格物,于‘之’字所未彻也。王文成之格物,知有之,而欲废此五者,不可也。故皆不知圣言之全。”(72)(明)王世贞:《读魏志》,见《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四,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176页。“王氏之学几矣,心体之淘洗,微有未莹也。”(73)(明)王世贞:《札记内篇》,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九十三,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6361页。“文成公之所谓良知足矣,乃至尽引经语以证吾、合吾、伸吾是,而彼之所谓是者亦出矣;吾证吾合,而诸牵蔓而不能悉合者,亦出矣。”(74)(明)王世贞:《书王文成集后二》,见《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四,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164页。从这些批评的话语,我们发现王世贞极看重儒学家看问题是否洞彻见底,是否悟透,是否见其全体,而评鉴是否悟透的标准,即能否发现其“致用”的价值。
(二)从欲、理对立到“欲即理,理即治”
“欲”“理”关系是宋明理学的重要范畴。朱熹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论。李贽与朱氏相反,强调以欲抗理,以“童心”抵抗“闻见道理”,以“净”斥“染”,转入另一种二元对立论。然而王世贞则趋向于“欲即理”“理即治”的“欲-理-治”合一说。这是明代后期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向。
王世贞认为认识事物须溯其源,依其本原,顺其本性,方可成理。“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一,成于两,此乾坤自然之妙也。是故,古之圣王独端其原,大其辅。”(75)⑤⑨⑩ (明)王世贞:《札记内篇》,见《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6370、6371、6448、6338页。人性之本是情欲,人之行事源之于情欲,故人生之道与治世之道须以此为基础,顺欲而成理,导欲化欲而成治。于是王世贞将欲引向理与治。
火无体,物为体,星然而发,燋宇宙,烁金石。欲最甚,怒次焉。夫犹火也,夫惟狂者以志成之,其秦始、汉武乎?夫惟圣者以道成之,其文王、太王乎?(76)⑤⑨⑩ (明)王世贞:《札记内篇》,见《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6370、6371、6448、6338页。
“欲”即“火”,不仅“星然而发”,自然而然,而且“燋宇宙”“烁金石”,力量无穷,以致成就狂者、圣者,做出成就帝王、圣人的伟大事业。由此观之,王世贞肯定情欲,并视之为本源和动力。情欲乃人之本,懂人之本乃理之基,导欲化欲乃治之方,于是“欲即理”,情理一也。“理即治”。即主张情理合一,合于用,合于治。
三苗之于舜也,其五帝之欲乎?鬼方之于高宗也,其三王之欲乎?昆夷之于文王也,其太甲成王之欲乎?荆戎之于平王也,其后世中主之欲乎?上焉者化之,欲即理,理即治。次焉者克之,又次制之。
人至于死而万用尽矣。圣人以之昭节揭轨,垂万世焉。夫妇之间一情欲感耳,圣人以之立纲陈纪,配天地焉。(77)②③ (明)王世贞:《札记内篇》,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明万历刻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6348、6362、6342页。
学生缺乏音素意识。在小学的英语授课过程中,跟读并仿读单词是常规的练习,由于缺少音素意识,学生跟读发音不准。我国的小学生缺乏音素意识,在拼读时习惯将音通过汉语来标注记忆,这种错误的习惯严重阻碍了学生的英语学习。
在王世贞看来,不只儒学之道以情欲为基,老、庄之道与释氏之道也无不建立于情欲之上。“夫人生有涯而欲无涯,以有涯之生而供无涯之欲,势不得不求之延年。以延年为有尽,势不得不求之离生死。”(78)②③ (明)王世贞:《札记内篇》,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明万历刻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6348、6362、6342页。道家求“延年”,释氏求“离生死”,皆基于解决人生中无涯之情欲与有涯之生命间的矛盾。需特别指出的是,王世贞承认人的情欲是人性的根本、万事万理之源,但其目的是依此而实现国家理想政治。他与李贽等人强调人性本私、追求实现人性本真而达到个体精神快乐的目的有所不同。譬如李贽倡童心,认为童心才是真心。真心方为真人,方一切皆真,方可写出天下之至文。失却童心,则失却真人,则一切皆假。惜童心丢失于随年龄增长而与日俱增的“闻见道理”中。王世贞则认为年龄日长而闻见道理日多,童心随之而失是自然之势,也是自然之理。对闻见道理,应“因时而节之”,存其童心而已。
天地之始浑乎?国之始璞乎?人之始婴儿乎?婴儿渐而童也,势也,亦理也,因时而节之。存始可也,反始则谬。(79)②③ (明)王世贞:《札记内篇》,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明万历刻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6348、6362、6342页。
王世贞与李贽肯定童心以求心真、人真的观点是一致的,皆为寻“致良知”之方。然又有细微差别。一个要节制“闻见道理”,一个要排斥“闻见道理”;一个要情理合一,一个要以情抗理。李贽当属“情、理二元论”者,而王世贞则属于欲、理一元论。从二元论到一元论,是明清之际思想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转向——由心学转向经世致用的实学。嵇文甫在总结明代末年思想发展的脉络时说:“进一层追求,观其会通,尚可以看出一个总趋势,即从超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是也。从悟到修,悟虚而修实;从思到学,思虚而学实;从体到用,体虚而用实,从理到气,理虚而气实。……这各种现实主义倾向渐渐汇合成一大潮流,于是乎清初诸大师出来,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相号召,截然划出一个思想史上的新时代。”(80)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70-171页。王世贞情-理-治合一、以致用为归的思想,正是这一大潮流中的重要一环。
(三)三教合一合于用
王世贞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却以为三教既不合于儒,也不合于道,而是合于心,道与佛皆归于心,所谓即心即道,即心即佛。心即道,心即佛,是禅宗慧能的思想,也是陆象山、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基本理数。慧能说:“自心皈依自性,是皈依真佛。”(81)(唐)释慧能:《忏悔第六》,见《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26页。然自性是清净之心,沾染尘缘便变为染心,不再清净了,于是出现净心、染心的二分法。而马祖道一则主张心、佛合一,“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此心即是佛心”(82)(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六,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134页。。又认为“平常心是道”“无造作,无是非”“无凡无圣”。(83)(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716页。王世贞承继慧能与马道祖一的一元论,认为心有净染之分,有即心即佛与非心非佛之别。又以马祖道一的平常心来破除净心与染心之惑。马祖道一所云“即心即佛”,是单刀直入法。又六祖云“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84)(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五,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110页。亦此意也。王世贞进而提出自己的“妙明真心”的心性观。
妙明真心与妄心本无有二,悟则为真,迷则为幻。知色即是空,则知空就是色。所以水冻为冰,冰融为水,若别求照心以破幻心,则又误也。(85)(明)王世贞:《屠长卿》,见《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二百文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937页。
王世贞认为真空是万物的本性,自在万物之中,自在人心之中,不需外求。“着意寻空空未得,若论空外本无空。从教了却真空意,千树桃花自在红。”(86)(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四十九,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2465页。人们只需在平常心的状态便可自得,故平常心即道。
王世贞所谓“心”,包括向内与向外两个层次。向内即体即悟,是对人与万物的体悟、认知,主张通过“自悟”“顿悟”而达到“无”“空”的最高境界,从而贯通、悟透三家学说。向外即向个体之外芸芸众生的社会,即“用”即“有”。而打通内之“空”与外之“有”的分界,即“空无乃大用”“其体至虚,而不无其用”。(87)(明)王世贞:《书道德经后》,见《弇州山人读书后》卷七,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247页。即心而能即佛的前提在一悟字。悟得彻即佛,悟不彻则非佛。王世贞对悟有自己妙得,他不赞赏渐悟,而主张顿悟,以为渐悟不一定能彻悟。王世贞所言顿悟分两个层级:解悟、自悟。自悟是自身直接悟透,而解悟乃是对别人理解的悟透。曾子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理解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王世贞认为“夫悟,解悟也,解悟非悟也”。(88)(明) 王世贞:《读坛经一》,见《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六,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216页。即解悟非自悟。而慧能的那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89)(唐)释慧能述、(唐)释法海录:《行由第六》,见《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12页。方是自悟,自悟方可成佛。
王世贞不受三教之束缚,其本于佛教的真空,固守“无相无心”之无,其所求之用,非儒家一家的治世之用,也有养性养生守神之用。而养性守神乃用之大者,所谓“其体至虚,而不无其用”。(90)(明)王世贞:《书道德经后》,见《弇州山人读书后》卷七,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247页。“夫道者,知学绝学,善用无为”是也。(91)(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见《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七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4页。如是,王世贞强调体用同源,既融佛禅于三教,使三教归禅,又坚守体用同理,强调即心即佛,即心即道,即心即用,使三教合一合于用。纵观王世贞一生对于朝政历史人物与文化典籍的评价,其一以贯之的标准乃是“体用”之功:
大抵所谓大人者,德位兼备之大人。而所谓学者,治国平天下之学。故于“格物”一章,遽及于无讼之为本,以见体不离用;“平天下”之章,绝不及国,而惟致辨于忠信、骄泰之得失,以见用不离体。而中以修身贯之,见大体之所在,而后可以言学。(92)(明)王世贞:《读中庸》,见《弇州山人读书后》卷四,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175页。
圣人之言远如天,愚以为近于地也。贤人之言近于地,乃时时远于天。凡圣人之言,未有不可践者也。
今二氏之所以渐衰,非其说之衰,亦以取验少也。(93)(明)王世贞:《札记内篇》,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刻本,第6334-6362页。
王世贞主张三教归一归之于用,而“用”终归之于“情”——合乎人情、方便人情。他常用是否合乎人情、便于人情作为评价思想价值的标准之一。
凡天下之术,有可久者,必其便人情者也。墨氏利天下,摩顶放踵,而为之恡者,不自便也。杨子拨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贪者不之便也,此皆非人情。是故,不待辟而自废,如便者,虽至今存可也。吾窃以为夫子而下,颜氏子醇乎?醇哉。曾子、子思盖庶几焉。荀子大疵而小醇者也。杨子醇与疵,俱小者也。孟子大醇而小疵者也。孟子之醇非诸贤之所能为醇也。孟子之疵者,犹之乎诸贤之疵也。(94)见韩国精神研究院藏书阁所藏《弇州读书后》卷四,因书前缺页,而不知该书为何版本,较之《四库全书》本,该书篇目明显增多,有些篇章的文字间有差异。
由体用而归之于人情,一切用的目的皆在于合乎人情。王世贞在《昙阳大师传》中很注重叙述其师对人情事理的态度,发现昙阳子“其持论恒依伦物,尤能察人情,识常变”。并以人之情理传道,“人道修身,圣道修神,神在身中,以有情为运用,以用情不用为修持,凡好名好事,交际往来,分别是非,一切种种,总持善趣,亦属尘缘”。而王世贞一生从不肯弃笔砚的人情债,也正是因“以有情为运用”“一切种种,总持善趣”所致。这一人情论是王世贞思想的一大亮点,既与其以情欲为道之源的观点相一致,又是其经世致用思想化为不违人情、方便人情的情治合一的表现。
四、结语
王世贞是位集古学、博学、考据学、经世致用思想为一身的集合型人物;又是明代晚期至清初思潮转型的枢纽式人物,对推进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转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是后七子复古学的领袖,主盟文坛前后达四十年,以富藏、广览、强记、博识,为一时之冠;著述宏博,雄踞天下,既是前代各种文体创作的集大成者,又是前后七子文学批评理论的总结者;异才博学、横绝一时,领袖群伦,搅动一个时代的古学、博学风气。
王世贞精于治史,欲以个人之力写一部《明史》,为万历之前明代史学的系统考察者。创“三史”互证的史料学考据法;《史乘考误》考证纠补《明实录》,开《明实录》考证之先河;《弇山堂别集》创朝堂典章制度流变的考述体;继杨慎而起,推进了明代考据学的兴盛。他倡导“致用”观,以之为标准批评历代经学之得失;反对情欲与天理的二元对立,导“欲”于“治”,主张“情即理、理即治”的情、理、治一元说,完成从二元论至一元论的理学思想转换。他主张三教合一合于心,致于用,认为心学蹈空,宋代理学失真,原始儒学不利于用,追求“经世致用”的价值观。
尽管王世贞著书立说凭记忆和兴趣爱好,难免粗杂而奇,但毕竟掀起了一个时代博学求实的风气,并在后继者的相继纠偏中逐渐走向清代的博而专而精。在此过程中,展示出明清之际,与明代心学潮流同行的另一派实学潮流——由古学、博学到考据学而最终走向经世致用实学——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95)这一个由古学而走向经世致用实学过程的另一重要脉络,则是王世贞—复社—顾炎武等明末清初太仓学派所兴起的实用思潮。复社即“复古”与“经世致用”思想的合流,显然是受王世贞复古与致用思想的影响。而此派的领袖张溥、张采,都是太仓人,与王世贞家相距咫尺。同时清初学风的奠基者顾炎武即是复社成员,又是昆山千灯镇人,且与王世贞家世代联姻。关于这一发展脉络,当另撰文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