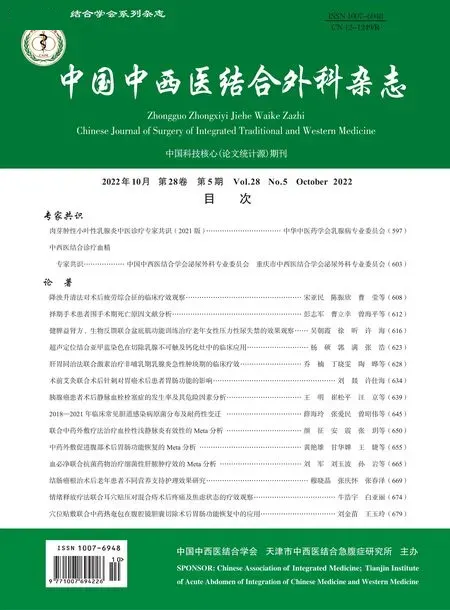疮疡外科“偎脓长肉”的理论源流与临床应用
周 彤,王 宁,王雪皖,邓莉娟,杨光耀,王 刚,鞠 上
“偎脓长肉”是中医疮疡外科的特色治疗理念之一,临床中广泛应用于压疮、慢性骨髓炎、糖尿病足等慢性难愈合创面,且临床效果显著[1]。然而中医古籍中关于“偎脓长肉”的记载较为散在,且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了“偎脓长肉”“煨脓长肉”“猥脓长肉”不同的文字表述,导致现代医家常常将其混用,为探索及应用该理论带来了困扰。因此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梳理“偎脓长肉”的历史源流,阐明其理论内涵并指导临床应用。
1 “偎脓长肉”的理论源流与释义
在“偎脓长肉”理论中,“偎脓”为理论与治疗方法,“长肉”为目的与治疗效果,故对“偎脓”的理论源流与概念含义逐一进行讨论阐释。
1.1 “偎脓”中“偎”的发展源流与含义 “偎脓长肉”理论最早且仅见于明代申斗恒的《外科启玄·明疮疡宜贴膏药论》:“在凡疮毒已平,脓水来少,开烂已定,或稍有疼痒,肌肉未生,若不贴其膏药,赤肉无其遮护,风冷难以抵挡,故将太乙膏等贴之则偎脓长肉,风邪不能侵。”[2]根据其中记载,外用膏药贴近创面可以遮护赤肉、抵挡风冷,进而“偎脓”以长肉。《康熙字典》中对“偎”字的释义为“昵近也”[3],故“偎”字可理解为挨傍、贴近。因此“偎”脓长肉主要指在创面外用膏药进行贴敷,覆盖创面以防止外邪侵袭,进而保护创面的脓液使肉芽生长。
及至清代,中医古籍中出现了“煨脓”“猥脓”的表述记载。“煨”脓长肉均见于清代吴谦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主要表述为“脓熟开之,外贴琥珀膏煨脓生肌治之……”“既溃宜八珍汤……因证用之。外用五色灵药撒之,化腐煨脓。”[4]分别用于治疗手部蛇头疔及便毒。其中所载琥珀膏由定粉(铅粉)、血余、轻粉等组成,五色灵药由黑铅、白矾、水银等组成,二者均具有解毒化腐、活血化瘀的功效。
《说文解字》中对“煨”字释义为:“盆中火也”[5],后经延伸,“煨”主要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微火慢煮;二是在带火的灰烬里烤熟[6]。故“煨”脓长肉可理解为在脓熟已溃而腐肉未脱的阶段,外用具有活血祛瘀化腐功效的中药膏剂或散剂,化腐成脓,通过调畅创面局部的气血,使脓液载邪外出,最终达到长肉生肌的效果。
“猥脓长肉”仅见于清代汪启贤《济世全书》:“万应紧金膏:治一切无名肿毒、疔疽发背、疮疖湿毒、臁疮,始觉时便贴患处即消,已成亦能猥脓长肉止痛,其效不可尽述。”[7]根据原文判断,此处“猥”作动词意,《康熙字典》中对“猥”释义为:“猥,积也。”又“猥者,多而疾來之意”[3]。故此处“猥”脓长肉可以理解为外用药膏以快速积聚脓液,促进创面湿润,进而达到长肉、止痛的效果。
综上所述,历代中医古籍中出现的“偎脓”“煨脓”“猥脓”三种文字表述,分别凝聚了各个医家对该理论的不同见解:“偎脓”侧重于对创面脓液的保护,与现代医学“湿润疗法”[8]理论内涵较为相似;而“煨脓”则蕴含了脱腐成脓长肉的理念,与现代医学“自溶性清创”[9]相近;“猥脓”则强调了脓液的多少,已经包含了对创面进行湿度掌控的治疗思想。而三种表述异中有同,均蕴含了我国古代疮疡外科通过施治于脓液而生肌长肉的治疗思想。因此,为了便于表述及后续探讨,笔者认为应尊重原著及历史源流,采用最早出现的“偎脓长肉”作为该理论的文字表述,并进一步阐明其理论内涵。
1.2 “偎脓”中“脓”的释义
1.2.1 疮疡外科之“脓” 《现代汉语词典》中“脓”的释义为:“某些炎症病变所形成的黄绿色汁液,含大量白细胞、细菌、蛋白质、脂肪以及组织分解的产物。”[10]现代医学中这样的“脓”往往与局部的感染、炎症等相关,是阻碍疾病向愈的不利因素,而中医古籍中对“脓”的阐释则更加丰富。
疮疡外科所述之“脓”在《灵枢·痈疽》中已有记载:“寒气化为热,热盛则肉腐,肉腐则为脓,脓不泻则烂筋……”[11],可知“脓”是由机体局部邪滞热盛以致肉腐而形成,此处的“脓”被作为病理产物来进行描述,与现代医学的“脓”最为接近。在“脓”形成后,伴随着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转归,“脓”也开始出现不同的性质表现。如清代祁坤在《外科大成·论脓血》中所述:“先出稠白脓,次流桃花脓,再次流淡红水,方为脓尽生肌之兆。”[12]即记录了疮疡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脓”的形、色、质表现。又如《外科正宗》所载:“溃后脓黄稠,新肉易生;脓液清稀,腐肉虽脱,新肉不生”[13],及《外科证治全生集》所云:“脓色故厚者,气血旺也;脓色清淡者,气血衰也”[14],则均表明疮疡后期脓液的色质预示着疾病的不同转归。
综合以上记述,可见“脓”不仅可以用来判断疮疡的转归,更在不同治疗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辨明“偎脓长肉”理论中的“脓”为何种含义,对阐释理论内涵及指导临床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1.2.2 “偎脓长肉”之“脓” “偎脓长肉”理论所论之“脓”可以根据来源分为以下三类。首先在腐肉未脱之时,应用祛腐化瘀类药物以化腐成脓,如《疡科纲要·外疡总论》所记载:“水亦尽,溃口又见稠脓,则肿势全消,内孔已满,新肌已充,而全功就绪矣”[15],此时的“脓”由腐肉化生,具有脱腐消肿、敛疮生肌的作用。
到了疮疡后期,创面久溃难愈往往与气血盈亏关系紧密,如《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所载:“脓少清稀口不敛,大补气血调卫荣。”[4]即阐述了脓液分泌不足导致创面久不愈合,需要从补足气血来论治。此时的“脓”由气血所化生,具有生肌长肉的作用,且往往与所用药物的温煦作用有关,正如王维德在《外科全生集》中所述:“热毒之化必由脓,脓之来必由气血,气血之化必由温也”[16]。现代学者研究认为,这种具有促进创面愈合作用的“脓”是在创面生长后期,创面内部出现的少量、黏稠、富含营养物质的温性液态物质,是有利于创面愈合的新生产物[16]。
在脱腐成脓、气血生脓的过程中,还蕴含着第三种“脓”的来源,即药疮交互成脓。通过外用药物作用于创面,可以促使腐肉、气血成脓,进而促进药物与创面的接触与融合,在此过程中,药物与创面的交互作用也使得创面微环境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产生了具有抗炎、促愈效果的“脓”[17]。
综上所述,“偎脓长肉”之“脓”具有脱腐化生、气血所生、药疮交互三种不同的来源含义,可见该理论在疮疡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应用思路。
2 “偎脓长肉”理论的临床应用
2.1 “偎脓长肉”的应用时机 明代汪机在《外科理例》中提出:“若脓血未尽,便用生肌,务其早愈,则毒气未尽,必再发。”[18]《外科大成》中也指出:“腐不尽,不可以言生肌;骤用生肌,反增溃烂”[14],二者均表明如果在腐肉未尽时即应用补益气血法来生肌长肉,可能导致局部残留的未尽之邪受到滋长,再次发病,以致创面迁延难愈。现代医学研究将创面愈合过程分为炎症反应期、增殖修复期及重塑期[19],中医外科学所述疮疡“脓血未尽”“腐不尽”的这一阶段即与创面炎症反应期类似。这一时期,大量炎症细胞及炎症因子聚集于局部创面,坏死组织溶解产生的组织细胞碎片以及伤口渗出液等成为这一时期创面脓液的主要成分[20],如果此时着眼于局部创面组织的增殖与重塑,则可能导致炎症反应难以消退。有研究表明,炎症反应期的延长是造成创面延迟愈合的重要原因[21]。现代著名中西医结合疮疡学家李竞教授也提出:“腐去肌生”是一切皮肤溃疡愈合的重要规律[22]。因此,应当根据创面所处不同阶段,选择恰当的“偎脓长肉”应用时机。
“偎脓长肉”的应用时机需要根据创面“脓”的情况进行辨证施用:若脓水淋漓、清稀臭秽,伴腐肉不脱者,此时不宜应用益气补血法,而需施用脱腐成脓之品,使所“偎”之脓既由腐肉所化,又由脱腐药物与创面交互所生,这样的“脓”具有稀释毒素、促进白细胞吞噬致病菌的作用,还能对创面进行湿润营养以促进肉芽与上皮组织的生长[23];待脓液减少、质地变稠,腐肉渐脱后,方可考虑应用温补气血来“偎脓长肉”,这一阶段的“脓”多为色泽鲜明、黄白质稠、略带腥味的脓液,现代研究表明,这种“脓”含有多种生长因子及微量元素,能够刺激内皮细胞生长及新生血管形成[1],同时富含免疫活性细胞及因子,能够有效调节局部创面的组织细胞功能[24],为创面肉芽组织生长提供必要的条件。
2.2 “偎脓长肉”的常用方药 目前“偎脓长肉”的常用外治方既包括中医古籍中所载经方,也囊括了现代医家结合古方及个人临床经验所得的自拟方,如太乙膏、生肌玉红膏、回阳生肌膏、煨脓长肉膏、阳和解凝膏、正阳膏等。根据适用阶段的不同,上述膏方中常用的中草药可分为两类:一是活血化瘀脱腐类,如三七、地龙、乳香、没药、琥珀、血竭、轻粉等;二是益气养血生肌类,如黄芪、肉桂、人参、白蔹、海螵蛸、血余、珍珠母等。陈实功曾在《外科正宗》中提出:“诸疮皆因气血凝滞而成,切不可纯用凉药,冰凝肌肉,以致难腐难敛,当用温暖散滞行瘀,拔毒活血之药为妥。”[16]因此在临床应用“偎脓长肉”法时,根据创面情况选择不同的药物组合,但总以活血温通、化瘀生肌为主要治疗原则。
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表明,外用中药可以起到营养、酸化及保护创面,以及调节免疫、止痛、杀菌抑菌等作用[25]。其中祛腐类中药可以增强巨噬细胞溶酶体的活性,并提高创面免疫细胞活性细胞的氧代谢,同时通过改善创面微循环、调节创面pH值,多靶点共同作用从而达到祛腐的治疗效果[26];生肌类中药则通过影响创面局部细胞及细胞生长因子间的网状交互调节作用,调节创面的微量元素含量及胶原表达比例,加强氧化代谢功能,并保持创面湿润,从而促进创面长肉生肌[27]。
3 小结
综上所述,“偎脓长肉”理论在历史发展中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阐明了脓液能够保护创面促进长肉,还涵盖了脱腐成脓、祛腐生肌这一阶段的内容,对创面外用中药有着独到的见解。相较于西医学“湿润疗法”以外用敷料保持创面湿润为主要内容,“偎脓长肉”理论更揭示了外用中药敛疮生肌过程中的“药疮交互作用”[23],是一个整体的、主动的修复过程。这既是“偎脓长肉”理论的优势,也是其亟待进一步研究与发展的内容,如“偎脓长肉”的作用机制、外用中药的剂型材料、遣方用药的标准等,从而使该理论更好地在临床进行推广并指导临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