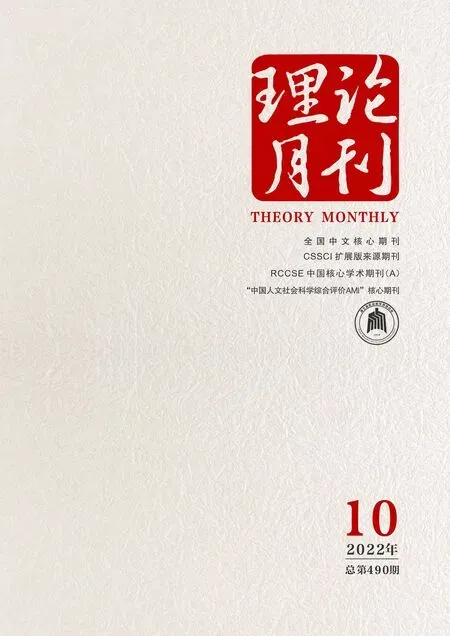“呼唤—回应”结构是一种出神结构吗?
——从亨利对马里翁的批评谈起
□涂 攀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0)
自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中首次建立了“显现—显现者”的二维结构后,这一结构就以各种衍生形态存在于后来的现象学之中,且规定了现象的含义①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中对“显现—显现者”结构进行了详细的界定,他指出:“根据显现和显现者之间本质的相互关系,‘现象’一词有双重意义。现象实际上叫作显现者,但却首先被用来表示显现活动本身,表示主观现象(如果这个粗糙的、在心理学上会造成误解的表达在这合适的话)。”(参见: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4.)胡塞尔至少为这一结构赋予了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这个结构规定了现象;另一方面,它规定了被给予性的形式。胡塞尔将其称为“显现的被给予性”(givenness in appearing)和“对象的被给予性”(the givenness of the object)。马里翁在《还原与给予:胡塞尔、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Reduction and Givenness:Investigations of Husserl,Heidegger,and Phenomenology)和《既给予:朝向一种被给予性的现象学》(Being Given: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Givenness)中都分析了胡塞尔的这一结构。。在经历了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存在论差异”(die ontologische Differenz)探讨[1](p108-141),以及列维纳斯对他者与自我的“面容”(visage)的原初“伦理他异性”的论述后,马里翁承接这一路线,将此二维结构推向了极限,并依照“呼唤—回应”结构①需要说明的是,马里翁并非唯一关注到纯粹呼唤结构的人,至少在他出版《还原与给予》的同时期(1989年),法国当代著名宗教现象学家克雷蒂安(Jean-Louis Chrétien)就提出了宗教学意义上的“呼唤—回应”结构(1991年),并认为祈祷现象学呈现了这一结构,且在1992年出版了《呼唤与回应》(L’Appel et la Réponse)一书。同时,在1991年那场著名的“现象学的神学转向”的争论中,保罗·利科(Paul Ricœur)也关注到并参与了“呼唤—回应”结构的讨论,并对此提出了批评。参见:Jean-Louis Chrétien.The Call and the Response[M].trans.Anne A.Davenport.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4:vii-xiii;Dominique Janicaud.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logical Turn[M].trans.Bernard G.Prusak.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0:127-176.界定了“充溢现象”(le phénomène saturé)②充溢现象指的是直观的被给予性大于概念的被给予性,充溢的直观无法用任何概念进行把握,它充分展现了事物自身的给予。与之对应,“贫乏现象”(phénomène pauvres)(如数学的对象)和“普通现象”(phénomène communs)(如物理学的对象)分别意味着概念过剩于直观,概念等同于直观。在马里翁看来,后两者限制了事物自身的给予。。然而,这一结构却面临着一个核心困难,即它如何在现象学中发挥作用,从而取代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列维纳斯的现象学结构,成为现象的最根本结构。在这个问题上,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从“出神距离”(Ecstasis)的角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笔者将依照马里翁的思路对上述批评予以澄清,然后试图揭示马里翁对亨利的反驳中存在的问题,探寻彻底驳倒亨利所需要的补充。
一、“呼唤—回应”结构与现象的可能
1989年,马里翁出版了“被给予性现象学三部曲”的第一部——《还原与给予》。他在该书结尾简单呈现了“纯粹形式的呼唤”,并在随后的著作中将其看作现象的一般结构:“现象性并不是对象之构成,而是对一些呼唤的回应。”[2](p261)在马里翁看来,纯粹的呼唤还原是相对于超越论还原与存在论还原的第三次还原,也是最终的还原,它直接体现的就是“被给予性”(donation)本身。然而,纯粹的呼唤还原所展开的纯粹呼应结构在现象学上并未出现过,甚至在哲学史上也不多见,反而因其与神学的融洽屡次招致批评。比如布莱恩·罗比内特(Brian Robinette)就指责马里翁的回应概念太过于被动:“不承认逻各斯并不是因为启示本身的缺乏,而是因为启示的接受者的无知或故意的否认。”[3](p93)亚当·J.格雷夫斯(Adam J.Graves)也认为马里翁的呼唤与回应概念之间存在着矛盾,他指出,“人们或许会质疑一个理论的连贯性,这种理论似乎既要求主体完全由被给予者产生,又要求它对产生它的被给予者提供某种抵抗,尽管这种抵抗是最小意义的抵抗”[4](p112)。这就导致回应概念在现象的显现方面存在困难。然而,最为典型的是亨利的指责。亨利在《现象学的四条原理》(The Four Principles of Phenomenology)中,以既赞扬又批评的矛盾心理分析了马里翁现象学的第四条原理:“越多的还原,越多的被给予性。”[1](p203-207)亨利认为,马里翁在呼唤与回应之间设定了绝对的出神距离,导致呼唤结构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原初现象,最终的还原不是导向纯粹的呼唤,而是生命的呼唤,因为生命没有任何距离。亨利指出:“……除了生命悲怆地爆发在我们身上,除了它的呼告,呼告的话语是由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激情、我们的爱所构成的,它不再有任何纯粹的呼唤形式,没有一个呼唤结构会超出或不同于这种悲怆。”[5](p18)
那么,亨利的批评是有效的吗?它符合马里翁对“呼唤—回应”结构的设定吗?进一步而言,亨利的批评是否动摇了马里翁将呼唤结构看作现象的一般结构的设定?要充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回到马里翁对呼唤结构的考察中去,追问马里翁在何种意义上以呼唤结构推进了原初的现象性。
在马里翁看来,现象学上已有的呼唤不足以建立起现象自身,反而限制了现象。比如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呼唤中,虽然“呼唤—回应”结构要呈现的是本真的生存论状态对此在的呼唤,使此在“自身愿有良知”[6](p377),但由于此在的回应总是通过“向来我属性”进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要么此在被存在的生存论境遇所规定,但是深度无聊却使存在的呼唤被悬置,此在对其“充耳不闻”[1](pp167-203);要么良知的决断通过此在的“向来我属性”而实现,但是这种“我属性”却损害了存在呼唤的纯粹性。因而,要想真正实现呼唤结构的纯粹性,就必须抛弃掉存在视域,甚至是任何视域。那么,呼唤结构是如何真正实现现象自身的呢?马里翁指出,现象的实现也就是现象的显现,它并非海德格尔所言的存在的现象,而是来源于现象自身的呼唤,是没有施加限制的现象自身的给予。马里翁由此将被给予性的两端,也就是“给予活动—被给予物”的两端,深化成了“呼唤—回应”的两端。一方面,在“给予活动”一侧,由于给予活动的展开,事物自身的给予发出了被给予性的纯粹呼唤。“呼唤实际上把每一种充溢现象自身当作其特征。”[7](p267)另一方面,需要某个回应者对此进行回应,因而涉及被给予物的一侧。在马里翁看来,正是这两侧的运作使现象得以显现。具体来说:发出呼唤的是事物自身,所发出的是纯粹的呼唤,进行回应的是某个“主体”——受予者(l’adonné),回应的结果是现象的显现或者隐匿。马里翁强调:“这个被给予的所有力量来自于对这个屏幕的撞击,从而一下子激起了双重的可见性。”[8](p50)因而,在呼唤的一般运作方式中蕴含了三个核心功能——“事物自身的给予”“受予者的给出”“现象的显现”。从逻辑上看,三者之间具有严格的充分关系,即“事物自身的给予”决定“受予者的给出”,前两者再合力决定“现象的显现”。
我们先来看“事物自身的给予”。在马里翁看来,每一种充溢现象都首先向我们发出了呼唤,然后才有受予者去不去回应的问题,而呼唤之所以可能,根源在于意向性的颠倒。“实际上,每一种充溢现象(或者悖论)都必然会颠倒意向性,因而使呼唤得以可能。”[7](p267)马里翁将意向性的颠倒看作呼唤进行的条件,他所强调的四种充溢现象都实现了意向性的颠倒。具体而言:在“事件”(L′événement)现象当中,事件在量上是过剩的。由于无法进行量的预测,自我便不再像意向性一样精准地朝向对象并将对象客观化。在这里,量的过剩发出了一种绝对的呼唤。在“偶像”(L′idole)(比如绘画)中,受予者在质上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偶像释放了一种绝对的可见性,在其中我们的意向性不能够将其构造成任何对象,只能在其中迷失。我们只能顺应这一呼唤去看它,偶像引导着我们的看。在“肉身”(La chair)中,它超越了任何关系,显现为“自行—感发”(auto-affection),因而“充溢了所有意向性的出神”[7](p267)。肉身不再是一种意向性的出神关系,而是肉自身的直接感受。肉自身发出一种呼唤,“我”投身到肉的直接性当中去。在“圣像”(L′icône)中,它因模态而不可凝视。我们不能够用意向性的目光去窥探他者,必须在他者的注视下服从于他人面容的呼唤。因而这四种充溢现象都发出了绝对的呼唤,这种呼唤本身不再与意向性相等同,反而消解了意向性。
然而,从形式上看,马里翁在此对意向性的反转在法国哲学中并无新义,这实际上是一条后海德格尔的道路。萨特、梅洛-庞蒂、亨利、列维纳斯、利科都行进在这条道路上,甚至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已经实现了意向性的反转。但问题不在于这种形式上的雷同,而在于意向性反转的程度与彻底性。马里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承续法国现象学的路线的。
马里翁认为,面对过剩的呼唤,作为回应的受予者自身也会经历还原,必须完全暴露在、倾注在、沉醉在这一呼唤之中。这是“呼唤—回应”结构中回应者的一般性规定。马里翁指出,“受予者不仅暴露在因其自身给予而自身显现的东西中(一般意义的现象),而且更为本质地暴露在一种悖论(充溢现象)之中,受予者在这一悖论中接收了一个呼唤,一个不能否认的呼唤”[7](p282)。也就是说,受予者一方面暴露在显现出来的一般现象之中,另一方面也暴露在绝对的充溢现象之中。这一暴露蕴含着受予者对呼唤的接受。在这种接受中,“受予者自身被完全交给了被给予性,以至于他给出了他自身,并最终获得了他的最后的规定性——根据被给予性的展开来接收被给予者,从而接受他自身”[7](p282)。由此,受予者把自己完全倾注在被给予物中,从而实现并确证了自身的绝对给予。
那么,纯粹呼唤的一般运作又如何使现象显现呢?马里翁认为,现象的显现是由受予者对充溢现象的呼唤的回应决定的,回应通过抵抗和变形而实现,这两者是统一的。抵抗意味着受予者在回应呼唤的过程中是一个挡板、屏幕、背景,它阻碍、抵抗、反向击打被给予者,从而把呼唤所释放的冲击力平摊开,因为给予的冲击是纵向的,显现就是把给予的力量平面化[8](p76)。要想获得更多的被给予性或者使事物自身显现更多,就必须依赖于受予者的抵抗程度。受予者越是抵抗,就越是将自身完全敞开、暴露在这一呼唤中,现象的显现程度就越高[8](p78)。而变形则意味着呼唤和回应的双重变形。马里翁指出,“显现是根据一个内在的轴线而展开的,如果要接收显现,我就必须对齐这一内在的轴线——所有这些都定义了被给予的现象的本质特征,它的变形”[7](p123)。当我移动自身,以便找到那个最适合现象显现的点时,现象和我的双重变形就实现了,现象也就显现出来了。首先,总的要求是我必须转换视角(空间、时间,或者别的视角)去适应事物自身的呼唤,要消除自身的意向性、自我意识,投入充溢现象中去。其次,我在变形中要进一步让现象的给出深入我的内在之中,并且让它比我自己更能了解自身,让现象自身庇护我、压迫我、拥抱我、强加于我。再次,在呼唤压向我的时候,我要找到正确的视角、切入点去抵制它们,并且使用、理解它们,最终要习惯它们。“习惯本质上意味着我们必须让自己习惯于适应它们。”[9](p4)习惯并非现象上的习惯,而是投身于呼唤并习惯于这一转向。最后,在现象压迫我的时候,它不停地变形,我也相应地变形,两者之间的互动使得现象从自身给予上升到了自身显现。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马里翁的纯粹呼唤结构不仅将呼唤回溯到了纯粹的无限性上,同时也将回应者回溯到了原初性上,即回应者是先于意向性主体或者此在主体的那个原初性主体。这就导致主体所显现的现象不再是胡塞尔所主张的由意向性构造的客观现象,也不是海德格尔所关注的存在现象,而是那个在显现和显现者两端都没有任何限制的现象自身。这样,马里翁所通达的就是事物自身的绝对被给予性,所显现的就是现象的真正自身。正是在这意义上,马里翁首次实现了绝对的被给予性原则。
综上,我们从“呼唤—回应”结构的三个一般功能角度呈现了它的一般运作及现象的可能。那么,这一结构又如何落入了亨利的批评中呢?
二、“呼唤—回应”结构与出神结构
如上文所述,亨利对“呼唤—回应”结构指责的核心在于呼唤与回应之间是有出神距离的,诠释这一距离的关键在于对出神的理解。亨利所指的出神是从意向性中引出来的,马里翁在《笛卡尔问题:方法与形而上学》(Cartesian Questions:Method and Metaphysics)中对亨利所言的“出神”有明确的阐述。马里翁指出:“我思,它总是意味着思维是出神的,通过从我思出发而游离自身,我思设定了作为它的对象的东西。”[10](p97)也就是说,我思依照意向性结构包含了一个与自身相异的思维对象,表象就在这里拉开了与我思的距离。所以,我思要去朝向、构造表象,它意味着思维与表象的距离。意向性的出神所呈现的是一种分离,而不是统一,它必须跨越自身去击中那个对象。尽管这一对象在胡塞尔那里经过还原被摆在了意识的内在性中,但在《显现的本质》(The Essence of Manifestation)中,亨利认为,这一还原根本不会被意向性自身所克服,因为意向活动的意向对象毕竟不同于意识自身。“在意识的范畴下,这种唯一的存在被赋予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给出了视域的展开性,这正是超越性的任务,在这样的视域形式下,超越性原初地构造了通往所有可能的客观性的纯粹路径;另一方面,它是所有超越性的根基,是那个唯一存在者。”[11](p21)同样,亨利认为这种出神同样也适用于海德格尔所言的存在。亨利认为,存在是此在必须超越自身才能把握的东西,此在为了获得自身的存在就必须出神。他强调:“存在只有在与自身保持一定距离时才是一种现象。现象学距离的运行被视为一种存在论力量,它是一种正在展开的距离,而不只是已经铸造好了的距离,恰恰由于建立了这样的间隔,存在才可以向自身显现。”[11](p66)这就意味着此在对存在的看不在自身之内,而在显现存在的这个显现者之外,此在为了显现存在的现象就必须跨越存在与此在的差异性距离。然而在亨利看来,要想逾越这个距离是不可能的,因为此在对存在的出神根植于现象显现的根本结构——存在与存在者的存在论差异之中。总而言之,出神的关键在于它总是某个主体的出神,它依赖主体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实现的是外在性、他异性,而不是内在性或者自行—感发。
那么,亨利又是如何将出神距离引到“呼唤—回应”结构上的呢?亨利指出,马里翁为了释放被给予性,将还原推到了极限,这个极限就是“一般形式化的呼唤本身”[5](p17)。但马里翁的这种做法与他所坚持的现象学的第四条原理“越多的还原。越多的被给予性”相矛盾。亨利指出:“第四条原理不是简单地把还原推到极限,把存在者还原到存在本身,然后再把存在的呼唤还原到一个不确定的X,还原到样式,一个纯粹的形式、绝对性上,或者还原到以纯粹形式的方式定义的超越性上。相反,它导致了被给予性和它的最高点,铸造了最原初的显现。”[5](p17)换言之,马里翁建立第三次还原的核心在于实现最高的被给予性,而不是要还原到某个纯粹的不确定的形式——呼唤本身上。这就导致还原方法与还原结果不一致,因而马里翁错失了还原所带来的成果。在这里,亨利对马里翁解读的关键在于他将纯粹呼唤与超越性画了等号,亨利实现了“不确定的X”“样式”“纯粹的形式”“超越性”之间的等同,并且把“超越性”放在最后加以强调。这恰恰说明在亨利心中,马里翁从海德格尔存在的呼唤中脱离出来所作的还原最终还是要恢复与存在一样的超越性,最终不仅没有真正通过还原实现现象的原初显现,反而犯了与胡塞尔、海德格尔一样的错误——设置出神的外在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亨利进一步认为“呼唤—回应”结构无非就是主体—客体结构的置换,本质上依然没有越出主客结构的形式。“呼唤—回应替代了经典的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并且凭借这种替代,要求更新了我们与存在的关系……”[5](p18)
具体来说,亨利将出神移位到呼唤上离不开两个重要的步骤。第一步在于将思维类比为回应,这样的话回应就是“我”的回应,它总是以期待、预期的方式朝向呼唤,并等着对呼唤进行回应,这与我思朝向表象是一致的。而这种趋向设定了呼唤与回应间的距离。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亨利说马里翁用“呼唤—回应替代了经典的主体—客体的二分法”才是成立的。亨利的第二步在于析出出神的超越论结构。这个超越性在形式方面实际上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二元性的双方互为超越,但在具体形象中,总是一个对另一个的超越。于是在意向性的出神中,胡塞尔区分了实在的超越和实项的超越,而在“呼唤—回应”结构中,马里翁设定了呼唤对回应的超越。亨利指出:“马里翁的呼唤结构远远没有摆脱存在的呼唤和他隐含的现象学,而是从这种现象学中获得了它自己的结构——出神的对立。”[5](p19)通过这两个步骤,呼唤结构就是一种出神的距离结构。
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亨利进一步认为,既然马里翁没有摆脱海德格尔存在的呼唤的出神距离结构,那么就没有必要坚持纯粹的呼唤。亨利在此实际上动摇了马里翁的现象学基础,导致其从纯粹呼唤推出被给予性的合法性的做法受到了质疑。因为在《还原与给予》中,马里翁正是通过“深度无聊”对海德格尔存在的呼唤和此在进行悬置,才得出了一般的呼唤——被给予性自身的呼唤的。亨利敏锐地看到了马里翁对海德格尔的还原的“缝隙”,即海德格尔存在的呼唤不再适用于一切呼唤,由此过渡到了“存在的呼唤之外”,那么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在纯粹呼唤之外的非呼唤”的原初性呢?亨利指出,这种非距离且非呼唤的原初性,就是生命。生命先于所有的回应,它在自行—感发,而且首先向我们袭来的不是别的,就是生命的贯穿。生命与我们自身不再有任何距离,它并没有某种一般的“呼唤—回应”结构,这导致没有回应的空间,生命全部压上“我”。“如果在这并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允许我们承担或拒绝存在的命运,那是因为,严格来说,我们不能再恰当地谈论呼唤……生命的呼唤已经把我们抛向了生命本身,在一种不可克服的悲怆的痛苦和欢乐中,把我们压在生命和我们自己身上。”[5](p19)因而,从原初性上看,生命的自行—感发自然就先于被给予性所施加的呼唤与回应的距离,或者说,先于纯粹呼唤造就的“异质—感发”(hetero-affection)。亨利认为,正是在这里我们才把握到了现象学还原的真正意义,还原要实现的是从出神距离到非出神距离的生命的跨越,只有这一生命才是真正的原初现象,才实现了第四条原理所彰显的最大的被给予性。
三、马里翁对亨利的回应与可能的补充
以上,我们呈现了亨利对马里翁的呼唤结构的质疑,这一质疑最终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方面,现象学还原的第四条原理不再适用于被给予性现象学,因而马里翁极其倚重的第三次还原变得无关紧要;另一方面,“呼唤—回应”结构无法实现现象的原初性,它与生命相比无法真正展开现象自身。鉴于此,马里翁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一质疑。在写作《既给予》、《论过剩》(In Excess)、《情爱现象学》(The Erotic Phenomenon)、《否定的确定性》(Negative Certainties)等现象学著作前,马里翁就对亨利的这一批评了然于心。然而直到亨利去世十多年以后的2015年,马里翁才真正正面回应了亨利的质疑。马里翁在《还原和“第四条原理”》(The Reduction and “the Fourth Principle”)中对亨利的批判进行了回应,马里翁认为,“呼唤—回应”结构并不具有亨利所说的出神结构,而是非出神的,在呼唤与回应之间事实上没有任何出神距离。“要求的条件和规定的原初缺席使得它能发出没有任何限制的呼唤。”[1](p204-205)总体上,马里翁是从以下三个角度切入的。
第一,马里翁认为,亨利的第一个误解在于,他止步于回应的预先等待,错失了“呼唤—回应”结构的非出神性。按照马里翁的表述,亨利所批评的呼唤结构的出神恰恰是由意向性带来的,而意向性在呼唤结构中就是回应对呼唤的预先等待。但马里翁强调,呼唤结构在回应层面上是非出神的,也就是受予者与呼唤的显现是无距离的。回应的预先等待与倾听会使一种静态距离蔓延开来,从而错失呼唤的非出神性。马里翁认为这一预先等待导致两种分离:第一种分离是受予者的倾听与呼唤的分离。他以等待晨曦的人为例,“如果他正在等待着晨曦,那么他就已经在守望着;如果他已经在守望着,定然是由于他此前已经被唤醒(éveillé)过一次,也就是说他被一个他已经回应过的不同的呼唤所唤醒了:他一定会承认,太阳定然在每个夜晚结束时会回来……”[12](p50)换言之,如果受予者在预先倾听,那他就已经用意向性规定了呼唤,造成了分离。在这个意义上,世俗的时间性被引入呼唤结构,正是因为呼唤在先,它才需要我去等待、预期,而回应则是延迟的。这种设定并不符合呼唤的“反—意向性”,回应并不是像期待一样是预期、可重复的,而是不可预期、偶然的,因此第一种分离并不存在。第二种分离是受予者自身的分离。按照亨利对出神结构的表述,如果主体要回应呼唤,主体自身就必须分离,否则向着呼唤的出神就是不可能的。但纯粹呼唤结构真的具有这层分离吗?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受予者正是在接受呼唤的一刹那给出自身的,即受予者的抵抗、变形导致受予者和呼唤是一同显现的,“一下子就激发出双重可见性”[8](p50)。因而,在接受呼唤的过程中,受予者、回应、呼唤的显现是没有距离的,这就使亨利的设定失效了。亨利第一个误解的核心在于,他一开始就错失了我们讨论过的充溢现象的呼唤以及它所展开的可能性——意向性的颠倒。
第二,在马里翁看来,亨利的第二个误解在于他并没有看到呼唤的匿名性所引发的非出神性。在纯粹的呼唤中,呼唤具有以下三种特征:(1)不确定性。“因为我并不会马上认识到是否真的有呼唤。”[12](p53)呼唤具体是什么,仍然未得到确认,可能是某个噪音。(2)呼唤是匿名的。我不清楚呼唤的来源和去向,我只能投身于呼唤中寻找呼唤的确认。(3)呼唤是缄默的。“因为只要我不确定它的意义,它就不会告知,以空形式呈现。”[12](p51)最终,这使呼唤并不会预先以某个具体的形象显现,而是在回应中与回应同时进入现象性,呼唤与回应共属一体,并无时间上的距离。“呼唤只有在回应中完成,而没有回应,它就不可接近。”[12](p53)马里翁在此想强调的是,只有“受予者的给出”不停地对“事物自身的给予”进行着抵抗,在抵抗或者回应中,呼唤才作为“现象的显现”呈现出来,才成为具名的“上帝的呼唤”或者“他者的呼唤”。否则,只要不回应,呼唤就将永远保持着匿名和不确定的状态,就无法成为主体出神的超越性,因为它的显现与回应是同时的。这再次说明了呼唤与回应之间不存在出神的间距,亨利的批评是存在问题的。
第三,马里翁认为,亨利颠倒了现象的原初性。亨利错误地认为呼唤结构是一种出神结构,所以才把没有这一出神距离的生命现象看作是最本源的现象。但是,亨利的生命现象真的是本源现象吗?马里翁从两点进行了反驳:(1)在亨利的生命现象学内部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无距离,而是存在着分裂。马里翁指出,对亨利生命现象学的常见批评是它导致两种不相容的现象,“事实上,他甚至声称,在‘出神的真理’和‘非出神的自行显现’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双重现象学’,而这构成了‘生命悲怆’的本质”[12](p56)。因而,亨利也没有完全摆脱这一距离。(2)亨利所言的生命现象不仅不先于纯粹呼唤,甚至就是由呼唤造就的。“由于第四条原理(和它在呼唤与回应结构中的推论)并未假设现象性的出神,它不仅没有落入亨利所批评的陷阱中,并且还可能单独设想出生命的非出神性的现象性。”[12](p57)在马里翁看来,亨利的生命现象学意味着对于每个人而言,生命是突然而来的,无法逃避,也没有距离,甚至没有延迟,它与我是绝对亲密的。这恰恰说明回应总是在既成事实中进行回应,因为当我们进行回应的时候,呼唤总已被强加给我。呼唤的事实性在原初性上先于亨利的生命现象学,后者只是回应的既成事实的显现,只是在呼唤结构中的自行—感发。马里翁由此将生命现象学放在了呼唤结构之上。
然而,对照我们已经呈现的“呼唤—回应”结构,除了马里翁提到的误解之外,亨利至少还在以下两个方面出现了对马里翁的误读。
首先是视域问题。亨利对呼唤结构的视域的理解与马里翁是有严重分歧的。在亨利看来,“呼唤总是被规定的。呼唤的规定是现象学的,它每次都在其实际的现象性中被耗尽,但是现象学却永远不会被耗尽”[5](p18)。亨利在这里提到的“呼唤的耗尽”与“实际的现象性本身的不耗尽”意味着两种不同视域的现象学。第一种就是马里翁所说的呼唤,由于它带有视域的出神,产生的现象便总是显现者之外的现象,因而是会被耗尽的。而实际的现象性由于不带有视域,才是最原初的、自行—感发的、不耗尽的现象。显然,亨利的这种解读并不符合马里翁的原意。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表明,马里翁在呼唤结构中所要建立的是没有视域的事物自身。这个视域意味着,不仅对于呼唤我们不能施加任何限制,对于回应也不能添加限制。正如马里翁在《还原与给予》中所指出的,主体在回应中“依据的只是绝对无条件的呼唤的视域与绝对无限制的回应的视域”[1](p204)。亨利对马里翁的批评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其次,受予者会遭受呼唤带来的惊讶或者意外。在马里翁看来,意外是一切出神的对立面。“毫无疑问,如果出神是在主体自身之外来建构主体,除非只从主体出发,并促使它回到自身,否则出神永远不会将主体外在化。”[1](p201)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出神要通过某种距离把握主体之外的东西,出神就必须设定它不仅从主体出发,且能够返回主体。因为无论在何种状态(存在论状态或者意向性自我状态)中的出神,它的出发点总是自身。为了不引起自我的分裂,它就必须在出神后返回自身。正是在这里,马里翁认为出神不同于意外,因为在遭受意外时,主体自身不仅无法再出神,而且也不能谈论从外在性的返回问题,它只能陷入意外之中。马里翁说道:“相反,意外从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和事件出发,抓取了被呼唤者,以至于取消了主体的任何构成、重构或者确定这种令人意外之物的意图。”[1](p201)意外不是主体引发的意外,而是从一个陌生的地方向我袭来。“我”还没有准备好,甚至没有任何准备,对突然而来的事件或者呼唤只能感到惊讶。马里翁认为,意外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抓住”被呼唤者的:(1)“主体”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主体性”,意外剥夺了构造的极,从而为接受意外作准备。(2)意外以事件的形式坠落到被呼唤者身上,被呼唤者无力占有或把握这一事件,甚至完全不理解事件,对此他只能目瞪口呆。亨利显然没有看到马里翁为回应者所设定的意外特征。
至此,我们依照马里翁的思路考察了他对亨利的批评的回应以及我们进行的可能的补充。然而,不论是马里翁的反驳还是我们的补充性回应都集中在出神的距离上,从表面上看似乎已经消除了亨利的误解,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已经彻底反驳了亨利的出神性指责吗?
四、对马里翁回应的质疑与进一步的补充
我们不能不产生一些疑问:即便“呼唤—回应”结构没有意向性的出神距离,那它是否还具有一种别的距离,即不同于出神距离的非出神的距离?因为出神总是与意向性有关,或者在呼唤结构中总是与接受呼唤的那个“我”有关。这样的话,如果只是为了反驳与“我”有关的出神距离,马里翁只需要在自我的层面或者回应的层面反驳亨利就足够了。换言之,马里翁对出神的意向性从呼唤的回应层面进行颠倒就可以了。从马里翁的三个辩护来看,他确实没有离开回应层面。比如第一个辩护,马里翁是从回应的非意向性以及抵抗层面来澄清的。马里翁说:“呼唤的接受者被这种呼唤所唤醒,并同呼唤一同显现,从他们自身的缺乏之深处突然迸发。”[12](p57)而第二个辩护虽然看似从呼唤的匿名性角度切入,从自身给予入手,但是马里翁的结论仍然落在显现层面。他说:“只有当回应将呼唤建构为某种可以被听见或看见的现象时,呼唤才会显现,否则呼唤不会单独显现。”[12](p58)最后,马里翁的第三个辩护是从呼唤的既成事实角度来囊括亨利的生命现象学的事实性的。虽然既成事实体现了呼唤的特征,是事物自身给予的层面,但正如马里翁在《既给予》和《论过剩》里所讨论过的那样,“现象的既成事实总是让我无法逃离”[7](p123)。既成事实意味着它被强加给我,我无法逃避,既成事实的表现就是事件,因而也归属于显现层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马里翁对亨利的反驳只在表面上有效,因为从深层次上看,马里翁还必须说明,现象自身不仅没有出神的距离,甚至连非出神的距离也没有。或者说,这个距离不仅在现象的显现层面不存在,而且在现象的给予层面也不存在。那么,这是可能的吗?
这样的质疑其实很容易从马里翁的“呼唤—回应”结构中引出,因为亨利对生命现象学的非出神距离的处理完全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进行的。也就是说,亨利认为,生命现象不仅不具有出神的距离,而且甚至没有任何间距,哪怕是一种非出神的距离也没有。亨利指出:“因为在生命的突然袭来中,在生命中——它贯穿我们,让我们因为它而流动。生命与我们没有任何间隔,没有任何能够后退的距离……”[5](p19)这里的距离完全被消解,生命在自行—感发。显然,为了彻底驳斥亨利,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回应两个问题:其一,马里翁的“呼唤—回应”结构到底有没有非出神的距离?其二,如果“呼唤—回应”结构确实存在着距离,这种距离还能够再一次统一亨利的生命现象学吗?
我们认为,在马里翁的现象学中,单从回应的显现层面看确实无法找到一种非出神的距离,除了上文马里翁自己的辩护以外,我们可以直接回到被给予性原则来进行说明。马里翁在《论过剩》中指出:“一切现象都显现,但只有就它们自身显现而言,它们才是显现的。”[8](p30)这里的自身显现在层次上还同自身给予相关,显现就是自身给予上升到自身显现。由于被给予性的普遍性,“任何自身显现都必须首先自身给予”[8](p30)。因而,在显现层面,被给予性与显现是没有任何距离的,因为不管如何显现,不论是胡塞尔的客观对象,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它们都首先被给予了。
而如果我们返回到给予层面,则会发现一个距离。马里翁自己强调:“解释学具有这样的强制性地位和功能:它以回应(概念或符号)解释呼唤(通常是直观),由此管理着自身显现和自身给予之间的间距。”[13](p39)甚至在“呼唤—回应”结构中也存在着这一间距或者距离。在马里翁看来,一方面,呼唤可以发出,但不一定得到回应,因而呼唤就不会进入显现的现象性层面。另一方面,回应总是有限的,无法完全重复、把握过剩的呼唤。呼唤在逻辑上总是先于回应的,两者之间具有不平等的关系,每一次回应都落入呼唤之中,回应却无法将所有呼唤显现出来。回应是不可选择的,但是回应的意义却是可以选择的。“回应施加的意义可以被选择、被规定,然后以偶然的方式降临,但是回应并不是一个能进行选择的行为,一个任意的选择,或一个偶然性——在其中,我们存在、生存着,并接受自身。”[7](p288)呼唤与回应之间的间距还通过另一个层面表现出来:在马里翁看来,呼唤与回应之间存在着绝对的距离。这一距离是由呼唤的过剩和充溢导致的,并且这一距离使回应具有延迟性。马里翁强调:“如果呼唤总是直接被给予,而没有显现自身——没有成为一种现象——除非在回应中它才能成为现象,那么一个本质性的悖论就产生了:回应完成了呼唤,但它是迟来的——相对于自身给予者而言,它推迟了它的显现。”[7](p289)通过这些例子,我们看到,在现象的给予层面,马里翁确实设定了自身给予与自身显现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是原初的,它先于任何时间性。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差异或者间距能够被统一吗?
在马里翁看来,被给予性总是通过一个褶子运作起来的,因而统一了自身给予与自身显现。他指出:“因此,自身显现就等于自身给予。‘被给予性’的褶子在展开自身的过程中展示了被给予性所给予的东西。对现象来说,自身显现等于展开被给予性的褶子,被给予性在其中作为一种礼物出现。自身显现和自身给予是在同一个领域中进行的,即在被给予者中展开的被给予性的褶子中。”[7](p70)这个褶子意味着,被给予性总是通过给予活动给出一个被给予者,而被给予者又总是在给予活动中确证被给予性,现象就意味着它在自行给予和自行显现,这进一步导致:(1)被给予性并不在被给予者给出之前单独存在;(2)被给予者并不在接受之前自身存在;(3)现象的显现(或者被给予者的给出)并不在被给予性和受予者对话前单独存在。因而,自身给予与自身显现的间隔只是被给予性自身的内部解释,是给予活动自身运作的差异,是它的被给予性程度的区别。被给予性自身并没有设定绝对不可弥合的距离。在显现层面存在着较小程度的被给予性,在纯粹给予层面则存在着较大程度的被给予性,它们都统一在被给予性自身中,不存在任何超越性的元素。
而且,为了进一步弥合这种所谓的距离,马里翁引入了解释学。在马里翁看来,解释学与回应是同一的,被给予性解释学存在的意义就是进一步展开被给予性的统一。马里翁从四个方面展开解释学:第一,呼唤总是匿名的,它不一定通过物理声音或是任何可见性显现出来,它总是需要受予者对其进行解释,从而确定呼唤是什么。“因此,我在我的解释中并通过这种解释听到了这个呼唤:我必然要确定有一个呼唤,并把我自己规定为它的接受者;只有这样,才会允许回应,即便是通过回应来拒绝。”[13](p41)因而,解释学的第一个效用在于消解呼唤的匿名性所衍生的距离,呼唤必然成为回应中的现象的礼物。第二,呼唤总是充溢现象的呼唤,但是充溢现象如何被把握和显现是需要解释的,解释学的第二个效用就在于通过回应的解释将对象转换为充溢现象,从而消除现象与回应者(或者显现者)之间的距离。第三,解释学实现了现象自身的连贯性,而不是将现象割裂为几种分裂的现象。这与亨利将现象分为出神的现象与非出神的现象是不同的。在马里翁看来,“从贫乏或普通现象到充溢现象,完全属于解释学的领域”[13](p44)。我们不能像形而上学一样设定贫乏现象、普通现象、充溢现象之间的绝对距离。第四,解释学“将一切现象分成对象或者事件,它也将对象转变为事件,或相反把事件转变为对象”[13](p44)。换言之,解释学在对象和事件之间实现了统一,胡塞尔的对象现象与马里翁的充溢的事件现象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关键就在于主体如何通过解释学去释放被给予性,从而实现现象的统一。
综上,经过被给予性的解释学,我们进一步说明了被给予性自身的统一性,而不是距离的分裂性。正如马里翁在《被给予性的解释学》(The Hermeneutics of Givenness)的结尾中所说的那样:“只有通过实施合适的现象学诠释学,被给予性的现象学才能处理自身给予与自身显现之间的间距,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把握到现象的自身。”[13](p45)马里翁强调的这个关键恰恰对应了亨利的误解的核心——亨利并没有看到事物自身(被给予性原则)在统一呼唤与回应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而言,尽管亨利强调生命现象没有出神的距离,甚至没有任何间距,但是他仍然不能摆脱被给予性的范畴。因为,生命现象的视域仍然囚禁着那个“我”,生命首先需要被给出才能压向“我”,才能在“我”身上显现。唯有统一了自身给予与自身显现的,没有任何视域[7](p199-212),也没有任何真实距离的事物自身,才是现象的典范。
五、结语
至此,通过这些质疑与补充,我们进一步强化了马里翁的结论:在“呼唤—回应”结构中,或者说在自身给予和自身显现之间并没有出神的距离,也没有任何真实的绝对分离的非出神的距离,显现与显现者是统一的。亨利的出神距离的批评并没有把握到马里翁“呼唤—回应”结构的核心,恰恰相反,马里翁凭借被给予性原则的褶子的运作,不仅使“呼唤—回应”结构成为现象的根本结构,还彻底释放了还原的意义——被给予性的最大实现与现象自身的显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里翁才在拓展现象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把海德格尔所说的“现象学的可能性”[6](p45)推向了新的高度。
——兼论现象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