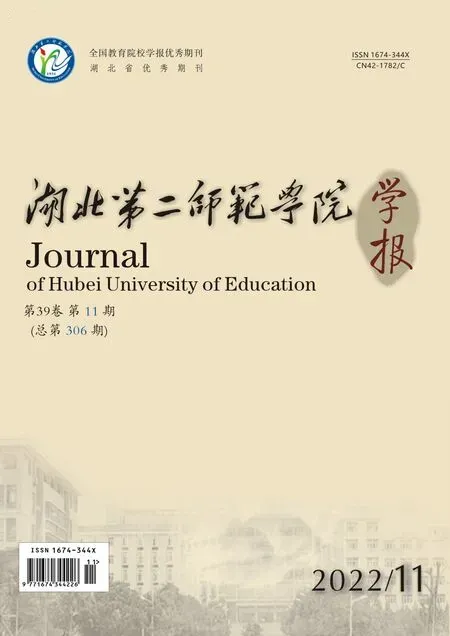墨戏沉雄: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笔墨的 “沉着痛快说” 研究
谢九生
(江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南昌 330022)
对于明代徐渭的艺术及相关研究已经十分的充分了,尤其是他痛苦不羁的人生与横绝古今的大写意花鸟画等,因而其作品 “本色论” “真我论” 和 “心性说” 等也已经被现代的研究者所津津乐道。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徐渭的戏谑、狂狷、怪异、侠义和悲苦的多面艺术人生表现出矛盾性的特征,而且他的人生的遭遇在其书画艺术之中的投射是十分明显的。而从中国写意画的角度看,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的笔墨仍然寓法度于狂放之中而体现出 “沉着痛快” 的中和之道,他以戏谑的伪装保护着自我之本真而在绘画之中表现出理性与感性的完美契合。虽然有论者认为是他的绘画造型能力不够而反复地画那些葡萄、蔬果等花花草草,以今天的角度看不够准确到位[1]15,但是中国写意绘画就是强调在 “似与不似之间” 的气韵生动和痛快淋漓。因此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的笔墨可以概括为 “沉着痛快” 的共性特质。
一、游戏与痛苦: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的 “墨戏” 人生
徐渭悲苦的人生多在其戏谑的游戏心态下获得宣泄, “因为‘游戏’,所以不拘法度,他要求一种率性而为、任意涂抹的痛快的创作方式,只有心中的感情得到宣泄才得以满足。”[2]70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的 “墨戏” 人生是痛苦的,因此只有逃入艺术创作之中这种 “痛苦” 才可能演变成 “痛快” , “游戏心态” 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否则必然无法生存下去,徐渭的人生就是典型的个案。因而 “游戏笔墨” 的徐渭必然会沉浸于文人绘画 “不拘法度” 的艺术理念之中,同时也与他的 “墨戏” 相当吻合。但是,这种 “不拘法度” 并不是不讲法度,而是在高度技巧的基础上对于技巧或法度的超越,这也是中国 “写意精神” 的要求。因为这种 “超越” 使得法度和技巧已经化在创作者的骨血之中,而且游戏的创作心态正是 “游于艺” 的传统要求。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提出 “游于艺” 的观点,儒家学派强调 “艺术” 是小道,对于观者来说是一种娱乐、欣赏活动,因此具有审美自由的传统认识, “艺” 主要是指古代的 “六艺” ,并且与道、德、仁是相辅相成的。当然由于游戏在古代是属于 “艺术” 的范畴,因此,也与 “游艺” 或游戏等有着紧密的关系。
而且,古代游戏文化的发展与传统艺术演进是相辅相成的,在本质上都是对于自由的向度,因此在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创作中其游戏的心态,其实是对于自由的向往。而现实的不幸和痛苦则是这种要求的绊脚石,这也可能是他多次自杀而寻求解脱的原因。同时,游戏也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并扮演了重要的力量,而且中国古代艺术与游戏文化也在艺术的 “游戏性” 和游戏的 “艺术性” 的密切关系中契合在一起,因此 “游戏” 也是 “戏谑艺术” 的理论基础之一。而 “游戏冲动” 与 “审美冲动” 虽然有许多共性,但是也有着不同,就是 “游戏冲动” 或 “游戏过程” 是基本没有痛苦,而只有快乐的,而在 “审美冲动” 之中有痛苦,而且这些痛苦可以为最后的快乐加持。因而审美冲动所带来的快乐既有 “痛并快乐” 的强烈对比的感觉,也可能给予创作者以极乐的 “痛快” 感受。
首先,徐渭的戏谑人生是一种痛苦的解脱,而表现在艺术创作之中的 “道在戏谑” 。徐渭怀才不遇的痛苦遭遇使得他不得不抱着 “游戏” 的心态来面对人生逆境,从而形成一种戏谑人格,同时这也是一种保护真我的手段。而越是身怀奇艺,则越与残酷之现实形成巨大反差,也就自觉地以 “游戏心态” 来麻痹自己,戏谑之后也多是万念俱灰,因此只有在艺术之中获得快乐。其次,艺术创作者必须在高度娴熟的艺术技巧或法度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优秀的作品,而大写意绘画就是在 “似与不似之间” 、以书入画的总体要求下把长期修炼的艺术技巧或法度以一种自然而然的下意识的本能冲动的形式反映在画面之中。再次,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艺术家们常表现出反复制作的现象。而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创作也是如此,他反复表现相同的事物或母题,包括题画诗也是反复出现在同一题材的画面之中,其构图看似简单,却变化丰富而不露痕迹,大写意的 “狂扫” ,恣意纵横,狂放不羁。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的笔墨所呈现出的 “墨戏” 特征,需要在笔墨技巧与功夫方面有着大量的艺术实践,才可能在用笔和墨法方面达到纯熟的程度。更高的阶段是忘却笔墨而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徐渭则以 “游戏” 的心态使得自己进入这种心斋状态,从而忘却前人笔墨传统,表现真我的性灵。
一方面以水墨来作为绘画艺术的主要手段,在明代之前已经有着比较深厚的传统,如南宋梁楷、法常等人的 “减笔画” 等。而徐渭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变革或创新,以其旷世奇才开大写意花鸟画之先河,呈现出狂逸、沉雄的画风。所谓 “沉雄即沉毅而雄健,也就是沉着痛快”[3]16,因此,沉雄或沉着痛快是对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笔墨的风格概括。另一方面中国绘画艺术中大写意中的 “泼墨” 或 “破墨” 等笔墨技巧不仅需要长期的学习与训练,同时也需要天赋与灵感,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在水墨的偶然性之中,创作者必须要使其成为某种必然性,才可能进入方便法门,否则可能永远在门外。特别是在生宣纸上有着无限的变化生机,而且宣纸水墨或水墨淋漓的天趣和化意,特别需要极为丰富的学养、敏锐的悟性和谨严的法度,而 “徐渭将‘趣在法化’的偶发效果推向极致”[4]68。因此,画面中 “欲达到沉着痛快,又必于法中求之。”[5]46因为 “游戏笔墨” 的创作情态如果没有法或高度技巧的支撑则多会坠入虚无之境,即齐白石所论的 “欺世” 。同时, “道在戏谑” 或 “趣在法化” 则使得水墨大写意绘画的偶然性成为某种潜意识下心手合一、自然而然的必然性。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 “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盥手涤砚,如见大宾,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而后有成。”[6]23这种 “心斋” “坐忘” 般艺术创作状态的获得需要在 “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盥手涤砚” 的外在条件下,驱使艺术家内在心理达到 “涤除玄鉴” 般物我合一的忘我之境。而且在重复始终和禅定神闲的惨淡经营之后的快乐是无以复加的,同时也不断增加了最后快乐的阈值。因此,郭熙的 “快意说” 其内在是 “沉着痛快” 的特性,而且郭熙也强调 “以书入画” 的写意追求。而对于大写意绘画来说,这种重复每一图(题材或母题)的方法是作者在反复地寻找这种 “必然性” 画面效果的独特方式。如徐渭代表作《墨葡萄图》(图1)就反复画过许多次,这也是其探索精神的体现,画面中水墨淋漓的效果恰到好处,其对于笔中水分的变化和用笔的轻重缓急有着极高的要求,而且这种绘画方式一旦出现错误就无法纠正,体现出即兴性与不可逆性的特点。因为在中国传统绘画之中,写意或大写意绘画多被认为是最高技巧的体现,落墨之后全凭胸有成竹的笔墨经验和技巧,这种技巧必须反反复复地实验或体会,包括用笔的速度、笔中水分的多少等,同时也需要相当的天赋和感觉。

图1 《墨葡萄图》
从某种角度看,徐渭反复的训练似乎显示出他在造型等方面有所欠缺,因此才有论者对于其造型能力的诟病。但是,对于强调在 “似与不似之间” 的造型理念之中的写意画而言,斤斤于外在的形是否准确是不对的,而应强调在转瞬即逝的瞬间忘掉笔墨或技巧而表现出画家艺术本真的魅力,这也正如中国传统绘画对于画如其人所推崇的,就是强调艺术家整个人生和才情的体现。
因此,在《墨葡萄图》中徐渭反复探索泼墨、破墨等对于墨色的水分度的掌握,使得水墨技巧和笔墨形态一方面呈现出葡萄之晶莹剔透的神韵,并在 “似与不似之间” ,追求笔墨的 “酣畅淋漓” 。另一方面, “以书入画” 的书法用笔所体现出的抽象意味在 “一笔到位” 的 “狂放” 之中把艺术家的内在情绪宣泄出来,但是这些看似 “放纵” 或 “率意” 的自由仍然寓于法度之中,因而对于水墨大写意绘画而言,狂放与放纵似乎人人都可以达到,但是真正的高超之处在于把握其中的 “度” 。因此,徐渭大写意花鸟画所具有的探索精神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已经走在了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沿。何等酣畅!何等痛快!……把穷愁和悲苦挥洒在画卷上方: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7]122
徐渭的绘画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大写意精神,不仅是在明清时期,而且到了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徐渭的大写意精神仍然是以儒家艺术观为主而衍生出的屈骚美学,特别是当艺术家的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激愤多成为其艺术创作的主调,从而表现出狂放纵意的精神面貌。因而 “徐渭的人生和艺术就是屈骚传统的审美宣言。……并进一步诉诸如‘狂似扫’的大写意。”[8]24-25这种 “狂扫” 大写意以中侧锋用笔为主,强调水墨淋漓的化机,同时在主观上追求 “游于艺” 的创作状态,因此从宋代以来多被称为 “墨戏” 。然而,元代以来也多被认为不是文人之 “雅玩” 而受到贬斥。其中的原因多是过于 “狂纵” 而易坠入 “荒率” 。因而在技巧与法度方面仍然要在某种 “度” 的范畴之中,也即是在这种戏谑的 “狂扫” 之中仍然有着谨严的法度和高度的技巧, “徐渭以水墨来写人生的戏,是为‘墨戏’。一片淋漓的水墨”[9]68,因而在徐渭 “墨戏” 的 “痛快淋漓” 之中仍然符合中和之道的传统特征。
二、沉雄与共鸣: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笔墨 “沉着痛快” 的共性特征
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中 “‘沉着痛快’所体现出的矛盾和张力,无疑是偏向于内在的,相反而相成的内容,处于不断调和之中,努力遵守着一种中庸、中和之道。”[10]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总体要求,矛盾产生的目的是调和,是变化丰富的中和之道,而非是某一种风格或范式的单一或统治,因而在不同的时代、阶段或时期,就可能有不同的 “沉着痛快” 。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笔墨的 “沉着痛快” 既有着狂放不羁的张力,又有着极强的控制技巧而停留在恰如其分的某种度之上。因而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要求,能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给予后来者深刻的启示和审美感兴方面的共鸣。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或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学与艺术的表现对象, “沉着痛快” 的内涵与美学特征是有所差异的,但是在 “总体上是一种沉凝中的飞动,是一种力量的克制”[10]。 “沉着痛快” 最先出现在书法艺术理论之中,张彦远《法书要录》中以及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品评皇象说: “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11]34而所谓 “‘沉着’,是就力度而言,指行笔沉稳有力,‘痛快’,是就速度而言,则指行笔之疾,酣畅流利。”[12]35由此可知,这种相反而相成的矛盾性与两者的和合性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特点,也是历代艺术创作者所追求的目标,即中和之道。书法艺术美学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学和文艺美学的统摄作用是从唐代就开始的,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艺术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徐渭自评其书法第一是有一些道理的,这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学的特点之一。在中国传统艺术之中,书画合一或诗、书、画三合一或诗、书、画、印四合一等都与书法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徐渭诗、书、画高度融合的艺术修养与技巧法度,都集成于其大写意花鸟画之中而主要体现出草书写意和沉凝飞动的意境。徐渭大写意花鸟画与其草书笔法或章法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而使得他的笔墨沉雄狂纵、气势凝练飞动,体现出其对于封建礼法的藐视与不屑。从中国绘画史的角度看,徐渭其实是把写意真正发展到大写意的开创者。从写意到大写意是一个飞跃,这种飞跃需要达到某种阈值的狂放张力,同时也需要能够控制这种张力的中和之力,才能进入某种自由之境。徐渭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在前人基础上的超越。
虽然 “徐渭曾说自己的画就是‘戏谑’之画,他甚至在画上落款‘天池山人戏抹’,意思即作画就是一场游戏”[2]69。但是,我们在其画中所能够体会到的是一种 “寓法度于自由之中” 的潇洒与飞动,因此,徐渭艺术创作中游戏心态的表现多含有自嘲和自谦的成分。当然,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艺术精神的个体反映。而且,徐渭的诗、书、画、曲等文学与艺术符合中国艺术精神的 “中道” 特征,仍然包含着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当然这种 “中” 或 “度” 的把握在徐渭的艺术之中显得更为重要。因此, “徐渭论‘中’涉及三教时则基本执守儒学之本,……透露出徐渭疏狂的表象之外尚有正统的一面。”[13]200也就是徐渭的文艺观与其书画艺术是相对应的,是 “寓法度于狂放之中” 对于 “度” 的把握。因而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笔墨既是 “墨戏” ,又不是 “墨戏” 。同时, “‘狂’、‘奇’与‘慎’、‘惧’的统一正体现了徐渭性情与思想中‘中道’的一面。”[13]19而 “徐渭确实展现了其‘奇’的一面”[14]91。这种 “奇” 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与反叛的精神,也多被贴上 “怪” 的标签。而以徐渭所留存下来的比较可靠的作品分析可知,其在传统大写意绘画中的开创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也给予后人深刻的启示。当然,这种开创表现是在广泛吸收传统的基础上的变革,因此,可以提出 “徐渭之前” 与 “徐渭之后” 的命题或概念。 “徐渭之前” 的明代沈周、陈淳等人的花鸟画,与徐渭的不同仍然是明显的,也就是写意与大写意的区别。 “徐渭之后” 的历代大写意画家都无法绕开徐渭对于他们的影响,难怪齐白石强调自己要做 “青藤门下狗” 。就今天或当代来说,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笔墨则更具有现代价值。
徐渭的 “墨戏” 同时也具有实验性和先锋性的主观追求和当代特性。因为 “徐渭的意义绝不只是他在形式上开创了水墨大写意画法,更重要的是人们从他那里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绘画开始从古典向近现代转换的最初呐喊。”[15]167因此,以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角度,徐渭之前与之后有着明显的不同,同时 “从古典向近现代转换的最初呐喊” 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近现代转换的标志,因而徐渭的艺术在古代艺术学研究之中有着尤为重要的地位。
而 “徐渭不仅以‘草书入画’还以‘草书入诗’,……画法即书法,画境有诗境,将书画融为一体,深化了艺术精神的传达”[16]86。这些是 “以书入画” 或 “草书入画” 和 “以书入诗” 或 “草书入诗” 等诗、书、画三者互相融通,同时成为绝响的 “草书主义” ,从而使得中国传统艺术朝着 “写意主义” 不断精进,而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演变路径与总体特征。
“徐渭在作品阐释中,运用其独立的笔墨语言,表达了狂啸的力量存在,……粗莽中有深沉之气。”[17]123这种 “深沉之气” 的特点就是 “沉雄” ,因而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笔墨则表现出 “墨戏沉雄” 的中和之道。同时 “观徐渭之画与读庄子之文有几分相似……在审美风格上都呈现出雄奇夸张、大气磅礴、汪洋恣肆、痛快淋漓的特征”[18]11。而越是雄奇夸张、大气磅礴、汪洋恣肆、痛快淋漓,则越容易坠入游戏笔墨和欺世盗名的泥沼之中。因此,徐渭对于大写意绘画的开创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
但在明末徐渭的画名是不显的,只是在诗歌、戏曲和书法等方面稍有影响。他去世后其才名才逐渐被时人所推崇,即使是如袁宏道等也只是强调他的诗文,而对于徐渭的画名而言,其大写意绘画仍然淹没在时代洪流之中。因此,从明末到清代初期,徐渭都是以诗文名世而被称为 “玩世诗仙”[19]94。但是随着清代以来徐渭书画作品特别是题画诗的公诸于世,逐渐扩大了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的影响力。同时在清代也出现了 “青藤白阳” 或 “白阳青藤” 等徐渭与陈淳并举的著述与评论。这些也说明陈淳和徐渭的写意花鸟画也多被并列提出,成为后世楷模。但是徐渭仍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崇,也没有获得定论。
到了清末民初,虽然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作品被诸多报刊或报纸文献所传播,但是对于其评价高度仍然是不如陈淳的,而且在当时的中国美术史教材和著作之中只是稍有提及,或多有忽略,而且就是有所著述也多与陈淳有关,或是附带提到姓名或名号而已。这与当时的美术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明清时期对于徐渭的推崇多因其为人、诗文、戏曲或书法等方面来论其绘画艺术,或是在野文人书画传承与收藏等小范围的火热。因此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美术史著述之中徐渭的画史地位都不是很高,或仅仅提及,或可有可无的忽略。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徐渭才声名日隆,同时 “其艺术价值也被学术界一致认可。”[20]66其时,画史之 “青藤白阳” 之名已成共识。
徐渭画史地位的变化,首先与其诗、文、书、画和戏等艺术文献的出版或传播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些活动使得其大写意花鸟画越来越被观众接受,当然这是其外在的因素,而内在的因素则是徐渭绘画艺术内在审美的人类共性特征,也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画家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或高度的显现成就了他的艺术地位。其次,徐渭之后历代失意文人画家因共同的遭遇与徐渭的艺术人生产生了共鸣,而使得这些失意文人画家在徐渭身上找到了发泄或宣泄的方式,从而走上了与徐渭相类似的艺术道路,如扬州画派等。徐渭画史地位的这种非自主的构建,既是接受史的主要课题,也是创作史有关共性特征的表现,其中所体现的美术观念或绘画观念是时代发展的总体趋势。当然就今天来看,这种戏谑、狂放、奇趣、怪异等大写意画风因为有着突出的个性而受到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的追捧与膜拜,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家世、身份等都无法与陈淳平齐,然而历经几百年的岁月冲刷,徐渭却受到当代人的推崇。这主要是因为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笔墨所具有的人类艺术的共性特征和精神让欣赏他的后人产生共鸣。艺术作品或艺术家是否是金子在于是否体现出了人类艺术精神的共性或永恒的精神价值,从而使得其艺术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体现出人类艺术的共同特征,即 “具有力量感,它源于人类对生命的共同感知和体悟。”[17]124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笔墨以 “墨戏淋漓” 的气势,给予后世欣赏者以极大的审美享受,这种审美共鸣所引起的艺术兴味也是其绘画艺术魅力的内在表现,同时也是徐渭以画名卓著于当代的主要原因。而 “沉着痛快” 则比较充分地诠释了徐渭绘画艺术的内在本质,这也是人类优秀艺术作品的共性特质,将给艺术创作者以深刻的启示。
三、结语
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笔墨的 “淋漓痛快” ,已经成为人类艺术的共同财富。个人永远都是在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之中而不可能绝对的孤立,艺术家应在人类艺术的 “共性” 方面着力极深,而在个性方面,由于人生事故等的作用,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本真,因而应强调对于艺术本真的唤醒或保持。本文通过对徐渭艺术及文献的分析,探究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笔墨体现出的 “游戏” 与 “痛苦” 地 “墨戏” 人生的艺术特征及其给予人们 “淋漓痛快” 的审美共性的艺术享受和启示,强调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笔墨的 “墨戏沉雄” 的 “沉着痛快说” 研究对于人类艺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认识的启示,以及突显出人类艺术的共性特征对于创作经典艺术和作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