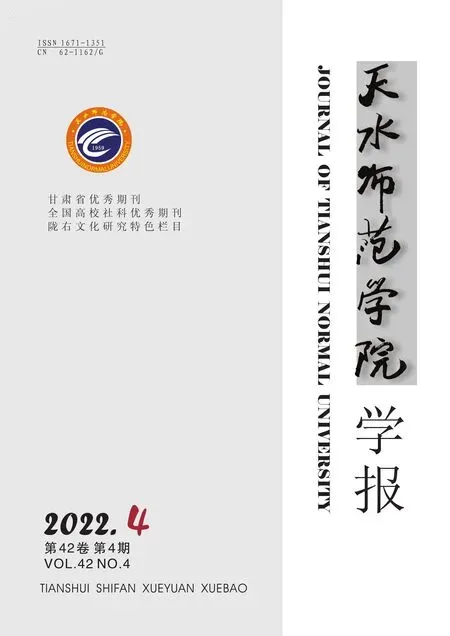“梦的解析”:汪聚应等《中国古代咏侠诗史》简论
薛世昌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江河中,侠文化是荡气回肠的一脉,侠文学奔涌不息于其中。汪聚应博士钟情于侠文学研究,他曾自述:“从少年时代的英雄崇拜到学术研究的侠文化、侠文学选题,多年来正是侠的这些仁义之德和行动人生激励与鞭策着我去做事做人做学问。”[1]521在这样的“激励与鞭策”之下,他终于学有所成:2007年出版《唐代侠风与文学》,小试剑锋。他的导师霍松林认为:“这是力图系统、全面研究唐代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的第一部专著。”2011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专著,即他锥处囊中久矣的《唐人豪侠小说集》。此著一俟脱颖,豪风扑面,豪侠之士,一时好评不断。2021年,他的《中国古代咏侠诗史》(以下简称《咏侠诗史》)由北京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一次,他不再孤勇,而是有了帮手。作为天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科掌门人,这一回他得到了霍志军博士与张文静老师的加盟和襄助。他们团队协作,完成了《咏侠诗史》《历代咏侠诗集》的著述。
一、《咏侠诗史》对侠的态度
《咏侠诗史》的著述,首先,毫无疑问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心力的工作,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挖掘、搜集、辑录,否则必有遗珠之憾;也需要进行严谨的考辨、筛选、勘校,否则必有混珠之误;其次,需要进行更具考验性的意义揭示与价值指认,否则就会浪费宝贵的学术资源并造成新的埋没与遮蔽。作为“史”性叙述,他们更重要的工作还有:对发展过程的线条勾勒、对发展阶段的板块搭建、对发展意义的清晰阐述等。所以,《咏侠诗史》的著述,其难度显而易见,其挑战剑气逼人,当然其过程应该充满乐趣——是一次不负韶光的“游侠”(游于咏侠诗)经历,而他们的辛苦工作分明地表现出以下的态度亮点。
(一)倾情的投入
历代文人,对侠义任游精神有着普遍的认同,如陶渊明之“抚剑独行游”(《拟古九首·其八》),李白之“纵死侠骨香”(《侠客行·赵客缦胡缨》),龚自珍之“一箫一剑平生意”(《漫感》)……而这样的情怀,《咏侠诗史》的三作者同样深怀兼备,他们同样渴望在自己的言说中能有热血词与激情句。他们确立了这样的写作信条:在对咏侠诗研究中探求侠士与文人的精神同构。这一信条,让他们的知识有了明确的运用方向。他们负笈而寻访天下的咏侠之诗,钩言稽沉,寻其气质与精神相通者而拥抱之,寻其轻生重义扶助弱小者而敬佩之,寻其正直公义快意恩仇者而称赞之……拜读此著,看得出他们重人生之诺如若侠士:不惜投入热情,不怕倾注心血,不惧直陈心声。
(二)真诚的致敬
《说文解字》“侠”与“俜”互训:俜,侠也。结合段玉裁注,则侠就是“轻财者”“好义者”,就是“相与信”者、“同是非”者……所以,一般人对侠有一个错觉:侠似乎与文人无关。事实上,文人与侠士,从来都是形影相随;文学与侠风,从来都是血脉暗通。《咏侠诗史》努力想证明这种相通。他们出游于中国古代的咏侠诗世界,不辞辛苦,一方面温习着那些被世人淡忘了的好施与仁爱,一方面也在追求人间的正义与公平;一方面在赞美侠士们的大无畏精神,一方面也在张扬文士们追求真理的书生意气!当年,那些活生生的侠士们浴血立功、奋身立德;当年,那些同样活生生的文人们毅然立言——留下了他们的咏侠诗,他们都是可敬的,而《咏侠诗史》则通过对史家立传和文人歌咏的结合性研究,热情地表达着他们对前侠士们的敬意。所以,《咏侠诗史》既是一部向侠者的致敬之书,更是一部向“咏侠者”的致敬之书。
(三)认真的探索
侠的精神内涵十分丰富:独立、特行、先义、后身、轻生、重名、报恩、济世、死知、生民……然而概其要者,侠的活动空间,自然也就是与“庙堂之高”相对的“江湖之远”;于是侠者,自然也就是“江湖中人”。对此,多年来阅侠无数的汪聚应博士看得真切:“正统社会上层统治者一般不提倡游侠。”[2]63于是侠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卢照邻《咏史四首》之二),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的“个人英雄主义”。
而最让文人们心醉神迷的,则是侠这一精神:隐中的不隐、出世中的入世、消极中的积极。如果要对其进行命名,可以名之为“侠之隐”。言其隐,是因为他们一般选择了不仕;言其侠,是因为他们并非绝对的沉默与无为。这个让他们实现“侠之隐”而安身立命的文字江湖,这个中国文人的千古梦想,这个“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剑客行》)的深藏之所,就是文字世界!他们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与英雄情结,在激扬文字的世界里得以自我实现。也就是说,一个文人,他可以不是血勇之侠,但是他可以是这些血勇之侠的歌咏者,比如《咏侠诗史》叙述到的那些咏侠诗作者,他们难道不是以自己的方式为天下苍生不平则鸣吗?
再退一步,他们即使不是以剑行侠,即使不曾以诗咏侠,他们至少也是那些咏侠诗的研究者。《咏侠诗史》三作者就是这样——在他们博学而“侠”思的笔下,《咏侠诗史》完美地体现了汪聚应博士对侠的定义:“侠是一种特具道德意志与力量的人物、形象或人格精神和价值观念,是社会存在与文学创作和大众心理需求的社会文化综合体。其存在表现为历史的、文学的、文化的三种文化形态,而以正义为其人格精神核心和最终的文化归宿。”[2]74在他们“折节”向侠的《咏侠诗史》中,既闪耀着侠义之人事的实存之剑,复闪耀着侠义之诗的歌咏之剑,更闪耀着侠文学研究的梳理指点之剑。三剑齐下,剑光夺目。
二、《咏侠诗史》对“侠”与“非侠”的判断
《咏侠诗史》对三作者的考验不只是态度上的,而且是能力上的。《咏侠诗史》无疑是对三作者学术辨识能力与学术阐释能力的一大考验。他们首先面临的考验就是叙述的基准、立论的起点。
侠是一个比较宽泛、广义的称谓。侠的筐子里装着侠之种种:如商业侠(刺客和杀手,受人之财替人消灾者)、武侠(谈兵论剑欲敌万人者)、游侠(一剑飘零任闯天涯者)、文侠(心游万仞而内在神勇者)与儒侠(仁孝礼义而骑士风度者)……李贽早就有过关于“广义侠”的表述:“侠之一字,岂易言哉?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李贽《焚书·杂述·昆仑奴》)显然,不能对上述种种侠一视同“侠”。值此全世界人们重新思考战争、呼唤和平之时代,尤其在此全世界人们一致打击恐怖活动之时代,《咏侠诗史》对侠之种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辨析。
(一)对私勇之“侠”和公义之侠的判断
私勇之“侠”,侠之小者,他们或以主恩为报,或以君恩为报,或以友恩为报,然而是非不问、善恶不分,甚至“作威福、结私交”,甚至“和公侯权贵相馈赠”,其“江湖气”和内在的胆怯、伪善同为吾邦一些国民的劣根性;公义之侠,行公义、为真理、心怀天下苍生,是为大众谋求公正者,是侠之大者,所以才有“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之说。然则,为众人而侠者、为整个社会的进步而侠者——公义之侠,毫无疑问是《咏侠诗史》的重点研究对象。也就说,那些为了个别人比如仅仅为其“恩公”而侠者,即使古代咏侠诗可能也赞美了其“私勇”,但《咏侠诗史》没有步其后尘,不加选择,人云亦云。可喜的是,《咏侠诗史》也确乎没有囿于立场而是非不分,比如,《咏侠诗史》就没有把州域闾巷间的民间游侠和征战边关的塞外游侠相提并论,也没有把“长安侠少”的“驻马而饮”和疆场战士的为国叱咤、为国捐躯混为一谈。
沈从文的《湘西散记·凤凰》讨论过湘西的游侠民风,他冷静地指出:“个人的浪漫精神与历史的宗教情绪结合为一,便成游侠者精神。领导得人,就可成为卫国守土的模范军人,这种游侠精神若用不得其当,自然也见出种种短处。”[3]166这是可贵的超乎于书生之见的冷静,当我们以这样的冷静而面对陶渊明“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咏荆轲》)句,我们的解读也必须冷静地越过个人之间的恩仇,而抵达国家层面的正义。比如,当我们以这样的冷静面对电影《英雄》中无名弃剑而不再刺杀秦王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就应该是:英雄无名已由私勇之“侠”一变而为公义之侠。必须指出的是,《咏侠诗史》也正是这样一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有所明辨的冷静之作。
(二)对执行指令之侠和秉持初心之侠的判断
在行侠仗义的过程中,是不折不扣地唯命是从,不假思索,还是在执行指令的过程中秉持初心,即如何处理类似的冲突事变,中国古人早已有过大量的痛苦思考。妇孺皆知的《铡美案》中的韩琪这一人物形象,就是这一痛苦思考的化身。相比于一般人认为的包公形象,其实韩琪才是真正应该得到广为阐释的形象,因为他才是良知不泯的真正的侠者。事实上像韩琪这样的大侠,一定是史不绝书,侠有辈出的。这样的侠之实存,不论是“先秦侠”还是“汉代侠”“唐代侠”,皆能以司马迁语界定之:“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4]3183但是,自司马迁《刺客列传》之后,这样的侠在正史中渐渐地少有记述。
没有记述,不等于没有发生。不记录这样的侠之实存,不等于没有这样的侠之实存。历史自有其坚韧的逻辑:被此处放逐了的,会被彼处收留——至少会被改造与重塑而后收留。中国历史收留侠之实存(或者说改造侠与重塑侠)的力量有三:一是官方改造,可谓之正化;二是民间改造,其民俗实证就是“袍哥”阶层的黑社会现象与“仗义每多屠狗辈”的江湖现象,可谓之俗化;三就是文人改造,这就是侠文化,就是知识分子对侠之实存的改造和换名,其中就包括了文学的重塑——把历史侠改造为符合自己想象的文学侠,包括纳入咏侠诗的书写。而这样的文学重塑应该是所有的重塑中独具色彩的重塑。这自然也是《咏侠诗史》必须面对的研究对象。《咏侠诗史》的三作者没有躲避这一使命,而是进行了认真辨析,表现出他们独立的思考和评说。
(三)对唯利是图之“侠”与坚持正义之侠的判断
唯利是图之“侠”,即雇佣侠,替人打架,本来难称其侠,因为“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5]7277,但是唯利是图之“侠”往往有着欺骗性的伪装,往往会表现出一些常人不易分辨的小恩小惠,并且往往把“利益”进行了正当化的辩解,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就是典型的以“利益至上”偷换了“正义至上”。这种“利益至上”的思想,无视正义的存在,把对真理的漠视伪装成商业;把正义第一位,篡改为利益第一位……庆幸的是,这种糊涂的价值观,没有出现在《咏侠诗史》。
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中引述韦尔斯《人类的命运》语曰:“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然后闻一多辩称:这“土匪”其实所指乃“侠者”。[6]469-473其实,我们的自己人鲁迅比韦尔斯这个旁人说得更加难听,他径呼那些“和公侯权贵相馈赠”的侠之末者为“终于是奴才”的“流氓”。[7]159-160然而,鲁迅的这一残酷判断却是正确的。鲁迅的判断让我们静言思之:当所谓的侠者仅仅是市井中局部现实的批判者,是绿林中局部社会的矫正者,而不能“为整个社会打抱不平”,不能“替天行道”,则我们不得不承认韦尔斯所言非虚,亦即我们必须直面所谓的侠之“正义与流氓人格精神的两面”[2]63,也就是说,《咏侠诗史》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职责,那就是破除对那些唯利是图的所谓侠者的迷信,甚至要撕掉他们侠之伪者的伪装。
“侠义”二字常常并举,人们也常视其为并列词组,其实“义”字不管是在侠字前还是在侠字后,它都是对侠的定语,是对“侠之义者”的“侠需向义”的强调。“所杀岂私仇,激烈为不平”(高启《游侠篇》),世人多有指谪《水浒传》之招安主题与封侯愿望者,然而,对土匪的收编(如清官之收编于麾下而“为王前驱”),对那些好汉们从游侠任气到征战沙场再到封侯起第的导向,让他们“归顺”而服务于社会的“升华”,从来都是人类文明不断走向法治社会的必然方向。《咏侠诗史》在对此文明方向的把握上心明眼亮,他们也努力要将自己的侠判断导入“义途”而不是“见利忘义”。甚至他们还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入——其剑锋还捎带着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糟粕:以成败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价值观对民族劣根性的形成罪莫大焉,《咏侠诗史》对此也是深恶痛绝。《咏侠诗史》没有一侠障目地对侠的历史实存做出泛侠化的泛泛之述,而是有所选择与突出,比如,对那些“功不成而名就”——事功不成而正文存焉——之人、之事、之诗的优选,这一切都表现出他们对待史识的严谨态度,也表现出他们基于基本人性的判断正义。
三、《咏侠诗史》对“文之侠者”的指认
时代变迁,咏侠诗的行为主体不再是侠而是诗人。于是,对咏侠诗的研究重点也就不再是侠而是侠文化:研究文化人如何对侠之实存进行文化命名、文化阐释与文化赋形,研究歌咏者与被歌咏者如何进行历史共建。所以,对咏侠诗的研究,必然要来到剑器之外、侠人之外、侠事之外的更大论域:文化。在这个世界,以“江湖”为活动环境的“侠本身”淡出,而“侠的阐释者”登场。这也就意味着《咏侠诗史》工程的重中之重,就是在探求文人与侠士精神同构的基础上,辨析文人与侠士的不同之处,叙述并重塑“文之侠者”的形象。《咏侠诗史》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咏侠诗史》指出了“文之侠者”的以下几个特点:
(一)文之侠者:不甘平庸的思想者
《咏侠诗史》的工作无疑是辛苦的:既要微观地考证分析,也要宏观地理论阐述,以免游谈无根;既要把侠文化与侠文学相互融合,也要把历史与文学相互渗透,力求论从史出;既要广泛搜集、汇辑研读,也要考证定位、选择分析,挣脱一般此类工程的辗转抄袭……这一切值得尊敬,而另一值得尊敬之处,是其字里行间闪烁出的思想之光,当然也包括对咏侠诗中那些“文之侠者”其宝贵思考、深刻见解的捕捉。
《咏侠诗史》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侠的文学形象体现着比侠的历史实存更为深厚的社会文化意义”[8]530,在这“更为深厚的社会文化意义”中,第一位的自然是其思想意义,而其思想之第一位,是对“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9]555的“乱”“犯”之辩。对此,《咏侠诗史》的回答是明确的:此“乱”此“犯”并非离经叛道、犯上作乱,其“乱”其“犯”,指的是独善其身、不随波逐流,这也就是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而为人们歌以咏之、念念不忘的合法性所在。
《咏侠诗史》还探讨了儒与侠的互补命题,即顾颉刚所谓“武士与文士之转换”。《咏侠诗史》对“以侠补儒”命题的思考,极显文献的功底,颇有思考的深度,但是他们没有停留在此,他们的目光抵达了一个更大的论域——如何“以儒补侠”?换言之,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兼济苍生?什么样的追求才是超越个体的天下为怀?什么样的力量才是真正撼动灵魂的力量呢?
这是中国古人一个向来的思考。比如《西游记》就表现了这一思考。读《西游记》,一般看热闹的世人皆尊崇孙悟空,认为他说走就走、说干就干,是具有行动力的“行者”,是无所不能的侠者,而以唐僧为百无一用、手无缚鸡之力(缺少执行力)之“儒士”。然而对《西游记》能深入体会者,却会如此感悟:孙悟空救唐僧乃是其叙事的表征——只是解救唐师傅的肉身,而唐师傅之救孙悟空,让泼猴走上正道、结成正果,才是真正的灵魂救赎。所以,一般人看《西游记》,看到的只是勇力为信仰开路,而看不到更深层面的信仰为勇力导航。是的,一方面是信仰为勇力导航,一方面是勇力为信仰开路,二者是互补的。同样的道理,一方面是“以侠补儒”,一方面是“以儒补侠”,二者也是合唱而共舞的。这也正如曹丕认为文章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但是杨炯却认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
《咏侠诗史》则接续了对“以儒补侠”这一重要命题的思考,他们努力于让“侠的文学形象更有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思想内涵,将侠的勇力引向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价值观念中”。[2]67他们的这一思考,无疑是对知识分子价值与使命的再次确证,也是对咏侠者形象的重塑——这些知识分子虽然不是侠,但是也利剑在握,这利剑就是他们的知识,就是他们先驱的思想、先锋的艺术、超凡的想象以及不屈从定论的对于真理的追求!也就是说,《咏侠诗史》所做的一切,其实也就是“以儒补侠”。
(二)文之侠者,不肯沉默的言说者
君子动口不动手,此言非为谬论,而是真理:文人也行侠仗义,不过文人侠是语言侠而不是刀剑侠。“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谔谔。”[10]2234侠之大者,也常出自文人。
韩愈《送董邵南序》:“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慷慨悲歌之士”,是韩愈无意中对“文之侠者”的命名。文人缘何不能称侠?侠又何必一定是捉刀提棒的“虬髯客”?侠之大者,在其侠骨;侠之真者,在其内在的神勇。以不能缚鸡之手握笔弄墨然而骨如钢、气如虹、行如风者,于世其实也多多。比如鲁迅,一个瘦弱的文人,却胆识过人,他对麻木的国民精神,犀利解剖;他对吃人的历史,无情揭露;他对腐朽的政治,挥笔直击……他难道不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他难道不是所谓“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以性灵游,以躯命游”(潘耒《遂初堂集·徐霞客游记序》)的一个活生生的侠者?
慷慨悲歌,谔谔之言,正是天下知识分子真正的侠骨、剑胆!对此咏侠诗作者们虽未执剑但是勇于言说,秉笔直书,进行了特意地指出和阐释。比如,《咏侠诗史》就看到了诗人杜甫的内在神勇。
杜甫出身于侠风世家,其叔杜并,为父亲杜审言复仇,手刃仇人,身虽死而孝义彰;杜甫的姑姑为抚养杜甫,竟顾不得自己的亲生儿子,以一女流而侠风浩荡感人;而杜甫的侠义精神则更趋内在,也更为实在。杜甫写过许多的咏侠诗,如:“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恩在斯须。”(《遣怀·昔我游宋中》)但是《咏侠诗史》没有把杜甫的侠骨仅仅理解成是诗章里的侠语。《咏侠诗史》甚至还触及了这样一个问题:杜甫为什么选择做了一位诗人?在“贫乏的时代”(海德格尔《诗人何为》),选择做一个诗人是需要勇气的。杜甫和所有的书生一样,南村群童,都可以欺他老而无力,然而,他却可以在朝堂上实话实说,为朋友叫屈,为生民请命,为天地立心。什么是神勇?这就是神勇。甚至杜甫后来的秦州之旅、同谷之行等在一般人看来的“流浪”生涯,如果从自古文人任侠好游的心性追求来看,应该也不是什么被迫无奈的逃难,而实在是有唐文人一种侠风浸染下书剑人生的“壮游”。而且,在这一问题上,《咏侠诗史》第九章的“剑气”之论,又进行了总结性的阐述,并特别强调了“气”之于“剑”更重要的意义:有其气,则笔亦是正义剑;无其气,则剑亦为烧火棍。这是道器有别的洞明之见,这也是心物有别的古老哲学,这也是侠文化研究认识的基准。可喜的是《咏侠诗史》贯穿了这一哲学,也站稳了这一基准。
(三)文之侠者,逸兴遄飞的想象者
“咏侠诗”三字中,有一颗赫然的“诗”字。这一颗字,不只是对《咏侠诗史》文化解读力的考验,也是对《咏侠诗史》诗性感知力与诗学判断力的考验。须知咏侠诗并不是侠文化的大众客厅。侠文化的大众客厅是武侠小说(一般人对侠的“最初情愫”也产生于此)甚至是武侠电影。咏侠诗是侠文化的一处密传内室。《咏侠诗史》能否将“侠”与“诗”这样看上去山水相远的两样事物做出逻辑通顺的甚至“浪漫主义”的沟通呢?能否让仗剑的侠士与行吟的诗人这两种长期以来的“两地分居”者握手拥抱呢?回答是肯定的:《咏侠诗史》在追寻侠士与诗人的精神同构这一方面,有着明确的意愿,也收取了显著的成果。
诗与侠在精神层面的最为接近之处,是它们共同的“离轨”属性:诗要重新命名万物,侠要挑战既得利益。以《咏侠诗史》大书特书的诗人李白为例,他就是唐代一个“十五好剑术”(李白《与韩荆州书》)的诗人之侠者。钱谦益注杜甫《赠李白》时说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钱注杜诗》卷九),传说李白甚至还搏杀过老虎——这当然是一般人对李白“武松打虎”一样的侠想象。而《咏侠诗史》对李白之侠的叙述并没有停留于此,《咏侠诗史》对李白侠骨义胆的诗作也没有停留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样的敢说。弥足珍贵的是,《咏侠诗史》对李白侠骨侠气的叙述深入到了李白天马行空、凌虚凭空、不同俗响的诗歌想象——指出了诗人最为可贵的品质:敢想!
诗人中的侠者也无一不是想象力这一“江湖”的佼佼者。清代文人金圣叹在评《水浒》时,多次为书中主人公的侠肝义胆与作者出人意料的语言拍案叫绝,认为“真才子也”。咏侠诗对侠的重塑无疑是想象性的重塑,于是《咏侠诗史》的撰写,如果只知侠而不知诗,没有“诗”见,缺乏“离轨”的诗想,则这样仅仅停留在泛文化层面上的解读,尘土满面,怕是谈不到贴切、深入,更谈不到面目的俊逸。
十年磨一剑,《咏侠诗史》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辛苦写作之后,带领我们看到了一个剑的宝库、侠的博物馆与咏侠诗的长廊。而更重要的是,《咏侠诗史》所描述的何止是咏侠诗的历史,它几乎就是一部旧时代中国人的苦难史,至少也是懦弱俗子精神胜利的想象史。所以,如果说“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则《咏侠诗史》也就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咏侠诗中侠客梦其历史“梦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