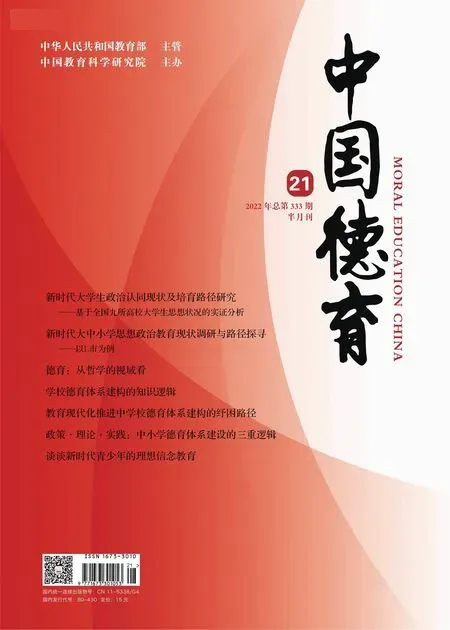德育:从哲学的视域看*
■ 杨国荣
道德教育包含多重内涵,以此为出发点,学校的德育体系建构需要兼顾不同的方面,包括确立德育的价值目标,并以此规范道德教育的过程;关注道德教育的内在根据和外在条件的互动,并确认其过程性。同时,学校教育也需要从德育与智育、美育、体育的相互关联上,进一步把握其系统性。要而言之,人格的完美性与道德教育的多方面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一、道德教育的价值目标
道德教育以培养完美人格为指向,后者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德性与能力的统一。德性的深层内蕴体现于对人自身为何而在(人生目的)的追问,这种关切所涉及的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以及人自身的存在意义。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①参见《孟子·离娄下》。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德性既确认了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本质规定,又从人是目的这一维度肯定了存在的意义。以此为内涵,德性同时也从精神世界的内在方面规定了人存在的价值方向,并引导其在成己成物的过程中展现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以避免异化为外在的手段和工具。
然而,德性固然包含价值的内涵,但如果离开了人的内在能力及其在知、行过程中的具体展现,仅仅停留于观念追求的层面,则容易使精神之境流于抽象、玄虚、空泛的精神受用或精神承诺。历史地看,以心性之学为主要关注之点的理学在某种程度上便表现出以上倾向。理学中的一些人物固然也谈到人的成长,但往往将后者限定于德性涵养等伦理之域,与之相联系的人的能力,也主要囿于以伦理世界为指向的德性之知,而未能展现人的全部本质力量。以此为价值立场,德性每每呈现思辨化、玄虚化的形态。所谓“为天地立心”等虽然体现了某种精神旨趣和追求,但当这种旨趣和追求脱离了现实的历史实践过程时,便常常显得苍白、空泛。历史上,理学一再以所谓内圣为理想的人格之境,这种人格每每主要以精神世界中的穷理去欲为指向,人的多方面发展及变革现实世界的过程则难以进入其视域。在这种抽象的世界中,德性往往被理解为个体的精神“受用”,其特点是隔绝于现实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之外,仅仅以反身向内的心性涵养和思辨体验为其内容。这一意义上的德性,显然难以被视为健全的精神形态。
另一方面,人的能力虽然内在地展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存在与现实作用必然合乎人性发展的方向。正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劳动的异化往往导致人本身的异化一样,人的能力也包含着异化为外在手段和工具的可能。在科学技术的层面,便不难注意到这一点:与对象化的思维趋向相联系,科学更侧重于对世界单向的发问与构造,后者往往导向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淡忘。就人的存在而言,科学本身当然并不仅仅表现为负面的形态,然而,当对象化的思维趋向引向对人自身的理解时,人是目的这一价值原则往往会变得模糊,而人本身也容易在被对象化的同时面临物化之虞。与之相联系的,则是人的能力的工具化趋向:当人本身渐趋物化时,人的能力也将逐渐失去作为变革世界和自身成长内在根据的意义,而仅仅被视为指向科学对象或达到某种科学或技术目标的工具和手段。
可以看到,人的能力离开了人的德性,便往往缺乏内在的价值承诺和理想的引导,从而容易趋向于工具化和与手段化;人的德性离开了人的内在能力及其现实的历史作用过程,则每每导向抽象化与玄虚化。合理的人格取向以人的德性与能力的统一为前提:一方面,通过人是目的这一本质规定的突显,人的能力展示出内在的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人的德性在基于人的能力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又不断超越抽象、玄虚、空泛的精神受用。人的德性与能力的这种具体统一,使人格逐渐趋向于完美之境。以学校的道德教育而言,既应注重培养个体健全的价值观念,也需要提高个体在价值层面的鉴别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德性与能力也呈现了相互的关联性。进一步看,在自觉进行价值取向方面引导的同时,需要从更广的角度,切实提升个体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能力;价值取向与理性能力的的统一,同时也从价值目标上规定了道德教育的方向。以成就完美人格为实质的旨趣,学校道德教育的展开,无疑应致力于两者的融合。
二、道德教育的内在根据和外在条件
如何通过德育过程,使以上人格形态获得现实品格?这一问题涉及多重关系。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其中关乎性与习、知与行、本体与工夫等不同方面。孔子曾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即“性相近,习相远”。从人格培养的层面看,所谓性相近,也就是指每一个人都有相近的本质(性),因而都具有达到完美人格的可能和根据;习相远中的“习”,主要指习行,它构成了达到以上人格的外在条件。对孔子而言,人固然皆可成圣,但唯有通过后天的习行以及社会环境的制约,这种可能才会转化为现实。后来孟子把孔子所说的性相近引申为性本善,并突出了成人过程的内在根据;荀子则将相近之性与性本恶联系起来,并着重由“习相远”而强调“化性起伪”,由此强调成圣的外在条件。广而言之,对中国哲学而言,个体在人格上达到完美之境,既基于知,也依赖于行。荀子在《荀子·儒效》中已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行之,明也。”性习之辨与知行之辩,同时又和本体与工夫的相互作用相联系。在人格培养的领域,所谓本体主要指由个体的内在道德意识所构成的精神结构,工夫则以人的道德实践活动为内容。根据中国哲学的以上看法,则人格的培养一方面需要以既有的道德意识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又离不开道德实践的展开,二者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本体与工夫的互动:“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2]以上看法的重要之点,在于既肯定内在道德意识在人格培养中的作用,又注意到外在的实践工夫在人格培养中的现实意义,从而避免内在道德意识(本体)的抽象化。
从德育的角度考察,中国哲学的以上思想表明,道德教育应当从受教育者的内在意识出发,充分考虑个体自身的意愿,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外在教化或灌输。所谓本有之性、内在本体,都可以视为人的已有规定,它们既构成了个体成长的根据,又进一步展开为人的内在意识。就道德教育的过程而言,尊重受教育者的内在意愿,意味着注重道德教育的引导性。这里同时关乎真理与道理的关系。作为广义的认识形态,真理与道理并非与人的存在及其成长毫不相关。当然,比较而言,真理固然形成于人的认识过程,但首先以对象为指向,表现为对实在的真实把握,其内容具有确定性,其接受则具有某种“强制性”:悖离真理必将碰壁。相形之下,道理主要体现于人与人的关系,其内容具有规范性,其接受则与说服相关。在一定意义可以说,真理因事(事实)而显,道理则首先因言(言说)而显。真理诚然也关乎语言的表达,但首先基于事实;道理固然也有事实的根据,但往往通过有说服力的言说而彰显,并为人所接受。道德教育基于道德实践,道德实践既以真理为依据,需要服从真理;也离不开讲道理的过程,应以道德为引导。道德行为的选择、道德实践的展开,关涉相关行为和关系的调节或协调,伴随以上活动的,是说理。与之相联系,道德教育的过程一方面要循真理,另一方面又需要讲道理。讲道理所包含的说服性质,体现了道德教育的引导趋向。
以知与行、本体与工夫的互动为内容的道德教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具体展开为一个过程。历史地看,孔子已提出了两种类型的人格典范,即圣人与君子。尽管圣人与君子同为理想人格的具体形态,二者的内涵在某些方面也交错重叠,但却分属两个序列。所谓圣人,按照孔子的理解,即是理想人格的完美化身,它构成了人格的最高境界。从逻辑上说,凡人皆可以成圣,但就现实性而言,圣人又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孔子本人从来不以圣人自许,《论语·述而》中有云:“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即使像尧舜这样的明君,孔子也不轻易以圣相称。按照孔子的理解,作为理想人格的体现,圣人的特点在于既具有内在德性,又展现了外在社会作用,他不仅包含完美的品格,而且在现实的社会层面致力于群体价值的实现,从而表现为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在这里,圣人同时呈现了某种引导的意义:作为理想人格的完美体现,人们不断地趋向于这一目标。孔子对圣人的如上设定表明,人格理想的追求本质上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人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达到某一个终点。同时,圣人作为一种引导的目标,为人提供了精神发展的方向,使人始终受到理想的鼓舞,从而能够避免世俗的沉沦,不断实现精神的升华。从现实形态看,作为道德教育的目标,人的成长和完美人格的形成,往往会经历各种反复,应当允许个体的彷徨、迷惘,并针对不同情况,耐心地讲理、说服。道德引导的过程需要持之以恒,并对道德教育的长久性具有充分意识。
三、道德教育的多方面展开
从实质的内容看,道德教育呈现综合性。宽泛意义上的道德教育,关乎多重方面。就学校教育而言,与目前学校的教育体系相应,道德教育也涉及不同维度。德育以人格之境的提升为指向,涉及的首先是内在精神形态的完善,然而,精神形态本身并非单一的规定,而是具有系统性。完善的道德意识,总是包含理性的明觉,后者既使德性不同于盲目的冲动,也使之区别于自发的形态。这种自觉的规定离不开知识的积累、理性能力的发展,并与智育过程相联系。事实上,在广义的学习和社会教育过程中,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便构成了重要方面;同样,在学校教育的多样环节中,智育也是其中的题中之义。按其实质,德育与智育作为人自身成长和人格培养的相关方面,无法截然相分。与之相关,在注重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智育。如前所述,广义的德育以形成德性与能力的统一的人格为价值目标,这一指向同时规定了德育与智育的关联。缺乏智育的内容,便难以提升人的理性能力,由此形成的人格,常常流于空疏、抽象。
完善的人格,同时应当包含美的意境。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看,审美本身便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同样,就学校教育系统而言,德育与智育之外,也尚有美育,后者与道德教育并非互不相关。美育以提升审美旨趣和审美能力为指向,同时关注人的审美情操。历史地看,中国哲学对审美艺术在人格培养中的作用,已给予了多方面关注,孔子便提出了“文之以礼乐”的观念,其中包含通过审美活动以陶冶人的情操之意。孔子很注重审美活动在成人过程中的作用,在《论语·泰伯》中即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表述,亦即通过礼乐教化来培养完美的人格。同样,荀子对艺术审美活动在成人过程中的作用也作了具体的考察。按荀子的看法,在人格涵养的过程中,音乐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方面,《荀子·乐论》中曾有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音乐更能展示主体的心路历程,也更容易激起心灵的震荡和共鸣,而在内心的深层感染中,主体的精神便可以得到一种洗礼和净化。从更广的视域看,“乐”甚至还有移风易俗的作用:“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也深,其移风易俗也易。”①参见《荀子·乐论》。所谓移风易俗,也就是影响或改变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而后者反过来将进一步制约个体的内心世界。在价值的层面,审美活动的融入,同时关乎真、善、美的统一:如果说,德育侧重善的品格,智育关乎真的把握,那么,审美过程则更多地指向美的追求。三者的相互关联使道德教育所塑造的德性扬弃了片面性而趋向于完整的人格。
人格的以上统一,主要以内在心性和精神为关注之点。“心”与“身”无法相分,人的具体存在也不仅仅涉及内在品格和价值取向,而是与人之“身”息息相关。人格固然不同于体格,但完整的人格无法略去体格。事实上,在人对世界的作用过程中,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便以“身”为内在环节,正是“身”的参与,使人的感性实践区别于单纯的观念活动,而本然意义上的“天之天”转换为合乎人的价值理想的“人之天”,也离不开“身”所参与的感性实践。在学校教育中,体育同样构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教育过程的重要环节,体育首先关乎人之“身”。完美的人格不仅仅表现为品格的健全,而且体现于体格的康健,学校教育以德智体美为指向,也体现了这一点。心之美与身之美相互关联,这里的“美”不仅仅是指外在形态,而且关乎身心的统一。道德教育不宜仅仅关注内在之心,而是应当关切身心的健康。所谓扬弃存在的片面性,也包括避免“心”与“身”的单一发展,其中蕴含着对“身”与“心”统一的肯定。中国文化较早时期已将“美其身”作为价值目标,荀子在《荀子·劝学》中已肯定“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这一观念也表明了以上趋向。具体而言,其中关乎与“身”相关的“四体”:“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①参见《荀子·劝学》。所谓“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也就是中国文化所注重的身心之学,其特点在于肯定“学”的过程不仅仅限于口耳讲述之间,而是需化为个体的行动意向,“著乎心”便意味着所学的内容内化为自我的内在意识。从中国文化对道德行为的理解看,也就是确认对礼义规范的把握,最后应转化为个体自觉的道德要求,而非仅仅停留于外在的言说。以此为前提,内在的道德意识进一步落实于践行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身心之学所引向的是实际的道德实践,它意味着个体的内在道德意识最后付诸于实践、体现于践行的过程,由此使德性化为德行。
德性或道德意识与身存在多方面的关联,“身”首先引向“行”:通常所谓“身体力行”,便表明行的过程总是与身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身”与实践具有内在的相关性。通过身与心、知和行的互动过程,不仅个体的言行举止将逐渐合乎规范,而且由“身”所展现的行为本身,也可以获得规范的意义:所谓“身教”,便体现了这一点。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看,说理固然不可或缺,前面提及的讲道理,便涉及德性涵养中言说这一面,然而,仅仅注重言说,容易流于外在的说教。道德教育过程中,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通过“身体力行”的身教,以展现道德实践中的示范意义。道德实践涉及如何做的问题,其中既关乎对道德规范的理性把握,也离不开“见贤思齐”的形式,后者便以“贤者”的实际示范为前提。这里既体现了“言传”与“身教”的统一,又从一个方面表明,对道德教育而言,与身教相关的“身体力行”并不仅仅具有外在的意义,而是构成了其必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