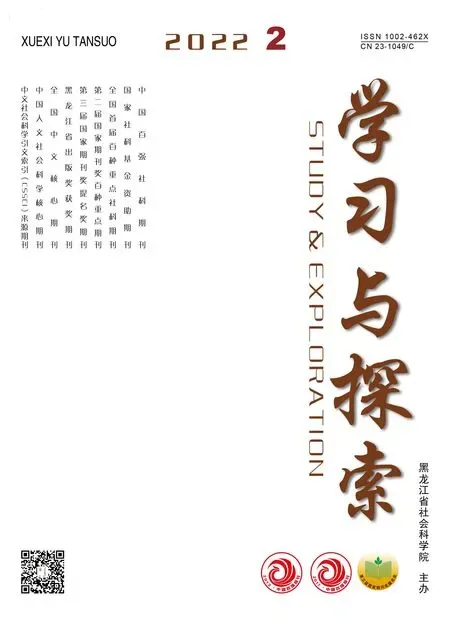阿多诺文艺观的伦理指向
曹 颖 哲
(1.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2.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哈尔滨 150040)
2021年,《新德国评论》(NewGermanCritique)推出了纪念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03—1969)《美学理论》(AestheticTheory)出版50周年的特刊。哈佛大学社会理论、历史和哲学教授彼得·戈登(Peter E. Gordon)在特刊导语中提到,当《美学理论》首次出版时,认为作者转向美学是“对社会责任的背离”,是“从政治退回到美学”,并为此深感惋惜的大有人在[1]。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阿多诺的美学思想仅仅是建立在幻象上的审美乌托邦,缺乏应有的现实面向和实践力量。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阿多诺对现代社会的矛盾、人类的苦难和人类生存状况有着持续的关注,其美学和文艺思想始终蕴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伦理指向,即指向人的自由、平等、尊严和解放,这也正是阿多诺与马克思主义关联最紧密之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R. Jameson)在《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辩证法的韧性》(LateMarxism:Adorno,or,ThePersistenceoftheDialectic)中强调,阿多诺的思想中体现着“善、真,以及美的传统哲学的三位一体”,而这一过程的完成是“独特曲折”的,其中从伦理学向社会学的“转化”是“关键的战略步骤”,是一种“最不可直接辨认的正式介入”[2]。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也认为,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想并非仅仅是一项理论建构,而是“既是程序性的,也是伦理性的”[3]55,这里的“程序”,指的是“能够激活……差异性”的程序[3]5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认为阿多诺的思想体系“是伦理学中的一个历史性标志”[3]57。
一、“公正对待异质性”:阿多诺伦理观的核心内涵
巴迪欧是围绕着“差异性”这个关键点,将阿多诺的思想归之于伦理的。在他看来,差异性是阿多诺思想体系的“纲要”[3]56,“对差异进行欣赏的必要性,对他异性的尊重”是其《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Dialectic)反复重申的主题[3]53,“与其将差异性放在理论语境中,倒不如只将它放在根本的伦理语境下对其进行考察”[3]56。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在《重构美学》(UndoingAesthetics)中指出,阿多诺美学中存在着“公正对待异质性”[4]96的伦理指向,阿多诺代表了现代美学的感性转向,因为正是在阿多诺这里,美学主导理念“由限制多元性的强制的形构,到公正地对待异质性”的转变才得以实现[4]95。正如两位哲学家所言,阿多诺的一切思想,包括他的非同一性哲学、美学思想和社会批判理论,都以异质性的存在应得到公正的对待和尊重为出发点和旨归,就像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所主张的,“主体必须弥补它对非同一性所犯下的过错”[5]125。(1)本文出自《否定的辩证法》的引文主要依据张峰的中译本,并参照Ashton 的英译本有所改动。参见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B.Asht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纵观西方传统哲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形而上学的发展史,就是异质性在同一性原则的暴力下一步步被压制的历史,因为“同一性规定的总体性”与 “传统哲学的理想蓝图”是一致的,也与“先验结构及其拟古的晚期形式——本体论”相一致[5]125。形而上学的奠基人巴门尼德以“存在”作为世界的本原,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转向奠定了基础。柏拉图构建了以理念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使具体而多样的可感世界与理念相分离,居于从属地位。亚里士多德尽管以具体事物为存在的前提,并以此与柏拉图划清界限,但同时也以“范畴”来界定存在并构建了其形而上学体系。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冲击下,形而上学有所衰落。而后,在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和近代科学跃进式发展的大背景下,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一方面以“我思”的不可质疑性为理性立法,开始了形而上学的重建;另一方面突出了以“思想”为其本质的心灵实体,奠定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但同时也使西方哲学陷入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不能自拔。18世纪,在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笼罩下,形而上学再度衰落,其体系的科学性因认识对象的超验性而遭到质疑。在此背景下,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一登上哲学舞台,就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即同时具有“否定或者批判的一面”和“总体化的一面”,是“批判与总体化”及“否定性与同一性”的“结合”[3]48。康德指出了知识的局限,认为人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将事物分为进入主体认识领域的“表现”,以及主体认识之外的 “物自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主体能动性的制约和对客体以及异质性的尊重。但是,康德对理性有限性的揭示和他的批判立场,是以解决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为目的的,归根到底是为了重建形而上学体系。因为并未超拔出二元对立的局限,康德的这一宏愿未能完成,该体系的最终完成者是黑格尔。由于传统哲学始终怀有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的理想,而差异意味着对同一性理想的瓦解,因此在二元论的立场中,异质性的存在必然遭到拒斥。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承认矛盾和差异的存在,他把差异看成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认为事物可以通过扬弃自身中的差异、矛盾和对立,动态地上升到一个更高、更完满的统一总体。可见,黑格尔承认异质性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压制和占有它,他把矛盾当作同一化过程中的一个工具,其真实意图是以差异和矛盾作为实现“同一”的中介。阿多诺客观地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正视矛盾的人”[5]131,但他也“始终如一地把非同一性消融在纯粹同一性中”[5]350。因此,虽然康德和黑格尔分别以显而易见的批判立场和辩证法中的否定性表现出“否定或者批判的一面”,但并没有突破同一性哲学的范畴,同一性原则仍“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呈现在康德的批判中……也明确地存在于黑格尔‘扬弃’一切事物的绝对统一性中。”[3]52作为启蒙理性主义的思辨顶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退为进,对形而上学体系的高峰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最富有成效的一次冲顶,在这个过程中,异质性最终被同一性吞噬和消解了。
阿多诺深刻地认识到了同一性哲学的这一缺陷并展开批判。当然,阿多诺并非反对同一性本身,因为“没有同一性人们就不能思维”[5]128。传统哲学追问宇宙的本原,渴求认识的确定性和普遍性,从感觉经验走向抽象思维,既是人类对世界进行哲学思考的必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阿多诺并不主张简单化地彻底抛弃同一性,但他认为“把同一性定义为自在之物与其概念的符合”是一种“罪孽”[5]129,传统思维的错误在于“把同一性当作目标”,而“非同一性是同一化的秘密目标,它是解救的目标”[5]128。如果以绝对同一性为目标的话,任何异质性的存在都会使同一性面临瓦解的潜在危险,必须予以“解救”,解救的方式就是使之同一化,因而异质性的存在就潜在地成了同一化的靶子。但同一化的目标是与世界的本来面目和事物存在的真实状态相矛盾的,因为“经验禁止以意识的统一来解决任何表现出矛盾的东西”。如果非要这样做,则势必会伴随着“某些贫乏的、想消除本质差别的总括概念的嵌入”,势必会伴随着“操纵”的发生[5]131。这样一来,同一性原则就成为一种暴力,在对差异的同化未能实现之时,轻则表现出对异质性个体的打压,重则表现为对异质性共同体的迫害。
阿多诺认为,“概念和主体的同一性是不真实的”[5]125,因为“概念不能穷尽被表达的事物”[5]3。同一性原则的暴力用思想的同一性来掩盖、压抑、消解、吞并非同一性和一切异质性,是一种精神化的强制,而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否定的辩证法。巴迪欧指出,《否定的辩证法》“可以被视为一场反对同一性原则总体效应的大型论战”[3]52,在这部著作中,阿多诺将同一性原则视作“对手”,而“目标就是差异性,差异就是否定辩证法最终的目标”[3]55。否定的辩证法要“考察一个事物在现实中的样子,而不是考察它属于什么范畴”,目的是“反对那些使事物固定化的概念”[5]译序9。阿多诺强烈反对从同一性的高度对个体性、差异性、丰富性的粗暴干预与整合,主张公正地对待异质性,还世界以本来面目。
因此,批判的精神、公平正义感以及对自由的向往是阿多诺毕生的坚持,他期望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确立存在的方式,那就是异质性的存在。这种伦理指向深刻地塑造了他的思想,渗透于他著作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记忆。阿多诺读书时曾经成为反犹主义敌视行为的对象,总是被同学中的某些小团体骂作“犹太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Moralia)的《坏同志》中,阿多诺把他的这些同学称为“法西斯主义早在进犯之前”就派来的“先锋队”[6],这一经历成了他“强烈厌恶‘随大流的同一性’的心理基础”[7]2。如果说童年经历仅给他带来些许心理阴影的话,那么大屠杀则成为阿多诺呼唤异质性的真正缘起。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andtheHolocaust)中分析了同一性思维和种族主义以及大屠杀的关系:种族主义“分离出某一种群的人”,一些“任何争论或者教育手段都无法触及(因此也无法有效地教化)他们,并因而必定会保持他们永久的异质性”的人,他们被视为“既不适合想象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适合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现实要素”,为了“服务于人为社会秩序的建造”只能被“切除”,而“驱逐”和“肉体上进行消灭”是两种“可以交互使用”的方法[8]。作为一名犹太人,阿多诺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就是同一性思维发展到极端的恶果,“种族灭绝是绝对的整合”[5]316。犹太人作为“西方世界中的异在物”成为同一性原则的靶子,被当作“完全无用的概念的偏差而真正灭绝掉”,“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5]316。阿多诺此后的所有思想和著作,都是对奥斯维辛的反思,“灾难反思深植于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根基处,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认识论和存在论意义”[9]。
二、“奥斯维辛之后”:现代艺术的伦理困境
在阿多诺看来,唯有艺术是能够“表现苦难的语言”,“在这个充满莫名奇妙的恐怖与苦难的时代”,“艺术可能是唯一留存下来的真理性媒介”[10]28。(2)本文出自《美学理论》的引文主要依据王柯平的中译本,并参照Kentor 的英译本有所改动。参见Theodor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Trans. Robert Hullot-Kentor,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muum, 2002。因此,只有通过艺术才能修复同一性暴力对差异性的损害,确切地说,只有现代艺术才能启动差异性的“伦理程序”,成为修复差异性损害的场所。但是,阿多诺的这一立场因为他那个关于奥斯维辛的论断而备受误解。1933年,由于纳粹上台,阿多诺不得不终止了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教学工作,辗转流亡英、美。这段时期,阿多诺在文化研究方面投入很多精力,先后参与了电台音乐研究计划、权力主义和社会歧视研究等。1949年,随着阿多诺结束流亡生涯返回德国,他的文化研究事业开始进入“德国问题”阶段,其标志就是后来被收入《棱镜》(Prisms)的《文化批评与社会》(CulturalCriticismandSociety)一文[11]。阿多诺在该文结尾处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却因措辞的犀利而饱受质疑,不少人认为阿多诺此言是将奥斯维辛之后的艺术与野蛮画上等号,进而预言艺术的终结。但阿多诺的本意并非如此。这一论断其实是关于后奥斯维辛时代艺术伦理困境的一种隐喻。
战后,德国文化领域内情况的错综复杂丝毫不亚于政治和社会领域,一方面,各占领国秉持不同的文化理念,都努力实施自己的文化政策,希望承担战后德国文化方向的带领和组织工作;另一方面,德国文化界也迫切希望在场和参与。与此同时,各阶层民众处于一种“我们是受害者”的社会集体氛围之中,而艺术似乎成为一种通过审美来逃离的方式,种种原因导致战后德国在废墟中匆忙进行文化重建。“奥斯维辛之后”命题就是阿多诺对战后德国文化重建的一种回应。在阿多诺看来,“奥斯维辛集中营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化失败了”[5]320。二战期间,荷尔德林的诗集曾印发十万册,用以“鼓励”德国士兵的“爱国主义激情”[12]。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也被纳粹利用,“成为宣传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10]360。这种时候,迫切需要的是反思,而不是匆忙进行重建。否则,艺术极有可能再度成为野蛮者的帮凶。
阿多诺认为需要坚决抵制的艺术有两种,一种在《艺术是愉悦的吗?》(IsArtLighthearted?)一文中提出的的愉悦的艺术,即堕落为文化商品的艺术。另一种是在《介入》(Commitment)一文中提到的,萨特和布莱希特主张并实践的介入艺术。对于愉悦的艺术,阿多诺坦陈,“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的”这一提法可能过于绝对,但至少“奥斯维辛之后,愉悦的艺术不再可能了”,艺术应该“与愉悦一刀两断”,“去反省自身”[13]251。阿多诺的态度如此坚决其实不无道理。到1949年初,柏林美国管制区内有76所电影院,大众对好莱坞电影趋之若鹜,而放映集中营题材影片的影院上座率几乎为零[14]142。据1947年的画刊《今日》描述,战后柏林的歌舞场就像地上的蘑菇一般疯长[14]171。在刚刚过去的真实的苦难面前,大量民众选择了遗忘。未经反省而进行愉悦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就是对奥斯维辛这一不容抹煞的历史性存在的漠视和践踏。
而关于介入艺术,阿多诺既反对“声嘶力竭的宣讲”,因为“任何直接的宣传效果很快就会烟消云散”[10]357,也反对“纯粹幼稚”的介入。对于后者,阿多诺以布莱希特的戏剧和卓别林的电影为例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在布莱希特揭露大独裁者阿尔图罗·威的喜剧中,“法西斯不再是社会权力集中的产物,而是一个意外事件,就像不幸的遭遇或者犯罪”[13]83。在由“意外事件”引发的嘲笑中,“法西斯的真正恐怖就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法西斯主义的喜剧性,就像卓别林的电影《大独裁者》中的那种喜剧性,同时也是它最极致的恐怖”[13]84。 他还提到《大独裁者》中的一个场景,一个犹太女孩用平底锅一个接一个地打纳粹突击队员的头,却依然安然无恙,没有被撕成碎片。类似的场面让这部电影“令人非常不快,讽刺力量尽失”[13]84。观众看到这样带着“正义感”的滑稽情节而哄堂大笑,对真正的受害者和死难者来说不啻为一种冒犯。这类介入艺术往往在艺术中直接置入对大屠杀事件的价值判断,摆出一种看似公正的道德态度,但事实上,所有的态度和判断都是基于某种具体的视角作出的主观判断,大屠杀真正的受难者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体验并没有得以呈现,反而被普遍性和绝对性所遮蔽,这与其说是为死难者主持正义,不如说是一种僭越,是“为了政治的介入而对政治现实的低估,同时也削弱了政治的影响”[13]84。
此外,还有一种艺术创作倾向也是阿多诺所谴责的,就是将大屠杀升华,把这一颠覆人类认知底线的暴行加以“诗化”。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便是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死亡赋格》(DeathFugue),许多人认为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命题就是以此为动因提出的。这首诗是策兰早期抒情诗的代表作,完成于1945年,取材于詹诺斯卡集中营的真实事件。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命令犹太小提琴手在行军、拷打、掘墓和行刑时演奏改了词的探戈,每废除一处集中营前,再把整个犹太人乐队全部杀掉[15]31。这种给集体屠杀配上音乐的事件在集中营里经常发生,“死亡探戈”成为纳粹行刑时演奏的音乐的代名词。在策兰的笔下,这一事件以“多变的节奏、副歌、反复出现的主题及头韵和罕见的节奏”被演化成了“诗化的音乐”[15]35。全诗四节均以“黑色牛奶”开头:“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傍晚喝/我们正午喝早上喝我们在夜里喝/我们喝呀我们喝”[16]17,这样流畅而富有节奏的韵律在每节诗的开头都重复一次,形成了一种朗朗上口、反复咏叹的乐感。诗中还有一些精巧而又一目了然的隐喻,如将焚尸炉冒出的浓烟比作“躺在那里不拥挤”的云中的“坟墓”[16]18。意象对比也很鲜明:“金发的玛格丽特”和“灰发的苏拉米斯”[16]18分别代表日耳曼女性和犹太女性,前者与歌德的《浮士德》女主角同名,后者是逾越节时朗读的《雅歌》中的少女。但苏拉米斯的头发本应是“紫黑色”,之所以是“灰色”,显然既是要与“骨灰”产生关联,同时也是通过与玛格丽特的金发形成对比,暗示犹太女性在这场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中的悲惨遭遇。
1952年,《死亡赋格》在德语世界一经发表,就大获成功,得到了战后欧洲“格尔尼卡”[15]28的美誉,人们不但把它编入课本、收入诗集,还在各种场合朗诵,甚至将其谱曲、上演。但是,这种“成功”却和作者本人的初衷相去甚远。比如,策兰曾经为诗中的“精巧隐喻”而后悔,“因为这样就分散了人们对该诗想要突出的重点的注意”[15]36,而清晰的乐感使这首诗听起来“既残酷野蛮又流畅悦耳”[15]39。如果说纳粹集中营里的真实事件是给死亡配乐,这首抒情诗又何尝不是“也将音乐强加于屠杀之上”呢[15]42?以审美化的语言去表现大屠杀,无异于“给屠刀绑上缎带”。阿多诺指出,“所谓的艺术渲染,即对那些被枪托打倒的人赤裸裸的身体痛苦的描绘,无论多么轻微,都包含着从这种痛苦中榨取快乐的可能性”。这种审美风格化原则“变了形,消除了某些恐惧。仅凭这一点,它就使受害者蒙受了不公”[13]88。
愉悦的艺术、介入艺术和“诗化”的艺术的失败意味着在奥斯维辛这一标志性的反人类事件之后,艺术陷入了一种无论言说与否都将堕入野蛮的伦理困境,艺术创作面临巨大的挑战。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同一性是不真实的”,理性与经验之间、概念和客观事物之间是异质的,是不对称和非同一的,概念和语言的有限性在面对大屠杀这类极端痛苦的经验时,显得尤其贫乏和无能为力,要么陷入自给自足的形式牢笼自娱自乐,要么以所谓公正的态度对异质性的经验进行遮蔽,或者像《死亡赋格》一样,对大屠杀进行诗化和美化。“奥斯维辛之后”命题正是指出了艺术本身处境的悖谬,其本意是在奥斯维辛之后对艺术仍寄予厚望的一种表达。就艺术的救赎功能而言,阿多诺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在《介入》一文中,阿多诺对“奥斯维辛之后”命题再次进行了阐释:“我不想缓和‘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论断;这个论断以否定的方式,表达了对文学要忠于职守的一种鼓励。”[13]87奥斯维辛之后并不是不能有艺术,而是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能够表现大屠杀的形式。
那么应该提倡什么样的艺术呢?在《美学理论》中,阿多诺指明了现代艺术发展的方向:“通过宣泄被压抑的东西,艺术将压抑性原则——也就是未加救赎的世界状况——予以内化,而不只是摆出徒劳的抗议架势。”[10]28也就是说,其一,艺术应该“宣泄被压抑的东西”,表明了艺术应该公平对待异质性的伦理意图,其二,指明了实现这种伦理意图的具体方法——“予以内化”,即不能通过“徒劳的抗议”,而要通过形式的介入。
三、形式的介入:现代艺术的伦理路径
在《新音乐的哲学》(PhilosophyofNewMusic)、《音乐社会学导论》(IntroductiontotheSociologyofMusic)、《文学笔记》和《美学理论》等多部著作中,阿多诺探讨了现代艺术如何可以经由形式的中介走出伦理困境。这一说法看似十分矛盾,因为阿多诺一直不遗余力地高度标举艺术的自律性。他认为,“自律性艺术通过形式律得以升华……艺术与这一骇人的社会保持距离,也暴露出一种不介入的态度。”[10]332的确,如韦尔施所说,“在古代,审美被置于哲学—伦理学的标准框架之中”,而“自律,这个现代美学的口号,最初意味着将美学从伦理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4]79。但是,对艺术自律性的强调却并不等于放弃艺术的伦理指向,从而使艺术陷入与现实割裂的伦理风险之中。在阿多诺看来,“艺术中可能进行社会批评的部分务必被提升到形式的层次上,并相应地不再明确强调或突出社会内容”[10]367。形式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内容的积淀”[10]216。“导向审美自律性的轨道,已经穿过无利害性阶段……艺术不会停滞在无利害性之中,而是在继续向前发展。这样,艺术便以不同的形式,再生出内在于无利害性中的利害。”[10]18可见,在阿多诺看来,通过形式中介,艺术的自律性可以实现对社会的他律性,即同一性的批判。在形式的介入下,审美与伦理两者的关系可以从先前的外部直接捆绑,演变为样式杂多的内在关系。
“形式是内容的积淀”虽然是在阿多诺的遗著《美学理论》中提出的,但早在1949年的《新音乐的哲学》中,在谈到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新音乐时,阿多诺就曾基于黑格尔的“艺术是精神的客观形式”,提出音乐材料是“沉淀的精神”,认为“一切音乐形式……都是积淀下来的内容”[17]154,而不仅仅是乐音的运动,“艺术形式比各种文献更真实地记录着人类的历史”[17]154。
阿多诺22岁时,曾师从新维也纳乐派的奠基人勋伯格的学生贝尔格、韦伯恩进行了一年的音乐学习。在维也纳创新作曲家圈子里学习无调性作曲法的这段经历与他的非同一性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共生关系。勋伯格的作曲普遍被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晚期浪漫主义阶段、无调性阶段和十二音体系阶段。其中,最能让阿多诺产生共鸣的是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勋伯格放弃了调性和传统作曲技法,形成了他的“自由无调性”的创作倾向。所谓调性,简言之就是乐音构成的系列,系列中有一个主音起家长式的主宰作用,其他各音与之形成各种关系。在调性系列中,各个音是不能平等发挥作用的,而且还存在着许多禁忌,如某些不协和音的禁用。漫长的西方音乐史,可以说一直处于调性的束缚之中,严重掣肘了作曲家的创作和创新[17]54-55。而勋伯格则试图把音乐从调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从1907—1908年的《第二弦乐四重奏》(作品第十号)开始了这种尝试,在创作中自由地大量使用不协和音,还使用不同音色来创作旋律[17]59。
对于阿多诺来说,当勋伯格告别调性,通过自由操纵音乐材料进行音乐表达时,音乐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就已经实现了:他发现了如何使音乐摆脱虚假的和谐,通过将不和谐作为音乐结构的原则,来反对对世界的虚构的表现。这种前卫的“自由无调性”是阿多诺一生所向往的音乐模式,这种真正自由和自发的、不受程式化技术约束的音乐是他的理想,正如他的非同一性理想一样。他认为“社会总体的权力也存在于像音乐那样表面上看来是派生的领域之中”[17]107,而新音乐中存在着“对异化社会的批判和抗议的因素”[17]25。当然,阿多诺并不是“粗暴地把音乐归于阶级和人群”[17]237,而是通过剖析音乐与道德伦理、音乐作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主张艺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应该被视为一种道德和批判力量。以不协和音为例,阿多诺认为“不协和音是作为紧张关系、矛盾和痛苦的表现而出现的。这样的不协和音是在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并且变成了‘素材’”[17]196。不协和音,恰恰是由于其不和谐,才具有了批判历史经验的独特力量。然而勋伯格新音乐的后续发展,也就是他的十二音技法最终对阿多诺来说却变得“面目可憎”,因为它把所有的表达和创造性,都置于一个死板的预先设定好的顺序的支配之下。所以阿多诺认为,“音乐不能落入十二音技法之手,成为它的奴隶”[17]223。
也许对勋伯格来说,十二音技法是自由无调性发展的必然。随着调性的破坏和由此导致的乐音的的解放,“如果音乐要形成没有调性约束的大型形式,就必须找到某种新的中心性原则来取代调性”[18]134。不仅在音乐中如此,在所有的艺术中似乎都是这样。然而“对阿多诺来说,真理而非秩序才是首要范畴。唯一重要的秩序是真实感知所必需的秩序,他视这种秩序为移动的、中介的和辩证的”[18]134。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阿多诺把“无调性”视为作曲的最高境界,而不能接受音乐中任何的同一化表达。他把音乐的真理性看成是对社会关系的现实状态的真实反映。在一个充满对抗和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时代,寻求这样一种完全一体化的和谐的音乐,只是耽于梦想和幻觉,而非真理。当音乐的元素被预先设定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时,它就不能成功地反映社会进程[18]136。这也正是为什么阿多诺拒绝将十二音技术作为音乐的未来。因为从根本上讲,他的音乐理论是一种“有关社会整体过程的、跨学科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7]5。无调性对有调性的反抗,不协和音对协和音的挑战,音色旋律对音高旋律的突破,其影响都不仅仅局限于音乐创作本身,而是对整个音乐文化工业的抵制,进而是一种反同一性的实践。因此,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音乐领域。
在阿多诺看来,如果说在形式的突破和创新方面,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在文学中存在着翻版,卡夫卡(Franz Kafka)的小说当之无愧。阿多诺曾经写了一篇专门献给卡夫卡的文章,于1955年作为作品集《棱镜》的结语出版,标题是《卡夫卡笔记》(NotesonKafka)。在这篇文章中,阿多诺主要以卡夫卡的长篇小说为例,讨论了其作品的主题和形式。阿多诺开篇就指出,卡夫卡的作品避免了一个“致命的美学错误”,那就是“将作家注入作品的哲学思想与作品本身的形而上学实质等同起来”。如果这两者被等同,“艺术作品将胎死腹中;作品会在说教中耗尽自己,而不是慢慢展开自身”。阿多诺把这种做法称为“直接跳到作品要表达的意义上的短路”[19]246。卡夫卡作品中不存在这样的短路,因为“卡夫卡的权威在于文本本身”,而不是任何自上而下的概念,所以,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时,“只有忠实于字面意思,而不是一种定向的理解,才有所帮助”[19]246。
阿多诺认为,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针对毫无限制的权力的,描述了一个个令人窒息的、极度同质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卡夫卡作品中的陌生人和孤独者无法被‘现存的权力’所容忍”[19]255-256。但卡夫卡并不通过直接模仿来描述这个社会,而是“在拒绝现实的基础上创造了艺术”[19]250。以卡夫卡的《城堡》(TheCastle)为例,“城堡”通常被认为是官僚权力的象征,但阿多诺指出,这种相似绝不是“任何直接的政治暗示”[19]258,并非直接勾勒出社会的轮廓与官僚权力的整体对应。卡夫卡作品的世界,仿佛“一个惊慌失措的人眼里”的世界,惊慌失措的人会“对所有的外物收回他的精神灌注,这些东西在他眼里犹如石化了一般,凝固成为第三种东西,既不是只能伪造的梦,也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由零散的碎片组成的神秘的形象”[19]263。阿多诺的这段话形象地描绘了卡夫卡作品的特征。首先,其作品中没有任何主体的精神灌注,意味着与主观性完全疏离,这赋予了卡夫卡的语言一种冷静客观的特点;同时,其作品通常呈现碎片化的外观,否定自身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因此卡夫卡小说中的内容,并不是通过完整、稳定的形式统一性来表达的,而是通过片段构成小说形式的神秘碎片来获得的。换言之,卡夫卡的小说具有一种“非历史性”,即并不是通过时间构成形式,也不以时间作为内在意义的统一体,而是由“内在形式”决定了其“碎片性”[19]264。可以说,卡夫卡是以文本的碎片性来对抗这个同质的世界,这使卡夫卡的文本世界呈现出一种绘画性的特征。正是基于上述特征,卡夫卡的小说以文本为自身的权威,仅仅从字面上,而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定向概念,表达了人类真实的历史状况。
与卡夫卡文本世界的绘画性相似的,是策兰越来越接近无机状态的晚期语言风格。阿多诺和策兰虽未曾谋面,但是二人围绕着“奥斯维辛之后”诗歌创作的可能性却多有互动。一方面,策兰在《死亡赋格》获得巨大成功之时,受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论断的触动,放弃了使此诗广为流传的流畅的乐感和明晰的表达,转而去探索一种冷静而晦涩的“密奥诗”(3)关于英译本中的“密奥诗”(hermetic poetry),国内学术界有以下几种译法:“遁世诗歌”(王柯平《美学理论》)、“密封诗”(王家新《阿多诺与策兰晚期诗歌》)、“隐秘诗”(杨国静《伦理》)。 本文根据“hermetic”一词的“密闭的”和“神秘的”双重含义,将其译为“密奥诗”,借以兼顾此类诗作形式上的封闭——诗歌意象的紧凑、密集,以及绵密的意象所带来的意义和内容上的深奥难解。风格,其目的就是将“异质性带入当下”,即便只是在一首诗里,“也让真正的他者自身发出声音”[20];另一方面,阿多诺从策兰创作风格的转变中,看到了奥斯维辛之后艺术创作的可能,从而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修正了之前的论断,提出“日复一日的苦难有权利付诸表达”[5]316,并在《美学理论》中,高度肯定了策兰的诗歌对那种“既无法经历也无法升华的苦难”[10]471的呈现。
阿多诺指出,传统的密奥诗有一个明确的标志,就是将艺术封闭起来,与经验现实隔绝,这种自我封闭源于一种“要求诗歌从主题材料和主观意图中分离出来”的压力。而阿多诺对这种封闭的程度提出了质疑,认为只能是一定限度内的封闭,而非绝对的封闭,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密奥诗与社会要素之间存在着关联”[10]470。 而且早在《论抒情诗与社会》(OnLyricPoetryandSociety)一文中,阿多诺就曾试图阐释如何通过抒情诗这样高度个性化和私密化的作品进行社会内容的表达。“抒情作品特有的悖论,即主体性转化为客观性,与语言形式的优先性有关……。”[21]43也就是说,这种从主观的内在性到外部社会、世界的转化之所以可能,不是通过显性的讨论, 而是通过语言。诚然,文学总是由语言构成的,然而,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在于诗歌的形式,就是其语言是作为形式的基本元素的每一个语言单位的并置和由此产生的句法结构本身。
能够给阿多诺这种观点提供有力支撑的正是策兰的晚期诗作,阿多诺视之为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密奥诗的代表。《你躺在》(YouLie)就是一首能够体现策兰晚期风格的诗歌:
你躺在巨大的耳廓中,
被灌木围绕,被雪。
去施普雷河,去哈韦尔河,
去看屠夫的钩子,
那红色的被钉住的苹果
来自瑞典——
现在满载礼物的桌子拉近了,
它围绕着一个伊甸园——
那男人现在成了筛子,那女人
母猪,不得不在水中挣扎,
为她自己,不为任何人,为每一个人——
护城河不会溅出任何声音。
没有什么
停下脚步[16]222。
在短短十几行诗中,《死亡赋格》的抒情风格和流畅的乐感消失了,只有众多压抑的意象,绵密得让人透不过气。这些意象指向大量真实的历史事件:既有1944年对暗杀希特勒者的处死事件,行刑之处就是哈韦尔河边普罗成茨监狱的绞刑架——“屠夫的钩子”,也有1915年震惊一时的政治谋杀事件,具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一座叫“伊甸园”的老旅馆里被残忍杀害,一个被乱枪打成“筛子”,一个被抛尸运河,成为漂浮的“母猪”。“筛子”和“母猪”这样极具侮辱性的措辞都来自当年“审判”时凶手和证人的回答。两个历史事件中间,还穿插着左翼被枪杀的旧址与几十年后充满了节日气氛的商业区的时空重叠:“现在满载礼物的桌子拉近了,它围绕着一个伊甸园——”诗歌最后以“护城河不会溅出任何声音。没有什么/停下脚步”戛然而止,暗指德国人的沉默和遗忘。这首诗显示出策兰语言风格的巨大转变。可见,策兰对密奥诗的探索,就是对一种新式的诗歌语言的探索。这种语言放弃对苦难作任何的艺术渲染,“越来越接近一种无机状态”[10]471。
关于这种语言,阿多诺在《抒情诗与社会》中就有所提及:“抒情作品的最高境界是那些主体不留下任何物质的痕迹,而是在语言中发声,直到语言本身获得表达的能力的作品。”[21]43在遗著《美学理论》中,他进一步明确了这是一种“无机的语言”:“它们模仿的是一种潜藏在人类无助语言之下的语言,甚至是潜藏在所有有机语言之下的语言:那是死者谈论石头和星星的语言。有机世界的最后残余也被清除……对于被剥夺了一切意义的死亡来说,无机的语言成为最后一点可能的慰藉。”[10]471这段话揭示了策兰创作风格的转变所蕴含的伦理意图。策兰的作品之所以堪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的重任,是因为他使用了一种无机的语言,即一种将主体性转化为客观性、从而将主观性最大限度消解的语言,通过对主体和主观性的超越,与导致奥斯维辛的深层原因——传统西方哲学的同一性思维相对抗。正是通过这种无机语言,在策兰的作品中,密奥诗的经验内容发生了颠覆,再也不是被严密封锁在作品之外,而是以独具特色的形式,实现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得以“使形式凌驾于内容,确切地说是思想内容之上。内容被转换成诗歌的实体,因为形式与之相适应……那虚伪的同一性、整一性的重要性得到削减。”[13]132
结 语
阿多诺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一种反抗,拒绝将世界的物质性和现实中的人类生命个体置于社会总体的指令之下。他坚信,艺术归根结底是一种应对现实而非逃避现实的方式,真正的艺术可以拯救世界。勋伯格无调性音乐对调性的解构,策兰密奥诗对抒情诗的超越,以及卡夫卡的文本权威对自上而下概念的消解,都是现代艺术通过形式对抗同一性、张扬异质性的典范。
平等对待异质性的意义在于,只有在真正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多元和共存,才能够捍卫人类个体的独立性、特殊性和完整性,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奥斯维辛之后,以形式介入现实的现代艺术,为阿多诺这一伦理旨归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