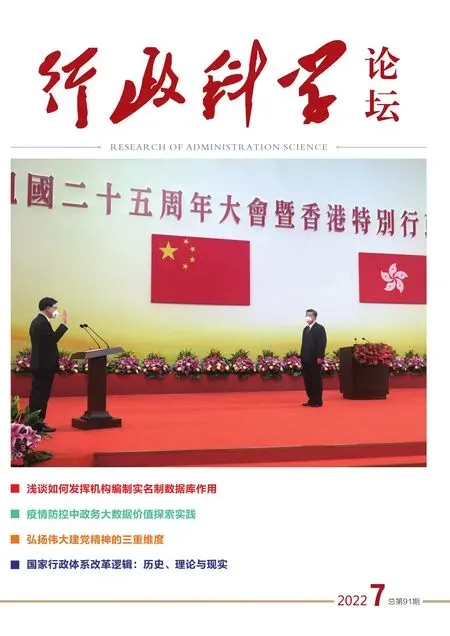中国传统勇德及其当代价值
徐猛香,赵 平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勇德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等诸多关系的道德规范之一,也是涵养君子精神、培养不惧品质的基础。孔子在《论语·子罕》中最早提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1]的观点,其后,《中庸》又将“勇”与“仁”“智”并称为“三达德”,“勇”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观念和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德目。其所蕴含的勇敢不惧、勇武坚毅、勇往直前等精神力量,寄寓着中国古代士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同时,勇德作为维系人类社会有序运行的美好德性,是道德行动的必要中介[2],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勇德在各朝代关键时期都起到道德规范和精神支柱的作用。当下,由于对勇德科学内涵的误读、普世价值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消解、市场逐利性的道德侵蚀以及大众传媒的流量异化等原因,催生了一系列“娘炮”“佛系”“躺平”等具有消极倦怠思想的群体,给勇德融入时代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一、中国传统勇德的内涵
在汉语语境中,“勇”字的基本义项为果敢、胆大[3]。《说文解字》释义:“勈,气也,从力甬声。”[4]段玉裁注曰:“气,云气也。引申为人充体之气之称。力者,筋也。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焉。故古文勇从心。”[5]《辞源》将“勇”解释为“果敢、胆大”[6]。《辞海》将“勇”与“有胆量、不退缩”相联系[7]。在当代《伦理学大辞典》 中有记载,勇敢属于道德范畴,是一种对人的肯定性评价,即为实现一定的道德目的所具有的不怕困难、危险和牺牲的精神[8]。综上可知,“勇”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美好德行。
从远古时代“崇力尚勇”到儒家“三达德”的思想建构,再到当代经济社会赋予勇德新的内涵,勇的内涵伴随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然而,要想追溯勇的元初含义与文化内蕴,就要从中华传统经典中探析。《论语》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共提及“勇”达16次之多,集中在《为政》《公冶长》《泰伯》《子罕》《先进》《宪问》《阳货》 7个篇章中,内容涉及勇的评价标准、勇与君子养成的关系以及勇与其他德目的内在联系等。而具体到“勇”的界定标准,孔子并未给出统一答案。对于仁、智、勇“三达德”的地位,孔子以“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9]332将三者并列,将“勇”纳入衡量君子的标准。在仁与勇关系上,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10]309,阐明了“仁”是“勇”践行的必要条件;在知与勇关系上,孔子说“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11]393,说明勇德实现要以“知”作为智慧支撑;在义与勇关系上,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12]35,“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3]407,阐释“义”对“勇”起到道德限制和规范的作用,勇是义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内涵表现,义是勇伦理秩序的强行制约;在礼与勇关系上,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14]165,说明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礼”成为“勇”的衡量标尺,以礼制勇、依礼而行,因此,子路问“君子亦有恶乎?”的时候,孔子把“恶勇而无礼者”[15]407当作憎恶的对象之一。由《论语》对“勇”的内容阐释来看,勇与仁、智、义等其他良好德性结合的过程中,勇德作为一种具有人类道德规范的理想德性,往往推动事物朝向积极方向发展。
孟子在继承孔子勇德思想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勇德的内涵。《孟子》中,共提及“勇”15次。集中出现在6处,概括之:养勇有方(《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匹夫之勇与君王之勇(《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好勇斗狠(《孟子·离娄章句下》)、有元之勇(《孟子·万章章句下》)、死而伤勇(《孟子·离娄章句下》)、勇士不惧(《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关于勇德的内涵,孟子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其一,“大勇”和“小勇”的层次之分。《孟子》中以“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的“匹夫小勇”,与“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的“武王之勇”形成鲜明对比,孟子认为,为政者要施仁政、践王道,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将勇从道德范畴延伸到治国理政。其二,浩然之气的养成。孟子认为“勇”者离不开“气”,他说:“曾子之勇,则有惧有不惧,一以义不义为断。此不独北宫黝之勇不如,即孟施舍之守气,亦不如也。”孟子理解的“勇”有境界之分,只有达到曾子之勇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德性之勇,因此,孟子的“养气”即“养浩然之气”,具体表现就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其三,践行大丈夫精神。孟子以天下为己任、以施“仁政”为政治理想,因此,孟子对大丈夫的定义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荀子对“勇”做了更进一步划分。《荀子》中,共提及“勇”31次之多。按的等级划分,勇可分为上勇、中勇、下勇(《荀子·性恶》);按儒家立场进行类型学划分,勇可分为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荀子·荣辱》)。
其一,划分了“勇”的等次。荀子在《性恶》篇中说:“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 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
荀子认为,“勇”之德性要分为不同等次的,上等之勇、中等之勇都与独立天地、坚守正义、舍生取义、恭而有礼等美好品德相联系,反对重利轻义、不辨是非、怯懦逃避的下等之勇。
其二,划分了“勇”的类型。荀子在《荣辱》 篇中说:“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 重死持义而不桡, 是士君子之勇也。”
荀子将“勇”与义利观相联系,见利忘义者,如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都是为人所摒弃的,在利益诱惑面前以义为先,为了坚持正义而不屈不挠的“士君子之勇”形象为社会所弘扬。相比孔子、孟子对勇的界定划分,荀子的阐释更加具体、明晰。
此外,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以“渔夫之勇、猎夫之勇、烈士之勇、圣人之勇”展示了不同职业身份的人在具体行为中的表现,以此彰显圣人之勇看透世事、穷通命运、大难不惧的崇高精神:“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
宋明以降,理学家保留先秦儒家对“勇”的基本解释,进一步研究“大勇”的内涵外延、“三达德”的排序问题以及勇德“为己”边界的拓展等内容,“勇”被赋予新的历史内涵。及至近代,在救亡图存、谋求独立的历史背景下,从国家层面来看,勇德彰显的尚武、尚勇精神成为时代亮色:梁启超以“孔子摄相事于鲁”论证孔子成为中国武士道精神鼻祖的可能;胡适以“儒是柔懦之人”激励儒家与勇武结合在一块,建构新儒家思想;毛泽东以“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阐释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激励人奋进前行。在个人德性修养层面,勇德突出表现为勇敢、勇毅的个人品质:袁隆平以打破科学权威的勇气,将杂交水稻播撒华夏大地;钟南山以武汉逆行的勇气,推进新冠病毒防治的进程,稳定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聂树斌案迟到的正义,重塑了现代律师的个人勇气。由古及今,勇德从来不是笼统的概念,而是积极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改善社会道德文明风尚、建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体系和提升个人德性修养的精神力量。
勇德精神在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激励人的战斗意志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正处于全球化、数字化进程的当代中国,受到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精神心理等多方面影响,勇德对当代社会影响趋弱。这就要求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思想中勇德遗产的同时,也要加深理解勇德中的健康合理的成分,既要发展符合当代中国转型期需要的勇德新时代内涵,又要弘扬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勇德力量,推动勇德在共融共进、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的局面中不断丰富其现实价值。当然,勇德的学理分析是肇始,更主要的是在践行过程中有利于个体健康人格的培养、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
二、中国当代勇德精神的缺失
勇德作为人的一种重要德性,是塑造人美好品质的“磨刀石”,是维系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阻尼器”,也是发扬民族精神、建设道德文明的“助推器”。随着经济全球化、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当代社会出现一系列与勇德精神不相符的事件,并深刻影响着社会道德风尚和新时代青年的健康成长。
目前,为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时代背景下,高速铁路、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新四大发明”成为互联网经济服务社会的新符号,新兴科技和商业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然而,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也催生了一部分不良企业,它们为了获得经济利益铤而走险,生产假冒伪劣、危害健康的产品,甚至出现偷税漏税、不诚信经营、见利忘义等行为。近年来,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校园贷”事件、电信诈骗案件、短视频色情产业以及2022年的“3·15事件”中的“土坑酸菜”等违法犯罪事件,更是向我们展现了社会中不良现象的存在,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市场经济中的商业资本一味逐利、忘记自身的责任和担当,在2020年,当互联网巨头企业相继投入大量资源入局生鲜社区团购时,《人民日报》针对巨头跟商贩“抢生意”的行为批评道:“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为。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24]不难看出,所谓“乱象”的背后是从个人到社会层面责任担当与敢于作为的勇德精神的缺失。
开放的中国带来了多元化思想,但也给予当代青年良莠不齐的精神食粮。在媒介流量和娱乐狂欢的表象背后,西方消费主义思潮正逐步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以游戏、电影、音乐为主要形式的娱乐内容影响着普通人,正如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在《全球化陷阱》中提出的“奶头乐”理论告诉大家的,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世界上80%的人口将被边缘化,为了化解矛盾,就需要制造出令普通人沉迷、消遣的娱乐产品,从而让这群人在享受快乐中丧失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和判断,以便达到“奴役”的目的。不难联想,近年来,互联网上常出现的“佛系青年”“光想青年”以及“躺平”思想等,这是不是物质条件不断优化的今天,部分青年在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生活两种模式切换后的一种回避、退缩?近年来,一些娱乐公司为了迎合青少年的心理,大肆鼓吹“娘炮”之风;娱乐圈对男明星“红唇、卖萌”等伪娘化包装,在社会上掀起一股“阴柔之风”。为了抵制这种泛娱乐化,坚定文化自信,2021年9月2日广电总局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强调要“树立节目正确审美导向,严格把握演员和嘉宾选用、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11]。为更好关心和培养下一代,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面对培养学生“阳刚之气”的热议,教育部也给出官方回应:“将从加强教育教师配备、加强学校教育制度顶层设计、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及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问题研究等方面更好解决这一问题。”[12]由此,从一个侧面可知多元思想影响到个体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信仰,反映在道德文明层面就是勇德精神、刚强之气的示弱。
“勇德”不“涌”反映着部分人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从“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商业竞争到“见利忘义”的不诚信、无担当的牟取暴利,可见不“涌”之勇、不为之勇已成为部分企业和个人的“庇护所”;从想而不敢、多思未践的“光想青年”,到追求平淡简单、平和淡然的“佛系青年”,再到驱阳向阴、除刚向柔的“伪娘”风气,隐含着部分当代青年逃避生活、惧怕困难、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需要以客观理性的精神探求当代社会“缺勇”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三、中国当代勇德精神缺失的成因
勇德作为人的一种重要的德性,对社会发展和个体生活都十分重要,当“缺勇”现象对青年身心健康成长产生负面影响时,我们应深入剖析其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经济发展是当代“缺勇”现象生成的物质根基。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当前中国经济已经从以前的快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这也导致社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内卷”,不少人的上升渠道和发展空间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造成部分人甘于躺平;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社会物质更加富裕,不少人开始停下脚步享受生活,这就很容易产生“佛系”、倦怠、停滞的人生态度。此外,市场经济自带的逐利性,催生少数人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当商业利益与道德文明相冲突的时候,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导向也容易受到影响,这也会致使“缺勇”现象的发生。
其次,思想多元是当代“缺勇”现象延伸的精神筋脉。一方面,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对中国的当代青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造成了及时行乐、自我逃避的“佛系”心态以及眼高手低、光想不做的“光想青年”等出现。在当今社会,一小部分青年不再笃定艰苦奋斗、勤劳致富,久而久之,这部分年轻人的勇德精神逐渐消弱、减弱。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水平赋予新时代青年优渥、富裕的物质生活,他们在父辈的庇护和养育下,缺少了冒险性、危险性的实践活动,这也就造成冒险精神、勇敢不惧等品质的缺失,而选择“宅”在家中、学校和宿舍等狭隘的生活空间,这些文化土壤必然不利于勇德精神的养成[13]。
最后,生活方式是当代“缺勇”现象发展的现代土壤。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赋予人类更多可能性,互联网空间极大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生活空间,多媒体也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代青年作为社会最具活力的群体,能够快速适应数字时代带来的快捷、便利,青年们的生活、工作、交友、学习、娱乐等行为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以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为代表的购物平台满足人们的日常消费需求,以微信、抖音、快手、B站等为代表的娱乐平台承载人们的娱乐行为。相应地,户外运动被虚拟游戏空间替代,实践活动被指尖科技完成,伴随着5G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技术的发展,更多的青年群体智慧变得愈加发达,但是,身体的灵敏度、灵活性、力量性却日渐弱化,由此,人类的勇德(包括勇气、勇敢、勇力、勇毅等)精神也相应地缺少身体上、精神上的磨砺。在以技术文明为代表的数字时代,人类勇德精神的潜在能量有可能在伴随人类智慧和思维提升的同时渐渐消退。
四、勇德精神的当代价值
“勇”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具有深刻而巨大的精神作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西方多元思想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中西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极易出现混乱现象,诸如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伪娘风”“娘炮”“佛系”“躺平”等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影响着健康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国家精神文明的建设。正确认识勇德精神的当代价值,是引导、塑造和培育青年勇德精神的关键。
首先,勇武不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复兴的基础。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旋律,但是,国家间各种形式的竞争从未间断。我们需要认识到国家竞争的残酷性,从大规模武力对抗到地缘政治、局部热战、经贸战、信息安全战和高科技领域的全方位“战争”,从关系国家科技命脉的芯片战到关乎经济发展的贸易战,从关系区域稳定的南海摩擦到关乎台湾统一的主权问题,从关系宇宙空间的探月工程到关乎“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赢,面对当代世界的极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面对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和阻挠,中国要确保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军队力量作为根本保障。必须将勇德精神融入到国家安全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轨道,紧抓百年机遇,实现强国之梦。
其次,勇敢进取是一个社会和集体有序运行、激发活力的源泉。中国儒家思想重视仁、义精神,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最具活力的小微企业需要更大的创新力、创造力,创业者们则需要更多勇气、勇敢,努力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从社会层面而言,“经济双循环”“放管服”等系列经济改革需要上层建筑的勇气;从社会现代化治理而言,“互联网+”、智能化、数字化和大数据等创新方式需要城市管理者的持续创新勇气;从国际社会共建共治而言,全球经济复苏、全球粮食安全等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以包容性、创造性的精神勇敢地迈出新的脚步。
最后,勇毅有义是个体生存发展、不断进步的阶梯。当代中国依托科技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在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中,中国在向西方传递东方精神的同时,也深受西方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是西方多元意识形态的渗透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盲目攀比、虚无和人生无意义的精神毒害。在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道德风尚营造双塔指引下,我们要对中国传统勇德精神进行扬弃,在批判、继承中重申其时代价值,以帮助陷入迷惘、孤独等精神危机的当代人积极面对生活,勇敢实现个人价值和理想,从而获得真实感、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