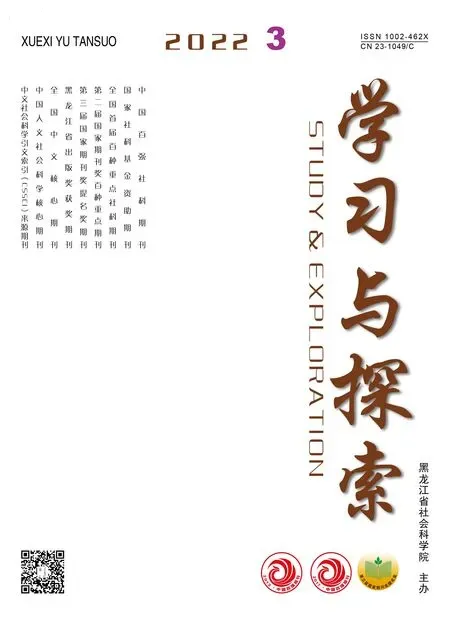“资产阶级社会”表面财富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张 一 兵
(南京大学,南京 210023)
1861年8月,马克思正式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内容不断扩大,形成了篇幅庞大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显然,这一手稿的写作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意外,因为,这里有一个从面对公众读者的阐释性话语向自己研究的生产性话语的无意识转换,开始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资本章”,后来在写作过程爆燃为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深入研究。
一
1861年8月,马克思正式开始写作出版合同已经规定必须交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可是写作过程中内容不断扩大,成为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深入研究。显然,这一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认识的思想实验,最终成了新的思想实验的酵素。我现在认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之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进程中的又一重要成果。手稿的写作从1861年8月开始,到1863年7月结束。这部手稿共有23个笔记本,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马克思写下的规模最大的手稿。在这份手稿上,马克思亲自编了页码,共1472页。应该说,在《回到马克思》中,这一文本在哲学构式的栅栏化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当我们将思考焦点转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来时,《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重要性则突显出来,特别是当我突破了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构式永久地没影于1845年的界限后,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完整构境也突显出来。这里自然就会涉及我在《回到马克思》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即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三个“理论制高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我现在的认识仍然坚持上述的判断。因为,虽然《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包含了极其重要原创性思想塑形和构序内容,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和历史现象学中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它们都是《大纲》思想革命的深化和系统完善。
在手稿的第一页上,马克思先简单地写下了这个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第三章的标题,“资本一般(Das Capital im Allgemeinen)”,然后明确地标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Capitalistische Production)”[1]6。与《大纲》中的“资本章”不同,虽然要讨论资本主义的生产,可马克思却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前,先讨论了两个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往往遮蔽人们视线的经济物相化(1)物相化,是我在本次研究中使用的新概念。在物理和化学等科学研究中,物相(phase)又称“物态”。一般指物质分子的聚集状态,是实物存在的形式。通常实物以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在特定条件下又会表现出“等离子态”“超导态”“超流态”等物相。但我所设定的物相化中的“相”却不仅仅是物态之意,而兼有实现出来的主体性爱多斯(eidos,共相)之意,因为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构境中的一般物相化,总是指一定的主体目的(“蓝图”)和理念对象性地实现于对象的用在性改变之中,这是看起来现成事物对象的消逝性来缘起。由于日本学界在日译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概念时,通用了“物象化”一词,而中文中与意象相对的物象概念本身带有某种主观显象的痕迹,所以,用物相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透视的用在性实存对象。马克思在自己晚期经济学的文本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经常使用materialisirt(物相化)一词来表达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活动(爱多斯)在塑形对象效用中在物质实在中的消隐。Karl Marx,Grundrissen,Gesamtausgabe(MEGA2)II/1,Text,Dietz Verlag, 2006,S.221;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4-1,Text,Dietz Verlag, 1988,S.47.当然,人历史地实现自身的主体物相化、人创造出不同历史时间质性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的社会物相化、工业生产中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技物相化,和商品市场经济场境中整体盲目无相化的经济返熵和反爱多斯(eidos)经济物相化是更难理解的。现象:流通和分配领域的贵卖贱买和钱能生钱的假象。我体会,因为这一手稿的肇始阶段,马克思自觉意识层面中还是在写作面向一般读者的阐释性话语构境,所以,这可能也是马克思想到一般读者在面对经济物相化时的直观社会现象。当然,这也是以往人们关注这个以可见的财产—财富表象为关注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论争层面。我们可以感觉得到,马克思似乎想特别说明停留在流通与分配领域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非法性。这正是马克思失形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话语实践、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的临门一脚。
首先,剩余价值并非是在流通领域中产生的。在此,马克思并没有像《大纲》那样,探究剩余价值的生成,而是将其视作一个已知项直接带入到对资本主义流通领域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里马克思讨论的资本,是在货币形态上进入流通的商业资本,在完成了从货币—商品—货币(G—W—G)这一过程的货币持有者那里,“他不过表现为这样规定的资本的人格化(Personnification),表现为资本家”[1]20。作为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场境中人格化的商业资本家,在其现实性上是商业资本“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个一般性的“关系总和”不同,这里人格化的资本家的“关系总和”是经济物相化颠倒后的伪主体,这也会是主体物相化在经济物相化中的畸变。这恐怕是很难入境的透视。在后来的讨论中,马克思说,“商业资本不是表现为与生产资本并列的特殊种类的资本,而是表现为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种类,只是表现为生产资本借以进行配置和执行职能的各特殊领域中的一个特殊领域”[2]72。这是对资本关系总体性的质性判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业资本不过是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子类。并且,“商业资本或作为商人财产出现的货币,是资本的最初形式,也就是只从流通(交换)中产生并在流通中保存、再生产和增殖的价值的最初形式,因而这种运动的唯一目的是交换价值”[2]11。这是交换领域中出现的货币,它是资本的最初在场,它表现为货币—商品—货币(G—W—G),这一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即交换价值。马克思指认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眼里,“在G—W—G这一运动中出现的价值,是从流通中产生,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且自行增殖的价值,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就是资本”[1]19。这当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中的财富增长的经济物相化假象。从配第开始,经济学家已经知道工业生产之上的这个商品—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价值,是不同于农业生产产品(自然财富)的“社会财富”的。所以,可以通过G—W—G(')得以增殖的价值,或者说能够带来更多财富的金钱就是资本。当然,马克思告诉我们,这只是处于流通领域中资本转换的表面现象,因为多出来的财富—剩余价值并不是在流通领域产生的。马克思具体分析说:
我们就拿某个国家的所有资本家和他们在一年内所进行的买和卖的总和来说,虽然某一个人可能欺骗了另一个人,因而从流通中取得了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但是,流通中的资本价值总额不会因这一活动而有丝毫增加。换句话说,整个资本家阶级(Gesammtclasse der Capitalisten)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得到了另一个人所失去的东西而发财致富,增大他们的总资本,或者说产生出剩余价值。整个阶级是不能自己欺骗自己的。流通中的资本的总额不可能因资本的个别组成部分在其所有者中间进行不同的分配而增大[1]26。
这是马克思对流通领域并不生产出剩余价值观点的一次最清楚的梳理。这当然还是在阐释性的话语构境之中。在一个国家的商业活动中,的确可能存在贱买贵卖一类的欺骗,可这种个人、企业或商业团体之间买卖关系中的你多我少,并没有增加流通领域中的财富总额。马克思客观地断定,这是资产阶级不可能自我欺骗的地方。这破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其他形形色色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在流通领域探寻财富增殖的幻象,因为在他们那里,“剩余价值竟被荒谬地解释成是由贵卖贱买产生的”。我们可以看得出,这里的阐释话语与《大纲》的研究性话语不同:一是剩余价值理论是全部《大纲》思想实验的经济学革命的最终成果,而这里,剩余价值已经是话语表层的起点;二是与《大纲》中“资本章”中马克思讨论资本关系的双重异化和事物化颠倒不同,这里分析的入口是让读者一看就懂的经验表象层面,马克思是从可见的经验塑形假象的透视中,再一步步深入到本质。这与思想实验中在复杂的逻辑关系赋型解析是根本不同的分析路径,在这里,深刻的理论生产和思想革命的成果已经转化为通俗的道理。
其次,分配领域中生息资本的G—G'的假象。这也是一般人都可以直观到的生活现象。这当然也是黑格尔所指认的,熟知却不理解的经验物像塑形。马克思接着上面的分析说,还有一种扰乱人们视线的假象,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apitalistische Productionsweise)”产生之前就存在的“钱能生钱”(G—G')的情况。他说,与商业资本一样,“资本的另一种形式同样是古老的,人们通常正是从这种资本形式出发形成了关于资本概念的见解,这就是放债取息的货币的形式,即生息货币资本(Zinstragenden Geldcapitals)的形式”[1]33。人们都能看见,当货币持有者将钱借给他人或者银行时,钱在回到自己手中时,都会多出一个以借贷利息方式出现的金钱余额。在这里,甚至上述第一个流通过程中商业资本构式的货币—商品—货币关系(G—W—G)也不见了,“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运动G—W—G,即先用货币交换商品,再用商品交换更多的货币,而只是这一运动的结果G—G:货币交换更多的货币”[1]33。这种从可见的货币直接生出货币(利息)的生息资本,甚至比上述的商业资本“更接近表象(Vorstellung)”。因为,这似乎是一般财富的金钱的自我增殖。马克思告诉我们,其实,钱是不会自己生钱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利息也就只是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和分支(besondre Form und Abzweigung des Mehrwerths),剰余价值后来分为构成各种不同收入的不同形式,如利润、地租、利息(Profit, Grundrente, Zins)”[1]34。这也就是说,利息并不是在流通领域生产出来的,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分配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实际上是生产资本付给生息资本的一种资金占用和使用的费用,这个看起来在银行中发生的“钱生钱”(G—G'),实际上是生产资本将从生息资本借贷来的货币投入到生产过程中,通过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获得的增殖,其中,剩余价值的分配中会分割出生产资本所必须支付的资金占用费,只是它最终回到银行中表现为遮蔽了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借贷利息。马克思特别界划说,“在资本主义生产(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本身的基础上,生息资本表现为派生的、第二级的形式(abgeleitete, secundäre Form)”[1]35。如果说,支配了生产的资本利润是生产(占有)剩余价值的第一级的形式,那么,生息资本获得的借贷利息就是参与分配剩余价值的secundäre Form(第二级的形式)。这种表述虽然有些复杂,但却是典型的阐释性话语构式。在之后爆燃出来的思想实验中,我们会看到生息资本与地租一起被透视为剩余价值的分配形式异化。马克思分析说:
在历史上,这种资本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发展以前就出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它只构成第二级的形式。就像商人财产一样,生息资本只需要是形式上的资本(formell Capital),是具有这样一种职能的资本,它在资本支配生产以前就能以这种职能存在,而只有支配生产的资本(Production bemächtigt)才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1]35。
以放贷为生的生息资本,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就出现了,与商业资本一样,它们并不构成那里社会生产方式筑模的本质,因为,那里的“资本还没有支配生产,还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资本”[1]35。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后,生息资本则成为生产资本之下的“第二级的形式”。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将生息资本称为“最完善的物神(Fetisch)”[3]303,这个物神的比喻,是说钱能生钱的神秘伪在场假象。他这样写道,“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automatische Fetisch),自行增殖的价值,创造货币的货币,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Dings,货币、商品)同它自身的关系”[3]304。这个物神假象的背后,真实发生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事物化颠倒和更深一层的劳动异化,只是它们的经济物相化过程都被完全遮蔽起来了。“作为生息资本的资本的充分的事物化、颠倒和疯狂(Versachlichung, Verkehrung und Verrücktheit),——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本性,它的疯狂性,只不过是在生息资本上以最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3]306这里的疯狂是指资本在交换关系的事物化颠倒的掩盖下,无止境地疯狂盘剥工人的剩余价值,当这种剩余价值转换为钱能生钱的利息时,无疑增加了金钱的神秘性,这也是经济拜物教徒追逐金钱的疯狂。显而易见,这种表述已经不完全是阐释性话语了。
二
在十分通俗地说明了上述这两个经济学上的财富增殖假象之后,马克思说,要想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仅仅从流通和分配领域中直接到场的财产和财富的经济现象表面讨论问题是不行的,这也就有可能走向否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这样的表象概念,从而确立透视不可见的capitalistische Produc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通道。具体到我们这里的思考线索,也就是说,仅仅关注“资产阶级社会”财富多少意义上的富人与穷人的对立,或者说,直接讨论与资本家对立的工人、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不行的。资本的秘密,只能在透视经济物相化迷雾之后,从日常生活中直观可见的财富进一步深入到资本关系的自身基础——与商品和货币(表面的对象性的一般财富)都相关的价值的本质关系出发。所以马克思说:
为了阐明资本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劳动出发。正像不可能从不同的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然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也是不可能的[1]36。
这是马克思阐释话语构境中十分特别的一个说法。如果要研究一个银行家,直接从生活常识中“他是一个白人”这样的判断开始是荒谬的,就像说明我们直接看到的蒸汽机,指认它是一种自然物质一样,研究人与事物的本质,必须实质性地探究这一人与事物背后不可直观的关系场境存在的历史发生和发展进程,所以,面对资本概念,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本就是劳动”这样的简单判断上。因为资本关系并不是具体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使用价值的用在性事物,如果想透视资本关系的本质,就要从不同于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物相化关系属性——经济物相化中特殊关系构序的价值开始,并且要从价值在流通领域中的商品交换的表现形式——交换价值出发。这是马克思在阐释性话语塑形中,慢慢地从日常生活经验常识向经济学话语构境的转换。马克思这里已经非常精确地理解,其实作为社会财富的商品和货币本质的价值关系,都是已经消除了所有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历史痕迹的抽象的对象化的劳动。“价值,不论是货币形式还是商品形式,都是对象化的劳动量”,即包含在商品中抽象的劳动时间。如果价值是对象化的劳动,那么此后由货币生发出来的资本当然也会是隐匿得更深的对象化的劳动,并且资本只是货币投入到生产过程并获得增殖时才是它真实的历史性在场。这样,资本与劳动在流通领域中的外部对立关系就必然转换成生产过程中对象化劳动与非对象化劳动的奇怪对立。它的实质是经济物相化的对象化劳动与不能直观的活劳动的自我对立。其实,当马克思使用Vergegenständlichung(对象化)概念的时候,就可能会接触到阐释话语的理解边界,因为这会是深奥的哲学构境。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也会偶尔出现的现象。在此,我们看到马克思第二次改写了自己在《大纲》中写下的那段著名的话:
唯一与对象化劳动相对立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活劳动(lebendige Arbeit)。前者是存在于空间(Raum)的劳动,后者是存在于时间(Zeit)中的劳动;前者是过去的(vergangen)劳动,后者是现在的(gegenwärtig)劳动;前者体现在使用价值中,后者作为人的活动(menschliche Thätigkeit)处于过程之中,因而还只处于自行对象化的过程中;前者是价值,后者创造价值(Werthschaffend)[1]39。
马克思对于这一文本片断的第一次改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稿中。(2)马克思第一次改写的内容为:“对象化劳动的唯一对立物是非对象化劳动,同客体化(objektivirten)劳动相对立的是主体劳动(subjektive Arbeit)。或者说,同时间上已经过去的、但空间上存在着的劳动相对立的,是时间上现存的活的劳动。这种劳动作为时间上现存的非对象化(也就是还没有对象化的)劳动,只有作为能力,可能性(Möglichkeit),才能,即作为活的主体的劳动能力,才能够是现存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2,Text,Dietz Verlag, 1980,S.86.与前两次表述的侧重点不同,这里马克思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出现在流通领域两种“财富”的表面交换,即资本与劳动的形式上平等交换中被遮蔽起来的生产过程中两种劳动的关系上。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作为生产条件到场的资本关系是对象性劳动,而对象性的劳动是价值,那也意味着资本不过是“存在于空间的劳动”,而与资本对立的劳动则是“时间中的劳动”,即处于“人的活动”和“自我对象化的过程中”的可能性的劳动,两者根本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已经被vergangen(过去的)劳动创造出来的现成价值,而后者作为gegenwärtig(现在的)劳动则是在生产过程中保存已有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的源泉。这个gegenwärtig(现在的)劳动从来不会出现在流通领域之中。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作过这样进一步的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a)包含在生产商品所消费的劳动资料和原料(如果有原料的话)中的过去的劳动时间;(b)最后追加的活劳动,简单地说,就是借助这些劳动资料而实现在这种原料中的劳动”[4]17。这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说明。显然,这不是我们流通领域表面看到的两种财产的对等交换,这是一个经济物相化中的双重假象:一是假扮成资本家资本(财产)的对象化劳动,这实际上是过去被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成果,然而现在它的社会关系场境本质却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总体性的支配关系;二是被当作工人出卖的“劳动商品”(财产),可交换中实际被变卖的却是工人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力,当这种被支配的劳动能力进入到生产过程后,它自己实现出来的gegenwärtig(现在的)劳动将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秘密源泉。所以,仅仅停留在流通和分配领域的财产关系上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一表征,恰恰可能会陷入经济物相化的表象认知之中,无论是掩盖经济剥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不公的各种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们的争执还是处于流通领域或者分配关系中的公平或改良上,都不可能真正透视这一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本质关系。这里,我们也会体知到,一旦马克思试图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时,他都会不自觉地使用非经济学的哲学话语,他应该是忘记了自己是在面对普通的读者,在写作方式中,专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阐释话语就被更深的研究性话语所“篡位”,公开出版的“书”就突破为思想实验性的“手稿”。于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也就逐渐没影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思想爆燃之中。
三
马克思说,在流通领域中,拥有处于时间中的非对象性劳动的当然就是工人,他还专门说明,“正如货币所有者作为对象化劳动、自行保存的价值的主体和承担者是资本家一样,工人同样也只是他本身劳动能力的主体、人格化”[1]42。这仿佛是说,我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直观看到的资本家和工人并不是真正在场的“人”,他们不过是这一社会生活中特定经济关系反向物相化场境的人格化。这既是历史现象学构境中对经济物相化的批判性透视,也是批判认识论中作为认知对象的社会伪主体,它可能恰恰是“社会关系总和”的否定形式。这让人想起拉康哲学中的否定性的关系存在论:人的个体心理自我会是镜像关系(小他者)的反向人格化——伪自我,而人的个体主体性则会是语言象征系统关系(大他者)的反向人格化——伪主体。可能,这也会成为阐释性话语中入境通道上的顽石。所以说,如果资本家是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场境中的人格化的话,那么工人就是雇佣劳动的人格化。两者都是经济物相化中畸形伪主体的在场。在工人这里,“他应提供出售的唯一商品,就是他的活的、存在于他的活的机体中的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1]41。(3)“Vermöge”一词在这里决不能理解为“财富”(fortuna, fortune),而应当理解为“能力”(Potenz,δúναμιζ)。在这里,马克思专门标注,工人在与资本家交换时出卖的商品不是现成的财富,而是可能性上的劳动能力。马克思在此还特别标注了希腊文中的δúναμιζ(力量)。这当然也是马克思对经济物相化中“劳动商品”的深刻透视,并且工人除了可以出售的劳动能力,一无所有。这导致,如果这种时间意义上存在的劳动能力要实现出来,工人就不得不接受拥有这种“空间上”存在的对象化的劳动条件的资本家的盘剥。
现在他之所以必须出卖他的劳动,是因为他的劳动能力只有出卖给资本才是劳动能力。因此,他现在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capitalistische Production subsumirt)、受资本的支配,不只是由于他缺少劳动资料,而且是由于他的劳动能力本身,由于他的劳动的性质和方式;他受资本的支配,因为在资本的手中不仅掌握着主体劳动(subjektiven Arbeit)的客体条件,而且也掌握着主体劳动的社会条件(gesellschaftlichen Bedingungen),工人的劳动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还能是劳动。(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3-1,Text,Dietz Verlag, 1976,S.254.
这也就是说,这里在劳动主体身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两种生产方式的转换,即从农奴或者小生产所有者脱型和转换为自由工人,这种生产关系变革中最本质的部分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现在,自由了的工人在雇佣关系中变得实质上更加不自由地依存于资本关系,因为他的劳动能力只在变卖给居有资本统治关系的人格化资本家才能成为现实的劳动能力,并且除了一无所有的被迫依附,更重要的方面是工人劳动的性质和劳动形式都深深地受到资本的支配。工人作为劳动的主体,其直接依存的客观的劳动材料和资料都属于资本,同时,全部能够使劳动实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场境也从属于资本的统治关系。关于这个对资本主义生产的subsumtion(从属)问题,将是马克思下面重点讨论的方面。在历史现象学的构境中,在经济物相化表象中可以看见的自由劳动力的自由,本质上是没有独立生存可能性的隐秘发生的不自由的依附性。这恰恰是表面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中秘密的被奴役本质。为此,马克思感叹道,在工人那里:
他没有,即丧失了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使他的劳动对象化的条件(Bedingungen zur Vergegenständlichung),相反地,这些条件,作为财富世界,作为对象财富世界(Welt des Reichthums),隶属于他人的意志,在流通中作为商品所有者的财产,作为异己的财产(fremdes Eigenthum),异己地(fremd)与劳动能力所有者相对立。(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3-1,Text,Dietz Verlag, 1976,S.32.
请一定注意这里马克思所强调的“财富世界”、流通领域的财产和别人的财产,因为这正是从1845年开始,支撑着马克思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话语实践中脱型而来的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话语构境的重要构件。现在马克思认识到,看起来资本家在这种形式上平等的交换中拿出了自己的财富,以等价的方式换取了工人的财产,而实际上,资本家的财富不过是工人过去劳动的对象化成果,而工人根本没有任何财产,他只是将自己无法对象化的劳动能力使用权当作“财产”卖给了资本家。马克思现在说,在可见的物性财产这一经济物相化表面出现的“这种自由的工人——从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能力所有者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产物,结果,是许多经济变革的总结,要以其他社会生产关系的灭亡和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1]42。人们能够看到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发生的财富意义上的“平等交换”,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经过了“许多经济变革”,以至于在经济物相化的迷雾中无法看到这种财富交换背后发生的真实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本质。
资本主义生产(capitalistische Production)的前提是:在流通中、在市场上找到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自由的工人或卖者。因此,资本关系(Capitalverhältnisses)的形成从一开始就表示,资本关系只有在社会的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才能出现。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历史上一定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属于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关系[1]42。
马克思这是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是在流通领域中可以找到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自由工人,这本身就是一个一定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的特定关系——资本关系,或者叫资本支配雇佣劳动的关系。如果说,人身依附等级的宗法关系是封建主义的本质,那么,这种资本支配雇佣劳动的隐秘依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因为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马克思说,“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Oberfläch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出现的商品,它表现为最简单的经济关系,资产阶级财富(bürgerlichen Reichthums)的要素”[1]42。他想告诉我们,在此作为讨论出发点的恰恰是那个以财产多少为尺度的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有产者的社会的表面,可见的商品是作为“资产阶级阶级财富的要素”,然而,如果我们深入一步透视这种经济物相化现象就会发现,这个作为最简单物性财富的商品(财富),也是“以社会成员之间历史上的一定的关系为前提的”,即劳动交换关系中客观抽象出来的交换价值。所以马克思说:
如果我们现在进一步研究,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产品才普遍作为商品来生产,或者说,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才表现为一切产品的一般的、必然的形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只有在历史上特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Grundlage einer ganz bestimmten historischen Productionsweise der capitalistischen)上才会发生[1]42-43。
其实,在封建社会中,用钱去购买一个有价格的商品的现象已经存在了,但是,当商品成为“一切产品的一般的、必然的形式”时,社会关系赋型已经进入到一个以Productionsweise der capitalistischen(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生活。这个新社会不是一个财产多少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本身的历史在场性就是资本关系的集体人格化,至此,马克思就已经实现了自己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上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不是财富关系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是一个资本关系成为社会总体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叫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马克思终于发现,不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也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建立在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我们科学认知的对象。这就完成了一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经过长达近二十年的漫漫理论征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建构基础最终得以完成。这也是马克思一生中继哲学方法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两个伟大发现之后,他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中第三个伟大发现的完成。
我发现,也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思考中,马克思终于使用了资本主义社会(c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这样的重要概念。有趣的现象是,他在同一页,并列使用了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马克思是在讨论重农主义的历史功绩时,提出这一概念的,他分析说,重农主义那里,已经出现了作为人身依附等级的宗法关系的封建主义“被资产阶级化”的情况,这样,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则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重农主义体系就成为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neue c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的表现”。(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3-2,Text,Dietz Verlag, 1977,S.345.似乎在这里,马克思想表达这样的构境意向:“资产阶级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期发展呈现样态,而neue c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成熟社会赋型。第二处出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是在马克思肯定“具有真正斯密精神的经济学把资本家只看成人格化的资本,看成生产当事人”的观点时,他指认:
(1)资本(从而也就是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只被看作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发展的当事人;(2)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aufkommenden c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的观点,对这种社会具有意义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不是享受,而是财富。当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还没有学会把剥削和消费结合起来,还没有使享用的财富从属于自己时,享用的财富对它来说,是一种过度的奢侈。(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3-2,Text,Dietz Verlag, 1977,S.590.
我还注意到,也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资本主义(Capitalismus)这个重要的概念。(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9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3-3,Text,Dietz Verlag, 1978,S.1114.虽然在整个《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里,他并没有普遍使用Capitalismus(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名词形式,但是作为c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c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目标已经是完全自觉的了。这样,马克思的这一经济学手稿也就超出了原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计划,第一次转变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研究的专门论著,它的核心就会是走向资本通过占有剩余价值使自己增殖的《资本论》。实际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无意识爆燃出来的思想实验主体在场,已经是集中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论》的草稿,当然,马克思在自觉意图中开始写作的《资本论》直接初稿是不久后写下的《1863—1865经济学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