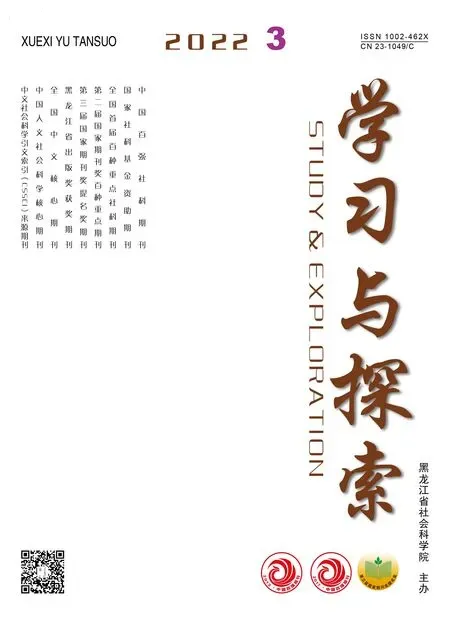卡西尔“符号形式”理论中的“生命”概念及其美学意义
曹 晖,陈 学
(黑龙江大学 a.哲学学院;b.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在1923年出版的《符号形式哲学》第一卷中,卡西尔提出:“‘生命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当代形式。”[1]111-114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其他著作中经常看到有关“生命”的主题。他在《语言与艺术》的演讲中指出:“文化生活总是与有机生命的生活条件息息相关。”[2]114在第三卷的导言中,卡西尔已经指出了写作“生命哲学”部分的初衷,即“定义和证明《符号形式哲学》对作为整体的当代哲学的基本态度”[3]xvi。在《人论》关于符号形式的探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卡西尔对“生命”现象非常重视。也许是碍于篇幅,卡西尔没有具体展开这一论述,但是我们可以在他谈论柏格森、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海伦·凯勒运用符号形式的生命能力、歌德的形态学思想时感受出他对这一理论的热情和兴奋。事实上,卡西尔所论述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所意指的不仅是这个术语在哲学史上通常所指的伯格森、狄尔泰、齐美尔的哲学和他们的追随者的哲学,他进一步将这个术语和从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到海德格尔的后唯心主义(post-idealistic)思想联系起来[4]x-xi。在卡西尔的词汇中,“生命哲学”并不仅仅指一种思想学派,而是指哲学思想的广泛的根本性转变,可以描述为试图在更全面的意义上陈述先验问题本身。
一、作为与“精神”产生整体性关联的生命
在论述“生命”概念时,卡西尔将其与“精神”这一概念相关联和比较,这源于哲学形而上学的时代要求。卡西尔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命”和“精神”的对立是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它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以至于它逐渐地吸收和消除了在形而上学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其他术语。“存在”和“生成”、“一”与“多”、“物质”和“形式”、“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关系,现在似乎都融入了这一完全基本的对立中。各种各样的、极其不同的思想活动,好像都受到秘密的地下力量引导似的,一次又一次地指向这个特殊的形而上学中心[4]8。这一时期,尼采和伯格森、狄尔泰和齐美尔,都参与了这场改变基本形而上学对立的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卡西尔对生命和精神的关联性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为了在《符号形式哲学》的第三卷中加入这一主题的内容作为最后一章,他推迟了第三卷的出版时间,但是由于这部分篇幅过长最终没有放入这一卷中。(1)克罗伊斯(John Michael Krois)和韦林(Donald Phillip Verene)在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第四卷的导言中谈道,在1929年出版的《符号形式哲学》第三卷中,本来卡西尔有284页是讨论生命和精神问题的(这一部分在1928年4月16日完成)。但是由于第三卷已经有571页的内容,再加上近300页的内容难免会变得过长,篇幅变得沉重,因此,卡西尔就将这部分拿了下来放到手稿中,打算将其放到第四卷发表。卡西尔在其前言中指出,他最终决定以“生命与精神——对当代哲学的批判”(“ ‘Leben’und ‘Geist’zur Kritik der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为标题先单独发表这篇文章[3]xvi。他的计划是接下来将其放入《符号形式哲学》第四卷中。不幸的是,1945年卡西尔意外离世,《符号形式的哲学》第四卷直至1996年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主题也成为该书第一章的内容。
克雷格·勒鲁(Craig Leroux)认为,在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形而上学中,“生命、精神以及它们之间持续存在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中心问题”[5]。在对生命和精神的研究中,卡西尔吸收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思想。事实上,尽管卡西尔的“符号形式”主要来源于康德的“图式”,是将康德的理性批判转向为文化批判的结果,但卡西尔受到深刻影响的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则是黑格尔。他在1929年写作第三卷的宗旨之一就是通过构建一种知识现象学,将前一、二卷的内容连接起来,在这种现象学中,科学思想被证明是伦理学和认知理论的前几个阶段的产物。他说:“哲学反思并不把(意识的)终点和起点对立起来,而是把这三者都作为一个整体运动中不可分割的因素。在这一基本原则中,符号形式哲学与黑格尔的表述是一致的,尽管它的基础和发展必然有所不同。”[3]xv因此,卡西尔在对生命的研究中自觉地运用了一种源自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并与当代威廉·狄尔泰、亨利·柏格森、马克斯·舍勒和乔治·齐美尔的生命哲学达成一致。
在1923年亨德尔为第一卷所作的导言中,探讨了卡西尔的“生命”(life)观与黑格尔的“精神”(spirit)以及舍勒“宇宙中的人”(man in the cosmos)之间的关系。亨德尔说:“卡西尔在他对舍勒‘宇宙中的人’这一主题的批判中赞赏地提到了黑格尔。黑格尔把精神和生命的关系视为自然领域中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推进。然而,在舍勒的哲学中,生命和精神似乎处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对立之中。但是,卡西尔说,它们不能‘属于完全分离的世界’,因为如果如此的话‘它们完成一件完全同质的工作是如何可能的?在构建一个特定的人类世界,即有意义的世界的过程中它们的合作并相互渗透是如何可能的?……难道这一渗透只不过是一个开心的意外吗’?这一问题是以设问的形式提出的:卡西尔本人坚持精神和生命的合作和相互渗透。”[1]61事实确实如此,卡西尔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继笛卡尔以来,唯心主义哲学在人类精神史中的具体而系统的最新尝试。在第三卷导言中,卡西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简短的介绍并明确指出:“在谈到知识的现象学时,我使用的‘现象学’这个词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而是黑格尔所建立并系统地奠定的基础意义上的。对黑格尔来说,现象学成为哲学知识的基础,因为他坚持哲学知识必须包含文化形式的整体,而且在他看来,这种整体只有在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换中才能显现出来。真理就是整体——然而,整体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呈现出来,而必须由思想以其自身的自主运动和节奏逐步展开。”[3]xiv卡西尔认为,起源于德国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学派的精神(Geist)和生命(Leben)的二元论在当代哲学人类学中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如果将精神和生命视为不同的秩序,而非相互对立的实质性本质,那么这明显的二元论就可以得到解决。精神可以被认为是生命的转变,并通过生命的回归而发生。此外,卡西尔赞同齐美尔对生命的超越性看法,认为与精神相比,生命并非有限不可超出自身的,生命以其超越自身而获得更大的自由。正因为如此,卡西尔将齐美尔赞为“当代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最好的人”。
生命和精神的关系还体现在卡西尔神话理论的阐释中,这体现了卡西尔有别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哲学的浪漫主义倾向。神话被卡西尔视为一种“生命形式”,其中身体活动成为文化意义的媒介。 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的特点是关注“更高”和更复杂的文化形式背后更“原始”的世界呈现形式——关注主要用自然语言表达的对世界的普通感性认识,最重要的是,关注处于最原始水平的神话世界观。它们位于精神生活的更深、更自主的层次,然后通过辩证的发展过程产生更复杂的形式。
二、作为一种不间断运动的生命
对卡西尔来说,生命现象不是固定的东西,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生命、实在、存在、实存不过是指同一基本事实的不同术语。这些术语并不描述那种固定、僵死、实质性的事物,它们应被理解为过程的名称。”[2]142在《符号形式哲学》第四卷中,卡西尔赞赏地引用了齐美尔对生命的定义:“生命是一种不间断的流动,是有一种被包围在载体和内容里的东西,它围绕着中点形成,是个性化的,因此总是一种不断地跨越它的边界的有界的形式。这就是它的本质。”[4]9作为生命,人类往往以过程为特征,但他们不仅参与了生命过程,而且通过符号形式意识到自己生命的存在。正如卡西尔所说:“神话、宗教、艺术、科学不过是人在其对生命的意识和反省解释中所迈出的不同步伐。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具有其自身折射角的人类经验之镜子。”[2]142我们可以通过回溯亚里士多德对生命的关注探究卡西尔生命概念的来源及其内在规定性。
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能动学说可以体现在他的“形式论”中。其中所表现的功能性、流动变化性以及生物有机体的过程性和时间性恰好表明亚里士多德对生命和过程的独特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推崇感官和感觉世界的价值,他开篇就指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6]亚里士多德试图从生命这一维度来解释理念和知识的世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在这两个领域中,我们可以发现同样不间断的连续性。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包含着目的论因素,在阐释实体(本体)的这一概念时,亚里士多德就对其做了规定。实体是原因,即“是其所是”。而“是其所是”的意思就是强调形式先于质料的先在性,或未完成时态。(2)苗力田先生在《形而上学》的注释中指出,“是其所是”的翻译指的是形式或本质意义下的实体。这个词组具有人称和时态的变化,不用现在时态,而用表示过去了的未完成时态en。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们多方查证了此类的用法,他们以不同的论证,认为这一未完成体所表示的是先于,甚至把它作为形式先于质料的佐证。参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在《论灵魂》第二卷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强调了“质料是潜能,形式是现实”[7]的观点。他认为,现实先于潜能,因为潜能需要通过现实才能实现,或者说,只能通过现实,潜能才能将潜在的因素变化为现实的因素,所以现实是先在的因素,没有现实,潜能也无法实现。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是一种不断的实现活动。亚里士多德将知觉活动(个体性)和理智活动(普遍性)联系在一起,认为知觉和认识、理念和知识是具有连续性的行动,它们如同生命一样是一种不间断的运动。
亚里士多德形式的生成目的论为后世发展提供了诸多借鉴。卡西尔指出,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生命能动指向充分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观与柏拉图的知识观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科学和知识可以单凭知觉活动而达到,但是当他从生命的角度出发来探讨问题时,他将生命的一体性、能动性作为探讨人的问题的重要维度。当作为一个生物学家而非哲学家时,亚里士多德拒绝感觉和理智、实体与现象的截然划分。卡西尔借由对亚里士多德的评价,指出了人的本性与生命活动的意义。在研究人的过程中,有机的生命活动是无法回避的,一切人类知识都来源于人类本性的一种基本倾向——这种倾向在人的各种最基本的行为和反应中都表现出来。感性生活的全部内容是被这种倾向所决定并且充分体现着这种倾向的。
在《符号形式哲学》第四卷中,卡西尔赞赏阿那克萨戈拉对生命和生成的看法,而这也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对阿那克萨戈拉评价的启发。亚里士多德接受了阿那克萨戈拉的生命观和生成概念,并在《物理学》中加以阐发:“由于看到了任何东西都生成于任何东西,阿那克萨戈拉就认为任何部分都是一个与整体同样的混合体。……万物必然在某个时候曾经在一起,而后在某个时候才开始被运动。”[8]卡西尔将阿那克萨戈拉的生成论用于对符号形式生命性的阐释之中:“阿那克萨哥拉谈到自然物体时说,它们都是一种胚种(panspermia),也就是说,它们不是由独立的离散元素组成的;相反,每一个物理整体都包含所有元素的胚芽和种子。这种关于自然组织、物理结构的说法,在更激进、更深刻的意义上适用于文化产品。”[4]6
卡西尔的生命哲学关注生物学中的生命有机形式。受到汉堡的同事、生物学家雅各布·冯·乌斯居尔(J.Von.Uexkull)《理论生物学》中有机形态功能性特征的启发,卡西尔强调生命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乌斯居尔的“Umwelten”(世界或环境)理论也为卡西尔关于动物和人类行为差异的概念提供了基础。在乌斯居尔看来,物理学试图用因果关系来解释世界上所有的联系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这意味着从科学中排除所有其他方式的联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因果决定论并不是我们用来解释世界的唯一规则。乌斯居尔始终坚持“内在目的”的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的哲学。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意味着每个单子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宇宙(cosmos),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了整个大宇宙(universe)。但所有这些个体世界都是通过先定和谐而彼此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它们是对同一宇宙秩序的表达。这些思想影响了17、18世纪的哲学方向,也影响了历史和生物学等知识领域。赫尔德在历史哲学中运用了这一观念,他反对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即将人视为创造的目的,尤其反对将受过教育的人的观点作为所有人的观点的做法。对赫尔德来说,人类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所有形式的总和中才能得到理解。每种类型都是必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要价值。歌德将这一基本思想从历史领域转移到生命领域。他也不断强调,从生命的整体中挑选一个单一的种族,并把它设定为目标、尺度和准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单个人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的模式[9]203-204。歌德强调生命的整体性,但并不固执于整体的永恒和静止,他首创了“形态学”(morphology)理论。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亨德尔(Charles W.Hendel)指出:“歌德对卡西尔的重要性怎么估量也不过分。”[1]30而卡西尔则由衷赞叹道:“形态学”的术语“对于18世纪的生物学来说,意味着何等重要和关键的方法论转向。一种崭新的知识观念,正是和歌德的‘形态学’思想及其‘有机自然之生成与转变’的概念一起被创造了出来。”[10]而这种有机体不断发展变化的理念推动了歌德对“本原现象”关注,从而也促成了卡西尔在探讨“符号性的包孕”概念时所秉持的知觉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原则。
三、 “符号性的包孕”:知觉整体性在符号形式中的“生命”体现
卡西尔在《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三卷中探讨了“符号的包孕”(Symbolic pregnance)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凸显了卡西尔符号形式对生命存在维度和对知觉整体性的关注,更体现出卡西尔哲学面向未来的指向和审美超越原则。卡西尔指出:“所谓符号的包孕,我们指的是作为感性经验的某种知觉同时包含它所直接地、具体地表象的某种非直观意义的方式。”[3]202这种“符号的包孕”本身是有序的,属于一个确定的意义秩序,是一种有意义的生命存在、一种“先验的真实”,是“本质上的第一要素”[3]203。卡西尔的重要研究者克罗伊斯(Krois)认为,由于德语“Pragnanz”在英语中没有对等词,他建议将这个概念用英语翻译为“pregnance”。这个术语包括两个含义:冲压(stamping)和分娩的行为[11]。克罗伊斯认为,卡西尔的符号意义概念的来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在阿比·沃尔堡的汉堡研究图书馆发现的人种学和人类学文献,失语症和相关病症的医学研究结果中,特别是在科特·戈德斯坦的工作和雅各布·冯·乌斯居尔的理论生物学中。”[12]而从哲学上来说,对“符号性包孕”研究的根源在于意图弥合笛卡尔以来的感性和理性的分立状态,这种状态如梅洛-庞蒂所描述的:“经验主义所缺少的是对象和由对象引起的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理智主义所缺少的是思维原因的偶然性。在第一种情况下,意识过于贫乏,在第二种情况下,意识又过于丰富,以至任何现象都不能引起意识。”[13]因此,在卡西尔看来,沟通和铺设人类灵魂与现实之路的是人类心灵的全部,包括它的功能、冲动、想象、意志和思维的总和。而“现实的真正概念不可能被表述成一个存在的简单和抽象的形式。它实际上包含了全部丰富多样的精神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新的‘符号形式’——不仅指认识的概念和体系,而且包括艺术、神话和语言的直觉世界——都再现了一个由内至外的内容,即‘一个世界和心灵的综合体’,它独自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真正的统一体。”[1]46因此,对“符号性包孕”的理解重点应在于突出知觉的整体性和能动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了解“符号性包孕”的内涵及其美学精神。
首先,“符号性包孕”和“包孕性的时刻”(pregnant moment)有一定的相似之处。18世纪德国的几位美学家莱辛、赫尔德和歌德都对后者有明确的表述。马丁·舒茨(Martin Schütze)认为,“包孕性的时刻”这一命题是与“形式的完善”以及“永恒”的概念相关的。他说:“用永恒的(ewig)这个词来表示形式的完善是18世纪最后一代伟大的德国作家的共同之处,它是一种超验主义的、主观的永恒概念。”[14]莱辛(Lessing)在《拉奥孔》中的所提出的著名的“最富孕育性的顷刻”命题隐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也意指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联系,即现在孕育着未来,它是达到顶点之前的片刻,这一时间性中充满了想象力和可能性。莱辛用它来阐释在空间艺术中,画家或雕塑家如何将对象的动作在静态的艺术品中表现出来,他说:“在这些顷刻中各种样子和关系之中,每一种都是以前的样子和关系的结果,都能成为以后的样子和关系的原因,所以它仿佛成为一个动作的中心。绘画在它的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15]而赫尔德(Herder)则在诗歌和艺术中通过结合亚里士多德对“功”(work)和“能”(energy)概念的区分,对这一命题进行阐释。“功”所表示的是持久的、永恒的(ewig)意味:“艺术家所要描绘的并非真实自然中的某个时刻,因为如果真的是永恒的,那么这个时刻将是没有生命的,相反,他们所描绘的是‘长久而幸福的表现、永恒的时刻等’(den langen, seligen Ausdruck, the ewige Moment, i.e.,)。”[14]也就是说,艺术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一种综合,通过艺术的完善,防止令人厌倦的重复观察,因此艺术中包含着抽象的、永恒的主观感受。艺术家不应该只着眼于一个完整的、至高无上的、能吸引我们全部注意力的时刻,而应该着眼于一系列不间断的动作,每一个动作都只是一个环节,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高潮。
而赫尔德认为,绘画中的“美”应定义为这样一种品质,“即通过将所有部分同时和谐地设置,使整体成为永恒图景(ewige Anblick)的合适对象”[14]。而歌德也从生物学的“类型”入手,探讨了对这一“理想的思维方式”的理解。歌德是林奈的伟大追随者,他的形态学更注重生命的转化过程,而不仅仅是抽象的结果。在诗作《恒久寓于变化》(DauerundWechsel)中,歌德表现出对在“瞬息万变中揭示出永恒”的“理想的思维方式”(ideal way of thinking)的理解。在永恒与变化之间的联系和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中,他寻求“理想的思维方式”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卡西尔通过引用歌德的话来表达对歌德理论的认同:“通过思想的‘理想模式’……我们应该逐渐提升至正确的观点,‘在那里,人类的理解力和哲学是一体的’……这种存在与生成、永恒与变化的独特混合,被理解为形式的概念,这成为歌德生物学概念的基础。”[9]138(3)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1704)中写道:“现在孕育着未来,并且满载着过去,一切都在协同出发。”参见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
卡西尔的“符号性包孕”具有莱辛、赫尔德和歌德的的这种“最富暗示性的顷刻”和“瞬息万变中揭示出永恒”的意味。但是它更直接的来源则是莱布尼茨的哲学。卡西尔指出,这一命题中包含着预期,是“莱布尼茨所说的‘包孕着未来’(praegnans futuri)的另一种表述,即现在充满了未来”[3]203。亨德尔称莱布尼茨是卡西尔“丰富灵感的来源”,因为毫不过分地说,是莱布尼茨将生命的特征写进了终极实在的本质中[1]23。在《启蒙哲学》中,卡西尔准确地抓住了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中的“单子”的生命特征及其创造的能动性:
莱布尼茨的“单子”不是一个算术单元,也不是一个纯数字单元,而是一个动力学的单元。这种单元的真正对应物不是特殊性,而是无限性。每个单子都是一个活的能量中心,正是单子的这种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构成世界的统一性。单子“在”,就因为它是能动的,而它的能动性正在于它不断地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断地从自身展开这些状态。……单子的每一简单因素都包含着它的过去,孕育着它的未来。……是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变异中的存在,变化中的恒久[17]。
在莱布尼茨哲学中,僵化的形式概念逐渐被打破。新的有机新哲学的基础被确立起来。在卡西尔看来,包孕并非指数量累积或联想组合,不能用简化为纯粹的推理判断行为来解释,而是一股生命和思想之流,通过流动的运动产生意识的多样性和内聚力、丰富性和连续性。无疑,符号的这种孕育、变化、预期流动性已经具有了美学的象征意义。“符号性包孕”不仅指的是当前的经验要求将过去的经验连接起来,而且要有将自己投射到未来的能力。正如卡西尔所说:“自我,认为自己是‘置于时间之内’的,它否认自己是静态事件的总和,而是一个向前延伸到时间中的存在,并努力从现在走向未来。如果没有这种形式的努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表征”,那么对我们来说,一个内容的实现就永远不会开始。”[3]180事实上,我们对现在的体验既受到我们对过去的记忆的制约,也受到我们对未来的期望的制约。所有的行动都需要我们整合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短暂的时刻。
其次,卡西尔的“符号性包孕”也与“格式塔”(Gestalt)理论相关联,并更深地基于歌德“本原现象”(Urphänomen)所指向的原始感知。“格式塔”即知觉的完形(perceptual Gestalt),意味着感官体验是一个生成或闭合的连续过程,知觉并不被理解为感觉数据的接收,而是一种完整的形式。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韦特海默(Wertheimer)使用术语“Pragnanz”来强调感知过程与给出清晰轮廓的行为的类比。格式塔另一代表学者卡夫卡(Koffka)认为,“包孕法则”或“完满法则”(law of pregnance)(4)Pregnancy一词除了“怀孕”的意思外,还有“完满”“意义或意味丰富”的含义。参见韦氏词典: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pregnant.2021.12.8。是指,“只要当时的条件允许,心理组织将永远是‘完善的’”[18]。这里的“完善的”是指形式的稳定性、封闭性或连接性,因为“包孕(Prignanz)影响形状、大小和表面属性,因此,如果场的条件改变得不太剧烈,那么对象最重要的方面就会被保留下来;也就是说,‘事物’像旋律一样是不变的或可转置的”[12]。卡西尔把形容词“符号性的”(symbolic)加在“包孕”(pregnance)上,创造了他的术语“符号性包孕”,因为实际上他用格式塔的“完满法则”描述了感知的整体性和意义在感知中体现的方式[3]202。卡西尔认为,“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每一种特殊的格式塔和格式塔形式也都对应着一种特殊的“包孕”(Praegnanz),既有有空间和时间上的“包孕”(Praegnanz),也有理论上的和美学上的“包孕”(Praegnanz),但在这里我们必须进一步从我们的角度说明这个问题,即“包孕”(Praegnanz)的具体特殊性是格式塔的具体差异的首要基础,并使其成为可能。所有表征(Vergegenwdrtigung)始终是特定“意义上”的表征[12]。卡西尔在第三卷中引用考夫卡的观点:“诸如‘友好’或‘不友好’之类的现象是极其原始的,甚至比蓝色的斑点更原始。”[3]65并提出知觉组织、表达和意义的初步统一是每个知觉的基础的观点[3]62。这种最初的统一被称本原现象(Urphänomenon)或表达现象(phenomenon of expression/Ausdruck),它是卡西尔所说的思想的表达功能(Ausdrucksfunktion)的产物,它与我们对周围世界中充满情感和情感意义的事件的体验有关,无论是令人渴望的还是可恨的体验,还是受到安慰的或威胁的体验。事实上,对卡西尔来说,这种意义是神话意识的基础,也解释了神话最显著的特征,即它完全无视外观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在克罗伊斯看来,这是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基础和先验原则。
“本原现象”一词最初来自于歌德,是歌德在1798年所写的一篇无标题的文章中首次提出的,也被称为“纯现象”(The Pure Phenomenon),即最初始、形态最简朴的原型。歌德将其与科学现象(通过实验发现的现象)和经验现象(日常常识中出现的现象)区分开来。对歌德来说,“本原现象”不能用因果推理来理解,而更需要用感知,因为其中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黑格尔也对歌德的“本原现象”很重视,他认为,“歌德的‘本原现象’并不是意味着一种理念,而是意味着一种精神——感性的本质,在纯粹的本质概念和感性世界的偶然现象之间进行调和”[19]。因此,“本原现象”既是一种知觉现象,也体现出知觉的局限性。歌德曾指出,通过测量的方法将颜色的差异转化为数字的差异会因此失去要解释的现象。对某些颜色,如火红或冷蓝的感知是一种“本原现象”,它无法作进一步的解释。
卡西尔借鉴了歌德的“本原现象”思想,并将其与“符号性包孕”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生命就是一个本原现象,它是基础的、首要的;它无法被定义,也不能作为概念来理解,符号是它的表现方式。“最根本的实在,在歌德看来,最终极的现象,的确只可以用‘生命’一词去称呼。这种现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以体验的;但它也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它不接受任何定义和任何抽象的理论解释。我们不可能解释它,假如解释是指将一种未知的事实还原为一种众所周知的事实的话:因为不存在任何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既不能给生命以逻辑定义,我们又不能找到生命的本原或第一原因。”[2]142克罗伊斯(Krois)认为,“符号性包孕”等同于“象征意义”(symbolism)的概念,即通过对“象征意义”的理解即可解读“符号性包孕”的内涵和它所承载的原初的知觉指向。“符号性包孕”描述了象征意义对人类世界的“结构和建构”的积极作用;而在知觉中,“符号性包孕”作为一种象征出现,从而使感官将自己“呈现”为一种超出它本身的东西。卡西尔指出:“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感知仅仅是被给予的……相反,每一种感知都包含一个明确的“方向特征”,通过这个“方向特征”,知觉指向它的此时此地以外的地方。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觉差别,它本身却包含着经验的整体。”[3]203
在卡西尔的现象学中,本原现象也被称为表达现象(phenomenon of expression/Ausdruck)。这体现出卡西尔在知觉研究中对“意义”的重视。在卡西尔的《知识现象学》中,意义是一种“本原现象”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卡西尔拒绝所有对“表达意义”的主观解释,拒绝它具有综合性、意向性,甚至是“关怀”的存在结构,而认为它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就如同“符号性包孕”一样,意义是一个“本原现象”或“基本现象”。这一主张表明因果解释无法穷尽知识领域。人的生命,就其能够理解和反思而言,不能被简化为动物世界的那种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包含了比动物生命更多的东西,即符号性包孕的要素。而人也不只处于一个法则的、物理的“知性世界”中,“我们还有一个生命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不能简单地思考绝对的法则和机械结构,而必须构想出解释时间变化的变化形式。”[1]33因此,卡西尔反对以实质性的术语来设想现实,事实上,存在是体现关系的真实过程,而非事物的固定顺序,身体的“同一性”概念需要作为关系体现出来。他将“关系的体现”表述为三个基本现象(Basisphenomena),即生命、行动和劳作(work)[12]。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对身体主体的考察中,多次引用了卡西尔在《知识现象学》中对意义的分析,特别是符号性包孕的关键思想。梅洛-庞蒂明确地遵循卡西尔的学说,即符号性的包孕先于任何一种给予意义的行为,它充满了原始感性和生命性。这里的原始感性不同于意识现象学,它不是有意识的综合,而是生动的原初的感性。卡西尔以神话为例阐释原始感性,在卡西尔看来,神话是一种主体间性的现象,它是“以原始感知模式为基础”的表达意义的“符号形式”[3]62。卡西尔反对用“意识行为”来理解神话或审美意识,如树林中的窃窃私语或沙沙作响,影子在地上的快速移动,水面上的灯光闪烁,所有这些现象,在神话意识中似乎是生动的,都是直接表达出来的。将这些表达的现象视为解释、意图、综合或移情行为的结果,会将某种东西引入不存在的现象中,而忽略了表达的独特之处,即即时的、生动的感官整体性。
四、艺术“构形”:生命经验活动的真理呈现
凯瑟琳·吉尔伯特(Catherine Gilbert)在《卡西尔的艺术定位》一文中认为,尽管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中没有一本关于艺术的卷本,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审美符号(即艺术)是卡西尔符号形式的顶峰[19]404。 哈里·斯洛克豪尔(Harry Slochower)认为,“艺术问题不仅是卡西尔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他方法和体系最具特色的扩展”[19]404。
卡西尔对艺术和美的阐释主要围绕着“构形”而展开的。构形(formative)即赋予经验以形式,也就是说,形式是用来规范和组织经验以便使其成为人类的认识对象的存在,也即知觉的完形和建构过程,其中不仅展现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而且显示出生命和存在的真理性。卡西尔从歌德那里借用了“Liben”(生命)一词,并在1941—1942年在耶鲁大学哲学讨论班上所做的题为“语言与艺术”的讲演中,引用了歌德的话:“真理,或与之同义的神圣,都不可能直接把握到,我们只有借助反光才能看见它们;即借助符号或例示,借助某个单一并相关的现象。我们把它作为不可理喻的生命来认识,然而我们又不能放弃理喻它的希冀。”[2]142
与康德一样,卡西尔将艺术放在人类认知的层面上去认识和理解。康德认为,形式是我们人类知觉得以形成的普遍和必要的条件,而且它的形成逐步成为我们智力可以理解的。形式因此“建构了”我们整个世界的经验[9]14-15。卡西尔认为人在面对经验对象时,总是将其提炼加工并加以解释,使外物成为自我的思想和形式化的存在,因为人在未将对象形式化和结构化之前,对象是无法被认识和把握的。“无结构不仅无法去想象,甚至也不能被客观地观察到,抑或不能成为一直觉的对象。”[21]53人类借用符号来认识事物,而符号就是形式化和结构化的结果,而艺术符号也是如此。卡西尔认为,“艺术的领域乃是纯粹形式的领域。它并非纯属色彩、声音、可触摸的性质的世界,而是型态和构制、曲式和节奏的世界”[2]134。而艺术的形式也并不是空洞的形式,它是人生经验的组织和构造,艺术可以包含并渗入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当我们沉浸在对一件伟大的艺术品的直观中时,并不感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分离。因此,艺术与其他文化一样,是理解人类自身发展和自我建构的一个途径。卡西尔认为,18世纪的哲学家对这种人性的独一无二的构形特征非常重视,如赫尔德和洪堡把这种愿望和能力视为语言的本质,席勒将其视为游戏和艺术的本质,康德将其视为理论知识结构的本质[21]17。构形的原则也体现在语言、神话、历史中。卡西尔对历史的阐释也体现出这种构形性,他认为回忆是一种构造活动,历史上的文化成果并非是给予的,而是人类构建的。历史的发生和人类对它的重建是一种反方向的过程,这是因为我们要找到历史的结构和逻辑。而人具有使思想客观化并形成坚固的形态的能力,这其实就是一种构形活动,也是人之为人非常重要的特征和能力,否则人类无法生存在人类世界的宇宙之中。因此卡西尔指出,“伟大历史学家们的才能正是在于:把所有单纯的事实都归溯到它们的生成(fieri),把所有的结果都归溯到过程,把所有静态的事物或制度都归溯到它们的创造性活力”[22]292。而“历史就是力图把所有这些零乱的东西、把过去的杂乱无章的枝梢末节熔合在一起,综合起来铸成新的形态”[22]108。可见,历史、艺术等都作为符号形式成为人类思想和精神形式化和客观化的重构力量。
人类总有赋予经验以形式的愿望,这是人性使然,因为形式和结构化的过程是“一种心灵的过程,作品由这种过程而出”[21]153。无论是对艺术欣赏还是对艺术创造来说,构形性的过程都是必然的先决条件和决定性的特质,因为“那种不能感受色彩、型态、空间形式和类型的人,遂被排除在艺术作品大门之外,由此,他不仅被剥夺了审美快感,而且还丧失了向最深层的实在切近的可能”[2]134-135。正是艺术的构形性向我们揭示了人生的深度,这是我们仅仅借由对日常事物的领悟是无法企及的。正如奥克斯(Oakes)在为齐美尔《社会科学解读论文集》所做的导论中所指出的:“尽管形式的范畴不能再现现实生命的属性,也不能从生命中推导或衍生出来,但形式本身是由不断的生命能量创造出来的。”[23]在艺术形式中,展示出的人的生命、生存和人类最普遍共同的情感,它是“人生的全部领域,是人生所有极端——快乐与忧伤、希望与恐惧,兴奋与绝望——之间的连续不断的震颤”[2]161。
构形是能动性的,构造的是具有动态的、生命力的形式。换言之,它不是恒定的、静止的,而是处在不断地变化运动之中的。卡西尔认为,美感也并非是被动的“被知觉的”的产物,而是“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性,而这种生命力只有靠我们自身中的一种相应的动态过程才可能把握”[22]238。美感的获得需要人的心灵的积极参与,美是一种“构造活动”。经过构形,知觉创造出一个形式的空间,即希尔德勃兰特所讲的“知觉空间”,它是一个新的领域,“不是活生生的事物的领域,而是‘活生生的形式’的领域[22]239。而每一种形式都是一种动态的生命力量,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运动,是对立的统一、悲伤和欢乐的集合体,“是以人类情感从最低的音调到最高的音调的全音阶;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运动和颤动”[22]236。所以卡西尔反对那种将艺术称为对空洞的形式的欣赏和享用的看法,因为构形的艺术关注的是全部生命的整体,是人生的真理和实在。如一个伟大的雕塑家,他的大理石作品就“不是死的材料,不是一块质料,而是充满了内在生命,充满了生命运动和能力的东西”[24]。艺术和语言一样,不仅仅是“第二自然”,而且经过符号构形的独特活动,艺术体现出人类整体的功能和能力。通过这种能力,人类组织和构造了自己的知觉世界。艺术作品就是人性或内在生命在直观、形象的感性形式中的显现,在对艺术作品纯形式的审美直观中,人既可以看到自己,也可以看到整个世界。
结 语
在卡西尔看来,生命是时间的展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融合在一起的存在,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在其中开展。符号本身既不是本体,也不是绝对,而是“现象”。符号是存在的,但是它并非本体的存在,而是现象的存在,它是历史的、经验的现象,而非超时空的绝对理念。它具有功能性、可能性、间接性和包孕性的特征,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把握方式和主体的一种能力。卡西尔通过接受莱布尼茨、康德、歌德、黑格尔以及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探讨了在以符号形式为中心的生命观中,生命与精神、理性和感性、事实与理想在知觉中如何结合在一起并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此外,生命的真理性的经验活动也体现在艺术构形中,构形的艺术关注的是全部生命的整体,凸显的是人生的真理和实在。
事实上,卡西尔的“生命”观还很集中地展现在他对神话理论的阐释中,限于篇幅,只能略述一二。卡西尔曾批评弗雷泽认为神话是“原始科学”的说法,因为这种观点歪曲了神话和科学。科学关注的是作为“它”(it)的世界,而神话是万物有灵论的,关注的是生命的统一。在卡西尔看来,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占星术是一套使用数学计算的高度编码的信仰,并成为人类思想的一项非凡成就,但它并非科学,而是神话的系统化。如它对恒星和行星的考察并非聚焦于它们的客观属性,而是集中在它们的“影响”上,它们好战、和平、精力充沛或被用来影响人类的性格和命运的其他个人特征。天体的这种个性化集中在它们独特的特征上,而不是像科学那样能够努力去概括,从而根据普遍规律的非个人系统来统一地看待所有天体。因此,正如克罗伊斯指出的,“即使将神话放入一个体系,也仍然是神话”[25]。神话中充满了生命和情感因素,但是这又绝非个人的情感,而是普遍化的生命和情感。神话的“生命观是综合的,不是分析的”[22]128。这种综合体现为以情感为基调渲染一切现象。“神话是情感的产物,它的情感背景使它的所有产品都染上了它自己所特有的色彩。原始人……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22]128神话中也包含着客体意识,但是神话中的客体意识并非经验科学中的“稳固的、完成的状态和以它们赤裸裸的‘自身’‘被给予’意识”[26]33,而是“由这种综合的统一体所组成……凭藉意识的基本方法、直觉和纯粹思维产生一种形成作用的产物”[26]33。换言之,神话的客体意识是主动的、建构的、积极参与的意识,这种意识既是生命活动的产物,也是符号形式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