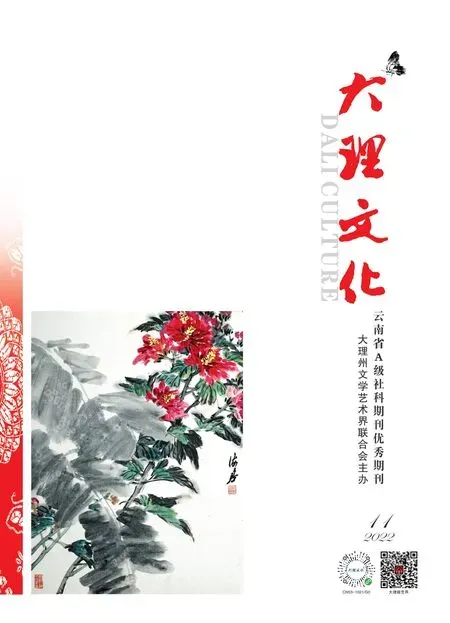诗歌是现实生存和文学梦想博弈的结果
—— 祥云农民诗人赵荣诗歌赏析
●李雪
近年来,祥云县的文学创作以其蓬勃的发展态势,逐渐引起了大理州乃至云南省文学界的关注。祥云的农民文学爱好者农忙种地,农闲创作,其文学创作的脉搏随农村改革、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发展而起伏跳动,涌现出以吴奎南、席政、张继前、赵荣、山雨、李志发等为代表的农村作家群,他们闲时笔耕,忙时农耕,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盛开在乡村间的灿烂之花。
赵荣是这个群体中很有创作个性的诗人。赵荣,男,普淜镇大井村人,右眼四级残疾,出版有诗集《远山》《短笛》。写诗近八百多首,发表作品近一百多件,三次自费到北京参加诗歌研讨会。他一边种地、放羊,一边努力写诗,诗歌带着土地和阳光的气息,亲切温暖,令人回味。对赵荣而言,笔者评论的不完全是诗歌,而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
一、农村生活与文学创作
大井是祥云县普淜镇的一个村子,距离县城90公里左右,很普通的山村,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子里出了一个扛着锄头放着羊却天天口袋里装着一本小笔记本的诗人,他就是赵荣。农民诗人赵荣今年70岁了。
2012年,赵荣公开出版第一本诗集《远山》。2020年8月,赵荣公开出版第二本诗集《短笛》,这是极其不容易的两部诗集。他的每一本诗集都是朴素的,完全是作者的心路历程。读者读诗的时候,脑海里应该会冒出一个场景:赵荣佝偻着身子挖着地,身边有一群黑山羊吃草,太阳暴晒,汗滴顺着赵荣黑瘦的脸颊流下来,他举手抹了一把汗,掏出口袋里的小本子,摸出笔,竟然就开始写起心里的句子来……一个把诗歌爱到这样极致的农民,在别人看来简直就是癫狂!在他的诗句里,有老石匠、镰刀、树墩、马缨花、桥、牵牛花、仙人掌、大井、大豆、炊烟、泥土、土豆、小院、泥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细细碎碎、日出月落,都化成他感悟生活生命的诗句。每读到他那些混合着阳光、土壤、汗滴甚至羊粪各种气味混杂的诗句时,读者的内心似乎寻找到最踏实的归属感,因为,所有的人,最终都是属于土地的。
赵荣在他的第一本诗集《远山》的自序里这样写道:“远远的山上会有什么呢?司空见惯!思空见惯!一条能容下脚的小路,一头系着古老的深处,一头连着浅浅的炊烟,庄稼和牛羊。香车不至,官人不达。远山,裸露着血色的脊梁,荫护着潮湿的凹滩。野草深深浅浅,树木叶绿叶黄,风永远是那个脾气,想来就来,想去就去,不知家在何方?悬崖,冷冷地翻阅着无边的时光。溪流下,不停地把日月歌唱……一个人,有一个坏了规距的山里人,一手拿锄,一手拿笔,在种苦荞、洋芋的同时,破天荒地在另一块“地里”种一种五谷之外的食粮。经过半辈子的打磨,他笔下的地里,终于有了收获,月积年累,便形成了远山中的《远山》。”这个“坏了规矩的山里人”,说的就是他本人。
在赵荣的笔下,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身份证》不是“装在衣兜里/而是裸露在手上”,这是很有画面感的诗句。山民们不愿寂寞,于是有了《山歌》,“山歌/从身旁飘过/竟然风干了/我满身/湿漉漉的寂寞”。《山村的早晨》人们很忙,一大早就下地的下地,上山的上山,就连守家看门的小狗,也有事外出去了。于是“村里/只剩下鸡们鸭们/情愿不情愿地/看守着/村边/门前的/时光”。总之,这《远山》上的一切,都是司空见惯、小而又小、凡而又凡的小事物。没有任何新奇。《远山》,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的真实情感。没有做作,没有虚假。
赵荣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劳动者,在辛苦的农业体力劳作中,还能够以诗歌这种形式记录内心的思想,而且他记录的都是发自内心的快乐、焦灼、思考,每一首诗真情流露,还原本真的和土地、庄稼、大自然的对话,令人感动。
二、诗歌的意象表达和梦想执念
如果说,第一部诗集里,赵荣用比较真实质朴的语言描写和记录着自己的农家生活,那么在第二部诗集《短笛》里,就有了更多的诗歌意象,通过独特的视角来表现诗人的梦想执念了。
赵荣在《短笛》的自序里说:“所谓短笛,其实就是用弯刀,从老山上砍来,再用火炷烙上几个眼,弄得出声音的一截苦竹罢了。并非,乐师在大雅堂上吹奏的那种。主人将它带在身上,田头地脚,沟边路脑。玩日升日降,弄喜怒哀乐,吹人间冷暖。”
比如,赵荣诗歌里的很有独特个性的语言:这时光真快啊,尤其是《五月的时光》“我只是/在地边上打了个盹/五月的时光/就不在了一半”。羊与人的那份《情感》,不晓得,有多少人能够说得上“今天它独自在皮卡车上/似乎有什么预感/故把我叫唤/并告诉我/它已从那里/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赵荣说,《短笛》里的“这声音,都是来自心底的声音。《短笛》,一截弄得出声音的苦竹而已。”
诗歌的意象表达很多时候都是明晰而痛苦的,也是特立独行的,更是寂寞和孤独的内心。因为在诗歌里有自己的执念,那是身边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孤独和苦痛,也是自我纠结的执念表达。如《节约与浪费》“从家到工地/有人走30分钟/有人走20分钟/我走10分钟/我将节约下来的时光/浪费在/一首诗/一个字上”……不得不承认,赵荣诗歌里总有着淡淡的忧伤和愁苦,那不仅仅是因为文学梦想实现的难度,更多的应该是身处山村环境而没有更多的心路“同行者”,作为诗人,在创作中的一种极其焦虑的倾诉困扰,使本来就在梦想执念中的诗人更加充满迷惑和怅惘。
三、诗歌里的“它们”和“我”
作家刘亮程的《一片叶子下生活》里说:“也许吹响一片叶子,摇落一粒草籽。吹醒一只眼睛里的晴朗天空,这些才是我们最想做的。”
赵荣诗歌里出现的很多事物都是他思考的对象,他的诗句创作没有那么多的技术技巧,更多的是熟谙具体表达上的虚实远近、物我内外,宏观微观,善于遴选叙述和抒情的视角和切入点。如《辣椒》即是鲜明一例。“一生的追求/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织一件火红的衣裳/当然不是为了别人/只是因为/自己要穿/尤其是垂暮之年/最怕/被苍凉感染。”显然,这是一个拟人的手法,这里有色彩、有穿越生物形象的想象。再如“一头太阳/一头月亮/一根弓起的扁担/一头太阳/一头月亮/连绵起伏的山峦/一头太阳/一头月亮/我走在那条生生不息的/路上”……这就是赵荣干净淳朴的诗句,句子里的那些“它们”和“我”每时每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2014年,我第一次去到大井村的赵荣家,前一天就联系好,赵荣满心欢喜,天才亮就起来杀鸡烀火腿,在村子前边的桥头等着我们。不善言辞的赵荣看见我们,只会重复说着感谢的话。握着赵荣粗糙而有力的手,我感觉我的想象画面完全符合这双手传递给我的信息。他的家坐西向东,一栋两层瓦房低调地坐落在村里的主干道边上。一番热切的文学交流和诗歌创作谈论之后,我们在院子里吃了一顿美味的农家饭。2022年的初春,我再次去看赵荣的时候,他正在羊圈里为一头小黑母羊接生,灿烂的阳光照在刚出生的小山羊身上,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一只,可身上微卷的黑毛却泛着光泽,十分可爱。“它们”是一只羊、一朵花、一条路、一把斧头、一根扁担……,而“我”有时候也是“它们”中安静的一员,只留下默默的思考。
短诗《因为走着》就是诗人的一个自画像:“因为走着/所以我写着/左边衣兜里是粗糙的口粮/右边衣袋里是半截秃笔和皱巴巴的纸张/因为走着/所以我写着/尽管充不了饥挡不了寒……”对于一个一辈子在土地里寻找生活出路的农民来说,耕地、播种、浇水、施肥、收获,历经春夏秋冬,面对寒风酷暑,感受土地的贫瘠和收获,在宁静的山村里凝望黑夜里闪闪发光的星光,我不知道赵荣是如何想到一定要用这最朴实的方式记录下一行行诗句,也许,土地、山羊、毛驴、山路、垭口、远山、树枝、老屋,正是赋予了赵荣最撞击心灵的感受,化作一首首充满思考的小诗。土地和乡情,应该给予了赵荣的诗歌最好的养分吧。
对赵荣来说,他的诗歌是现实生存和文学梦想博弈的结果,生活是现实的,而文学梦想是精神支撑,相互之间有时候彼此和谐,有时候彼此博弈,而博弈的结果,就是诗歌的灵感不断闪现,生活也继续往前。在《短笛》的后记里,赵荣写道:“一辈子,就爱这么一件事。只要日子还在自己手里,诗歌,就不会弃我而去。”赵荣就是这样一位一直坚持跋涉在远山山路上的诗人,无论在大井村的普昌河畔,还是普淜天峰山之麓,他走到哪里,诗歌就在哪里,他除了收集一地厚厚的落叶,或者赶着一群暮归的羊群,还是背着一捆田里的稻草,他依然是那个舍不得放下诗稿的人,只要这样一直写下去,即使每天在烈日下或是暴雨中,生存和梦想相互交织相互胶着,他依然能够收获丰硕的果实!
编辑手记:
近年来,祥云县的农民作家以其蓬勃的发展态势,逐渐引起了大理州乃至云南省文学界的关注。他们忙时农耕,闲时笔耕,以坚韧的创作态度、扎实的生活阅历和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将来自于大地的灵感灌注于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中,以关注乡土文学、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书写火热的现实生活,努力讲好红土地上的乡村故事。赵荣是这个群体中很有创作个性的诗人,他右眼四级残疾,出版有诗集《远山》《短笛》。写诗近八百多首,发表作品近一百多件。本篇评论从他的诗歌入手,结合赵荣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解读其诗歌的意蕴和内涵:他的诗歌是现实生存和文学梦想博弈的结果,生活是现实的,而文学梦想是精神支撑,相互之间有时候彼此和谐,有时候彼此博弈,而博弈的结果,就是诗歌的灵感不断闪现,生活也继续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