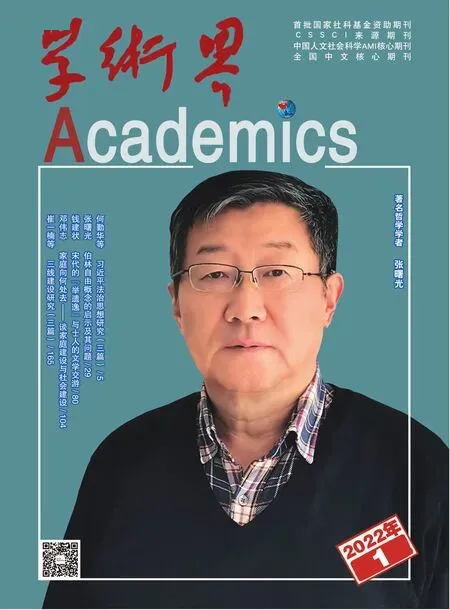宋代的“举遗逸”与士人的文学交游
——以“隐士”投献为考察中心
钱建状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以粉泽太平、移风易俗、网罗奇才、遗才为政治目的,宋朝政府在科举、门荫之外,又另设“举遗逸”一途。“举遗逸”是在宋代尊隐尚贤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选官机制,在宋代的选官体系之中,以“举遗逸”而入仕的士人,数量不多,官品较低,但它毕竟是一种选官机制,卓绝能文而失意场屋者,或藉之以起家,退处求志者,亦可藉之以成名。因此,尽管这一取士制度,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在宋代士林当中,所造成的振荡却不容小觑。宋代的士人,因各种原因退处之后,尚能砥砺名节、修身养德,以道德自律,坚守儒家伦理规范与核心价值,又常能潜心著述,以期有用于世,并能与地方政府、朝廷中的名臣、重臣保持良好的学术互动与文学交游,部分原因,或可从这一制度中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宋代“举遗逸”的政治文化功能
“遗逸”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汉书》卷二十七载,武帝元狩六年,“是岁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节巡行天下,存赐鳏寡,假与乏困,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1〕遗逸,乃在野遗贤、逸民之省称。《后汉书》有《逸民列传》,典出《论语》“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矣”,〔2〕宋代诏举遗逸,亦多用此典。因此,宋人所谓“遗逸”,大致与今人通称之“隐士”相近。《宋史·隐逸传》所列四十余人,与《宋会要辑稿》“举遗逸”名单高度重合。《宋史·选举志》言“举遗逸”之政治文化功能,一曰“幽隐必达,治世之盛也”,一曰“振清节、厉颓俗”,都是正史隐逸传常见用语。所以,宋代荐举遗逸的主要对象是隐士群体,大致不错。
不过,从宋代“举遗逸”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所举荐的对象远不止为隐士群体,其所发挥的政治文化功能也不止于粉泽太平、美化政治和移风易俗。盖宋代科场以文词、经术取士,而人之才性又各有偏擅,能诗赋者,未必深于儒术,能经义者未必能文词,而科场考试文体则相对固定。每开科场,必有遗珠,又考试过程中常有取士不公的现象发生,故士林之中,每有遗才之叹。此其一。
其二,宋代科举取士,数量虽不少。但被黜落者、屡试不第者,则数倍、数十倍于中第者。这些场屋失意之士,多有积怨,散在民间,是一股不稳定的异己力量。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富弼上奏朝廷,曾忧心忡忡地说:
窃思近年数牓以来放及第者,如河北、河东、陕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绝少者何?盖此处人物禀性质鲁,不能为文辞中程试,故皆老于科场,至死不能得一官。岂三路之人独不乐富贵哉?盖求之而不得也。今纵有稍在显官者,亦不过三五人而已。此数路之人虽不能为文辞,若其大才大行及强悍奸雄,则诸路不及。向时天下无事,则此等人或在场屋,或在农亩,或为商贾,或为僧道,屈伏不能有所为,但怨望思乱而已。〔3〕
富弼将求官而不得、失意场屋之士与强悍奸雄联系在一起,并非危言耸听。而辟“荐举”一途,既是牢笼有才行士人的一种手段,也是安慰失意士人的一种权术。因此,各地落第之举子而有名望者,往往成为荐举之对象。宋代大规模地征召“遗逸”,一在嘉祐六年(1061),一在熙宁三年(1070)。《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载:“(嘉祐)六年五月七日,舍人院试诸州敦遣进士:徐州颜复、成都府章禩、润州焦千之、开封府韩盈、荆南府乐京、许州辛廱、大名府李抃策、论第三等下,赐进士出身;相州刘安道、安州赵畴、邵武军王景、潭州陆湘策、论第四等上,赐同进士出身;渝州牟载、赵州左用策、论第四等下,通州随翊、潭州廖倚、太原府崔远策五等,并为试秘书省校书郎。”〔4〕“(熙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舍人院试诸州敦遣人:滨州刘蒙、处州管师常、阆州贾蕴、雍之奇、嘉州李逵、衢州周颖、齐州胡鄢论、策并第三等下,赐进士出身;太原府李抗,忠州谭立之,眉州孙潜,太原田籍、张由,剑州陈舜岳,大名府尚景淳,汉阳军窦恂论,策第四等上,赐同进士出身;眉州任通夫、邢州国采、荆南伊瑑论、策并第四等下,并为试衔知县、判司簿尉。时蒙号处士,师常等皆进士。”〔5〕两次征召共34人,除刘蒙一人号称“处士”,余皆是进士。
《宋史·选举志》“举遗逸”条说:“科目既设,犹虑不能尽致天下之才,或韬晦而不屑就也,往往命州郡搜罗,而公卿得以荐言。若治平之黄君俞、熙宁之王安国;元丰则程颐,元祐则陈师道,元符则徐积,皆卓然较著者也。”〔6〕由此来看,宋朝政府设荐举之制,征召“遗逸”,除了达到振清节、厉颓俗、粉泽太平等政治用意之外,还兼有在科举取士之外,牢笼失意士人,搜罗奇才、异才的用意。这从《宋会要辑稿》“举遗逸”所载若干以某种著述被荐命官的事例,也可见出此点:
1.(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正月十五日,以怀安军鹿鸣山人黄敏为本军助教。敏明经学,著《九经余义》四百九十篇。益州路转运使滕涉以其书上,诏下两制,晁迥等言有可采故也。〔7〕
2.(同年)六月二十九日,以湖州进士许既济为本州助教。既济词学为州人所推重,两浙转运使得其所著《四民论》上之,故有是奖。〔8〕
3.(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以梓州草泽东方自牧为本州助教。自牧表上所著《易论》,故有是奖。〔9〕
4.(仁宗)嘉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以草泽宋堂为国子四门助教。堂,成都双流人。……著《蒙书》数十篇、《春秋新意》、《七蠹》、《西北民言》。颇究时务,数为近臣所荐。至是,翰林学士赵概又上其所著书,特录之。〔10〕
5.(高宗绍兴)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诏抚州草泽邓名世令阁门引见上殿。以吏部尚书胡松年看详到名世所著《春秋四谱》六卷、《辨论谱说》十篇、《古今姓氏书辨证》一十四卷,学有渊源,辞亦简古,考订明切,多所按据,故有是命。后赐进士出身,充史馆校勘。〔11〕
仁宗嘉祐四年十月,朝廷下举遗逸之诏,有曰:
学术行能,见推乡里,困于草野,是谓遗贤。属我治朝,所宜搜采。应天下士人,素敦节行,兼通学术,又为乡里所推者,委转运使、提点刑狱臣僚同加搜访,每路各三两人。仍与本处长吏具从来所为事实及所通学术,连书结罪保举闻奏。委中书门下再行询察,如非妄举,当议特加试用。〔12〕
节行与学术皆为乡里所推者,才能称得上“遗贤”。若德行有亏或才学无闻,皆不能被荐举。今存宋代士大夫的荐举遗逸的荐章,基本上是按这个原则来揄扬受荐士人,并且按照惯例,要附荐章呈上士人之“所业”,也就是受荐者的著述,以便中书进一步审察。以范仲淹荐举李觏为例,其《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核心内容有二:
1.李觏退隐养亲,道德可称。辩博明达,有孟轲、扬雄之风:
臣伏见建昌军草泽李觏,前应制科,首被召试。有司失之,遂退而隐,竭力养亲,不复干禄,乡曲俊异,从而师之。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杨(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赐采收,识者嗟惜,可谓遗逸者矣!〔13〕
2.介绍李觏的著述情况,并拟附上所业:
臣观李觏于经术文章,实能兼富,今草泽中未见其比,非独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业《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序》一篇、《平土书》三篇、《易论》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编为十卷,谨缮写上进。伏望圣慈当乙夜之勤,一赐御览,则知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14〕
荐章言及李觏之德行者,仅“遂退而隐,竭力养亲,不复干禄”一句,其余的内容皆为称扬、介绍李觏之学术特点及其卓绝之处,其写作的重心实际上是围绕李觏的学术才能展开的。欧阳修荐苏洵之荐书,也有类似的特点。嘉祐五年(1060),其所作《荐布衣苏洵状》曰:
往时自国家下诏书戒时文,讽励学者以近古。盖自天圣迄今二十余年,通经学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胜数。而四海之广,不能无山岩草野之遗。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闻。此乃如臣等辈所宜求而上达也。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其所撰书二十篇,臣谨随状上进。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15〕
荐状从文、行两方面揄扬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守道安贫,不营仕进”二句,言苏洵之德行。余则以飞扬之笔,从辞辩闳伟、博古宜今、言有可用、言有可采等诸方面点评老苏之才、之文,以此证明苏洵正是朝廷孜孜以求的通经学古之士。言其德行较虚,乃当时通行荐举处士之常用词,而言其文,乃就苏洵二十篇所发,实为玩味已久、确有所见之言,故较实。老泉一生著述之特点及其属词命笔之用意,于此荐章也稍能见出。
由以上所论可知,宋朝政府诏求“遗逸”,其主要政治用意之一,是在科举取士之外,搜罗文、行兼备之士。士人在政治上、学术上、文学上的才能,也就是宋人常称的与“行”并举的“文”,是宋人所谓“遗贤”最重要的精神内涵,也是士大夫在搜访、推荐“遗逸”时,尤其要属意之处,也是朝廷循名责实,复核、考察“遗逸”,并决定是否命之以官的最重要的硬性条件。因此,无论是士大夫主动荐贤推善以报国,还是士人希求荐举而求官。才学与著述,往往是联系上与下、尊与卑,官与民、举主与被荐者最重要的纽带。正因为如此,宋代的荐举遗逸,才有可能促进了宋代士人之间的文学交游。
二、宋代的“隐士”及其文学交游
如前考述,进士、隐士是宋代“举遗逸”的最主要的征召对象。进士是入世的,隐士是避世甚至是出世的。从对政治的疏离感与社会参与度来看,二者自当有所区隔。但是从宋代征召、荐举的实际运行来看,“进士”与“处士”“布衣”“草泽”等名称,经常是互相替代的,二者的区隔与界限并不明显。北宋中期,在荐举遗逸的过程中,还一度出现“朝入科场,暮为敦遣者”〔16〕的现象,由此引起士论的不满。进士、隐士在名称上的混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代隐士群体产生的制度背景是科举取士,宋代下第之举子,实际上是宋代隐士群体的最主要来源。《宋史·隐逸传》所列举的一些著名隐士,不少都有应举的经历。如与苏洵齐名的蜀人张俞(愈),“游学四方,屡举不第”;〔17〕王安石、曾巩的友人孙侔,“志于禄养,故屡举进士。”〔18〕为西昆诗人杨亿所推赏的周启明,四举漕试,皆为第一。后又举贤良,“既罢归,遂不复有仕进意,教授弟子百余人,时号处士”。〔19〕名列闽中四先生之一的陈烈,“尝以乡荐试京师不利,即罢举”,〔20〕亦号称处士。前引熙宁三年惟一以“处士”应召的刘蒙,曾游于京师,“负其千镒之宝,欲求良工大贾而售之”,〔21〕以文求知,以此求应制举。今之“刘处士”,即昔之“刘贤良”,并非不事科举。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应举不第,甚至是屡举不第,退而求其志,也就是由进士蜕变为“隐士”“处士”,是不少宋代士人的人生轨迹。“道穷吾何之,只得归荷锄。”〔22〕这是一群因科场蹭蹬而不得不退隐田园的士人群体,与避世、避祸、愤世嫉俗、待进而动、以退为进、求仙问道、奉养父母、向往山林等主动退隐的士人相比,宋代的这一批“隐士”“处士”,或多或少,普遍性地带有以下若干特征:
1.出身寒微,舍科举无以起家。
2.多次应举不第。
3.才性偏擅,在学术、文学方面有自己的特长。
4.不甘沉沦与无名,退隐之后,能潜心著述。
5.思想上信奉儒家,能恪守儒家道德规范。
6.退而为乡绅,仍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7.群体意识较强,与朝野士人学术、文学交往频繁。
8.一旦有机遇,愿意出仕。
以上特征,落实到个人,可能有所缺省和变异,但总体来看,以宋代隐士的家世、出处、交游为线索,结合宋代荐举遗逸的制度背景,来揭示宋代隐士群体的人生轨迹与心理世界,常常能知微见著,有所发现。以下试以李觏、吕南公为例,来对这一问题详加说明。
李觏为宋代大儒,其生平事迹,详见门人陈次公所撰《墓志铭》,以及宋人魏峙所撰《直讲李先生年谱》,《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儒林》有传。今人论宋代隐士,多引其事迹,〔23〕但李觏晚年出仕,且以儒业名世,所以不能入《隐逸传》。陈次公《墓志》、魏峙《年谱》皆不录李觏的家世。李觏为其生母撰《先夫人墓志》,提及“先父府君”,“先君尝学,不应举,以教其子作诗赋,亦乐施惠”。〔24〕其母姓郑氏,三代皆不仕。因此,无论是从父系还是母系来看,李觏皆为平民出身,他并不具备门荫入仕的可能性。李觏生十四年而其父没,“是时家破贫甚,屏居山中,去城百里,水田裁二三亩,其余高陆,故常不食者。”〔25〕家境的贫困,迫使李觏不得不走读书应举之路,“家世贫乏……饥焉而无田,寒焉而无桑”,故“喁喁科举,求不可望之禄以为养”。〔26〕但是他的应举干禄之途并不顺利。其《上余监丞书》曰:“十岁知声律,十二近文章……耳目病困者既十年矣。而公不举于州郡,私不信于闾里,梯天莫见明主,穷海未遇知己。”〔27〕其《上苏祠部书》曰:“生长好学,由六七岁时,调声韵,习字书,勉勉不忘……年二十七矣……进不得州郡举,退不得乡曲誉。”〔28〕大约在李觏二十七岁前,他并没有获得州郡发解的资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李觏二十八岁时,他由家乡南城赴京城汴京,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京师忠贤所萃,策试亡私,奔走西向,将觊觎其万一”,〔29〕希望能在京城获得开封府发解的机会;一是通过投献,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在赢得社会誉望的同时,走荐举入官一途。由于景祐三年,朝廷未开科,“贡举已罢”,李觏科举入仕的希望再次破灭。但通过向京城闻人如宋庠、李淑、聂冠卿、叶清臣等投献,其所著如《潜书》十五篇、《野记》二篇、《礼论》七篇,及其《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等,学术、文学价值得到了朝野士人的重视,李觏在士林中的声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京师归乡,李觏一方面潜心著述,著《富国》《强兵》《安民》三十策等,拟应制科。同时,以投献为中介,与当时士大夫保持密切的文学与社交活动。景祐四年(1037),李觏由京师往饶州见范仲淹,并以《潜书》《野记》《礼论》等写为一册,及平时所业五卷为贽。饶州之行,意义非凡。自此李觏受知于范仲淹,其政治上有见识的构想,在范仲淹所主导的庆历革新中,依稀可见。〔30〕而范仲淹对于李觏的荐举,也一直不遗余力。庆历二年(1042),李觏制举落第,下第后,李觏再次潜心揣摩时事,作《庆历民言》三十篇、《周礼致太平论》五十篇,并于庆历四年投献给范仲淹、富弼。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向朝廷荐举李觏,并上李觏所著《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序》一篇、《平土书》三篇、《易论》十三篇,次年,范仲淹再次荐举李觏,敦促朝廷劝奖其人,并再录其《明堂图》并序,同年,朝廷特旨授将仕郎、太学助教。李觏是以隐士的身份被荐举的,所以范仲淹在荐章中说:“建昌军草泽李觏,前应制科,首被召试,有司失之,遂退而隐,竭力养亲,不复干禄。”但考之李觏自己的心迹,他自称无位,实际上“其所留心,何尝不在天下国家”,〔31〕他曾向范仲淹坦言:“执事表知乐之士,有自褐衣而得召者。如觏等辈,庶可依归。”〔32〕并不隐瞒他儒者的用世之心与企望由获荐举入仕的动机。李觏是大儒,是一个入世甚深的士人,也是一个屡举不第的进士。他的被迫退居,以及退居后频繁的文学、学术交游,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吕南公,事迹入《宋史·文苑传》。他出生于建昌军南城,系李觏的同乡。李觏卒时,吕南公才13岁。从时代上看,他们是前后相继的两代人。吕南公之世系,详见其所著《吕氏家系》,其曾祖、祖、父,三代不仕。其父“少孤,不及仕学”,〔33〕吕南公《上知县书》说:“昔者先人有户于此邦,而生是寄焉,则据之以为家。方缘贫苦之故,未免随应举觅官之后,则虽食无田而栖无山,犹不可以舍而之他也”,〔34〕可见其出身之贫寒。与其同乡李觏相似,吕南公出生于贫寒的农家,并无荫补之可能。读书应举,既是其惟一的入仕之路,就不可能不专意于此。吕南公善于古文,而不善于辞赋、经义,因此屡举不第。〔35〕《宋史》吕南公本传说:“熙宁中,士方推崇马融、王肃、许慎之业,剽掠补拆临摹之艺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时好,一试礼闱不偶,退筑室灌园,不复以进取为意。”〔36〕所谓“一试礼闱不偶,退筑室灌园”,并不符合实际。考之本集,《上曾内翰书》曰:“某再以举子绌于有司。”〔37〕《请见叶太守书》:“某……犬马之齿三十五矣……再三至京师,经由郡国不啻十五数。”《请见郑太守书》:“某昔在举场十许年间,经见五守令。”〔38〕等等,乃多次应举之明证。本集有《上曾内翰书》,为曾布而作,开篇曰:“往在熙宁之初,阁下以令长进京官,遭值圣君贤相,留神至治,而阁下遂为参赞新美之腹心。当是时,某再以举子绌于有司去。”〔39〕曾布赞新政,为熙宁三年,是年,吕南公已再绌于有司。《送刘进士序》:“余从熙宁以来,深于冻馁之忧,亦隐忍于白襕以随群辈步武,盖四往而三黜。”〔40〕熙宁共开科三次,则至元丰初,南公仍在应举。吕南公归隐时号“灌园”,其《中山感怀》一诗,提及两次下第。第一次下第:“春官未相识,退作暴腮鲤。惆怅问乡程,东随汴波驶。……稍赴建康城,筋骸倦如死。”〔41〕第二次下第:“颠沛翅便垂,思山对蟾朏。……倍道怯粮空,逢人类囚罢。……无数吊唁声,伤怀泪如洗。”〔42〕写两次科场铩羽而归的疲惫、倦怠与落魄,乃多次失意科场的痛定思痛之作。诗末有“柴薪渐营度,且阅灌园枝,必可了余生,功名付尘滓”〔43〕等句,流露了明显的退隐田园的心理。诗的开篇自称“西村灌园生”,则“灌园”一号,是吕南公屡试不第而归隐田园的自白。其始称“灌园”不知何时,本集中,《测幽记序》作于“熙宁八年”(1075)以后,《讲师李君墓表》作于熙宁十年,自称“灌园公”,《庐陵徐俊和画像赞》作于元丰四年(1081),《石陂寨新置军储仓记》作于元丰六年,《普安院佛殿记》《真如禅院十方住持新记》作于元丰八年(1085),末皆署“灌园吕某”。本集中,又有《老懒轩记》,作于屡试不第、心灰意冷之时,文中流露出了浓厚的处顺委蛇、与世浮沉的遁世思想。是文作于元丰四年(1081),“年中半于七十”。〔44〕由此看来,随着科场的一再失利,至熙宁末,吕南公渐有归隐之意,至迟在元丰四年,吕南公已决绝退出科场而安心归隐。南公卒于元祐元年(1086),真正归隐的时间,约为五年,时间并不长。
吕南公以文学自期,其用世之心本不强烈,加之心性谦退,因此交游并不算太广。但自其应举时,他与同时代的朝野士大夫,特别是宦游、占籍江西的士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交游关系。其《请见郑太守书》曰:“昔在举场十许年间,经见五守令,乃至苟有位在此,皆纳谒而造请”,〔45〕证之以本集《请见张太守》《请见蔡太守》《请见叶太守》《上知郡郎中书》《请见韩签判书》《请见蔡签判》《请见曾签判》等书信,可见此言不虚。在多次应举皆垂翅而归后,南公渐生退隐之心,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唯当勒成一家,俟之百世”,〔46〕期以立言不朽。熙宁十年前后,南公以“杂文一卷”,投献给古文名家曾巩。在《上曾龙图书》中,南公表达了志于文学的心迹,以及多年来的文学追求,并希望曾巩“收拾引掖,使至有闻”,〔47〕成为自己的知己。这次投献,获得了曾巩的首肯。曾巩在《与王向书》中说:“比得吕南公,爱其文。……吾子与吕南公、黄曦皆秀出吾乡,一时之俊。私心喜慰,何可胜言!”〔48〕喜得英才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此后南公与曾巩多有交游。元丰六年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藉着地缘及与曾巩的交游,约在元丰八年前后,南公先后上书曾肇、曾布。其《上曾吏部书》有曰:“某求仕于科举而不得,则无所道矣。去老于丘园,治田桑以饱暖残齿,耕稼暇日,尚能作为诗书,以歌咏太平君子之声烈。百世之下或有传焉,则曰阁下之旧乡,农圃野夫乃有功于文字也。”〔49〕其《上曾内翰书》末曰:“世俗之请见,必先之以高妙无底之谭辞……某则不敏,惟阁下幸肯降意,而终赐之见,则某将有自此之继承焉。”〔50〕味其语意,盖仍欲以文学受知曾氏兄弟。自此以后,南公与曾肇有文字交往。曾肇《寄吕南公》诗末曰:“倾盖相知胜白首,扁舟临别重徘徊。”〔51〕颇有相见恨晚之叹。
元丰年间,藉着文学交游,南公在士林中的声望渐起。元丰四年,郑掞知建昌军,已有“不过门之恨”,〔52〕故假南城令之口,表达了愿意结识之情。元丰七年,陈绎自翰林学士谪知建昌军事。对人说:“吾不以左官为(不)意,而荣于获灌园先生。”〔53〕深以与南公相识、相知为荣。今本《灌园集》中,有《奉和内翰太中城南放鱼》《奉和内翰太守腊雪出郊长句》《内翰太中以某伏谒郡斋特赐长句谨和拜酬》等,皆可见二人文学之私谊。陈绎在任时,命有史才的吕南公重修《韩愈传》,并将此文函呈曾肇,请他为之延誉。又“将闻于上”,藉此为荐举吕南公制造声势。〔54〕吕南公《内翰太中以某伏谒郡斋特赐长句谨和拜酬》一诗末曰:“更剡荐牍辨玖琼,匹夫有获万口称。此世不复投清泠,正恐疏阔如樊英。”由“更剡荐牍”一语,及用隐士樊英应诏入仕之典,知元丰末,因陈绎之荐,南公已再有受荐入仕之意矣。
元祐初,朝廷立十科荐士,曾肇时为中书舍人,遂以吕南公应诏。曾肇《荐章处厚吕南公秦观状》曰:“建昌军南城县布衣吕南公,读书为文,不事俗学,安贫守道,志希古人,常举进士不合,退处畎亩,躬耕著书,不求人知,自足丘壑,江南素称多士。如南公言行卓然,少有其比。臣今保举堪充师表科。”〔55〕宋人符中行《灌园集序》载:“元祐中,在朝诸公,交口称荐,欲命以官。”〔56〕至此,吕南公的隐名、文名与卓行,广为士人所知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大约是对吕南公退隐之后不甘沉沦、潜心著述的最丰厚的回馈了。
三、荐举遗逸与隐士投献
如前所述,宋代的士人,特别是平民出身、屡试不第的举子,在退隐之后,以学术、文学活动为纽带,仍然与士人群体保持相当密切的交游关系。更有甚者,一些士人,如李觏、吕南公等,以投献为中介,藉以扩大自己的学术、文学影响,并通过当世闻人的延誉,提高自己在士林中的声望。换句话说,投献仍然是隐士展开学术、文学交游的一个重要方式。宋代隐士之投献,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投献,将自己在学术、文学上的重要成果公诸于世,以期立言不朽;一是以投献为手段,与中央、地方的重臣、名臣相识、相知,并由此获得荐举入仕的机会。前者是显性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后者是隐性的,往往很难为人所察觉。但是,如果文献足征,细考宋代士人的生平交游,隐士投献的心理动机及其与宋代荐举遗逸制的关联,自会浮出水面。试以宋代著名的隐士黄晞为例。黄晞少通经,留心古学。然年至四十,始随乡贡至礼部,又上五十策,求应制举,皆不得志,遂生退隐之心,僦居京师,潜心著述,以教授为生。黄晞游京师时,以乡里之故,曾馆于宰相章得相之门。又“献所为文”于苏绅,苏绅深器之,遂馆之于书室,令子苏颂与之游从。苏绅曾对黄晞说:“成子名者,韩稚圭也。子宜贽文见之”,〔57〕建议黄晞向韩琦投献,借此成名,以希荐举。黄晞听从了苏绅的建议,以文投韩琦,果受钦重。“其后荐之于朝,命之以官”,〔58〕皆借韩琦之力。据苏颂《杨子寺聱隅先生祠堂记》所载,嘉祐年间,“公卿大夫交章论荐者数十人。朝廷用丞相韩魏公言,将以为国子监直讲。”〔59〕《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举遗逸”条载:
(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建州草泽黄晞为太学助教致仕。……前后荐者,自宰臣韩琦而下三十余人。至是,端明殿学士李淑上言晞“赡学敏文,识亦优博。晦名安道,笃行有守。恬约弗耀,见称时流。甚齿淹恤,宜被甄奖。有臣寮论荐,欲望检会,召补学官,庶令训导诸生,敦劝浮俗”,乃有是命。明年以疾而卒。〔60〕
关于黄晞的有时无命,释文莹《玉壶清话》有一段记载:
黄晞,闽人,皇祐初游京师,不践场屋,多以古学游搢绅之门。凡著书,自号聱隅子。走京尘几十年,公卿词臣无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驰走无倦。后词臣重晞之道者,列章为荐,尽力提挽。朝恩甚优,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国子监。将有司业之命,始拜敕,遍谢知己。才三日,馆于景德如意轮院,一日晩归,解鞍少憩,谓院僧曰:“仆远人也,勤苦贫寒,客路漂泊,寒暑未尝温饱,今日方平生事毕,且放怀酣寝一夕,请戒僧童,慎无见喧。”僧诺之,扃扉遂寝。翌日大晓,寂无所闻。寺僧击牖大呼,已卒于榻矣。〔61〕
黄晞“嘉祐二年四月,无疾卒于隆和坊”,并非诏命下之三日而卒,亦非卒于僧寺。《玉壶清话》所载,盖小说家言,不足信。黄晞“景祐中,年四十”,至嘉祐元年,年近六十,故仕进之心已薄。苏颂《杨子寺聱隅先生祠堂记》载,“朝廷用丞相韩魏公言,将以为国子监直讲。先生自谢于富丞相曰:‘老生岂任仕宦者耶?必不可辞,愿得七品闲官还南方足矣。’”〔62〕苏象先《魏公谭训》卷六载,“及黄(晞)老,有一子不克肖似。诸公将特起之。黄不愿仕,但欲得七品官以荫其子孙。诸公以问祖父,祖父以实告,遂除国子四门助教致仕”。〔63〕黄晞长期为苏绅家馆客,与苏家子弟相厚。苏颂、苏象先所述黄晞出处心迹,当近实而可信。但黄晞在中年屡试不第,仕进无门之时,“多以古学游搢绅之门”,投献京师名臣、重臣之门,“驰走无倦”,亦在情理之中。释文莹所述,并非全诬。
黄晞名入《宋史·隐逸传》,据本传:
黄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经,聚书数千卷,学者多从之游,自号聱隅子。著《歔欷琐微论》十卷,以谓聱隅者枿物之名,歔欷者叹声,琐微者述辞也。石介在太学,遣诸生以礼聘召,晞走匿邻家不出。枢密使韩琦表荐之,以为太学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64〕
限于著书体例,《宋史·隐逸传》为了突出传主一以贯之的淡泊名利、高蹈不仕的出世形象,往往有意隐去或淡化传主入世、进取,甚至是热衷功名的一面。这就必然模糊了一些宋代“隐士”的真面目。《宋史》黄晞本传缺漏太甚,且传文特书走匿邻家、不愿受石介一节,以突出其谦退逃名的一面。但正如前考,黄晞中年游走京师,本有仕进之意。其不受石介之聘,另有原因。蔡襄《答赵内翰书》曰:
伏蒙示下众荐黄晞奏草。晞闽人,与之游甚久,以书自喜,不苟于人,诚高世怀道之士。足下荐之于朝,庶乎盛时无有遗材。足下之存心,不特为晞发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国子监时,请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诈善不直,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见知人,识虑高远也。”襄以谓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晞避介聘为学正,不肯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岂足为晞高识远虑哉?〔65〕
据蔡襄此书,黄晞避石介之聘为学正,乃“不肯为介下耳”,是学人相轻心理作怪,并不能以此作为黄晞谦退淡泊的依据。覆按黄晞的出处心迹,此言甚是。《宋史》失考。
四、隐士投献的特点
1.投献对象的选择
宋代“举遗逸”的主要目的,一是点缀升平、移风易俗;一是做出求贤姿态,以此来笼络民心、士心;一是通过奖掖退居有守的道德典范,借此来安慰失意的士人。从客观效果来看,也还有搜罗人才、弥补科举取士之不足的功用。其所发挥政治文化功能,不可谓不重要。但综合来看,荐举遗逸,在宋代选官体系当中,仍处于相当次要的地位。宋代平民欲藉荐举入仕者,其入官之难与授官之低,远较前朝为甚。宋代的布衣、草泽之士,欲藉“举遗逸”之途入仕,一要文行卓著,在士林之中颇有誉望;一要得朝中名臣、重臣的力荐,方能如愿。通常情况下,举主越多,举主的政治身份与地位越高,荐举遗逸更容易成功。这是宋代“举遗逸”的一个特点。反之,若士人的社会声望未著,或仅有个别臣僚荐举,则未必能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仁宗皇祐年间,陈襄知孟州河阳县。其友人陈烈与其通启,有仕进意。然陈襄位望皆轻,不敢举荐。因此,写信给起居舍人、知制诰蔡襄,请他荐举陈烈。至嘉祐年间,因知福州曹颖叔、翰林学士欧阳修交章荐之,朝廷才授烈以官。元祐年间,科场多次失意的士人李廌写信给苏轼,希望能援陈师道之例,通过荐举入仕。苏轼给这位门生回信道:“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荐之,轼亦挂名其间。会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轼孤立言轻,未尝独荐人也。爵禄砥世,人主所专,宰相犹不敢必,而欲责于轼,可乎?”〔66〕
必得朝廷重臣、名臣或有荐举权的士大夫荐举,是宋代布衣入仕的关键环节,退隐而复有仕进之意的士人,自然也不在例外。宋代的隐士,藉由投献,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而其投献的对象,多为名臣、重臣,原因即在此。前引李觏向范仲淹、富弼投献,吕南公向曾巩投献,黄晞向苏绅、韩琦投献,此外如苏洵在京城向欧阳修、韩琦、富弼等投献,皆属此类。
隐士在选择投献对象时,除了衡估对方的政治地位,受卷者是否有汲引好士之心,以及彼此之间是否志趣相合,也要考虑在内。以北宋中期为例,李觏向范仲淹投献,一方面是因为范仲淹在士林之中,能“表知乐之士”“自褐衣而得召者”庶可依归;另一方面,李觏以儒学名世,又有经济之怀,其所著《明堂定制图》《庆历民言》等,皆关乎朝廷典章制度,以及国计民生之利弊,非徒为空言。在庆历革新的政治思潮中,更易受知范仲淹。同理,一些士人如苏洵以《洪范论》《史论》等向欧阳修投献,首要原因当然是“欧阳文忠喜士为天下第一”,〔67〕他对士人投卷,持肯定鼓励的态度。再次则是因为,欧公乃当时文坛盟主,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与裁鉴力,远非他人所能比。若投卷者在文学上确有过人之处,际遇欧公,不至于明珠投暗。
宋代的举主与被荐人之间,往往有政治上的连带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种荣辱与共的情况,偶尔在荐举遗逸中也存在。邹浩《道乡集》卷十一《寄阳行先》曰:“曾以高风入冕旒,未闻释耒起南州。当缘我罪投荒远,亦使君身得滞留。万卷功名闲处立,一瓢境界静中收。它年太史无虚美,卓行还能与祖侔。”邹浩曾以遗逸荐阳孝本,〔68〕但因举主邹浩被贬谪,朝廷遂格征召孝本之命。故邹浩有“当缘我罪投荒远,亦使君身得滞留”的自责之语。此为举主连累被荐人。反过来,也有被荐人连累举主的情况。如胡寅《斐然集》卷十《谢御札促召家君札子》载:
三舍之初,例察提举学事官。到任未久,论荐遗逸二人,为属吏所诉,以为所荐之人乃元祐宰相范纯仁门客,党人邹浩素所厚善。其时蔡京当国,怒臣父沮毁学法,俾湖南北两路刑狱官置狱推治,除名勒停。〔69〕
由此看来,在北宋新旧两党的互相倾轧政治背景下,士大夫荐遗逸,与处士希求荐举,恐怕双方都要考虑一下彼此的人际交往与政治取向。熙宁五年前后,布衣徐禧以《治策》二十四篇投宰相王安石,其卷轴前所附《上丞相王荆公书》有曰:“明王之迹既远,而屡更乱世,所谓千百年绝道之后,而乃有圣君卓然兴起于此时。视其势,且非小小之作。”〔70〕又曰:“某之今日不能以默然,特见士大夫之议论与夫奉法长民者之所为,其未足以识圣主贤相之意而易此时之光阴者甚多。而窃有伤焉,诚恐法之未孚,吏之未虔,民之未明,而已移可爱之日车于羲和也。”〔71〕从写作策略来看,这封书信相当成功。上书人对熙宁之初的政治走向有非常明确的把握,并将无保留地支持变法的政治态度表达得非常清楚,因此甚得受卷者王安石的赏识。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六载:“布衣徐禧得洪州进士黄雍所著书,窃其语,上书褒美新法。”王安石赏其言,“奏除官,令于中书习学检正。”〔72〕徐禧《策论》今已不传,他是不是文偷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向王安石投献之前,已充分揣摩了受卷人的政治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写作。类似徐禧这种投献之前的政治考量,在其同时代的隐士身上,也有所体现。吕南公之于曾布,即是如此。
2.待机而动
投献,是宋代士人藉文学为手段,扩大交际网络,融入士人群体中的一种方式。投献的有无,以及频繁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蠡测士人的入世、用世之心。隐士以淡泊明志、不求闻达自处,世人也以此高之。隐士的出处动静,事关声誉。正如苏轼告诫李廌所说的:“若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损矣。”〔73〕若著述未成、在士林中声望未著而投献,或贸然投赠求进,不考虑彼此双方之贵贱、亲疏之分别,皆可能有损隐士的清誉。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时机而进行投献,就显得相当重要。试以吕南公、苏洵为例:
吕南公《上曾内翰书》有曰:
昔阁下之自桂而北也,旗旌过故里,道路为之荣耀,巷儿闾妇毕出倾仰,而某不获伏谒导骑之前,则以阁下未尝还乡国,其于不敏宜不知。今且莫有为穷困之先者,将以轻易得罪于行尘,故不敢也。及阁下以哭亡来归,而某又不得速往,则以既未尝得见,而遽以贱吊贵,非礼之情,又不敢也。虽然,某终愿一识阁下颜面,以慰岁久想咏之区区,以稍异于邻不觌之徒,以不尽废夫贱敬贵、少敬长、不肖敬贤之礼义,而使阁下亦幸肯降意而导焉,以知乡国之寒晚,有可与言乎否也,是故来伏屏外。〔74〕
此书作于元丰七、八年之间。据此信,吕南公屡次想谒见曾布,第一次无先容之介绍,故不敢谒见。元丰五、六年间,曾布因丧母归南丰,此时南公从曾巩游已久,曾布实已知其人。此时本合见焉,但双方并未见过面,“遽以贱吊贵”,不合礼义,故又不敢谒见。可见欲谒见,皆因时机未成熟而作罢。动静之际,可谓审慎有度。
又据本传,吕南公退隐之后,曾“欲修《三国志》”,〔75〕借史笔以褒贬善恶。元丰四年前后,此书尚未修成。他在《上徐龙图书》中遗憾地说,“某著作未成,今所存者乃间常应用之作,适可观其言之工否。而明公以为可也,则献之屏墙。”〔76〕此次交游,吕南公仅以书代贽,来试探受书人的反应,文卷并未附之于后。可见著述未成,仍不是投献的最好时机。
苏洵青壮年时,先后应进士举、应茂才异等,皆不中,遂“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77〕潜心著述,期以立言传世。他在《上韩丞相书》中说:“洵少时自处不甚卑,以为遇时得位,当不卤莽。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78〕可见其退隐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与无奈。苏洵退隐之后,以处士的身份,与西蜀士人张愈等交游,周旋文谊,声名渐起。〔79〕张方平入蜀时,苏洵在蜀中士人之中,已有相当的誉望。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曾以追忆的口吻,记叙与苏洵的交游缘起:
仁宗皇祐中,仆领益部,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独乏耶?或曰:“勿谓蜀无人,蜀有人焉,眉州处士苏洵,其人也。”请问苏君之为人,曰:“苏君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然非为亢者也,为乎蕴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余不仕。公不礼士,士莫至;公有思见之意,宜来久之。”〔80〕
苏洵本有用世之心,从其内心深处来看,即使退隐之后,其仕进之心并未完全泯灭。只是蕴而未施,而人莫知之。他缺少一个知己,一个礼贤下士而能荐举他的士大夫。一旦其人出现,有“思见之意,宜来”,这就是隐士的待机而动。张方平的这段记述,很能反映宋代隐士出处之际的心理活动。由此看来,当著述已成,又在士林之中有一定誉望时,不少宋代的隐士,尤其是屡试不第、被迫退隐的士人是愿意出仕的。
苏洵求仕无望之后,“归,焚其所为文,闭户读书,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复为文。”〔81〕其一生之最重要著述,如《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均完成于至和二年以前。苏洵在给欧阳修、田况的信中,曾谈到了隐居蜀中、苦心求学后所达到的创作状态:
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82〕
曩者见执事于益州,当时之文,浅狭可笑,饥寒穷困乱其心,而声律记问又从而破坏其体,不足观也已。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83〕
昔非而今是,字里行间充满了自信。至此,苏洵自觉其学已成。于是在至和二年(1055)谒知益州张方平,并以《权书》《衡论》上之。张方平得苏洵所著,大为延誉,且荐苏洵于朝,欲聘其成都学官,但朝廷未回应。考虑到蜀中地理僻远,不足以成苏洵之名。张方平建议苏洵游京师,投献名公,致书欧阳修,以为先容。苏洵听从了张方平的忠告。次年,也就是嘉祐元年(1056),携二子苏轼、苏辙至京师。先以《洪范论》《史论》七篇投翰林学士欧阳修,又以所著《权书》上枢密使韩琦,又以《审势》《审敌》二策、《权书》十篇投故人枢密副使田况。经欧阳修等闻人延誉,苏洵文名大盛。
苏洵在入京向欧阳修等投献之前,是做了充分的人事准备的。至和二年,苏洵送吴照邻赴京,托吴“携其文至京师,欧阳文忠公始见而知之”。〔84〕其入京时,又携雷简夫致韩琦、欧阳修,张方平致欧阳修的三封推荐信。雷简夫给韩、欧二人信中,对苏洵的文行推赏有加:“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85〕“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尝著《六经》、《洪范》等论十篇,为后世计。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86〕由此看来,在苏洵正式向韩琦、欧阳修等当世闻人投献之前,苏洵其人、其才、其德、其行,其在蜀中之声望,对方已有较全面的了解并有较深刻的印象。有了这些铺垫与中介,苏洵虽以一介布衣,自蜀赴京,上谒显官,才不致于唐突。
嘉祐初年,处士苏洵在京城的文学交游是相当成功的。他著述已成,始萌再次仕进之心,符合儒家学有余力方入仕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以布衣谒高官显宦,有先容、有铺垫,虽然进取,但出处之际,从容慎静,无躁静之嫌。这种行为准则与交游方式,在当时的隐士、处士当中,是有代表性的。
五、名篇、名作的生成——隐士投献的文学意义
宋代的一些隐士,特别屡试不第而被迫退隐者,其遴选作品,编辑文卷,向当世闻人投献。一方面固然是希求延誉,提升自己在士林中的声望;另一方面,也还是希望藉此途径,得到名臣、重臣之推荐,从而以“遗逸”的身份,走向仕途。因此,宋代隐士之投献,在时间上往往与宋代的荐举遗逸前后相续,从而与名公品题、名公荐举、中书审察、诏书任命等,形成环环相扣的一个流程。在这个流程当中,投献的作品会经由多种渠道,以各种文本样式,被反复传写、品题,其独有的内蕴、价值与风格特征,会被逐渐辨认、认知,并为士林所认可。由此看来,宋代隐士之投献,对于促进其作品在当代的经典化,对于名篇、名作的生成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隐士投献之作,一经当世名公品题、延誉,而广为士林所知的事例,在宋代并不鲜见。前引苏洵诸文,在至和、嘉祐年间,迭经张方平、欧阳修等名公的延誉、品题,以抄本的形式,迅速传播,“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87〕就是一显例。又据《长编》《孙公谈圃》记载,宋仁宗末年,崔公度因任右职,非其所好,又应茂才异等,因疾不赴,遂退隐还乡,恬晦不仕,闭门读书,后崔公度以所作《感山赋》投裴煜,裴煜遂以此赋示欧阳修、韩琦。欧阳修评此赋曰:“司马子长之流也。”〔88〕韩琦荐崔公度奏章曰:
博学多闻守道,其所为文章雄奇赡逸,当求比于古人,而时人未易得也。〔89〕
宋英宗治平二年七月,因韩琦之荐,“以三班差使、殿侍崔公度为和州防御推官、国子监直讲。”〔90〕欧阳修等名公的延誉、品题、推荐,使崔公度文名大盛。《感山赋》也因之广传士林。华镇《上崔学士书》曾提及崔公度以赋受知于君相之美事:
嘉祐、治平之间……时明公啸傲淮海之上,以弦诵自适,裹足怀刺,不游高门。一言之出,人乐传诵。浸以先达于京师,君相览而悦之,下优厚之诏,置之造士之地,而无疑色,非诚有以大过于人者焉,能与于此哉。故宏词伟论,瑰丽之华藻,有足以发明天子之深意,形容一世之盛烈,无愧乎黍谷西河之士。非曩时所谓窃处士之虚名,遵仕宦之捷径者也。〔91〕
崔公度以《感山赋》而受知于欧阳修、韩琦等当世名公,由隐入仕之后,还曾以《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上时相王安石,虽非“窃处士之虚名”,但也不是“不游高门”。华镇所云,与事实不符。但他所说的“宏词伟论,瑰丽之华藻,有足以发明天子之深意,形容一世之盛烈”,显然是沿袭了韩琦等名公对崔公度《感山赋》的品鉴之语,代表了当时士林的公论。南宋以来,《感山赋》曾入选《圣宋文海》及吕祖谦编《皇宋文鉴》。《宋史·艺文志》著录崔公度《感山赋》一卷,可见此赋曾以单行本流传于世,颇受宋代士人的重视。
又以李觏《明堂定制图并序》为例,李觏一生多次谒见名公巨卿,皆以此投献,或提及此篇:
景祐二年(1035),李觏年二十七,以《礼论》七篇、《潜书》十五篇净写编成一册,投献给苏绅。在《上苏祠部书》中首次提及作《明堂定制图并序》。
景祐三年,李觏年二十八。以《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投叶清臣、李淑。又以《潜书》十五篇、《野记》二篇、《礼论》七篇,投献聂冠卿,再次提及《明堂定制图并序》之大旨:
觏尝以明堂者,古帝王之大事也。而去圣久远,规模莫见。《周礼·考工记》、《大戴礼·盛徳篇》、《礼记·月令》“室个”之说,参差不齐。繇汉迄唐,老师大儒,各执一经,相为矛盾。有国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宫,缺而不立。虽有作者,皆取临时处置,非复先王之法象。觏谓《周礼》、《大戴礼》、《礼记》皆圣人贤人之所作述,不宜辄有乖异。反复思念,则三家所指,制度果同。但立言质略,意义弗显。训传之士,泥文太过,遂成派分。故尝挟而正之,决而通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三家之说,坦然大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见成王、周公享帝视朔,朝诸侯于其上。因作《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约五千言。〔92〕
景祐四年,以《潜书》十五篇、《野记》二篇、《礼论》七篇投范仲淹。其所附书信中有曰:“尝所著《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前日度支魏公以列于座隅,兹不再献。”〔93〕
康定二年(1041,是年十一月改元“庆历”),李觏三十三岁,应茂才异等,以策论等投王尧臣,再次提及《明堂定制图》一道并序。此次“因旧本漫灭,未敢自陈。俟请见后再献矣”。
《明堂定制图》一篇并序,乃李觏精心结构的经学著述,李觏自谓能在三礼的基础上,考证明堂制度之异同,疏通窒碍,驳正汉唐先儒之曲见陋说,而还经文之本来面目。因此,自景祐至康定的七年之间,李觏反复以此投献,并因此声望渐起,其在经学上的造诣逐渐为士人所认可。如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在回李觏信中说:“润州掌学胡瑗秘阁校理见《明堂图》,亦甚奉仰”。又,张宗古《送李君南归序》曰:
泰伯家江西,嗜古学。以谓今天子享上帝,朝诸侯,虽有其礼而无其位,乃潜心愤悱,贯览数家之说,自《周官·考工记》、《大戴礼·盛徳篇》、《礼记·月令》、《汉白虎》诸儒及历代论议,参总会一,稽同合异,曲者畅之,滞者通之,为《明堂定制图》一篇并序,凡数千言。朅来京师,挚见时彦,若李宋二紫微,左史聂长孺,集贤叶道卿,皆旴衡接纳,郑重推许。〔94〕
“集贤叶道卿”,指“叶清臣”,景祐年间,叶清臣得李觏所贽“小文编及《明堂图》”,“披玩寻绎,弥增景服”,认为汉唐以来的经学家,于明堂位无甚高论,阔略已甚,而李觏此图此文,“披文会今古,援笔考同异。面势本《周官》,纤悉探吕氏。俯拾林甫长,仰擿康成盭。昭发老生蒙,符作者意。”〔95〕能合诸家之长,能得圣人之原旨。故以一启一诗报之,郑重推许。
通过书、启、序、诗等文学样式,名公巨卿尽力为李觏延誉、推挽。《明堂定制图并序》随之也享誉士林。范仲淹在《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中说:“李觏,丘园之秀,实负文学,著《平土书》、《明堂图》,鸿儒硕学,见之钦爱。”〔96〕可谓实录。其后范仲淹荐举李觏的《荐章》之中,多次提及此篇,并附荐书上进。
皇祐元年(1049)十一月,范仲淹荐举李觏,中曰:“(李觏)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今取到本人所业《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序》一篇、《平土书》三篇、《易论》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编为十卷,谨缮写上进。”〔97〕
次年,范公再荐李觏,其《荐章》曰:
伏见建昌军草泽李觏,十余年前曾撰《明堂图》并序一首,大约言周家之制,见于《月令》及《考工记》、《大戴礼》,而三家之说少异,古今惑之。觏能研精其书,会同大义,按而视之,可以制作。臣于去年十一月录进前人所业十卷,其《明堂图序》一卷,必在两制看详。今朝廷行此大礼,千载一时,何斯人学古之心上契圣作。臣今再录其图并序上进,伏望特赐圣览。〔98〕
皇祐二年(1050),朝廷因范仲淹之荐,经中书审察合格,特授李觏将仕郎、试太学助教。所下《告词》曰:
敕建昌军草泽李觏:藩臣仲淹以觏所著文二十四篇来上。予俾禁掖近侍详较,皆曰学业优,议论正,有立言之体。且履行修整,诚如荐章所云,故特以一命及尔。〔99〕
从上述李觏《明堂定制图并序》一文的流传与接受来看,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印象:
其一,李觏对于《明堂定制图》及序的学术内涵与应用价值,有异乎常人的自信。
其二,此图此文在李觏生前流传甚广,其学术价值已得到了当时在政治上、学术上、文学上有地位的人充分的肯定。
其三,当时的名公巨卿,用书、启、诗、荐章等文体,对此图此文之学术内涵皆有不同程度的发覆。如张宗古《序》曰:“参总会一,稽同合异,曲者畅之,滞者通之。”〔100〕叶清臣的诗曰:“披文会今古,援笔考同异。”〔101〕范仲淹的荐章曰:“研精其书,会同大义,按而视之,可以制作。”〔102〕这些品鉴,与李觏对此图此文的自我评价,有互相呼应之处。
其四,朝廷的两制官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在看详此图此文(也包括李觏的其余学术著作)时,认可了荐举人的品评,并给予李觏其人其学以官方的肯定,李觏因之而被授予官职。
文本流传之广,士林品评之高,独特而有价值的内涵,是衡估经典作品的几项重要指标。从这几个的重要参数来看,李觏的《明堂定制图并序》在其生前,就已被经典化了,至少已经是礼学名篇。南宋之时,唐仲友《明堂说》《帝王经世图谱》、周必大《礼部太常寺议明堂大礼状》、卫湜《礼记集解》皆援引李觏《明堂定制图并序》,以为己说,《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亦收录此序,由此可见此篇的影响之大。李觏的门生陈次公在《李觏墓志铭》中回忆道,李觏临终无他言,“独执次公手以《明堂制图》为托,又以为《三礼论》未成为恨。”〔103〕这个细节,所喻示的欣慰与遗憾,是李觏对自我一生的总结。《宋史》李觏本传,介绍李觏生平仅寥寥数语,而于《明堂定制图序》详加节引,达千字以上。这是宋代《国史》史官,同时也是《宋史》的修撰者对李觏的评介。李觏的《明堂定制图》及序,是李觏学术形象的缩影。这个缩影的形成,显然是与李觏的投献分不开的。
以上本文从宋代荐举遗逸的主要政治文化功能、宋代受召士人的人员组成与身份特征等方面,揭示了宋代士人在退处之后,仍不失用世之心,并和当时士林保持良好的学术互动与文学交游的制度背景。以此为中介,进一步分析了宋代隐士投献的若干特点,及其对文学传播、经典生成方面所产生的正面推动作用。联系过往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宋代隐士身上与社会疏离的一面,以及其作品中的恬淡、出世的成分,重心也往往落在一些名隐、“真隐”身上,本文从制度感召入手,借助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隐士投献,来说明宋代“举遗逸”制对于退处型士人人生轨迹、心路历程与文学活动所造下的深刻影响,研究的重心也相应转向下第士人,以及一批由隐而仕的士人身上,希望这一转向,对于揭橥宋代尚隐之风的形成,以及隐士文化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能稍有助益。
注释: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09页。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8页。
〔3〕〔宋〕富弼:《上仁宗乞诏陕西等路奏举才武》,〔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93页。
〔4〕〔5〕〔7〕〔8〕〔9〕〔10〕〔11〕〔12〕〔60〕〔89〕〔9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933、5934、5926、5926、5926、5928、5931、5933、5929、5929、5929页。
〔6〕〔17〕〔18〕〔20〕〔36〕〔64〕〔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54、13440、13443、13443、13122、13441页。
〔13〕〔14〕〔96〕〔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清〕范能浚编集、薛正兴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第2004年,第398、398、557页。
〔15〕〔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4册,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698页。
〔16〕〔宋〕郑獬:《请举遗逸》,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6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8页。
〔1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49页。
〔21〕〔宋〕司马光:《答刘蒙书》,《司马光集》,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47页。
〔22〕〔宋〕吕南公:《壬戌岁归治西村居奉答次道见寄长句》,《灌园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页。
〔23〕参见刘文刚:《宋代的隐士与文学》相关章节,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
〔24〕〔25〕〔26〕〔27〕〔28〕〔94〕〔95〕〔99〕〔101〕〔102〕〔宋〕李觏:《李觏集》,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8、377、309、312、313、507、508、492、508、496页。
〔29〕〔宋〕李觏:《上叶学士书》,《李觏集》,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3页。
〔30〕参见〔宋〕李觏:《上范待制书》《寄上范参政书》《庆历民言》等,见《李觏集》卷二十七、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1〕〔宋〕李觏:《与胡先生书》,《李觏集》,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2页。
〔32〕〔93〕〔宋〕李觏:《上范待制书》,《李觏集》,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9页。
〔33〕〔34〕〔37〕〔38〕〔39〕〔40〕〔41〕〔42〕〔43〕〔44〕〔45〕〔49〕〔50〕〔74〕〔76〕〔宋〕吕南公:《灌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0、110、103、132、103、89、21、21、21、94、132、105、104、103、106页。
〔35〕吕南公对于科举失利的反思,见《灌园集》卷九《老懒轩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4页。
〔46〕〔宋〕吕南公:《与汪秘校论文书》,《灌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5页。
〔47〕〔宋〕吕南公:《上曾龙图书》,《灌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5页。
〔48〕〔宋〕曾巩:《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7页。
〔51〕〔55〕〔宋〕曾肇:《曲阜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4、356页。
〔52〕〔宋〕吕南公:《请见郑太守书》,《灌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2页。
〔53〕〔75〕〔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24、1525页。
〔54〕〔宋〕蔡延世:《跋吕南公删修韩退之传》,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17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56〕〔宋〕吕南公:《灌园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页。
〔57〕〔58〕〔63〕〔宋〕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六,〔宋〕苏颂:《苏魏公文集》附录一,王同策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54、1154、1159页。
〔59〕〔62〕〔宋〕苏颂:《苏魏公文集》,王同策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84页。
〔61〕〔宋〕释文莹:《玉壶清话》,郑世刚、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0-51页。
〔65〕〔宋〕蔡襄:《蔡襄集》,吴以宁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72-473页。
〔66〕〔73〕〔宋〕苏轼:《与李方叔书》,《苏轼文集》第4册,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0页。
〔67〕〔宋〕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全宋笔记》第二编(九),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69〕〔宋〕胡寅:《斐然集》,容肇祖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12页。
〔70〕〔71〕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10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2页。
〔72〕〔宋〕司马光:《涑水记闻》,邓广铭、张希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1页。
〔77〕〔80〕〔87〕〔宋〕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3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
〔78〕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79〕〔宋〕员兴宗:《夫人员氏墓志铭》:“安舆者,字文饶,才茂异常,与西州处士苏洵明允,张愈少愚通书,周旋文谊。当是时,巴蜀学士深心翰墨者,莫不共高此三人。”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21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5页。
〔81〕〔宋〕曾巩:《苏明允哀辞》,《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60页。
〔82〕〔宋〕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83〕〔宋〕苏洵:《上田枢密书》,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8-319页。
〔84〕〔宋〕苏轼:《跋先君书送吴职方引》,《苏轼文集》第5册,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92页。
〔85〕〔宋〕雷简夫:《上韩忠献书》,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38页。
〔86〕〔宋〕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38-539页。
〔88〕〔宋〕孙升:《孙公谈圃》,《全宋笔记》第二编(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91〕〔宋〕华镇:《云溪居士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7-498页。
〔92〕〔宋〕李觏:《上聂学士书》,《李觏集》,王国轩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1页。
〔97〕〔宋〕范仲淹:《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范仲淹全集》,〔清〕范能浚编集、薛正兴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398-399页。
〔98〕〔宋〕范仲淹:《荐章》,《李觏集》,王国轩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6页。
〔100〕〔宋〕张宗古:《送李君南归序》,《李觏集》,王国轩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07页。
〔103〕〔宋〕陈次公:《李觏墓志铭并序》,《李觏集》,王国轩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