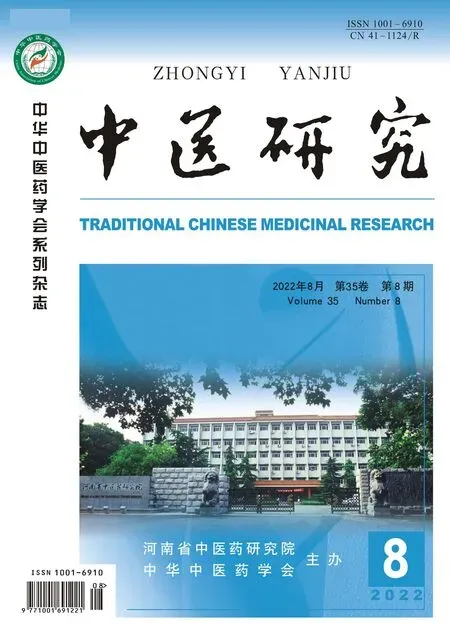宋金伤寒研究中对“六经之为病”的认识*
程传浩,张海燕,白 杨,李青雅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 郑州 450046)
“六经之为病”即《伤寒论》中三阴三阳六病的提纲条文,即“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等6条,在《伤寒论》研究中常被视为六经辨证纲领。笔者发现,在宋金时期的伤寒研究中,“六经之为病”并未受到宋金医家的广泛重视,反而更加侧重于《素问·热论篇》《伤寒论·伤寒例》逐日传变的论述,视之为纲领,与明清医家高度重视“六经之为病”形成鲜明的对比。本文就此现象对现存宋金时期伤寒著作进行考查,总结其对“六经之为病”的认知,并与“热论”“伤寒例”进行比较,分析其产生的背后原因,以总结此时期伤寒研究的特点,对分析伤寒学术、学派演变的脉络有一定的意义。
1 《素问·热论篇》《伤寒例》及“六经之为病”相关内容的比较
《素问·热论篇》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溢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从经络角度对伤寒逐日传变进行分析,并提出三阳宜汗、三阴宜下的治法。《素问·热论篇》曰:“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又曰:“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1]
“伤寒例”逐日传变出自宋本《伤寒论》中“伤寒例”篇。“伤寒例”中“逐日浅深”传变的条文为“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鼻干、不得卧;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2]。“六经之为病”即《伤寒论》中论述三阴三阳六病条文,分别为“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热论”和“伤寒例”明显有经络辨证的印迹,内容相近,都以伤寒为外感热病,三阴三阳均表现为热证。但在传变日数上,“伤寒例”将“热论”的单日传变改为约略的双日传变,又增加了脉法内容,以脉法为纲,脉证结合,可视为对“热论”的补充与完善。在治法上三阳宜汗、三阴宜下两者亦同,可见“伤寒例”与“热论”是一脉相承的。而“六经之为病”不论是六经证候的复杂性,还是治法的多样性上,与前两者明显不同,如《伤寒论》六经皆有表里、阳明主里、三阴经多虚寒。故而六经之为病更能符合《伤寒论》六经之提纲。此外,“六经之为病”不以“伤寒”起句,直述三阴三阳“之为病”;不述日数而直言脉证,亦不述六病治法。可见,“六经之为病”条文与“热论”“伤寒例”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宋金医家研究伤寒多以《伤寒论》为主体,而又以“热论”“伤寒例”为纲,其间辨证、治法存在诸多抵牾之处,可于“六经之为病”窥其肯綮。那么宋金医家又是如何认识并处理其间关系就值得深究。
2 宋金医家著作对“六经之为病”条文的认识及处理
宋代时期伤寒研究著作现存者共14部[3],同时期北方金代亦有《伤寒明理论》《注解伤寒论》《伤寒直格》《伤寒心镜》《伤寒医鉴》《伤寒心要》等伤寒研究著作,因其大多有承袭关系,本文选其代表性著作《伤寒微旨论》《伤寒总病论》《类证活人书》《伤寒明理论》《注解伤寒论》《伤寒百证歌》《伤寒百问歌》《伤寒补亡论》为研究对象,进行考查。
2.1 《伤寒微旨论》
《伤寒微旨论》是北宋医家韩祗和于元祐元年(丙寅,1086年)所撰,以韩氏对《伤寒论》的研究心得为主要内容,又涉及《黄帝内经》《难经》中关于伤寒的论述。韩氏继承“热论”以伤寒属热证的认识,对伤寒病因提出“伏阳学说”。韩氏重视“热论”的纲领性意义,在“病源篇”中以“热论”逐日传变为纲,释“伤寒之为病,只受于三阳三阴”之理。在“总汗下篇”中,认为“热论”所述“三阴三阳受病之日,乃是圣人立条目之法”,治法以汗下为主,“凡治伤寒病,若能辨其汗下者,即治病之法得其十全矣”。对于“伤寒例”,韩氏以为“黄帝作三阳三阴证在前,仲景述三阳三阴脉在后”[4],两者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韩氏对“六经之为病”的内容及条文,全文均未提及。
2.2 《伤寒总病论》
《伤寒总病论》是庞安时约于元符三年(1100年)撰写的,是作者研读《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经历数年而撰成。此书述六经证治,重视“伤寒例”的纲领性地位,三阴三阳六病均以“伤寒例”为纲,其间未论及“太阳之为病”条文,阳明病提及“胃家实”三字[5],少阳证中于“伤寒例”条文下,列“少阳之证,口苦,咽干,目眩也”[5]26;三阴证中在“伤寒例”下列出了“六经之为病”的内容[5]32,与“伤寒例”同列。可见庞氏已重视到“六经之为病”,但整体上仍置于“伤寒例”框架之下,如在治法上循“伤寒例”三阳宜法,三阴证入腑应行下之法;太阴病“宜大承气汤下之”[5]36,少阴病“大承气汤下之”[5]38,厥阴证既用“桂枝麻黄各半汤”又“宜承气汤下之”[5]40。同时,亦保留引用了太阴证“当温之,以四逆辈”,厥阴证乌梅丸等方[5]44。可见,庞氏对“六经之为病”的处理是以“伤寒例”脉证、治法为主纲,又选择性保留了“六经之为病”及三阴温法的部分内容。在处理两者的抵牾时,庞氏以“伤寒例”为主,兼纳部分“六经之为病”,而无辨析。
2.3 《类证活人书》
《类证活人书》成书于1108年,作者为朱肱。卷首“经络图”中即以“伤寒例”为主体,设六经证候答,间接引用仲景六经病欲解时及《伤寒论》相关方剂,可见其以“伤寒例”为伤寒之主纲。但对于“伤寒例”的证候表现,又依“六经之为病”而有所增益,如太阳病部分增加了“发热恶寒”[6]3,少阳病增加了“或口苦舌干,或往来寒热而呕”[6]7,太阴病增加了“手足自温,或自利不渴,或腹满时痛”[6]11,少阴病增加了“或口中和而恶寒”[6]12,均出处“六经之为病”相关条文。然于阳明病下独不引“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6]13。此外,在卷三、卷四中,“问阳证”“问阴证”中提到了太阳的“发热恶寒、头疼腰痛而脉浮”[6]28,阳明的“不恶寒反恶热,汗出,大便秘”[6]29,少阳的“发热而呕,或往来寒热”[6]33,少阴的“微细心烦,但欲寐,或自利而渴”,厥阴的“消渴,气上冲,心中疼热,饥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等[6]34,亦出自《伤寒论》中“六经之为病”部分。可见,朱氏已经重视“六经之为病”的内容及其重要意义,但不能将其与“伤寒例”做区分明辨,仅采用了并列、糅合的方式混于一体,明显更重视“伤寒例”的纲领性作用。
2.4 注解《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
《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为金人成无己所著,书成后传入南方,为宋人推崇而刊行。《注解伤寒论》开仲景《伤寒论》注解之先河,其意义在于突破了宋人研究伤寒病的模式,转为研究《伤寒论》本身。即使如此,成无己于《伤寒论》认知的整体学术思想上仍承袭前人,如对于“伤寒例”逐日传变脉证条文时,与前人认知相较并无创见。在注“六经之为病”原条文时亦未高度重视,注解时复引“伤寒例”为释;“阳明之为病”,则引用华佗“热毒入胃”之说;“少阳之病”,引《黄帝内经》《甲乙经》胆经证候。成无己对于“三阴之为病”的注解是遵从“热论”“伤寒例”的认识,以为三阴病属热证。“至四五日,少阳传太阴经,邪气渐入里,寒邪渐成热,当是时也,津液耗少,故腹满而嗌干。至五六日,太阴传少阴,是里热又渐深也”[7],以为三阴皆为阳热而渐深。如“太阴之为病”,成无己认为“太阴为病,阳邪传里也”,并以热证病机释“自利益甚,时腹自痛”[8]8。成氏特意将太阴腹痛与阴寒腹痛进行鉴别。“阴寒在内而为腹痛者,则为常痛”,而“阳邪干里”则为“时腹自痛”[8]53。如“少阴之为病”,成无己注为“少阴为病,脉微细,为邪气传里深也。卫气行于阳则寤,行于阴则寐。邪传少阴,则气行于阴而不行于阳,故但欲寐”[8]54,亦当指从热证而非阴寒。“厥阴之为病”,成无己认为“邪传厥阴,则热已深也”[8]55,亦从“热论”。可见,成氏对于三阴病六经之为病的认识服从于“热论”及“伤寒例”中六经皆热的认知,虽注“六经之为病”而不脱热论、伤寒例之巢窠。
2.5 《伤寒百证歌》
此书为许叔微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撰成,参考朱肱《类证活人书》,将《伤寒论》中关于证候、方治的内容以七言歌赋形式编为五卷一百证(症),以便后世学者习诵。许氏对于《伤寒论》中“八纲辨证”的思想着力甚深,然因袭于朱肱,未能突破“热论”“伤寒例”的认知框架。如卷一“三阴三阳传入歌”,首引“伤寒例”,如太阳病中“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当一二日发。以其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余经皆如此。对于仲景“六经之为病”内容,存见于卷二、卷三的伤寒症状中,如第八十三证“口燥咽干歌”中,引“少阳之为病”;第七十三证“腹满歌”中,引“太阴腹满必时痛”;第七十四证“阴证阴毒歌”中,引“少阴之为病”“厥阴之为病”相关内容。但未将其作为提纲处理,而且此几处显然将“三阴之为病”的表现当作热证来认知处理的。
2.6 《伤寒补亡论》
此书为郭雍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成书。编次“自岐黄以及近代诸书,凡论辨问答证治,合一千五百余条,总五万字,分七十余门”[9]。该书设问自答,系统总结、讨论、梳理了郭氏之前伤寒、热病中的各种学术问题,是一部伤寒研究阶段的总结性著作。此书对伤寒病的认识仍以“热论”“伤寒例”为宗旨,而“六经之为病”则依然未做深究。如在第二十二问中,系统论述了六经循行、六经日数、六经意义、六经脉状等主要问题,独不论及“六经之谓病”。在“六经统论”中,皆从热论经络传变及三阳宜汗、三阴宜下之说,其涉及“六经之为病”处,将其附于“伤寒例”逐日脉法之后,以“又曰”方式复引“六经之为病”。可见郭氏已经重视到六经之为病的条文,但将其附于“伤寒例”条文之后,可见更重视“伤寒例”。总体而言,郭氏仍以仲景“伤寒例”为主,坚持六经病皆为病热,三阳宜汗,三阴宜下,同时又根据仲景条文做了补充。如厥阴病中,治法方药就汇总了大承气汤、桂枝麻黄各半汤、乌梅丸、四逆汤、理中丸、苓桂术甘汤等治法。
2.7 其他著作
宋金时期的其他著作如《活人书括》《伤寒类证》《伤寒要旨》《伤解惑论》《伤寒百问歌》《伤寒直格》《伤寒心镜》《伤寒十劝》《伤寒医鉴》《伤寒心要》《伤寒类书活人总括》等书,大多因袭前人之论,受朱肱《类证活人书》影响最大[10],或不论“六经之为病”,或袭前人而将其糅合于“伤寒例”中,并无突破性认识。北方金人又受刘完素《伤寒直格》影响较甚,亦守伤寒从属于“热论”之论[11]。
3 宋金医家未重视“六经之为病”的原因
综上所述,宋金伤寒著作中多以“热论”“伤寒例”为伤寒之纲领,对“六经之为病”,或不论涉,或以“或曰”“又曰”的方式附于“热论”“伤寒例”之下,或糅合于“伤寒例”之中。而“热论”“伤寒例”与整个《伤寒论》诸多矛盾、抵牾之处,宋人明显未予以重视。如经络受病证候与“六经之为病”证候的矛盾,“伤寒例”脉法与“六经之为病”脉证的矛盾,“热论”“伤寒例”尽为热病与三阴三阳寒热并现的矛盾,“逐日汗下”治法与三阳有汗下、三阴汗下温的矛盾。宋金医家或已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未能深究而有所突破,可能有以下原因。
3.1 研究对象的不同
宋人研究伤寒时,其对象主要是伤寒病,而不是《伤寒论》本身,这一点前人早有论述。宋人研究伤寒病时,虽以《伤寒论》为主体,但以广义的伤寒热病为主,包括温病乃至时病在内。这种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宋金医家更侧重于“热论”为主要框架的辨证体系,将《伤寒论》条文置于广义外感热病的范围之上,对《伤寒论》条文选择性引用,同时有所增删,增以其他医书、医论及方剂,又增加温病[12]及妇儿科内容。
3.2 研究方法的影响
早期的医著如《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前人著述是以广纳诸论的文献汇集方法为主,以时间先后为序整理相关内容,则必然以《素问·热论》为渊薮,其他医家则为支流。《伤寒论》显然只是众多医家中的一家,故在对待伤寒诸多问题上,仍要从属于“热论”等经典理论的局限。宋金医家研究伤寒时,受以上著作体例及研究方法影响较大[13],故不能舍“热论”而就“六经之为病”。此外,不辩驳、批判前人,因循经典的遵经思想,亦是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14]。
3.3 认为“伤寒例”为仲景所述
“伤寒例”不但在《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中有述录,而且亦录于政府主持校订的宋本《伤寒论》中,作为纲领性内容列于六经病之前。在宋金医家眼中,“伤寒例”出自《伤寒论》原文,是仲景所述,有高度的权威性,故不否定而必遵从之。
3.4 对《伤寒论》研究的侧重
宋金医家对《伤寒论》本身的研究上亦多侧重于证候学,尚未深入理法方药。如朱肱开《伤寒论》“类证”研究专著之先河之后,《伤寒百证歌》《伤寒类证》《伤寒百问歌》《伤寒类书活人总括》等以伤寒症为主要研究内容,或设问答,或编为诗赋,便于记诵[15]。故而宋金阶段,医家研究《伤寒论》主要侧重于证候学[16],而其他问题尚未及之,这是学术发展的阶段性侧重所致。
4 明清医家对“六经之为病”的重视
随着对伤寒病及《伤寒论》研究的深入,一些医家意识到宋金医家的局限之处。如庞安常著《卒病论》、朱肱著《活人书》、韩祗和著《微旨》、王实著《证治》,虽皆互有阐明之义,但未能尽张仲景之深意。方勺《泊宅编》载朱肱《类证活人书》遭时人指摘之事,曰:“肱之为此书,固精赡矣。尝过洪州,闻名医宋道方在焉,因携以就见。宋留肱款语,坐中指驳数十条,皆有考据,肱惘然自失,即日解舟去。”[17]
宋金诸家将“热论”“伤寒例”六经与《伤寒论》六经混为一谈,给深入研究仲景的辨证论治规律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热论”“伤寒例”与“六经之为病”为代表的辨证论治体系的矛盾为医家揭示。为解决此问题,部分医家将“伤寒例”视为王叔和撰次《伤寒论》时加入的个人认识,而非仲景原文,以此斥责“伤寒例”之非,保证仲景六经辨证的整体精神。元朝王履最早指出王叔和“惜其既以自己之说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杂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乱”,认为王叔和整理《伤寒论》时将自己的观点与仲景思想混为一谈[18]。明朝方有执承王履之说,认为“伤寒例”等内容为“太医令王叔和附以己意”所加入,非仲景原文。在此基础上直接删“伤寒例”,错简重订,使《伤寒论》的研究摆脱了“热论”的束缚,从伤寒病的探讨转向辨证论治方法的研究[19-20]。即使主张维护旧论的张志聪、陈修园诸伤寒家也主张删去叔和序例,可见“伤寒例”与“六经之为病”的学术逻辑的不可调和已成共识。明末喻嘉言直斥叔和之非,“其序例一篇,明系叔和所撰”,并作“驳正王叔和序例”,以为叔和“造不经之说,混乱经常”,“以此网罗英贤,悉入彀中,其授受之途,盖已千年长夜矣”[21],“庞安常、朱肱、许叔微、韩祇和、王实之流,非不互有阐发,然不过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见为仲景之功臣也”“林、成二家,过于尊信叔和,往往先传后经,将叔和纬翼仲景之辞,且混编为仲景之书”[21],明显在批评宋金时伤寒研究缺陷。明末清初柯琴亦认为:“夫叔和不于病根上讲求,但于病名上分解,故序例所引内经,既背仲景之旨,亦舛岐伯之意也。”[22]与之相应的就是“六经之为病”条文的地位得到提升,成为三阴三阳辨证的纲领。如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将“六经之为病”条文移至六病头条,如认为太阳之为病,“此揭太阳之总病,乃三篇之大纲”;阳明之为病,“胃实反得以揭阳明之总”。此后喻氏《尚论篇》、柯琴《伤寒论注》、尤氏《伤寒贯珠集》等均作此调整,视“六经之为病”为六经辨证的提纲。由此以“错简重订”为端,开始了伤寒学派的争鸣阶段,以“六经之为病”为代表的六经本质的讨论,使伤寒研究突破了“热论”“伤寒例”关于外感热病的限制,扩大至临床杂病方面的运用,如柯琴最早提出“夫一身之病,俱受六经范围者,犹周礼分六官而百职举,司天分六气而万物成耳,伤寒不过六经中一症”“夫热病之六经,专主经脉为病,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同时温病学派亦因此而脱离伤寒研究,自立门户[23],亦是伤寒学研究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