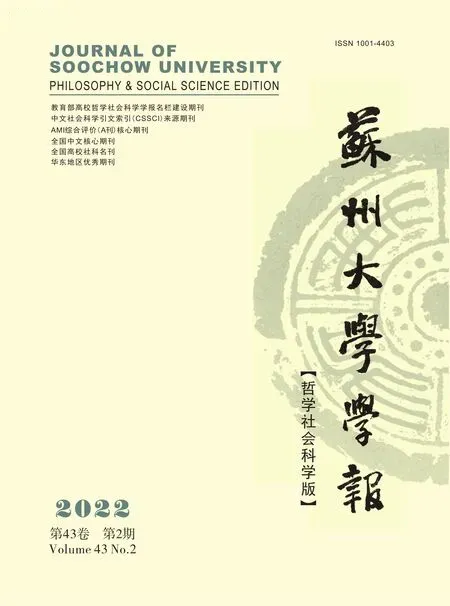卡尔·波普尔渐进社会工程理论及其贫困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
邹志鹏 张 浩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作为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主张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科学,认为“只有对于科学才可以说我们经常从错误中学习,才可以清楚明白地说到进步。而大多数其他人类活动领域虽然有变化,却很少有进步”(1)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页。。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波普尔将批判理性主义应用到了政治哲学领域,形成了渐进社会工程理论。渐进社会工程理论以“最小痛苦原则”为价值指向,批判整体主义社会工程以某种终极状态为蓝图按图索骥地改造社会,主张以一种和平、试错和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尽管渐进社会工程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改良,但作为一项治理和改造社会的方案,它并不能解决阶级社会的固有问题,因而也难以掩盖其理论的贫困。
一、渐进社会工程的哲学基础和价值旨归
科学是波普尔渐进社会工程理论的出发点,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便是由经典物理学中不具有科学决定论推理而来的。在此基础上,波普尔进一步断定历史决定论者极可能具有极权主义倾向。这一理论呈现出了明显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特征。
(一)批判理性主义:渐进社会工程的哲学基础
首先,波普尔认为可证伪的知识才是科学的知识。为了明晰“科学”的概念,波普尔认为有必要对“科学”与“非科学”进行界定。科学是从猜想到反驳的过程,是“猜想的知识”和“寻求和消灭错误并服务于真理的方法”(2)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而非科学尽管经常得到正确的结论,却错误地将知识视为静态的封闭系统和经验的集合。因此,非科学作为“自相矛盾的系统必须排除”(3)Karl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2,p.12、12.。在波普尔看来,从提出一项猜想,到反驳其中的不合理部分,这个过程就是证伪的过程,亦即科学的过程,正如加西亚所说,“在波普尔看来,可证伪性是一个合适的划界标准,成为经验理论的标志”(4)Carlos E Garcia.Popper’s theory of science:an apologia.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06,p.9.。波普尔科学观的精髓就在于批判,即用逻辑力量和理性批判不断地排除知识的错误方面,通过不断证伪无限逼近“真理”。波普尔将这一过程总结为一个著名的四段图式:一个问题→试探性理论→排除错误→新的问题(P1→TT→EE→P2),即通过不断发现错误和排除错误推动社会发展。
其次,波普尔认为科学是知识增长的动态过程。在四段图式中,“TT”和“EE”代表了知识增长中的最重要部分——“猜想”与“反驳”。承认科学知识从猜想到反驳的不断变化的知识增长过程就是波普尔科学观的核心思想,正如他所说:“与其把这些非常美妙的演绎系统(从古到今的科学家们的宇宙论和认识论)看成目的,不如看成是台阶:我们走向更丰富、更能经受检验的科学知识的重要步骤。”(5)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16、310、518页。为了度量科学知识增长的程度,波普尔提出了“逼真度”的概念,认为一个理论排除的错误越多,可检验的程度越高,这个理论的“逼真度”就越高,接近真理的程度就越高。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波普尔对柏拉图和马克思的整体主义社会工程提出了批判,他认为柏拉图和马克思预设了一个永恒的、静止的理想蓝图,这“将永远是纯粹的猜想”,经不起反驳,因而不符合科学的基本规范。
最后,波普尔在历史哲学领域提出了历史非决定论思想。在将科学理解为只是不断增长的动态过程的基础上,波普尔将目光转向了社会历史领域,他认为人们只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排错和证伪,就能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势”以及“哪一种理论是更好的理论”,正如他所说:“我们甚至可以在一种理论收到检验之前就知道,它如果通过了某些检验就将比其他理论更好。”由此可知,波普尔将科学知识增长的非决定结构视作历史非决定论的逻辑前提和论证依据。他认为,自然界的演变具有自在性和纯粹客观性,但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却参与了历史进程,“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人类知识的增长引发了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而且以人类有限的观察能力也难以把握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因此“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6)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2页。,所以他认为柏拉图、马克思等人描绘的历史蓝图毫无科学可言。
(二)尊重个人的主体地位:渐进社会工程的价值旨归
首先,波普尔指责整体主义社会工程本质上是一种极权主义。波普尔认为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必定追求平等,因为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无论他可能具有怎样的批判能力或理性,都应归之于和其他人的交往”,所以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而整体主义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在哲学王统治背后隐藏的是对权力的追求,给最高统治者的画像就是一幅自画像”(7)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其本质上是一种破坏平等的极权主义,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正如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指出的,“共同目标对人们并非一种终极目标而是一种能够用于多种多样意图的手段的地方”(8)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自由主义者批判整体主义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的目标就是要让“共同目标”成为全社会的信仰,对每个社会个体进行思想控制和改造,利用善良的人“制造人间地狱”。为此,渐进社会工程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主张“每代人都不必为将来的一代一代而牺牲,为一个可能永远实现不了的幸福理想而牺牲”(9)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516、514、513页。,认为不可避免的苦难应该尽可能地由大家平等分摊,而不是由某一代人独自承受。
其次,波普尔阐述了渐进社会工程实现个人幸福的方式。波普尔认为,从目标上看,整体主义工程“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的方式很难取得成功,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标准不同,所以人们对幸福的感受程度也不相同。而且相较于“增加幸福”的需要,人们对“祛除苦难”显得更为急迫和确定,因为“针对苦难、不公正和战争的有系统的斗争比为了实现某种理想而战,更能获得广大人民的认可和赞同”(10)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304页。。而且从科学的角度看,追求幸福也需要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必须经过“猜想—反驳”的环节进行渐进性证伪。波普尔指出:“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是一代代逐步减轻人生的苦难,减少不公正”,即通过逐渐减轻或消除人生的苦难与不公正,从而不断接近生活的幸福与平等。波普尔在政治哲学中坚持“最大限度消除痛苦”与其在科学哲学中排除错误的做法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都是证伪主义原则在不同科学中的运用。
最后,波普尔阐述了渐进社会工程的“最小痛苦原则”。波普尔认为“并不存在使一个人幸福快乐的制度手段”,只有“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要去实现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手段来建立幸福。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才能找到追求幸福的科学方法。波普尔将人类的苦难视为一种直接的道德诉求,认为人们既然无法直接寻求“最大限度的幸福”,那么就应该尽可能地只承受“最小痛苦”。诚如波普尔的助手希尔默(Jeremy Shearmur)所言:“波普的观点最好被解释为一种道德实在论(ethical realism),在这种立场上,波普在他更具一般性的著作中发展起来的认识论方法也可以被运用于道德判断。”(11)杰里米·希尔默:《卡尔·波普的政治思想》,储智勇、毛兴贵译,吉林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30页。由此可见,波普尔在论述渐进社会工程理论的过程中内含了自由主义和消极功利主义的价值追求和道德判断,即以祛除不平等与消除苦难作为其理论的价值追求。
二、和平、试错与渐进:渐进社会工程的实现路径
波普尔认为整体主义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是通过整体主义方法建立的,而整体主义方法是柏拉图时期就已有的古老方法,带有“前科学时期的特征”(12)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整体主义社会工程采用野蛮落后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暴力和极权。只有通过渐进地试错和改革,才能使社会历史实现科学发展。
(一)将暴力置于和平与理性控制之下
波普尔从理性出发,认为理性主义有正确与错误之分,错误的理性主义推理出了乌托邦主义,而乌托邦主义又导致了暴力的错误行径。在波普尔看来,乌托邦主义者不可能理性地制定科学目标,因为他们预先设定了一个终极目标,而为了维护这个目标的“科学性”和“神圣性”,“唯一的方法似乎又是诉诸暴力,包括宣传、压制批评和消灭一切对立面”。但科学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过程,不存在某种最终状态,乌托邦主义这种抽象而虚假的慈善,非但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反而会使人生活在专制统治与暴力威胁之下。与整体主义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不同,渐进社会工程推崇“真正的理性主义”,即通过和平与理性的方式推动社会制度的完善。
首先,渐进社会工程明确反对勾画蓝图的做法。波普尔认为:“只有放弃在意见上以权威自居的态度,只有确立平等交换意见和乐意向他人学习的态度,我们才可望控制由虔诚和责任所激起的暴力。”(13)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08、512、508、509页。波普尔的这一观点源于他对自然科学的观察:“任何物理学都不会告诉一个科学家,他制造犁、飞机或原子弹是对的。他必须选定目的,或者给他规定目的;他作为科学家的工作仅仅是构造可用于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波普尔通过旁引自然科学的方法试图证明,预设蓝图与计划的做法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而是暴力发生的条件。其次,渐进社会工程主张采取辩论的方式解决分歧。波普尔认为,渐进社会工程与整体主义社会工程的分歧在于:“渐进工程的工程师可以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整体主义者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事先就一口咬定彻底改造是可能的和必然的。”(14)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0、70页。波普尔将辩论与暴力视为解决分歧的两种对立途径,认为辩论是合乎理性的态度与方法,是比整体主义更为科学和谦卑的方式。因为辩论意味着对观点的正确与否保持开放态度,没有结论式地下判定,因此也是“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
然而波普尔和平的主张也并非完全出自严谨的理性论证,正如他所说的:“我的理性主义不是自足的,而是依赖于对理性态度的非理性信仰。”其实波普尔对暴力的憎恨和对和平理性的推崇与他自身经历和所处时代有很大关系。早年的波普尔也曾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但在目睹了青年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游行示威而惨遭血腥镇压后,波普尔开始厌恶用流血的暴力方式来诱发阶级革命,并逐渐转向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曾回忆:“与马克思主义相遇是我智力发展中的大事之一。它教给了我许多从未忘记的教训。他教会了我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不知道。’它使我成为一个可错论者,使我铭记智力上谦虚的价值。并且它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15)Karl Popper.Unended Quest: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2,pp.36-37.波普尔虽然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但他对社会主义抱有的偏见及“非理性信仰”使得他产生了这种折中式的渐进方法。
(二)试错法是另一种伟大的艺术
试错法是波普尔“猜想—反驳方法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表现,是渐进社会工程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波普尔指出:“政治学中的科学方法意味着那种确信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无视错误,掩饰错误,或把错误归罪于人的伟大艺术让位给另一种更伟大的艺术——为错误承担责任,力图从错误中学习并应用这一知识避免将来犯错误。”波普尔称试错法为一种伟大艺术,试错法在“P1→TT→EE→P2”的四段图式中属于反驳(EE)的环节,包含了批判、试验和排错三个实践进路。
试错法是一种批判的方法。波普尔认为:“批判可以说是在一个非遗传的(外体的)水平上继续自然选择的工作:它假定客观知识以表述的理论的形式存在。因此,只有通过语言,自觉的批判才成为可能。”(16)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在波普尔看来,批判就是通过语言以理服人。正如有学者所解释的:“批判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是‘批判性辩论’‘理性探讨方法’‘批判性反省’,是批判地选择更好的理论,淘汰被证伪的理论。”(17)文援朝、胡慧河:《波普尔试错法评述》,《求索》2002年第2期,第87-89页。在波普尔看来,批判的方法本质上就是一种去伪存真的证伪的方法,当一个理论被证伪时,就应该彻底放弃它。
试验是试错法必不可少的一环。波普尔说:“一切理论都是尝试,都是试验性的假说,它们是否成立都要经过检验;而一切实验的确认则不过是以批判精神进行试验的结果,为努力发现我们理论的错误而进行试验的结果。”在波普尔看来,社会发展不存在规律,要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试验是必不可少的。整体主义或许也有其社会试验的理论,但整体主义在试验前就已预先认定了一个观点或结果,试验只是来验证其观点的一种“结果未知的行为”,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总之,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认识某些真理。
试错法的本质是排错法。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方法不同的是,证伪主义在“猜想—反驳”的过程中寻找真理:“理论总是试探地提出,再受到检验。检验的结果如果表明理论错了,则排除这个理论;试错法本质上就是排错法。”(18)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47页。排错是“猜想—反驳”方法论四段图式的重要一环,也是渐进社会工程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关键一步。渐进社会工程通常找寻和克服最严重和最迫切的社会弊病,“采取有步骤的措施来反对某些错事,反对不公正或剥削等具体情况,反对可以避免的苦难(例如贫困和失业)”(19)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57、54页。。因此,波普尔认为渐进社会工程不寻求某种终极的善,而是通过多元和充分的猜想与排错推动社会的进步。
(三)渐进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妥协
与整体主义社会工程不同,渐进社会工程秉持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采用批判的、审慎的和零星的技术手段推动社会改良。波普尔指出:“我的方法与历史决定论者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其标志与其说在于它是一种技术不如说它是一种渐进的技术。仅就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技术而论,它的方法不是渐进的而是‘整体主义’的。”(20)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57、54页。波普尔将渐进社会工程视为“一种渐进的技术”,主张通过审慎的方式逐渐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
渐进的方法要求合理控制意外。在波普尔看来,渐进社会工程与整体主义社会工程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意外事故的估计和防备。渐进工程师之所以反对整体主义的方法,是因为“整体主义的变革越大,他们的未意料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从而迫使整体主义工程师不得不采取渐进改进的权宜措施”(21)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57、54页。,并且这种权宜措施会不断迫使乌托邦工程师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最终“导致众所周知的无计划的计划”。而渐进社会工程不设定整体的计划,只在某一系统或领域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在出现未意料之事时,渐进的方式可以有效控制毁坏的危害。
渐进的方法要求逐步进行局部的改良。波普尔认为不存在整体上重建社会的可靠知识体系,“社会生活如此复杂,以致很少有人或者根本无人能够在总体的规模上评价某项社会工程的蓝图;评判它是否可行;它是否带来真正的改善;它可能引起何种苦难;以及什么是保证其实现的手段”(22)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波普尔指出,整体主义要求为全社会制定蓝图,然而实际上人类无法把握全局,以整个社会做实验最终将带来一场极大的灾难。唯一科学可行的方法就是采取理性方式改进社会:“通过零星的(piecemeal,另译:渐进的)方法,我们可以克服所有合乎情理的政治改革遇到的及其重大的现实困难。”总之,在波普尔看来,渐进的方法是“一种达成合乎情理的妥协”,是一种通过“民主的方法”实现渐进改良的理性方式。
三、渐进社会工程理论的贫困
卡尔·波普尔通过对以往社会工程理论的批判,形成了极具批判精神和开放性质的渐进社会工程理论,对于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而言,渐进社会工程对当代社会提出的一系列改进方案确能提供一些启示,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渐进社会工程理论在哲学基础、实现路径和价值旨归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
(一)历史非决定论:波普尔社会工程理论的哲学贫困
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是在全面批判马克思历史观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观,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或“经济的历史决定论”,只需要找出一个不符合历史规律的历史事件,便可以证伪历史规律的存在。波普尔先验性的历史观,实际上是证伪主义原则在历史哲学领域运用的结果。因此,要验证波普尔的观点是否科学,必须对证伪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一个重新的审视。
一方面,必须看到证伪主义方法的局限性。波普尔曾在他的自传中不无得意地指出:“现在大家都知道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名存实亡了,但似乎没有人怀疑这样一个问题——‘谁负责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谁做的?’我恐怕必须承认责任。”(23)Karl Popper.Unended Quest: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2,p.99.波普尔宣告自己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他的具体方法就是用一个单称命题证伪全称命题。然而,这种对全称命题的“猜想—反驳”式的证伪必须建立在单称命题的证实基础之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单个事例是由单称命题陈述的,对单称命题的严格检验要求它所陈述的事例既能被证实,也能被证伪。”(24)赵敦华:《赵敦华讲波普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换言之,对全称命题的证伪必须建立在对单称命题的证实基础之上。因此,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并没有扼杀逻辑实证主义,而只是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补充和发展。至于证伪主义在社会工程中的核心方法——试错法,虽然为解决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和平、渐进、可控制的方式,但需要指明的是,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积累到无法调和时,局部的、渐进的技术改良便无济于事,“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并非经济决定论。波普尔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作为“历史决定论”或“经济的历史决定论”,其目的就是要借助单一历史事件来证伪马克思所称的“历史规律”:“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26)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卷首。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是简单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的历史决定论,恩格斯曾用“历史合力论”阐释了唯物史观:“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哈贝马斯也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以实践的意图拟定的社会理论”(28)尤尔根·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是基于客观现实情况的社会理论。柯亨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辩护:“但生产力的变化比生产关系的变化更根本,生产关系的改变是因为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进步。”(29)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76页。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并非经济决定论,它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
(二)技术改良:波普尔社会工程理论的方法贫困
波普尔对马克思暴力革命论的批评主要表现在:第一,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理由是“似乎很难设想一个完全联合的和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30)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波普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工人的福利和保障不断得到加强,因此工人阶级不是在联合而是在不断分化。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生产和竞争的无节制扩大,只是预示着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而不必然导致暴力革命。综合以上两点,波普尔认为暴力革命说已不合时宜,主张“宁可在用辩论说服另一个人上遭到失败,也不愿用势力、威胁和恫吓甚或花言巧语的宣传来成功地压服他”(31)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07页。,即采用一种和平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但和平理性的技术改良需要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否则就会沦为无意义的空想。
一方面,波普尔的和平改良方式缺乏社会平等的基础。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衰弱、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完善,波普尔所主张的局部的、渐进的和平改良方式,似乎为战后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更为切实可行的社会改造方法。但波普尔所主张的和平辩论和渐进试错,是以某种程度的理智和谦卑为前提的。社会中的人,不是相互孤立的原子,当个人走向群体后往往容易产生一种“群体无意识”,就如庞勒所描述的,“意识人格消失了,无意识支配人格,暗示的传染性将思想情感引向同一方向,有立刻落实指令的倾向——这些就是群体中的个体的主要特点”。(32)古斯塔夫·庞勒:《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马晓佳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一旦丧失了理性的基础,和平辩论就成了各说各话和无济于事的空谈。此外,和平辩论还必须建立在双方共同意愿的基础之上。现行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当社会改革触及资产阶级利益时,无产阶级的改革方案便会受到法律、政策和制度等国家机器的镇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因此,在暴力手段缺位的情况下,和平改良的路径表现出了极大的空想性,这种空想性恰恰使渐进社会工程成为波普尔所批评的“乌托邦主义”。
另一方面,暴力革命在阶级社会中不可避免。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有文字记载的整个人类历史,发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6页。,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逐渐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通过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并通过资本集中,不断加深对工人的剥削和奴役。伴随着资本的垄断,生产逐渐萎缩,社会矛盾逐渐尖锐,最终“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因此,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才会立场鲜明地强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当然,在马克思语境中,暴力革命并非是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马克思保留了一些国家存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仍然认为暴力手段作为一种最有力的保障手段不能被无产阶级放弃。总之,波普尔的资本主义改良方案难以取代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在暴力手段的缺位情况下,渐进社会工程必将造成方法上的贫困。
(三)抽象的个人本位:波普尔社会工程理论的价值贫困
波普尔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抨击整体主义社会工程,是因为他认为整体主义工程师借群体幸福之名行个人集权之实。对整体论的批判显示了渐进社会工程理论的个人主义立场,尽管波普尔也在尝试合理解决个人与国家间的张力从而实现社会化公平,但他所理解的个人是抽象的个人,其理论所指向的“最小痛苦原则”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波普尔的渐进社会工程理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实在论。波普尔认为,与整体主义社会工程所追求的虚无缥缈的全体人的共同幸福相比,“祛除不平等”与“祛除苦难”显得更为科学与紧迫。因此,渐进社会工程理论主张通过不断地消解不平等与苦难来实现“每代人的平等”和每个人的“最小痛苦”目标。渐进社会工程的这一价值追求,反映了其实际上是建立在个人本位上的消极功利主义,旨在实现从“最大幸福”向“最小痛苦”的目标转换。但是,要实现“最小痛苦”原则,必须解决以下四个问题:“谁的痛苦最小化?什么样的痛苦最小化?是否能够最小化?如何做到最小化?”(37)杨和英:《析波普尔政治哲学之困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第一,“谁”的痛苦最小化?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往往出现利益冲突,当渐进社会工程师“祛除疾苦”时,他必须要选择是“牺牲一部分人以满足其他大多数人的快乐”,还是“牺牲大部分人以满足一部分人的快乐”,而这些都是渐进社会工程师对社会的干预,都会陷入他所批评的“极权主义”立场。第二,什么样的“痛苦”最小化?波普尔批评传统功利主义在原则上假定了一种衡量幸福的“幸福—痛苦”标度,认为“幸福”不能被衡量和界定。但人们对痛苦的界定同样是不确定的,因而无法判断使什么样的“痛苦”最小化。第三,何为“最小”?迪维尔热指出:“因为只有在物理学中可以进行精确的测量;而在其他情况下,测量往往含糊不清。”(38)莫里斯·迪维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王大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如果无法衡量“最小”,那么“最小痛苦原则”也就是一个伪命题。第四,如何做到“最小痛苦”?波普尔的方法是通过政府的有限干预和社会道德的要求践行,然而他并未对“有限”的程度做出说明,而道德要求只是一种弱作用,同样无法使“最小痛苦原则”落实下去。综上可知,波普尔追求的平等与幸福是抽象的人的平等与幸福,“最小痛苦原则”是对“开放社会”的幻想,缺乏理性论证,难以在现实社会中践行,更难以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途径。
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个人与群体相统一,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反对将人看作是一种“实体”“类”或者“观念”的存在,认为现实的人是在生产中实现的,而现实实践的人必然走向联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摆脱对人和物的依赖、走向真正的个性解放的人的存在的运动。这里的“人”,不是波普尔和其他个人主义者理解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一种与社会双向互动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的“自由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从现实的、实践的人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工程的价值追求,导致他成为一个方法论上的唯名论者和价值论上的自由主义者。总之,“马克思考察主体问题的一个关键之点就是主张从活动结果的角度看待主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实的主体当然必须是受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制约着的”(40)刘森林:《追寻主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工程或者说共产主义运动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目标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