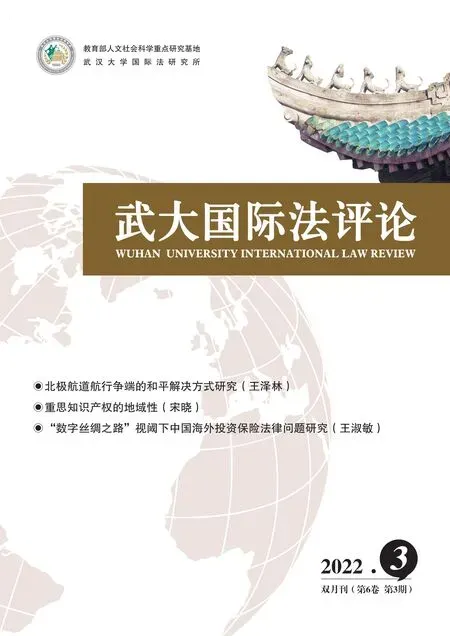重思知识产权的地域性
宋晓
一、为何应重思知识产权的地域性
地域性是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涉外知识产权法律适用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逻辑起点。关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在我国现有研究成果中,徐祥博士作出了迄今最为深刻的论述,这集中体现于他的两篇论文:《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论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①参见徐祥:《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601-606页;徐祥:《论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第37-43页。在此之前,我国知识产权学界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理已有初步阐述,但因缺乏国际私法的维度,其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足。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以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从根源上消除了该领域的国际私法问题,导致该领域并不存在法律冲突,一国法院不太可能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因而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理及可能存在的国际私法问题并无深入探讨。①例如,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权威国际私法教材就否定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存在:“尽管各国的立法互不相同,但由于这类立法是以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权利独立原则为基础制定的,如果各国不签订条约,彼此承认和保护依对方国家法律所获得的知识产权,那么,在严格地域性限制的条件下,就不可能产生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2页。知识产权的国际私法问题在欧美国家也长期被忽视,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得到真正重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理由此得以被重新审视。②See Graeme B.Dinwoodie,Developing a Privat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The Demise of Territoriality,51 William&Mary Law Review 711,713(2009).
正是在西方学界兴起对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研究的最初一波浪潮中,徐祥博士作为一名国际私法学者,在国内几乎最早捕捉到了这一新动态,并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彼时西方学界因起步不久,这一领域仍充斥种种陈旧顽固的观念,加上问题本身复杂缠绕,所以常令研究者望而却步。何况我国国际私法研究恢复不久,知识产权领域无国际私法问题的陈旧观念,更是主宰着学界,徐祥能够跨出重要一步,实属不易。时至今日,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为何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法律冲突?涉外知识产权争议为何在一定情形下还应适用外国法?如何在知识产权地域性基础上构建双边冲突规范?这一系列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的根本问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
知识产权虽以地域性为基本特征,但自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诞生以来,知识产权几乎与生俱来具有国际化的需求和动力,因为文学、艺术的跨境传播是其自然本能,附载知识产权的商品也在不断开拓全球市场。知识产权地域性与其国际化、全球化之间自始就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为回应这种紧张关系,西方从19世纪末以来,就致力于以统一的国际立法方式,确立国民待遇原则,树立统一的最低保护标准,以促进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国际统一法方式最初是以独立的知识产权条约的面目出现的,③早期最重要的两项公约: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称《巴黎公约》)和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称《伯尔尼公约》)。可自从WTO成立以来,便更多寄寓在国际贸易法框架中,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又或诸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RCEP)等区域性贸易条约中。国际统一法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贡献无论如何高度评价都不为过,但是,国际统一法所贡献的知识产权的实体法规则仍然非常有限,涉外知识产权个案的权利保护仍主要依赖各国国内法。令人遗憾的是,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在西方长期落后于国际统一法的发展,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有显著改观。
以徐祥博士的两篇论文发表为界,在此之前,论及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时,我国学界也主要关注和重视国际统一法,而鲜少去探究知识产权的国际私法。那时尚无对知识产权地域性问题的深刻认识,也缺乏对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本质追问,知识产权国际私法问题因此难以真正浮出水面。徐祥博士的两篇论文,正是以国际私法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深层次阐述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真正含义,并将西方开始重视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研究的前沿信息传递到了中国。
徐祥博士两篇论文发表后的近20年中,西方国家快速推进了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的立法和示范法编纂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推2008年欧盟《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以下称《罗马条例II》)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法律选择规则之立法,以及为回应知识产权全球化问题的几部代表性示范法,包括2008年美国法学会推出的《调整知识产权跨国争议的管辖权、法律选择及判决原则》(Intellectual Property Principles Governing Jurisdiction,Choice of Law,and Judgments in Transnational Disputes,以下称ALI原则)、2011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小组完成的《知识产权冲突法原则》(Principles on Conflict of Law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CLIP)、韩国和日本国际私法协会成员起草的2010年《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原则联合提案》(Joint Proposal on the Principl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及2020年国际法协会知识产权国际法委员会在日本京都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知识产权与国际私法的指南》(Guideline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以下称《京都指南》)。另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开始重视国际私法问题,联合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2019年推出了《当国际私法遇到知识产权法——法官指南》,①See Annabelle Bennett&Sam Granata,Whe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Mee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A Guide for Judges(WIPO and the HCCH 2019).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上述代表性立法、示范法和指南在短短20年中连番问世,既反映了国际社会希望以国际私法方式来回应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全球化问题的迫切愿望,也同时表明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的研究获得了极大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准备过程中,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起草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建议稿》(以下称《学者建议稿》)。《学者建议稿》为了彰显知识产权国际私法问题的重要性,以专章形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徐祥博士即为《学者建议稿》知识产权国际私法规则的核心起草成员。②参见黄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建议稿及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其中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规则规定在第六章“知识产权”第50、51条,另外,知识产权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定在第58条,知识产权侵权规定在第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采纳了《学者建议稿》关于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主要规则,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三个核心问题,即知识产权的内容和归属、转让和许可合同以及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规定在第七章第48~50条之中,体系完备程度一跃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单行立法。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七章规定,知识产权及其侵权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这是各国普遍认可的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尽管我国有了相对完备的立法,但司法实务界至今对被请求保护地法这一系属仍然较为陌生,而且产生种种法律解释上的误区,其根源还是在于没有深入掌握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基本原理,没有深入理解地域性和以被请求保护地法为系属的双边冲突规范之间的关系。实践中经常将被请求保护地法简单认作法院地法或侵权行为地法,其实际效果就是最后都适用了法院地法,而几乎无适用外国法之实例,等于否定了依据外国法来保护外国知识产权之可能,这就违背了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扩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立法初衷,第七章的立法价值因此几乎丧失殆尽。
学界也并没有因第七章之立法告成,而廓清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概念迷雾。在过去十年中,有数篇专门论述知识产权地域性的论文,其中有继续像徐祥博士的论文那样综论知识产权地域性的,也有专门论述知识产权其中一个分支诸如专利地域性和商标地域性的。①其中,代表性论文主要有阮开欣:《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域外效力》,《河北法学》2018年第3期,第81-97页;徐升权:《专利权地域性之省思》,《知识产权》2014年第9期,第11-17页;黄汇:《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的理解立场及适用逻辑》,《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80-96页。可认真检视这些论文后可以发现,徐祥博士在其论文中早已澄清的若干理论误区,却仍然再三出现;徐祥博士已经为某些问题指明了路径的,只要沿此指示就不至于迷失前行方向的,可它们最终还是误入了歧途。从这些新作的注释文献中可知,它们都漏引了徐祥博士的论文。或许是因为徐祥博士的论文过于理论和抽象,也或许是无法对发表之后的最新发展,诸如《罗马条例II》、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七章之立法以及广有影响的诸示范法,作出具体有效的回应,才导致这些新作忽略了其学术价值。但在研究知识产权地域性问题时,漏引国内已发表的具有开创性价值的文献,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综合而论,新近论文主要在以下问题上仍然云遮雾绕:第一,知识产权是否和一般私法一样具有地域性,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一般私法的域内域外效力有何关联?第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是否等同于公法的属地性,一国知识产权法是否可以域外适用?如可域外适用,是否等同于公法的域外适用?第三,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是否削弱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应该更多依赖于国际统一法还是各国国际私法?第四,知识产权的地域性限制了双边冲突规范的发展吗?被请求保护地法的认定和知识产权地域性有何关联?针对上述理论难题,本文将在徐祥博士论文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新作中的种种误解,重作反思和探讨。
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一般私法的属地性
知识产权是知识产权法赋予的,因而知识产权法的地域性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在一般情况下可视为同义词。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浅层认知,我国学界并没有多少分歧。知识产权地域性是指一国法律赋予的知识产权的空间效力范围只及于该国领土范围。对此,徐祥博士概括为:“各国依法授予或确认的知识产权的空间效力范围限于本国内,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地域性。”①徐祥:《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602页。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直接带来的法律后果是,对于同一知识产品,例如同一文学作品,或同一发明,得到一国赋权后,若希望同时得到外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则需要外国知识产权法重新赋权,而且各国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内容和保护方式不尽相同,各自平行展开。这就是知识产权的独立保护原则。
知识产权为何具有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历史发展看,知识产权起源于封建特许权形式,而封建特许权自然具有严格的地域属性。②参见徐祥:《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602页。但是,封建特许权早成了历史遗迹,知识产权早就属于各国普遍承认的民事权利范畴,这就不能从历史起源来解释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了。既然知识产权是其中一种民事权利,就需要从一般民事权利或一般私法的角度出发,来认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如果一般私法具有地域性,那么知识产权无非承其特性而已,也相应具有地域性;但如果一般私法不具有地域性,或两者的地域性内涵具有本质差别,那就需要深入考察其背后成因了。
(一)法律的属地性问题
当论及法律的空间效力范围时,我们常用法律的属地性概念。法律的属地性是指一国颁布的法律只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而在外国无效。这里所指的法律包括主权国家颁布的所有法律,包括公法性质的法律和私法性质的法律。在民族国家形成和主权观念涌现的历史阶段,国家主权从观念上和现实上极大强化了法律的属地性,法律的属地性被认为是国家主权的自然产物。荷兰法学家胡伯在其“胡伯三原则”的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中,阐明了强化版的国家主权原则和法律属地性:“每个国家的法律只在其境内有效,约束境内所有臣民;所有居住于境内的人,无论永久居住或临时居住,都视为其臣民。”③胡伯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参见Ernest G.Lorenzen,Huber’s de Conflictu Legum,13 Ill.L.R.375,403(1918-1919)。仅根据这两个原则,所有法律都是绝对属地主义的,只适用于本国境内,而不可能适用于境外。反之,任何国家在境内都不可能适用外国法。胡伯为了缓和绝对属地主义,在前两个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重要的第三原则:“主权国家出于礼让,可以保护外国法赋予的既得权,只要不减损本国的主权权力和本国臣民的利益。”④胡伯第三原则,参见Ernest G.Lorenzen,Huber’s de Conflictu Legum,13 Ill.L.R.375,403(1918-1919)。
以胡伯为代表的荷兰学派最强调法律的属地性,但也同时承认法律的属地性不是绝对的,一国在必要时应该保护外国法律赋予私人的既得权,事实上仍然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应该适用外国法。据此,任何国内法都具有属地性质,但通常不是绝对的。真正的难题在于:我们何时应坚持法律的属地性,何时应缓和法律的属地性?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国际私法正是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的部门法。从国际私法发展至今的结果来看,一般私法的属地性已经大为缓和了,甚至问题本身得以消解,所有涉外私法的法律关系都有可能适用外国法。
那么,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一般法律的属地性究竟是何种关系?知识产权法作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当然也具有属地性,但如果地域性等同于一般法律的属地性,似乎就没有必要另行强调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了,可见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必然不同于一般法律的属地性。我国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是特殊的属地性,较之一般私法来说,具有更为严格的属地性;地域性通常只指向知识产权法,而不指向其他私法,地域性是一种狭义的属地性。①参见阮开欣:《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域外效力》,《河北法学》2018年第3期,第84页。但这仍然没有回答为何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不同于一般私法的属地性。如果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较之一般私法的属地性更为严格,其严格程度又是如何表现呢?
(二)知识产权地域性与有形财产权地域性之差异
我国权威知识产权法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地域性特征,源于知识产权不同于一般有形财产权:对有形财产的保护原则上没有地域性限制,当有形财产从一国移至另一国境内,所有权并不会失去其法律效力;而知识产权则不同,依据一国法律获得承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境内有效,除非条约有相反规定,他国没有义务保护该知识产权,任何人均可在他国自由使用该知识产权,既无须权利人同意,也无须向权利人支付报酬。②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1页。
我国还有其他学者,同样从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区分角度来论证知识产权为何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在甲国取得的动产进入乙国后,只要仍对其进行有效占有,乙国就可依本国占有制度,推定其为合法所有人并加以保护。相比之下,知识产权因其无形性,权利人根本无法进行实质上的占有,因而也根本谈不上因占有而进行的权利推定。”③刘家瑞、史威:《知识产权地域性冲突法评述》,《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第9页。
在甲国取得的有形动产进入乙国后,如果没有新的法律事实导致物权变动的,则物权维持不变,这是各国国际私法普遍承认的涉外动产法律适用规则。④See Lawrence Collins(with Specialist Editors),Dicey,Morris and Collin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336-1340(Sweet&Maxwell 2013).但是,其背后原理并非基于占有的权利推定。当在甲国取得的动产进入乙国后,只要根据乙国法不发生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如买卖、赠与或抵押等,不管动产由原所有人占有,还是由其他人占有,都不会发生物权的变动。如果根据乙国的物权法,发生了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则物权发生变动,即使物权发生变动时仍由原所有人占有。总之,动产从甲国移动到乙国,在乙国是否发生物权变动,取决于根据乙国法是否发生了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因此,认为有形动产可维系于占有,而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财产无法维系于占有,以此来证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理是不能成立的。
有形财产从甲国进入乙国,只要不发生物权变动的事实,物权就可以在乙国得以延续,那为何作为无形财产权的知识产权却无法在乙国延续呢?是否就是基于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区分呢?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无形财产权不仅包括知识产权,还包括其他多种类型,例如股权、债权等。依据甲国法在甲国获得了甲国注册公司的股权,如在其他国家发生相关股权争议,其他国家的法院通常会适用公司注册登记地法即甲国法,保护依据甲国法获得的股权。①例如,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即作出了类似规定。同样,当在甲国依据甲国法获得一项债权后,其他国家也很有可能保护该项债权。因此,有形财产权可在外国获得保护,无形财产权同样可在外国获得保护。从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区分上,并不能证明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发生机理。
有形财产权和无形财产权都可以延续到外国,并得到外国法的保护,我国有学者据此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专利的地域性:“物权法等领域并不强调权利的地域性,那么专利权领域为何却要僵硬地为地域性辩护呢?”②徐升权:《专利权地域性之省思》,《知识产权》2014年第9期,第14页。依此观点,专利权和其他有形动产物权或无形财产权并无本质区别,专利权的地域性也就失去了逻辑基础。继续推导下去,所有知识产权的地域性都将缺乏逻辑基础。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其他有形财产权或无形财产权都可以在不同国家继续延续并获得保护,但知识产权则不能。对于同一知识产品,在甲国登记注册获得甲国的知识产权后,如果希望在乙国境内获得保护,就需要在乙国重新注册登记,两个国家对同一知识产品的保护是独立进行和平行展开的。因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是一种独特的“事实存在”。当我们不能从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区分上去证明它时,就需要探索其他理由。
我国有学者从另外角度提出,知识产权之所以比一般私法具有更严格的地域性特征,本质原因在于“知识产权是法定权利,同时也是一国公共政策的产物”。③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诚然,知识产权含有鲜明的公共政策色彩,国家一方面需要促进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传播、鼓励发明创造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另一方面需要保护权利人的专有权利,知识产权法需要同时平衡上述政策目标。相较于一般私法来说,知识产权法确实具有更强的政策导向。但是,刑法和众多经济管制法等公法,其公共政策导向更强,是否就具有和知识产权法相同的地域性特征呢?对此,我国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论证知识产权地域性原理的学者,几乎都没有给出有力的阐释。相反,他们往往又会从公共政策的立论上后撤:“公共政策导向的权利正当性并不否定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本质,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程度和私权属性存在密切联系”。①阮开欣:《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域外效力》,《河北法学》2018年第3期,第88页。钟摆又摆回到了私法一端。但是,私法中的大量规则也同样具有公共政策因素,例如不动产法,那为何不动产法没有知识产权法的地域性特征呢?这又回到了问题起点:知识产权法在地域性特征上为何有别于一般私法?
(三)一般私法属地性问题之消解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新考察私法属地性的发展。在国际私法诞生初期,法则区别说认为,物法只具有域内效力,而人法才具有域外效力。这是从法律的性质和内容出发,来认定私法的域内效力或域外效力。②参见[法]亨利·巴蒂福尔、保罗·拉加德:《国际私法总论》,陈洪武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06-307页。至少可以说,具有域外效力的人法已经突破了法律的属地性。荷兰学派从主权原则的高度,重新强调了所有法律的属地性质。从国际私法的发展角度看,将严格的属地性强加于所有法律,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现代国际私法奠基者萨维尼正确地指出,从主权原则高度强调法律的属地性固然正确,但不能解决问题本身——在涉外案件中如何进行法律适用,何时适用法院地法,何时适用外国法呢?③参见[德]萨维尼:《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李双元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萨维尼抛弃了法则区别说的单边主义法律适用传统,另辟蹊径,发展出了多边主义的法律选择方法,将所有国家的私法置于平等的可相互置换的地位。依据萨维尼理论,当涉外法律关系的本座位于甲国,即案件与甲国有最密切、最本质的联系,则适用甲国法;反之,则适用乙国法。甲国法和乙国法事实上处于平等的可置换的地位,相互之间都具有域外效力,只要案件与另一国有更密切联系,原则上就应适用另一国法律。④参见[德]萨维尼:《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李双元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49页。萨维尼从法律关系的性质出发,发展了多边主义的法律选择方法,事实上是绕开了法律的属地性问题,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消解了这个问题本身。在萨维尼框架中,谈论法律的属地性,乃至于讨论法律的域内域外效力,已经失去了意义。
如果定要从属地性角度考察萨维尼的方法论,则在萨维尼国际私法体系中,任何国家的私法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被外国法院所适用,因而任何国家的私法都具有了域外效力,私法的属地性事实上不复存在。但是,这一结论只适用于涉外法律适用领域。在纯国内案件中,法院当然只适用本国的法律,而不可能适用外国法律,因而法律在纯国内案件中仍然保留了其属地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称“我国《民法典》”)第12条之规定承袭了我国《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的原有规定,狭隘地宣告了私法的属地性原理。①我国《民法典》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殊不知《民法典》既可能适用于纯国内案件,也可能被我国法官适用于涉外案件,还可能被外国法院的外国法官所适用。在后两种情形下,事实上都不存在民法典的属地性问题。在今日全球化时代,我国《民法典》无视涉外案件与纯国内案件平行存在的现实,而一味固守私法的属地性,为此受到了我国国际私法学界的猛烈批评。②参见许庆坤:《我国民法地域效力立法之检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条第1款为中心》,《法商研究》2015年第5期等。
知识产权法为何没有跟上一般私法的步伐,在涉外案件中突破法律的属地性呢?从本质上说,各国知识产权法不同于一般私法,彼此并不是平等的、可置换适用的。在一个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即使被告和侵权事实都发生在甲国,案件和甲国具有最密切的联系,也并不一定适用甲国法,因为甲国可能并不承认该知识产权。只有适用承认该知识产权的国家的法律,知识产权才可能获得保护。从形成原因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是被各国知识产权法明示或默示加以规定的,各国知识产权法对同一权利客体独立提供保护,这从根本上否定了相互置换适用的可能。
在一般私法领域,权利客体上只存在一个权利,比如一个物权、一个监护权、一个合同权利,其权利将依据国际私法规则,在某个特定的国内法体系中最终予以确定。但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于同一个权利客体或知识产品,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或法域,在其上就可以存在多少个平行展开的知识产权。这是知识产权法和一般私法的本质不同之处,因而一般私法在涉外案件中已经消解了法律的属地性问题,而知识产权法仍在强调地域性原理。徐祥博士已经在其论文中深刻指出:“知识产权不同于物权,后者奉行一物一权原则,承认外国物权法的域外效力,必定限制本国物权法的域内效力。而前者,同一知识产品上依法存在多个知识产权,承认外国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不要求限制本国知识产权法的域内效力。”③徐祥:《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604页。如果深刻理解了这段论述,我国现今关于知识产权和一般私法的地域性异同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认知,就可以涤除了。
三、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公法的属地性
从国家主权概念的逻辑出发,一国制定的任何法律,包括公法和私法,都具有属地性,法律的效力边界等同于领土边界。但是,在涉外民商事领域,依据多边主义的国际私法体系,不同国家的一般私法处于平等的、可相互置换的地位,一国私法随时可能被外国法院适用,此时也就突破了法律的属地性,而具有了域外效力。各国一般私法通常放弃了法律的属地性规定,其域内域外效力问题完全托付给国际私法另行集中规定。因此,私法的属地性问题一般只限定在纯国内案件中才有意义,而在涉外案件中,私法的属地性问题就被多边主义的国际私法给消解了。私法所赋予私人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自由处分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私人权利在全球形成并在全球流动。国际私法为赋予全球形成和全球流动的私人权利以安全和秩序,于是拆除了私法的属地性藩篱。
(一)公法的属地性及其域外适用
一国制定的公法,典型如刑法和行政法,其属地性特征并未弱化,更不存在被消解的可能。公法的属地性特征表明,公法的效力边界及于一国领土范围。一国法院或行政机关一般是不会去适用外国公法的,而本国制定的公法也不会期待被外国执法机构或法院所适用,这就是各国普遍承认的“公法禁忌”原则。①See William S.Dodge,Breaking the Public Law Taboo,43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61(2002).一国公法集中表达了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各种公共政策,动辄与他国公法表达的同类政策和利益相互抵触,适用外国公法就意味着损害本国主权权利和公共利益。即使两国公法各自所表达的政策和利益相互兼容,各自也是独立表达和独立适用。因此,各国公法彼此不可能相互平等并可置换适用。今日全球化时代,各国公法仍固守属地性之藩篱,只能通过条约方式去实现有限突破和推进国际合作,诸如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国际贸易管制合作以及其他各类行政执法合作。
公法的效力只及于领土范围,公法赋予的权力或权利亦不能延续至他国领土,这和知识产权的效力只及于领土范围,并且不能延续至他国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公法的属地性非常类似。知识产权法较之一般私法具有更强的公共政策属性,是国家保护创新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有力工具,因而其地域性特征区别于一般私法,而趋近了公法的属地性特征。
今日各国人员和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由流通,跨国法律事务层出不穷,但基于公法属地性原理,各国公法管制只限于本国领土范围,因而无法有效应对跨国公法事务时常需要统一管制。国际公法虽能实现统一管制,但制度供给远为不足,因而在各国属地管制和全球统一管制之间,还存在大量的法律真空地带。为了防范这一法律真空地带可能带来的混乱状态,也为了防止由此可能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害,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国内公法的域外适用或域外管辖制度。②参见宋晓:《域外管辖的体系构造: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之界分》,《法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190页。例如,各国常常依据积极属人管辖原则、消极属人管辖原则、保护性管辖原则,甚至是普遍管辖原则,将本国刑法适用于境外的犯罪行为;又如,各国常常依据效果原则,将本国反垄断法适用于境外的反垄断行为等。①参见2018年美国《第四次对外关系法重述》[Restatement(Fourth)of Foreign Relations Law]第402节。从理论上说,从刑法到各类经济管制法,所有公法都可能进行域外适用或域外管辖。因公法种类繁多,管制目标和方法各不相同,公法的域外适用零散而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方法,更不可能像私法那样形成一个涉外法律适用的部门法体系,即国际私法体系。这就更加给人以公法的域外适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感觉。
知识产权法在这一点上,非常类似于公法。知识产权法具有严格的地域性特征,亦被严格限定在本国领土范围内,但文学艺术作品渴望全球传播,专利产品和注册商标产品或服务亦希望驰骋全球市场。如果说地域性几乎是知识产权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而知识产权事务的国际性也同样几乎是其与生俱来的现实需求。为回应知识产权的国际事务的迫切需求,国际社会在过去一百多年中不懈努力,制定了一系列统一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这对于推进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贡献巨大。但是,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所形成的统一实体法还非常有限,知识产权的种类、内容和保护方法,主要还是各个国家国内法的事情,知识产权保护还主要由各国国内法担负起主要任务。因此,知识产权领域和公法领域一样,同样面临国际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因而为回应知识产权的国际事务的需要,各国也在不同程度地扩大本国知识产权法的域外适用。
(二)知识产权法的域外适用
从广义上说,当法律关系中的人、行为或财产中的一个因素或多个因素位于境外时,本国法律适用于该法律关系时,便构成了域外适用。就知识产权法而论,域外适用可能基于行为本身,也可能基于行为的效果。当一个侵权行为实际上是由境外行为和境内行为共同构成时,本国知识产权法基于境内那部分行为实施的立法管辖权,其法律适用的效果其实也及于境外那部分行为。这事实上是将整个跨国行为“本地化”于境内,而在本国法律看来,这甚至就是一种单纯的域内适用,而未必承认是域外适用。但是,如果此时行为人的国籍或经常居所位于境外,无论如何应被视为是一种域外适用。当本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是基于效果时,即行为发生在境外,而行为的实施效果发生在境内,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域外适用。知识产权法的三大分支,都存在域外适用的情形。相对而言,著作权法和专利法,更偏重于考察行为本身;而商标法,则更偏重于考量行为的效果而非行为本身。
在跨国著作权争议中,某些典型行为具有跨国性质,这就引发了本国著作权法是否适用于该行为的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法院曾经认为,违反著作权法的电视节目转播,侵权行为地被认定为卫星信号的接收地,而非卫星信号的发送地。但是数年之后,就有美国法院扩大了行为地的概念范围。在全美足球联盟案中,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认为,侵犯著作权的电视节目转播行为,发生在“被保护作品通向观众的任何一个步骤”。据此,通过卫星信号的电视节目转播行为,既发生在卫星信号的接收地,也发生在卫星信号的发送地,从而美国著作权法就可适用于境外的信号发送行为。①See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v.Primetime 24 Joint Venture,211F.3d 10(2d Cir.2000).同样,美国法院认定在线著作权侵权的侵权行为地,既包括在线作品被下载和阅读的本国境内,也包括上传在线作品的境外服务器所在地,于是美国著作权法也同样适用于境外上传行为。②See Graeme B.Dinwoodie,Developing a Privat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The Demise of Territoriality,51 William&Mary Law Review 711,727(2009).通过这种扩张解释方法,本国著作权法中所规定的诸如复制、转播等行为,均可包括一连串完成行为的境外行为部分。
在专利法中,以美国为代表,对专利实施行为的认定,已呈现出地域扩张的趋势。在2005年著名的NTP公司案中,原告作为专利受让人,起诉加拿大公司侵犯了其无线电子邮件技术专利。被告辩称侵权行为并不是发生在美国,而是发生在加拿大,但加拿大并没有授权此项专利。在此案中,被控侵权的专利是专利系统,被告发送设备位于加拿大而非美国。尽管加拿大政府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认为基于地域性原理,被告行为不构成侵权,但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仍然认为:被告行为虽然不是全部发生在美国,但系统最后在美国使用,消费者在美国,信息交换和经济收益均发生在美国,所以被告行为构成了专利侵权。③See NTP Inc.v.Research in Motion Ltd,,418 F.3d 1282(Fed.Cir.2005).
美国专利法的域外适用,不仅发生于未经许可制造、销售专利产品或使用专利方法的专利直接侵权案件,还发生于专利间接侵权案件,对侵权行为的解释也扩张到了境外的行为。专利间接侵权的主要形态,是通过向他人提供专用于制造专利产品的零部件而帮助或引诱他人实施直接侵权行为。④参见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83页。据此,如果外国出口商向美国出口构成美国专利产品的零部件的行为,就可能承担美国专利法中的间接侵权责任。⑤美国专利法对间接侵权作出了特别规定,参见35 U.S.C.§271(c).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1条借鉴了美国专利法,也对间接专利侵权作出了规定。我国有学者主张,应效仿美国司法实践,将引诱侵权行为扩张解释为包括境外的引诱行为。⑥参见韩书立:《我国专利法的域外适用问题研究》,《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第160页。
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的侵权规制对象主要是行为,而商标法的侵权规制对象则是行为所引发的效果,即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的商标,将产生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的效果。当行为发生在外国,而效果发生在本国时,如本国适用本国商标法用以规制外国行为时,这便是将本国商标法域外适用于外国行为。无论如何,依据效果来规制外国行为,其背后更多体现的是域外管辖原理而非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理。美国是根据效果原则来实现商标法域外管辖的典型国家。例如,在1994年的先令药业公司(Sterling Drug)案中,美国原告在美国法院起诉德国被告商标侵权,但德国被告只在德国使用商标。德国政府提供了法庭之友意见,根据地域性原理主张德国被告不构成侵权。但联邦上诉法院最后认定,德国被告的行为虽发生于德国,却在美国境内产生了误导美国消费者和损害美国市场的实质效果,因而违反了美国商标法,应承担侵权责任。①See Sterling Drug Inc.v.Bayer AG,14 F 3d 733(2d Cir.1994).
商标法规制的重心在于效果而非行为,当一国可能依据效果原则扩大商标法的域外适用范围时,也应适当依据效果原则来反向限制对境内行为的不法认定。在过去许多年,围绕商标贴牌行为在我国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问题,司法实践多有分歧,理论更是有争议。②参见黄汇:《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的理解立场及适用逻辑》,《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91-92页。在商标贴牌加工案件中,我国境内的加工方只负责加工产品,并贴上委托方指定的商标,贴牌产品全部出口给境外委托人,由境外委托人自行在境外市场销售。那么,境外商标权人能否以境外市场的商标混淆为由,在我国法院要求加工方承担商标侵权责任?或者,境内相同商品的商标权人,能否在我国法院要求加工方承担商标侵权责任?在上述两种情形下,贴牌加工商品只在境外市场销售,而没有在我国境内市场销售,因而有可能在境外市场发生混淆,而不可能在我国市场发生混淆。也就是说,商标混淆的效果只可能发生在境外。根据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理,贴牌行为本身并没有违反我国的商标法。但是,我国法院可能依据知识产权侵权的冲突规范,适用外国法认定贴牌行为构成侵权。
在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中,依据行为标准实现法律的域外效力,本质是将境外行为和境内行为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行为来看待,当著作权法和专利法适用于本国境内的行为时,也同时适用于境外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行为。但在商标法中,依据效果进行法律的域外管辖时,行为全部发生在外国,本国境内产生的效果并不直接成为境外行为的一部分,因而依据效果标准的域外适用,其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突破要大于依据行为标准的域外适用,实践中也更容易引发不同国家的利益冲突。美国法院在适用效果标准时,也认识到应进行平衡和协调,应考察被告的国籍、与外国商标法的冲突程度,进行必要的自我克制。③See Graeme B.Dinwoodie,Developing a Privat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The Demise of Territoriality,51 William&Mary Law Review 711,784(2009).
从上述知识产权法的域外适用的分析可知,知识产权法如同公法,在承认地域性的大前提下,在特殊情况下都有可能进行域外适用。徐祥博士指出:“各国知识产权法原则上仅在本国内有效。但是,也存在一国知识产权自设域外效力的特殊情形。”④徐祥:《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603页。知识产权法和公法的域外效力,都是各国自设的。国际习惯法对域外效力存在哪些限制,目前还不是特别确定。当然,只有在经济、科技和金融各方面占有优势的强国,自设的法律的域外效力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对于弱小国家而言,当其想要实现法律的域外适用时,或因缺乏商业连结因素而难以行使司法管辖权,或因判决作出后败诉方在本国境内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因而即使本国法律自设了域外效力,最后也很可能只是一纸空文。
一国法律在突破地域性原理而进行域外管辖时,极易和外国法律或政策产生冲突。因此,各国对于域外立法管辖一般都会采取克制态度。在今天域外管辖表现得最为强势的美国,也以“反域外适用之推定”为其逻辑前提,即首先推定本国法律没有域外效力,只有在两种例外情形下,法律才能域外适用:其一,法律本身明确表明了域外适用的意图;其二,在法律没有明确表明域外适用的立法意图时,境外行为落于国内立法的规制焦点范围之内。①“规制焦点”方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10年莫里森案[Morrison v.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561 U.S.247(2010)]中提出的。在该案中,证券欺诈行为发生在美国,而证券交易发生在澳大利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美国证券法的规制焦点在于规制境内证券交易而非境外交易,因而认为美国证券法不适用于该案。详细分析参见William S.Dodge,The New 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ity,133 Harvard Law Review 1582(2020)。对于知识产权法而言,从地域性原理出发,反域外适用之推定同样应予适用。各国知识产权立法明文表明域外适用的情形较为罕见,上文所讨论的域外适用的各种情形,基本上都落于“规制焦点”范围之内。例如,著作权和专利权的规制焦点是境内行为,当境外行为是境内行为不可分割之一部分时,则落于规制焦点范围之内。同理,商标法的规制焦点是本国市场发生的混淆和误认,当外国行为导致本国市场发生了商标的混淆和误认,则落于本国商标法的规则焦点范围之内。
从法律的地域性以及突破地域性的域外适用或域外管辖的角度出发,一国知识产权和公法几乎没有差别。但是,知识产权法毕竟是调整私人因创造或使用智力成果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其调整的手段和适用原则主要是民法的手段和原则。②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同时,知识产权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事权利,以列举方式规定在我国《民法典》之中。③参见我国《民法典》第123条。这就决定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必定不可能等同于公法的属地性特征。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最终并没有阻碍知识产权国际私法规则的发展,而在可预见的将来,公法因其属地性都不可能发展出公法的国际私法规则。④参见徐祥:《论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第38页。“在公法领域并不存在冲突法规则,只包含起直接调整作用的单边适用规则。”徐祥博士此处所说的单边适用规则,即指单边域外管辖规则。下文即详细展开此论点。
四、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国际私法规则的发展
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一般被认为长期阻碍了知识产权国际私法规则的发展。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理出发,容易延伸出两个结论:其一,在司法管辖方面,一国只受理侵犯本国知识产权的案件,而不受理侵犯外国知识产权的案件;其二,在法律适用方面,一国在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中只适用本国知识产权法,而不会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上述两个结论在世界范围内很长时间支配着人们的观念,以致许多人认为,当国际社会需要发展跨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实现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时,只有通过条约缔结方式才是可行的,只有通过制定统一适用的实体法规则,才能最终超越地域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百年之中,知识产权条约法因此得到了很大发展,而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则几乎被视为一个“伪问题”。
(一)知识产权条约对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限度
欧洲工业革命成功之后,对专利和商标两项工业产权提供国际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1883年《巴黎公约》成功问世,三年之后,促进著作权国际保护的《伯尔尼公约》也顺利诞生了。这两个公约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支柱性公约,经过多次修订,被各国广泛认同和加入。在《巴黎公约》谈判之初,许多人幻想通过多边协议制定统一的、超国家的国际知识产权,但是这一理想旋即破灭。①关于《巴黎公约》的形成过程,参见[美]阿伯特、[瑞士]科蒂尔、[澳]高锐:《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国际知识产权法》(上),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74-282页。《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最后不仅未能打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相反,两个公约都从地域性特征出发并以之为基础,结果是固化和强化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②黄汇教授认为:“商标地域性原理可追溯至《巴黎公约》第6条”。这种说法不能成立,知识产权地域性原理早于公约的形成,《巴黎公约》只是承认了工业产权地域性的现实而已。参见黄汇:《商标使用地域性原理的理解立场及适用逻辑》,《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81页。
国民待遇原则是《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首要原则,其要求缔约国给予外国国民的待遇等同于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本国知识产权法应统一、无歧视地适用于本国国民和外国国民。③参见《巴黎公约》第2条第1款、《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1款。国民待遇原则无疑扩大了对外国国民的保护,因为如果没有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可能就无法在本国申请注册工业产权了,或外国人的作品就无法获得本国著作权法的保护了。但是,国民待遇原则是以承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为逻辑前提的。我们可以对比一般民商事领域的情形:各国的一般私法早就破除了地域性限制,依据国际私法规则,彼此可平等地相互置换适用;无论是本国国民还是外国国民,如果在涉外案件中适用本国法律,则享有本国法律赋予的民事权利,如果适用外国法,则享有外国法律赋予的民事权利,因此国民待遇原则在一般私法领域没有意义。但对于知识产权而言,外国人在本国境内享有本国知识产权,而不享有外国知识产权。因此,国民待遇原则与两公约所规定的独立保护原则是相辅相成的。
除了国民待遇原则,《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在诸如保护期限、优先权等问题上规定了最低保护标准。《伯尔尼公约》确立了自动保护原则,作品无须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审查、批准和授权,就可获得成员国著作权法的自动保护,而且扩及在其他缔约国产生的作品。①参见《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因此,较之《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提供了更高的国际保护水准,但自动保护原则也以独立保护原则为前提。
对以两公约为基础的国际知识产权法所提供的最低保护,发达国家并不满意。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国家组织,借助于国际贸易公约的谈判平台,利用它们贸易市场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施压,最终在WTO框架中订立了TRIPs协定。TRIPs协定强化了多边协调,并在多方面提升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由此迈入了新阶段。21世纪之后,WTO的更进一步谈判逐渐陷入僵局,新的阶段所开启的利用贸易公约平台推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就从全球性的多边贸易协定平台,转入了区域贸易协定平台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平台。②对知识产权国际公法发展进程的详细描述,参见P.Sean Morris,Priv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ulation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26 U.C.Dav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Policy 147(2019)。
《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开启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可一百多年来,国际社会并没有创设出完全超国家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仍以国别和地域性为其基本特征。诚然,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标准在不断提高,国际统一实体法规则在不断深化和扩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地域性。但是,这种超越是极为有限的,个人知识产权保护最终还是主要依赖于国内法,原因如下:第一,各个时期的公约都以国民待遇为基本原则,以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独立保护原则为前提条件,虽有最低保护标准突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但其实在更大范围内固化和强化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第二,公约所提供的最低保护标准的统一实体规则,无论是数量还是保护内容,与各国国内法规则都无法相比,知识产权保护主要还是依赖于后者。第三,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在许多缔约国不能被法院直接适用,③我国司法实践似乎倾向于否定知识产权条约的直接适用性质,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条约的可直接适用时特别增加了但书:“……但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条约已经转化或者需要转化为国内法律的除外。”虽然我国《民法典》没有承继《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法院一般不直接适用知识产权条约的司法实践则是清晰的。而是被纳入国内法后间接予以适用,当条约规则被纳入国内法后,从形式上就不再是国际规则,而成为国内法规则,并和原有国内法规则一样具有地域性特征。第四,除极个别区域性共同法院,如欧洲统一专利法院之外,私人知识产权的纠纷尚缺专门国际司法机构解决,而仍留待各国国内法院解决。因此,不能扩大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对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作用。
知识产权条约所构建的国际保护机制,并不能满足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需要,而一国动辄扩大本国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以实现对本国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则容易导致各国恶性竞争。各国争相抢夺对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立法管辖权,将会在更大范围内加剧各国法律冲突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在多边国际条约机制和单边域外管辖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大片中间地带,那就是国际私法发挥作用的领域。在整个涉外民商事领域,以条约方式存在的国际统一实体法,无异于是汪洋大海中的几座孤岛。各国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协调和解决,主要还是依赖于以多边主义法律选择规则为主体的国际私法。为何在涉外知识产权领域,国际私法方法会被长期忽视呢?这主要还是因为受限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
(二)地域性与涉外知识产权管辖权规则之发展
对于侵犯外国知识产权的案件,一国是否享有司法管辖权?长期以来,受知识产权地域性原理的影响,各国普遍表现出了犹豫的态度,英美法系国家更甚。①See Graeme B.Dinwoodie,Developing a Privat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The Demise of Territoriality,51 William&Mary Law Review 711,734(2009).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还曾经作出裁决,认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侵犯日本专利的案件没有司法管辖权,应由日本专属管辖。该判决背后的核心理由便是认为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特征,应由各国独立进行保护,而且知识产权法是市场规制工具,一国不应干涉外国登记注册的行政行为;知识产权法的本质关乎公众利益,是一国决定公众应该为合法垄断支付对价的问题,应由该国自行决定。②See Mars Inc.v.Kabushiki-Kaisha Nippon Conlux,24 F.3d 1368(Fed.Cir.1994).如果一国拒绝对外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就不可能引发法律选择问题,遑论最后选择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
从逻辑上说,司法管辖和法律适用并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涉外案件自始不可能适用外国法,并不妨碍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因为法院最后还可以适用法院地法。但在起诉侵犯外国知识产权的案件中,如果法官依据知识产权地域性原理,认定不可能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来保护外国知识产权,同时也不可能适用本国知识产权法来保护外国知识产权,意味着法院根本不能对侵犯外国知识产权的案件提供任何救济,那么自始不去行使司法管辖权,便似乎是合理的。因此,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和法律选择问题彼此就成了恶性循环之存在:没有司法管辖权,就不可能发生适用外国法的问题;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问题,行使司法管辖权便失去了意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欧洲国家1968年《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以下称《布鲁塞尔公约》,现发展为2012年《布鲁塞尔条例I(重修版)》,统称为欧盟布鲁塞尔管辖权体系]为代表,宣告了涉外知识产权的管辖权开始与一般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趋近,一国可以受理涉及外国知识产权的案件。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的法律选择问题也随着司法管辖权的扩大而涌现。涉外知识产权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这一法律选择规则,逐渐被各国国际私法立法所采纳。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知识产权章就以被请求保护地法为最基本之系属。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加剧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复杂程度,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受到了学术界史无前例的重视。面对互联网新时代,各国国内法遽然难以实现相应改革,于是各知名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纷纷投入示范法之制定,诸如ALI原则、CILP和《京都指南》相继问世,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在过去20多年来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新技术条件下跨国知识产权实践对国际私法提出了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界在不断地重新审视和反思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理。
徐祥博士在论及知识产权地域性与专属司法裁判管辖权的关系时指出:“实际上,为避免适用外国法于争议而拒绝行使司法管辖权,与法院确保当事方适当司法保护的义务背道而驰,公正和便利的利益可通过允许一个当地管辖权能实施由外国法确定的权利得到更好的实现。对于大量产生的国际知识产权关系,充分发挥各国司法机关的管辖权能,是强化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重要环节。”①徐祥:《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605页。据此观念,如果能够突破“涉及外国知识产权的案件应由外国法院专属管辖”的狭隘观念,一国适当扩大司法管辖权,并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以保护外国赋予的知识产权,这不仅能够提升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效率,而且还能扩大对外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最终提升全球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水平。
在欧盟布鲁塞尔管辖权体系中,除了规定注册类知识产权的登记和有效性争议由注册登记地法院专属管辖外,其余涉外知识产权争议适用普通民商事争议的管辖权规则。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和侵权行为地都可以作为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客观管辖依据。依据上述三个管辖依据行使的管辖权,案件所涉知识产权均可能是外国知识产权,而非法院地国的知识产权。特别是依据被告住所地行使的一般管辖,不仅案涉知识产权可能是外国知识产权,而且被告的行为也可能发生在外国。知识产权案件也同样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只要选择不违反关于注册类知识产权的有效性的专属管辖。当事人合意选择的管辖法院,未必就是案涉知识产权注册地的国家的法院。因此,在欧盟布鲁塞尔管辖权体系中,知识产权诉讼的原告行使诉权就变得更为便利了,原告可以在知识产权的注册地国家以外,选择对其更为便利和有利的国家的法院提起诉讼,这就从管辖程序上扩大了对原告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欧盟布鲁塞尔管辖权体系坚持注册类知识产权的有效性问题由注册地国家的法院专属管辖,是因为知识产权授予集中体现了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及国家对知识产权种类和范围这些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事务的独立判断,在此问题上仍须捍卫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而知识产权有效性之外的其他事务,诸如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等,已经偏离了有效性的核心问题,更多关涉当事人相互间的私人利益,因而可以由非注册地国家的法院管辖。当知识产权的债权问题和有效性问题发生交叉时,有效性问题还需要由注册地国家法院专属管辖吗?对此,欧盟布鲁塞尔管辖权体系明确规定,无论是直接起诉注册和有效性问题,还是将有效性问题作为抗辩理由,均适用专属管辖规则。②参见《布鲁塞尔条例I》[Regulation(EU)No.1215/2012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Recast)]第24条第4款。2006年德国法院受理的两个德国人之间的知识产权诉讼,涉及法国专利侵权,一方当事人提出了法国专利的有效性问题,德国法院认为其在侵权之诉中对有效性问题仍有管辖权,因为德国法院最后作出的有效性判决只约束当事人,而不会产生对世效力。但欧盟法院则认为,非注册地国家对效力问题作出认定,本质上是对世的,而且会造成不同国家效力认定的冲突,因而应严格适用欧盟布鲁塞尔管辖权体系的专属管辖规则。①See GAT v.Luk,Case C-4/03,2006 E.C.R.I-6509.
欧洲只在注册类知识产权的有效性问题上适用专属管辖,而在其他方面适用一般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规则,这一立法模式逐渐获得各国普遍认同。但在知识产权合同之诉和侵权之诉中,一方以知识产权的有效性作为抗辩,此时是否需要由注册地国法院专属管辖,对此还存在争议。②例如,《京都指南》第11条第2款规定:专属管辖之外的法院也可以对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作出裁决,但此裁决结果不能影响第三人。
(三)地域性与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的解释和适用
涉外管辖权规则和法律适用规则是联动的,这种联动效应在知识产权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一国扩大对涉外知识产权的管辖权时,如果再固守知识产权只适用法院地法而不可适用外国法的陈旧观念,就不再适宜了。正因如此,各国逐渐承认了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亦是如此。但是,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不仅在当时并不为我国司法实务界所熟知,时至今日仍为我国司法实务界所误解,有将被请求保护地法简单等同于法院地法的,也有将被请求保护地法简单等同于侵权行为地法的。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在我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适用。③我国司法实践将被请求保护地法直接认定为法院地法和侵权行为地法的司法案例及其相关情况,参见黄志慧:《我国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法律适用规则的检视与完善》,《法商研究》2020年第5期,第187页。
被请求保护地法较之国际私法的其他系属,确实更容易令人误解。正确理解被请求保护地法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厘清其与知识产权地域性之间的关系。被请求保护地法这一概念最早形成于《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该款规定各缔约国应对产生于缔约国范围内的作品自动提供保护,但鉴于各国著作权法的地域性限定,具体保护内容和方式由各国著作权法独立规定,因而权利人主张依据哪国著作权法提供保护的,就应适用该国著作权法。《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2款事实上规定了著作权应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只是作为法律选择规则,它远不够清晰和简明罢了。但无论如何,它为知识产权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这条普遍而简明的规则铺平了道路。
知识产权的效力和内容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这最早获得了普遍承认。知识产权许可或转让合同,其中不涉及知识产权效力和内容的,只涉及合同之债的部分适用合同本身的准据法,这种分割方法也被普遍认同。但唯有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最易产生争论。一种思路是,区分知识产权权利和侵权之债,分割适用,权利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侵权适用侵权准据法。另一种思路是,两者不作区分,统一适用一个法律,或者统一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或者统一适用侵权之债准据法。上述哪种方法更为合理呢?
侵权之债通常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双方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可作为例外适用双方当事人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侵权之债的法律适用现在还普遍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①例如,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也有类似规定。如果知识产权的侵权之债建立在知识产权和债权分割的基础之上,当侵权行为地法律和注册地法律不是同一个法律时,则很可能导致注册地国家认为是侵权的,而侵权行为地法律却不认为是侵权;或者相反。如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就被全面突破而不复存在了。同样,如果只是统一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因侵权行为地法很可能不同于注册地法,这也将导致知识产权地域性被全面突破而不复存在。欧盟《罗马条例II》第7条明确规定知识产权侵权统一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而且不允许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方式偏离它,就是为了继续捍卫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理。②参见欧盟《罗马条例II》第7条第1款、第3款。
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给了原告自由处分的权利,原告依据某个国家的法律来陈述其诉讼请求,并请求依据该国法律来保护其知识产权,这个法律就是被请求保护地法。被请求保护地法很可能与法院地法或侵权行为地法重合,但也有可能彼此分离。以下对三者的分合情况进行分类说明,以更好理解被请求保护地法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
第一种情形:原告在甲国法院起诉被告侵犯其甲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地位于甲国,此时原告一般会请求依据甲国法来保护其知识产权,因而被请求保护地法、侵权行为地法和法院地法三者合一。
第二种情形:原告在甲国法院起诉被告侵犯其乙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地位于乙国。如法官在本案中适用法院地法即甲国法,由于甲国知识产权法具有地域性,无法保护乙国的知识产权,因而原告将会败诉。如法官在本案中适用乙国知识产权法,对乙国境内的行为进行制裁并保护乙国的知识产权,原告得以胜诉。甲国法官适用乙国知识产权法,这并不违反乙国知识产权法的地域性,因为是乙国知识产权法支配乙国境内的行为,最后保护了乙国的知识产权。因此,原告在这种情形下只应选择乙国法为被请求保护地法。
第三种情形:原告在甲国法院起诉被告侵犯其乙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地位于甲国。如原告主张甲国法为被请求保护地法,因甲国法无法保护乙国的知识产权,所以原告将会败诉。如原告主张乙国法为被请求保护地法,因侵权行为地位于甲国,乙国知识产权法限于地域性,无权支配境外的侵权行为,所以原告无法依据乙国法而胜诉。但是,侵权行为尽管发生在甲国,但如行为效果发生在乙国,依据域外适用的效果标准,乙国法可能主张域外适用于发生在甲国的行为。如果甲国法官承认被请求保护地法即乙国法的域外适用效力,则原告可以胜诉。但是,甲国法官很有可能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视为公共政策,认为乙国法的域外适用违反了甲国的公共政策,从而仍然判决原告败诉。
第四种情形:原告在甲国法院起诉被告侵犯其甲国知识产权,而侵权行为地位于乙国。如原告以侵权行为地法乙国法为被请求保护地法的,则乙国法无法保护甲国知识产权,原告将会败诉。如被请求保护地法为甲国法,因甲国法不能适用于乙国的侵权行为,原告一般也会败诉。但是,如果甲国知识产权法认为可以域外适用于乙国境内的侵权行为的,原告可能胜诉。
第五种情形:原告在甲国法院起诉被告侵犯其乙国知识产权,而侵权行为地位于丙国的。如甲国法或丙国法为被请求保护地法,则甲国法和丙国法都无法保护乙国的知识产权。如乙国法为被请求保护地法的,乙国法也不能适用于丙国境内的侵权行为,但如果乙国法主张域外适用于丙国的侵权行为,那就最终取决于甲国法官是否承认乙国知识产权法的域外管辖效力。
依据上述分类讨论可知,被请求保护地法是由原告通过自己的诉讼请求塑造和选择的。①See Lawrence Collins(with Specialist Editors),Dicey,Morris and Collin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2242(Sweet&Maxwell 2013).但是,被请求保护地法并不能理解成原告单方选择的法律,因为如果原告可单方选择决定知识产权的准据法,就不可能给予法官充分的指示,令其结合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理,包括从地域性原理出发的域外适用规则,去综合判断原告主张的法律是否适用于具体案件。诚然,被请求保护地法并非理想之概念,它不够确定,须留待法官个案判断。法官在进行个案判断时,应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知识产权地域性原理和域外效力规则作出整体判断。然而,当下并没有比被保护请求地法更好的概念,用来满足上述个案判断的要求。而且,被保护请求地法规则还隐含了一个实体价值判断,那就是促使法官去逐个考察法院地法、注册登记地法和侵权行为地法,考察其中哪个法律在满足知识产权地域性原理的同时又能同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那么这个法律就应该被当事人和法官认定为被请求保护地法。
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尽管有不确定性之缺陷,但还是获得了各国国际私法的普遍认可,成为涉外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基础规则。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在形式上无疑是双边冲突规范,表明一国法院在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中有可能适用外国法。这是知识产权法真正区别于公法之所在,因为依据公法禁忌原理,一国法院是不应适用外国公法的。同时,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又是非常特殊的双边冲突规范,它以承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理为逻辑起点,其适用须臾离不开地域性原理的辅助和指引。其他双边冲突规范的适用,并不需要附带结合地域性原理,更何况在涉外案件中,一般私法已经消解了地域性问题本身。
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得到公认后不久,就迎来了网络技术飞速发展时代。网络知识产权侵权对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在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中,一个通过网络方式的单个侵权实施行为,损害发生地可能位于数国,甚至成为无处不在的全球性侵权。不管是著作权网络侵权,还是工业产权网络侵权,原告依据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可能请求法院同时适用数国或更多国家的法律,这些平行的独立提供保护的知识产权法,同时成为解决侵权纠纷的被请求保护地法。尽管从理论上说,同时适用多个被请求保护地法并无不可,但这毕竟会加重外国法查明的技术困境,以及增加同时解释和适用多国法律的困难。多国法律甚至相互冲突,不同的保护内容和保护标准叠加在一起,从实体结果上也无法保证个案公正。因此,国际社会于此尤为着力,ALI原则、CLIP和《京都指南》都作出了有益探索,尽管各自的具体规则不尽相同,①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法律适用突破地域性原理之规定,参见ALI原则第321节、CLIP第3:603条、《京都指南》第26条。但它们的方向是一致的,都追求在网络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上突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限制,寻求一个合理的法律统一适用于全球知识产权侵权。在可预见的将来,国内立法采纳这些规则是完全可能的。
五、结语
我们为何需要重思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这是因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长期困扰着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的发展。尽管在西方社会,这一现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以根本改观,但我国学界依然存在诸多认识误区,司法实务界至今未能正确理解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的立法本意,以致常常将被请求保护地法简单等同于法院地法或侵权行为地法。
知识产权自始即存在地域性和国际化需求之张力,但地域性至今仍是知识产权或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特征。一般私法在涉外法律适用领域已经消解了地域性问题,而涉外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尽管发展出了以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为主的双边冲突规范,但被请求保护地法规则的适用仍要结合地域性原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有类似于公法属地性的方面,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共享公法的单边域外适用的方法,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最后并未阻挡双边冲突规范的发展,一国在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中是有可能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的。但公法出于公法禁忌原理则不可能发展出双边冲突规范,一国法院一般也就不可能适用外国公法,这就是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公法属地性之间的本质区别。
徐祥博士对于知识产权地域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研究,揭示了如下原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不应阻碍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的发展,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同样可以促进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徐祥博士是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研究当之无愧的开拓者,本文便是对徐祥博士研究成果的补充、扩展和深化,希望有助于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廓清盘踞在知识产权地域性问题上的种种迷雾。
徐祥博士一生钟情于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研究,未曾汲汲于学术上的名和利,只知以“不苟且”的学问态度投身其中。他从不贸然发表论著,写下为数不多的学术成果,必求己心之所安。本文不敢也无意效仿太史公作《伯夷叔齐列传》,慨叹“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去为徐祥博士谋取身后名。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萨维尼早就道出了其心声:“书成深感欣慰。我书中也许含有不少真理的种子,或将在他人著作中滋养生长,结出累累硕果。在学术推陈出新的过程中,本书播下种子,然后退居幕后,甚至将被遗忘殆尽,可这又何足道哉!个人作品只是匆匆过客,如同个人之肉身。但擦亮了个人一生的思考却是不朽的——所有痴爱于思考的我们,将连缀成一个宏伟的永续的共同体。个人所作贡献,即使微不足道,也在共同体中觅得了永生。”①See William Guthrie&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a Treatise on the Conflict of Laws,and the Limits of Their Operation in Respect of Place and Time,Introduction,xxxi(Andesite Press 1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