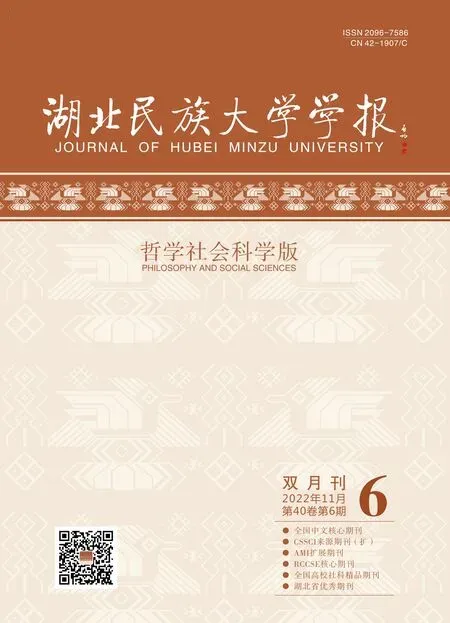西方人类学民族志范式的转型与发展
杨海燕
民族志作为一种认知、表征和传播异文化的知识载体,一直是人类学的“看家本领”。民族志的生成涉及“在那里”和“在这里”两个过程。前者意味着与异文化接触、观察、参与和对话等构成的“田野”过程,后者意味着“田野”归来之后的文本写作。将这两个过程勾连在一起的是民族志的认知问题,即作为认知主体的民族志者和人类学家(1)民族志产生的历史上,民族志者与人类学家并不总是同一个认知主体,比如在业余民族志阶段二者由不同的人员担任。,如何体认异文化和自身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拿什么样的认知形式、认知工具和认知框架来认识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2)卢成仁:《社会人类学的认识论传统及其启示》,《思想战线》2020年第4期,第44-53页。。民族志者所持的认知框架不仅影响他们认知与他者之间差异的性质,而且也决定了民族志文本何以表征他者。基于此,从认知方式、认知框架以及反思认知过程和社会本体参照几个方面在民族志生产过程中的比重差异,将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发展划分为业余、科学、反思与“本体论转向”四个阶段。(3)高丙中教授曾将民族志划分为三个时代,但他更侧重对不同时代的民族志特征的描述,较少涉及不同时代背后的认知特征。详见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58-63页。
一、业余民族志阶段
如果将学科职业化和研究方法的系统化作为学科成立的标志,那么人类学产生于20世纪初的欧美。将民族志界定为一种跨文化的求知见证行为,其历史非常久远。弗洛朗斯·韦伯在其《人类学简史》一书中,便将民族志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4)弗洛朗斯·韦伯:《人类学简史》,许卢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6-25页。欧美的民族志实践主要开始于15世纪末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后,在此之前,关于世界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主要来自古希腊和穆斯林群体。从进入美洲一直到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所倡导的科学民族志的诞生,西方民族志对自身与他者之间差异的界定分别处于神学与进化论的认知框架下,而具体的认知形式与认知工具主要聚焦在如何用更好的方法获取资料。根据人类学家与民族志者之间的关系,可将这个时期内的民族志生产分为两个子阶段。
第一子阶段:以传教士为主要民族志者的《圣经》民族志时代。这个阶段从15世纪末一直持续到17世纪。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后,尽管存在对原住民认知的不同思潮(5)还有批评殖民者的暴力和屠杀行径等其他思潮。,可欧洲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的认知依然处在《圣经》的神学统治之下。印第安人是否与欧洲人一样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印第安人是否与欧洲人一样具有灵魂?最终形成了欧洲人的优越论,这种优越论建立在圣经对人的定义上,即将具有食人习俗的土著视为与欧洲人不同的非人类。基于这种人与非人的认知和属性划分,欧洲人对土著进行了屠杀和奴役。(6)费雷德里克·巴特、安德烈·金格里希、罗伯特·帕金,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王晓燕、欧阳敏,等译,宋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8页。
虽然对印第安人的属性认定局限在神学解释的范围之内,但是这个年代的民族志者与原住民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亲密的,对文化差异性也有特别尊重和开放的一面。比如蒙田(M.E.de Montaigne)对于民族志报道人的选择更倾向于当地人,而非西方的理论家或知识精英。另外,传教士长期居住在印第安社会中,他们的民族志资料是建立在与当地人的亲密互动以及对其他传教士工作的广泛认知上,因而得以保障民族志的高质量。(7)参见弗洛朗斯·韦伯:《人类学简史》,许卢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40-79页。同时,熟知两边文化的当地人以及当地贵族和混血儿写了一些类民族志文本,成为见证殖民者对当地社会破坏的民族志资料,以及分析欧洲人如何看待土著人、原住民如何感知最初与欧洲人的接触等问题的重要经验资料。
第二个子阶段:“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与“抽屉式”的民族志时代。这个阶段从17世纪开始,旅行者从之前的传教士、水手变为博物学家、画家、语言学家和民族志者。民族志这种与异域体验相结合的经验知识形态开始进入欧洲的知识领域当中。根据这些异域知识来争论人类的起源,贯穿于整个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这个阶段对原住民与欧洲人的差异从神学认知中解放出来,转向进化论和传播论。对人类历史的探寻与基督教神学决裂,转而探寻“人类的自然史”与人类的原始文化。于是,对土著人的认知便被纳入这样的认知框架之下:他们在人类自然历史中是属于欧洲人的祖先,还是猴子与人之间的中间阶段?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源于何处,代表了人类历史的什么阶段?进而在操作方法上产生了颅骨学激发下的人体测量学和社会进化论。前者将土著人运送到市政厅、学校等地方,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测量和拍照,以此分析原住民的脑容量和智慧程度。(8)参见弗洛朗斯·韦伯:《人类学简史》,许卢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36-158页。后者则“从各种旅行报告中专心的挑选着民族志资料,以证实人类学家关于人类文化形式演化阶段的高论”(9)乔治·史铎金:《人类学家的魔法:人类学史论集》,赵丙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7页。。
该阶段民族志资料的获取已不再是旅行者私人性的知识活动,为了保证民族志者获取的资料能够被人类学家用于分析人类历史的伟大设想,产生了指导民族志者获取资料的方法。其中一份是《论观察野蛮人时遵循的多样方法》,这份指南提到了旅行者在没有字典也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要注重身体语言和符号语言、土著语言标记法以及旅行者必须观察的土著个体和集体现象的清单。(10)参见弗洛朗斯·韦伯:《人类学简史》,许卢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17-118页。这份方法的部分内容一直保留到1870年出版的《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后文称《问询与记录》)中。在1870—1920期间,《问询与记录》出了四版,发展为对民族志者的培训手则。同时,将大量业余人员拼凑且分散的观察,转化为可供比较的数据。该阶段总体上是民族志者去填充资料,而人类学家在房间对其进行分析。
这样的分工模式,即使到了19世纪后期,资料由自然科学家改行的人类学家进行搜集时,也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888年,海顿(A.K.Haydn)从托雷斯海峡进行科学考察,回来之后将资料按照《问询与记录》中的分类进行编写发表。1894年,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澳洲中部进行考察,他因参与了当地人整个仪式的过程而记录的文化属于整体性的文化表演,其资料也并未按照《问询与记录》中的分类进行。可是,斯宾塞只是费雷泽(J.G.Frazer)的“现场替身”,他并未产生民族志方法方面革新的意识。(11)乔治·史铎金:《人类学家的魔法:人类学史论集》,赵丙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2-19页。他的民族志观察本质上依然属于将远方的资料装进人类学家的理论和方志“抽屉”的民族志形式,将不同的社会文化对应到不同的发展等级。
二、科学民族志阶段
科学民族志代表性的标志是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科学方法意识的觉醒,而人类学家和民族志者也合二为一。这个阶段的民族志从一种次要的技术变为人类学获取知识的首要方法,而赋予民族志如此重要地位的是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革新意识最初受到里弗斯(W.H.R.Rivers)的“具体方法”的启发,这个方法包含以下几个内容。(1)谱系法:通过追溯原住民的亲属关系来分析基本的社会结构。(2)强调民族志工作的整体性与民族志者的单一性:认为由欧洲人划分的宗教、教育、艺术和技术等领域在原始文化中是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考虑到考察团不同成员的多种活动会在当地引起骚动和混乱,主张民族志观察由单个民族志者进行。(3)主张民族志者角色的专业化:要想让民族志考察达到深入研究的目的,不能依靠缺乏训练的政府官员和传教士,而应由受到科学方法训练或有经验的人担任专业民族志者。里弗斯的方法论与之前的“抽屉式”民族志相比,更追求对地方的深入研究与对“具体事实”的关注。可是,这与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论革新仍有距离。从调查场所来看,前者在布道船的场所或布道站的走廊,而后者则走进村落中心。从民族志工作者的角色来看,前者属于考察者,后者是以某种方式加入村落生活的参与者。(12)乔治·史铎金:《人类学家的魔法:人类学史论集》,赵丙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7-38页。
马林诺夫斯基的科学民族志方法论,是他在几次深入调查过程中觉醒的。1914年他在莫尔兹比港进行考察时就表示对已有方法的不满。他难以接触到真正的野蛮人,对他们的观察不够。他也没法说当地语言,无法进行深入考察。在梅鲁岛考察几个村庄时,他在土著人的宴会中停留三晚,意识到一种直接介入当地生活的民族志方法的潜力。1915年在分析梅鲁岛资料时,他便做出单独在土著人中间从事工作要比在白人住所中开展的工作更深入,住得离村庄越近,越能在实际上看清土著人的论述。(13)乔治·史铎金:《人类学家的魔法:人类学史论集》,赵丙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8-65页。马林诺夫斯基革新方法论的核心目标是“将土著人的行为纳入土著人的意义”,也就是通过他者的视野来分析他者的行为。带着这样的方法论意识,他分别于1915年和1917年两次进入特罗布里恩岛进行参与式田野调查,写就了第一本具有科学意义的现代民族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他在这本民族志的导论部分集中阐述了他的方法原则(14)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梁永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不仅证实了自己的田野工作,也证实了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可能性与客观性。可是,随着马林诺夫斯基日记的出版,他所倡导和推动的科学民族志方法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不管怎样,科学民族志自提出之后的半个世纪内,成为很多国家民族志方法的准则。
该阶段也是西方人类学不断繁荣发展的时期,设置人类学专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不断增多。田野方法准则很大程度上得到统一,对群体差异的认知框架变得更为多元,几个西方国家纷纷从进化论的认知中解放。在英国,尽管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对群体差异的认知也是从进化论出发,可最终落在了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社会结构的功能主义的普遍性探求上。布朗最初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将安达曼作为田野点,安达曼人因为身材矮小被认为是人类生命最原始和最基础的状态,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级。后来他受涂尔干思想的影响,放弃了进化论的观点,转而关注不同群体社会结构的特征,进而将非西方群体与西方人之间的思维和文化差异纳入不同社会结构的功能差异上。类似的,马林诺夫斯基也将不同的文化与社会差异解释为人类个体需求发展的不同特征。这种解释文化与社会差异的认知与进化论的传统决裂,群体差异在人类心智的一致性中得到了协调,差异性所代表的先进和落后的等级关系被消解。
在德国,由于现代启蒙的相对滞后性,使得德语区对他者的研究一直带有种族中心主义的倾向。这集中体现在对语言、习俗和文化差异几个方面的研究,认为非德语民族在历史上或生物学上低劣一等。这些民俗文化差异通过大量博物馆的展览,潜藏着激发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和种族主义的支持以及对帝国主义和殖民野心的支持。后期德语区的人类学对进化论的抵制而产生的传播论、功能论、文化圈理论和民族主义情绪大多与体质人类学相结合,导致德语区的人类学在纳粹时期卷入到了合谋、迫害犹太人的时代情景当中。这些人类学家反对英国的人性统一观,反过来支持对种族差异的研究。他们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反犹太宣传、种族评估等活动,以此来支持纳粹意识形态或亲纳粹意识形态。(15)费雷德里克·巴特、安德烈·金格里希、罗伯特·帕金,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王晓燕、欧阳敏,等译,宋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0-159页。总之,文化差异在民族主义情绪下与体质研究相结合被视作种族差异,助推了种族屠杀意识形态的实施。
在美国,博厄斯(Franz Boas)学派将差异视为是独立发生的文化现象。该学派看来,族群差异既非是直线进化论所强调的先进与落后状态,也非传播论所认为的文化接触的结果。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用历史特殊论强调不同文化现象发生的相对自主性来反驳种族主义和文化传播论。即使文化相对主义受到不同学派以及学派内部的挑战,但通过博厄斯学生的多部民族志的验证,文化相对主义依然得到广泛的认可。文化相对主义将不同的文化置于平等的地位,强调文化的无可比较性,每一种文化对其自身而言都是特殊的,并且只有通过自身才能够被理解。基于此,文化相对主义将人们对于群体间差异的认知从种族决定论和单线进化论中解放出来。法国的人类学历史上一直与社会学比较接近,人类学家与民族志者合二为一的田野工作在法国发展得较晚。法国在该阶段的民族志范式并没有明显的转变进程,而对文化差异的研究长期受到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结构主义的影响,从进化论的余音下逐渐转向探求人类社会结构的普遍性特征。
三、反思民族志阶段
20世纪60年代之后,面对去殖民战争、越南战争、马林诺夫斯基日记的出版以及后现代思潮对民族志带来的冲击,人类学内部产生了两类应对危机的方式。
一种是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式结构主义分析:减少民族志在人类学中的重要性。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成功让人类学重新获得社会喜爱的地位,他的结构分析拒斥在分析中融入调查关系。结构分析将田野经验作为获取材料必不可少且会引起不适的阶段,而在文本分析阶段将神话化约为一个文本及其变体,且排除对调查关系的分析,排斥搜集文本产生的语境。在这样的普遍性研究中,列维-斯特劳斯将民族志置于研究中的从属地位,这也是他没有一本代表性的民族志作品的原因之一。他再次将民族志者、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进行分工,民族志者负责搜集资料,民族学者负责综合地方性的资料,而人类学家则负责在人类性的层面进行普遍性的综合。他这种废除调查关系的做法是为了使人类学免除殖民语境而必须付出的代价。(16)参见弗洛朗斯·韦伯:《人类学简史》,许卢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28-233页。
另一种是在批判性审视中重建民族志。与列维-斯特劳斯不同的是,越南战争对美国人类学的冲击,使得美国的人类学家在批判性直面问题的同时,寻找方法论方面的出路。如果说之前的民族志都在围绕着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握关于他者的信息和文化这一问题,那么,反思民族志的回应方式将焦点转向认识民族志者认识他者的方式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渐使人类学的民族志事业从科学领域转向人文领域,民族志的使命也不仅限于追寻他者文化这一本体论问题,同时也要研究追寻“他者”这个过程的认识论问题。这种在批判审视中寻找出路的转向可以归结到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认识相对主义。为了回应社会对民族志这种跨文化认识于科学研究的可行性、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质疑,格尔茨以全新的认识论观念去审视跨文化研究的本质与意义。格尔茨指出与科学民族志所宣扬的立场不同,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不可能完全认识当地人的精神世界与经验,民族志的研究只是一种通过对当地人理解其社会运行规则的概念和符号等的解释,是一种对解释的解释(17)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7-21页。,也是一种“就什么说点什么”的阐释。而人类学的民族志描述追求的是一种把握地方性知识的“深描”。通过对巴厘岛斗鸡这一公共文化符号的“深描”,格尔茨证实了通过“深描”文化符号来阐释地方社会深层文化意涵的可能性。(18)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28-534页。在具体方法层面,可以通过“近经验”和“远经验”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操作方法回应了这一问题:如果外来者无法认识当地人的文化,那么被西方文化训练的当地人的认知依然受到西方文化视角的影响,也不可能达到完全从当地人的视角认识当地文化的效果。因此,人类学家作为民族志者可以通过“近经验”结合“远经验”而形成的“深描”,来达到作为外来者却以“文化持有者内部视角”来描述他者文化的效果。(19)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71-92页。那么,民族志工作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格尔茨提出“事实之后”的概念与解释,也就是说文化事实的发生具有即时性,民族志工作不可能完全复刻事实本身,做的只是一种事后的深描与解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志的工作完全是虚幻和建构的,转身离开的大象留下的脚印代表事实确实存在和发生过。另外,格尔茨认为追求事实反映的是人类意识产生的本质:先发生事实,后形成观念。(20)Clifford Geertz,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20.
第二个层面:反思民族志田野过程与瓦解民族志知识权威。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出版之前,人类学家的“目光”大部分聚集在如何获取关于他者的文化和信息,而在民族志文本中部分显露民族志者“在场”的经历,也只是为了服务于民族志知识权威的建立。(21)比如埃文斯·普理查德在《努尔人》中展现了不少他在田野中的情况,只是这种展现并不是为了反思,而是为了令读者信服,树立权威。反思民族志认为现实中的“在场”,其实充斥着由认知主体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社会结构关系及由此而来的象征性暴力,这种暴力会被施加在与认知主体对话的人身上。因此,调查关系在两个方面都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它是一种以民族志者为发起人的入侵,他单方面地在没有任何初步协商的情况下,指定谈话的目的和用途。当研究者在不同类型的资本以及文化资本的层级结构中占据比被调查者更高的位置时,这种不对称性就会因社会不对称而加倍。(22)Ferdinando Fava, Illusion of Immediate Knowledge or Spiritual Exercise? The Dialogic Exchange and Pierre Bourdieu’s Ethnography. In Matera Vincenzo and Biscaldi Angelaeds, Ethnography: A Theoretically Oriented Practi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32.在此之前的民族志者未认识到“关系性”作为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实际条件,常常使社会和文化研究以及从事这项研究的人蒙上一层模棱两可的神秘面纱。另外,反思的视角进一步延伸到民族志者的身体在民族志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简言之,民族志的意义不在于理解民族志者要处理的事物是如何存在的,而在于这些事物是如何存在于民族志者内心的;它们是如何通过民族志者有知觉的身体被构造出来的,只有这种对现实的感知才能导致民族志的构建。身体作为信息机器和有知觉主体的有效身体,前者用来传达被感知和“加工”的东西,后者通过激发民族志者的主体性来传递对接受到的事物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视觉经历了整个认知阶段。而民族志者为了确保这个过程的完整性和深度,必然充分和有意识地使用凝视,通过主体意识的运作将观察到的事物,经过自身的概念体系与社会本体进行模拟和参照性的转化,变成他者的经验现实。也就是说民族志从第一步开始,必不可少的要通过民族志者的身体与凝视。(23)Francesco Faeta,The Anthropologist’s Eye: Ethnography, Visual Practices, Images, In Matera Vincenzo and Biscaldi Angela(eds), Ethnography: A Theoretically 0riented Practi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p.231-263.因此,民族志的实践不再是试图客观化,而是反思性的探索、与田野现场的对话。
马库斯(George E.Marcus)他们聚焦民族志文本的生产过程——写文化,认为民族志的文本写作本质上是在发明文化而非再现文化,在发明文化的过程中充满了民族志者为了树立权威而使用的修辞、省略以及隐藏信息等技术,这种揭示与保密技术的使用是民族志者为了建立一种系统性的知识来支配“第一时间”的知识。(24)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6页。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欧美人类学提出不同方向的应对路径。朱炳祥将其总结为三类应对方案:第一类是“求知主体的对象化”,将民族志作者的研究过程作为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以拉比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为代表。第二类是“对话式”路径。尽管民族志中的很多知识都是对话的产物,是民族志者和土著人之间的对话,土著人和土著人之间的对话,可是对话却完全消失在民族志文本中。“对话式”路径通过暴露民族志者的经验资料处理过程及其对资料的把握程度来解构民志者的知识霸权,以德耶尔(Kovin Deyer)的《摩洛哥对话》为代表。第三类是“开放表述”路径,在寻求民族志者与研究对象对话的基础上,尝试将读者卷入民族志的解读当中(25)朱炳祥:《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39-50页。,这类路径也想通过读者的参与消解民族志者的知识权威。
第三个层面:反思西方文化基底对民族志认识论的影响。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认为西方基督教对人性本恶以及神的存在是维持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认知,这深深植根在西方社会科学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的认知当中。“把个人需求和贪婪当成社会性之基础的不断尝试,已经成为传统人类学更能诱发人们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这一种形式的人类学功能主义就是开化的亚当理论的另一种遗存……上帝并不是神话了的社会,相反社会是神话了的上帝。”(26)马歇尔·萨林斯:《人性的西方幻象》,赵丙祥,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75、77-78、118页。而在人类学对他者研究的过程中依然沿用了这样的认识论底色。“大量的人类学研究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将其对象的最初分化状态综合起来的持续努力,把它未经反思就在各文化领域间作出的区别综合起来。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分化和区别是按照我们(西方)自己社会提供的模式作出的。”(27)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6页。这样的认识论转向将西方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地方化,寻找不同国家和文明差异的主体性,与后期的本体论转向具有相似的认识觉醒意识。同样的民族志走向存在于杜蒙(Louis Dumont)的研究当中,杜蒙认为西方现代性以来的个体主义,其实是根植于基督教对抽象的人的认知当中(28)路易·杜蒙:《论个体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意识形态》,桂裕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1-55页。,而他对印度研究的民族志表明印度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性与宇宙观(29)路易·杜蒙:《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王志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8-52页。。在认识方法论方面,杜蒙倡导整体主义的认识观以解决长期以来一直盛行的二元对立的区分性比较法所带来的他者的被表征问题。杜蒙的整体主义认识观强调,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些对立因素,其组合方式的差异会对地方社会的总体形态产生影响。杜蒙举了一个例子,在两个社会中都包含A、B两种因素,在一个社会中,A从属于B,而在另一个社会中,B从属于A,这就足以产生一切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在这种认识观下,群体间的差异并不是本质性的差异,而是人类一些共有因素不同组合关系所产生的结果。(30)路易·杜蒙:《论个体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意识形态》,桂裕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6-7页。
四、“本体论转向”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本体论转向”成为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从宏观社会背景来看,20世纪是人文主义的时代,“人”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共同属性成为人类学的本体论承诺以及伦理标准。人文主义寻求在人性的共同点上培育相互理解的种子。然而,21世纪的人类不再被视为是适应外在压力的进化物种,人类自身已经成为影响发展条件的决定性力量,此时人类干预自然的规模与力度是任何历史时刻都无法比拟的。在这样的人类世和“后人文主义”或“跨人文主义”的时代,人类需要重新定位自己,也需要重新审视人类这个概念本身。(31)Thomas Schwarz Wentzer and Cheryl Mattingly, Toward a New Humanism: An Approach from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8, no.1, 2018, pp.144-157.那么在“后人类”时代,如果人类学不仅仅是对人类的研究,那么它可能是什么?如果人类学在分析上不能再依赖人性作为相互理解的共同点,那么民族志的文化翻译与解释又能基于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需要人类学家重新批判审思人类学的学科基础,二需要生产一些新的知识帮助人类走出“人类世”的灰烬。(32)Amiria J. M. Salmond, Transforming Translations(part II): Addressing Ontological Alterity,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4, no.1, 2014, pp.155-187.因此,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和新的民族志理念与实践便得以提出,并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将民族志从后现代的认识论困境中解救出来。
(一)后人文主义和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与原则
2014年,英戈尔德(Tim Ingold)发表一篇名为《关于民族志,够了!》(33)Ingold Tim, That’s Enough About Ethnograph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4, no.1, 2014, pp.383-395.的文章,在文中他谴责了人类学转向“研究自己的工作方式”的状态。英戈尔德强调民族志的本体论承诺(我们对世界的发展和形成所负责任的一种言行实现)及其作为教育实践(引导新人走向世界,而不是向他们的头脑灌输知识)的重要意义,以此避免将民族志简化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这样会使得民族志变得毫无价值。英戈尔德希望通过民族志的本体论承诺与教育实践的意义,为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人类世所产生的问题寻找出路。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要想民族志践行本体论的承诺,必须进一步强化民族志的反思性。他们认为后现代的反思人类学其认识论的反思程度不够彻底,其反思范围依然局限在西方社会的本体论范畴之内。在跨文化的民族志研究中,依然以西方社会本体来“映射”非西方社会,以及他们与世界和非人类之间的关系。在《本体论转向:人类学的探索》一书中,霍尔布拉德(Holbraad Martin)和彼得森(M. A. Pedersen)就指出,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核心其实是一种严格的方法论议程,一种民族志的描述理念。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并不关心正统哲学所探寻的世界“真正真实”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相反,本体论转向提出本体论问题是来解决认识论问题,而人类学中的认识论也必须与本体论有关。即一个人如何看待事物的认识论问题,首先变成了要看见什么的本体论问题。(34)Holbraad Martin and Morten Axel Pedersen, 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9-10.目前,欧美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并未形成清晰、一致性的范式,而且互相之间存在较大的争议。(35)Carrithers Michael, Candea Matei and Sykes Karen, 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vol.30, no.2, 2010, pp.152-200.但是,在《本体论转向:人类学的探索》一书中,他们总结了本体论转向与之前的人类学相比,从自反性、概念创新以及实验性三个方面延续和强化了传统人类学的三个关键原则。
首先,认识论的彻底反思是对民族志自反性形式的强化和更彻底的承诺。本体论转向之前民族志的认识论基础,是建立在对“世界本来是怎么样”的本体预设之上,而这个预设世界的基准样态是西方社会以及西方世界,是西方视域中的世界。而本体论转向认为,这正是后现代反思民族志反思得不够彻底的地方。人类学一直在处理人类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但这种研究的变化通常是在文化范式和相应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框架内形成的。这种范式的本体论基础依赖于一种假设:它允许并支持多种文化世界或世界观。本体论人类学希望打破这一图景,给予他者本体性地位,包括探索“多元自然主义”。因此,人格不再仅仅与人类联系在一起,而是非人类本性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认为给人类学家戴上“有色眼镜”的不是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文化方面的预设,而是本体论的差异。过去认为民族志中长期存在的关于民族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等认识论的问题,在本体论转向这里被重新定义为本体论的问题。以人类学中最有名的毛利人礼物之豪为例,传统的民族志解释将礼物流通视为集体表征不同的一种体现形式,而在本体论转向这里,这是一种新的集体样态。前一种解释强调是本体一致,形式不同,后一种强调本体性的不同。
其次,本体论转向民族志需要重新开放概念。将实在差异从西方的认知框架下开放出来,要搁置本体论预设,需要将它们重新概念化。(36)Holbraad Martin, Ontology, Ethnography, Archaeology: An Afterword on the Ontography of Things,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vol.19, no.3, 2009, pp.431-441.以这种方式提出本体论问题,将反思民族志解构的消极过程转变为积极的重建过程。当然,概念化在人类学中一直扮演着重要作用。而本体论的重新概念化与传统概念化的区别在于,通过民族志中的本体性差异,提供真正的另类思维。传统的概念化过程是一种单向抽象的过程,比如将一只狗抽象为四足动物。在这种单向抽象的过程中,不仅充满本体性的预设(以西方社会本体和认知思维为预设框架),而且还充满了对实在的缩放与裁剪,以及对模糊性的控制。(37)Holbraad Martin and Morten Axel Pedersen,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30-145.本质上,这是一种将实在与概念相对化的进程。而本体论对相对化的强化在于,首先使所有人类学知识生产的这些基本的本体论意蕴成为分析关注的主要对象,在此基础上开展重新概念化的议程。也就是说,本体论转向将社会文化分析的传统范式和文化概念转向本体论。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用一种避免西方现代哲学主导范式(无论是理性主义、结构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本体论,来重新思考我们对世界或世界性的概念。(38)Thomas Schwarz Wentzer and Cheryl Mattingly, Toward a New Humanism: An Approach from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8, no.1, 2018, pp.144-157.
再次,本体论转向人类学也是传统人类学实验性的一种延续。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也具有实验性,只是这种实验性与自然科学的方式比起来,更多体现在民族志田野过程中,研究者将自己作为生产数据的研究工具,同时将自身和田野对话者作为知识和洞察力的主要来源。本体论转向对实验性的传承与强化体现在,将实验的范畴从民族志的田野维度扩展到分析的理论、思想维度中。传统民族志对现实社会所产生的实验性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批判的功能上,而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对实验性传统的强化,在于将文化批判直接转化为创造概念(观念)。(39)Holbraad Martin and Morten Axel Pedersen, 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24.
总之,本体论转向对人类学三个传统原则的延续与强化,从认识论的维度上通过“杀死西方”来为其他类型的本体性存在提供可能;在人类知识或思维层面上通过审思人类学现有知识体系和重新概念化实在,来展现差异的不可通约性;在实验维度上将差异视为改变现实的可变知识的来源,是促进关于世界形成方式的不同真理。本体论转向从这三个层面来回应21世纪人类世所面临的问题。
(二)本体论转向的民族志进路
目前以本体论转向为标签的民族志实践非常丰富和繁杂,尚未有清晰的定位与分类。朱晓阳在其文中指出,国际社会有人将诸多本体论人类学指向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类型,前者包括了各式本体论指向的论说,后者指受到法国结构主义影响的视角论、结构本体论和对称人类学等。(40)朱晓阳:《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南》,《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46-68页。同样,科恩(Webb keane)认为本体论转向可以分为强本体论和弱本体论两种。弱本体论指的是观念层面,看待事物的不同解释方式,是关于世界理念的言语表征;强本体论指的是,卡斯特罗(E.V.de Castro)和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为代表的一类研究,强调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的经验、观念以及和自然环境互动的不同方式,这不仅仅是表征方式的不同,而是他们的世界本体性的不同。(41)Webb Keane, Ontologies, Anthropologists, and Ethical Life,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3, no.1, 2013, pp.186-191.在具体路径上,萨蒙德(Amiria J.M.Salmond)认为本体论转向的民族志可分为三种,一是以英国人类学家英戈尔德为代表的生态现象学进路,是一种栖居本体论视角;二是以法国人类学家德斯科拉为代表的本体论绘图制进路,将世界划分为万物有灵、图腾主义、自然主义和类比主义四种本体论模式;三是以卡斯特罗为代表的透视主义与多自然主义本体论模式。(42)Amiria J. M. Salmond, Transforming Translations(part II): Addressing Ontological Alterity,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vol.4, no.1, 2014, pp.155-187.而科斯塔(Costa Luiz)和福斯托(Fausto Carlos)将它们划分为两种研究传统,一种是认知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传统,另一种是现象学的传统。(43)详见Costa Luiz and Fausto Carlos,The Return of the Animists: Recent Studies of Amazonian Ontologies, Religion and Society: Advances in Research, vol.1, no.1, 2010, pp.89-109.当然,还有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以及科学技术研究,即客体指向的本体论模式。(44)详见Holbraad Martin and Morten Axel Pedersen, 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0-46.以及Kohn, Eduardo, Anthropology of Ontologies,Annu. Rev. Anthropology, vol.44, no.1, 2015, pp.311-327.在此,选择以英戈尔德、德斯科拉、卡斯特罗三位代表性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者的民族志实践来显示以上三种人类学原则,以及在他们学术实践中的运用与体现。
第一种是英戈尔德的生态现象学——“栖居”进路,正如英戈尔德所解释的那样,他的整个学术作品加起来无异于一次持续的尝试,试图纠正“西方思想和科学的整个大厦建立在一个单一的、潜在的缺陷之上,即将人类和自然的‘两个世界’分隔开来的缺陷”(45)Morten Axel Pedersen, Anthropological Epochés: Phenomenology and the Ontological Turn,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50, no.6, 2020, pp.610-646.。他主要弥合的是西方社会思想中存在的作为生物的人与作为文化人之间的分裂。传统的西方思想一直认为人是自足的主体,在文化浸润下的个体对世界已经做好了设计(筑造视角)才进入世界当中,与物质性的世界是分离的。英格尔德受发展生物学的启发,发展生物学认为生物的形态与能力与其说是基因决定的一种表现,不如说是生物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生物在特定的环境中活动,建立起特定的关系场域,而生物的形态与能力就在此关系场域中自然的浮现。因此,英格尔德提出“栖居视角”,认为人作为生物和文化的有机生命的连续体,是具身化在周围的世界和其他物种中的能动者,即环境中的能动者。在这样的关系领域中,环境不再是能动者面对着的周遭环境之物,不只是影响能动者行为的背景。环境只是相对能动者而言,以其特性和可支持性持续地进入能动者的活动之中,并与能动者互相渗透、相互形塑。(46)白美妃:《超越自然与人文的一种努力——论英戈尔德的栖居视角》,《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54-59页。正如他自己提出的:“世界不是我所看的事物的外部领域,也不是我所做的事情的外部领域,而是与我和我周围的事物一起进行着或经历着不断的生成。”基于此,栖居进路反对特定的知识与文化形式,认为知识是从直接经验中产生的,是能动者通过不同的方式与世界及其人类和非人类居住者接触而产生。通过将文化回归自然,使人类从超脱于世界之上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也重新定位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打破了传统的文化与自然二分的认识论基础。(47)Costa Luiz and Fausto Carlos,The Return of the Animists: Recent Studies of Amazonian Ontologies, Religion and Society:Advances in Research, vol.1, no.1, 2010, pp.89-109.
第二种是德斯科拉的结构主义——“本体论地图学”进路。德斯科拉作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弟子,其思想来源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在处理与西方不同的野蛮思维时,列维将野性的思维视作与科学一样没有本质差异的思维方式,因为两者都是同一种分析推理的表达,以此赋予野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同等的地位。受列维神话研究的影响,德斯科拉也将神话作为其研究的切入点。列维认为神话是从自然到文化的过程,而德斯科拉更感兴趣的是动物和人类(自然和文化)之间以及人类和神(文化和超自然)之间存在的连续性。他的万物有灵论在1992年提出,是他关于阿丘亚人的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概括。在亚马逊社会中,人类将自己的内在等同于非人类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德斯科拉继续研究它的逻辑对应物,即具有相同内在性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必然是社会性的。如果人类和非人类(包括动物、灵魂、植物和物体)具有相同的内在性,那么万物有灵论就建立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和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主体,在这个世界中,所有存在物之间的默认互动模式是主体之间的互动。
2013年,德斯科拉的著作《超越文化与自然》在英语世界出版。他将世界上存在的不同本体以文化的方式追踪到它们被发现的地理区域,因此被称之为“本体论地图学”。他根据人类与其他实在的内在性与物质性作为两个关键区别因素,将世界划分为四种类型的本体论。(48)萨林斯在与德斯科拉对话的过程中,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将德斯科拉的四个本体论类型都归于一种本体论来源。详见Marshall Sahlins, On the Ontological Scheme of 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4, no.1, 2014, pp. 281-290.(1)图腾主义:面对另一个实在,人类或非人类,它拥有与我相同的物质性和内在性的元素;(2)类比主义:它的内在性和物质性都不同于我的;(3)万物有灵论:有相似的内在性和不同的物质性;(4)自然主义:内在是不同的,物质是相似的。德斯科拉的分类可以说将西方的本体论更为彻底的“本地化”,将它们降到四种可能的本体论中的一种。对他来说,泛灵论是一种人类思维的“系统”,在所有社会中都可以在不同程度和不同的混合中找到它。而与传统的图腾分类系统相比,“泛灵论系统是图腾分类的对称倒置”。在图腾系统中,非人类被视为符号。在泛灵论系统中,他们被视为一种关系的术语。因此,德斯科拉认为万物有灵论的宇宙论是以“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连续性”为前提的。(49)Holbraad Martin and Morten Axel Pedersen, 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3.而且,与传统的结构主义只注重先天的认知结构不同,德斯科拉运用康德的图式理论来调解概念与实在之间的关系,将人类和非人类之间所有可能关系的客观属性综合进“习性来源”的范畴中,强调了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之间的具体实践活动的生成性。(50)Costa Luiz and Fausto Carlos,The Return of the Animists: Recent Studies of Amazonian Ontologies, Religion and Society: Advances in Research, vol.1, no.1, 2010, pp.89-109.总之,这种转向中的人类学者,将民族志的任务视为要阐明传统上被视为(文化或认识论)表征的本土宣言和实践,是具有本体性的实在。
第三种是卡斯特罗的“透视主义”视角——“新万物有灵论”进路。卡斯特罗是人类学“本体论转向”最初的提出者以及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他的“透视主义”是一系列关于美洲土著人思想和实践的“抽象概括”,属于当地人的宇宙论。在这个宇宙论中,人类和非人类作为不同类型的主体能动者,都被赋予了相同的灵魂。这意味着,不管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一样的。其他物种也会以人类的方式看待他们自己的身体和行为。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透视主义”只是德斯科拉万物有灵论的一个变体。可事实上,他们的方法有显著的差异。卡斯特罗认为,德斯科拉对万物有灵论的描述只是将传统的图腾崇拜的对称倒转,这只是一种古典的认知方式,而非宇宙学本体论存在。因此,万物有灵论不再是一种认识(认识论)和接触自然(实在)的方式,而是西方自然主义的对称倒转。西方自然主义假定身体(生物、进化、基因)的连续性,并将差异置于精神(文化、心灵)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透视主义不同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本体论所蕴含的认识论是一种相对主义。在这种认识论中,不同的文化对单一的自然有不同的理解。相反,透视主义认为自然才是多元的,而人类和非人类以同一种文化认知世界。这是一种单一文化,多元自然的本体性存在。因此,透视主义又被称之为“多元自然主义”和“新万物有灵论”。
那么,不同物种之间的连续性是如何在民族志上表现出来呢?美洲虎和人都以同样的文化方式看待事物,同一样东西,在美洲虎眼中是“木薯啤酒”,而在人类眼中的却是“血”。人类在河边看到的是一片泥泞的盐渍地,而貘看到的是它们举行仪式的大房子等。这种视点的差异(不是对单一世界的多个观点,而是对不同世界的单一观点)来自哪里呢?卡斯特罗认为这种差异不能从灵魂(精神)中衍生出来,因为灵魂是存在的共同基础。共同的灵魂保证每个物种都视自己为人类,分享人类文化和语言。相反,建立视点差异的是身体,因为身体和它的情感(身体影响和被其他身体影响的能力)是本体论分化和参照分离的场所和工具。在传统的文化相对主义那里,身体是不同视角的客体,而在透视论这里身体是视角分化的场所。同样的,卡斯特罗认为人类与非人类物种之间的视角转换,需要依赖于“神话”原则,即宇宙中的每一种存在都有转变成其他存在的潜力,因为所有存在都内在地包含着彼此的视角。比如,萨满教、做梦以及狩猎等元素均是实现视角转换的“神话”的体现。(51)详见Holbraad Martin and Morten Axel Pedersen,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pp.157-199.
五、不同民族志范式的认知过程与群体差异形态
民族志作为一种认知活动与表征异文化的文本载体,涉及三组关系:(1)西方和世界实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西方的人类学家如何看待世界的形成与变化这个问题;(2)非西方群体与世界实在之间的关系:非西方社会如何看待世界,这是土著社会的宇宙学问题;(3)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关系:非西方社会作为欧美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时,意味着他们从一个自足的存在被纳入西方社会的视域当中便产生这组关系。而这组关系又包含两对子关系:一是民族志者如何看待他们与非西方人之间的差异;二是人类学家如何看待土著社会认知他们自己与世界实在之间的关系。这三组关系在不同的民族志阶段强调和侧重的内容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图1)。

图1 四种种民族志阶段认识发生过程图。注:带边的中空箭头表示阶段一和二:业余民族志和前科学民族志;虚线箭头代表阶段三:反思民族志;实线箭头代表阶段四:本体论转向民族志。
在业余民族志和科学民族志阶段,西方人类学对于这三种关系的认知还未完全分离。在业余民族志阶段,对于他者的认知还聚焦在如何更好地指导民族志者获得关于他者的资料,而到了科学民族志阶段,认为民族志研究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操作可以实现如实客观反映他者的社会状态。可如图所示,该时期对非西方社会的认知是笼罩在西方社会如何认知世界与社会的知识框架之下的。在《圣经》作为西方认知世界的主导框架的业余民族志阶段,民族志者眼中西方人与美洲原住民之间的差异便成为人与非人的差异。而原住民自身认识世界实在的宇宙学原理也被放入西方社会认知世界实在的宇宙学原理的框架之下,以西方的认知原型为参照点来“裁剪”原住民的世界认知。比如,自然与文化的二分,个体与社会结构的二分等认识模型。同样的,在社会进化论作为主导欧美社会认知世界变化的科学民族志阶段,人类学家眼中西方人与非西方人之间的差异便成了先进与落后,现代与原始的关系。文化相对主义主导的阶段,不同群体间的差异被视为是各自社会独特发展的文化结果。而文本上的民族志,被当时的人类学家认为是完全等同于他者文化,并未意识到文本上的民族志只是被西方社会认知框架裁定过的民族志,与经验中的他者并不对等。
在反思民族志范式下,西方人类学认识到人类学家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与认知并非完全客观与科学,只是一种认知相对主义,意识到田野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会对民族志的生产有影响。人类学家对他们的理解与解释,只是他们对原住民的解释的一种再解释。而这种认知相对主义在田野过程中,是由民族志者与当地人之间的社会地位、文化资本差异所带来的权力关系,以及民族志者的单向凝视和身体感知等因素共同构成。另外,民族志者对当地文化的相对理解,同样掺杂了民族志者自身生活与成长社会的认知基底。因此,该范式下的民族志认知是一种虚的“散点”认知与研究过程。最终的民族志文本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按照传统“建构”他者文化的文本,一部分为呈现民族志田野过程的文本。而这些文本依然是带有人类学家背景以及西方社会认知框架的“滤镜”,是一种“滤镜”下的民族志文本。该范式在人文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52)齐泽克认为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否定、颠倒和自我参照形式,一种带有距离的种族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对他者特殊的尊重是肯定自身优越的恰当形式,而支持文化多元主义的背后其实是无根的跨国资本。详见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5-251页。价值理念的主导下,西方与非西方的差异成为一种各有自身价值的平等的存在。该范式下的民族志认识到田野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对民族志认知活动和民族志文本与地方活生生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本质,可是尚未意识到西方人类学概念知识体系以及社会的本体预设对认知他者的影响。
在“本体论转向”范式下,暗含着作为民族志者的人类学家,要搁置基于西方社会自身的认知基础与社会的本体论预设,抛掉已有的知识与概念体系,要将民族志的焦点从如何认识转向看到了什么。在这种范式下,将差异作为新认识发生的出发点,而不是将这些差异裁剪、模糊然后纳入西方的知识体系内部。因此,在这种范式下,西方社会自身认知世界实在的方式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非西方社会认知世界实在的方式也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在这个层面上,本体论转向依然处在古典的单一本体和多元文化的层面上。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本体论转向认为即使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在物质上面对应的是同一个世界实在,然而由于不同的认知方式,世界实在是以一种本体性差异的方式出现在不同的文化中。因此,在本体论转向这里,不仅不同的认知方式是一种本体性的差异存在,而世界实体本身也是本体性的差异存在,打破了过去认为世界实在是单一本体,差异只存在于文化和认知方式之中的观念。搁置了本体论预设以及西方概念知识体系之后,本体论转向的民族志暗含着文本上的民族志就是一种“镜像”民族志,能将他者完全“反射”出来。即使,“本体论转向”对如何实现这样的“镜像”反射并未做出交代;可是,“本体论转向”的民族志希冀能够从本体的角度完全呈现差异性他者,在此基础上探寻不同的知识生成与世界构成方式。
最后,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的人类学界出现为了建立中国的知识主体地位而开展的海外民族志,以及为了克服“非中即西”二元分立的学术格局,尝试用中国传统的思想去解释“非中非西”社会(53)梁永佳:《贵货不积:以〈老子〉解读库拉》,《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71-93页。的人类学实践等。面对这些新的人类学与民族志趋势,中国的人类学如何从西方的民族志传统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保持警醒的同时开创有别于西方民族志实践的意义和可能性,是新一代中国人类学者必须要考量和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国人类学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公共方面是健康的,但智识层面却几乎停滞”(54)George E. Marcus and Marcelo Pisarro, The End(s) of Ethnography Social/Cultural Anthropology’s Signature Form of Producing Knowledge In Transi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23, no.1, 2008, pp.1-14.的世界人类学可能有所贡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