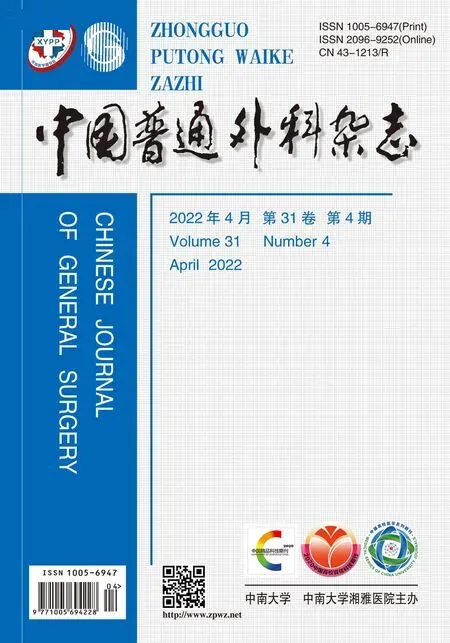肠道菌群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和诊断治疗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宋德心,王伟东,高瑞祺,卫江鹏,李晓华,王士祺,余鹏飞
(1.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陕西西安710032;2.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2017级学员一大队一队,陕西西安710032)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最新发布的报告,CRC 发病率和病死率在全球范围癌症中分别居第3 位和第2 位[1]。其中散发型CRC占比超过75%。在散发型CRC 中,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动物脂肪和各种加工肉类的过度摄入、纤维摄入和运动量减少都会加重罹患CRC 的风险[2]。CRC 患者5年的总生存率为50%,一旦发生转移其总生存率降至10%[3-4]。因此,CRC 患者的预防、早诊早治至关重要。近年来,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在CRC 中的作用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肠道菌群通过影响肠道炎症[5]和肿瘤相关信号通路[6]与CRC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还可以调节局部免疫反应,进而影响化疗[7]和免疫治疗[8]效果。现对肠道菌群在CRC 发生发展、诊断治疗中的作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CRC与肠道菌群的关系
1.1 正常肠道菌群
人体正常肠道中大约有100 万亿个共生细菌,总重量约1~2 kg,被称为最大共生体[9],大约包含300 万个基因。共生肠道菌群参与维持肠道稳态,在消化吸收、物质代谢及抑制病原体侵袭定植、调控免疫反应、保证肠黏膜屏障完整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具有高度多样性、稳定性、抗性和适应性[10]。在正常肠道菌群中,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占微生物总数的90%以上,放线菌门和梭杆菌门则不到10%[11]。肠道菌群和宿主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彼此受益。菌群黏附并定植于肠道,参与肠内食物加工,营养宿主[12],同时促进肠上皮成熟,维持人体免疫系统的完整性和天然屏障功能。
1.2 肠道菌物紊乱与CRC
肠道菌群按一定比例组合分布,彼此依存又相互制约,维持动态平衡。当致病菌入侵或机会致病菌异常富集时可引起菌群失衡[13]。肠道菌群失衡,其中益生菌(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和类杆菌等)会减少,同时致病菌如产肠毒素的类杆菌、大肠杆菌和艰难梭菌数量增加。致病菌通过分泌有毒因子损害肠上皮细胞,触发慢性炎症反应并损伤黏膜组织以破坏肠屏障,同时改变肠道微环境,从而促使CRC 发生[14-15]。此外,肠道菌群可引起DNA 损伤、癌基因表达和抑癌基因沉默进而驱动CRC 发生。如今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进步和宏基因组学的发展为研究CRC 相关肠道菌群提供了很好的检测方法。研究结果显示,CRC 患者与健康者的肠道菌群结构有较大差异,CRC 患者的粪便菌群中拟杆菌属、志贺菌属、粪肠球菌、埃希氏菌属、雷伯氏菌属、克链球菌属、消化链球菌属数量显著增多;而罗氏菌属、毛罗菌科等可产生丁酸盐的细菌大量减少[16-17]。丁酸可为肠上皮细胞提供能量,缓解局部炎症[18]。除了CRC 患者和健康人群间肠道细菌丰度存在显著差异,肿瘤组织与邻近正常组织之间包括粪杆菌属、梭杆菌属、胃瘤球菌属、阿克曼氏菌属、链球菌属、紫单胞菌属、疣微菌科在内的7 种菌属或菌科分布也明显不同[19]。由于肠道沿线pH 值和其他生理因素的变化,肠管不同区域细菌的定植和多样性同样可能会有很大差异。研究[20]表明,CRC 患者中乳酸杆菌科和双歧杆菌科丰度的降低分别与结肠肿瘤和直肠肿瘤相关。
肠道菌群是如何诱导CRC 发生及发展的,目前人们普遍认可有两种模式,即Alpha-bugs 模型和Driver-passenger 模型。Alpha-bugs 模型认为肠道菌群一方面通过分泌毒性蛋白直接诱导肠上皮细胞癌变;另一方面其自身结构的改变会导致黏膜免疫反应发生异常,无法及时清除癌变的肠上皮细胞不断累积引发CRC[21]。Driver-passenger 模型认为,诱导肠上皮细胞DNA 损伤和触发炎症的pks+大肠杆菌和产肠毒素脆弱拟杆菌等“司机”菌群”作为CRC 始动因素,率先引发肠道微环境的改变,进而使得梭杆菌、链球菌等在肿瘤环境中具有生存优势的“乘客”菌群进一步促进CRC 的产生[22-23]。综合两种模式背景进行研究,肠道菌群参与CRC 发病的机制具体可包括以下几方面:慢性炎症反应;肠上皮细胞DNA 损伤;免疫反应;肠道菌群代谢产物与细菌酶[24]。肠道菌群失调诱导肠壁通透性的增加,促进细菌易位和内毒素进入肠黏膜,并诱导肠上皮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形成自由基,进而引起慢性炎性反应,致使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发生改变[15],从而激活Wnt、Notch、TGF-β、NF-κB、STAT3、MAPK 和Akt/PKB 等信号通路[25],同时加剧细胞损伤和肠黏膜不典型增生,最终诱发CRC 并加速其进展[26]。细菌及产物还可进入肿瘤基质,激活肿瘤相关髓源细胞和免疫细胞分泌IL-23 和IL-17,进一步驱动“肿瘤炎症反应”,从而诱导免疫抑制并促进STAT3 活化以激活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信号通路的传导,促进CRC 进展。
在CRC 相关的致病菌中,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Fn)、产肠毒素脆弱拟杆菌(enterotoxigenic Bacteroides fragilis,ETBF)和pks+大肠杆菌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Fn 是起源于口腔内的厌氧共生菌,Kostic 等[27]首次报道并证实Fn 在CRC 患者肠道富集和致癌性。Fn 主要依靠其表面的毒力蛋白发挥致病作用。FadA 是Fn 的关键毒力因子,可激活E-钙黏蛋白(E-cadherin)/β-连环蛋白(β-catenin)通路,诱导NFκB、癌基因c-Myc 表达增加,提高CRC 细胞膜联蛋白A1 水平以活化细胞周期蛋白D1[28]。其中FadA 可黏附侵袭宿主细胞,诱导促炎反应和致癌效应;Fap2 则在黏附肿瘤组织的同时抑制免疫反应;RadD 参与多种生物膜形成和种间黏附。此外,FadA 还可促进组蛋白2AX 生成,促进肿瘤生长[29]。FadA 与血管内皮E-cadherin 的共定位使得内皮通透性增加,增加细菌移位,引发全身的感染和脓肿[30]。另一重要的毒力蛋白Fap2,则通过与T 细胞免疫球蛋白ITIM 结构域(T cell immunoglobulin and ITIM domain,TIGIT)受体结合,抑制T 细胞和NK细胞功能,介导肿瘤免疫逃逸[31]。除了毒力蛋白,Fn 还可分泌甲酰三肽和短链脂肪酸至TME,募集肿瘤浸润的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MDSC),并诱导巨噬细胞向促肿瘤的M2 型转化,从而促进TME 的炎症反应,进一步促进肿瘤的形成[32]。
ETBF 致CRC 的关键因素在于脆弱拟杆菌毒素(bacteroides fragilis toxin,BFT),BFT 通过外膜泡传递至宿主细胞,介导E-cadherin 的降解,增加肠上皮通透性,活化下游β-catenin 使原癌基因c-myc 表达增加,促进细胞增殖和肿瘤形成[33]。ETBF 通过BFT 和IL-17 促进结肠上皮细胞肿瘤的发生。研究[34]表明,BFT 可触发IL-17R、NF-κB、STAT3 参与的促致癌级联炎症反应,这一过程可诱导髓系细胞募集并分化为MDSC,进而上调一氧化氮合酶2(nitric oxide synthase 2,NOS2)和精氨酸酶1(arginase 1,ARG1)水平,生成一氧化氮,并抑制TME 中的T 细胞增殖。ETBF 可通过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2B(jumonji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2B,JMJD2B)诱导CRC 的细胞高干性。研究[35-36]报道,长链非编码RNA-BFAL1 在ETBF 相关的CRC 中过度表达。BFAL1 通过竞争性结合miR-200a-3p 和miR-155-5p 来抵抗微小RNA(microRNAs,miRNAs)抑制作用,从而激活RHEB-mTOR 途径,影响多种致癌信号,引发染色体不稳定(chromosomal instability,CIN),诱导CRC 产生。
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E.coli)又称大肠埃希菌,是一种常见定植于健康人群消化道的条件致病菌,属于革兰氏阴性厌氧共生菌。依据系统发育,E.coli 大致可分为A、B1、B2、D、E 和志贺氏菌5 个主要类群[37]。B2 类群中有34%的部分可携带“pks”基因岛,一种编码聚酮合成酶和非核糖体肽合成酶的基因簇,负责合成基因毒性聚酮非核糖体肽—大肠杆菌毒素。pks+大肠杆菌可损伤上皮细胞DNA,生成γ H2AX 灶,导致DNA 不完全修复进而产生CIN 和后期桥[38],增加罹患CRC风险[39]。
除Fn、ETBF 和pks+大肠杆菌外、牛链球菌、空肠弯曲杆菌厌氧消化链球菌等其他致病菌可通过DNA 损伤、激活CRC 相关多种致癌信号通路、抑制抗肿瘤免疫、促肿瘤代谢物的产生诱导肠上皮癌变。除了致病菌,有研究[40]证明肠道中存在保护性细菌,如丁酸梭菌可调节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抑制细胞增殖和次级胆汁酸生成,诱导细胞凋亡并增加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的产生。
2 肠道菌群在CRC诊断与筛查中的价值
目前肠镜筛查仍是降低CRC 发病率和病死率行之有效的方法。随着16SrRNA 测序技术、宏基因组和代谢组测序技术的发展,肠道菌群作为新一代生物标志物在CRC 早筛与预后中的潜力得到进一步的探索。Dai 等[41]对来自不同国家的526 个宏基因组样本进行分析,确定了7 种在CRC 中富集的细菌(具核梭杆菌、脆弱拟杆菌、不解糖卟啉单胞菌、中间普雷沃特菌、微小小单胞菌、食氨基酸热厌氧弧菌、芬氏别样杆菌)可作为潜在的诊断标志物。具核梭杆菌作为CRC 相关肠道菌群的核心成员,是当前临床研究热点之一。研究[42]证明,Fn 联合粪便免疫化学试验(fecal immunochemical tests,FIT)检测CRC 的灵敏度较高(92.3%),受试者工作曲线下的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95。中山大学的一项研究[43]证实,利用具核梭杆菌与益生菌种群[柔嫩梭菌群(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Fp)、双歧杆菌属(bifidobacteria,Bb)]的比值,可显著提高CRC 诊断效果,AUC=0.943。Fn/Bb 敏感度为84.6%,特异度为92.3%。Fn/Bb 和Fn/Fp 联合检测I 期CRC 的特异度为60.0%,敏感度为90.0%(AUC=0.804)。结合整合素α4(integrin α4,ITGA4)的DNA 甲基化、Fn 及厌氧消化链球菌(peptostreptococcus anaerobius,Pa)与FIT,相比于单独的FIT,可更好地鉴别CRC 患者及进展期腺瘤患者。另有研究[44]提示基于粪便共生梭状芽孢杆菌的新型生物标记物可提高早期和晚期CRC 的检测率,甚至在CRC 早期无创诊断中比报道的Fn、FIT 和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等标记物更有效。
研究[45]发现CRC 患者粪便中Fn 与血清12、13-EpOME 水平升高呈正相关,肿瘤组织中高水平的细胞色素P450 2J2(cytochrome P450 2J2,CYP2J2)也与III/IV 期CRC 患者的高Fn 水平和更差的总体生存率相关,这可能是Fn 感染CRC 患者的临床生物标记物和新治疗靶点。膜联蛋白A1 是Wnt/βcatenin 信号调节因子和CRC 的关键生长因子,其表达水平可通过FadA 激活E-cadherin/β-catenin 通路上调,现已被证实是一种新的结肠癌复发生物标志物,并与癌症分期、分级、年龄和性别无关[46]。在预后判断方面,研究发现Fn 和ETBF 在CRC 预后较差患者中丰度较高。Fn 可通过增加CRC 细胞糖酵解促进肿瘤生成,提示Fn、ENO1-IT1 和ENO1 三者密切相关并可预测患者预后,同时靶向ENO1 通路在Fn 感染CRC 患者中或可成为一种潜在的治疗策略[47]。黏附侵袭性大肠杆菌(adherent-invasive E coli,AIEC)是一类驻留在肠道内的侵袭性细菌,研究[48]发现AIEC 在III/IV 期CRC 患者肠黏膜上的定植比I 期患者更为普遍,这表明AIEC 有可能参与晚期CRC 的进展,并且可能是一个预后因素。除了关注CRC 相关肠道菌群在丰度上的改变,最近一种基于肠道微生物单核苷酸变异(singlenucleotide variant,SNV)标记物构建的CRC 预测模型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且该模型在训练和验证队列中均表现出较高的准确性[49]。
3 肠道菌群在CRC治疗中的影响
3.1 肠道菌群对免疫疗法的影响
近年来,免疫疗法作为一种新的有效治疗策略逐渐活跃在大众视野。目前,经典的肿瘤免疫治疗包括免疫检查点阻断(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ICB)、治疗性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ies,MAB)、癌症疫苗、过继性T 细胞转移、小分子抑制剂和免疫系统调节剂[50]。其中,ICB 通过抑制肿瘤免疫逃逸来发挥抗肿瘤作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发展,如选择性抗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1,PD-1)、抗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和/或抗细胞毒性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 4,CTLA-4)单克隆抗体治疗是癌症治疗方案的一次革命,在消化道肿瘤中,CRC 是免疫治疗效果较差的肿瘤之一,其中仅很小部分错配修复缺陷(DNA mismatch repair,dMMR)或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的CRC 患者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有较好的疗效,对于大多数错配修复正常(proficient-MMR,pMMR)或 微 卫 星 稳 定(microsatellite-stable,MSS)的患者而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较差。在癌症免疫反应中,宿主免疫与肠道菌群间存在彼此调节、相互作用的交叉反应。共生菌和病原菌对全身肿瘤免疫具有复杂的免疫调节作用[51],同时癌症也会影响肠道细菌组成,促进免疫抑制[52]。此外,微生物的某些代谢产物可能影响适应性免疫和先天免疫,例如厚壁菌门的Fp 可通过代谢产物丁酸盐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s),抑制多种致癌信号通路和炎症反应,从而抑制CRC 发展[53]。SCFA 不仅可作为肠上皮细胞的重要营养素,促进其分化和生长,保持肠上皮屏障的完整性,并防止肠道内毒素进入血液引起代谢性内毒素血症[54-55],还可通过影响细胞代谢,增加巨噬细胞前体细胞的数量,强化CD8+T 细胞功能,维持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之间的平衡[56]。
研究[57]发现肠道菌群重建能改善PD-1 的抗肿瘤免疫治疗。嗜粘液阿克曼菌可通过IL-12 和增加CCR9+CXCR3+CD4+T 淋巴细胞向肿瘤微环境的募集来逆转PD-1 阻断的作用[58]。具核梭杆菌在改善CRC 免疫治疗方面的影响已得到证实,Gao 等[59]提出CRC 中的“坏”细菌,或许能在免疫治疗中发挥“好”的作用。该研究发现Fn 可通过p65 磷酸化上调环GMP-AMP 合酶(cyclic GMP-AMP synthase,cGAS)表达并激活IFN 基因刺激因子(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STING)信号,进而促进NF-κB 诱导肿瘤细胞表达PD-L1,并招募(IFN-γ)+CD8+TIL浸润,从而提高肿瘤对PD-L1 阻断治疗的敏感度。另有研究[60]提出鼠李糖乳杆菌(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LGG)诱导cGAS/STING 依赖性的I 型干扰素可增强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答,LGG 通过DC 中的cGAS/STING/TBK1/IRF7 轴诱导自身产生IFN-β,触发DC 活化,增强抗肿瘤CD8+T细胞交叉启动,从而增强抗PD-1 疗效。
研究[61]显示,使用抗生素1 周或更短时间可使肠道菌群在6 个月甚至2年时间内发生持续性显著变化(包括多样性和特定分类群的代表性显著丧失、抗生素耐药菌株的激增以及抗生素耐药基因的上调),这提示抗生素可能通过肠道菌群影响肿瘤免疫治疗疗效。通过对172 例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肾细胞癌、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胃肠道间质瘤、肉瘤等晚期癌症患者研究[62]发现,在治疗开始后的30 d 内使用抗生素,患者的总生存期显著降低。此外,在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之前,也需慎用广谱抗生素,否则患者的总生存期会更短,应答率也更差[63]。有研究[64]对568例黑色素瘤患者的数据分析发现,相较于未使用过抗生素的患者,在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之前使用抗生素其总生存期显著降低,且更易罹患结肠炎,这可能与抗生素会改变肠道菌群结构与数量,从而影响免疫治疗效果。但最新研究[65]报道,聚酮类抗生素mithramycin-A(Mit-A)可增强ICB 在CRC 中的疗效。mithramycin-A 联合αPD-L1 能显著提高CD8+T 细胞浸润程度,并减少免疫抑制性MDSC 和抗炎巨噬细胞的比例,从而提高αPD-L1有效性,显著抑制CRC 肿瘤生长。目前,抗生素对CRC 免疫治疗是否会产生明确正向或负向作用尚无统一定论。
一项研究[66]通过对74 例接受PD-1/PD-L1 单抗治疗的晚期胃肠道癌症(包括CRC、胃癌、食管癌等)患者的粪便菌群进行分析,发现普氏菌属/拟杆菌属的比值升高,对抗PD-1/PD-L1 治疗有较好的反应,并且特定的亚组反应者中普氏菌属、毛螺菌科及瘤胃菌科的丰度显著较高,不同反应的患者在核苷/核苷酸生物合成、脂质生物合成、糖代谢和短链脂肪酸发酵相关的途径上具有不同的丰度。能够产生SCFA 的肠道细菌,包括真杆菌、乳酸杆菌和链球菌,与不同类型胃肠道癌的抗PD-1/PD-L1 反应呈正相关。基于此特定细菌分类群构建出的模型,可较准确地对患者分层(AUC=0.78)。综上,肠道菌群与免疫检查点阻断反应相关,提示肠道菌群可能影响PD-1/PD-L1 单抗对CRC患者的疗效。
3.2 肠道菌群对放化疗效果的影响
晚期CRC 患者最初对化疗敏感。然而,几乎所有患者最终会因耐药出现肿瘤复发和转移,晚期CRC 患者的5年生存率低于10%[67]。因此,阐明CRC 患者化疗耐药的机制至关重要。肿瘤化疗耐药是基因调控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发现化疗后复发的CRC 患者组织中富含Fn,并与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相关,Fn 靶向TLR4、MYD88和特异度microRNA(miR-18a*和miR-4802),激活自噬通路并诱导CRC 化疗耐药。Fn 刺激自噬相关蛋白pULK1、ULK1 和ATG7 的表达,介导CRC 细胞对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5-FU)和奥沙利铂的耐药[68],这一研究同时提示Fn 丰度与CRC 复发风险相关,术后检测Fn 丰度可有效预测CRC 患者预后。此外Fn 可通过调节膜联蛋白A1 水平使CRC产生化疗耐药性[69]。不可否认,肠道菌群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诱导CRC 化疗耐药性的产生,而也有研究[70]阐述肠道菌群可以缓解CRC 患者化疗的不良反应,实验证实在接受伊立替康治疗的CRC小鼠模型中,益生菌移植可显著缓解小鼠体质量减轻和腹泻的症状,其肠黏膜的损伤程度也大大减轻。有研究[71]对纳入的150 例接受5-FU 治疗的CRC 患者评估证实,化疗期间给予LGG 干预可降低患者的病死率,改善腹泻等胃肠道不适的症状,同时能够显著降低患者所需的有效化疗剂量。除了肠道微生物在化疗耐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代谢产物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最新研究[72]结果表明,肠道菌群代谢产物丁酸可通过促进IL-12 信号通路,以ID2 依赖的方式在体外和体内直接增强CD8+T 细胞抗肿瘤细胞毒性效应,促进奥沙利铂的抗肿瘤疗效。
CRC 的放射治疗与各种不良副作用有关,如胃肠道毒性和其他后遗症等,严重损害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揭示放射治疗抵抗和相关副作用的潜在机制,制定致敏放射治疗和减轻辐射相关损伤的策略非常重要。探索肠道菌群与CRC 放疗的关系为缓解放疗副反应提供了新途径。已有研究[73]证明,双歧菌、嗜酸菌、链球菌和干酪乳杆菌等肠道微生物可以缓解放射性肠炎和腹泻的严重程度。目前关于肠道菌群影响CRC 患者对放疗疗效影响的研究文献报道尚且不多,最新研究[74]发现,口腔微生物群可影响放射治疗CRC 的疗效和预后。口腔中的Fn 可迁移并定植于肠道,在CRC 患者肠黏膜中大量富集,对放疗的疗效和预后造成不良影响,而用甲硝唑治疗可对其加以阻断。
3.3 肠道菌群对CRC靶向治疗的影响
目前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的5 种经典靶向药物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包括贝伐珠单抗、阿曲贝西普、西妥昔单抗、帕尼单抗和雷戈拉非尼。这些治疗方法主要针对癌细胞中发现的特定生物学功能改变或对癌症发展至关重要的途径,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促血管生成途径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靶向细菌β-葡萄糖醛酸酶能够消除伊立替康引起的腹泻,这对于削弱CRC 化疗药物的副作用有较大帮助[75]。有研究[76]发现,靶向参与大肠杆菌毒素合成的关键酶ClbP 可在体外阻断这种毒素的有害作用,并使得体内肿瘤数量显著减少,提示ClbP 是一个潜在的治疗靶点。Fn 感染通过miR-1322/CCL20轴和M2 极化促进CRC 转移[77]。锌指蛋白90(zinc finger protein 90,Zfp90)通过TLR4-PI3K-AKT-NFκB 信号通路,介导CAC 的发生,Han 等[78]最新研究结果发现,普氏菌为主的肠道菌群可能介导CAC 发展过程中Zfp90 的致癌作用,CAC 小鼠模型中肠道菌群的缺失能够消除Zfp90 的致癌作用,这一发现为临床CRC 预防和靶向治疗提供了新靶点。
传统观点认为,在治疗初始发生的基因突变导致了肿瘤对靶向治疗的耐药。然而,2019年《Science》发表的一项研究[79]提出,靶向治疗可诱导CRC 耐药突变。该研究发现,在接受EGFR/BRAF 抑制后,患者肿瘤组织中MLH1 和MSH2 两种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相关蛋白表达水平降低;DNA 聚合酶从高保真转换为低保真,从而提高DNA 修复出错几率,进而易于突变,并触发微卫星不稳定性,即抗EGFR 的西妥昔单抗靶向治疗可诱导CRC 细胞系MMR 和同源重组(homologous recombination,HR)修复水平下调,使肿瘤细胞获得耐药性,或许能为临床治疗提供一种新思路。例如,可评估下调的HR 蛋白能否使癌细胞获得对多聚ADP 核酸糖聚合酶抑制剂的敏感度或者可利用遗传干扰或药物来抑制癌细胞发生药物驱动的适应性诱变,以减少治疗期间新突变的产生。
3.4 其他
宿主和肠道菌群共同通过新陈代谢相互影响,调节膳食成分代谢已成为临床治疗CRC 的一种常见手段。肠道微生物通过编码的基因代谢大量膳食营养素,包括低聚半乳糖、胆汁酸、低聚果糖等人体不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并产生短链脂肪酸包括丁酸和丙酸。丁酸盐和丙酸盐均可发挥抗炎作用,其中丁酸盐明确诱导CRC 细胞凋亡[80]。近年来,粪菌移植技术在治疗难治性梭菌感染上取得的成果证明,益生菌可改善肠道菌群,维持多样性,帮助致癌物清除,预防CRC 发生,抑制肿瘤进展。常见的口服乳酸菌和双歧杆菌活菌制剂等益生菌治疗不断被应用于临床,可显著降低CRC 术后感染率,表现出令人满意的疗效[81]。最近,一种新的益生菌罗伊氏乳杆菌被证实能够抑制CRC 进展[82]。除此之外,通过生物工程抗肿瘤细菌菌株增强适应性和先天免疫的工程细菌免疫疗法[83],以及通过产生抗癌细胞因子,而不会产生明显副作用的细菌外膜囊泡全身给药[84],可能成为新的癌症免疫治疗策略。有研究[85]报道,补充CC4(4 个梭菌目菌株混合物)疗效甚至可超过抗PD-1 免疫治疗。此外,基于细菌的CRC 光动力疗法[86];细菌性癌症疗法[87]等均为临床CRC 的预防、治疗和预后改善提供了新思路。
尽管肠道菌群与CRC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并在治疗方面不断显示出新的潜力,但不容忽视的是,利用肠道菌群改善CRC 患者生存质量和提高预后的安全性亟待验证,有研究[88]曾报道2 例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在接受同一来源的粪菌移植后感染抗超广谱β-内酰胺类药物的E.coli,导致严重菌血症,其中1 例患者死亡。如何做到安全、精准、高效靶向肠道菌群治疗CRC,目前仍需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的反复验证,并亟需制定出严格的筛选排除标准。
4 总结与展望
肠道菌群在CRC 的发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定CRC 相关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可为评估CRC 的发生提供诊断依据,特别是对肿瘤的早期筛查和预后判断。生物标志物检测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检测手段则体现出更加便捷、安全、经济的优点。与潜在有害的肠道微生物相比,一些肠道菌群在免疫治疗和放化疗中显示出积极的抗肿瘤作用,特别是对其致病机制的研究为靶向治疗提供了许多有效的潜在靶点。另外,一些看似危害性的菌类却可在促进PD-1/PD-L1 抗肿瘤免疫治疗效果上展现有益的一面。此外,健康饮食、避免不必要的广谱抗生素、使用益生菌和粪便细菌移植来调节肠道菌群,都有可能成为降低CRC 风险的方法。目前,肠道菌群作为一种独特的生物标志物正逐步应用于临床CRC 患者放化疗和免疫治疗敏感人群的筛查,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技术和研究方法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标志物的筛选在灵敏度和特异度方面仍有较大的局限性,如何筛选合适的菌株,如何克服具核梭杆菌等CRC 相关致病菌诱导化疗耐药性的难题还需要未来的进一步探索。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