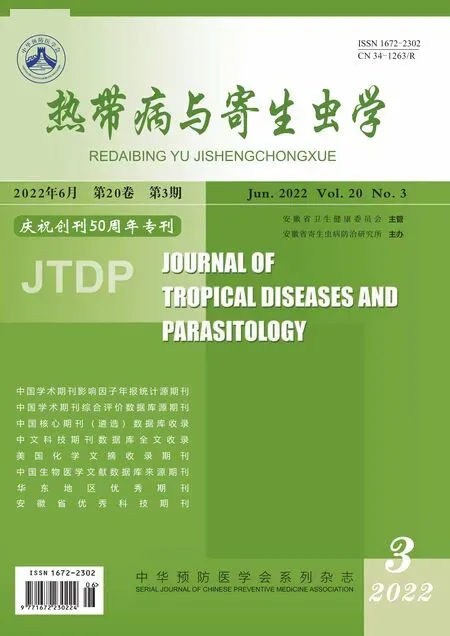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的进展、挑战与对策
操治国
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安徽省血吸虫病重点实验室,安徽 合肥 230601
血吸虫病是一种被忽视的热带传染性寄生虫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阻碍流行区经济和社会发展[1-3]。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统计,目前血吸虫病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78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感染者约2.4亿人,其中至少有90%分布在非洲[4]。血吸虫病引起的伤残大于死亡,可给患者、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疾病和经济负担[5]。2016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表明,血吸虫病疾病负担高达186万伤残调整寿命年[6]。但即便如此,其造成的实际疾病负担仍然被严重低估[7]。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危害严重。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调查,流行区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感染者1 200余万人,病牛约120万头,钉螺分布面积达148亿m2。血吸虫病的肆虐给流行区广大群众带来深重苦难,毛泽东主席在《七律二首·送瘟神》诗词中所描述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真实反映了当时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方针,遵循“因地制宜、科学防治”的原则,经过70余年的积极防控,取得了巨大成就[8-10]。当前,我国血吸虫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要在2030 年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消除目标,仍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
1 我国血吸虫病流行现状
1.1 全国疫情现况 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450个县(市、区)、3 352个乡(镇)、28 376个村流行血吸虫病,流行村总人口数为7 137.04万人;全国现有晚期血吸虫病(简称晚血)患者29 517人,主要分布在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四川、云南和浙江等8个流行省份,其余4个流行省份(上海、福建、广东和广西)均无晚血病例报告。2020年,全国仅湖北省报告1 例急性血吸虫病病例;12 个流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群血清学阳性率为1.58%,病原学阳性率为0.001%;耕牛血清学阳性率为0.22%,病原学阳性率为0;全国现有钉螺面积36.50亿m2,其中湖沼型、山丘型和水网型流行区分别占94.66%、5.30%和0.04%。从地区分布来看,湖南省钉螺面积约占全国一半,为17.25亿m2;江西、湖北、安徽、四川、江苏和云南等6个省钉螺面积也较广,分别为8.36亿、7.11亿、2.62亿、0.85亿、0.19亿、0.11亿m2;而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5 个省份钉螺分布均较局限,合计钉螺面积仅为0.01亿m2[11]。
1.2 国家监测点疫情情况 为及时了解全国血吸虫病疫情现状与流行趋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2015年起,按照《全国血吸虫病监测方案(2014年版)》的要求,在全国所有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设立国家监测点,开展疫情监测工作。结果表明:2015—2019年,国家监测点本地居民和流动人群血清学阳性率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本地居民血清学阳性率从2015 年的3.35%降至2019 年的1.63%,流动人群血清学阳性率从2015 年的1.15%降至2019 年的0.75%;5年内国家监测点累计发现病原学阳性者132 例,包括97 例本地居民和35 例流动人群,其中本地居民阳性者分布于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4省,且2019 年本地居民首次未发现病原学阳性;2015年和2016年,国家监测点耕牛病原学阳性率分别为0.04%和0.01%,2017—2019 年未发现病原学阳性耕牛[12-17]。2015—2019年,在国家监测点分别查出钉螺面积7 426.63、6 997.76、6 940.60、6 545.70、7 096.93 hm2,累计新发现钉螺面积147.20 hm2,累计复现钉螺面积831.10 hm2,累计捕获活螺997 408只,虽然镜检未发现感染性钉螺,但通过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LAMP)检测发现18 个阳性混合钉螺样本,其中湖沼地区15个,山丘地区3个[18-19]。
从全国总体情况和国家监测点情况来看,当前我国血吸虫病疫情已进入低度流行阶段,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与防治初期相比,患者人数急剧下降,且现有病例以晚期患者为主,急性病例呈偶发、散发状态[20-21];二是作为血吸虫病重要传染源的耕牛数量和感染率均明显下降,但对其他传染源尤其是野生动物传染源的重视程度和控制措施明显不足[22-23];三是全国钉螺面积近年来下降不明显,且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湖区5 省,易受洪涝灾害等因素影响而扩散[24-25];四是从总体来看,全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部分流行区仍能发现血吸虫核酸阳性钉螺或孵化出血吸虫毛蚴的阳性野粪,提示血吸虫病传播风险依然存在[26-27]。
2 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历程
回顾70 余年来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的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除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外,还得益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保证了在不同防治阶段采取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疫情特点相适应的科学防治策略。根据防治策略的演变,可将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历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2.1 以消灭钉螺为主的综合防治阶段(1950 年—20 世纪80 年代初) 在这一阶段,主要是成立防治专业机构,开展大规模调查摸底,并采取以消灭钉螺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受当时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限,缺乏敏感、特异的血吸虫病检查方法和高效、安全的病原治疗药物。这一阶段所采用的主要灭螺措施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通过使用化学药物来直接杀灭钉螺,当时的灭螺药物有生石灰、溴乙酰胺、五氯酚钠等;另一类是通过改造钉螺孳生环境来消灭钉螺,主要方法包括挖新沟填旧沟、水田改旱地、蓄水养殖、土埋灭螺等。在大力实施灭螺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人、畜查治病和危重患者救治。通过这一策略的实施,有力推进了我国血吸虫病防治进程,绝大多数水网地区和大部分山丘地区防治工作取得了极大成效,钉螺面积大幅压缩,上海、广东、福建、广西等4个以水网型或山丘型流行区为主的省份先后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28]。但在湖沼地区和地形复杂的山丘地区,受水位控制难、钉螺孳生环境复杂、药物灭螺成本高且污染环境、环境改造灭螺代价大等因素影响,以消灭钉螺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难以实施,且实施后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2.2 以人畜化疗为主的综合防治阶段(20 世纪80年代中期—2003年) 随着高效低毒的新型抗血吸虫药物吡喹酮的问世和简便易行的血吸虫病免疫学诊断方法的突破与普及,并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以病情控制为血吸虫病防治目标的情况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将血吸虫病防治策略调整为以人畜化疗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该策略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1992—2001 年)的资助下得到大力推广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9-30]。2002 年评估表明,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人群血吸虫感染率从6.93%降至3.14%,耕牛血吸虫感染率从6.38%降至3.17%,分别下降了54.69%和50.31%[31]。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在实施该策略后,还于1995 年达到了消灭血吸虫病标准。尽管以人畜化疗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可在较短时间内将人、畜血吸虫感染率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对减少感染和减轻病情能起到积极作用,但其局限性也较明显。由于流行区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血吸虫病流行因素依然存在,因此,人、畜再感染难以避免,从而不能彻底阻断血吸虫病传播,且一旦防治力度减弱,极易引起疫情反弹[32-33]。
2.3 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阶段(2004—2015 年) 为解决人群和家畜重复感染问题,我国于2004 年提出了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新策略,对血吸虫病防治策略作出重大战略性调整。该策略通过采取以机代牛、封洲禁牧、家畜圈养、改水改厕等关键技术措施,辅以查灭螺、查治病和健康教育等常规措施,达到阻断血吸虫病传播的目标[34]。事实证明,该策略实施后历经几个传播季节,血吸虫感染率就明显下降,可以有效地控制血吸虫病传播[35-36]。该策略在全国推广应用后,取得了巨大成效,极大推进了我国血吸虫病防治进程。至2008年,全国所有流行村人群和家畜感染率均低于5%,达到了疫情控制标准[37];至2015 年,全国所有流行村人群和家畜感染率均低于1%,且连续2年以上未查到感染性钉螺,达到了传播控制标准。2015 年,全国血吸虫病患者数降至7.72 万人,当年无急性感染病例发生,病牛数降至315头,与新策略实施前的2003 年(患者18.49 万,急性感染病例9例,病牛663头)相比,分别下降了58.25%、100.00%和52.49%[38]。这说明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是适合我国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疫情流行规律的最佳策略。
2.4 迈向消除血吸虫病的防治阶段(2016年至今)2016年以后,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已全面向传播阻断乃至消除目标迈进。在此阶段,我国坚持并优化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在大力推进耕牛淘汰力度和强化有螺地带禁牧的同时,实时分析不同地区主要传染源的动态变化,因地制宜地开展传染源防控措施;此外,完善血吸虫病监测预警体系,加强疫情监测和风险评估工作,大力推进精准防治,确保及时发现和消除血吸虫病传播隐患[39]。通过实施优化的传染源控制策略,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如期实现了《“十三五”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确定的目标。在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份中,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和上海于2016 年通过了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的复核并一直维持防治成果,四川、江苏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达到传播阻断标准,云南、湖南、湖北于2020年省级自评达到传播阻断标准。2020 年全国450 个流行县(市、区)中,已有98 个实现传播阻断目标,占21.78%;337个实现消除目标,占74.89%[11]。实践证明,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仍将是我国迈向血吸虫病消除阶段的最佳策略。
3 当前防治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其造成的公共卫生危害也已显著降低,但要实现消除目标,仍然面临着较大困难和挑战。
3.1 传染源种类繁多,难以彻底控制 血吸虫病是一种人兽共患寄生虫病,传染源除人外,还包括牛、羊等40余种家畜和野生哺乳动物,其中牛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高达75%[40]。自2004年以来,我国大力推广实施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新策略,积极推进传染源控制关键措施的落实,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41]。但在一些流行区,牛、羊养殖是当地农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且耕牛仍是耕作的重要工具,而传染源控制措施的配套服务又未能跟上,导致牛、羊淘汰工作难度较大,传染源控制策略不能有效落实。此外,近年来调查显示,野鼠等野生动物在部分地区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目前我国对野生动物传染源尚缺乏有效的监测和防控手段,这给当前血吸虫病传染源控制工作带来了新挑战[42-45]。除动物传染源外,流行区的渔船民等流动人群也给传染源控制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他们接触疫水频繁、流动性大,是感染的高危人群,但有效管理存在较大难度[46]。
3.2 钉螺分布广泛,有螺面积压缩难度大 钉螺是日本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在血吸虫病传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与防治初期相比我国钉螺面积大幅下降,但近十年来现有钉螺面积一直在35 亿~38 亿m2徘徊,有螺面积下降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进一步压缩现有钉螺面积难度较大。现有钉螺面积主要分布在水位难以控制且植被较为茂盛的湖沼地区,还有一小部分呈点状分布在地形复杂的山丘地区,上述地区药物灭螺措施难以有效实施;再加上近年来血防综合治理项目减少、药物灭螺和水产养殖矛盾日益突出等,导致钉螺控制难度较大[47]。二是受洪涝灾害、苗木移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影响,钉螺扩散现象时有发生。2017年在江西省南昌市中心城区的滨江公园首次发现有钉螺分布,面积为12.9 hm2[48];2018年在上海市松江区非流行区的叶榭镇新发现有螺面积10.47 hm2[49];2019年广东省韶关市在连续30年无钉螺分布的情况下再次出现大面积钉螺分布[21]。此外,2020 年长江流域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其对钉螺扩散势必也会造成较大影响。
3.3 部分地区传播风险依然存在,防治成果尚不稳定 自2015年实现传播控制目标以来,我国血吸虫病疫情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由此部分地区也产生了松懈麻痹思想,防治工作力度有所减弱,导致疫情出现回升。如风险监测表明,一些地区的部分环境仍能查出可孵化出血吸虫毛蚴的阳性野粪,因此感染性钉螺出现的可能性较大,人、畜感染的风险依然存在;一些地区由于灭螺措施和疫情监测不到位,钉螺面积不降反升,甚至出现大面积回升;还有一些地区药物灭螺与水产养殖矛盾问题突出,部分有螺环境甚至是重点易感环境多年不开展药物灭螺,导致这些环境出现感染性钉螺的风险很大[50-53]。另外,随着疫情逐渐降低,流行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也逐渐淡化,尤其是渔船民反复接触疫水的现象仍较普遍,加之一些地方监测预警技术比较落后,不能及时发现钉螺扩散或疫情苗头,极易造成疫情发生[54]。
3.4 防治能力和防治技术仍显不足,难以满足消除工作的需求 近年来,随着血吸虫病造成的危害逐渐降低,一些地区对血吸虫病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再加上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推进,很多基层血防机构被陆续整合到疾控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被分流,导致防治力量有所减弱;与此同时,我国基层血吸虫病防治队伍目前普遍存在学历不高、能力不强、年龄老化、流失严重等问题,防治能力难以满足消除血吸虫病的实际需求[55-56]。此外,要想彻底消除血吸虫病,最终要依靠科技的进步。但我国血吸虫病科研能力远不能满足防治工作需要,一些制约防治进程的关键技术一直未能取得突破,尤其是现有的诊断技术漏检问题比较突出,已不能适应低流行状态下的防治需求;钉螺调查技术长期未取得进展,导致钉螺调查效率仍旧低下;风险监测和预警技术也较落后,监测体系敏感性不高[57]。而当前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正在从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变,急切需要更加先进和高效的防治技术,以适应消除进程中的实际需求。
4 如期实现消除目标的主要对策
当前,我国血吸虫病防治正处于攻坚制胜的关键阶段,针对在进一步推进防治进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今后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以确保2030年如期实现消除目标。
4.1 继续坚持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 自2004 年以来的防治实践和防治成果充分证明,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是适合现阶段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实际需求的。因此,在迈向消除血吸虫病进程中,必须继续坚持,并大力推进。与此同时,需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建立传染源控制长效机制,避免牛、羊淘汰后又出现复养,防止疫情回升。此外,要加强对渔船民等流动人群的管理,科学、合理地开展人群血吸虫病查治工作,进一步降低人群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同时,要继续做好钉螺调查工作,规范实施药物灭螺,进一步降低钉螺密度、压缩钉螺面积。当然,由于各地经济条件、主要传染源种类、疫情特点等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在实施传染源控制策略过程中,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
4.2 加强监测预警,防止疫情回升 防治实践表明,当血吸虫病疫情降低到一定程度后,防治工作的难度并不会随之降低,反而会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随着疫情的逐步控制,人、畜感染率和感染度均会出现下降,导致现有诊断方法和监测技术的检出效果也出现降低,进而造成传染源和传播风险不能被及时发现;二是当疫情处于较低水平时,血吸虫病的危害大大降低,流行区干部和群众对防治工作可能会产生松懈麻痹思想,导致防治工作的力度和效果大打折扣。而血吸虫病防治具有反复性的特点,工作力度稍有放松,疫情就有可能死灰复燃。因此,要在现有监测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监测预警系统的敏感性,同时加强对重点地区疫情传播风险的监测力度,及早发现并及时处置疫情传播风险,以巩固防治成果,防止疫情反弹[58]。
4.3 加强防治能力建设,研发防治新技术 以我国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的公共卫生体系改革为契机,加强医防融合,明确乡(镇)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血吸虫病防治职责,理顺管理机制,积极构建新型血吸虫病防治体系。此外,要加强血吸虫病防治队伍建设,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福利待遇,保持基层防治队伍相对稳定。同时,要积极开展血吸虫病防治知识和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的防治能力。消除血吸虫病的关键还是要依靠防治技术突破。因此,要摒弃传统的“重防治、轻科研”的思想,进一步加大科学研究力度。要针对当前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开展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联合攻关研究,加速研发新型防治技术和方法,争取在钉螺调查、血吸虫病诊断、监测预警等关键技术领域有所突破,从而为消除血吸虫病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59]。
5 结 语
血吸虫病是一种人兽共患的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反复性的特点。经过70余年持续不懈的努力,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当前正向着2030 年实现全面消除的伟大目标奋力迈进。在此进程中,尽管会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防治技术的进步,只要坚定信心、奋力拼搏,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消除血吸虫病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与此同时,我国在消除血吸虫病进程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先进防治技术,也必将为推动全球血吸虫病防治进程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