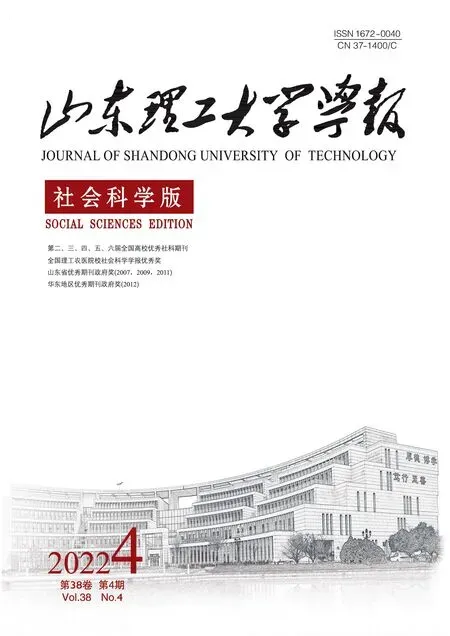齐国婚俗中的女性地位探析
石 志 丹
从蒙昧时代的群婚制到文明时代的专偶制,人类早期婚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婚姻形态和家庭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母系时代向父系时代过渡,女性的社会地位伴随着婚姻制度的变化逐渐降低。 至父权制绝对强化和稳固的周代,礼制兴起,男尊女卑制度确立,女性的社会生活空间进一步被禁锢,其从属地位更加明确,婚姻逐渐成为了女性的主要舞台,也成为了女性社会地位体现最为直接明了的所在。
齐国作为西周之初分封于东夷之地的诸侯国,其婚制基本遵从周王室,女性地位在整体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更加弱化,被奴化和物化的从属身份是其在社会与婚姻中地位的主要体现。 但由母系向父系的过渡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其间存在两者的斗争与反复,母系风俗在此时依然有一定的延续,齐国“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使东夷地区尊崇女性的旧俗得以留存,因而这时的婚俗与女性地位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女性一方面受到了严苛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又保留着一定的婚爱自由,甚至出现了两性之间较为混乱的现象。 此外,商工立国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纺织业兴盛发展,这给予女性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和较高的经济地位,皆在齐国婚俗中有所体现。 整体而言,齐国女性地位在主流婚姻形态中展现出符合时代的“卑”的特征,而在特殊婚俗、家庭经济及伦理观念等方面又呈现出区别于他国的独特性。
一、主流婚姻形态中女性从属地位之卑下
(一)从聘娶婚制看女性从属地位
在中国古代婚姻的发展历程中,“婚姻”一词出现较晚,陈顾远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婚姻史》中认为,“婚姻”称谓的出现较之男女嫁娶的事实晚许多,并采用东川德治《中国法制史研究》一书中“婚姻之称,似始于周代,周代以前称嫁娶,不称婚姻”为注释[1]6。 而周代“婚姻”之称的出现和婚姻形式的完备,与“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礼记·内则》说:“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2]985,可见,周礼的制定是始于男女嫁娶之事,《礼记·昏义》篇也提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2]1110,《礼记·郊特牲》则说“夫昏礼,万世之始也。 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2]977,说明婚姻之礼是诸礼之根本。 周礼甫一开始便对男女之别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对两者的思想和行为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准则。 换言之,“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3]82的维护父权利益的周礼,在两性界别的问题上,本质就是对奴化女性的合法化、社会化的许可。 作为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形式最为普及的聘娶婚,也兴于周代。 何谓聘娶婚?陈顾远先生在《中国婚姻史》中言:“聘娶婚者,男子以聘之程序而娶,女子因聘之方式而嫁之谓也。”[1]71聘娶婚源于原始社会的买卖婚,传说“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4],这种以财物缔结两性嫁娶的行为或可认为是买卖婚的一种表现。 后随着社会发展,买卖婚逐渐以聘娶的形式出现,因聘娶婚除买卖之实外,还具有契约性质,更加正规和文明,符合“礼”之需要,因此被周代确定为官方婚制。 一般认为,聘娶婚有三个重要的要素,即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和聘约。 尽管这一时期依然有抢夺婚、买卖婚间或出现,但多以聘娶婚的形式为伪饰,使婚姻的建立合礼化。 周代以后,聘娶婚成为社会主流婚姻形式。
齐国的婚嫁也以聘娶形式为主流。 关于齐国贵族的聘娶婚,史料有多处记载。 《左传·文公四年》载:“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 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曰:‘贵聘而贱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废之,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 不允宜哉。’”[3]583“贵聘而贱逆”中的“逆”为迎娶之意,意思是以尊贵的礼节行聘却以低贱的礼节迎娶,“贵聘而贱逆”正是关于聘娶婚的记载。[5]除此之外,《左传》还有多处记载,如“公子翚如齐逆女”[3]106,“齐侯来逆共姬”[3]206,“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3]949,等等,皆为关于春秋时期齐侯聘娶婚的记载。 关于平民的聘娶婚,则在《诗经》中有所体现。 《齐风》中有“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2]208的诗句,“必告父母”“匪媒不得”正体现了聘娶婚的两大重要因素。 战国时期,社会对于聘娶婚的重视进一步加深,表现为对媒聘的重视程度远超之前。《孟子·媵文公下》说:“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6]111《管子·形势解》也说:“妇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 故曰自媒之女,丑而不信。”[7]858可见,当时无媒而婚是被世人所耻的。由此可知无论在齐国的贵族还是平民中,聘娶婚都已成为被广泛认可而普遍实行的形式,居于主流地位。
聘娶婚制是我国婚姻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开始,对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的存在使男女双方家庭缔结的婚姻具有契约性质,从而保护了婚姻的稳定性、合法性和社会信用度,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男女嫁娶而造成的社会纷争,对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就女性地位而言,聘娶婚制无疑体现了女性地位的从属性与被动性。
其一,就针对女性制定的规则而言。 《仪礼·丧服》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2]788这句话清楚地宣告了女性的从属地位。 女性并不作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依附于男性的附属品,其所有权,在成婚前归属父家,成婚后归属丈夫和儿子,聘娶婚事实上是男方通过聘礼的形式将女性所有权从其父家买断,名正言顺地占有女性的形式。
《礼记·内则》说“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 聘则为妻,奔则为妾。”[2]987按照《礼记·内则》的记载,男子二十岁时加冠,开始学礼,三十娶妻,一生应广博地学习各种知识,广交朋友,出仕参政,其行为多规范于社会属性之中。而女性则不同,女性长到十岁就不能像男孩子那样外出,必须待在家里由女师教导,学习品德言行、纺织女红以及祭祀礼仪等。 女性十五岁,举行笄礼,表示已成年,二十岁可以出嫁,如有特殊原因,可推迟到二十三岁。 这段话明确了男女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和行为准则。 在周礼兴盛的时代,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大致为两个主题,出嫁之前为“男女有别”,出嫁之后为“男尊女卑”,完全被压制在父权制度之下。 这样的规定几乎否定了女性的社会属性,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中。
所谓“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是说女性如果在举行了聘娶的礼仪和程序后成婚,那就是婚姻里的正妻,其婚姻地位才能得到社会认可,但如果是无媒无聘而自行成婚,那就是地位非常低下的贱妾,将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以及双方家庭的认同,齐国即是如此。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缗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8]3709又载“襄王(法章)既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是为君王后,生子建。 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 终身不睹君王后。”[8]3710太史敫的女儿因无媒无聘而与落难时的法章成婚,尽管法章最终继承齐国国君之位,太史敫之女被立为王后,即君王后,但太史敫始终对女儿不守礼仪而成婚的事耿耿于怀,一生没有再见她。 然而这样的规定,却仅为对女性的单向要求,妻与妾的地位天差地别,但男性在这样的规则中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约束,并没有两种不同身份,即便不经六礼和媒聘,也依然拥有一夫一妻多妾的权利。 女性在聘娶婚制中的从属地位由此可观。
其二,就嫁娶之礼而言。 首先,在当时的齐国乃至各诸侯国,男女结为夫妇,皆以男子为“本位”。 《礼记·昏义》记载“昏”原文作“昬”,说的是古人成婚在黄昏时候,汉代郑玄注:“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孔颖达疏:“男以昏时迎女,女因男而来。 嫁,谓女适夫家。 娶,谓男往娶女。”[9]古籍记载中的“逆女”“归于”“归家”等等表述体现出婚姻对男子而言是“娶进来”,而对女子而言为“嫁出去”的观念。 女子出嫁后居从夫家,其本身也作为财富的一部分,连同其陪嫁之物一同归属于夫家。 其次,在嫁娶之礼的执行中,女子为被动一方。 关于周代婚姻礼仪,“婚礼有六”的传统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事实上,关于周代婚礼,有不同的说法。 《春秋榖梁传·庄公二十二年》载“礼有纳采,有问名,有纳徵,有告期,四者备,而后娶,礼也”[2]1804,以此观之,婚礼有五;《仪礼·士昏礼》和《礼记·昏义》中则都记载婚礼有六,分别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迎娶。 郑玄之后,六礼之说被公认为周代婚礼的规范,但学界对此观点不一,陈筱芳在《春秋婚姻礼俗与社会伦理》一书中认为,根据春秋经传所载之史,春秋时期婚姻礼俗仅为聘(又名委禽)、纳币(又名成昏)和逆(迎娶)三礼[10]。 关于礼者几何的问题,学界或存争议,但婚姻之礼由男子主导,女性居于被动一方,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每一项仪式皆由男方掌握主动权。 以齐国迎娶之礼为例,“逆妇姜于齐”“公子翚如齐逆女”“齐侯来逆共姬”皆为男子迎女子回家,表达出了“男先于女”的思想,也体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被统治地位。
(二)从媵婚制看女性的从属地位
媵婚制是一种通行于周代贵族阶层的陪嫁婚制,是侄娣陪嫁,以妾的身份与姑、姐共同嫁与同一男子的制度。 媵婚是一夫一妻制之下,男权对于一夫多妻事实的伪饰。 媵的本意,为送。 《尔雅·释言》道:“媵,将,送也。”[2]2189《仪礼·士昏礼》中有“媵御馂”[2]650一说,媵为女方陪嫁的女子,御为男方服侍的女子,“媵御馂”意为媵和御吃主人吃剩的食物,郑玄注曰:“古者嫁女必以姪娣从,谓之媵。”初时之媵“不惟以女,且复以男”[11],如《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乃为有莘氏媵臣”[8]151,说的是商汤辅臣伊尹原本就是媵臣身份。 可知,媵婚最初为送婚,后发展为陪嫁婚。 学界一般认为媵婚起源于族外群婚,应出现较早。 《尸子》记载唐尧将两女嫁与虞舜的事情:“妻之以媓,媵之以蛾”[12],《左传·哀公元年》载,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3]1792,说的是夏代两姐妹嫁给了少康。 商代帝乙归妹之事,也普遍被学界认为是媵婚形式。至周代,嫡长子继承制确立,需建立起与之对应的嫡庶妻等级制度,因而媵婚制发展为当时的重要婚制。 春秋是媵婚的鼎盛时期,文献所记载媵婚史实很多,仅《左传》所记载的媵婚为四十余处,绝大多数记载发生在诸侯国的联姻之中,可见当时媵婚十分普遍。 到战国时,随着宗法制、分封制的瓦解,媵婚逐渐衰弱和消亡。
齐国的媵婚亦有多处记载,《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 其侄鬷声姬,生光,以为大子。”[3]1153《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以藩载栾盈及其士,纳诸曲沃。”[3]1182成公八年宋华元聘伯姬,九年晋人来媵,成公十年《经》曰: “齐人来媵。”[3]926此外,《诗经》中也有对于媵嫁之礼的描述,《齐风·敝笱》中有“齐子归止,其从如云……齐子归止,其从如雨……齐子归止,其从如水”[2]209的诗句,描写齐国女子出嫁时,众多陪媵和送亲之礼的盛况。
《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载:“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 姪者何?兄之子也。 娣者何? 弟也。 诸侯壹聘九女,诸侯不再娶。”[2]1615《左传·鲁成公八年》载:“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3]918。 这些记述历来被学界作为研究媵婚制的主要依据,但这两处记载与史实多有不符,齐国的婚嫁记载就有许多与之相悖之处。 如诸侯娶妻人数问题,根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8]3656齐王田常为篡夺姜氏齐国,娶了一百多个七尺身高的健壮女子,生下七十多个儿子,最终真的夺权成功,建立田齐政权。 可见齐侯并未按照“诸侯壹聘九女”的方式娶妻。 再如“同姓媵之,异姓则否”的问题,《左传》所记载齐国的媵婚明显都违背了这一准则。 除齐国之外,各诸侯国一娶再娶、异姓往媵、多国来媵的例子比比皆是。 原因为何? 其主要原因应当是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周礼的约束力越来越小,各诸侯国都将利益放在首位,通过联姻的方式获得政治联盟,媵的人数、方式自然是根据本国需要进行设置。 可见,媵婚本质上即是服务于男权的政治工具,而女性多为牺牲品。
关于媵的地位,可从几个方面加以探析。
就政治属性而言,媵具有一定的与其身份相应的政治地位。 媵婚为贵族婚制,作为媵的女子也多出身贵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母国的利益,因此一般不会受到过度的苛待。 她们与陪嫁的主嫁女虽有主妻和次妻之分,但地位比妾要高。 主嫁女和媵作为利益共同体,往往共荣共损。 若主嫁女过世,媵有资格作为继室,若主嫁女无子嗣,媵之子也有资格作为承继,这在“其侄鬷声姬生光,以为大子”等记载中可以探知。
但就人格属性而言,媵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其一,周礼对媵制定了诸多规范,如《仪礼·士昏礼》中“媵布席于奥”“媵、御沃盥交”“媵衽良席在东”“媵馂主人之余”[2]648,等等,可见尽管媵具有高于妾的地位,但在婚姻生活中依然处于服侍主人的地位,其本质为奴。 其二,在政治婚姻的圈层下,媵是主嫁女的附属品和陪嫁物,她们仅仅作为政治和生育的工具,毫无独立人格可言。 在父权社会中,女子本已是男性的附属品,即便作为主嫁女也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媵作为附属品的附庸,其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 因与主嫁女是利益共同体,因此不仅没有选择婚姻的权利,甚至当嫡妻与夫家关系破裂而被出妻时,媵也要一同被出。 《左传·文公十二年》中有这样的记载:“杞桓公来朝,始朝公也。 且请绝叔姬而无绝昏,公许之。”杜预注:“不绝昏,立其娣以为夫人。”[3]641这是一处关于夫妇绝婚,嫡妻被出,媵继为夫人的记载。 将其单独标注,或可说明此事为一例外,“绝婚”一事的常规操作即为媵随嫡妻一同被出。 尽管齐国并无此类记载,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媵婚之制在各诸侯国应是相通的。 其三,这种多妻制从开始就将女性圈禁在一种狭促的被奴役的空间里,女性之间存在地位、名分、财物、性爱等多种矛盾,不得不更深层次依附于男性,通过子嗣等方式换取自身需要,女性地位越来越低,最终完全变为男子的附庸和奴役对象[13]。
总之,周代媵婚制是为了构建嫡庶妻等级制而形成的婚制,是男尊女卑制度下的产物,也是一种男性对女性单向的、不平等的控制和占有,目的在于维护男权的统治。 从原始群婚到封建婚制的文明进步,伴随着女性地位的持续下降。
(三)从政治联姻看女性的从属地位
两周时期,诸侯国之间的联姻都是政治联姻,各国通过联姻形式建立起政治、军事联盟,而在列国的政治联姻中,齐国始终居于重要地位,其联姻之事十分活跃。
西周时期,“周齐世婚”的特点十分突出。 周武王的王后为齐国君主姜尚之女,名邑姜,自此开始,西周共有13 位王后来自齐国,几乎每隔一代周天子就会娶一位姜姓女子[14]66。 因此《史记·周本纪》记载春秋时期齐襄王以上卿的礼节接待齐国国相管仲,并称呼齐国为舅国,“王曰:‘舅氏,余嘉乃勋,毋逆朕命’”[8]294。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弱,齐国与周的联姻明显减少,有明确记载的大致为几处,《春秋》载庄公元年:“王姬归于齐”[3]170,《春秋》载庄公十一年载:“冬,王姬归于齐”[3]202,《传》云:“齐侯来逆共姬”[3]206,《左传·宣公六年》载:“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齐”[3]751,“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齐”[3]752,《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官师从单靖公逆王后于齐。”[3]224春秋时期,齐国与鲁国的联姻较为密切,《左传·哀公二十四年》载鲁国礼官的话“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3]1925,因此又称为“齐鲁世姻”[14]68。 除了与周王室和鲁国的联姻,齐国的联姻之国非常多,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主要诸侯国[15]。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联姻,如《列女传·贤明传》 载:“周宣姜后者,齐侯之女也”[16]56,《左传·隐公三年》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3]33,等等。 春秋早期,在广泛联姻的作用之下,齐国对列国政治形势和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推进,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诸侯国由春秋初年的一百八十一个缩减至战国初期的二十余国[14]201,这一时期齐国联姻的记载较少,但位列战国七雄,齐国联姻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更加明确,以大国外交为主。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湣王……四年,迎妇于秦”[8]3688,说明田齐与秦国有过联姻。
政治联姻多是各诸侯国之间政治、军事等方面角逐较量的辅助手段,女性作为联姻的当事人,实则是诸侯国外交的礼物与筹码,也是各国在进退之间的权宜之所在。 一方面,作为国际外交的关键人物,联姻的女性拥有一定政治地位,既是族邦稳定的主要因素,又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另一方面,联姻女子的使命即是维护所系诸侯国的利益,而毫无情感可言,在联姻中失去了对生活选择的权利,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丧失了生命。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庄公的夫人哀姜,因与庆父私通,引发国人暴动,逃到邾国,后被齐国引渡回国,却不想被母国杀害,并将其尸体返还于鲁。 哀姜的悲剧固然以其自身品行不端为诱因,但作为一枚政治联姻和诸侯邦交的棋子,她对于母国与夫国而言,都仅仅只是一件工具,其悲剧的发生也有极大的必然性。
(四)从“同姓不婚”看女性从属地位
《礼记·曲礼上》言:“取妻不取同姓”[2]887,“同姓不婚”是自周代开始整个中国古代普遍实行的婚姻禁忌制度,它源于周族与姜姓族、姞姓族、任姓族、姒姓族等的联姻[14]28。 母系时代晚期,对偶婚产生之时,已经出现了氏族禁止族内通婚的制度,开始实行族外婚制,当时的同族即意味着同姓,族外婚即为“同姓不婚”,这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至周代,“同姓不婚”被提升到礼制高度,成为服务于宗法制的制度。
据现存文献来看,齐国婚嫁尽管出现了两例“同姓相婚”的个例,分别是棠姜嫁崔杼和庆舍之女嫁卢蒲葵,但就整体而言,是遵循和符合“同姓不婚”规则的。 古籍文献中,并没有出现齐国君主娶同姓女子的事件,而齐国女性也皆嫁给了异姓国君,如文姜嫁给了鲁国国君,齐庄公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皆为姜姓的卫国、邢国、谭国国君等。
为什么“同姓不婚”体现了女性地位的从属性?
首先,从“同姓不婚”的目的来看。 “同姓不婚”成为制度,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 《礼记·郊特牲》:“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附远”是说通过联姻与血缘与他国建立合作同盟;“厚别”是说禁止同姓相婚,避免造成纲常秩序的混乱。 “同姓不婚”即为“附远厚别”的重要内容,通过联姻和他国建立姻亲关系,并对这样的邦交优势加以充分利用。 东周时期,诸侯国公子向舅国求助的案例比比皆是,如齐国公子纠在争夺君位时回母亲的国家鲁国求助,卫惠公逃难至母亲的国家齐国,在齐襄公帮助下起兵复立,等等。 可知男性政治联盟的搭建和政治利益的实现皆包含了对女性价值的充分利用。
其次,从女性生育地位来看。 姓是母系社会的产物,所以至今许多姓都带有“女”字,如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姚、妊,皆以“女”字为部首,姓的存在是为了区分部族。 女子之姓在母系观念较重的时代并不会被刻意强调,如商代很长一段时期中女子并不称姓,女子之名与男子同用干支,如妣甲妣乙、母甲母乙之类,因此无所谓是不是“同姓不婚”。 但到周代,大姜、邑姜、大姒等等女性皆已称姓,可见殷周之间男女地位发生了巨大转变。 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年代,女性在生育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生殖能力受到尊崇。 在母系时代,人们的婚配只需要排除母方的亲属即可,且对于母系亲属的辨别十分简单和直观,不需要刻意强调是否为同姓。 但进入父系社会,尤其周代以后,男性的生育功能被片面性强化,父权和宗法制的统治之下,男性的血统被定义为尊贵,而女性的生育功能及地位则逐渐被轻视甚至忽视,因此父权制下普遍认为只要避开父系血亲即可进行婚配[14]30,而母系亲属则无关紧要。 但避开父系亲属的方法不像区分母系亲属那么直观,尤其在宗法体系之下,父系家族往往是人员众多、等级庞杂、关系繁复的大家族,很难简单地以血缘进行区分,因此只好以宗族共同的姓作为标准,所以“同姓不婚”被强调,甚至上升到制度的高度。 生育地位的下降直接说明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同姓不婚”制度的形成体现了女性地位的低下。
(五)从“出妻”看女性从属地位
“出妻”即丈夫休弃妻子。 《孟子·离娄下》说:“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6]166,《荀子·解蔽》说:“孟子恶败而出妻”[17],《仪礼·丧服》说:“出妻之子为母期”[2]787,皆有“出妻”的说法。 春秋战国时期,男子“出妻”十分普遍,女性在婚姻存续与否的问题上并没有太多话语权,除战国时期的秦国制定了“出妻”需要到官府登记的政策之外,其余诸国的“出妻”都十分自由和随意,甚至可以任性而为,齐国自不例外。 《左传·僖公三年》记载:“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 公惧,变色。 禁之,不可。 公怒,归之。”[3]313归妻,即为休妻。 意思是齐桓公和夫人蔡姬在泛舟游玩,蔡姬顽皮,摇晃着小舟与齐桓公玩闹,齐桓公因胆小而吓得脸色大变,一怒之下,仅仅因为一个玩笑而将蔡姬休弃。 《管子·小匡》记载,管仲建议“士三出妻,逐之境外。 女三嫁,入于舂谷”[7]385,明确提出限制夫妻离婚、再婚,或可见当时“出妻”现象之频繁。 但这一规则,在限制男性“出妻”的同时,也对女性的再婚提出了限制,可见这一规定只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并非出于对女性的保护。
战国时出现了“七出”之条。 《大戴礼记·本命》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这为当时男子休弃妻子提供了七条正式理由。 尽管在一定意义上说,“七出”与《大戴礼记·本命》所载的“三不出”(即: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18])约束了男性随意“出妻”的行为,在保护女性方面产生了一定积极意义,是一种制度的进步,但究其根本,依然是男权社会的产物。 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制、分封制的瓦解,大家族逐渐弱化,小的家族和家庭兴起,一夫一妻为主的家庭逐渐成为主要形态,因此家庭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夫权凸显出来,男女之间的地位悬殊体现更为直接和具体,“七出”的提出正是符合这种夫权需要的。
女性被丈夫离弃,除了“出妻”之规,还有更加残忍的方式,有时连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战国策·齐策一》记载:“章子之母启得罪其父,其父杀之而埋马栈之下。”[19]255另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是鲁国臣子,齐国攻打鲁国的时候,因妻子是齐国女子而遭到鲁王怀疑,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8]4502。 生命尚且随手可夺,足见当时女性地位实是卑微至极。
二、特殊婚俗中女性母系地位之遗存
(一)“巫儿”习俗
根据史料记载,“巫儿”是齐地独有的婚俗。《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记载:“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20]1482。 这一记载是历史文献中对于“巫儿”一词最为清楚的解释,但历来在学界存在许多争议,如齐襄公与姑姊妹的关系是否为“兄妹婚”;“巫儿”习俗是否真的存在;齐地长女是否皆不外嫁,而须居家主祀;“巫儿”的身份究竟为何;“巫儿”现象在贵族与平民中各自的体现为何;“巫儿”居家主祀,其地位究竟如何,等等,受史料所限,“巫儿”婚俗历来争议颇多,这些问题大多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故不详述,仅试从母系遗存角度对“巫儿”进行论述。
首先,“巫儿”习俗在齐国应为真实存在。《战国策·齐策四》记载,赵威后问齐国使者:“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 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又载:“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19]328有学者认为“至老不嫁”的女婴和“邻人之女”即为“巫儿”。 “巫儿”习俗的产生源于母系时代的婚姻制度。 “姑姊妹婚”是母系时代群婚制的遗存,多夫多妻制时期众兄弟姐妹皆可为婚,而在由母系向父系过渡的时期,这样的旧习依然少量存留在人们的婚俗之中。 但齐襄公与文姜各自皆有婚配,二人的行为并不属于“兄妹婚”的性质,而应当属于婚外私通,所以在当时并不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 旧的制度仍在产生影响,发生了姑姊妹不嫁的混乱现象,后来演化成“长女不嫁”的习俗[21]。 但这一遗存到春秋时期已经弱化,不再是社会普遍现象。
其次,“巫儿”居家主祀的习俗源于母系时代。 “巫”在原始社会的部落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对性别的选择为“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说文》曰:“巫,祝也。 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所谓“事无形”,即指看不见的鬼神,那时的人们认为女子可以侍奉神秘的、难以具象的事物,因此女性在“巫”的领域十分重要。 《周礼·春官·女巫》记载,巫的职责在于“掌岁时祓除、衅浴。 旱暵,则舞雩。 若王后吊,则与祝前。 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2]501。 《礼记·檀弓下》载:“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 于以求之, 毋乃已疏乎?’”[2]921说的是天旱之年鲁穆公欲通过暴晒女巫以求雨。 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女巫的地位遭到了男权力量的打击,但依然保留一定影响力,尤其东夷地区尚母的习俗影响之下,“巫儿”习俗在齐地保留下来。 在现今为止出土的齐国铜器中,有一铜器名为“齐巫姜簋”,其铭文记载:“齐巫姜作尊簋,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宝享用。”[22]这证明齐“巫儿”有较高的地位。 但“巫儿”所主的祭祀内容应当是有所局限的,《春秋公羊传·哀公六年》载“陈乞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愿诸大夫之化我也’”[2]1756,或可认为,其祭祀为宴饮祭祀。 按照周礼的规定,当时的祭祀,应以男子为主,女子为辅,国家、宗族等重要的祭祀活动应为男子主祭,而女性祭祀应多局限于家庭范畴[14]157。 可见,当时由母系时代延续而来的“巫儿”习俗尽管依旧没有消失,但早已不再是社会主流形态,仅为特殊现象。
再次,“赘婚”现象为母系时代遗存。 上文所载“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一事被普遍认为与齐国“赘婚”现象相关。 女子被选择为“主祀”之人,以婚嫁之权交换主祀之权,但不代表她不能进行婚配及生育子女,而是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进行,比如“赘婚”。 男子“入赘”女家本是母系时代以女子作为婚姻核心而形成的风俗,周代以后,这种风俗仍有保留,齐国尤其突出。 《战国策·秦策五》载:“太公望,齐之逐夫。”[19]231“逐夫”即为赘婿。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8]7385姜太公和淳于髡两位齐国名人皆为赘婿出身,可见齐国的“赘婚”现象在当时并不鲜见。
(二)“烝报婚”
“烝”婚制是指父亲死后儿子继娶继母与庶母为妻的婚姻形式,“报”婚制则是发生在旁系亲属之间,如叔父或兄长死后,侄娶婶母或弟娶寡嫂的婚姻形式。 “烝报婚”继承自原始社会的收继婚,又叫转房婚,是母系时代晚期随着对偶婚制形成而产生的婚姻形态,在古代各民族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左传》中提及了五“烝”一“报”共六事,与齐国相关的皆为“烝婚”。 分别为: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3]157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娶于贾,无子。 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3]260闵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 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3]291。 “烝报婚”是两种特殊的婚姻形式,为后儒所批判,被称为“淫”。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说:“上淫曰‘烝’……夷姜或是庄公妾,为宣公庶母。 宣公与夷姜通奸。”但顾颉刚先生认为,“烝报婚”是春秋时期十分普遍的家庭婚姻形态,带有原始婚姻的痕迹,为当时社会所普遍认可[23]。
转房之后的女性在婚姻中依然具有较高的地位,可以位列正妻的身份,如上文所述夷姜、宣姜皆是如此,其子女也享有与其他子女相同的地位,可以承袭君位,如宣姜和昭博“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五个子女中有两个儿子做了国君,两个女儿成为了国君夫人。 尽管春秋时期,“烝报婚”本质上是维护父权地位的婚姻形式,是一种继承来自女方氏族财产的方式,女性大多没有自主选择是否进行“烝报婚”的权利,但女性在这种婚姻制度中的地位,明显有别于后世女性改嫁所普便面临的被区别以待的境遇,除了因为东夷传统和齐国独特民风等因素之外,还或可理解为在向父系过渡时期,母系婚俗和女性较高地位的延续。
三、家庭经济中女性主体地位之明确
齐国女性地位区别于他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齐国女性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
周王朝以农耕立国,农业生产倚重男耕,女性依附于男性,这成为了周代女性地位下降的物质原因。 诸国之中,唯独齐国与众不同。 齐国统治者自立国之初,就根据实际国情选择“因其俗,简其礼”,制定了可以充分发挥齐国优势的经济方针。 《史记·货殖列传》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 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8]7559《汉书·地理志下》载:“太公以齐地负海潟卤, 少五谷而人民寡, 乃劝以女工之业。”[20]1481《盐铁论·轻重篇》也载:“昔太公封于营丘……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24]姜太公在立国之初就制定了大力发展纺织业的经济政策,因此齐国“女工之业”极为发达,“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以至于成为纺织业中心。 而纺织业的开展以女性为经济主体,女性的纺织劳作为齐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齐国女性在具有相对独立的劳动地位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家庭经济地位,这使她们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对于男性的依附性。
经济的相对独立,使女性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两周时代处于父权兴起的时代,女性地位被礼制所严格限制,《礼记·内则》关于女子财富的规定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2]981,剥夺了女性的经济权利,使其不得不依附男性。 但齐国女性却呈现出与主流规制并不一致的独特性,她们拥有一定经济地位,呈现出较之他国女性更加开放、活跃的特点。 齐国独有的“巫儿”习俗的存在,以及“赘婚”等现象的突出皆是与齐国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密不可分的。
四、伦理观念中女性开放自主之推测
(一)对爱情的追求
如前文所述,两周时期聘娶婚已成为社会主流婚姻形式,但因去古不远,男女的恋爱和婚姻尚且留有宽松自由的空间。 自由恋爱在平民之中较为常见,《诗经》中有大量关于爱情的诗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等等。
齐国女性追求爱情的主动性十分突出,这不仅局限于平民之中,还体现在出现了跨越阶层的爱情追求。 据《列女传》记载,齐国传奇女子钟离春,相貌丑陋,却极具才能,她主动请见齐宣王,欲入宫为后妃,以隐喻的方式指出齐宣王执政问题所在,吸引了齐宣王的注意,最终成为了王后。《列女传》还记载,齐国即墨有孤逐女与齐襄王对谈国事,凭借其超凡的谈吐、不卑不亢的态度和卓越的见地最终嫁给了齐国国相为妻。
可见,尽管在“聘娶婚”这一主流婚制下,女性情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但在齐国特殊的风俗和经济特点等因素之下,齐国女性依然表现出追求爱情的意愿和勇气,或可理解为其开放自主的群体性格特点。
(二)贞节观与改嫁
两周时期贞节观已经出现,《仪礼·丧服》道:“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二斩也,犹曰不二天也。”[2]788《国语·鲁语下》对女性有“妇不淫”[25]的告诫。 《管子·五辅》也言:“为人妻者,劝勉以贞。”[7]181贞节观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禁锢的要求,以此来强化父权时代的婚姻伦理观念。 对女性来说,这是一种单向的、不平等的约束,也是女性地位沦落最直接、最冷酷的表现形式。
这一时期,女性地位普遍较低,但还没有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女性受到的约束和禁锢也相对较小,与后世相比还有一定的自由度。 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贞节观、“从一而终”的言论,但女性的贞节观念还比较淡薄,社会对此包容度也较高,尤其在齐地独特的历史遗风和经济政策之下,齐国女性的婚外恋、再婚现象较为常见。 齐襄公与文姜的私通、棠姜在丈夫过世后改嫁崔杼、蔡姬被齐桓公“出妻”后改嫁他国等,皆为例证。
(三)女性智慧的展示
《诗经·陈风》有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齐国女性被各国男子视为“佳偶”[26],这在当时应是一种共识。 齐国女性的出众,除容颜俊美之外,还体现在其政治格局、生活智慧、勇气与口才等方方面面。 《列女传》中有多篇相关记载,如齐姜施计将沉迷于齐国安乐生活的丈夫重耳带离齐国,助他复国,建立霸业;管仲的妾婧凭借丰富的生活智慧巧解“白水诗”,辅助管仲招揽了人才宁戚;杞梁妻在郊外迎接丈夫战死的尸体,通过有理有据的表达说服齐庄公前往家中为杞梁吊唁,等等。 这些女性智慧的展示一方面是依靠才能的蓄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齐国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敢于表达、敢于追求、敢于作为的主动性,以婚姻的视角展示了齐国女性的开放、独立和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