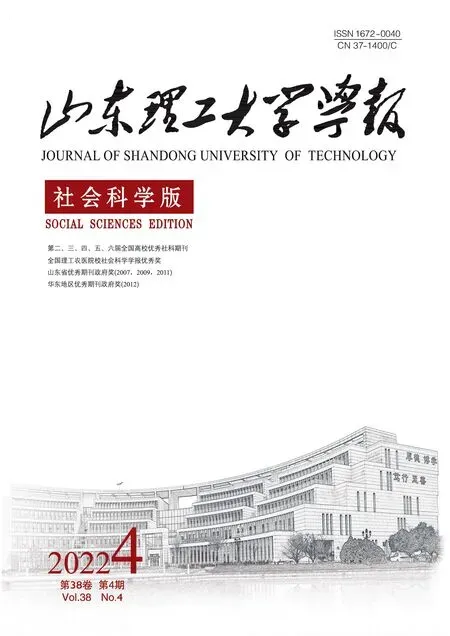全形拓艺术的历史传承与发展趋向探究
孙 超
一、全形拓的发展渊源
传拓的历史悠久,《隋书·经籍志》载:“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1]今存最早的拓片为唐太宗的《温泉铭》碑拓,永徽四年(653)制。 “皇祐三年(1051),诏命秘阁及太常,把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棰拓以赐宰相……。 清嘉庆以后,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始据自藏之器拓墨并合各家拓本而辑成,拓本才被人们重视,开了吉金拓墨风气”[2]105。
全形拓又称立体拓,是在金石平面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够以墨传拓青铜器的拓片形式,它能够全方位、立体形象地展现青铜彝器的造型全貌。 全形拓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今见最早的全形拓片为释六舟拓制,其在《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中记载始拓全形的时间为道光十年(1830)。 全形拓分为“全纸拓”与“分纸拓”两种,代表作为陈介祺的《毛公鼎》。 其后,周希丁、马子云将全形拓推上了新的高峰。
全形拓对先秦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的尊崇,是其“传古”思想的重要体现。 这种追根求源的历史精神,也体现了这一艺术门类对中国文化源头的尊崇。 从历史承传角度讲,全形拓的“传古”思想,主要传达古圣先贤之精神,探求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陈介祺曾言:“至文王、周公,极世之文。至孔子,极人心之文。 至秦燔,而自古圣人之所以文斯世之言与世荡然矣”[2]102,“好古文儆徇玩物,明至理耻动机心”[2]103,对先贤至理的探求,实为其金石传拓的本心。
全形拓始于清代嘉庆年间,其产生与清代金石学的兴盛密切相关。 而金石学正是在清代“存古”“传古”的时代风气下发展壮大的,是学术界的主流。 晚清学者总结金石学有两个派别:一是“覃溪派”(翁方纲为代表),其主张精购旧拓,讲求笔意,属于赏鉴家一类。 其源头出自宋人《法帖考异》《兰亭考》等书,翁方纲是金石鉴赏派的代表人物,其后的学者有康有为、叶昌炽、沈增植、李瑞清等人。 二是“兰泉派”(王昶为代表),其主张搜采幽僻,援引宏富,属于考据家一类。 其源头出自宋人《金石录》《隶释》等书①缪荃孙:《王仙舟同年金石文钞序》载:“国朝谈金石者有二派:一曰‘覃溪派’,精购旧拓,讲求笔意,赏鉴家也——原出宋人《法帖考异》、《兰亭考》等书;一曰‘兰泉派’,搜采幽僻,援引宏富,考据家也——原出宋人《金石录》、《隶释》等书,二家皆见重于艺林。 惟考据家专注意于小学、舆地、职官、氏族事实之类,高者可以订经史之讹误,次者亦可广学者之闻见,繁征博引,曲畅旁通,不屑以议论见长,似较专注书法者有实用矣。”参见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文海出版社,1966 年版,第9 页,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5 辑 945 册。。
在全形拓技艺快速发展的乾嘉时期金石文化圈,大致可分为“浙江金石圈”与“京师金石圈”。“京师金石圈”的组成以潘祖荫为中心,汇集了江苏、山东及京畿等地区。 “浙江金石圈”的组成以阮元为中心。 由于金石文字的研究对于经史、小学的研究大有裨益,是乾嘉学者考据的重要资料,故而,带有金石铭文的青铜器物弥足珍贵,便成为以“传古”为目的的全形拓学者的首选目标。
“金石学的发展带动社会收藏金石风气,访碑、拓碑的活动增多,金石拓本随之丰富,增加了多种金石材料……使得社会的‘传古’、‘嗜古’的社会氛围浓厚”[3]。 因此,全形拓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与“存古”“传古”的学术取向紧密相联,它实为清代金石学的衍生物。
今见最早的全形拓拓片为释六舟拓制,徐康《前尘梦影录》记载,全形拓这门技术,创自马傅岩,六舟得其传:“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 浙禾马傅岩能之, 释六舟得其传。”[4]
金石学的兴盛是在清政府大兴文字狱的历史大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 由于文人士大夫的才智抱负无处伸展,郁积于胸,要找寻路径寄托情怀,由托古传情转向金石学研究,则是他们的重要选择方向之一。 他们通过研究金石文物,虚拟盛世蓝图,心中追溯、重现曾经辉煌的历史,聊以自慰,沉浸其中,并籍此挖掘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探本求源,启智修身。
齐鲁大地在存古、访古、追古的大风气下,成为一个金石研究的聚集地,齐鲁文人购买、收集、交流金石彝器蔚然成风。 陈介祺在致吴大澂信中这样描述道:
格今近妄,然负贩求之于乡,牧竖求之于野,能使三千年上文字之在瓦砾者,裒而传之,此亦归里数十年真积之力,从此齐鲁人人心中知有此事,则古文字所全多矣[5]9。
然而,金石彝器的实物或大或小、或轻或重,易碎而不易搬迁,远远不能满足金石研究者的需求与交流,因此,将古器物化身万亿的全形拓技术便应运而生。 全形拓以“传古”为取向,承载着中华古代的文明,能最大程度地展现金石彝器的全貌,成为追溯古代文化的真面目、探求古代文明之源的重要载体,这应是全形拓产生的初衷。
二、全形拓的发展流变——从“传古”到审美
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清代中叶青铜器大量现世,私家收藏青铜彝器蔚然成风,收藏家之间的研究交流十分活跃。 由于收藏者们相隔甚远,实物精贵沉重,加之交通不便,收藏的实物难于进行交流、欣赏,需要有相应的传播载体。 原先的平面拓法无法全面真实地再现器物原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全形拓这种传播载体,经过文人们的探索开发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当推清代学者陈介祺。 叶昌炽《语石》载:
叶书盛称陈簠斋拓法为古今第一,簠斋与吴子苾承刘燕庭之后,日事毡蜡,讲求益精,东州好古者传拓金石,悉宗其法。 若王文敏、丁陶斋之于彝器碑版,高翰生之于砖瓦,王念庭之于泉币,纸墨皆与寻常不同,晚近名家守其法者周季木也。 季木所招宾客为之拓金石者,多黄潍两县人,得簠斋之真传,是周氏拓本,一望而知为齐鲁间之法也[6]。
陈介祺与拓工姚学乾、田智缗、姚学桓、胥伦等人经过反复的研究,力求精益求精,使得全形拓的技法更加完善与系统,深受金石书画爱好者与大雅之人的青睐,极大地满足了文人们对金石彝器传播、收藏、研究与欣赏的多种需求。 因此,“传古”的需求,应为全形拓产生的初始动因,这既与金石学的兴盛有着共同历史初衷,也是时代风气所衍生出的逻辑必然。
借用晚清学者对清代金石学的分门别派,全形拓的发展也可分为以“存古”“传古”为目的和以审美鉴赏为目的的两条流脉——“传古”派与“取象”派。 金石收藏家中,“传古”派的代表人物为陈菽园、陈介祺等,与之有一定关联的人物还有张廷济、何绍基、阮元等人。 力求真实,是他们制作全形拓的宗旨。
陈介祺认为在“传古”中,从文献到文献,从文本到文本的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实物器皿却可以立体全方位地为人感知与理解。 “探解圣人之心,追求圣人之道,是其共同的思古情怀”[2]102,“我辈好古,皆有真性情真精神与古人相契,方非玩物丧志。 夸多斗靡,与玩珠玉无异。故必重在文字,尤重有真知有思古获心之喻也”[2]103。 陈介祺否认了此项事业的娱乐性(与之相反,以审美鉴赏为宗旨的全形拓便有此种趋向),而着重强调其对圣人之道的追索。 正可谓“好名之心不必有,传古之志不可忘”[7]。
“传古”中的全形拓传拓活动是一个多工序、按严格程序相互合作的过程,陈介祺的传拓思想是“传古”,他在传拓方面研究颇深,著有《传古别录》,这是第一本关于拓字的专门著述。 陈氏对传拓的工具、材料、选纸、剔字、去锈、护器、上纸、施墨、棰按等均有详细的说明,对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他将全形拓的技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陈介祺对传拓每个环节的要求非常高,可谓达到了严苛的地步。 全形拓从制作到汇总的流程,按照先后次序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辨伪、剔字与去锈。 全形拓中,以“传古”为目的的主要传拓对象是青铜器,也就是金石中的“金”,器物中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十分珍贵,故而成为全形拓传拓的首选对象。 第二阶段:传拓阶段。 传拓的宗旨为精拓,目的是信今与“传古”,即探求古人留存文字中的真正内涵,从中窥测古圣先贤的活动。 陈氏提出精研与摹刻乃是学问之事,必须审慎面对,应严格处理拓片上纸、揭纸、上墨、纸张质地、扑墨时机、扑包蘸墨法等工序细节。 第三阶段:拓毕阶段。 陈介祺制定了细致严格的整理、著录编订体例,首先将材料进行整理,再分门别类并汇总,以便进行系统分析研究。 陈介祺注重夏、商、周三朝的器物,特别注重镌刻有铭文的器皿古物;对没有文字的秦代器皿,以及仅有制作年月、地名、官名、工名等铭文的汉代器皿,则记录其年月、尺寸、斤两、地名、器名、官名、工名。 然而,后来研究全形拓的学者并不是照此流程进行严格著录,实在令人遗憾。
全形拓的发展流脉并非只有“传古”一派。清代金石学兴盛下,金石两派之一的“覃溪派”,在金石收藏中侧重精购旧拓,讲求笔意,以“鉴赏”为目的,使得“崇古”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风气。 全形拓以墨来传拓,通过浓淡干湿的墨法展现器物的造型与神韵,其所构成的黑白艺术世界,暗合了大道至简的传统审美,由此,全形拓很快被众多文人学者接受并成为一种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和审美对象。 全形拓从一种审美形式到审美客体的转变,既是“传古”一派发展的衍生,同时也与金石学兴盛所形成的审美风气互相影响。
在“传古”与“鉴赏”两种既相互影响又具彼此独立功能的相互作用下,全形拓便有了不同的制作目的,进而产生了“古器存真”和“博古清供”的两种艺术风格。 前者,是金石学家的职责,他们以流传真实图像为己任,力求原器传拓,目的在于“存古”;后者,常常作为书画家创作的画面点缀元素,目的在“取象”。 早期“取象”一派的代表书画家有释达受、虚谷等人;而作为画面清供元素之一,书画审美视野中全形拓质量的草率与非原件传拓是其特点。
“存古”与“取象”两者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区别,便是鉴真辨伪,这一点恰恰是“古器存真”最重要的环节。 我们知道,青铜器的仿制肇始于宋朝,其后滋生出古器物作伪的风气。 清中叶以后,好古之风日渐炽盛,仿制者为了谋求暴利,催生了许许多多的作伪高手;其中,以苏州的顾湘舟、西安的张二铭(凤眼张)、潍县的刘学诗最为著名,作伪水平之高令人叹服。 作伪之风的炽盛,去伪存真则成为古器吉金收藏者首要的难题。 陈介祺在长期的古器吉金收购中,练就了一双巨眼,他首先提出文字辨伪之法,认为:“古人之文理文法,学者真能通贯,即必能辨古器之文,是谓之文定之。”[5]23这一辨伪方法见地高绝。 可见,如无饱读诗书的学识,断不能从容地去伪存真。 其次,陈氏从篆书的书法笔法角度进行真伪鉴定,他认为:鉴藏古器吉金,必先研究古人书写篆书的用笔方法,在通晓篆书笔法之后,以篆书的笔法为参照,审视笔画铸刻的失真程度,再通过析读古器物上的铭文,进而辨别其真赝。 陈介祺通晓诗书画印,学养丰厚,且涉猎广泛,尤以收藏印章而著称,家筑“万印楼”,贮藏古印宏富,显然具备多种修养。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就曾赞誉陈介祺“三代彝器之富,鉴别之精,无过长者,拓本之工,亦从古所未有”[5]22。 针对青铜器物铸刻文字的真赝辨别,陈介祺提出:“铸字刻字必可辨,铸字佳者,每上狭而下宽。 古人之字只是有力,今人只是无力。 古人笔笔到,笔笔起结立得住,贯得足,今人如何能及。”[5]23又云:“玩其每笔之篆法与通篇自然之章法,勿徇好奇急获之见,而平心察之。”[5]23由此可见,其辨伪工作精细之至,已经由笔法而具体到关注文字的铸刻工艺。 陈介祺搜求古器之前,必先从古董商处索取拓片,而且拓片必须是精拓,经过反复研究考据之后再重金求购。
以“鉴赏”为目的与以“传古”为目的的全形拓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其不同之处在于:在全形拓制作的三个阶段中,“鉴赏”对于第一阶段古器物内容的择取与第三阶段拓毕后对拓片中古器物的研究,均明显表现为重视程度不够。 即在第一阶段中,对所拓古器物的选择取向,多侧重于审美方面,主要看古器物造型美丑以及轮廓外型是否美观。 在第二阶段的传拓技法中有所侧重,并加入传拓者的审美理想。 如为了拓片效果有意加入勾线、二次加工的水墨效果、以拓片效果为轴心的技法渲染等,为了炫技而失去了技艺背后的内涵,故而偏离轨道,失之下品。 而对于传拓的第三阶段,则不需要细致严格的整理、著录编订体例,只是以“赏鉴”为目的遴选出艺术效果好的拓片而已。
“传古”虽是全形拓发展的初始动因,然而并非一以贯之地居于主流地位。 在摄影技术发展起来以后,以“存古”为宗旨的传拓,便很难与摄影技术对古器物原相再现的真实程度相媲美,这使得全形拓发展中的审美动因后来居上。 因此,综观全形拓的发展变化,它是从“传古”为主、“鉴赏”为辅,慢慢发展到以“鉴赏”为主、“传古”为辅,两者既相互影响又彼此独立。 因而,许多文人学者,既是金石收藏爱好者,又是书画家。
三、全形拓发展的衍生——结缘书画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可以获知,全形拓脱胎于金石学,也是“古董收藏”的一个门类,其主要的作用与目的在于“传古”。 由于工序繁复,技艺讲究,故而全形拓技艺很难普及开来。 此后,由于珂罗版印刷术的大量使用、西方摄影技术的广泛传播与普及,以“传古”为目的的全形拓拓法,便落后于西方先进的科技,出现断层。 然而,全形拓拓片所透露出来的“古意”,却暗合了清代金石学兴盛下所衍生出的审美风气,为文人士大夫所重。由此,全形拓拓片开始与书画结缘,成为深受文人士夫喜爱的全新审美对象和审美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能引全形拓入画的书画家,大多是擅长于金石考据的文人学者,他们将金石“古意”引入画中,开创了一代书画审美之风。 近代擅长此道的书画家有吴大澂、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人。 全形拓入画,在清末渐渐成为一种流行风气,当然也与书画家的个人趣味和审美旨趣分不开。 这些书画大家,大多诗、书、画、印、金石兼擅,既崇古意,又能鉴古物,可以很好地将全形拓拓片与书画结合起来,在画面中营造出一种古意盎然的意境。 “清代文人们不仅利用全形拓的方式研究金石考据之学,也没有中断对古器物造型纹饰和铭文美的探索……当古器物参与博古花鸟画的创作,古器物便褪去了它自身的实用性功能,进而彰显出它纯粹的装饰性功能”[8]10。
全形拓与书画艺术的结合,具有某些内在的共性。
首先,全形拓“传古”思想与传统书画追求“古意”的旨趣暗合。 元代赵孟頫曾经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 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 吾所作画,似可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 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9]追求“古意”是书画艺术的一个重要传统,是文人画的共同审美趣味。 在近代,金石学的兴盛,全形拓的出现,无不是“传古”思想的产物。这种古意盎然的古器物传拓,增加了书法和绘画画面的持重感,营造出一种“古意新传”——基于传统的新的艺术形式,并为书画家所接受和喜爱。
其次,全形拓的墨相与传统的书画笔墨相呼应。 由于突出古器物的凹凸形体,必须通过墨色的浓淡干湿来体现其体积感,全形拓传拓的墨色,与国画皴擦点染等笔墨技法中的“墨分五彩”暗合,这是一种新型的墨色与书画笔墨的呼应和配合。
再次,“由于古器物的大小、开口的方向和器物造型的不同决定了所补花卉的疏密、长短、轻重等各不相同,花卉植物随古器物而变换自身的位置等关系”[8]11,即为配合全形拓中古器物的造型,考虑它在画面中的位置,使其成为画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书画完美结合,书画家必须匠心独具地“经营位置”——这既能衡量一个书画家的基本功,又是一个极富趣味的挑战。为此,近代擅长此道的书画家常常殚精竭智而又乐此不疲。
同时,全形拓中古器物的造型,也决定了书画家选择何种书体与全形拓“取象”之间的配合。一般来说,为了与全形拓的“取象”相呼应,书画家会选择那些沉雄古拙、敦厚大气的书体。 此外,金石拓片的书法题跋,不仅是全形拓作品整体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法的艺术价值和内容的文史价值,也对书画家在书画艺术、古文字、古器物学等方面的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上几点,是全形拓与书画结合的重要基础。全形拓的意境、墨相、造型暗合中国书画的审美追求、笔墨技法和画面的经营与构成。 全形拓拓片中的古器物与原物等同无二,效果逼真,也与西方传入的素描造型手法和照相技术暗合,且其造型准确度比之中国传统绘画有明显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画重写意轻造型的不足,使得全形拓画作的格调雅俗共赏,深受各个阶层的喜爱。
四、当代文化视域下全形拓的发展趋向
全形拓发展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在摄影技术与数码图像处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它的发展并非一以贯之、恒定不变,而是受多种学科领域及其审美思潮的影响,且有其特有的发展趋向。
首先,“传古”思想仍然是全形拓发展的主旨。 虽然摄影和数码图像处理技术在当下已经广泛使用,但全形拓特有的纸拓视觉感受仍然不能被摄影或数码技术所形成的图像所完全取代。 因此,以“传古”为指归的全形拓,如果能吸收先进的技术,进行不断完善与提高,仍然具有发展的巨大潜力与空间。 如全形拓全盛的晚清、民国时期,在周希丁、马子云、傅大卣诸辈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借鉴西洋透视、素描之法,将“分纸拓”发展为“整纸拓”,制作出造型精美、立体逼真的作品而勇超前代,便是极好的例子。 然而,这种全形拓在时下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一,所拓古器物既要真而且要美,得其一尚且困难,两者兼得则难上加难;其二,传拓技艺要求极高,不但工序繁多,而且各个工序的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难于玉成其事,这在陈介祺《传古别录》中均有详细的记载。
其次,以审美鉴赏为目的全形拓,既简化了制作流程,也泛化了“取象”题材。 与书画结缘的全形拓,方法趋向便捷、普及,有时甚至为拓片而拓片,简化了拓片制作流程。 这与以“传古”为目的的全形拓相比,省略了第一环节中的辨伪、剔字与去锈的环节,省略了第三环节中的护器环节,还省略了将拓片分类汇总研究的环节。 同时,全形拓“取象”的题材也日益多样化,除了古器物、秦砖汉瓦等古代遗迹以外,砚台、笔洗等文房用具,灵璧石、太湖石、昆石、太英石等名石以及把玩物件,均因审美需求而成为捶拓的对象。 所拓物件均出于捶拓者的审美需求与意愿,不受约束,自由多变。 这些物品只要器型符合审美要求,画家便可应物象形、经营位置而入画,成为应景之作。 这种趋势,拓展了全形拓的审美范畴,但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一些问题:所捶拓物品的泛化,使得这一技艺因便捷而增强了随意性,且其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不断变少,“传古”的价值和意义日渐缩水。 当然,“取象”题材的泛化,一方面与古器物受国家严格保护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市场化带来的全形拓作品日渐大众化和多样化密不可分。 因此,反思“取象”题材泛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厘清全形拓的发展源头,重申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在市场化的当下,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再次,全形拓作为一种不可多得的审美对象和审美形式,随着制作流程趋向便捷化和流通的市场化,也造成了全形拓审美倾向呈现多元化的趋向。 市场化的家庭装饰,往往需要有格调的艺术品装点,无形中给全形拓的市场流通带来了很多的机遇。 时下,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格调也逐渐提升,收藏热潮也唤醒了人们的好古之风。 全形拓拓片,以其兼具吉金珍石与书情画意之长而又承载悠久的文化基因而雅俗共赏,且非名贵器物的拓片廉价易得易拓,因此,必定会成为大众欣赏的艺术品类。
全形拓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其承载的文化、历史内涵以及它与书画结合所带来的审美价值,必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此,它不应落入为技艺而技艺的窠臼。 在这一方面,有很多反面的例子,如篆刻艺术史上的“浙派”,在篆刻的刀法推进与发展中造诣颇深,然而,却仅仅局限于刀法的因袭之中,师徒相授,导致路子越走越窄,最终被“徽派”替代。 前车之辙,后车之师。因此,技艺有尽而道无穷,当代全形拓的发展,应该根植于广袤的文化土壤中,吸收其营养,呈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否则,将变为无根之水,不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