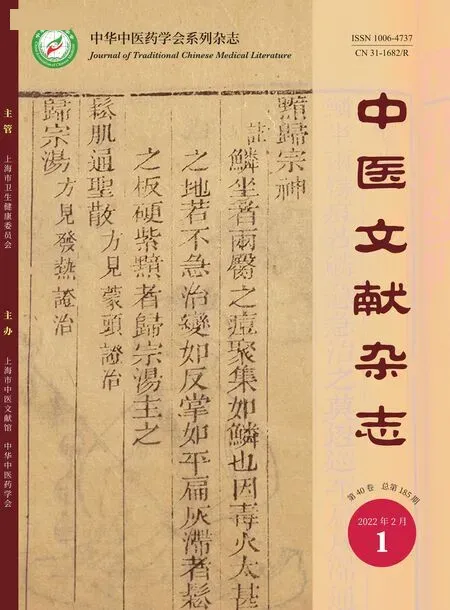风痫、伏瘟、痉瘟与疫痉
——近代江南中医对急性传染病“流脑”的认识*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杨奕望 徐超琼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epidemic cerebrospinal meningitis),简称流脑,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发生于冬春季节。患者以儿童为主,其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头痛、呕吐、出血点及颈项强直等脑膜刺激症状[1]。现代名医姜春华研究认为,该病之症状古书多有记载,《黄帝内经》《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诸书之痉、中风,即含有是项疾病[2],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最早记载,当推唐代的《外台秘要》[3]。《外台秘要·卷十五·风痫及惊痫方五首》引“崔氏疗暴得惊痫立验方”后,论及“紫石汤方”道:“永嘉二年,大人、小儿频行风痫之病,得发例不能言,或发热半身掣缩,或五六日或七八日死。”[4]据姜春华考证,西晋永嘉二年(308年),是现存文献中记载流脑在我国流传的最早时间。《外台秘要》将该病称为“风痫”。
时至近代,西风东渐。江南地区对流脑进行报道时,西医学的病原体、症状、治疗、预防等的表述更为清晰和明确。如戊午年(1918年)四月,院长王彰孚、医生张绍修报道了该院“公立上海医院发见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之警告”,该病“死亡之数颇多,传染之力甚大,且传染后治愈极难”[5]。次年,流脑在江浙沪多处流行,包括浙江临海。浙江临海医家蒋树杞(字璧山),于1920年所撰的《伏瘟证治实验谈》,记载了己未(1919年)之冬、庚申(1920年)之春在当地发生的流脑疫情。他认为该病系时感伤寒引动内伏之症,定名为“伏气瘟症”,简称“伏瘟”,亦名“痉瘟”[6]。“痉瘟”之名,与两年前江苏鸳湖医家徐石生回答《绍兴医药学报》的名称完全一致[7]。
1929年春,流脑又于南汇出现,在上海再次暴发。经统计,上海的发病患者逾500人。美国哈佛大学卫生学博士李廷安(字广文),学成回国后对此轮疫情展开调研。李廷安时任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第四科科长,撰文《民国十八年上海脑膜炎流行之经过》,首刊于当年7月的《卫生月刊》[8],次年4月以竖版形式再版于《中华医学杂志》[9]。文中翔实的数据和图表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1931年4月的《中华医学杂志》也对浙江省(尤其是下辖海宁县)脑膜炎的流行状况进行了报道[10]。
辨析病因病机
针对流脑发热、头痛、颈项强直等症状,中医界大多将之与传统的“痉病”联系起来。在沪的武进名医恽铁樵、谢利恒等都支持这一观点。同时,少壮派的海上中医,如宁海严苍山、上海秦伯未、江湾蒋文芳等进一步提出,流脑除了有角弓反张之“痉”,更有传染性之“疫”的特征,在中医命名上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11]。
针对猖獗的流脑疫情,神州医药总会作为近代上海中医药界的重要学术团体,迅速推选出蒋文芳、萧退庵、徐相任、包识生、谢利恒、薛文元、顾渭川、程迪仁、方公溥九人组织时疫研究委员会[12],并很快在会刊《神州医药》上发布研究成果。“现时流行疫症(西医所谓脑膜炎、脑脊髓膜炎),业经本会征求治方,接到诸同仁寄来函件、理论、方案等,不下百余起,迭经开会讨论研究,结果制成总摘报告。”报告中首先明确了病证的中医名称,“(甲)病名:疫毒进脑之痉症,简称‘疫痉’”[13]。“疫痉”之名,经集思广益后讨论汇总,逐渐为中医药界所认可。对于疫痉的病因,也形成了两种主要看法。
1.与非时之气有关
气候的异常变化,让疫病暴发的风险不断增加。海上名医陈存仁认为,1929年流行的疫痉与冬春易令、阴阳乖逆有关,“去冬气候不正,当寒反温,今遇春气触发,苟其人头部会受振荡,精神兴奋,或过于劳动,即易诱而患此”。即冬应寒而反温,春应回暖而酷冷,天时不正影响身体,奇疫乃发。陈氏也提到,该病变延甚速,“十二小时内亦能致命,通常凡三日毕命,惟逾十日无变动者,可望无虞”[14]。
川沙医家陈桐候在十多年后的回顾中,对疫痉运气的叙述更为详尽。“自民国十八年己巳仲春后,一度流行后,至三十二年癸未之冬,天气应寒反暖,时值季冬,大寒节后,芦芽长尺许,翌年甲申,阴历二月,疫痉大发,蔓延月余,死亡甚多,但十有八九,为未成年之儿童。”[15]故陈氏认为,疫菌的繁殖,与气候有很大的关系。上述两位及不少医家都认为,非时之气,即反常的气候变化,是导致疫痉发生的重要因素。
2.与疫毒关系密切
除了非时之气,随着近代医家逐步了解细菌学知识,更认识到疫毒之邪至关重要。如浙江定海医家翁性初,所撰《疫痉——急性传染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一文中论及病因,“西籍以为细胞内脑膜炎球菌之传染而起,为两个镰状体对连之重球菌,多生存于细胞膜球等内,故颇似淋球菌;传染之径路,大约多从鼻道或咽头之扁桃腺等处”[16]。
神州医药总会时疫研究委员会群策群力形成的研究报告,讨论了疫痉的病源,“疫毒煽引肝风,循督脉而上犯于脑”,并结合西医神经学与中医经络学说予以说明,“疫毒内侵,引起神经系之病理变态,循督脉所附之脊椎上入于脑”[13]。疫痉源自疫毒的观点,中医界普遍接受。如江苏嘉定医家沈朗清,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编辑的《脑膜炎新书》,收录了众多医家在报刊上讨论疫痉的观点,从脑膜炎的名称、症状、原因、疗治、预防五方面展开[17],沈氏也认同疫痉由疫毒引发的观点。
治疗手段多样化
20世纪30年代,亚历山大·弗莱明发明的青霉素、格哈特·杜马克发明的磺胺药物,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广泛使用,也没有传入我国。针对流脑,当时西医主要采用血清疗法。如时任淞沪卫生局局长的西医刘绪梓建议,“头痛甚剧者可用冰袋置头部救急……至于根本的治疗方法为注射脑膜炎血清,普通在注射前先放血20 CC,随即注射血清20 CC。余以为,如欲注射血清20 CC,似应先放血30 CC,使压力减少,较为适宜”[18]。但是,作为特效药的脑膜炎血清,价格昂贵且难以置办,因而平民百姓自然选择了中医药治疗。面对肆虐的流脑疫情,近代江南医家各擅其场,开展了积极救治的活动。
1.严苍山治疗疫痉
宁海世医严苍山,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承丁甘仁先生,毕业后主持上海四明医院医务,救治过大量流脑病人,并与其他中医名家共同创制了“疫痉”病名。严苍山根据近4年的临证经验,于1932年撰成《疫痉家庭自疗集》(又名《脑膜炎家庭自疗集》),该书成为我国第一部以疫痉命名的疫病学专著[19]。
流脑患者多有头痛如劈、项强等症。当时中医对此有肝风、瘟毒、惊风等不同观点,结果治法各异,疗效不佳。严氏主张治疗疫痉,需疏通表里,祛外寒、透郁热,增津液、养营血,以解疫气[20]。严氏精擅辨证,对于疫痉偏寒者、疫痉热重者,治方多变。前者祛寒邪,投以葛根汤加减、达原饮加减、当归四逆汤等;后者治以清热,投以防风通圣散、调胃承气加葛根黄芩汤、葛根白虎加芍药花粉汤等。对于疫痉神昏者,据病情变化增减化裁,创葛根栀豉汤、新定羚羊舒痉汤等。对于疫痉独头痛者,严氏认为,血虚之体,风阳上僭清空,故头疼甚,项微强,无寒热,治以清轻之药,拟方新定菊花达巅饮。若有热象者,则以新定羚羊熄风汤、加减龙胆泻肝汤治之[21]。严氏“处方应变,果然着手成春,风声所播,凡患脑膜炎者,竞送四明医院,沪埠一隅,奉为脑膜炎之唯一救星”[22],足见其医术高超。
2.顾渭川治疗疫痉
1925年,浙江嘉善世医顾渭川受邀再度来沪,悬壶北泥城桥北兴里[23]。1929年上海疫痉流行,《新闻报》推广其治疫经验,“顾渭川医士医学渊博,久负时誉。近日九亩地同裕祥主之女忽患脑膜炎症,其状甚危,幸延顾医士诊察,内投清瘟败毒,外用金针刺哑门、百会脑等,神志即清,病苦立除云”[24]。针药合力,彰显出顾氏的大家风范。顾渭川认为,是否受到疾病的侵袭与人体抵抗力的强弱有关,指出人体抵抗力弱则易患疫病,反之则不易患疫病。因此,当随季节、环境、气候的变化,及时施以对症的中药,扶助正气,使人不为疫病所害。
3.陈桐候治疗疫痉
鉴于中医古籍中疫痉的治法较为少见,川沙医家陈桐候治疗疫痉,采用武进恽铁樵的千金惊痫法制方治之。方用龙胆草五分、黄连三分、犀角三分、滁菊花三钱、鲜生地五钱、当归三钱、回天再造丸半粒。若患者有身体抽搐、昏迷等症状,加羚羊角三分;若症状较轻,则加龙胆草二三分。当甲申春,疫痉流行之时,陈氏效仿铁樵先生方法进行治疗,却发现得失参半。他进一步观察疫痉致死之由,发现这些逝者存在病前曾患疟疾或肺病、或有其他疾患还未痊愈的情况,皆为元气已虚。“故而元气犹足以支持者,亦可治也”[15]。
4.时逸人治疗疫痉
近现代名医时逸人(江苏无锡人,1896—1966年),当时正在上海各中医院校任教。时氏指出,疫痉初发时,恶烦发热、心烦头痛。该病与普通感冒的头痛部位有所差异,疫痉头痛,痛在脑后,位在小脑,连及脊柱,甚者角弓反张,疼痛程度远剧烈于普通感冒之头痛。时氏建议宜用紫金锭10粒,每隔2小时服2粒,研成细末,开水冲下,外用菖蒲、薄荷、佩兰、郁金、知母、象贝、瓜蒌皮、赤苓等药,甚者加郁李仁、紫背浮萍等,以新开透达、芳香化浊[25]。简单方便的中成药,在疫痉治疗中得到广泛使用。
20世纪30年代,中西医论争进入白热化。“晚近社会,欧化之医到处充斥,持其科学病名,号召于世,几于妇孺皆知。”[26]对于流脑,西医将抽吸脊髓、注射血清作为治疗该病的唯一方法。与此同时,中医治疗疫病表现出极好的效果。如《脑膜炎为“疫性痉症”概述》一文,医家钱甦石立足于疫痉,更表达了开明的学术态度,认为中西医“各有其认识,各有其方治”,当“认清目标,埋头赶去,小心大胆以临事……俾国医方治,具有特殊效验,庶几可得同样之昭信于社会”[26]。
预防方法科学
近代中医也认识到隔离、消毒对于预防疫痉等传染病的重要性。神州医药总会时疫研究委员会1931年的研究报告,详细论述了疫痉的六条预防措施,对于其他传染病也颇有启示:(一)离开有疫区城;(二)避免风尘,无事少出;(三)宁静恬淡,少用脑力;(四)勿入公共场所;(五)勿乘拥挤之车辆;(六)戒除刺激、剧烈之饮食品[13]。
1.消毒、隔离与卫生预防
江南医家把传染病预防方法加以具体化。如名医严苍山主张,疫痉患者需要送往医院治疗,若隔离在家中,家中仅派一人服侍即可,以免传染。对于服侍者,尤其注意病患的排泄物与汗液,倘若有所接触,需洗涤消毒;和病人说话时,不可口鼻相对,以免疫气通过口鼻传染。严氏还提到不同的消毒方式。对于病患所食之食器、所御之衣服等,可用“沸汤泡洗”;对于病人用品,不能沸汤等消毒者,宜“曝诸日下”;对于病人之便桶、尿壶,以及痰盂等,需“洒以臭药水”;又言用茵陈、大黄、红枣,共烧烟,在病室中“熏之”[21]。
杨志一(江西吉安人,1905—1966年),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与严苍山有同门之谊。杨氏在日常诊疗的同时,于1932年在上海西藏路平乐里创办《大众医学月刊》,传播医药知识。1934年,杨氏将第9期、第10期合刊,定为“脑病专号”。杨氏提出,“当本症流行之时,流行区域,固不宜涉足,而剧场、游戏场等多人屯集之所,亦宜少人,以防传染”[27]。这些建议都包含了近代公共卫生中隔离、消毒、切断传播途径等理念。
2.养生、情志与药物预防
疫病预防中,饮食起居、情志调节、日常劳作等,是中医一贯所关注的。如名医陈存仁在其主编的《康健报》上论述脑膜炎的预防时,反复强调“力防头部盖骨受任何震动;饮食清淡为宜;精神勿过兴奋,力求清净;与患者隔绝;勿过劳动,稍觉头晕神疲,即宜购甘杞子三钱、甘菊花三钱、生石决三钱、珍珠母三钱,煎汤代茶饮之”[14]。杨志一也认为,防止疫痉病毒侵袭的关键在于人体本身,“其在平日,宜节饮食、健肠胃,营活泼之运动,锻炼身体,得使强壮,致病毒无侵袭之路”[27]。陈存仁、杨志一等中医利用当时报刊等新兴媒体宣传中医药知识,为民众了解疫痉等传染病的常识增添了便捷渠道。
20世纪40年代,青霉素、磺胺类等药物引入我国,开始用于流脑的治疗,取得了良好的疗效。20世纪70年代以后,流脑疫苗研制成功,更成为了全球预防流脑的有效手段。然而,传染性强、危害性大的流脑,至今仍列为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依然需要防范。2005年,当代学者吴文清曾对疫痉的认识和防治进行了深入研究[28],《温病大成》[29]、《近代中医界重大创新之研究》[30]等专著,均采纳了她的观点,这也为拙稿提供了思路。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情况下,重新回顾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的数次流脑疫情,近代身处长三角地区的中医前辈们对其从风痫、伏瘟、痉瘟到疫痉进行病证命名,条分缕析病因病机、多种多样的治疗方法(汤方、成药、针灸),以及采用消毒、隔离等科学化的预防方法,并通过神州医药总会等学术团体组织、讨论,集思广益,从而达成基本共识。这些都为现今中医对于疫病(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分析、诊治与预防,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