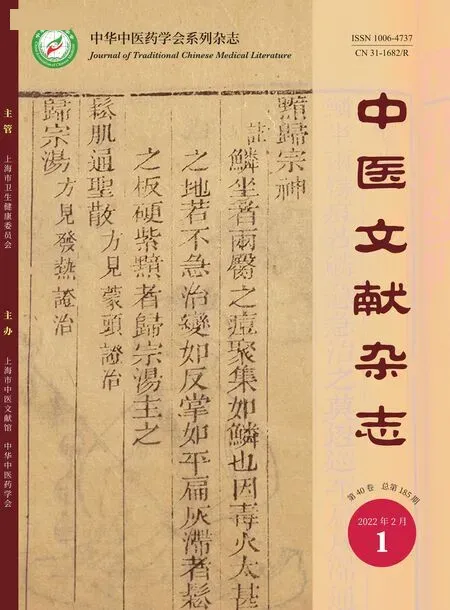名医李重人中医教育观点述要*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404120) 田红兵 黄玉静 陈代斌
李重人[1]4-23(1909—1969年),当代名医,中医教育家,原名伦敦,小名奉生(又写作“凤笙”),弱冠后名“重人”(意为“敦厚待人”),雅号“重翁”“文史活字典”,原四川省奉节县柏杨坝(现湖北省利川市)人。先生一生以医为业,又与中医教育结有不解之缘,曾先后任教于成都中医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前身)和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先生在卫生部中医司教育科工作期间参与了我国最早的中医学院的筹建,组织编写了中医学院使用的统一教材。笔者研究生毕业后来到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工作,作为中医药文化研究团队成员,参与了陈代斌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三峡地区中医药学术流派传承研究”的工作。我们在整理长江三峡地区中医药文献时,接触到了李重人的资料,认真研读后发现其治学思想独特,对发展中医教育大有裨益,现梳理如下。
加强古文学习,突破古文字关
李重人出身书香门第、中医世家,从小即受到家庭文化熏陶。其祖父李春霖系清代晚期奉节名医,父亲李建之是当地名医,母亲张氏亦粗通文墨[2]。他四岁开始学文习字,稍大即在清末秀才冯某指导下学习古典文学,又受到前清拔贡毛子献的教导,后入奉节“昭文私塾”读书,师从“火神郑钦安”之高足郑仲宾[3],成为“夔门郑氏温病学派”传人[4]。先生兴趣广泛,不仅研习文学、诗词、书法,而且对古文字学钻研颇深,金文、收藏、文物鉴赏等亦有涉猎。这些学习经历为他日后阅读中医典籍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凡历史上有成就的医学大家,大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过去拜师学医,师父择徒的首要标准是要文章通顺,文字根底扎实。这是因为古典医籍均用文言文写成,要读懂这些典籍,必须要有坚实的古文基础。所以先生主张在学习中医的同时,还要学好古文,突破文字关。只有具备了相当的古文水平,才能深入研习中医古籍,领悟医学文献要旨。他在《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1]343-348(史称“五老上书”)中强调,“不突破文字关,必不可能深造”,建议扩充“医古文选”内容,增加课时数,加强音韵、词汇、音义等方面知识的学习,其目的就是培养学生阅读古医籍的能力。
中医药院校建立之初就设有医古文课程,并作为中医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但由于我国高考招生政策是文理分科,以及医学专业招生录取倾向理科生等原因,理科生进入高校学习中医类专业时,感觉阅读中医古籍很吃力[5]。《医古文》教材以传统涉医文献和古汉语为主要内容,文章以繁体字写成,涉及很多古汉语知识,学生学起来感觉像被困在“故纸堆”里,枯燥乏味[6]。甚至有些师生认为医古文课就是“额外负担”,有些学校也不重视医古文的教学工作,导致该课程没有真正发挥工具性课程的作用[7]。客观来讲,中医学生的知识结构中需要医古文的内容,因为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要从事临床工作,而要想成为高水平的中医师,就得从中医古籍中汲取营养,以提高医疗水平和学术修养,如此方可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8]。由此看来,先生在“五老上书”中提出扩充医古文课内容,精读百篇左右古文和背诵60篇左右医古文的意见,是符合中医人才培养规律的,在当前中医教育中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重视经典学习,博采众家之长
学习经典对中医人来说是成才的必经之路。中医经典是中医理论的渊薮,也是指导临床实践的法则,作为中医人必须学好经典[9]。先生主张学医当从《黄帝内经》《难经》等经典起步,从难而上,从源到流地学习,对经典医籍全面了解后再研读秦汉以后医籍,如此方可全面继承前贤理论[10]。这种方法是先深后浅、深入浅出的学习法,刚开始学习时较难,可一旦入门则有豁然开朗之感,历代医籍可一通百通,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先生重视经典学习,与其师门传统有关。先生师祖郑钦安非常重视经典的系统学习,师父郑仲宾少时曾随郑钦安研读中医典籍[3],从医后又精读《黄帝内经》等典籍并写有读书心得。有人研究《名老中医之路》中所列的97位名医的成长轨迹后发现,他们的成才无不是重视经典学习、循序渐进、坚持不懈、触类旁通的结果[11]。可见,先生重视经典学习并不是食古不化,而是对中医成才规律的深刻认识。所以他在“五老上书”时强调要增加《内经讲义》的课时数,对《内经》原文精心挑选后加以精讲,要解释清楚理论原则细目,以期学生能理解中医基础理论的实质。
先生不但崇尚经典,而且能博采众家之长,毫无门户之见,并反对以古非今、泥古不化。他认为,中医理论是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自古及今中医学派林立,诸派各有所长,只有客观了解各派特点,博采众家之长,才能扬长避短,提高自己的水平。《黄帝内经》等经典医籍成书时间较早,理奥趣深,涉及天文、地理、历法、术数等众多学科,只精读原文实难把握要义,为了吃透经文要义须泛读各家著作,兼采众家之长,如此才能有全面认识,才能较深地理解经文原意。自古以来,凡成大医者,无不重视中医经典[12]。他们熟读经典,善于吸收前人经验,并能结合个人的临床实践,从而对中医理论有所突破、有所发挥、有所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14]。学习经典就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在学中用,在用中学[10],学用结合,才能深刻领会经典原旨,才能将经典学习与临床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而相得益彰。 先生带徒时要求徒弟们半日临证半日读书,就是在践行学用结合的经典学习之路。
读书讲究方法,熟读精思吟诵
“读书不知要领,则劳而无功。”读书得讲究方法,方法得当才能事半功倍。在“五老上书”[1]347中,先生指出,学校须大力提倡读书(背诵)的风气,让学生练好背功。他强调读书就要高声朗诵,口不绝吟,力求读懂读通,这样读不仅可以帮助记忆,而且可以加深理解。还有,根据内容不同,读书方法亦有所侧重。精读的内容要读得深、细、透,直至能背诵,然后反复玩味,深思研究,写出读书笔记,甚至能作批注;泛读的内容或读懂,或背诵,或有较深概念即可。两种读书法应结合起来,否则“只有精读,没有泛读,其见者少;只有泛读,没有精读,是无根之木,没有基础”。通过精读获得阅读古医书的基本能力后才可泛读。 先生不仅让学生读书,还要教师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并且将“指导读书列入教学计划的时数之内”。他认为,教师指导学生读书的重要性并不次于课堂讲授,只有课堂讲授与指导读书并重,才能让学生学得更深更透。
现代研究证明,精泛结合的读书法是有科学道理的。该法能充分调动人的眼、口、心、脑多器官参与学习,起到眼看、口读、心想、脑记之协同作用,可有效提高学习效率,与宋儒朱熹心到、眼到、口到的三到读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读书过程中“越是熟读便越能理解深刻”“只有熟读熟记,才能心领神会,才能学以致用”[9]。精泛结合的读书法就是通过反复背诵来强化记忆,减慢遗忘速度,该法能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增加长期知识储备,有利于系统掌握知识[14]。熟读精思吟诵,精泛结合的读书法值得每位中医学子学习和使用。
临床善用经方,用药简便廉验
先生临床善用经方[1]224-225,但崇古而不泥古,制方用药刚柔相济,总能根据病患体质、病势、病程、邪正盛衰等情况来酌定方剂大小、剂量轻重,临证依君臣佐使配伍原则拟方。他指出,学方剂就要学古人的学术思想和精神实质,学前人制方的原则,掌握其加减变化的规律,不能生搬硬套、一成不变地套用古方,或不加辨证地任意组方,更不能无目的、无原则地堆积用药,临证要根据中药特性和患者病情灵活化裁。临床疗效的高低,不在于用药味数的多寡和分量的大小,而在于是否有正确的辨证、严谨的组方和恰当的配伍。他“常以仲景临床观察细致、分析透彻、组方严谨、用药少而精自勉”。从先生现存为数不多的医案[15]和遗方[1]50-53中,可以看出他组方思维周密、药少力专,尽显中医药简、便、验、廉之特征[2]17。先生在临证开方时总是首写经方,后列加减,如此安排既尊重前人原创,又不失承前启后之意,让人一看便知方之来源出处,一代儒医严谨的治学风范、高尚的学术道德和大医精诚的仁心仁术,于一方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反观当下医界某些人,不顾病情轻重,不加辨证,堆砌用药,动辄开几十甚至上百味中药,以期偶中病情,且不问临床效果,但求经济效益,如此处方不但于患者病情无益,更增病人经济负担。此类无德医人实乃含灵巨贼,败坏了杏林风气,降低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感,损坏了医生的社会形象,加剧了医患矛盾,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先生遣药组方之思想,对培养医生仁心仁术和高尚医德,肃清杏林歪风邪气,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客观看待西医,主张为我所用
先生在《现代中医应取之途径》[1]81-84中指出,西医精于病理,中医长于治疗,中西医各有长短,应当采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融会贯通,使中西医学术各臻完善。他认为,在继承祖国医学的基础上,不固步自封,不墨守成规,吸取现代科学知识,学习研究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药理知识,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去解释剖析古人经验,从而发扬中医学,使中国医药学出现新的面貌。他曾将诊室取名“三理斋”,勉励自己研习《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先生创办起华中医院时主张以中药为主,西药为辅,结合运用,反对以现代医学之名套用中药。他在“五老上书”中指出,“中医学院加西医课,其目的在于使现代的中医师具备一些自然科学和现代医学的基本知识,为将来医学科学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这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在保证学好中医的前提下加西医课”[1]343-348,避免出现计划要培养出中西医兼通的人才,结果是西医没学好、中医也没学深学透。他明确指出,学习西医的目的是更好地发扬和提高中医,“使之成为世界医学的组成部分”[1]121,而不是削足适履,也不能以西律中,而是把民族医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将它发展成为世界医学,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理解、认识。先生的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积极意义。时下,大批反中医人士和某些利益集团利用各种手段抹黑中医,炮制所谓的中药肝毒性、肾毒性,轮番掀起网络舆情,误导人们对中医药的认识。而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医药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有用的,不仅护佑中华民族繁衍至今,而且能够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当下中医药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取得的卓越疗效即是最好说明。国人当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抓住时机,守正创新,将中医药发扬光大,守护人类健康。
发展中医教育,传承民族瑰宝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力孱弱,饱受侵略之苦,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西医长驱直入,中医遭受重创,其合法地位摇摇欲坠。继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漏列中医案”之后,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又制造了震惊中医界的“废医案”,其内容之一就是将中医学校教育排除在国民教育序列之外[16]。消息传出后,激起中医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各地中医人通过请愿等方式奋起抗争。在此背景下,先生组织万县市中医同道通电反对“废医案”,声援中医界的抗争。经过此番抗争后,先生认为,振兴中医应当从教育入手[17],只有培养大批高质量的中医人才,才能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传承民族瑰宝。“废医案”后,先生便和中医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1]4-23。1930年,他自费与好友向蛰苏到上海考察中医学校办学经验;1951年担任万县市中医业余进修学校副校长;1954年初秋调成都中医进修学校(成都中医药大学前身)任教;1956年1月奉调北京,任卫生部中医司教育科副科长,负责全国中医教育工作,组织编写中医学院使用的统一教材;1962年秋调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任副教务长兼中医系副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1958年至1963年,先后到保定、南京、合肥、南昌等地交流中医教材编写经验;1963年参加在江西庐山举行的“全国中医学院第二版教材审订会议”,11月参加在合肥召开的“全国中医学院教材修审会议”。
先生为了发展中医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在成都中医进修学校期间,先生编写了《中医病理与诊断》进修教材,为中医系统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作了有益探索。调到北京后,先生全力投入到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中去。继1956年四所中医学院建立之后,许多省份也筹建了中医学院。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先生参与起草、修订中医学院的教学计划,组织编写中医专业使用的一版、二版教材和中医中专的教材,多次参加全国中医教材评审会。除此之外,他还起草和修订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教学计划,并起草了卫生部党组报送毛主席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为了培养高素质的中医后继人才,先生对中医教育存在的普遍问题和第一批中医毕业生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调研后,认为有必要对中医学院的教学计划进行讨论修改,于是与秦伯未、于道济、陈慎吾、任应秋四人联名写了《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先生执笔起草)上书卫生部,得到卫生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在1962年修订教学计划时基本采纳了该意见。不幸的是,先生却因此意见招来横祸而蒙冤屈死。
回顾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历程,60多年来,中医药院校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中医药人才。但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中医类院校中西课程设置比例不合理,不能突出中医的主体地位,医古文等基础课程课时偏少,黄帝内经等经典课程课时数不足,甚至沦为选修课,学生中医思维欠缺,在校跟师临床时间少,毕业后临床业务水平低下,难以胜任中医临床诊疗工作等。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中医教育的质量和国家健康事业的发展。2020年9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加快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创新,全面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作出系统部署,更对中医药院校教育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改革措施,强调“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教育”“强化中医药专业在中医药院校中的主体地位……强化传承,把中医药经典能力培养作为重点,提高中医类专业经典课程比重,将中医药经典融入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程,强化学生中医思维培养。建立早跟师、早临床的学习制度,将师承教育贯穿临床实践教学全过程”。《黄帝内经》云“善言古者必合于今”。研究先生的中医教育观点,与《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关于中医教育改革的精神高度一致,对发展现代中医药院校中医教育大有裨益,对培养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能够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法,深入研究其中医教育观点必将有利于当今的中医药院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