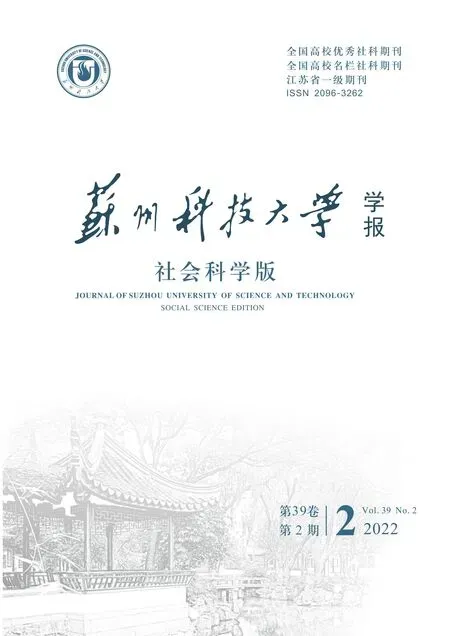方苞的遗民家世、交游及其文化认同 *
任雪山
(合肥学院 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在清代学术史上,方苞与刘大櫆、姚鼐并称“桐城派三祖”,影响深远。但汉学家对方苞颇有微词,从钱大昕、王昶到江藩、阮元再到梁启超,一以贯之。(1)相关研究参见任雪山3篇论文:《钱大昕与方苞的一桩学术公案》,《兰台世界》2017年第8期第103~106页;《江永、方苞京师之会的书写与汉宋之争》,《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第31~39页;《文界革命:梁启超论桐城派》,《学术界》2015年第1期第208~218页。梁启超甚至称方苞、熊赐履、李光地等庙堂理学家为“依草附木”之人,认为他们是一群没有风骨的“乡愿”。[1]汉学家批评方苞,有多重原因,但与其清廷“御用文人”身份不无关系。其实,只要深入了解方苞的遗民家世、交游及其文学书写,就不难发现,方苞虽为清人,但对明朝亦怀有一份眷眷之情。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司徒琳所说,即使在康熙年间成长起来的汉族士人,仍然对大明王朝抱有一种复杂的感情[2]。有鉴于此,有必要重新考察方苞的形象。
一、不忘故国:方苞祖父与江南遗民
康熙七年(1668),方苞生于江宁。清代初期的江南不仅是“各种反清运动的频发地,亦是悖逆言辞生产的策源地”[3],还是清军入关后抵抗最顽强的地区,曾出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江南地区抗清运动“声势之猛烈、地域的辽阔,完全出乎清廷意料,几乎有难于招架之势”[4]。在这些抵抗运动中,明遗民是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心系国家存亡,时常穿梭于武将、乡民与各种社会团体之间,鼓舞气势,群集力量,方苞的先辈方以智、方文、方其义、方授等都活跃其中。
方苞祖父方帜(1615—1687),字汉树,号马溪,年十一入安庆府学,与里中诸名士结“环中社”。后随父迁居金陵,“垂五十年,牛首、雨花之间题咏无虚日”[5],被师友推为“江上十子”之首。多年后,方苞为其作墓志铭称:“大父文学为同时江介诸公所重。”[6]490顺治十四年(1657),方帜以年资贡于礼部,当朝廷对第一,铨选授官,坚决推辞不就,归与江南诸遗民耆旧林古度(号那子)、白梦鼎(字孟新)、杜濬(字于皇)、顾梦游(字舆治)等相唱和。林古度(1580—1666)在金陵遗民诗人中“年辈最长并声名甚盛”[7]65,常与遗民诸老聚会酬唱。方帜厕身其间,心有所许,其诗《立冬前五日林那子招饮南郊看菊同顾舆治白孟新》曰:“小春天气恰如春,胜地徜徉赖主人。十月寻秋宁惮远,一卮对菊竟忘贫。艳当日午全无恨,高立霜初独有神。今岁看花才两度,同游犹集旧时宾。”[5]更多时候,他们是彼此相随,以酒为令,吟诗填词。后来林古度去世,方帜题诗《吊林翁那子》三首,深情追忆老友,其一曰:“江南不见老诗人,百岁难留十四春。袖底一钱存万历,舌端千首忆双亲。竟陵在日诗名并,宗伯遗风墨迹新。乱后欲详天宝事,白头宫女委青磷。”[5]
康熙十三年(1674),廷议复明经得授,方帜不得已出任芜湖训导,其实心有苦衷:“我是烟霞客,应举多苦衷。廷对冠六经,名在铨选中。贱比报关吏,岂有麟阁功。一命视河清,出处两从容。”[5]身在曹营心在汉,是清初不少汉族官员的心态,方帜亦如此。他经常感觉人在樊笼,不得自由,惟以道家思想自我开解:“少年颇好道,中为尘俗牵。家国阅沧桑,此心已了然。犹记拘幽日,萧萧岁暮天。身在樊笼外,胜陟方壶巅。”[5]清廷发布剃发易服令,激起汉人的极大愤慨,方帜《剃发》诗揭示了江南士人在剃发易服令笼罩下的惊恐人生:“一剃一回老,惊看白渐繁。易同春草长,难共葛巾存。废镜逃清照,衔杯学醉髡。岂惟栉沐简,更掩雪霜痕。”[5]艰难岁月,幸好老友尚在,心多宽慰,白梦鼎曾专程看望他,方帜写诗《喜白大孟新来芜相晤限秋莺二字》云:“江上怀人正蚤秋,人来江上雨初收。海棠倚砌红如滴,家酝倾杯绿可浮。茂叔同官多意气,参军作客尚淹留。故交新好成星聚,未许忙回白下舟。”[5]
在家族成员中,方帜与著名遗民诗人方文往来密切。方文(1612—1669),字尔止,明亡后别号明农,入清不仕,与“复社”“几社”中人交游,以气节自励,钱谦益称其为“遗民宿老”[8]508。方文自号嵞山,诗集亦命名为《嵞山集》,嵞山在怀远县城外,为朱元璋起兵之地,以“嵞山”为号,饱含不忘故国之意。尤其是一些特别的日子,如甲申年(1644)农历三月十九,崇祯帝煤山自尽,统一的大明不复存在,从此这个日期“成为民族情绪的标志”[7]160。一些文人便于此日作诗怀念明王朝,如黄宗羲《三月十九日闻杜鹃》、顾炎武《三月十九日有事于攒宫时闻缅国之报》、冷士嵋《三月十九日圣忌日偶成》等。方文几乎每年是日皆作诗,方帜亦颇为感慨,有诗《三月十九日偶作》曰:“吾家高尚嵞山老,此日年年一作诗。歌断首阳愁夕雾,节同寒食感春时。嵩呼昨夜随来众,弓坠煤山记得谁。独焚瓣香更野服,不堪啼血过青枝。”[5]方帜与方文一样,对大明怀有眷眷之情。平常叔侄也感情甚笃,即便一餐美食,方帜都会念起这位本家:“四月鲥鱼价渐平,一双那得易为情。雨中好就阶前洗,兴至须拼瓮底倾。举室欢声因此出,无端感慨忽然生。醉余频诵春江句,叹息诗坛失步兵。”[5]
方苞父母的结合,是方文为媒,并作《枞川夜集送从孙懂次就婚六合》诗祝贺:“今夜张筵对雨窗,来朝挂席下秋江。不知新妇于归后,可许人言有阿双。”[9]616方苞在《先母行略》中记载此事[6]493,在《同知绍兴府事吴公墓表》中亦云:“(外祖)往来金陵,与吾宗故老嵞山及黄冈二杜公游。见先君子诗,许以吾母继室。”[6]338
二、不仕清廷:方苞父亲与江南遗民
方苞父亲方仲舒(1638—1707),字南董,又字董次(懂次),号逸巢。早年就读于国子监,但旋归故里,终生不仕清廷,与明遗民杜濬、杜岕、钱澄之、方文、方授、张怡、胡其毅等相友善。方苞尝说:“先君子所交,皆楚、越遗老。”[6]502
金陵遗民之著名者,有“余杜白”,即余怀、杜濬、白梦鼎。杜濬(1611—1687),字于皇,号茶村,湖北黄冈人,“侨居白下,以诗名”[10],有《变雅堂诗集》《变雅堂文集》。杜濬之弟名杜岕(1617—1693),字苍略,号些山,有《些山集》。兄弟二人皆为明诸生,明亡后流寓金陵。因为方帜与杜濬、杜岕相友善,方仲舒遂从游,又加之二杜所居之地距离方仲舒较近,彼此“以诗相得,旦晚过从,非甚雨疾风无间”[6]400,方苞兄弟常“奉壶觞”随侍左右,杜濬亦视方仲舒及其二子如家人。抑或良辰美景,方仲舒、杜濬等结伴出门,“寻花莳,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视而嘻,冲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系牵也”[6]250。杜濬不在金陵时,仲舒时常怀念老友,《江舟食蟹有怀茶村先生》诗曰:“年年秋老共持螯,大梦堂前饮兴豪。今我几番夸砍雪,知公何处快挥毫。”[11]康熙二十五年(1686),杜濬感觉自己去日无多,携襆被登门,交代身后之事。数月后,杜濬客死扬州,方仲舒为其执绋送葬,检查墓穴,并嘱咐方苞为其作墓志。方苞为杜氏兄弟作《杜茶村先生墓碣》《杜苍略先生墓志铭》。
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晚号田间老人,桐城人。崇祯时秀才,南明桂王时,担任翰林院庶吉士,与陈子龙、夏允彝、方文、方以智等结社,尤负诗名,与同时的顾炎武、吴嘉纪并称“江南三大遗民诗人”,著有《田间诗集》《田间文集》《藏山阁集》等。康熙二十五年,方仲舒携方苞回安庆应试,路过枞阳时,钱澄之凌晨主动前来探望,曰:“闻君二子皆吾辈人,欲一观所祈向,恐交臂而失之耳!”[6]336-337能够被遗民老辈、文学宗师引为“吾辈人”,不管是同好诗文,抑或心系故国,都让人欣慰。这是身份的认可,也是精神的鼓舞。自此以后,钱澄之“游吴越,必维舟江干”,招方苞“兄弟晤语,连夕乃去”[6]337。同时在学术祈向上,钱澄之与杜濬等明遗民劝勉方苞兄弟不为科举所束,摒弃八股时文,致力于经学古文。作为桐城遗老耆旧,热心关怀后辈的成长,亲身垂教,对后辈人生与学术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云:“望溪少时承其(钱澄之)绪论,后遂蔚为儒宗。”[12]
张怡(1608—1695),上元(今南京)人,初名鹿徵,字瑶星,甲申后更名“遗”,以诸生荫锦衣卫千户,明亡后归里,隐居摄山白云庵,号白云道者,有《濯足庵文集钞》《玉光剑气集》《白云道者自述稿》等。朱彝尊《明诗综》称其“甲申陷贼不屈,受刑洁身”[13],卓尔堪《明遗民诗》称其“麻衣葛巾终其身,五十余年不入城市”[14]1。其常往来者,多为明遗民,如杜濬、方以智、钱澄之、方文、白梦鼎、方仲舒等。方苞作《白云先生传》,称其与“海内三遗民”之沈寿民、徐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方仲舒与余公佩拜访张怡,见其架上有书百卷,皆儒家经典或史著,请求抄录副本,并刊印其著述,张怡不许。乾隆三年(1738),方苞主持诏修三礼,征求张怡遗书,未果。
胡其毅,字致果,号静夫,上元人,明清著名刻书家胡正言之子,有《静拙斋诗选》《微吟集》等。卓尔堪在《明遗民诗》称其“平生谦谨自持,至老不变,为诗亦尚冲淡”[14]514。胡其毅与钱谦益、杜濬兄弟、孔尚任、彭士望、王大江等皆有往来。方仲舒致胡其毅诗云:“南轩欣得句,北郭觅知音。学积穷愁长,交凭淡漠深。枯鱼供小酌,野雀听高吟。翻覆看流俗,迂疏存古心。”[15]方仲舒视胡其毅为知音好友,二人在曹寅的江宁织造府时有交集,这里是江南遗民雅集的一个中心,有诗为证:“造物如春愁烂漫,酒杯由客谩操劳。北山拄杖西城屐,何处登临吟最高。”[16]
由交游来看,方仲舒与真正的遗民无异,他的遗民本家方文也是非常认同,有诗《喜从孙懂次见访草堂》曰:“尔去灵岩结好因,村居虽僻远嚣尘。身闲努力为诗伯,年少甘心学逸民。交有萦河真莫逆,才如明圃更无伦。过江每念嵞山老,把酒看花日几巡。”[9]792“逸民”与“遗民”虽有不同,但方文常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词。方文称方仲舒是与自己一样的遗民,且把他与本家另一位遗民诗人明圃相提并论。明圃即方授(1627—1653),字子留,崇祯末年诸生,明亡后出家为僧,秘密从事抗清运动,可惜“悲困忧郁以死”[14]51,英年早逝。方授是方大美四子方应乾的第三子,方仲舒是方大美三子方象乾之孙。方仲舒对其推崇有加,存诗一首,礼敬族叔:“嗣宗真矍铄,坐立似苍松。白发登临兴,青鞋笑傲踪。寻花时有约,踏月每相逢。一杖徒虚置,天教付仲容。”[11]方仲舒与大多数明遗民一样,生活困苦,常常在诗酒唱和中寄托理想,其诗《赠方贻子》表明自己的出处态度与人生祈向:“两代遭逢成汉魏,半生踪迹各西东。今朝共醉非容易,故国风云在眼中。”[11]
三、志趣相投:方苞与江南遗民
余英时曾说,治遗民志节者必不可忽视其家庭背景。[17]93方苞的遗民家世,使得其自小与遗民常相往来,方苞尝说:“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6]174其实何止少时,纵观方苞的一生,其志趣术业相近者多为明遗民或其后裔。
方苞结识的前辈遗民主要有5位:钱澄之、杜濬、杜岕、黄周星、万斯同。黄周星和万斯同与方苞的交往,学界较少提及。
黄周星(1611—1680),字九烟,又字景明,湖南湘潭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户部主事,入清不仕。黄周星与杜濬相交甚笃,杜濬有《跋黄九烟户部绝命诗》。刘季高校点的《方苞集》以戴钧衡《望溪先生全集》为基础,其中无黄周星的任何信息。《望溪集》乾隆十一年(1746)初刊本由方苞手定,保存有黄周星的批点。该本汇集了当时147位评点者的批语。这百余位评论者中,方苞尊为“先生”者有5人,其中钱澄之、杜苍略、黄周星为明遗民。在公开出版物上称反清的遗民为“先生”,不仅凸显方苞的遗民心态,而且反映了其社会交往与价值认同。黄周星非常欣赏这个后辈,曾化用枚乘《七发》之言高度评价方苞的《书孟子荀卿传后》:“深识卓论,文体峻削,如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18]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师事黄宗羲。康熙间荐博学鸿词科,不就,“以遗民自居,而即任故国之史事以报故国”[19]。后人熟悉万斯同以布衣身份主修《明史》,而经常遗忘其明遗民的身份。康熙三十年(1691),方苞随师高裔进京,结识万氏。此后十余年间,方苞为生计和举业奔走于江淮和京畿。在京期间,方苞常参与万氏讲经之会,说万氏常“质余以所疑”,方苞亦质疑万氏。[6]520-521离京期间,二人则通过信札传递训息,《望溪集》不少篇章记其事,如《与万季野先生书》《明史无任丘李少师传》《梅征君墓表》《书杨维斗先生传后》《汤潜庵先生逸事》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方苞与万斯同曾有一次长谈,万氏不仅传史法、文法于方苞,而且有意传藏书于方苞。康熙四十一年(1702),万斯同卒,方苞因葬兄长百川于故里,未能参加万氏葬礼。康熙五十七年(1718),方苞作《万季野墓表》云:“余辍古文之学而求经义自此始。”[6]332由此可见万斯同对方苞影响之深远。
方苞往来较多的是与他一样的遗民后裔,如王源、左未生、方正玢、乔介夫、查慎行、梁质人等,尤以王源、左未生、方正玢为代表。王源(1648—1710),字昆绳,被方苞称为“敦崇堂四友”之一,其子王兆符为方苞弟子。王源虽籍贯为大兴,但从幼年到青壮年,大部分时间在江南,大量结交明遗民。其父王世德为明代世袭锦衣卫,甲申之变后归隐于江淮间,与明遗民魏禧、梁以樟、方文等过从甚密。魏、梁二氏都是王源的老师,“对王源一生影响尤甚”[20]。作为方苞最重要的好友,王源是典型的遗民二代,其父所著《崇祯遗录》,献于万斯同的明史馆。王世德考虑到生计,支持王源参加科举。父亲去世后,王源便放弃举业。在王源中举之日,方苞就曾致书:“吾兄得举,士友间鲜不相庆,而苞窃有惧焉。退之云:‘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愿时自觉也!”[6]667方苞对王源的规劝,也是对自己的警策。
左未生(1653—1720),即左云凤,号集虚,字未生,左光斗长子左国柱之子。左国柱为崇祯十二年(1639)副榜贡生,官武康知县,甲申之变后挂冠归隐。《望溪集》收录左未生家族文章6篇:《送左未生南归序》《左未生墓志铭》《祭左未生文》《左华露遗文序》《左仁传》《左忠毅公逸事》。方苞在故里“兄事者”三人,即戴名世(1653—1713)、刘北固和左未生,且“与未生游处为久长”[6]189,并称与其“臭味之同”[6]471。左未生在《南山集》案发时,自恨不能亲去相送;方苞扈从塞上,他千里探望。未生卒,方苞撰写墓志铭,并题字“皇清故友文伯集虚左先生之墓”于墓碑。该碑至今矗立故里山间,其深情日月可鉴。
方正玢字弢采,为方以智长子方中德之子,雍正七年(1729)举人,著有《梁研斋诗文集》。方中德(1632—1716)兄弟三人,与其父一样皆为明遗民,余英时称:“若密之三子,则皆可谓能世袭遗民者矣。”[17]93方苞之父方仲舒与方中德兄弟相友善。方正玢与方苞之兄方舟关系较好,后又与方苞常相往来。方苞称方舟为“十五弟”,曾为其子作《族子根颖圹铭》。此外,方苞曾于康熙壬午(1702)为方以智《截断红尘图》画外题跋:“江子长先生尝称为‘四真子’云,盖谓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也。此幅乃为摄山中峰张白云先生作也,笔墨高古绝伦,藏之名山,得垂不朽,亦幸矣哉。”[21]其对方以智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方苞的另外两位好友戴名世和朱书(1654—1707)也都有深沉的遗民情结,二人皆属方苞心中的“四君子”。戴名世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参与《明史》修纂工作。康熙五十年(1711),因《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抗清史事,并多用南明年号,戴名世被赵申乔参劾,罹难。《南山集》案发有多重因素,但与大量遗民书写直接相关。纵观该集,或歌颂抗清义士,或表彰入清不仕的志士仁人,或揭露清军江南屠城的罪恶,或刻画清廷剃发易服令后“画网巾”先生这样的悲壮形象。在《与余生书》中,戴名世甚至直接使用南明的年号,其对明朝的眷眷之情清晰可见,“史学家的良知与遗民情绪是混合并存的”[22]24。戴名世“虽生长于大清王朝,没有经历过明清之际的时代巨变,而他关注前朝之史,表彰守义之士,无所顾忌,如此行文,颇与清初的遗民相似”[23]。
朱书的父亲是典型的明遗民,明亡后以秀才身份在乡间授徒,拒绝科举。朱书深受父亲遗民意识的影响,虽然他后来迫于生计参加科举中进士,但其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前明的一片丹心。朱书的遗民意识可从五个方面来认识。其一,文章多次使用明朝年号纪年,与戴名世相仿,甚至更无所顾忌;其二,广泛搜罗明代文献,表达黍离之悲;其三,为方文作传,表彰他的抗清志节;其四,康熙三十九年(1700),与张垣、卓尔堪、王概、范莱诸友拜谒明孝陵,寄托旧国之思;其五,与遗民及其后裔如李颙、万斯同、梁份、王源、方苞等人交往密切。
通过一个人的交游可以看其情感倾向及心理认同。赵园说:“交接即在平世,也被认为节操所关。当明清易代之际,其严重性不能不百倍地放大了——尤其遗民的交接。”[24]通过其交游可以发现,方苞与父祖辈一样,与遗民更为亲近。方苞能够得到阅历丰富的遗民老辈的认可,并长期与江南遗民群体保持良好的关系,皆来自其足够真诚的言行举止。
四、继志述事:方苞的遗民史事书写
方苞的遗民家世背景,不仅生成其价值观念,而且直接影响其文学创作。方苞临终前曾托付全祖望:“箧中文未出者十之九,愿异日与吾儿整顿之。”[25]373方苞箧中未出的“十之九”文章是否与遗民有关,不得而知,但现存的《望溪集》在清代如毛细血管一样的文网管制下,仍然保留了大量书写遗民志节与史事的文章。
墓志碑铭是对前人的祭奠。《望溪集》祭奠明遗民的文章有5篇:《田间先生墓表》《杜苍略先生墓志铭》《杜茶村先生墓碣》《万季野墓表》《季瑞臣墓表》。这类文章主要揭示明遗民人生的三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的困难与坚守。选择遗民身份,就意味要放弃仕途,失去重要的经济来源,所以遗民生活大多艰苦;但他们不会因此屈从政府官绅,而是始终保持其独立的品格。比如大名鼎鼎的杜苍略,其家“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号,客至无水浆”[6]250。二是声名远播的奇节壮举。特别是影响较大的遗民,总与一些奇节壮举相连,比如钱澄之以溲溺当众溅阉党御史;万斯同一生的壮举是以布衣修《明史》,不署衔,不受俸,主持史局二十载。三是与方苞家族之交游。方苞深情回忆杜氏兄弟“流寓金陵,朝夕至吾家,自为儿童捧盘盂以侍漱涤”[6]337。不仅如此,方苞兄弟还从学于杜氏:“即教以屏俗学,专治经书古文,与先生所勖不约而同。尔时虽心慕焉,而未之能笃信也。及先兄翻然有志于斯,而诸公皆殁,每恨独学无所取衷,而先兄复中道而弃余。每思父兄长老之言,未尝不自疚夙心之负也。”[6]337-338
传记是对传主过往的记录,亦为传主人生之臧否。《望溪集》收录传记15篇,明遗民或遗民后裔占三分之一,如《孙征君传》《白云先生传》《四君子传》《左仁传》《孙积生传》等。“四君子”和左仁、孙积生基本为遗民后裔,孙征君和白云先生是真正的明遗民。孙征君即孙奇逢(1584—1675),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入清后屡召不仕,故曰“孙征君”,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方苞极为推崇孙奇逢,为其删定年谱并作传。其传名曰《孙征君传》,而不曰《孙奇逢传》,本身就包含了对孙奇逢的人生取舍与价值定位。世人提及孙奇逢,皆知其学问、义行及门墙广大,方苞却独不若此。他认为上述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6]136,征君“荦荦大者”[6]214是“志事”,是“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强以仕”[6]213的品节。没有这个品节,他只是一介学人,谈不上大儒。真正的大儒,要超越学问本身进入更高的“道”的层面。孙奇逢的“屡征不起”,以政治而言,是不与清廷合作;以时代而言,是保存故国;以士人传统而言,是保己全身。方苞曾援引《周易》卦词“介于石,不终日”来说孙奇逢,可谓的论!
白云先生即张怡,方苞为其传,突出三点:其一,抗清的壮举,虽身陷被辱,最终竟然感动贼人而获释。其二,弃世之高格,与“海内三遗民”之沈寿民、徐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弃世”与“自我放逐”,皆不可消极视之,在当时的语境下,前者是对清廷的蔑视,后者是为明朝的留存。其三,高尚的品节,可以视死如归,无视棺木优劣,但葬仪需“附身衾衣,乃卒”。“衾衣”为何?清初的剃发易服之令遭到汉人强烈反抗,清廷被迫做出让步,规定“十从十不从”,其中第二条即“生从死不从”。因此,不少汉人,包括被迫降清贰臣,死后穿戴故国衣冠下葬,表达其身心的归属。想必如张怡者亦如是。
纪事不像传记,全面反映史事,而是截取人生片段加以描绘。《望溪集》涉及明遗民逸事的,主要有《石斋黄公逸事》《明禹州兵备道李公城守死事状》等。其所涉人物为黄道周、李乘云,方苞与他们并无直接接触,而是心慕其人,笔书其事,其中写黄道周事尤其传神。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南明隆武(1645—1646年)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因抗清失败被俘。方苞记载黄道周两件逸事:一为“拒顾媚事”,记述黄道周面对秦淮名妓顾媚的诱惑,坐怀不乱,传为一时佳话;二为黄道周就义之前,在狱中淡定从容。作为逸事,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其体现的精神风貌与遗民品节(2)张则桐考证方苞所记黄道周之事,与史实难符,但也肯定其所传达的黄道周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风貌是准确而有效的。参见张则桐《方苞〈石斋黄公逸事〉疏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2期第75~78页。,让人过目难忘。方苞谈及史传文章时说:“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则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6]62这是典型的文学家写法,不拘于史实,截取片段,彰显人物性格,与史家“据事直书”不同,既承续了《史记》以来传记文学的叙事传统,也体现了文学家历史书写的特征。
礼赞崇祯帝是方苞明遗民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书孙文正传后》《书卢象晋传后》《书杨维斗先生传后》《书泾阳王佥事家传后》《书潘允慎家传后》《书熊氏家传后》《书曹太学传后》《跋石斋黄公手札》诸篇,都在讨论一个主题:明亡。方苞认为明亡最主要原因是奸臣当道、忠臣搁置和良将败死,而不提崇祯皇帝的责任。方苞文集多次提及崇祯之死为“殉社稷”或“死社稷”,他认为“君非有凉德也,朝非有暴政也,众非有离心也”[6]123-124,他称赞崇祯是“聪明刚毅之君”[6]120。这种赞美崇祯之举被视为“遗民史学的一项志业”[3]289。方苞对崇祯以及明代的态度,透露出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与明遗民一致,与清廷相反。
赞美崇祯就是歌颂大明,与此相对的,是揭露清军的暴行,特别是通过大量女子贞烈史事来进行书写。“清初文人对推广贞女形象的不遗余力,与他们的民族身份感亦密切相关”[26],这一现象“折射了亡国之际对于‘节’与‘忠’的思考,以此维持其政治伦理与道德价值”[27]。从现实层面观之,明末清初大量贞女节妇的出现,与“殉社稷”有关。方苞明确把烈女与明亡联系到一起,写甲申之变后盗贼流寇蜂起,“女子自投于水火及骂贼而毙于锋刃者,不可胜数”[6]127。方苞曾详细记载罗经甫一家女妇在“扬州十日”屠城时之惨烈:“(烈妇)乃别其姒刘氏及经甫妾梅氏、李氏。时烈妇有身八月矣,抱幼女,持宦姑而语众曰:‘吾多见古书中,妇人遭乱而求生者,忍以身试乎?’众皆哭,从而登楼者凡十人。命一婢下举火,火发,亦奋身跃入。兵定后,众骨藉藉,惟婢一足尚存。”[6]381-382在经历《南山集》案的打击之后,方苞还能够在文集中收录描写清军屠城之类的文章,足见其内心对清廷的态度。
文学是“人的身份认同得到了最具启示性的揭示的空间”[28]。通过遗民书写可以发现,方苞对遗民志节的高度赞扬与文化认同。
五、结 语
综上,梳理方苞一家三代家世背景可以发现,其价值观念、情感倾向、士人交游等方面皆有相似性和传承性,遗民情结是其三代血脉贯通的精神寄托,他们以自己可能的方式,保持着与明遗民及其后裔或显或隐的联系。这种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既是清初江南遗民文化的反映,也是他们长期与遗民交往的必然结果,同时表现在文学创作中。这些书写都是委婉其辞,隐约其事,“以隐语传心曲”[17]193,毕竟方苞一直生活在《南山集》案的巨大阴影中。在清廷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只能借助春秋义法,把一腔孤怀与幽怨“迂回盘折于词意之中”[22]25-26。
透过遗民家世与文学书写,重新审视方苞与清廷的关系,绝非“御用文人”可以涵括。方苞会试中式后放弃殿试,在清廷长期以白衣身份从事修书工作,后期担任官职也每每推辞,晚年致仕归里,全祖望评价他“犹喜素丝在,未为缁所移”[25]2181,凡此种种,是否与遗民家世有关?细究其理,皆关涉方苞的文化身份问题。身份认同是个体对于“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她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29]。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是非判断,而是自我与他人、家庭与社会、本族与异族、情感与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交织。遗民先辈杀身成仁的志节与反清复明的壮举,着实令人敬仰。但作为大清子民,也有现实忠君爱国的臣子要求。方苞处在明清、满汉之间,难以避免旧国与新朝的“角色困扰”[30]。因此,就文化认同而言,他虽是清人,但对明朝亦怀有眷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