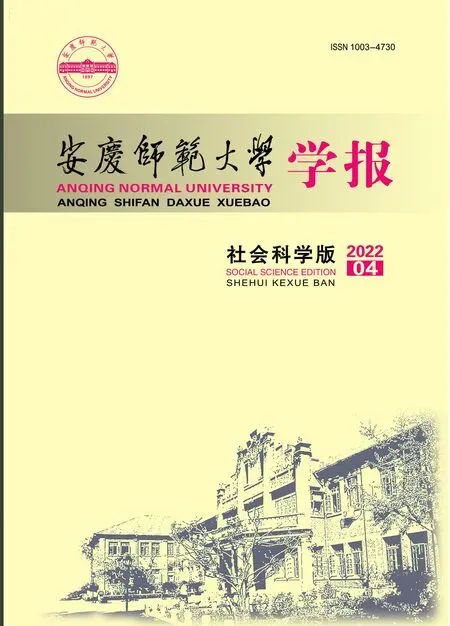方苞遭乾隆罢黜深层缘由探微
宋豪飞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南山集》案彻底改变了方苞的命运。方苞因文才突出,享有盛誉,再加上大学士李光地力救,得以免死,以布衣入直南书房,成为康熙的御用词臣,此后供奉内廷,以修书为务。方苞与李光地、徐元梦等朝中重臣交往密切,彼此切磋问学,谈论时事,甚是相得,但他拒绝二人举荐为官,然所见闻时弊,多有指陈。雍正继位之初,对方苞更添恩宠,释其旗籍,还归族人,由是方苞感念“天恩”浩荡,思以图报。及其接受雍正授予官职,便开始上疏言事,忠心至诚,深得雍正宠信,官职屡迁。方苞个性刚直,直言无隐,因而招致同僚忌恨。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八日,雍正驾崩,乾隆登基。方苞于乾隆朝为官七年,七十五岁时归里。乾隆对方苞的态度以乾隆四年(1739)为界,明显地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初加恩宠,后予斥黜。今笔者探析方苞遭乾隆罢黜缘由,揭示其中的深层原因,或有助于人们对清廷皇权专制的认识和对方苞的客观评价。
一、乾隆对方苞的态度
乾隆嗣位之初,确实极为器重方苞,“有意大用先生”[1]882。当时乾隆欲追践古礼,议行三年之丧,特下诏命群臣详稽典礼。王大臣令礼部尚书魏廷珍偕方苞拟议。方苞因欲复古人以次变除之制,随时降杀,定为程序,乃作《丧礼议》。虽受到大臣阻挠,未获施行,但方苞仍坚守古礼,而且他所教习的庶吉士,在守丧期二十七日内,斋宿馆舍,无人敢饮酒食肉,其他部院则没有谁这样做。
当年,顺天乡试考官顾祖镇、戴瀚以前列十卷进呈,乾隆因料理雍正丧事,“正哀痛迫切之时,岂复能留心文字”[2]196,故特旨命徐本、福敏、方苞、杨超曾四人“覆阅”,拟定进呈。当乾隆知悉本年顺天乡试“弊窦甚多”,遂将两位主考官革职,拿交刑部严审;对于方苞等人“毫未经心,漫无觉察,亦著交部严察议奏”[2]196,但并未有任何惩处。乾隆元年,乾隆还命令从今科会试落选遗卷内,“尚有文理明通,可以取中之卷,应拣选进呈,续出一榜,准其一体殿试”[2]406,所有荐卷,著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侍郎邵基、张廷瑑、学士方苞,共同阅看。
乾隆元年(1736)春,乾隆因为方苞工于时文,命令方苞裒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以为举业指南,且要求方苞“务将入选文,逐一批抉其精微奥窔之处,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以拳服摩拟”[2]502。直至乾隆四年(1739),方苞选择时文告竣,奉旨题名《钦定四书文》。
是年,乾隆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兵部尚书甘汝来为《三礼义疏》馆总裁,礼部尚书杨名时、礼部左侍郎徐元梦、内阁学士方苞、王兰生为副总裁。方苞奏请出秘府《永乐大典》,取宋元人经说版本以校勘文献,首开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先河。
方苞于乾隆元年(1736)春,69岁时,一度再入南书房。乾隆还给予特别关照,“夏六月,上怜先生老病,命太医时往诊视”[1]883。乾隆二年(1737)六月,乾隆擢升内阁学士方苞为礼部右侍郎,但方苞自陈年老衰疾,步履艰难,筋力自效之事,乞赐宽免。乾隆遂下旨,予以“特权”,“诏免随班趋走,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方苞“虽不甚入部,而时奉独对;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谘先生,先生多密陈”[1]883,但也正因如此,方苞遭致臣僚更大的忌恨,“于是盈廷侧目”[1]883。同年十二月,方苞复以老病“恳解部职,专力修书”,得以批准,“著仍食原俸,在书馆行走”[2]952,并教习庶吉士。
然而,乾隆四年(1739),乾隆对方苞的态度大变,对其大加斥责,并最终罢黜其职。乾隆因何如此?《清史稿·方苞传》有如下记载:“苞以事忤河道总督高斌,高斌疏发苞请托私书,上稍不直苞。苞与尚书魏廷珍善,廷珍守护泰陵,苞居其第。上召苞入对,苞请起廷珍。居无何,上召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苞移居城外。或以讦苞,谓苞漏奏封语,以是示意。庶吉士散馆,已奏闻定试期,吴乔龄后至,复补请与试。或又以讦苞,谓苞移居乔龄宅,受请托。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3]10272方苞所做的这三件事,被视为方苞犯下的三大过错,导致了罢职的结果。
《高宗实录》对此亦有记载,乾隆怒斥方苞,并道出事情的大概情况。笔者录之如下,两相参证,以便考察实情:
(乾隆)又谕曰:“方苞在皇祖时,因《南山集》一案,身罹重罪,蒙恩曲加宽宥,令其入旗,在修书处行走效力。及皇考即位,特沛殊恩,准其出旗,仍还本籍。又渐次录用,授职翰林,晋阶内阁学士。朕嗣位之初,念其稍有文名,谕令侍直南书房,且升授礼部侍郎之职。伊若具有人心,定当痛改前愆,矢慎矢公,力图报效。乃伊在九卿班内,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众所共知。适值伊以衰病,请解侍郎职任,朕俞允之,仍带原衔食俸。上年冬月,因伊条奏事件,朕偶尔召见一次,伊出外即私告于人,曾在朕前荐魏廷珍而参任兰枝,以致外间人言藉藉。经朕访闻,令大学士等传旨训饬,伊奏对支吾,朕复加宽容,未曾深究。近访闻得伊向住魏廷珍之屋,魏廷珍未奉旨起用之先,伊即移居城外,将屋让还,以示魏廷珍即日被召之意。又庶吉士散馆届期,伊已将人数奏闻。内阁定期考试矣,伊复于前一日,将新到吴乔龄一名,补请一体考试。朕心即疑之。今访闻得伊所居之屋,即吴乔龄之产,甚觉华焕,显系受托,为之代请。似此数事,则其平日之营私,可以概见。方苞深负国恩,著将侍郎职衔,及一切行走之处,悉行革去,专在《三礼》馆修书,效力赎罪。其武英殿事务,著陈大受、刘统勋管理。”[4]416-417
乾隆痛斥方苞之“罪”,似乎言之凿凿;其于盛怒之下,对方苞厉语诘责,不免过激。综观这三件事,看似事实清楚,然细加探究,耐人寻味。
二、方苞“三宗罪”
方苞所为三件事,在乾隆看来,涉及“营私”“泄密”“请托”等“罪状”,已经触及到他的专制皇权底线了。于是他绝不容忍,直接罢黜了方苞的官职,剥夺其“特权”,责令其修书效力。表面看来,方苞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问题是,方苞为何这样做?如若深究方苞之所为,窥探其内心深处的难言之隐,或自有其迫不得已之处,亦存在合乎情理之处。笔者妄加揣测,意在分析其“罪”之“是”与“非”。
(一)方苞所犯“三宗罪”
1.方苞与高斌的矛盾:“罪”涉“营私”
方苞初入内廷,于蒙养斋修书,高斌即已供职斋中。方苞认为高斌日后必将发达,高斌也很尊重方苞,二人一度相处友善。雍正十一年(1733),高斌署理江南河道总督一职,负责治水。乾隆元年(1736)四月,黄河涨水,乾隆命高斌提出治水之策。高斌建议疏浚毛城铺城以下河道,并于相应位置开河建坝。此议被乾隆采纳,但遭到众多朝臣反对,御史夏之芳、甄之璜等人抗颜力争,竟至下狱。方苞为此请徐元梦禀奏皇上,“不当以言罪谏官”[1]884,乾隆即日释放了二人。与此同时,方苞又独自上疏乾隆,指陈高斌刚愎自用。高斌自请入朝面对,乾隆知其与方苞关系亲密,就出示方苞奏疏给他看。高斌获悉内情,心中愤恨不已,寻思报复方苞。他于是呈交乾隆方苞曾经写给他的书信,信中方苞请求高斌关照在他手下供职的方苞的一个门生。此事即《清史稿·方苞传》中所记“高斌疏发苞请托私书”。此后,高斌屡屡弹劾方苞,又因方苞在朝中竟至树敌太多,所上数疏,“驳不行”“格于廷议”,乾隆二年(1737)十二月,方苞自知孤立,乃密陈其状,且以病为由而不得不请辞礼部右侍郎之职。
方苞主动辞职,直接源于他与河督高斌矛盾的爆发,而方苞为其弟子请求高斌予以关照,“罪”涉“营私”,虽然乾隆对此并未过重指责方苞,只是“稍不直苞”。此事已经影响到乾隆对方苞的态度,但尚未达到令乾隆愤怒的地步。当方苞提出辞职时,乾隆便即刻应允。乾隆四年(1739)二月,乾隆下诏重刊《十三经》《廿二史》,还命方苞充经史馆总裁。方苞上疏请勅内府、内阁藏书处遍检旧本,谕王大臣及在京各官家藏旧本,并勅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督抚购送旧本,详校改正。乾隆听从了他的建议。四月,《四书制义选》成,奉表以进,命名《钦定四书文》颁行天下。其后于乾隆九年(1744),该书始定为乡试、会试及岁、科试的标准教材。
2.方苞搬离魏廷珍居所:“罪”在“泄密”
乾隆三年(1738)十一月,方苞上疏言事,乾隆为此召见方苞,并征询他关于左都御史的合适人选。方苞便推荐了礼部尚书魏廷珍。方苞与魏廷珍向来关系密切,当时魏廷珍奉命守护泰陵,方苞寄居于魏邸。此次召见之后,方苞即私下“泄露”与乾隆谈话的内容,并声称是他举荐了魏廷珍。不久,乾隆果然任命魏廷珍担任此职。然而在魏廷珍的人事任命尚未正式下达之前,方苞就搬离魏邸,移居城外,以此“暗示”魏廷珍将获升迁。此事传扬开来,流言四起,乾隆下令追查,并派大学士等传旨训饬方苞。
在乾隆看来,方苞的这种做法涉嫌泄露朝廷“机密”。更为严重的是,方苞散布其举荐魏廷珍、弹劾任兰枝之言,弄得“外间人言藉藉”,人或以为方苞干预朝臣任免,这已经触犯了皇帝“用人之权”,犯了大忌,自然招致乾隆的愤怒。
3.方苞临时增添吴乔龄考试:“罪”在“请托”
乾隆四年(1739)五月,庶吉士散馆考试名单已经上报,且在内阁定下考选日期,然而在准备考试的前一天,方苞又临时增补吴乔龄的名字,允许他参加考试。方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搬离魏邸后,即借住在吴乔龄家里,如此一来彼此之间就发生了利益关联。方苞此举确实很不妥当。纵然方苞认为吴乔龄错过这次考试机会实在可惜,本着为朝廷荐举人才的目的,添补他参加考试,这种做法或许无可厚非。只是在这种情形下,方苞这样做,被告发“显系受托,为之代请”,遭到乾隆斥责,他为此百口莫辩。官员“营私”“请托”,历来是封建官场的痼疾,清初皇帝亦一再严厉惩处,但终究难以彻底根除。不管方苞是否真的“请托”,但已是罪责难逃。
(二)关于方苞“罪”与“非罪”之辩
1.方苞“泄密”,事关皇帝“用人之权”
方苞私下“泄露”与乾隆的谈话,涉嫌“泄密”,并声称是自己举荐魏廷珍,这已经触犯了皇权大忌,事关皇帝的“用人之权”。
清朝自康熙始,即加强封建专制集权,首先就表现在“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5]。康熙就说过:“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6]586故臣下不得专擅。他将用人之权收归自己“上裁”,高度垄断,不许臣僚僭越。如果有人宣称举荐某人为官,康熙则严词驳斥:“今用一人,外人即曰,某大臣荐举,故用之。或有商议之事,即声言某大臣称某官之优,言某官之劣。致躁进之徒,营求奔竞,从此而起。凡官之优劣,若不问,何由而知?大臣虽有荐举,用舍皆出于朕。间用一二人,亦朕所知而用者;若但因大臣荐举而用之,朕所理者,又何事耶?虽有问九卿举出之人,亦得者半而不得者半,此皆倖遇耳。”[6]446此后清代帝王皆严控用人之权,不容他人染指,也十分忌讳大臣传言荐举某人。另外,皇帝召见大臣独对,所言内容臣子当不可肆意外传。如康熙宠臣李光地,“光地益敬慎,其有献纳,罕见于章奏”[3]9898。一代名相张廷玉,深得雍正宠信,雍正赞其“敬慎小心,十一年如一日”[7]406。张廷玉自己也说过:“内直趋承,无日不蒙召对,每有刍荛一得之见,或口奏,或具折,皆请皇上特颁谕旨,宣播于外,从来未留片稿于私室。”[7]405他若举荐翰林,“有所荐举,必深知其人之材品而后上闻,即擢用,终不以语人。其诸所陈奏,虽家人子弟,不得以间请,非宣示,人终莫得而知也。”[7]558(汪由敦《光禄大夫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致仕谥文和桐城张公廷玉墓志铭》)李光地、张廷玉等能做到“敬慎小心”,根本在于他们深知帝王权术、官场规则、为臣之道。而方苞竟然敢对外传言是他荐举魏廷珍,显然触犯了皇权禁忌。
2.方苞搬离魏宅,力避“朋党”嫌疑
乾隆斥责方苞的过错:“近访闻得伊向住魏廷珍之屋,魏廷珍未奉旨起用之先,伊即移居城外,将屋让还,以示魏廷珍即日被召之意。”这条指责有点似是而非、强词夺理之感。但笔者所思考的问题是,方苞得知魏廷珍即将提拔重用,虽任命尚未下达,他何以要急于搬离魏府?或以为方苞不愿攀附权贵,以此保持距离。此说难以成立。二人向来交情深厚,且同朝为官,以方苞刚直个性,自然不会攀附臣僚。方苞如此而为,笔者臆测,正在于避免授人以“结党”的口实,落下“朋党”的嫌疑。先前他为自己的门生任职而写信向高斌打招呼,事涉“营私”;此后因居住在吴乔龄宅中而临时增补其名字以使其应试,关乎“请托”,方苞所作所为,或许让乾隆警觉,这种“营私”“请托”涉嫌“结党”,一旦形成“朋党”势力,则是皇权难以容忍的,必须坚决打击。
清廷对朋党忌讳尤深,对官员结党营私最为痛恨,一再严禁。“朋党是专制政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特殊利益集团,它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形态,但却在师生、故吏、同年、乡族等亲情关系推动下,基于共同的或相似的政治利益,以一人或数人为核心,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群体,其成员在政治生活中采取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和态度,互相支持,互相攀援,以维护其共同的利益。”[8]康熙对大臣结党营私之情状了然于胸,他曾斥责大臣:“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有职掌官员以上,全不恪勤乃职,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为援引倾陷,商谋私事,徇庇同党,图取货赂,作弊营私,种种情状,确知已久。”[6]441故而他一再告诫大臣,“卿等职任,俱关重要,各宜恪体朕衷,持廉秉公,实心尽职,毋得营私结党,师生亲友,互相徇庇,听受嘱托,遇事推诿,自图便安,务期于国计民生,实有裨益。”[6]586并严厉警告群臣,如不改朋党之习,“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交结朋党之罪”[9](《康熙圣训·饬臣工二》)。然收效甚微,在朝大臣自大学士以下,互相交结,蔚然成风。雍正继位后,初次御门听政日,即面谕诸王文武大臣,“谆谆以朋党为戒”[10]355,次年御制《朋党论》颁示群臣,严词训诫,恩威并施:“今之好为朋党者,不过冀其攀援扶植缓急可恃,而不知其无益也。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亦甚可悯矣。朕愿满汉文武大小诸臣合为一心,共竭忠悃,与君同其好恶之公,恪遵《大易》《论语》之明训,而尽去其朋比党援之积习。”[10]358-359早在顺治时,陈名夏结党较为典型,但最终身败名裂。康熙时,以徐乾学、高士奇为代表的汉官集团和以明珠为代表的满官集团互相争斗。乾隆即位之初,朝廷中即已形成以鄂尔泰、张廷玉为中心的朋党势力,满洲大臣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两派泾渭分明,互相攻讦,势如水火。昭梿在《啸亭杂录》中就记载道:“上(乾隆)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朋党论》戒之。”[11]面对此种情形,乾隆早已警觉,其后便有逐步打击双方势力的举措。
方苞当然知晓当朝朋党之争的现状,也清楚乾隆对此莫大的猜忌。他写信给高斌,请其关照一下他的门生,就人情世故而言,此举本无可非议,不料却与人口实,视作有“结党”嫌疑,未免冤屈。他急于搬出魏宅,有意避开外界的闲言,力避“结党”之忌,这应是他难以言说的苦衷,但这样做却被乾隆认为是“泄密”,而他却根本无法为自己辩解,只能默默承受乾隆的怒斥。乾隆七年(1742),方苞回归南京之后,杜门著书,不接宾客,江南总督尹继善三次登门求见,方苞皆以疾辞而不见。这是否也可以看出方苞为避免“朋党”嫌疑而有意为之?其良苦用心几人能知?同样,方苞临时增补吴乔龄姓名,使其得以按时参加庶吉士散馆考试,有人告其“请托”,此举或许有违规定,但方苞也许不忍其错失这次考试机会,亦未可知。或认为方苞借住吴宅,受之“请托”,已然结为朋党,而乾隆为之震怒,进而罢黜其职,也就不难理解了。
乾隆善于玩弄权术,刻薄寡恩,猜忌群臣,严防大臣结党,以此驾驭群臣,与康熙、雍正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再举他对待魏廷珍为例,可见一斑。乾隆三年(1738),他授魏廷珍左都御史;四年,迁工部尚书;五年,魏廷珍以老病乞休,乾隆将其罢官。数日后乾隆与礼部尚书任兰枝谈话,他知晓任兰枝与魏廷珍为同年进士,“因不怿,谕:‘朝臣师友门生援引标榜,其端不可开。’”[3]10277二人同朝为官,因为是同年进士,乾隆就“不怿”;在他看来,二人就是朋党,岂不荒谬?然由此佐证乾隆无端猜忌朝臣,极其痛恨朝臣“结党”,则显然可知。
三、方苞与同僚矛盾激化
方苞与河督高斌的矛盾,引起乾隆“稍不直苞”;乾隆对方苞已经心生不满,虽然并未惩处,但毕竟态度已有所改变。而方苞“泄露”与乾隆谈话的内容、搬离魏廷珍寓所,及补请后到者考试,这几件事看似是导致方苞“落职”的直接原因,但细加分析可知,方苞“落职”其实是他与同僚长期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亦成为乾隆利用此事借机打击前朝旧臣、为自己立威,意在惩戒朋党,以巩固皇权专制统治的手段。
方苞与同僚的矛盾,大体上以雍正九年(1731)方苞受官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为开端。随着方苞任职,也随着他积极上疏言事,刚直敢言,不自觉中得罪了一些权贵,遭致同僚的忌恨,渐渐树立了众多的对立面。如雍正十年(1732)冬十二月,孙嘉淦以刑部侍郎为顺天府尹兼祭酒,因为个性刚直而为和硕果亲王所憎恨。亲王于是派人劝说方苞上疏弹劾孙嘉淦,并允诺他取而代之。方苞严词拒绝,来人“以祸怵之”,方苞“以死力辞”。没过几天,孙嘉淦竟被人弹劾贪赃而下狱。方苞对鄂尔泰说:“孙侍郎以非罪死,公复何颜坐中书?”[1]881于是鄂尔泰以全家百口性命来担保孙氏冤枉,孙氏遂得以免罪。方苞此举自然得罪了果亲王,遭其忌恨,或伺机报复,亦是意料中事。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方苞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虽然方苞以足疾辞,但雍正仍命他“专司书局,不必办理内阁事务,有大议,即家上之”,予以优待与“特权”,然而方苞“自是益不谐于众矣”[1]882,更加难容于那些忌恨者。
方苞在《寄言》一文中记其与九卿“要人”交恶的缘由:“仆见恶于九卿要人,自廷议北河始。仆谓:非于淀外别开一河,导浊流直达海口,则忧无可弭。要人曰:‘子书屋中人也。顾总河、李宫保之明达,久谙河事,吾辈乃绌所奏而用书屋中议,如无成功,孰任其咎?’仆曰:‘其然,诸公连章治某之罪可也。’不得已乃私于用方。”[1]651某位九卿要人摒弃方苞所提出的治河方案,彼此之间的矛盾随之激化。且憎恨方苞的朝廷要员还有数人,方苞在《答陈可斋书》里写道:“与鄙人同心者,惟顾用方、德济斋、陈秉之,而一二要人不惟深疾鄙人,并憎二三君子,此西林所以忧愚之致祸也。”[12]57他在《答尹元孚书》亦道出实情:“仆以确守经书中语,于君不敢欺,于事不敢诡随,于言不敢附会,为三数要人所恶,常欲挤之死地,赖圣主矜悯,尚存不肖躯。”[12]59
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继位不到一月,即下诏令文武诸臣轮班条奏,“各抒所见,深筹国计民生之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2]183。此后乾隆多次下旨,广开言路,俾大臣皆可密封折奏,上疏言事。方苞因此连上三疏:《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疏》《请定常平仓谷粜籴之法疏》《请复河南漕运旧制疏》,三疏俱下部议行。乾隆元年(1736)三月,方苞上《请备荒政兼修地治疏》《拟定纂修三礼条例疏》;冬,上《请定经制疏》。乾隆二年(1737)六月,方苞擢升为礼部右侍郎。方苞仍以足疾辞,但乾隆下诏允其“免随班趋走,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方苞“虽不甚入部,而时奉独对;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谘先生,先生多密陈”[1]883。可以说,方苞因受乾隆宠信,官职晋级,奉诏独对,密陈大事,招致“盈廷侧目”,他与对立面的矛盾越发严重,甚至激化。方苞与河督高斌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尖锐化,此事引起乾隆对方苞的不满。《方苞年谱》还记载有数事:“礼部荐一赀郎入曹,亲王莅部已许之,先生以故事:礼部必用甲科,不肯平署。会新拜泰安为辅臣,起河间魏尚书为总宪。忌者争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为,若不共排之,将吾辈无地可置身矣!’自是凡先生所奏疏,下六部九卿议,皆合口梗之。河督亦劾先生,礼部中又有挺身与先生为难者。”[1]884他们逐渐形成了一股势力,为了自身利益,极力仇视方苞,针对方苞的奏疏所提建议一概“驳不行”“格于廷议”。故而半年之后,方苞请求辞职,乾隆慨然应允,令他仍带原衔,食俸,教习庶吉士。但是,那些忌恨方苞者仍不罢休,“众以上意未置公”[13]89,(全祖望《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他们在寻找机会,定要除掉方苞而后快。直至乾隆四年(1739),方苞增补吴乔龄应考,被他们抓住把柄,告发方苞受人“请托”,乾隆大怒之下罢黜方苞,但命其仍在书局行走。
朝廷中存在着方苞的敌对者,他们因为某种利益或见解不同而敌视方苞。试想一下,乾隆怒斥方苞的这些“罪状”,乾隆从何得知?当然是得知于那些臣僚们的告讦。《清史稿·方苞传》即写的明白:当方苞从魏廷珍府邸搬出,移居城外时,“或以讦苞,谓苞漏奏封语,以是示意”;当方苞补请吴乔龄参加庶吉士散馆考试时,“或又以讦苞,谓苞符合居乔龄宅,受请托”。这些反对者如此这般搬弄是非,抑或无中生有,夸大其词,以此密告乾隆,意在扳倒方苞,终于达到了目的。所以说,方苞被罢职,是他与同僚们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
方苞罢职以后,专在《三礼》馆修书。乾隆六年(1741)冬,方苞编纂完成《周官义疏》,进呈乾隆御览。乾隆留览兼旬,命发刻,一无所更。乾隆七年(1742)三月,方苞转呈大学士等上奏,请求告老归家:“革职侍郎方苞奉旨在《三礼》馆效力赎罪,分纂《周礼》已竣。年老患病,可否准其回籍调治?”乾隆恩准,“赏给翰林院侍讲品级顶带,准其回籍。”[14]于是同年四月,方苞离开京城回到南京,从此结束了他的仕宦生涯。自此杜门著书,不接宾客。再七年,辞世,年82岁。
四、陈祖武对方苞之评价
陈祖武写有《方苞》传记文,见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九卷)。文中简述方苞的生平经历,前半部分文字大抵平实,但他在概述方苞于乾隆朝作为,涉及对方苞的评价,笔者以为,则有失公允。我们先摘录其中的两段文字:
方苞素喜结交朝廷显贵,康熙时的大学士李光地,雍正朝显赫一时的徐元梦、鄂尔泰、张廷玉等,无不与他有密切往来。他不仅通过这些人奏陈政见,影响国事,而且还利用文学侍从的便利,在奉旨召见时,进行秘密陈奏。这种趋炎附势的痼疾和诡密莫测的劣习,日渐激起同僚憎恶。同河道总督高斌的倾轧,更把他假道学的虚伪面孔暴露无遗[15]302。
已届七十高龄的方苞,在官场倾轧中受挫后,于乾隆二年(1737年)十二月,以老病为由,疏请辞去礼部右侍郎任。乾隆准许了他的请求,命他在翰林院以原衔教习庶吉士。如果方苞自此专意课徒授业,或许还可望争取一个较好的晚景,但是封建官僚以权营私的痼疾驱使他不能甘于寂寞,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5]303。
很显然,著者对方苞的评价极其负面,多加贬抑之词,斥其具有“趋炎附势的痼疾”“诡密莫测的劣习”“假道学的虚伪面孔”“以权营私的痼疾”等诸多恶劣品行。这固然是他对方苞缺乏全面真实、客观细致的研究,也显然缺乏客观理性的态度。他做出如此评价,与《高宗实录》里所记载的乾隆对方苞的斥责何其相似,或许就是受之影响。这“三宗罪”关乎乾隆对方苞态度的转变,并最终导致方苞被罢黜,其仕途走向终结。乾隆盛气凌人,对方苞妄加谩骂,任意贬斥,后人自有公论。而今学者陈祖武先生仅依凭这三件事就对方苞肆意贬抑,承袭乾隆之言,作如此评价,显然有失公允。
可以看出,《清史稿·方苞传》对方苞的记载,坚守史家“秉笔直书”的原则,尽可能客观地书写史实而不予置评。如何看待史实并如何评价传主,这是作传者和读者的识见,见仁见智,无法强求。然而知人不易,它需要对传主有一个客观理性全面深入的了解,这是传记写作基本的要求。盖棺未必就能定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对关涉方苞的“三宗罪”展开辨析,上述文字已经明了,其“罪”之“是”与“非”,应该予以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我们不必讳言其“罪”,但我们更需要在历史的语境下细致剖析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
五、结语
方苞因事得咎,触怒乾隆,乾隆对方苞不但予以严词斥责,而且革去一切职务。乾隆言辞尖酸刻薄、盛气凌人,他指出方苞经历《南山集》案后,蒙受康熙、雍正及自己对他的恩遇,方苞理当感恩图报,而现在他认为,方苞“在九卿班内,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众所共知”;断言方苞“其平日之营私,可以概见”,对方苞人品个性痛加斥责,对其形象全面否定,不留丝毫情面。不仅如此,其后御史张湄上疏,言朝廷群臣阻塞言路,箝制言官之口,乾隆阅之,不禁怒火中烧,斥之“狂妄”之辈,所奏“为此狂瞽之奏,显系比附傅为□,而薰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盗名之恶习”[4]483。这次又牵连到方苞,为方苞增添一条新罪名,并召见满、汉奏事大臣谕之。
及至两年之后,御史仲永檀参奏提督鄂善,奏本中“又奏称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则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乾隆辩解道:“其有宣洩于外者,则皆系本人自向人言,以邀名誉,而反谓自内宣洩,以为掩饰之计。”他又以方苞为例,“朕犹记方苞进见后,将朕欲用魏廷珍之意传述于外,并于魏廷珍未经奉召之前,迁移住屋以待其来京。此人所共知者。”他对此耿耿于怀,亦可知极其深恶痛绝,故而对此奏疏所提及之事“必须彻底清查,不便含糊归结,亦正人心风俗之大端”[4]999。
乾隆对方苞的态度急剧转变,他对方苞虽是无情,但也并未绝情,最终允许方苞以翰林院侍讲衔告老还乡。方苞个性刚直,出言无忌,故遭人忌恨,亦是必然。方苞去职后,乾隆曾对方苞有一个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始先生既落职,上屡顾左右大臣言曰:‘方苞惟天性执拗,自是而非人,其设心固无他也。’”[13]85(雷鋐《方望溪先生行状》)但方苞终究不为臣僚所见容,“一日,吏部推用祭酒,上沉吟曰:‘是官应使方苞为之方称其任。’旁无应者。”[13]89(全祖望《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方苞罢职后,见到弟子沈廷芳,感叹道:“老生以迂戆获戾,宜也。吾儿道章数以此谏,然吾受恩重,敢自安容悦哉?”[13]95(沈廷芳《方望溪先生传》)方苞挚友朱可亭于乾隆二年就曾告诫方苞:“子性刚而言直,吾前于众中规子,谓子幸衰疾支离,于世无求,假而年减一纪,尚有国武子之祸。欲诸公谅子之无他,而不以世情相拟耳!宾实(杨文定字)既没,吾病不支,子其惧哉!”[1]689-690(方苞《叙交》)其实,方苞何尝不清楚自己的个性呢?他之所以固执于刚直敢言,不惧祸患,正是要以此报答康雍乾三帝对他的知遇之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