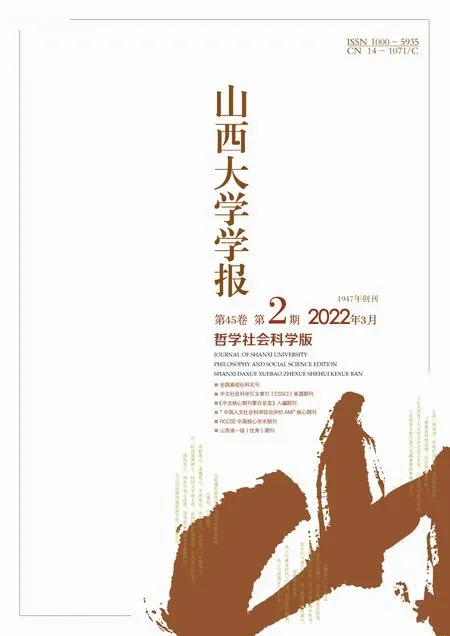回归经典再出发的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
张 亮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体系进入内部矛盾活跃期,各种问题、各种危机不断暴露、爆发,这在让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破产的同时,也让陷入长期低谷徘徊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等待已久的复兴发展契机。较之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曾经达到的理论高度、学术影响深度和社会影响广度,我们认为,尽管在成果数量上拥有看似繁荣的景观,但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的发展尚未实质性地摆脱冷战结束以来的相对衰落[1]。不过,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始终没有停止探索创新的脚步,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只是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创新,而在于如何创新。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曾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热衷于解构与批判、与各种“后-”学嫁接等方式“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当作陈旧过时的无用之物丢弃一旁。时间是公正的,能够鉴别玉之真伪、材之优劣,以及道路、方法之行与不行。于是乎,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自觉改进曾经的“时尚之病”,努力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期冀从中汲取思想与道义的力量,以科学地批判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问题,实现真实有力的理论创新。迷途知返,往哲是与。审视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理论创新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把握前者的创新理论,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校正我们自己的创新道路。
一、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持久价值
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170多年前的19世纪40年代,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不过,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总是会展现出自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不是一经形成就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体系,而“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每当这种时刻来临,就会有人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给当代问题提供直接现成的答案而怀疑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试图用远离的方式来“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也是因此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技术及其变革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社会的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更具民族国家差异,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变得不像过去那样直接明显,从而让西方理论家们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是否依旧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美国社会理论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率先做出系统回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正在超越19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中,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不再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也不再有效了,最终,贝尔含蓄而不失得意地宣称资本主义胜利了:“后工业的转变意味着工具力量的加强,超越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越人的力量。……后工业的转变并没有提供‘答案’。它只给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新的制约和新的问题——所不同的是,现在这些新的规模是世界历史上过去从未想象过的。”[3]随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左派社会理论家也陆续做出回应,或主张“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或推出“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三部曲”,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宣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过时”了。面对马克思主义“过时”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发生明显分化:有的抱残守缺、坚守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的退回学院、反思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向右转;还有的则选择与各种新兴“后-”学相结合,试图在时髦的学术潮流的嫁接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多元分化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光芒被遮蔽、重要性被淡忘。1991年12月26日,红旗落地,苏联解体。冷战以美国的胜利突然结束。新自由主义者们狂热地宣称,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已经终结于美国式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也陷入巨大的迷惘与困境,尽管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逆势而上,强调“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4],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还是黯然失色,被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日益远离。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远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相对缓慢的渐进过程,但重新发现、拥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则在新千年即将来临的前几年发生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让包括新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意识到,虽然苏联解体了,但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摆脱马克思所揭示的内在危机。在此背景下,1998年,巴黎召开了规模宏大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大会”,大会组织者之一拉扎尔夫人(Francette Lazard)说:“《宣言》不是一般的书。它不是冰,而是碳,放在锅里能使水沸腾起来。我们为什么不使历史重新沸腾起来呢?”这次大会的召开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艰难走出苏联解体的阴影,缓慢而坚定地回到西方世界。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千年思想家”大型调查,被人遗忘的马克思不仅成功入围,而且名列第一!英国自由主义评论家米尔克斯威特(John Micklethwait)不得不承认,尽管马克思是“自由主义的死敌”,但他却对资本的全球化作出了成功的预言,“关于这个特定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立即会承认的事情之一是他最后发现的一个悖论:全球化越成功,它给予自己的后坐力就越大。这个过程与冲向沙滩的海浪确实不无相似之处:后浪击碎前浪,更有后浪在后头。”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命运问题,依旧具有现实性:“如何克服全球化表面上的坚不可摧与内在的虚弱之间的悖论,依旧是新的21世纪的最重要挑战。”[5]既然如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选择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就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进入21世纪后,“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欧洲难民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2020年新冠疫情、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重大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发生,新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论”不断遭受打击而最终破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持久价值则一次次得到验证,激励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汲取思想与道义的力量,推进理论创新。
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而言,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意义深远:第一,它终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长期思想钳制,勇毅地突破“历史终结论”幻象,重新开始构想人类社会的非资本主义未来;第二,它终于否定自己曾暗自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再次确认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资本主义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只要资本主义没有被扬弃,马克思主义就始终具有不可超越的现实性,就此而言,它依旧是19世纪的马克思的同时代人;第三,它终于超越自己曾经的颟顸与自我膨胀,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在这个方面,不同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问题不同,回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自然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是都努力把握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科学地批判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新变化新特征新问题,让马克思主义“活”在当下、发挥作用于当下。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哲学批判再出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近一次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滥觞地,也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重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登陆点。这当然不是巧合。过去,人们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怀疑“两个必然”,放弃了对唯物史观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信心;现在,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仍按照以前的方式运行,并没有进行任何改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其原因在于它所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不仅没有丝毫软化,反而变本加厉地愈发无情和极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因此愈加中肯。”[6]1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让人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两个必然”没错,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旧是科学地批判地认识资本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建构21世纪的资本主义哲学批判理论,由此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哲学批判建构中,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回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一些广为人知的大众名著,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几乎不征引经典作家稀见的手稿、摘录笔记等“秘籍”,从而与国内学界当下言必称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的倾向构成巨大反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不“专业”呢?这是因为他们清楚:第一,MEGA2的使用者主要是极少数文献编辑出版专家以及需要解决文献编辑争议的小众学者,不是像他们这样的理论家、一般研究者,也不是阅读他们论著的广大普通读者,更不是他们要与之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这些广为人知的大众名著里得到了非常权威、足够充分的阐述,是后世的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文献来源,尽管MEGA2提供的文献学信息可能改变人们的某些理解,但这些改变在数量上是极少的,在重要性上是无关宏旨的、相当次要的;第三,在当前历史阶段,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将可能的左派力量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遗忘或失望中争取过来,绝非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这种无甚趣味的文献文本文字考古学。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唯物史观申辩,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重要工作。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其变革的核心就在于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一切历史唯心主义从思想中、从政治变动中寻找历史变动最终原因的观点,“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从而形成了与之根本不同的历史观[7]。20世纪社会主义的成败、资本主义的兴衰直接影响了西方社会对唯物史观的接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为唯物史观正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则走向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工作是由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做出的。早在2003年的《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已经开始尝试驳斥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曲解和质疑,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即通过论战去证明“我们所熟悉的反马克思主义论调都是错误的”,“即便这些论调并非一无是处,也至少是站不住脚的”[6]1,其最终成果就是2011年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在这本篇幅不大、平实易懂的畅销书中,伊格尔顿对10个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指控或质疑进行了驳斥,其中3个涉及唯物史观。由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曾对唯物史观进行了不准确的经济决定论解读,结果谬种流传,西方社会始终有人认为唯物史观是否定个人的自由与个性的世俗版宿命论。针对这一指责,伊格尔顿主要基于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让人们意识到,唯物史观中存在两条相互补充的逻辑:一条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为核心的客体性逻辑,强调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必然性;另一条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主体性逻辑,强调人的行动的能动性。对唯物史观而言,承认必然性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主体性,相反,必然性总是通过主体性得以实现的,因此,“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马克思是一个否定人类自由行动的宿命论者。恰恰相反,他是个人自由的明确拥护者,并且一直热衷于讨论人如何超越历史的局限,选择不同的道路”[6]56。那么,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学说的唯物史观是不是只关注经济因素而忽视人类经验的复杂性、轻视人类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力量?伊格尔顿也都基于对相关经典著作的解读,一一做出了有说服力的驳斥。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辩证唯物主义正名,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颇为引人注目的一项工作。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对此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分化:苏联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而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绝大多数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则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并因此质疑、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冷战时期,只有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对唯物辩证法的某些理论进行过有影响的论述,其中,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1968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再)开始》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人本主义立场,要求将历史唯物主义置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宣称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开启新的革命方向[8]。1988年,巴迪欧出版《存在与事件》第一卷,开始在数学本体论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辩证唯物主义体系,进入21世纪后,他继续笔耕不辍,先后出版《存在与事件2:世界的逻辑》(2006年)、《存在与事件3:真理的内在性》(2021年)等,基本完成其新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建构,产生很大影响,有力修正了西方世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刻板化、污名化理解。此外,斯洛文尼亚左派学者齐泽克(slavoj Žižek)也一直致力于阐释黑格尔、列宁、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形成了一种拉康化的唯物辩证法学说体系,使得西方世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广度与深度都有所扩大。
基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发展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数字异化批判,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正着力推进的一项工作。1999年,基于当时正迅猛发展的互联网经济,美国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概念,并初步认为数字技术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9]。随后,数字资本主义在全球野蛮生长,带来了新机遇新发展,也导致了新问题新挑战。如何认识、评价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资关系?新的剥削现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等老一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运用异化劳动理论阐明了自己对现代数字劳动异化的批判性认识,不过,更系统的工作还是由年轻一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完成的,其中英国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的表现最为亮眼。2012年,福克斯携其与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共同主编的《马克思归来》文集强势闯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进而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2014年)、《社交媒体批判导言》(2014年)、《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与经济》(2015年)、《在信息时代读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 〉的媒介与传播研究》(2016年)等论著中,系统阐发了自己对数字劳动、数字异化的批判性认识,引发热烈讨论,推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发展,提升了异化理论的当代影响力。
三、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新建构
历史反复证明,创作于19世纪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是蕴含着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无论它们多少次被宣布“过时了”,但只要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人们就会再一次想起、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发展新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世纪之交,这一幕再次重现:来自不同流派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重新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从其中的“机器论片断”、经济危机理论、资本逻辑学说中汲取思想资源,试图在21世纪续写《资本论》,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批判。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变化,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出现了大量依靠智力劳动赚取高额收入甚至能够获得大量股权的新工作岗位如程序员、创意阶层等,许多科技精英、创意精英靠知识成果的转化迅速积累巨额财富跻身富豪之列。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人都是“知本家”,他们的大量涌现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被超越。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这些新现象新变化呢?在2000年的《帝国》一书中,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指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们正在基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以及非物质劳动概念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进行新思考[10]。此后,奈格里、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维尔诺(Paolo Virno)等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即今天所谓的“机器论片断”,进行了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建构。在这一手稿片段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1]也就是说,马克思预见到,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到来将使得直接劳动越来越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科学知识和技术将成为财富生产至关重要的因素。从马克思的论述出发,奈格里、维尔诺等阐述了科学技术在财富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资本追逐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性和内在矛盾,进而强调当代劳动形态与马克思时代的劳动形态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成了一种非物质形态的劳动,即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这种非物质劳动是“生产非物质产品,譬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应的劳动”,或是智力或语言劳动,或是情感劳动[12]。据此,他们提出,在科学技术发挥全面支配作用的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非物质劳动打破了生活与生产的界限,实现了资本的全面控制,成为“生命政治的劳动”,构成人类生命的全部内容。博当(Yann Moulier-Boutang)、韦塞隆(Carlo Vercellon)、卡芬特其斯(George Caffentzis)等进而基于非物质劳动概念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概念,认为随着生产的自动化转向和知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的提升,以知识和智力等为代表的认知劳动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的主导形式,“资本和资本的积累规律……推动了知识的积累过程,并使劳动不再是价值的来源,劳动时间也不再是衡量价值的手段。结果呢,交换价值也不再是衡量使用价值的尺度”[13]。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今天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不再是传统的物质劳动,而是来源于以智力、发明和创造等为代表的认知劳动[14],认知劳动成为主导劳动形态的时代就是认知资本主义。在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变化的是剩余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不变的则是资本与劳动的权力和统治关系即剥削本身。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长期沉寂后开始复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回到《资本论》,从利润率下降、过度积累、消费不足等理论视角出发进行深入思考,最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使之走向全面复兴。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热拉尔·迪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等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规律造成的结果,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竞争机制的说明依旧具有科学性。布伦纳赞成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作为分析支点来解释利润率下降机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走向集中和科学技术应用导致的企业成本短期无法回收,必然出现产能过剩,导致利润率下降。新自由主义力图缓解这一趋势,“降低成本、新自由化以及全球化的措施……或多或少地构成了急切地解决持续普遍的利润率下降问题的尝试。但是,压倒一切的不是恢复经济活力,实际上,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再次恶化。”[15]大卫·哈维基于《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积累机制的论述,提出了过度积累危机理论,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市场自由化——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将不会产生一个和谐的国度,其中所有人都会非常富裕。相反,它将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公平。马克思预言,这还将产生严重的和持续增长的不稳定,并最终会带来长期的过度积累危机。”[16]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新自由主义发明了一种新的积累机制即掠夺性积累,力图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操控和国家再分配等各种措施破坏原有模式,甚至不惜制造恐慌和资产贬值,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财富,但这种掠夺性积累并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危机。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则强调消费不足是导致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是以隐藏的方式在发挥作用,大部分中下层人群之所以会过度借贷消费,原因恰恰在于他们的支付能力不足,而借贷市场之所以会迅速膨胀,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无限制地追逐利润的逻辑[17]。此外,卡多·贝洛菲尔(Riccado Bellofiore)和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等立足MEGA2最新文献研究成果,重新梳理《资本论》及其手稿,建构出了自己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当代阐释。
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学派、英美的“新辩证法”学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形成的两个较小规模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从形成之初就致力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进入21世纪后,这两个流派都再次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努力在MEGA2新文献基础之上重建《资本论》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新马克思阅读”学派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资本论》第二版《跋》等经典文献为基础,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商品》章中的论述,重申把握价值形式对于理解《资本论》总体逻辑的重要性。“新辩证法”学派再次强调必须利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概念辩证法来重新解释《资本论》,认为“马克思著作的批判优势不仅在于对剥削在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体系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物质性证明,而且在于它穿透了价值形式的结构……价值形式的逻辑在它们自我相关的抽象中就是黑格尔逻辑中思想自我运动在现实中的体现。”[18]在此判断基础上,“新辩证法”学派试图用所谓“体系辩证法”替代“历史辩证法”,将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限制在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形态中进行分析,继而完成了其对资本增殖逻辑的系统说明。2014年,法国理论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了向马克思致敬的《21世纪资本论》,基于财富分配不平等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虽然该书无法取代《资本论》成为新时期人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指南,但确实有效扩大了《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影响力。
四、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政治批判创新潜能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政治批判理论居于体系的最外层,通常是经典作家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引,分析、研究具体的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成果,易于随着时空条件的变换失去其直接的理论效力。因此,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往往更注重引入新的理论、运用新的方法分析大量涌现的新政治现象政治问题,形成新的政治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21世纪以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日益发现,在其震荡发展的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的文明和谐外观不断剥落、野蛮剥削压迫本质重新彰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的一些判断、论述再次显现出它们的当代适用性,这促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批判理论创新过程中,更多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努力寻找蕴含其中的创新启示。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思考资本主义政治问题的中心。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的变化、全球化造就的新的世界生产格局及其动荡、重新剧烈发作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推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重新关注阶级问题,构建新形态的阶级理论。奈格里、维尔诺等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回到《资本论》,在传统阶级主体概念基础上,把“大众”确立为新的无产阶级、新的革命主体。认知资本主义流派在分析当前西方无产阶级生存境况时,以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中介,同样回到了《资本论》,力图重新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权力及其对劳动过程的作用,揭示当前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新型剥削关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生命政治学的阶级意识理论,也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圣麦克斯》章中得到某些启示。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加快构建单极霸权秩序,展现出了帝国主义的国家本质,同时,东亚东南亚建构了一种基本不同于欧美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方式,这些推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功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复兴。在“帝国三部曲”(《帝国》《大众》和《大同世界》)中,奈格里和哈特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得到了重要的理论启示。而在大卫·哈维、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等人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中,列宁、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以及《资本论》,同样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作为当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鲍勃·雅索普(Bob Jessop)在其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理论中,重申了马克思有关世界市场和国家思想的重要价值,阐述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与不同形态的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相互依存关系。
空间批判理论是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成就。21世纪以来,空间资本化的发展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推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持续深入展开,并强化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论连接。作为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重要创立者,哈维强调:“切断我们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就是切掉我们敏锐的嗅觉以满足现代学术流行的肤浅外表”[19]。在21世纪以来的系列新作里,哈维高度关注《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中的资本批判学说,并提出了新的资本空间转化模型,指出:“一旦投资被嵌入某一特定地域的土地,如果资本不出现贬值,资本就必须在那个地域使用。资本运动在空间上受到限制,而资本则致力于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增加流动性。时间消灭空间是资本重塑世界市场空间和时间的重要现象。”[20]204他同时强调:“在全面分析资本在时空中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再生产时,资本作为运动中的价值不能脱离其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去理解,它不仅经过市场也通过国家权力来调节。”[20]233索亚(Edword Soja)、彼得·马尔库塞(Peter Marcuse)、麦利菲尔德(Andy Merrifield)等年轻一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家,也都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空间生产与城市学说。麦利菲尔德就提出,“正是恩格斯开启了都市马克思主义及对形成过程中的现代大都市的现代分析。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我们城市里的天使,则第一次理解了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现代大都市的纹理、现代性的辩证经验。”[21]
与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重要政治批判理论成就不同,生态批判理论在其形成时期就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建立了较为自觉紧密的联系。进入21世纪后,生态马克思主义从自然观和政治经济学两个维度深入推进生态批判理论的当代建构,从而将过去关注不够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也纳入自己的理论资源库。
五、简要的评论
较之于20世纪,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能力确实有所下降,即便如此,它们依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22]研究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我们既要关注其创新成果,更要关注其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因为我们研究它们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分析、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中国问题不可能照搬照套国外理论,只能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中国实际自主探索创新解决。就此而言,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通过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实现理论创新的路径,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23]11
聚焦经典、关注思想,是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等经典作家都是勤奋的思想家,都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遗产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经典作家本人生前的公开出版物,这类文本清晰、稳定地展现了经典作家在特定时间点的思想图景;二是前者的过程性文献,如手稿、准备材料等,这类文本在基本确定的框架中展现了经典作家思想发展更丰富、更生动的细节,更便于观察他们的思想生成过程与机制;三是经典作家的摘录、笔记和批注等自由探索型文本,这类文本往往是高度碎片化的,闪烁着令人着迷的思想星光,但很难确定把握;四是经典作家的书信、电文等。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过度关注、畸形崇拜经典作家非公开出版物的“时尚”,仿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只存在于这些经典作家的同时代人往往不甚了解的“秘籍”中似的。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让我们再次确认,四类文本各有各的起源、各有各的意义,但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而实现当代创新发展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经典作家经典性的公开出版物以及少量重要的过程性手稿。皓首穷“秘籍”,或许能够成为博闻强识的学究,但绝对创造不出振奋人心的思想。
理论联系实际、带着问题意识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启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界广阔、知识丰富,著作卷帙浩繁,遨游其间,很容易让人在叹服其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的同时,迷失自己前进的方向,感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怎么才能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不为海量文本所困呢?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启示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带着问题意识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理论联系实际,就容易发现问题、形成问题意识;有了问题意识,就容易缩小范围、深入思考,最终实现重点突破、举一反三,达成理论创新。福建时期的习近平同志就是这样学经典、用经典的[24],最终实现了个人思想的突破,为未来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站稳当代立场、以开放的心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第三个重要启示。早在1895年,恩格斯就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5]如今,又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更不能指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存在着直接可用于当下的真理。不过,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让我们再次确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是真理,而是通向真理的道路!因此,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站稳当代立场,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2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