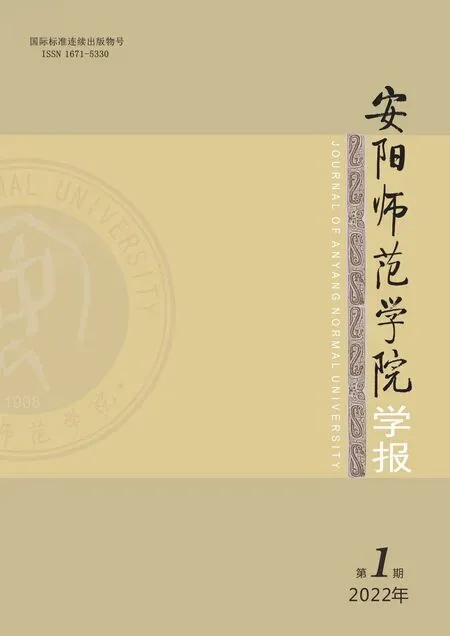改铸古史:上博简《成王既邦》古史编纂思想探研
刘 承
(许昌学院 文史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所谓“改铸古史”,是指在原有的史实基础上,通过完善体例、增添情节对古史进行重新加工、创作,以符合编纂者的史学倾向和当时的社会需求。先秦史学源远流长,记言记事早已成为史学传统。至战国时期,史学编纂与诸子之学并行向前且互相联系。将口述史转化成文本,对古史进行重新编辑整理,创作出战国时人心目中的古史,这种新史学的创作,在当时已蔚然成风。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八册)中的《成王既邦》篇,就是这类史著的典型代表。这一篇久佚的先秦儒家文献,原篇共16支简,总计319字。多数简下两端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缺文较多,文意不甚连贯。整理者濮茅左先生进行了开创性的编联和校释工作,对于我们阅读和研究此篇文献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为方便讨论,兹将这篇简文摘录如下。
成王既邦,周公二年,而王重其任,乃访……王在镐,召周公旦曰:“呜呼,敬之哉!朕闻哉……而欲明知之。”周公曰:“旦之闻之也,各在其身,而……伯夷、叔齐饿而死于雝瀆,不辱其身,精……焉不曰日章而冰澡乎?”
成王曰:“请问天子之正道?”周公曰:“皆欲俗其新而亲之,皆欲以其邦就之,是谓天子之正道。弗朝而自至,弗审而自周,弗会而自专。”成王曰:“请问其事?”(周公)曰:“榯、市明之,德其世也。……而贤者能以其六藏之兽(守)取新焉,是谓六亲之约。”成王曰:“请问其方?”(周公)曰:“……先国变之修也。外道之明者,少疏于身,非天子……道大才宒。呜呼!欲举之不果,以进则退焉。达……是谴之不果,毁之不可,其状膏(骄)脞(淫),以泽深厉……皆见章(彰)于天。”
成王曰:“夫夏缯氏之道,可以知善否?可以知亡(无)哉?可谓有道乎?”周公曰:“是夫重光,重光其昌也,可羿而寡也,此六者皆逆。民皆有夬廌之心,而国有相串割之志,是谓重光。”[1](P171-188)
此文形式以记言为主,类于《国语》,通过记叙言辞来展现一代圣君贤相的嘉言善语。简文内容讲述的是少年成王向周公垂询君主自身修养和治国之道,周公一一进行回答,并以历史上曾有的“重光其昌”来勉励成王创建当世的重光之治。该文反映了战国儒生对于周初历史的追忆,对于了解战国时期的古史编纂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本文即以此篇为研究对象分析如下。
一、述史完备:生动翔实的古史编纂
白寿彝先生在论述史书编纂体例时曾这样说过:“在体例问题上,首先应该注意两点。一是要注意内容和形式间的关系,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可能有一种更好的形式。在编纂史书时,当然以采用更好的形式为宜。二是,形式是为了体现内容,内容不当因迁就形式而对自身有所损害。同时,形式也应有自身的完整性,也应该适当地保持一个相当完整的形象。这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必须妥为处理。”[2](P17)所谓“内容”,是指呈现于纸面上的历史事实,是便于读者览观的文字记录;所谓“形式”,是指史书的编排方式(编年、国别、纪传等)和史家的语言风格。将内容和形式处理得当,使二者完美结合,才能更好地体现史家的学术素养和编纂思想。
上博简《成王既邦》篇就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古史编纂情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对于战国时人而言,周初的历史并不遥远,简文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个“近古史”中一个片段的追述,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作者在编纂这段古史时对于“内容”和“形式”的处理可谓匠心独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叙事简练,开宗明义。从篇首至简文的第一部分“焉不曰日章而冰澡乎”,大致意思是讲: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第二年,成王愈发尊重周公,于是在镐京访问周公,向周公请教修身之道。周公认为个人的修养在于自身完善(“各在其身”),就好似伯夷、叔齐那样,即使饿死也不辱及自身人格(“不辱其身”),如同太阳照耀使冰雪融化一样(“日章而冰澡”)去感化世人。
从材料可以看出,简文先以简单的叙事开篇,叙事虽简,却明确记录了时间(周公二年)、地点(镐京)、人物(成王、周公)、事件起因(“王重其任,乃访周公”)等等,表明已经具备了述史记事的基本要素,说明作者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意地遵循自己拟定的体例来编纂这段古史。再看成王的第一句问话,“呜呼,敬之哉!朕闻哉……而欲明知之”。成王想要“明知”什么?从下文周公在答话中大谈修身正己的内容可以推测,成王是想要知晓身为人君该如何端正自身。作者开宗明义,一上来就描写了成王对周公的敬重和二人谈话的主旨,尤其是“欲明知之”一句,生动突出了少年天子所表现出的与年龄不相称的稳重和强烈的求知欲,也为接下来二人继续探讨治国之道以及周公所阐述的重光之治作了行文上的铺垫。
其二,语言生动,人物对话层层递进、丝丝入扣。在受到周公以伯夷、叔齐之例勉励自己立志君修的启发后,成王首先发问:“请问天子之正道?”周公直言“天子之正道”在于“皆欲俗其新而亲之,皆欲以其邦就之”,意思是说要不断变新百姓的旧风俗,使其在邦国内安定生活。此外,君主还要做到“三弗”,即“弗朝而自至,弗审而自周,弗会而自专”,指出天子要昭忠信于天下,以做表率,四方诸侯自来朝见;法令已明,不必天子巡视诸侯自会安定;太平盛世,诸侯之间互敬互重,没有纷争,相互之间自会协调处理。成王第二个问题是:“请问其事?”周公回答说,凡事须“榯、市明之”,要求天子要贴近百姓,与民同乐,重要事件、法令必须在城门、集市等公共场合予以公示,以示政治清明。周公又举“六新之约”来告诫成王,谓“贤者能以其六藏之兽(守)取新焉”,意指要治理好国家,君主还要懂得革故鼎新的道理。成王接着提出了第三个问题:“请问其方?”周公回答说,君主先要以身作则,明辨是非,远离骄奢淫逸,提醒成王世事难料,治国往往会陷入“欲举之不果”“毁之不可”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致使国势危难。成王最后又向周公探询了“夏缯氏之道”的问题,周公告诉成王历史上确实曾出现过圣人的重光之治,要想重塑过去的美好盛世,人民要有明断是非之心,国君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才是当世真正的“重光其昌”。从整篇来看,成王的发问直切主题,层层深入。而周公的回答每一句都切中要点,直面解答。二人一问一答,逻辑顺畅,毫无滞涩感,这些都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
其三,生动传神的人物对话,其目的在于突出人物品质,树立成王、周公的伟大形象。先看成王的四个发问:“请问天子之正道”“请问其事”“请问其方”“夫夏缯氏之道,可以知善否?可以知亡哉?可谓有道乎”。这一连串发问,层层递进,体现了少年天子尊重长者、虚心聆听的态度和善思、自律的稳重性格,颇有治世明君的潜在气质。再看周公的答话,三次用到同一个句式“是谓……”,对成王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代名相对于少年天子的忠诚和殚精竭虑的奉献精神。尤其是周公对于重光之治的阐述,短短数语便为成王描绘了一幅理想盛世的蓝图。简文作者将主要篇幅以对话的形式表述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既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又增强了可信性,不仅突出了成王的少年有为和周公的远见卓识,又体现了君臣之间的融洽之情,二人的高尚人格由此跃然于纸面,如此述史也更加符合作者那个时代的要求。
从本篇简文的记言风格来看,战国时期的古史编纂已经脱离了早期史学那种简单记述的范式,历史文学开始悄然进入史家的编纂意识当中。对于史与文的结合,章学诚曾称赞《史记》是“书圆而神”[3](P50),认为司马迁能够很好地运用生动的文字和不拘一格的体例来活灵活现地表达历史面貌。诚然,该篇简文远不能与《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同日而语,但它在叙史方式上的确有了“书圆而神”的影子。一方面,作者是用准确凝练的语言去追述这段丰富的古史;另一方面,又用生动传神的人物表现再现成王、周公的圣贤形象。由此看出,《成王既邦》篇在编纂形式、语言风格、文字修饰上,都比《春秋经》前进了一步。相较同时期的《国语》《左传》,虽然在篇幅上不能与之相比,但在述史完备上则与这二者不分轩轾。由单一记录转向丰富古史内容,《成王既邦》篇反映的正是那个时期史学变迁的一个缩影。
二、裁剪熔铸:上古史影与今世观念相交融
谈及战国时期的古史编纂,给人的印象就是早已摆脱了生硬的记录方式,着重将记言与叙事并用,通过增添情节、突出人物言行来完善古史的内容。那个时期人们对于古史的追述,并非只是单纯的史籍整理,而是有着浓厚的经世致用的意识。《易·大畜·象传》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礼记·经解》谓:“疏通知远,书教也。”述史记事的目的在于“多识前言往行”,在于通过古史提供的鉴戒来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提出对未来历史趋势的看法。
然而,真实的历史是转瞬即逝的,遥远的古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只剩下大致的轮廓。撰写者在捕捉古代史影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融入古史的编纂中。对此,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有深刻的总结:“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人类所真正需要的是在想象中去重现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4](P220)
克罗齐这段话可谓一语道出史家编纂古史的要义。如何做到“重现”“重想”遥远的历史呢?晁福林先生在阐述周代“以史为鉴”观念的实质时曾说:“接受历史教训的过程,就是一个改铸历史的过程,而这个‘改铸’,还可以说是必然的。这是因为不经‘改铸’,历史鉴戒就无法进入人们的历史认识领域,‘以史为鉴’就不能起步……人们‘改铸’历史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为现实需要服务,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保证‘现在的生动和自由’。”[5](P419)可见战国时人对于古史的追忆,正是一个“重想过去”的过程,其对古史的创作,正是采用“改铸历史”的方法来完成的。换言之,就是用当时的社会思潮来描绘古史,又采录真实的史料来传述古史,将古今史影裁剪熔铸于一体,使上古史影与今世观念相交融。以古喻今,改铸古史,正是战国史学所独有的一种编纂特色。
上博简《成王既邦》正是这样一个熔古今史影于一体的原始文本,保留了很多那个时代的编纂痕迹。作者在叙述成王、周公对话的同时,于有意无意之间穿插了战国时人的一些思维习惯和社会观念。这些痕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处。
首先,简文开篇提到的“周公二年”指的是周公摄政第二年,而非成王即位年号。这种以大事纪年的方式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已十分普遍。战国彝铭中就有很多关于这种纪年方式的记载,如楚《鄂君启节》铭谓“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6],系以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将昭阳大败魏军于襄陵(今山西襄汾县襄陵镇)之事立岁。楚《大府镐》铭谓“秦客王子齐之岁”[7](P32-36),系以楚怀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3年)齐、韩、魏共攻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以求援之事立岁。这种以大事纪年的方式,与西周、春秋时期“唯王某某年”的周王纪年迥然不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战国时人的心目中,周天子以往那种天下共主的影响力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各国诸侯相继称王称霸,所以各国彝铭屡以国内所发生大事来纪年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简文作者将“成王既邦”与“周公二年”并称,在明确指出成王践位的同时,仍以周公摄政之事作为纪年的起点,可以看出作者是用战国时期的编纂习惯叙述周初历史,这一小小的细节也恰恰反映了那个时期尊王观念的巨大变迁。
其次,简文中周公所举的伯夷、叔齐的事迹,是流传于战国时期的一段广为传颂的故事。据传说伯夷、叔齐生活于殷、周之际,但在西周文献里却找不出一丝他们的踪影,直至春秋末期才开始有了这二人的传说。最早的记载见于《论语》,孔子将他们列入“逸民”,称赞他们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过春秋时人对于伯夷、叔齐的事迹描绘得还很简单,仅仅是说他们饿死于首阳山下而已。到了战国时期,伯夷、叔齐的形象便不断被放大,在当时可谓是贤圣的代名词。如孟子谓:“伯夷,圣之清者也。”韩非谓:“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尤其在庄子后学那里,夷、齐之事甚至被演义成一段感人而又凄美的悲剧故事。在《庄子·让王》篇中,其增饰的内容大致有三:(一)明指二人的身份是孤竹国君之子;(二)武王以国士之礼优待,“加富二等,就官一列”;(三)二人相视而笑,隐于首阳山,并道出宁肯饿死的原因是坚持“遇乱世不为苟存”的道义。战国时人对伯夷、叔齐是相当崇拜的,将他们完全塑造成一个抱节守志、舍生存义的古代贤士的典范,推其原因,应当是战国时期隐士阶层兴起于社会的反映。《成王既邦》篇作者将这个当时流传甚广的故事比附于周初,也正是简文中何以会出现周公以伯夷、叔齐之事来教导成王的原因。
最后,简文作者借成王之口引出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夏缯氏之道”来阐发“重光其昌”的社会理想,这种美化上古时代、以古人注我的述史方式,正是风靡于战国时期尊古崇古代社会思潮的反映。战国时期的儒、墨、道等学派的知识分子普遍对遥远的古代有浓浓的眷恋,他们认为上古时代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所以在立论时动辄以“昔者”“古者”“尧舜禹汤”开首,从先王之道那里找寻依据。这种崇古思潮的出现,与当时剧烈的社会变革不无关系,残酷的现实使得一些有识之士难以承受社会震荡所带来的巨大阵痛。迷茫、矛盾、痛苦、愤怒,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为探索心中的理想国而找寻古史的模板。《淮南子·修务》篇曾有一段十分精辟的分析。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8](P1355)。
正是由于“乱世暗主”,时人“多尊古而贱今”,战国时期的古史编纂才会出现如此之多关于黄帝、尧、舜等先王之道的赞颂。《成王既邦》篇关于“夏缯氏之道”的记载,同样也是深受这一文化思潮的影响。作者将当时的社会观念推想到周初,这才有了篇中成王、周公关于重光之治的阐述。
由此可见,简文作者是将战国时期的社会观念推想于周初,用后世的思维习惯来追述古史。但是需要澄清的是,作者对于这段古史的撰述并非向壁虚构,而是保存了一些周初的史影。这些史影于史可征,符合周初的历史实际。
其一,简文用很大的篇幅记述了周公对成王的耐心阐述和殷切教导,虽有作者增饰的成分,但周公教导成王之事,却是十分确切的史实。《尚书》所保存的周初文献中就有很多周公诫勉成王的语录。《无逸》篇载:“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无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此处的“今嗣王”即指成王,这里周公是在教导新即位的成王不要纵于酒色湛乐和游戏田猎之娱,而要以百姓事为先。《洛诰》篇载:“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终。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此“冲子”亦指成王,周公训诫成王要重视祭祀和享献。而《成王既邦》篇所载的周公对于成王的教导之语,其中心思想与《无逸》《洛诰》所述并无二致。据此我们可以说作者所采集的史料来源很古,其核心内容也是真实可信的。
其二,简文提及的“三弗”,即“弗朝而自至,弗审而自周,弗会而自专”,反映的正是周公关于大规模封建诸侯的政治构想。周公吸取武庚之乱的教训,对殷商方国联盟旧制进行了两点重大改动。一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将大批姬姓子弟和其他异姓贵族分封到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战略要地和经济富庶地区,使之作为王畿的屏障,对周天子负有守土之责。二是“授民”“授疆土”(《左传·定公四年》),明确所封诸侯对所辖封地内所有土地和民众的政治管辖权,同时也确立诸侯对周天子所承担的经济义务。周公所推行的分封制在政治上明确了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使得周天子“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9](P238)。
从加强王权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分封较之以往的方国联盟制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首先,诸侯作为守土之臣对周王负有各种义务,如定期朝见、聘享、纳贡,有时还要受天子派遣出征,或参与天子主持的祭祀和会盟等,这正是简文“弗朝而自至”所表达的含义。其次,诸侯国君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质,周公分封的目的就是要求诸侯在拥戴周天子的同时又不过分依赖周王室,使他们能够在各自的封地内实施有效的统治,而这也正是简文“弗审而自周,弗会而自专”所阐述的内容。《成王既邦》篇关于“三弗”的总结,表明周公在摄政之初既已开始酝酿新的分封措施,这个记载也与实际的历史发展相吻合。
三、结语
上博简《成王既邦》篇对于我们认识战国时期的古史编纂情况颇有启发意义。当时的古史编纂约略可分为三类:一是依据丰富的前朝遗留材料所整理的体例完备的史著,如《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以及新近整理的清华简《系年》等;二是散见于诸子立论中的史事,如《墨子·非命》《荀子·儒效》《韩非子·五蠹》等,其共同点就是述史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援引史事作理论上的辩诘;三是搜集传说中的史料素材作理性化的历史叙述,并融合当时人社会理想的古史作品,如《尧典》《禹贡》等,表现出浓厚的儒家圣王之治和天下一家的思想观念。应当说《成王既邦》篇亦是这类古史作品的典型代表。作者运用现实的剪刀,将那段周初历史进行重新裁剪,既保留了部分可信的史实,又把若干今世的观念点缀于其中。作品中移今于古,以古喻今,将古今史影裁剪熔铸于一体,既是《成王既邦》篇的编纂特点,也是战国时期史学多样化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