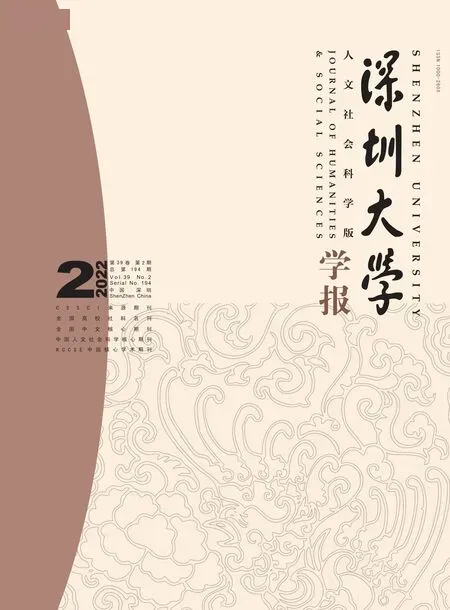“野望”事象的诗性存在与书写
殷学明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古往今来,中国诗学惯于从物象的空间静景中寻找诗意,而相对忽略从事象①的时间动图中构造诗性。 事象是“一个民族历史中各种事变和动作的内部指导的灵魂”[1],它有“声与政通”乐象之美,也有“象事知器”易象之神、“属辞比事”史象之妙。 季札观乐,美其诗音;子之武城,闻其弦歌,皆有微而显的事象。 与物象、意象相比,事象也是中国诗学的独创。 黑格尔指出:“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见诸现实”,“动作、反动作和矛盾的解决的一种本身完整的运动,这特别是诗才有的本领”[2]。中国事象的诗意也是由动作营造的,但中国的事象不同于西方的情节,它不着力描绘“完整的运动”,而是力求在动作的细微片断中透射人生、体验生命。张籍的《秋思》“忽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的诗意就不是由意境构造的,而是通过“临发”和“开封”两个传神的动作画面营造的。 诗歌事象是各民族历史整体演进与诗人个体生命体验的结晶,蕴含着令人神往的诗性智慧和诗性记忆。 在中国古代,“卧听”“折桂”“凭栏”“野望”等诗歌事象已不是个体性的随意动作,而是有着民族灵魂、文化精神等集体性的诗意动作,并作为中国特有的诗性生存方式代代相传。
“野望”作为一种心理事象在诗性文本中频频出现,成为中国古代士人尤其是诗人挥之不去的文化现象而被不断地书写。 如王绩《野望》“东皋薄暮望,……长歌怀采薇”;杜甫《野望》“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元回《春日野望》“野外登临望,苍苍烟景昏”。 “野望”作为一种文化事象伴随着华夏民族诞生而产生,见证了华夏文明的整个历史进程。 与单纯的物象相比,“野望”事象不仅真实记录了中国古人尤其诗人在困厄之时不避险难、致命遂志的豪迈气概和诗性情怀,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华夏民族社会变迁、时代更迭和文化焦虑的历史真相,其诗意性书写有着一般历史所不能替代的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一、“野望”事象的诗性存在与演化
“野望”事象在中国古代不是一种孤立的诗歌现象,而是一个普泛的诗性存在。 就狭义的诗歌文本而言,《诗经》中“野望”事象出现了20 多次;全唐诗中“望”字出现了4556 次,以其为题的有1750首,“野”字出现了3116 次,以其为题的有202 首;宋诗中有“望”字的诗句13120 条,有“野”字的诗句12432 条②。 就广义的诗性文本而言,《庄子》 中的“野”字出现了18 次;《史记》中的“野”字出现了138 次。 另外,在诗之变体的词赋、诸子百家、民间口传叙述等诗性文本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野望”事象。 中国古代士人尤其是诗人为何钟情于“野望”?其内在又是如何诗性演化的?又透露出何种社会心理和文化焦虑? 沿波讨源,“野望”事象的诗性演化主要经历了3 个历史阶段。 一是山野的张望,率性而朴质;二是朝野的观望,苦闷与抗争;三是文野的守望,认同与超越。 这3 个阶段既是中华民族从朴野走向文明的文化史,也是中华民族在文明进程中焦虑、矛盾、斗争的心灵史。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3 个阶段不仅是一种历时性、整体性的演进过程,而且也是一种共时性、交叉性的类型划分,它们或隐或现地存在于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一)山野的张望,率性而朴质
上古之时,举代淳朴,佃于山林,渔于川泽,诗性之智发,劝力之歌生,民渐趋文明。 这段历史虽不甚明朗,但透过“野望”事象却可见一斑。 从“野”字的演化来看,其甲骨文为(前4.33.5)、金文为、小篆为(说文),林中“里”(居也。 从田从土)的字形转化过程就隐性记录了华夏民族从森林走向城邑的文明进程。 从“望”字内涵来看,“出亡在外,望其远也”(《说文》),“望,惘也,视远惘惘也”(《释名》),则又反映了早期华夏民族从城邑返向森林的渴望与矛盾。 就先民居处而言,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 在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的洪荒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野”多人迹罕至,地处广远。及至商周,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县士掌野。 “野”自此从地处广远的模糊意念走向了官属分明的邦治概念,即“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说文解字》)。 具体来说,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谓之“野”。 在中国封地建制、掌邦治国之后,“野”已不是华夏民族主要的栖居之地,而只是一种割舍不断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 面对这场历史性转折,道家主张“无以人灭天”,崇尚天性的“野”。 儒家尽管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对于“野”也采取了审慎的态度。 在孔子看来,“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3]。 孟子则直接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4]。
与先哲思想上的领悟相比,诗人可能对“野”的感悟更为直接。 上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有“野”的刚健;《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有“野”的自由;《左传》“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有“野”的正直。 朴略尚质、刚健正直、率性自由就是“野”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其诗性魅力也恰恰源于此。 这种诗性魅力在《诗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据不完全统计,《诗经》中“野”字出现24 次,“望”字出现11 次,且多在《国风》之中。 譬如“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野有死麕》)、“野有蔓草,零露漙兮”(《野有蔓草》)、“我行其野,芃芃其麦”(《鄘风·载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之子于征,劬劳于野”(《小雅·鸿雁》)、“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小雅·鹤鸣》)、“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小雅·我行其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小雅·小明》)、“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小雅·何草不黄》)、“駉駉牡马,在坰之野”(《鲁颂·駉》)。 概而言之,《诗经》中的“野”有两种类型:一是“风”中之“野”;二是“雅”中之“野”。 前者朴略尚质、率性而为,具有朴质的野性美,以《野有死麕》为代表;后者化性起伪、修辞立诚,具有严整的秩序美,以《鹿鸣》为代表。 两种不同类型的“野”既有矛盾,也有统一。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野有死麕》之诗让人们看到“野”的自由与奔放;“之子于征,劬劳于野”,《鸿雁》之诗又让人们怀念“邑”的安逸与舒适。 对“望”而言,《诗经》则有“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邶风·燕燕》)、“升彼虚矣,以望楚矣”(《鄘风·定之方中》)、“乘彼垝垣,以望复关”(《卫风·氓》)、“谁谓宋远? 跂予望之”(《卫风·河广》)、“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魏风·陟岵》)等等。 在《诗经》中,已经形成了“远送于野”的婚恋事象、“我行其野”的征战事象、“升彼虚矣”的忧国事象等诸多典型事象,成为后世用之不竭的原型事象。
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提出了“野性的思维是异于近代科学的另一种科学”的观点。 早期人类非时间性生存并不简单意味着粗野和无知,而是蕴含着将“同时性与历时性生存矛盾”相互调和的诗性智慧。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经历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的洪荒时代,逐渐向城邑文明的方向发展。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的自然性(野性)与社会性(文明)不断发生着冲突,致使诗人的身(物质)与心(精神)经常处于矛盾之中。 “肃肃宵征,夙夜在公”“东方未明,颠倒衣裳”,这是文明的另一个侧面,也是诗人“野望”的内在根源。 中华民族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形成宗教的终极关怀,但却形成了“野望”的诗性文化。 在“野望”中,诗人回到了自然、回到了自我,从而净化了心灵、体验了生命力和创造力。 可以说,中国早期的“野望”事象不仅记录了华夏民族文明的发端,也记录了华夏民族心灵的动荡。透过“野望”事象,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早期诗人的心态和诗歌内涵。
(二)朝野的观望,苦闷与抗争
如果说山野张望是人与自然的探求,那么朝野观望则是人与社会的探索。 从山野张望走向朝野观望意味着华夏文明从身体生存空间拓展向心理精神空间探求的转向。 曰若稽古,庄子可谓是中国古代心理之野深度探索的第一人。 如果说“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是庄子地理之野的寻求,那么“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的心斋则是庄子心理之野的开拓。 《庄子》 一书中,“野”字共出现18 次,“望”有登昆仑而南望、望洋而引野语之叹等等,庄子“野望”主要从“无以人灭天”的思想出发,强调人之素朴的野性,反对“落马首,穿牛鼻”有违自然性的行为,最终实现身与心的逍遥游。 可以说,庄子之野望思想为后世诗人旷野之作提供了哲学基础。 继庄子之后,屈原“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成为中国古代个人勾画野望事象的宗祖。
自秦大兴土木、奢于台榭、囿于形制以来,尽管物质性文明程度得到很大的提高,但人的自然之性却受到挤压,心理之野的诉求逐渐提到历史进程中来。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物质文明的进程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这在《两都赋》《两京赋》《三都赋》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然而致饰之后,亨通则尽矣。 治人者身居宫室、出舆入辇、犓牛之腴的文明倦怠,又让诗人们无比渴望自然的天性、朴野的自由。 对此,枚乘《七发》、张衡《七辩》、曹植《七启》等作品都表达了这种诉求。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就指出:“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此前谁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第二时代的高级人类是被市镇所束缚的动物”[5]。 这种城邑文化对人的束缚主要体现在2 个方面:一是活动空间的束缚即“身”的约束;二是自主时间的束缚即“心”的约束。 前者多是物质上的束缚;后者多是制度上的约束。 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6]。 由理智所创造的文化在使人走向文明的同时,又在另一个侧面将鲜活的生命纳入程式之中,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束缚得寸步难行,于是君子固穷也要坚决反抗。 也正由于诗人的不懈追求,华夏民族才有了各种各样的诗意生活。 竹林七贤开创了魏晋风度、陶渊明开启了田园生活、谢灵运开始了怡情山水的旅行……
如果说屈原流放于野的远望是一种被迫行为,充满着绝望的反抗,以诗人之死的方式创造了一种诗人品格;竹林七贤任性于野的观望是一种主动行为,以怪诞不羁、愤世嫉俗的方式形成了一种诗人品格的话,那么陶渊明“守拙归园田”则是一种自觉行为,且“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还活出了一种诗性的骨气。 与其说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不如说是与“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的人事制度绝交。 与其说陶渊明是与“饥冻虽切。 违己交病。尝从人事。 皆口腹自役”的生活抗争,不如说是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矛盾的斗争,其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道出了诗人心理的苦闷和抗争。罗宗强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指出:“他(陶渊明)有世俗的种种纠结,但是他安于贫穷,他用儒家的固穷的思想,用般若的万有皆空的思想,摆脱了世俗的种种纠结,走向物我泯一的人生境界”[7]。 在陶渊明看来,野外罕人事,只有冲破樊笼,才能复得自然,找到归宿。 陶渊明在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斗争中走了出来,创造了诗人固穷不失志的理想典范,成为中国历史上真正自然的诗人。
(三)文野的守望,认同与超越
有唐以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鸿沟被填平,文野相待而生,中国古代士人尤其是诗人野望从心理需求转向了文化需要。 也正基于此,“野望”事象在唐代形成了儒、道、释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和野望情结,分别以“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野望》)的杜甫、“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见野草中有曰白头翁者》)的李白、“性野趣无端,春晴路又干”(《独游》)的皎然为代表。 儒家“敏于事”,是有为之学,杜甫的“野”是朝野之野,其“望”是“穷则独善其身”的“望”。 这类野望蕴含着“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野望》)怀才不遇的悲凉和“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忠君爱国的忧思。 杜甫通过野望所勾画的“诗史”受儒家文化影响很大;道家“事无事”,是无为之学,李白的“野”是野逸之野,其“望”是“逍遥乎寝卧其下”的“望”。 这类野望则蕴含着“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的闲适和“野酌劝芳酒,园蔬烹露葵”(《赠闾丘处士》)的野趣。 李白“任其自然”的“诗仙”之风与道家文化的熏陶有直接关系;释家“息人事”,是执空之学,皎然的“野”是闲云野鹤的野,其“望”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望”。 这类野望蕴含着“昂藏独鹤闲心远,寂历秋花野意多”(《题周谏别业》)的超脱。
宋代以降,诗人野望现象变得普遍起来。 据宋诗分析系统统计,带“望”字的诗句有13120 条,比唐诗增加了8564 条;带“野”字的诗句有12432 条,比唐诗增加了9316 条;以“野望”为题的有56 首,比唐诗多出25 首。 宋诗中的“野望”事象增多,一方面与其收录数量增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宋代诗人已把野望作为一种审美文化看待有关。 如果说魏晋时期逃离城市、隐逸山野是诗人对各种人事制度压抑的反抗以及素朴人性回归的话,那么宋代诗人野望更多与市井生活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 前者是一种被迫、对抗的行为,而后者则是一种自觉、认同的行为。 与宋代都市文化相比,市井文化是一种生活化、自然化、无序化的世俗文化。 “市井”即市集或街道,它既蕴含着繁华与喧嚣,也包含着鄙陋与粗野。 由市井所孕育的市井文化介乎文明与野蛮之间,成为士人尤其是诗人野望的桥梁。 就诗歌追求而言,宋代已明确提出“野意”的诗性追求。就诗人而言,不管是“露花倒影”的柳永,还是“身如不系之舟”的苏轼,其诗词中都能找到“野”的意蕴,并且在野之时的心态也变得更加达观、随性。 同样是野望,唐孟郊之诗“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的偏狭、牢骚之蔽显而易见;宋苏轼之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通达、安适之态不言而喻。
及至元代,士人尤其是诗人野望成为一种趣味被把玩,野趣普遍被诗人认可和接受。 杨维桢《野亭》诗云:“孟郊得野趣,野有真曜庐。 魏先得野趣,野有野堂居。 云间沈东氏,草衣傲野夫”。 韦居安《梅磵诗话》云:“‘荷叶无多秋事晚,又同鸥鹭过残年。 ’亦颇得野趣”[8]。 明代以后,由于“商业的繁荣与随之而来的城市生活环境、市民生活习惯、生活趣味这些因素为士人提供了更为多样的生活条件,影响他们的生存状态,从而影响他们的观念,影响他们的心境”[9]。 其中狂癫者有之、隐匿者有之,而李贽可谓野性十足。 在罗宗强看来,李贽狂痴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逍遥于礼法之外,源于其高度的自信与独立的人格。 其褊急、鄙俗与“野”的自然本性有很大关系,在其诗《初到石湖》“入室呼尊酒,游春信马蹄”中可见一斑。 清代诗人姚淑、吴伟业、王士禛等诗人都有着浓郁的野望情结,其野望诗具有更深的文化意义和生存价值。 吴伟业《野望》“日暮悲笳起,寒鸦漠漠飞”何尝不是中国古代落寞诗人的生存写照与文化缩影? 至此,野望成为中国诗人心灵深处的文化符号和集体意识而走向了成熟。
二、“野望”事象的诗性呈现与表述
中国古代“野望”事象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诗性呈现也独具特色,其惟妙惟肖的人事描画、压抑情绪的书写对我们诗性还原历史文化、了解中国古代士人尤其是诗人的生活状态和心态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第一,“响字”构造动图是“野望”事象诗性呈现的基本特色。 与“春花”、“秋月”等物象呈现不同,“野望”事象不单是场景的呈现,而更是动作的再现。 从根本上说,物象是静图,便于移情;事象是动图,长于言事。 “野望”事象是诗人在“野”的自然空间中凭借“望”构筑诗意图像,起到释放压抑、舒缓心情的作用。 具体来说,“野望”之“望”为动作,在时间流动中构成事态行为。 “野望”之“野”为视域,在物象转换中构成诗性空间。 更进一步说,“野望”事象的诗性呈现就是时间空间化的审美和再现,其不以“情节”见长,而以“罔象”取胜,它无意于再现完整事件和宣泄情感,而是在动作的细微片断中透射人生、体验生命。 中国诗歌事象尤其“野望”事象的传神性的诗性书写一般是将动作提炼成 “响字”来呈现的。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引吕本中诗论云:“诗每句中须有一两字响,响字乃妙指。 如子美‘身轻一鸟过’,‘飞燕受风斜’,‘过’字‘受’字皆一句响字也”[10]。 与“卧听”、“夜闻”等听觉事象呈现也不尽相同,“野望”事象不是付诸于听觉,而是付诸于视觉。 听觉的诗性呈现主要通过线性的持续流动产生美感,而视觉的诗性呈现主要通过画面的并置组接构成诗意。 前者更多属于时间性审美,后者则主要属于空间性审美。 但与叙事相比,“野望”与“卧听”事象都不是纯粹的时间性审美或空间性审美,而是时间空间化审美。 “野望”诗歌事象的呈现犹如一盘有意蕴的沙画在时间轴中自由绵延一般,其力度和深度是有目共睹的。 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事象把汉末乱世之象写尽,让人扼腕悲叹;杜甫《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事象则把盛唐转衰之象写尽,让人凄切哀叹。这些力透纸背的诗性呈现都是通过动作构图的方式即事象塑造实现的。 可以说,“野望”事象通过动作营造的诗意图像是中国诗歌才有的本领。
第二,“托事于物”与“假外象喻人事”是“野望”事象诗性呈现的基本方式。 就物色而言,物有其容,野有其色。 诗人感物,流连万象。 在刘勰看来,“灼灼”呈现了“桃花之鲜”、“依依”再现了“杨柳之貌”。以《诗经》为例,旷野中的蔓草、野苹、芣苢、卷耳等物色的诗性呈现是诗人着力点。 譬如“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就是通过蔓草及其零露繁多的样貌来呈现诗意的。 “蔓草”呈现“野”的特性,“零露漙兮”则是“望”的诗性状态。 后世经典诗句“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陶渊明《归园田居》)之“野外”、“野桥齐度马”(杜甫《野望因过常少仙》)之“野桥”、“野树侵江阔”(杜甫《野望》)之“野树”、“亭景临山水”(杜甫《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之“野亭”、“行歌荒野中”(李白《见野草中有曰白头翁者》)的“野草”、“野水多游鱼”(张籍《野居》)的“野水”、“野鹤一辞笼”(白居易《自题酒库》)的“野鹤”等物象为野望诗性呈现提供了载体。 旧题王昌龄《诗格》指出:“若上句说事未出,以下一句助之,……如崔曙诗云:‘田家收已尽,苍苍唯白茅。 ’……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11](P158)。就人事而言,“野望”事象多通过“事对”呈现方式书写。 譬如王绩《野望》“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的诗意就是通过两个事象对偶而成的。 刘勰云:“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言对为易,事对为难”[12]。 王昌龄《诗格》亦云:“夫诗,有生杀回薄,以象四时,亦禀人事,语诸类并如之。 诸为笔,不可故不对,得还须对”[11](P168)。与事对呈现相比,野意书写更难。 宋代诗论家魏庆之 《诗人玉屑》载曰:“人之为诗,要有野意。 盖诗非文不腴,非质不枯,能始腴而终枯,无中边之殊,意味自长。 风人以来,得野意者,惟渊明耳”[13]。 陶渊明将农耕生活诗意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尽乡野人事之趣。 陶渊明所呈现的与外人隔绝的桃花源既有“芳草鲜美”的乡野物色,又有“往来种作”的朴质劳作。可以说,“野”的诗性呈现是中国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常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爰得我所”理想生活的追求。
第三,沉重、低沉是“野望”事象诗性呈现的主题和底色。 中国古代士人尤其是诗人的野望主题表达是多种多样,但总的来说,孤独、惆怅型事象居多,而闲适、欢愉型事象较少。 具体来说,有忠君爱国而不得志的野望,杜甫《野望》“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为代表;有贬谪而身受排挤的野望,苏轼“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为代表;也有“唯将迟暮供多病”病老的野望;更有感慨时局“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野望、“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苦闷的野望;更有生死终极叩问的野望,比如熊孺登的《寒食野望》“冢头莫种有花树,春色不关泉下人”。 当然也有梅尧臣《野望》“新晴宜野望,最爱是山前”的轻快与欢愉、杜甫壮游时的野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皎然《陪卢判官水堂夜宴》“爱君高野意,烹茗钓沦涟”的闲适。 但整体而言,中国古代士人尤其是诗人野望主题更多是沉重、低沉的,带着一层令人窒息的压抑感和凝重感。 从根本上说,野望的本质就是反抗与解放。 反抗的是人事的枷锁;解放的是心态的平和。 从此意义上说,野望起到了心灵净化和宣泄的功能,对中国古代士人尤其是诗人心态平和与诗性生存意义重大。
“野望”事象在诗歌中是如何具体呈现的?下面以杜甫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在秦州所作《野望》为例,通过“假外象以喻人事”的易象(事象)剖之,以见其概。 全诗如下:
清秋望不极,迢递起曾阴。
远水兼天净,孤城隐雾深。
叶稀风更落,山迥日初沉。
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
王夫之云:“如此作自是《野望》绝佳写景诗,只咏得现量分明,……俗目不知,见其有‘叶落’‘日沉’‘独鹤’‘昏鸦’之语,辄妄臆其有国削、君危、贤人隐、奸邪盛之意,审尔,则何处更有杜陵邪? ”[14]在我们看来,“有杜陵”不在“物”,而在“事物”,即“托事于物”言“不可述之事”。
在众多诗人中,被世人称为少陵野老的杜甫可谓是野望诗的集大成者。 杜诗中不仅“野望”事象出现得最多,而且专以“野望”为题的就有5 首,“野”字入诗的有165 条,“望”字入诗的则有136 条。杜甫此诗以“清秋望不极,迢递起曾阴”为总领,描画了秦州秋野五个现量的场景(物象),隐含了五个易象(事象)。 一是“远水天净”的远景,可谓“一望清旷”。 此象与“云上于天”即“水天一色”乾下坎上“需”的人事卦象有可征之处。 需卦有“需于郊,利用恒”的卦辞。 “需”者,待也。 杜甫辞去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的职务,携妻带子,翻越重重陇坂(今关山),来到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时年四十八岁。 关于杜甫西向客秦,就有“寻亲访友”说。 以“水天一色”的外象喻杜甫怀远道、思君王之“需”,“不可见之事”显而易见。 二是“孤城雾深”的近景,此可谓“再望迷离”。 此象与“有言不信”困卦之象有类似之处。 此卦既有“入于幽谷,三岁不觌”的孤独,又有“困于酒食,朱绂方来”的迷茫。 关于杜甫西向客秦,就有“求食问衣说”。 《唐书》载:“关辅饥,(杜甫)辄弃官去”。 以“入于幽谷”事象喻杜甫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之“困”,“不可述之事”溢于言表。 三是“叶稀风落”的近景,此可谓“三望萧疏”。此象与“山上有木”的渐卦之象有相似之处。 “渐”即“进”“动不穷也”。 假“山上有木”的事象喻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渐”,“不可言之理”深切著明。 四是“山迥日沉”的远景,此可谓“四望沉冥”。 此象与“天在山中”的大畜卦之象有可征之处。 假“天在山中”的事象喻杜甫“君子藏器,待时而动”之“大畜”,“不可达之情”灿然于前。 从时空观念上看,前两个事象是空间事象,后两个事象是时间事象。 从此事象中,我们可以深刻领会杜甫生存空间挤压而郁闷、时间流逝而惆怅的感慨。 最后以“独鹤归晚”“昏鸦满林”图景作结,良可叹矣! 其间蕴含了多少惆怅和无奈、大唐王朝气数将尽等不可述之事。 正如清代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指出:“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 ”“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15]。 在中国古代,以易引诗、释诗是中国诗歌的创造,也是中国诗学的创新。 聂济冬教授就指出:“唐代宗大历年间,杜甫常引汉儒易说为典入诗, ……这成为大历年间杜诗的一个写作模式。如大历元年在夔州作《热》诗,‘雷霆空霹雳,云雨竟虚无。 ’该诗反用《周易·系辞上》:‘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日月运行,一寒一暑’”[16]。 杜甫“野望绝佳”的美誉也许就是源于此。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说:“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 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17]。 “野望”事象就是为了使人摆脱日常之事的纷扰,在“事物”的诗性世界里去感受和体验应然生活,从而使人心灵得以净化,生活得以提升。
一言以蔽之,“野望”事象的呈现特色是“响字”构造动图;呈现方式是“托事于物”和“假外象喻人事”;呈现主题多是沉重、低沉的。 “野望”事象是中国古代诗人矛盾、迷茫、压抑等各种心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华夏民族各种事变和动作的灵魂,蕴含着中国诗人无比坚韧的民族性格和诗性智慧。
三、“野望”事象的诗性功能与精神
“野望”作为一种诗歌事象和文化事象,对中国古人宣泄情感、释放压抑、返归自我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野望”是中国古代诗人自我救赎、干预世事的最重要的方式。 “野望”事象提供人事更迭、文化焦虑、士人心态等人生百态的真实图景,具有诸多诗性功能,发挥着重要的精神作用。
第一,“野望”事象对人的自然本性回归功能。从深层意义上说,人所有的困惑多是由于人的动物性(自然本性)与社会性(文化和文明)之间产生的矛盾。 野望不管是作为一种诗歌事象,还是文化事象,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矛盾和困惑。 一方面,人之为人是由于人具有了社会属性。 马克思曾指出:“不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活动,而是人的活动决定了人的存在,人的存在不再是纯粹的自然规定,而是人的活动过程本身及其成果即社会”[18]。 另一方面,人的社会属性即人类文明一般又是以“化性起伪”的代价换取的,人的自然本性丢失又谈何完整意义上的人呢?在席勒看来,诗人或者是自然,或者是寻求自然,前者使他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使他成为感伤的诗人。 诗的精神是不朽的,不仅那通达自然的道路永远为他敞开着,而且有一种不可摧毁的强大冲动不断地促使他回到自然。 对中国古人来说,“野望”正是“一种不可摧毁的强大冲动”,促使古人回到本性、回归自然。 可以说,“野望”既是为了回归人素朴的自然本性,也是为了扬弃厚重的社会属性。 “野望”事象的诗性功能与精神就在于其能在深层意义上对社会、文化与文明起到否定之否定的解构功能,从而消解人类自设的各种枷锁、回归人类应有的诗性生存。 就此功能来说,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为中国古代士人诗性生存提供了一种自由和自然的范本。
第二,“野望”事象的灵魂净化功能。 毋庸置疑,人是在历事和言事中生存的。 “心有此事,即有此事之象”,如白居易云:“大凡人之感于事,……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19]。 从此意义上说,事象对个人而言,就具有了灵魂净化的功能。 不仅如此,事象将“不可述之事”变成可述之事,滋养人的灵魂、诗意人的生活。 在中国古代,通过“望”这一特定动作、“野”这一特殊处境不仅能使诗人回到自然本性,而且还能使诗人灵魂得到净化,创作出非同凡响的诗作。 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云:“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是故文章之作, 恒发于羁旅草野”[20]。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人通过野望所达到的灵魂净化并不是宗教性的,而是通过天人合一的物化即“物我界限消解,万物融化为一”达成的。从庄子物化撄宁的“齐物论”到陶渊明《形影神赠答诗》再到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都有所体现。 就此功能来说,苏轼的“野望”事象达观、随性,为中国古代诗人的灵魂拷问与净化提供了成功典范。
第三,“野望”事象的现实超越功能。 “野望”作为中国古代士人尤其是诗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文化事象既有现实性,也有超越性。一方面,“野望”事象一般都是基于现实的,事象诗人去伪存真、明白入素、立象尽事,创造有尊严的生活。 在民族危难、诗歌困厄之时,揭示真相的事象诗人就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真实事象的揭示不仅铸就了杜甫“诗史”的伟大与担当,而且在现实性上也实现了审美救赎功能。 另一方面,“野望”事象又都是基于想象的,诗比历史更真实、更富有哲学意味就源于此。 不管是亚理士多德“诗人的职责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的思想,还是叶燮“事之入神境者”“想象以为事”的主张都说明了这一点。人最深刻的方面一般通过动作才见诸现实,包括“野望”在内所有事象都致力于动作构图来形成诗意。汪元量《湖州歌》诗云:“殿上群臣默不言,伯颜丞相趣降笺。 三宫共在珠帘下,万骑虬须绕殿前”,默、降、在、绕为“响字”构成动作乃传神之笔,耐人寻味。 杜甫《春宿左省》“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把“一落风尘下,方知为吏难”的谨小慎微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微妙之处不在动作的连续性,而在动作的片断想象即事象中。 可以说,“想象以为事”使中国古代诗人具有了现实超越性,诗意的栖居也就成为可能。
第四,“野望”事象的诗学文化功能。 不可否认,人以历事的方式改造世界、以事象的形式认识世界。“野望”事象是诗人在“野”的自然空间中,凭借“望”构筑的诗意图像,对准确把握、认识中国古代的诗学文化、生存智慧、诗人心态、审美情趣等意义重大。 就生存而言,儒、道、释都有“野望”情结,只不过文化特性不同而已。 儒家“敏于事”,崇尚“有为”,铸就了杜甫诗史事象;道家“事无事”,注重“无为”,成就了李白诗仙事象;释家“息人事”,强调“执空”,造就了王维诗佛事象。 华夏民族的诗性记忆、生命体验、诗学文化需要诗歌事象呈现。 从审美文化的角度看,“野望”事象属于宏阔、撕裂的壮美,有着崇高的悲剧特质。 这与闲适、平和、优美的“卧听”事象明显不同。
从“野望”事象的诗性精神来看,中国古人是自然的人,打动我们的是活生生的现实。 然而尽管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现代人已不是自然的人,而是文化的人,打动我们的也不再是现实,而是充满着各种矛盾的观念,但正如席勒所言,虽然想象力和理解力的自由使人离开自然的朴素、真实和必然性,但在人类文明当前的情况下,能够强烈激起诗的精神的仍是自然。 从此意义上说,中国古代“野望”事象的诗性精神还是值得传承的。
注:
①“事象”是中国古代独创的概念,在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诗学等领域广泛使用,产生了民俗事象、社会事象、心理事象、诗歌事象等诸多概念。 对诗学事象进一步考察,可参阅拙文《中国诗学中的事象说初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 期;《中国诗学事象刍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2-28(第1875期)。
②本文唐诗与宋诗中“野望”事象的统计数字是通过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开发的《全唐诗分析系统》和《全宋诗分析系统》检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