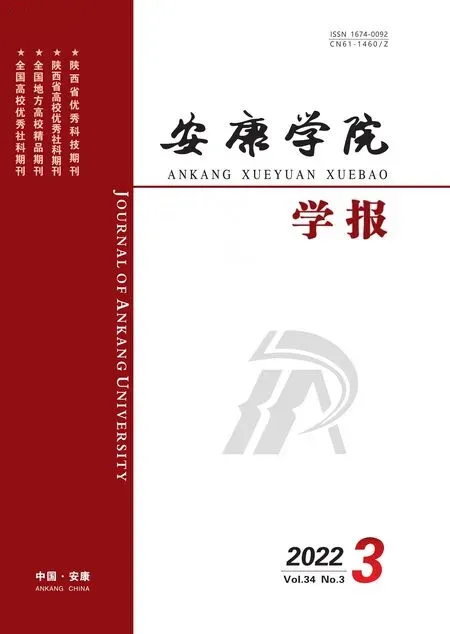嘉道年间清政府的陕南“山防”政略及其历史影响
王 振
(泰山学院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山东 泰安 271000)
清代,“陕西由略阳、凤县逶迤而东,经宝鸡、郿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郧西、上津,中间高陵深谷,千支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宁羌、褒城逶迤而东,经南江、通江、巴州、太平、大宁、开县、奉节、巫山、定远、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二竹、房县、兴山、保康,中间高陵深谷,千支万派,统谓之巴山老林”[1]。可见,陕南即古代“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所属而现归陕西管辖之区域,其大部即古史常称之“南山”。清代自康熙年间起,随着人地矛盾的凸显,湖北、四川、河南、安徽和江西诸省流民大量进入包括陕南在内的秦巴山区垦食,到乾隆末年,人数已达数百万之众。清政府于此地控制力薄弱,且山民经常遭受胥吏盘剥和啯匪袭扰,民生维艰,故容易受到白莲教传教活动煽惑,终成农民起义渊薮。
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如何通过有效治理恢复陕南统治秩序,巩固“山防”安全,成为清政府亟须筹思谋划的重要问题。曾长期任职陕南的严如熤于道光年间亲赴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壤山区,综核陕南“山防”形势,提出办团练、安流民、筑堡寨、习兵法和兴文教等巩固“山防”和重建陕南流民聚集区域社会秩序的系统措施,为白莲教起义后陕南“棚民”社会治理和“山防”筹划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提出的陕南“山防”政略对当今陕南社会治理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鉴于此,本文从陕南“山防”问题的历史背景出发,探讨严如熤为系统筹划陕南“山防”所提出的具体政略和特点,分析其对当今陕南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
一、严如熤与嘉道年间的陕南“山防”问题
乾嘉之际正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前夜,也是清王朝告别康乾盛世走向衰落的重要节点。故而,在乾嘉之交,清王朝各种社会危机交织,其突出表现之一便是白莲教起义的爆发。对于清王朝来说,白莲教起义虽遭到镇压,然其给清朝统治造成的冲击、镇压起义中暴露出来的秦巴“山防”安全问题、“棚民”社会治理问题和区域社会治理问题等,都是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嘉道年间,乾嘉考据学虽仍为学术主流,但亦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具体问题,道咸经世派的先驱严如熤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严氏仕途虽不如同时期之林则徐、贺长龄和陶澍等顺畅,却在白莲教起义后在陕南“山防”筹划中通过实地踏勘和系统调研提出了以区域开发和安抚流民为核心的系统政略,为白莲教起义后陕南社会治理体系的优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严如熤的陕南社会治理政略,正是在秦巴山区“棚民”社会形成、白莲教起义遭到清政府镇压和陕南“山防”安全问题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一) 严如熤生平
严如熤(1759—1826),字炳文,号乐园,湖南溆浦人。严氏少时曾入岳麓书院随经世名家罗典习天文、地理和军事。乾隆六十年(1795),湘贵苗民起义爆发后,正在沅州明山书院执教的严如熤受湖南学正张尧成举荐入湖南巡抚姜晟幕,参与筹划镇压起义和善后事宜。嘉庆三年(1798),严氏因参与平叛“苗乱”之功举孝廉方正,并受湖北巡抚毕沅之托著《苗防备览》一书。嘉庆五年(1800),白莲教起义爆发,严氏廷试奏对《平定三省剿匪方略》,得嘉庆皇帝嘉许,亲擢其为廷试第一并授职军机处。此时,清廷与白莲教起义军激战正酣,亟需实务人才。严氏于嘉庆六年(1801)结束京官生涯出补陕西旬阳知县,两年后调任定远厅同知,又五年调潼关厅同知。嘉庆十五年(1810),升任汉中知府,道光元年(1820),升任陕甘兵备道,道光五年(1825),调任贵州按察使,未赴任。翌年,调任陕西按察使不久病逝[2]。严氏任职陕南凡二十六年,期间曾著《三省边防备览》 《汉中府记》 《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等书,为学界了解清中期陕南移民社会和清政府为治理流民社会所采取的“山防”政略提供了宝贵史料。
(二)“棚民”社会的形成
陕南地处秦巴老林,虽地接中土腹地,却自古人烟稀少,犹化外之地。康熙年间,清王朝推行“摊丁入亩”,规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极大促进了各省荒地的开垦和人口滋长。我国古代人口自秦汉以后一直在五六千万左右徘徊,到乾隆末年已突破三亿。人口大幅滋长导致湖北、四川、河南、江西和安徽等传统农业条件较为优越地区之人地矛盾凸显,而秦巴老林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土著人所种者十分一二。招外省客民纳课,数金辙指地一块,立约给其垦种,客民亦不能尽种,转招客佃,积数十年有至七八转者,一户分作数十户。客租只认招主,并不知地主为谁”[3]卷11。在此背景下,自康熙末年起,数省流民徙入秦巴老林垦食谋生,到乾隆末年,人数已达数百万人[4]。秦巴老林聚集之流民,清政府称其为“棚民”。严如熤称,“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做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寫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避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3]卷11。
(三)“山防”问题的由来
清代中期,陕南移民于秦巴“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若遇荒年,山内产粮无疑供养,则可能“添数十万无业流民”,成为影响区域安定的一大隐患。同时,“棚民”社会结构复杂,民风剽悍,人心不古。对此,严如熤分析称,“川陕边檄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呼朋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奸拐之事,无日不有。人理既灭,事变所以频仍也”。山民散落居住且经常面对匪徒威胁,为保安生多入教结社。对于山民容易受到白莲教等秘密教门影响之原因,严如熤认为“开山种土,良民为多,其间与匪徒相比者,亦自有故”,因为“山内村落绝少”,“匪徒窃劫,难资守望之力”,“不敢与匪徒为难”,而“教匪之煽惑山民,称持咒念经,可免劫杀,立登仙佛。愚民无知,共相崇信,故入教者多”[3]卷11。
“教匪”之外,山内还有称为“啯匪”者,其“较教匪为悍”,平日多隐匿“未开老林之中”,遇有“场集”,则“猝至”,敲诈“场头”,或“劫掠敛钱”而去。“啯匪”多由山内无业游民构成,而赌博之风盛行是造成一些山民破产失业的主要原因。山内赌博风气之盛,令人唏嘘。严如熤称,“山内地虽荒凉,而赌局绝大,往往数百两千两为输赢之注,无钱以偿流而为盗”,匪徒中还有“领账房之名”者,“遇民间红白事”则以开赌局之名对主家行敲诈勒索之实,“所输之数,勒主人作保担认,强抢牛马,逼卖田产,无所不至”,而“此类领账房者皆匪中豪长,与胥役兵丁多相勾结,甚至衙门兵丁受其岁遗陋规”,故官府查拿多流于形式,而“地方绅耆保正无敢过问”。另外,“山内各色痞徒闲游城市者,统谓之闲打浪”,其“值有军兴则充乡勇营夫,所得钱粮随手花消,遇啯匪则想从劫掠”,“闲打浪既入便成啯匪,啯匪之众即为教匪”[3]卷11。山内赌博风气盛行,啯匪横行乡里,秦巴老林中的“棚民”社会处于严重失序状态,以至该地成为白莲教传教的温床,终至白莲教起义于嘉庆元年(1796)爆发后陕南迅即成为白莲教起义军转战和补充的重要地区。
白莲教起义自嘉庆元年(1796)爆发,到嘉庆九年(1804)被彻底剿灭,前后历时九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清政府不仅大力整肃朝纲,惩办和珅以缓和阶级矛盾,还严惩了在川楚陕前线作战失利的二十三位一、二品大员,且前后为此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导致国库空虚,以至有史家将白莲教起义视为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清政府虽“竭宇内之兵力”[5]残酷镇压了白莲教起义,然陕南“棚民”社会中存在的社会秩序失控、政府统治力薄弱等问题依然存在。故而,在镇压白莲教起义后,清政府亟须恢复陕南秦巴山林的社会统治秩序,并通过军事建设和社会治理消除流民社会存在的安全隐患。严如熤正是在此背景下调任陕南,并著《三省边防备览》等书。嘉道年间,清政府为重建秦巴老林“棚民”社会秩序而在军事建设和社会治理中采取的消除社会安全隐患的一系列措施,即是“山防”问题。本文以“山防”为名,是因道光年间著名经世思想家魏源在其所著《皇朝经世文编》中将严如熤等陕南地方官员讨论秦巴棚民社会治理问题的著述汇编后,以“山防”条目称之[6]。此即为嘉道年间陕南“山防”问题之由来。
二、嘉道年间清政府加强陕南“山防”安全的政略措施
嘉庆九年(1804),白莲教起义终遭清廷镇压。为平息起义,清廷不仅耗尽国库,还彻查和珅贪污案以整肃朝纲,并严厉拿办了镇压起义中办事不力之文武大员数十人。尤其是镇压起义中暴露出绿营难敷其用的问题,迫使清廷允许地方官员筹办团练。起义遭镇压后,清廷朝野对起义原因进行反思,认为秦巴山区人地矛盾凸显所导致的民生危机、流民社会治理秩序的失控以及清政府控制薄弱是导致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此背景下,嘉道年间长期在陕南任职的严如熤亲履秦巴山区,深入了解陕南秦巴山区之民生物产、山川要塞、建置沿革和绿营驻防情形,并在总结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陕南“棚民”社会治理和巩固“山防”安全的系统政略措施。
(一)设重臣以一事权,分州县以专治理
秦巴山区地接川、楚、陕、豫、甘五省,高陵深山,控制不易,加之分省管理,使得该地一旦出现“山防”安全问题,难以通盘查办。因而,若能于秦巴山区设置统一的行政建制单位,并设重臣统理,便可收统一事权之效。为此,明政府曾于成化十二年(1477)设置郧阳巡抚,驻地为郧阳府郧阳县,掌管包括陕南在内之秦巴山区五道八府军民事务。清初,清政府为应对西南战事曾沿袭郧阳巡抚建置,后于康熙三年(1644) 裁撤。康熙十五年(1676),“三藩之乱”期间清政府复设郧阳巡抚,旋于康熙十九年(1680) 彻底裁撤[7]。
针对秦巴山区行政归属分散和事权难一的问题,严如熤建议参考明朝设置郧阳巡抚的经验,设重臣以一事权。严如熤认为:“安置南山之大计,莫如适中之处设重臣以一事权。”[3]卷11严如熤还认为,“县治过大,难以兼顾”也是陕南“山防”存在的重要问题,并建议于“太平之城口,洋县之华阳,安康之砖坪,平利之镇坪”等地“辽阔之处分州县以专其治理”。严如熤认为加强政府对秦巴山区之控制,“添营不如分县”,因为大量驻防绿营仅“资弹压而已,未能责以抚绥导教”,“虽增添额兵”,然“其民不能管也”[8]465。
设重臣,分州县,必相应增加绿营驻防人数,加之各级官吏胥役之食用开支,若强令生存维艰之山民供应则会加剧官民矛盾,然自外地转运,山高路远,耗费尤多。为解决该问题,严如熤建议在“勘定之初”推行“屯政”,认为“安边之猷,兵食并重”,“惟屯政最安边良法”,政府可综核“棚民既有水田”而成土著者之田为“屯田”,“编其人为屯丁,定为口分世业,设屯卞以管束之,作屯堡以团聚之,寸土颗粒,官无利焉。再为清出叛产绝业,收其租课,以供屯务之杂用”,以收“兵寓于民”之效[8]466。
(二)审形势通盘筹划,守要塞固圉保民
我国传统地缘安全思想主张“守庭圉不如固藩篱”。陕南地属秦巴老林,其“汉中、兴安、商州”三地与“四川之保宁、绥定、夔州,湖北之郧阳、宜昌”交壤,“地均犬牙相错。其长林深谷,往往跨越两三省,难以界画。故一隅有事,边檄悉警”。陕南还与关中相接,“山防”不惟维护山内安定,更在保障关中大局,故巩固“山防”实际贯穿着“保藩固圉”和以藩为屏的地缘战略意图。严如熤认为,陕南“山防”须将其纳入三省秦巴山区视为整体考量,并以地缘安全视野对区内山川形势通盘筹划,以收“固圉保民”之效[9]467。严如熤认为,山内出现兵乱,应通过对秦巴山内道路、隘口尤其是出山峪口的重点卡守,将“匪患”堵截在山内剿灭,切不可纵之于平原,因为“平原千里,贼之往来飘忽者,四处可以扰乱,官军虽健”,却难以堵截,“自来贼之扰平原,较起山内者,裁定为更难”[9]469。显然,从“山防”目的和形势来看,勿纵“匪患”于平原而确保将其截留山内剿灭的思路是正确的。
为此,严如熤在躬亲踏勘后对秦巴“形势”进行整体分析,认为“南山在陕西西安府之南,山高而长,西为太白山,北为华岳山。由秦陇而来,逾北栈,经五郎、孝义,东出商、洛,融结河南诸山。镇安、旬阳、汉阴、石泉、洋县各山,皆其分支别派。弯岩邃谷,老林深菁,多人迹所不至”,自古为“南山盗贼”潜伏之渊薮,而“巴山老林,跨川、陕两省,周行千数百里”,“老树阴森”,“山幽谷暗”,“入其中者蒙蔽不见天日”,故“稽防难周,宜其为逋逃薮也”[9]467。面对如此封闭而复杂的地缘形势,严如熤建议要严守秦巴老林出山之山路、隘口和要塞,要积极借鉴历史上秦巴山区防维戍守的历史经验,不要“自撤藩篱”,“阴平无备”以至“疏于防维”,如“守秦中者,则由华州,经蓝田,至宝鸡,共七十二峪口”,“故当办理贼之时”,宜“于各峪口遍设卡扼,以重省城门户”[9]469。
(三)安流民听其经营,轻科征与民生计
剿灭“匪患”和严密防维只是治标,而如何对“五方杂处”的“棚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才是治本,而清政府控制基层社会惯用之“保甲法”在山内并不可行,因为“棚民本无定居,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处”,“保正甲长相距恒数里、数十里”,难以做到“朝夕稽查”,不仅“徒滋胥吏之鱼肉”,还“废时失业,多费口粮”,置于“客店之循环簿”因“外省流民入山,多寄宿林岩,匪徒则山径取捷,均不在客店安歇”,故也无实际意义。严如熤认为:“山内防维之策,总以安辑流民为第一要务”,“流民开山作厂,既各安其业,奸徒亦不能以煽惑”,“土流安业,自不至轻有生心”[9]471。秦巴“棚民”社会本就是“湖广”和“广东、安徽、江西”各省流民为求生计迁移聚集而成,故秦巴山区“山防”安全和“棚民”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于“安流民”,其关键在于与民生计。
随着“棚民”聚集繁衍,山内人地矛盾逐渐凸显,其人耕种之外在“山内木、笋、纸、耳、香蕈、铁、沙金各厂”从事专业或兼业便成为重要的谋生之途,“流寓客民所藉资生者,而木厂为大”,其“大圆木厂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此外更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山内丰登。包谷值贱,则厂开愈大,人聚益众。如值包谷清风,价值大贵,则歇厂停工。而既聚之众不能复散,纷纷多事,此防范之最难者”。此前有秦巴山区地方官员认为“贼匪滋事之始”,建议清政府“严行驱散”。严如熤认为“是大不然”,“若不准开厂”则平添“数十万无业流民,难保其不附从为乱”,“故只当听其经营”,政府可于每厂“设卡伦,无事安心工作,有警协力防堵”即可[10]473。在许民开厂务工的同时,针对“一邑钱粮不逾千两,而民间有数万之累”之情形,严如熤认为“山内征收悉从轻科”尚不足,催科之众“差役、地棍”之害,“花户”所谓“截粮”之弊,亦应破除,并建议地方官“随到随收”,“或分期下乡”许民“就近完纳”,其“征银不满一钱者,准以铜钱完纳”[3]卷11。
(四)禁赌博清盗之源,崇儒教移风易俗
秦巴山区“山防”问题的出现除与当地民生艰难有关外,还与“棚民”社会“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造成的乡土民风有关。因而,巩固陕南“山防”安全,仅与民生计以抚流民尚不足,还要引导山内民风,帮助山民兴文教以化育风俗。严如熤认为,“棚民”社会中流行之赌博陋习严重扰乱了山内社会秩序,因为“匪徒之聚,大抵皆由赌博”,且其多为“山内痞徒闲游城市者”,当地人称为“闲打浪”,“此辈值有军兴,则充乡勇营夫”,钱财挥霍耗尽若“遇啯匪则相从劫掠”,故“闲打浪既久,便成啯匪”,更甚者在于“啯匪之众,即为教匪流贼”。因而,严如熤认为“严明守令,能禁赌博,即为清盗之源”[10]471。
“啯匪”是“教匪”来源之一,然两者又大不同。“啯匪”多“无赖恶少,不能谋衣食”而生,故只要官民一体设计擒杀,易为清肃,然“教匪”则不然,秦巴山民入白莲教者“多系有田产之人”,并对其教“持斋念咒”之仪式和所宣扬之“戒贪戒淫,成仙成佛”的教义坚信不疑,故“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资粮,衣食相通,不分尔我”,一旦“地方有传教之人,久之引诱渐广,村落中则乡约、客头吃教,城镇中则差役、书办吃教”,导致官府“所用稽查之人,即为教中之人。教首窜伏大村庄,互相蔽护,难于拘捕”。严如熤认为,陕南“山防”安全的基础在于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将“棚民”社会纳入常轨,其关键在于广兴学堂,崇儒重道,通过儒家正学实现“棚民”社会的风俗易化,进而破除白莲教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土壤。为此,严如熤指出,“欲正教之兴,则必使城镇村落之间,多读书务正之人”,建议“山内州县崇重师儒,广设义馆”,若“村落中有一二明理之童生,即可少数十户吃教之愚民,认为这是“拔祸本、塞乱源之至计”[10]474。
(五)筑堡寨坚壁清野,办团练以为辅助
秦巴山区自古为农民起义军聚集之地。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兵败洪承畴后曾于商南县城南之黑漆河畔的“闯王寨”休养三年,后入河南,经山西,攻入北京。李自成和张献忠在陕北举兵之初,曾进袭山西,并都曾被崇祯年间时任兵部左侍郎卢象升败于山西,而卢象升所用之策便是坚壁清野。在清政府于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过程中,坚壁清野之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严如熤认为清政府应积极借鉴卢象升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军时采用的坚壁清野之策,并将其作为筹划陕南“山防”的“第一要略”。针对秦巴山内“村落绝少”和民户“零星散处”若遇“匪徒行窃,孤掌难鸣”之情形,严如熤认为“惟行聚堡之法”,以使民人“众志成城”[11]475。聚堡之法还可有效削弱“贼势”,使其得不到钱粮供给,因为白莲教起义军与清军不同,所用钱粮资用多随地补给,使“民尽倚险结寨作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可使其“无人可裹,无粮可掠”,则“贼势自衰”[3]卷11。另外,聚堡寨既可“保民”,还可以协助官军清剿。清军镇压白莲教起义时,一般只要“大兵追击得及,鲜不获大胜”,但“贼匪奔窜山谷,不由路径”,筑堡寨并“加以团练”使民“据险以拒”便可收迟滞起义军行动以待官军到来之效[11]476。针对过去所修“城堡”“旋修旋圮”的情形,严如熤还提出了“用土不如用石”以及“只可石片加高”等用料和施工上的改良之法[3]卷11。乾隆末年以后,绿营战斗力下降,导致嘉庆皇帝在镇压湘西苗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中被迫允许地方士绅兴办团练。在镇压秦巴白莲教起义时,各省抽调之绿营“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肥,习以为常,山内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疲,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而矫捷坚实可恃,必以黔兵为第一”。严如熤分析黔兵战斗力较强的原因认为,“贵州地无三里平壤”,其人“日走险路十里、十数里,则脚力练定”,其地“风土瘠凉特甚,市集无千金之货,宾朋鲜兼味之筵,茹苦食穷,安之有素”,故黔兵往往“极淳朴,极耐劳习险”[12]。严如熤总结清政府在镇压两次起义中开办团练的经验并分析黔兵战斗力较强的原因后认为,秦巴“山民质朴劲勇,耐劳习险,非平原百姓气浮而脆者可比”,尤其是“山中打生猎户”和“州县民壮”[3]卷11,其淳朴耐劳之性堪比黔兵,可通过办团练对其组织训练并以之协助官府控驭地方。
镇压白莲教起义时,清政府兴办团练,只是绿营不堪其用情势下的无奈之举,故团练兴办之初,清政府依然对地方士绅掌握军队存在防范心理,而在镇压白莲教起义过程中,地方团练多为辅助,而非担任主攻职责。严如熤认为,“团练乡民,不过令其保聚,无遭蹂厢,非欲以此邀战功也”,同时“百姓各有身家,不当使致命于必死之贼”,因而亦不必以绿营标准对团练乡民教习,其仅“演火铣、击石子,能于百步外中靶为上,不必今习刀矛”[3]卷11。严如熤主张,鉴于秦巴山内绿营汛塘驻防过于分散且兵额不足之情形,“当相县之大小,大县设一百名,中、小亦必八十名,责成县官,勤加操练”,同时团练之民“每名岁支口粮一十二两”,其“经费即查明从前叛产绝业,将佃租动拨,自可敷用”。此外,严如熤还驳斥了以团练为“劳民”的观点,认为“团练之众,虽不足以当大贼”,却可于平时起到张“声势”以震慑“小贼”的作用,亦可于有事时担任“探侦”、运输辎重以及协剿等任务,而其“每月操练两次,不过费两日之功,余二十八日,尽可力作”[13]。
三、嘉道年间清政府陕南“山防”政略的历史影响
乾隆末年,清王朝开始告别康乾盛世的辉煌,并因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产生而江河日下。其中,因白莲教起义而出现的“山防”问题既是清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一个重要推手。“山防”问题与嘉庆年间秦巴“棚民”社会秩序失控密切相关,故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如何筹划“山防”安全,其关键仍在于如何安抚流民和治理“棚民”社会。白莲教虽被镇压,然秦巴山区流民聚集问题依然存在,故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清除诱发农民起义的土壤。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任给事中卓秉恬上《川楚陕老林情形疏》,建议嘉庆皇帝“合三省而共议之,并“於扼要之地,专设大员控制”[14]。嘉庆皇帝对此高度认同,并将该疏转给当时三省督抚商议施行。同年,升任陕安兵备道不久的严如熤接受四川总督蒋攸铦委派,“遍历南山”,在实地踏勘的基础上提出了巩固陕南“山防”安全和推进“棚民”社会治理的系统策略,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以严如熤为代表的学者官僚躬身踏勘,实地调研,密切关注“山防”安全问题,对于嘉道年间清代学风的转变产生了推动作用。长期以来,学界探究道咸经世之学,多以魏源著《海国图志》和《皇朝经世文编》等为源头,且以咸同间张穆著《蒙古游牧记》和何秋涛著《朔方备成》为其延续。实际上,严如熤所著《三省边防备览》等书及其筹划陕南“山防”的系统政略不仅在乾嘉清学的落日余晖下闪耀着超越时代的理性光彩,而且从学术渊源上亦可作为道咸经世学术之滥觞。秦巴山区虽处天下腹心,然因域内高陵深山,丛林密菁,长期如化外之地。故精通文史、长于舆地的严如熤在陕南“山防”筹划中从事著书立说的活动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嘉道学术大背景下也具有边疆史地研究的经世内涵,对于推动后世学人走出故纸堆去探究经世致用之学,乃至“睁眼看世界”,都起到了一定的引领示范作用[15]。正因如此,《海国图志》的编纂者魏源在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时将严如熤关于秦巴山区“棚民”社会治理的著述遴选入册,并以“山防”条目名之。
严如熤提出的陕南“山防”政略,核心问题在于安抚流民和治理“棚民”社会。实际上,“棚民”作为清代流民之一种,并非仅在秦巴山区存在,其出现不限于一时一地,尤其是清代中期以来随着山林封禁政策的解除和适合高海拔山区种植的玉米等农作物的引进推广,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现象。严如熤立足秦巴山区实际所提出的“以安抚流民为第一要义”的系统政略,将重置行政区划、统一地方事权、兴修水利、鼓励屯田、发展工商业、修筑堡寨、兴办团练、查禁赌博和移风易俗等系列政策有机结合,有力推动了陕南秦巴山区“棚民”社会从秩序失控到秩序重建的转变,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实现了陕南“棚民”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有利于维护秦巴山区“棚民”社会的安定,也为山区人民安心生产和安居乐业提供了基本保障,并对近代以来秦巴山区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严如熤在筹划陕南“山防”时并未将其简单视为一个地域性的安全问题,而是将其上升到地缘政治安全的高度,将“山防”安全理解为一个关乎关中、华中和四川腹地安定乃至全局稳定的重大地缘安全问题,在陕南“山防”安全筹划中贯彻了“保藩固圉”的地缘战略思想。同时,严如熤在筹划陕南“山防”问题时也未将其仅仅视为一个军事防御问题,而是更多将之纳入社会民生视角之下,并力图通过安抚流民、优化民生、争取民心和加强基层社会控制来探索构建适合陕南“棚民”地域特点的社会治理体系。严如熤提出的陕南“山防”政略,对当今陕南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