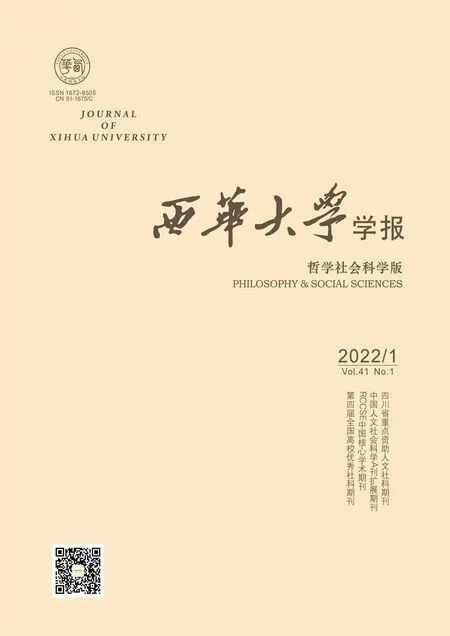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谢桃坊
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 四川成都 610071
一
《朱子晚年定论》是明代著名心学家王阳明于正德九年(1514)在南京时辑录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三十件而编成的。在这些书简中,朱熹流露出对以训诂注释的治学方法的悔悟。王阳明认为此乃朱熹晚年真正闻道而与其心学之旨相合,试图以此平息一场关于理学与心学的争论。正德十年(1515)冬,王阳明为此编作序,当时抄本已在学术界流传;至正德十三年(1518),门人袁庆麟等刻印于雩都(江西于都县)。《朱子晚年定论》对明代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自南宋以来,濂洛之学由朱熹发扬光大,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明王朝建国之初,科举考试即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及理学家注释的《五经》命题,继而将由朝廷颁布的《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作为士子学习和科举考试的经典,由此,朱子之学盛行。清初理学史家黄宗羲说:
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 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自姚江(王阳明)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1]
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刊出,标志着明代理学发展的巨大转变,从此心学成为学术的主流思潮。袁庆麟自述其为学经历时提及,其早年崇尚朱子之学,正德十三年(1518)夏天见到王阳明,读了《朱子晚年定论》之后,忽然有悟,尽弃旧学。他说:
及读是编,始释然尽投其所业,假馆而受学,盖三月将有闻焉。然后知向之所学朱子中年未定之论,是故三十年而无获。今赖天之灵,始克从事于其所谓定见者,故能三月而若将有闻也。非吾先生(王阳明),几乎已矣!敢以告乎同志,使无若麟之晚而后悔也。[2]
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反映了明代中期许多志于理学之士子已转向于接受阳明之学了。
朱熹晚年治学旨趣的转变是否与阳明之学相合或会通呢?对于这个问题,明末以来学术史家们的意见是肯定的。理学家周汝登说:“夫论以晚定,则前当有未定者存,或先生(朱熹)论而未逮,门人记而未详,遂以失先生之旨。故不当一以定论为准,而摘其语于后。嗟乎!观先生前后诸语,而知先生于道也深矣。”[3]他同意王阳明之说,即假设朱熹晚年悟道之后,来不及改正治学未定之说,或者门人记述之语录有误,遂造成其中年未定之说与晚年之定论相矛盾,而以为朱子之学是一贯与阳明之学相合的。清初理学家孙奇逢说:“文公(朱熹)资学兼到,故晚年有误人之悔,痛自惩艾,此真夫子(孔子)之所谓闻道也。然此一闻也,正从深造之后,方有此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盖其实录耳。必欲以未闻道之先,强合于既闻道之后,徒知尊崇文公,却失文公之心,亦未见其为闻道也。”[4]他强调论朱子之学应以其晚年悔悟而闻道之旨趣为定准,这才是对朱熹的真正的尊崇。黄宗羲说:“阳明子为《朱子晚年定论》虽或有出于早年者,其大意则灼然不失也。一辈学人,胸无黑白,不能贯通朱子之意,但惊怖河汉,执朱子未定之论,不敢信孔孟,并不敢信朱氏,是岂朱子之所欲哉!”[5]他认为朱熹早年与晚年之学大致是相同的,应以晚年之论贯通其全部学说,执着于其早年未定之说则非朱熹本意。
近年来,将朱熹与王阳明学术思想会通是理学史研究的基本倾向。例如认为朱王同宗孔孟,都是承传儒学的大家,他们都旨在研究如何修身,如何成为圣人,所以可以说二学同根,正所谓“千古正学同源”;或从理一分殊来理解朱王之会通,以为由“理一”,故朱王之学即心即理,由“分殊”故朱王之学其性各异,“天理”与“良知”在本体上是会通的;或从进德修业的工夫来认定朱王之会通,以为当朱熹谈“工夫次第”的工夫论时,阳明即批评其“知而不行”,一旦朱熹检讨自己做工夫不得力而反省自责并立志实践时,阳明就觉得朱熹之意与己相同,实际上二者并不是真有什么绝大冲突[6]。
北宋兴起的新儒学着重探讨儒家学说的义理。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等新儒学创始者认为,汉唐的经师和唐代以来的古文家皆非真正的儒者,只有他们自己才发现了儒家之道的秘密,才是儒道的承传者。当时学术界及新儒学家们通称此新儒学为“道学”,故《宋史》特从传统“儒林列传”分出“道学列传”。这一名称很不确切,而且易于与道家之学相混淆,故南宋中期逐渐称其为“理学”,而陆九渊之学与传统的濂洛之学相异而创为“心学”,自此道学析为两派。它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相异趣或是相对立的。南宋中期朱熹与陆九渊于鹅湖之会引起的朱陆之争,明代中期由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引起的朱王之争,在本质上都是理学与心学之争,二者是不可能会通的。
二
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1472—1529)因向朝廷上疏营救被阉党陷害的忠良之臣,触怒皇帝,遭受廷杖,罪谪为贵州龙场(贵州修文县)驿丞。在龙场的三年,他对怎样认识宇宙人生的问题忽然有悟,由此创立自己的学说,史称“龙场悟道”。王阳明自述: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朱熹),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著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力量,因指亭前竹子,命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龙场)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为圣人,人人可做到,便自有担当了。[7]
理学家们的治学目的是使自己成为品德至善的圣人。王阳明悟得的成圣之路不是通过“格物致知”途径,而是不必去认识客观事物的真理,仅由自己的“良知”去感悟,以增进道德修养便可成圣了。关于成圣之路,南宋时朱熹与陆九渊即发生争论:朱熹主张“道问学”,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在龙场时,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请王阳明为贵阳书院主讲,问“朱陆同异”,王阳明未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谈了自己之所悟:“忽然有省曰:朱陆异同,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8]可见,这时又重新提起“朱陆异同”的问题了。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升任南京鸿胪寺卿,宣扬“致良知”之说,薛侃、陆澄、郭庆、徐爱等弟子同聚师门,日夕讲学。这在学术界引起崇尚正统理学—朱子学的理学家的反对与批评,掀起了一场关于怎样重新评价朱子学的争论。王阳明后来回忆说:“留都(南京)时,偶因饶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耳。”[9]当时宗朱子之学的魏校任南京刑部主事,他与王阳明的弟子们争论,他说:“近本《大学》(指王阳明编的《古本大学》),颇窥圣人之枢机,至简至易,说者自生烦难。阳明盖有激者也。故翻禅学为公案,推佛而附于儒,被他说得太快,易耸动人。今为其学者,大抵高抬此心,不在本位,而于义利大界限反多依违。”[10]此争论迅即传到京都,而在浙江隐居的黄绾致书在杭州任的李逊庵云:
近者京师朋友来书,颇说学术同异,乃以王伯安(阳明),魏子才(校)为是非:是伯安者则以子才为谬,是子才者则以伯安为非;若是异物,不可以同。子才,旧于公处见其书,其人可知。伯安,绾不敢阿所好,其学虽云高明而笃实,每以去心疚,变气质为本,精密不杂,殆非世俗谤议所言者,但未有所试而人或未信。……子才素讲于公,学问根本宜无不同。盖皆朋友用功未力,好起争端,添驾为疑,以致有此,诚可叹也。[11]
黄绾请魏校的业师李逊庵出面调停此争议,他们皆倾向赞同阳明学,主张以同倡圣学为重,希望殊途同归。黄绾在这场争论中同朱陆之争时的吕祖谦一样,是调和双方的人物,然而并未使争议平息,实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场论争是围绕着“朱陆之异同”的重新评价而展开的[12]。我们要理解这场争论的实质,就很有必要追溯南宋时“朱陆之异同”的争论。
三
在中国理学史上,朱熹被认为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13]424者,陆九渊的思想在哲学上则是“主观唯心主义”[13]563。他们的认识论相异,治学的方法亦不同。南宋淳熙二年(1175)五月,吕祖谦约朱熹与陆九渊兄弟于江西铅山县的鹅湖寺讲学辨论,引发理学与心学的治学方法之争,为期十日,江浙诸友皆来参会。在相会之前,陆九渊希望其兄陆九龄与其学术观点保持一致,经过讨论之后,陆九龄赞同其弟的观点,作诗一首有云“留情传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转陆沉”。这是对朱熹治学侧重致知穷理的传注训诂的否定与讥讽。在前往鹅湖寺的途中,陆九渊和诗有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认为自己主张主观感悟的途径必将得以发扬,朱熹主张的泛观博览的方法是支离破碎的而必将沉没。吕祖谦在鹅湖寺为调和朱陆之争,问陆氏兄弟近来治学心得,陆氏兄弟即举两诗相示,朱熹一时无言以对,面有惭色。次日,吕祖谦与朱熹提出十余个学术问题,皆为陆九渊所破除,继之辨论亦以陆氏为胜。此后,吕祖谦与朱熹又提出关于《周易》的问题,陆九渊回答之后,总结说:
盖本心既复,谨始克终,曾不少废,以得为常,而至于坚固。私欲日以消磨而为损,天理日以澄莹而为益,虽陟危蹈险,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动。然后于道有得,左右逢其源,始凿井取泉,处处皆足。[14]
吕祖谦与朱熹听讲后甚为佩服。三年之后,朱熹和诗有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自信其治学更为细密谨严,而求新知的义理愈益精深了。他说:
鹅湖之会,渠作诗有云:“易简工夫终久大。”彼所谓“易简”者,苟简容易尔,全看得不仔细。“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之物,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顺之物,顺理而为,无所不能,故曰简。此言造化之理。至于“可久则贤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则贤人之业”,可大者,富有而无疆。易简有几多事在,岂容易苟简之谓乎![15]
指责了陆九渊对“易简”的误解,及其学问之空疏。鹅湖之会,朱熹显然处于劣势,而吕祖谦的调和也失败了。这次争议的主题实为治学应以“尊德性”或“道问学”为宜。陆九渊回忆说:
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观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16]400
所谓“尊德性”,即培植道德修养;“道问学”,即增进学问知识。前者致力于社会道德的实践,后者注重学术的研究:朱陆之异即在于此。陆九渊认为二者是不能合一的。如果说陆氏之学是形而上的,朱氏之学就是形而下的。陆九渊同意弟子们的这种见解,但批评说:“晦翁之学,自谓一贯,但其见道不明,终不足以一贯耳。吾尝与晦翁书云:‘揣量模写之工,似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节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16]419他指出探讨名物度数之类的形而下之学,是朱熹的根本缺陷,这使其不能认识儒家之道。朱熹则认为儒者之进德修业当以穷理致知为先,他说:
物理无穷,故他说得来亦自多端。如读书以讲明道义,则是理存于书;如论古今人物以别是非邪正,则是理存于古今人物;如应接事物而审处其当否,则是理存于应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专,则格物亦非一端而尽。如(程颐)曰:“一物格而万事通,虽颜子亦未至此。但当今日格一件,明日又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处。”此一项尤有意味。[17]391
理学家提倡的穷理是不断探求与穷尽客观事物之真理,而心学家则主张凭主观感悟的认识去主宰万物。鹅湖之会由“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辨论,进而引起了关于“格物致知”的真实涵义的探究。这一辨论在明代中叶由《朱子晚年定论》而再度展开,且更为热烈。
四
明末刘宗周论及阳明之学时,即认为王阳明阐释和发展了陆九渊心学的未尽之意,他说:
象山(陆九渊)直信本心,谓“一心可以了当天下国家”,庶几提纲挈领之见,而犹未知心之所以为心也,故其于穷理一路,姑置第二义;虽常讥朱子之支离,而亦不非朱子之格致,格致自格致耳。惟其学不本于穷理,而骤言本心,是以知有本心,不知有习心,即古人正心洗心皆信不过。窥其意旨,委犯朱子心行路绝,语言道断之讥。文成(王阳明)笃信象山,又于本心之中指出“良知”二字,谓“为千圣滴骨血”,亦既知心之所以为心矣。天下无心外之理,故无心外之知,而其教人惓惓于去人欲存天理,以为致良知之实功,凡以发明象山未尽之意。[18]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心”是主宰个人思想意识的器官,而心学家则以其为宇宙万物之本源。陆九渊说:
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此吾之本心也。[19]
他认为心即是理,可以支配个人的思想言行,同时也提到“良知”和“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但是,刘宗周以为陆九渊忽略了“穷理致知”所以受到朱熹的讥讽,而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发挥并阐释了个人“本心”之义,在理论方面是一种突破与创新。然而王阳明的学说在当时不能为理学家们所接受,故在南京引起一场争论。王阳明为使学术界接受其学说,亦为平息关于朱陆的争论,调和心学与理学的对立,特从朱熹的书简中挑选出三十余件,以证实朱熹在晚年对以前之治学途径有悔悟而与陆九渊之学术观一致了。王阳明于正德十年(1515)作的《朱子晚年定论序》谈到了自己曾学习理学,感到众说茫然;继又学习佛家与道家之学,又感到它们与儒学相违,难以寻求到成圣之路;自龙场悟道之后而识“圣人之道”。他发现自身学说与朱熹之学相矛盾或对立,于是作出“朱子晚年定论”之说:
及官留都(南京)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讹讹人之罪,不可深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政正而未及。而其诸语录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说,犹有大相谬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说,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予既自信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间然。[20]
他认为朱熹影响最大的著述《四书章句集注》和《四书或问》是其中年未成熟之作,而弟子们所记的《朱子语录》亦与朱熹原意有异,因而不足为凭;宋以后的学者们习于朱熹未定之说,遂未注意到其晚年之悔悟。王阳明认为,朱熹悟道之后的见解恰与自己相同。这样,学者们便不致怀疑其说,而可使“圣学”明于天下了。王阳明自信由于《朱子晚年定论》的刊行问世,其学说不致再受怀疑与攻击了,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出其所料。
尚在正德八年(1513),王阳明的弟子王道已怀疑其师之学。他问:什么是善,它原在哪里,现在何处,怎样去明善,与诚身的先后次第如何。王阳明复信说:
纯甫(王道)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堕于空虚也,故假是说以发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纯甫此意,其实不然也。天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吾心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为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21]
这一回复将阳明学的基本观点表述得很清楚,他否定了理、义、善的社会标准,否定了客观事物的存在,认为处理事物完全出于个人主观的“理”便是“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解说,并不能避免空虚之蔽,自然也不会令其弟子王道信服。
批判阳明学最激烈的是罗钦顺,他为弘治五年(1492)进士第一,后任南京国子司业,嘉靖初年拜南京吏部尚书,是正宗的理学家。他对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之言给明代学术界造成的“无穷之祸”给予了严厉的指责,并认为片面讲求“尊德性”,因欠缺“问学工夫”,必致对德性的认识发生偏差。当他读到《朱子晚年定论》,立即致书王阳明,指出几个事实的错误:一,断定朱熹“晚年”以什么为标准;二,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和《四书或问》成书于四十八岁时,以为是其中年未定之作是失之详考;三,录朱熹《答黄直卿》书简中增添“定本”二字无据,朱熹《答吕东莱》书简所言“定本”并非指《论语孟子集注》和《四书或问》。罗钦顺最后说:“凡此三十余条者(朱熹书简),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间然者’,安知不有毫厘之不同者为祟其间,以成牴牾之大隙哉!”[22]王阳明回答说:
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早岁晚岁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23]
他承认在事实上的疏失,表明是不得已而作的委曲调停南京的争论,自有苦衷。关于与朱子学说的牴牾,他坚持认为求“圣道”而表示自己的意见是有益于学术发展的。
嘉靖元年(1522),绍兴学者徐守诚与友人因《朱子晚年定论》涉及到朱熹学术思想“未定”的问题展开争论,又重新提起“朱陆异同”的问题。徐守诚是崇奉朱子学的,他指责王阳明在对待朱陆异同问题时“含糊两解”的态度,似乎朱熹与陆九渊既“尊德性”亦不废“道问学”。徐守诚为朱熹辩解云:“虽其专以‘道问学’为主,未免失于俗学之支离,而其循序渐进,终不背于《大学》之训。若象山之一于‘尊德性’,则虚无寂灭,非复《大学》‘格物致知’之学矣。”王阳明在复函回答说:“夫既曰‘尊德性’,则不可谓堕于禅学之虚空;堕于禅学之虚空,则不可谓之‘尊德性’矣。既曰‘道问学’,则不可谓失于俗学之支离;失于俗学之支离,则不可谓之‘道问学’矣。”[24]2156他仍是以含糊两解的方式,主张不必各执一端,强辩是非,而实际上也回避了争论的本质。关于陆九渊讥讽朱熹治学的“支离”问题,王阳明说:
独其乎日汲汲于训解,虽《韩文》(《韩文考异》、《楚辞》(《楚辞集注》)、《阴符》(《阴符经注解》)、《参同》(《周易参同契考异》)之属,亦必与之注释考辨,而论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虑,恐学者之躐等,而或失之于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无不明,然后有以实之于诚正,而无所谬。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至有敝力终身,若其难而卒无所入而遂议其支离,不知此乃后世学者之弊;而当时晦庵之自为则亦岂至是乎![24]2159
他认为朱熹从事注释考辨是由致知达于诚意正心的境界的,而后世学者一生专致于注释考辨却离正途愈远;所以治学之支离乃是后来某些学者的弊病。这样的辩解有助于平息“朱陆异同”之争,亦有助于贯通朱熹治学“未定”与“晚定”的关系,更可作为其“朱子晚年定论”的理论依据。关于“朱陆异同”,黄宗羲沿袭了王阳明的意见,他说:
道本大公,各求其是,不敢轻易唯诺以随人。此尹氏(尹焞)所谓“有疑于心,辨之弗明弗措”,岂如后世口耳之学不复求心得,而苟妄以自欺,泛然以应人者乎!况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陆九渊)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朱熹)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有先有后。[25]
罗钦顺指出,王阳明所辑朱熹书简中有并非晚年者,王阳明也承认确是如此,但其中大多数是其晚年的书简。朱熹无论在中年还是晚年,在与友人书简中都偶然表示自己努力进德修业的“成圣”过程中工夫做得不够,这方面不如陆九渊等辈。他的“悔悟”,应是在与朋友书信往来中的自谦之辞,并未改变自己治学的途径,也未赞同陆九渊的论学宗旨。绍熙二年(1191)朱熹六十二岁,应属于晚年了,他对弟子们说:
前番不合与林黄中、陆子静(九渊)诸人辨,以为相与诘难,竟无深益。盖刻划太精,颇伤易简,矜持已甚,反涉吝骄,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辟杨墨,也只得恁地辟。他说刻划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说得太分晓,不是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会不得,被众人拥从,又不肯道我不识,又不得不说,说又不识,所以不肯索性开口道这个是甚物事,又只恁鹘突了。[26]
他回顾当年鹅湖之会时,颇为感叹,特以孟子批评杨朱、墨翟的异端之说,比拟其与陆氏兄弟之争。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朱熹力主格物穷理以求致知,陆九渊指责其为“刻划太精”,有伤于“易简”。朱熹则坚持穷理、格物、致知,具体地认识事物之理,因而在晚年犹以为陆九渊论学含糊不清。鹅湖之会后,朱熹仍然致力于传注训释的“支离事业”。庆元二年(1197)朱熹六十七岁时开始修订《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次年,当弟子蔡元定贬谪时,朱熹于贬途相会讨论《参同契》的学术问题;庆元四年,朱熹六十九岁时亲将《书集传》手稿附与弟子蔡沉并口授有关问题嘱令继以完成,此年又完成《韩文考异》十卷;庆元五年,他七十岁时《楚辞集注后语考辨》完稿;次年三月改定《大学》“诚意章”后三日,朱熹去世。这些是朱熹晚年的事实,王阳明未暇考究而匆匆草成《朱子晚年定论》,其所谓“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之说虽然受到许多正宗理学家们的批评与否定,但有助于其“致良知”学的发展,使其学似理学正宗,进而成为明代中期以后的学术思想主流。他认为每个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和思想便是理、义、事,其本质是“善”,知即是行,于是可以不必致知穷理即可成为“圣人”。这是“成圣”的较容易的途径,故其说广为一般学者和士人接受,又经其门徒的发挥,于是出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和“满街都是圣人”的狂怪文化现象。虽然王阳明仍是以“善”为儒家的最高道德伦理标准,亦发扬理学家“兴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但是仅凭个人的良知和自以为的“善”,则会导致人们无视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以天理掩蔽人欲,也会使学术空疏而荒芜。在晚明王学发展至极端时,学术界和统治集团明显地见到其流弊,因而自清初以来统治集团仍然采用程朱理学作为治道的理论,学术界则在批判王学之后转向考据和经世的实学。我们回顾理学史时可见到:陆九渊的心学在朱陆鹅湖之争居于优势,但其学却难延续发展;王阳明以《朱子晚年定论》平息朱陆异同之争,使其说取得胜利,却最终导致整个“道学”—包括理学与心学—的衰微和终结。这一学术思想史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五
理学家们的治学目的是以进德修业而成为道德高尚完美的圣人。理学的创始者程颐说:
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异同者是也。是二者皆无益于身,君子弗学。[27]319
他认为“圣人之学”是注重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这是为学的根本,因而古文家以文为主、学者以训释考据为主是为向外的舍本逐末。然而理学家是提倡“致知”的,他们努力学习儒家经典,特别是从《论语》《孟子》《大学》与《中庸》经典中去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而对儒学的义理更是通过精微细密的思辨去艰苦地探讨。程颐认为,如果对儒家义理缺乏真正的认识,遇到异端邪说便难以辨别是非与选择,从而偏离正途。他说: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不识道以知之,则有异端者出,彼将流宕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恶,外不知是非,虽有尾生之信,曾参之孝,吾弗贵矣。”[27]320
由此可见,这与心学家的“成圣”途径是不相同的。朱熹被誉为理学正宗濂洛之学的集大成者,但在众多理学家中是极特殊的,即他既是道学家,更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在本质上是道学家,以“尊德性”为归依。他是受北宋考据学影响,主张泛观博览和采用实证方法治学而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学者。朱熹在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所以王阳明有“未定”与“晚年定论”之说。
关于儒学义理的探讨,理学家们是非常认真的,而且用功极深,力求“穷理致知”。怎样理解《大学》所谓“致知在格物”呢?程颐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己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27]361朱熹发挥程颐之说,以为:“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致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故其精处无不到也。”[28]4此解甚为确切。他还补充说:
格物致知,彼我相对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得一分;于物之理穷得二分,即我之知亦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甚多,则我之知愈广。其实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所以《大学》说“致知在格物”,又不说“欲致其知者在格其物”。盖致知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另有致处也。[17]399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逐渐积累而予以类推便可丰富个人的理性认识,从而获得真知。致知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通过观察实验,反复研究而认识某一事物的性质与规律;一是由泛观博览进行形而上的理论的分析与思辨。由客观的实证考察所得的认识,加以综合、分析、归纳,再通过学理的探讨、反复的思辨、反复的理性推求,这应是合理的方法论。王阳明在龙场试以静观默想去格物,以致数日之后疲劳成病,忽悟得仅凭个人的主观意志来理解事物,使万物皆备于我,从而否定了格物致知在认识过程的意义。理学家虽然努力“成圣”时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操,但他们格物致知是偏重于探求儒学的义理,因各个理学家对义理的探求务求达于精微的极致,故出现“理一分殊”的学术现象,从而推动了理学的前进。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是极为深入细致的,孜孜不倦地以思辨的方式探求义理。他们对儒家经典的阅读是仅凭自己对文献的含义的理解,并不考虑文字句意与篇章的确切训释解诂。这样所得的对义理的认识在学理上往往经不住验证,可能是主观的片面的认识。朱熹“道问学”是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传注训释以进求义理,尤其注重实证的方法。理学家最看重的经典是《大学》,其中引用了许多诗句,他们并不详究其文献出处,而朱熹则在《大学章句》中进行了详注和训释,例如: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商颂·玄鸟》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诗·文王》之篇。穆穆,深远之意。于,叹美辞。缉,继续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澳,于六反。菉《诗》作绿。猗,叶韵音阿。僴,下版反。喧,《诗》作咺;諠,《诗》作谖;并况晚反。《诗·卫风·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兴也。斐,文貌。切以刀锯,琢以椎凿,皆裁物使成形质也。磋以鑢钖,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泽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之。治玉者,既琢而复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绪,而益至其精也。瑟,严密之貌。僴,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忌也。[28]5-6
如果对《诗经》的这些文义无确切了解,便很难了解所引用之文的意义了。朱熹说:
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指,相穿组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29]
他的训释解诂皆是有依据的,于治学强调“无徵不信”。例如孔子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朱注:“徵,证也。宋,殷之后。三代之礼,孔子皆尝学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礼既不可考证,殷礼虽存,又非当世之法,惟周礼乃时王之制,今日所用。”[28]36这里提出对文献的考证的必要。《中庸》第二十九章云:“王天下有三重焉(议礼、制度、考文),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朱注:“上焉者,谓时王以前,如夏商之礼虽善,而皆不可考。”[28]37无徵不信,即没有证据的皆不可信。近世学者梁启超总结清代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时说:“其治学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徵不信’。”[30]4他认为这已同于近代的科学方法。
关于儒家经典的注释,朱熹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孝经刊误》等,并编辑理学家著述和语录以及史学资料,此外还有《阴符经考异》《周易参同契注》《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著。其弟子蔡元定著有《律吕新书》《洪范解》,张洽著有《春秋集注》,叶味道著有《祭法郊社外传》,蔡沉著有《书集传》,陈淳著有《北溪字义》。朱熹及其弟子的这些著述,即是陆九渊等心学家讥讽的“支离事业”。然而其中有关儒家经典的传注却是学术名著,大大超越了狭义的理学意义,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故广为流传,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即使在理学史终结之后仍有其学术生命。
现在回顾《朱子晚年定论》引起的理学与心学的争论,可以认为朱熹与陆九渊、王阳明于儒家的“圣人之学”,皆坚持“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皆主张“兴天理,灭人欲”,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朱熹注重“尊德性”,而更致于“道问学”的“穷理格物”的学术追求,尤其采用实证方法以求真知;陆九渊与王阳明则专注“尊德性”而轻视或否定“道问学”,采用主观感悟的思辨方法,排斥纯学术的传注训释,走向空疏狂妄的“成圣之路”:这是他们治学的相异之处。朱熹之学不存在中年未定与晚年悟道的矛盾,他是通过“道问学”而达于“尊德性”的,故无疑在理学家中思想与学术皆是取得最高和最大成就的。现代理学史家们认为:
在程朱理学派中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其学术成就趋过程颐。在整个理学史中,朱熹的地位也非陆九渊、王守仁(阳明)所可比拟。尽管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学派不同,程、朱与陆、王不好相比,但他们同讲天理,同论本心,在整个理学史中,论成就与影响,不得不以朱熹为首。[13]429这应是对朱熹在理学史上地位的定论。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于事实与学理皆不能成立,而“朱王会通”之说则更是极勉强牵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