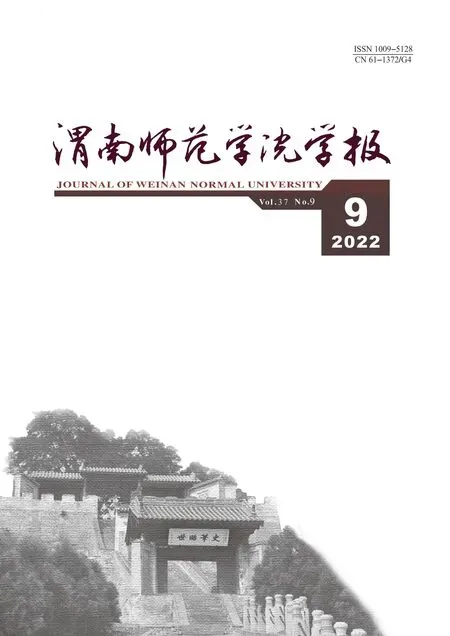《史记》篇章人物指称与社会性直指
王 娜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100872)
古汉语人物指称涉及的是人物称谓,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古代某一个具体称谓的研究。而本文所涉及的《史记》篇章人物指称并不讨论某一具体称谓的使用,具体来说主要是从篇章角度分析司马迁在指称同一个人物时是如何选用不同称谓的。
篇章在生成过程中需要重提上文中出现过的实体,这种现象被称为回指(anaphora)。回指是篇章语言现象,篇章语言现象是在语言使用时跨越篇章结构而产生的。《现代语言学词典》中“回指”的定义是语法描写中用来指一个语言单位从先前某个已表达的单位或意义(先行语)得出自身释义的过程或结果……是标明正在表达的和已经表达的两者所指相同的一种方式。[1]19陈平指出回指是话语中提到某个事物之后,再要论及该事物时,一般使用各种回指形式,同上文取得联系。[2]他根据回指语的形式将汉语中的回指分为三类:零形回指(Zero Anaphora)、代词回指(Pronominal Anaphora)、名词回指(Nominal Anaphora)。具体来说,零形回指是指语言表达中再次提及上文中的指称实体时,选用零形式指称,即文字符号和语音形式都不存在的指称。代词回指是指语言表达中再次提及上文中的指称实体时,使用代词进行指称。名词回指是指语言表达中再次提及上文中的指称实体时,使用名词进行指称。结合三种回指形式的定义,可以发现,零形回指没有可见的词汇形式,这明显不同于有明确词汇形式的代词回指和名词回指。
多数情况下,篇章在指称同一个实体时,并不是只运用其中一种指称形式,而是三种指称形式交替使用。具体到篇章回指中,随着篇章叙事的展开,当重提某一个篇章实体时,需要考虑选用何种回指形式。篇章中最终选择哪种回指形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回指的词汇形式来看,零形回指是无形的,代词和名词是有形的。徐赳赳等认为零形式在词汇上是无表现的,代词在词汇上是可以穷尽的,而名词回指在词汇上是最多变的,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3]由于其立论的依据是现代汉语,所以有些内容并不符合古汉语语言的事实。古汉语中零形式在词汇上也是无表现的,代词在词汇上是非常有限的,代词回指中主要是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名词回指在词汇上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本文篇章人物指称主要关注的是名词回指,即同一个人物,后文在回指的时候选用哪种名词形式。名词回指属于高信息量词汇,信息量表现为词汇形式。名词回指的词汇形式长信息量最多,同时名词的不同形式可以提供新的信息。名词回指直接使用人物的姓名、官职等名词来指称人物。几乎不需要借助其他信息就可以达到语义内容上的理解。所以名词回指的作用不仅在于回指,还可以提供新信息。
篇章回指形式的选用实际上是寻求将发话者的注意视角与语言形式的选择以及篇章结构相匹配的过程。选择某一回指形式来回指篇章实体就是为了将发话者的意图与注意中心相对应。发话者的意图和信息量相关。发话者认为有必要提供更多的信息,就会选用名词回指。名词形式是语篇意图在话语表层的反映。
本文考察对象选取《史记》篇章中的实体“高祖”,以篇章语段为基本单元,追踪《高祖本纪》在回指“高祖”时如何选用不同指称。文本使用中华书局2014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根据我们的统计,《高祖本纪》中“高祖”共有46个回指链(1)回指链(anaphora chain)指篇章中的一个实体被引入篇章,后文重提时使用零形回指、代词回指、名词回指,这些用来指称同一个篇章实体的所有回指形成的链条。。在分析回指链中的回指形式时,我们看到回指链中选用不同的名词回指来指称同一个实体高祖。其中名词回指有诸多实现形式,不同指称在文章中出现的顺序依次是:高祖、刘季、沛公、汉王、皇帝、上。既然一个实体有多个称谓,那么名词回指中这些称谓是如何选用的呢?
一、《高祖本纪》“高祖”称谓考察
《高祖本纪》中用“高祖、刘季、沛公、汉王、皇帝、上”来指称刘邦,名词回指内部不同长度的词汇形式提供不同的信息量。刘大为认为在一个话语片段中,发话者可能认为某一个语篇实体是受话者所不了解的,需要补充必要的背景或相关知识,也可能认为该实体表达的信息不够充分或不太完善,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或提供更多的细节,这种在话语片段中对信息进行精细加工的意图,就是信息的精致(elaboration)意图。[4]篇章名词回指中不同名词形式体现了信息的精致加工。
从篇章整体来看,《高祖本纪》中用来指称高祖的不同称谓的选用有其内在规律。我们对不同称谓逐一分析。
高祖
《高祖本纪》中“高祖”第一次出现时,用名词“高祖”将指称对象引入篇章,“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接下来的语段在叙事过程中,名词回指选用的都是“高祖”。使用“高祖”时出现了1次例外,选用的是“刘季”。
刘季
文章从“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开始使用“刘季”来指称高祖。篇章中称谓使用很严格,名词回指中选用的都是“刘季”。从篇章角度来看,称谓发生变化是因为段首有时间状语“秦二世元年秋”,表明前后叙事层级发生变化。同时相比于前面几个语段,这个语段中“刘季”不是语段主题,语段主题是“陈胜”和“沛令”。选用“刘季”受到语段中其他实体的影响,因为在限定的时间内从“陈胜、沛令”与“高祖”的关系来说,只能选用“刘季”,而不能选用“高祖”。这是称谓“高祖”向“刘季”转变的主要原因。
沛公
篇章叙事中有“乃立季为沛公”,刘邦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所以开始用新的身份“沛公”来指称他。这部分称谓使用也很严格,只使用“沛公”。
汉王
篇章叙事中“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更立沛公为汉王”,也是因为刘邦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开始使用“汉王”来指称。
皇帝
上面提到使用“汉王”称谓时,回指链中名词回指已经使用“皇帝”来指称“汉王”,但是到这个地方才说明使用“皇帝”的原因:“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也就是高祖被尊为皇帝之前已经开始使用“皇帝”来指称高祖。
上
按照指称选用顺序,在“黄帝”之后选用“上”来指称“刘邦”。
根据以上刘邦不同称谓的选用情况,司马迁指称刘邦时对不同称谓的选用很严格。往往是根据刘邦身份地位的变化,指称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语言学方面考虑,这种现象是event-related,即实体的职位官职名称往往会和特定事件、情境联系在一起。文章中“沛公”“汉王”“皇帝”这三个称谓的使用都有明确的语境“立季为沛公”“立沛公为汉王”“尊汉王为皇帝”。这些不同的称谓第一次出现时属于“情景语境”。
高祖的不同称谓在所出现的语段中使用比较严格,具体表现为当开始选用某一个称谓后,语段内部名词回指都选用这一个称谓,不会选用其他称谓。无论是前面已经使用过的,还是后文中即将出现的称谓,直到“情景语境”中出现新的称谓。但是在《高祖本纪》中也出现了例外。
高祖、刘季
篇章在一开始使用“高祖”时,出现了1次“刘季”。出现“刘季”的语段回指链中名词回指为:高祖—高祖—高祖—高祖—刘季。刘季出现之前全部使用的是名词“高祖”。
汉王、高祖、皇帝
篇章在选用“汉王”指称时,“汉王”的使用并不像前面几个称谓那么严格。中间有一段同时出现了“高祖”“皇帝”“汉王”,但这一部分语段在其他地方选用的都是“汉王”,语段内容如下: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5]477
高祖、上
篇章在选用称谓“上”时,也使用了“高祖”。“上”和“高祖”交替使用。
针对上边例外选用“刘季”,梁玉绳《史记志疑》“卒与刘季”条:“案:史称‘刘季’凡十一,此称在当时人则可,迁数呼之可乎?且忽曰高祖,忽曰刘季,于例亦杂也,此等处《汉书》为密。”[6]214梁玉绳已经注意到了此处选用“刘季”,与篇章体例不符,同时提出《汉书》的使用更为严密。
针对上边例外“高祖、皇帝、汉王”混同并用,梁玉绳《史记志疑》对此例中的人物称谓也有质疑,认为:续古今考云:太史公岂信笔乎?韩信是时为齐王书曰“淮阴侯”,汉王未为皇帝书曰“皇帝”。追书人臣即从轻,人主则从重乎?董份云“至下方尊皇帝,则不宜即着此二字”。余谓“高祖”二字亦错出,皆当作“汉王”。“淮阴侯”当作“齐王信”。又是时周勃为将军,其封绛侯在六年,何以不与柴武称将军而书曰绛侯耶?孔将军、费将军即功臣表蓼侯、费侯也。陈贺封费亦在六年,乃不曰陈将军而曰费将军,非但与孔将军之称姓异,抑且古无以国冠官而称之者。至《西京杂记》谓孔、费二将军皆为假名,恐不可信。[7]228梁玉绳不仅对刘邦的称谓质疑,也对“韩信”“绛侯”“费将军”的称谓有质疑。主要原因是刘邦此时“未为皇帝”,所以不应该用“皇帝”来指称,也不应该使用“高祖”。按照篇章中“刘邦”称谓使用的整体情况,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的“皇帝”和“高祖”都应该选用“汉王”。这样才能保持篇章内部称谓的一致性和纯粹性。
二、《史记》与《汉书》人物称谓选用比较
上文提到梁玉绳在讨论例外时提到此处“《汉书》为密”,我们将《汉书·高帝纪》和《高祖本纪》中刘邦的称谓进行比较。《汉书·高帝纪》中刘邦的称谓按照出现的顺序为:高祖(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沛公(高祖乃立为沛公)、汉王(更立沛公为汉王)、帝(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上。以上称谓从“帝”开始,“帝”和“上”“高祖”混合使用,《高祖本纪》中例外也是这种情况。但是三者的使用次数不同,“帝”仅使用了3次,“高祖”2次,“上”71次。其中“上”用于高祖和大臣的对话中,“上曰”用例较多,共21次,主要是为了在对话中表明说话人的身份,体现人物之间的身份差异。
从两个文本称谓使用的整体情况来看,《汉书·高帝纪》和《高祖本纪》中称谓的选用顺序高度一致,都是“高祖、沛公、汉王、皇帝、上”。但是《汉书·高帝纪》中刘邦称谓的使用较《高祖本纪》更为严格,主要体现在例外《高祖本纪》中和“高祖”一起出现的“卒与刘季”。《汉书·高帝纪》为“卒与高祖”,此处《汉书》在称谓上更加严密。例外《高祖本纪》“高祖、皇帝、汉王”同时并用的语段,《汉书·高帝纪》中没有相同的内容。查检文献,只有《太平御览·机略二》中引用了相似段落,但是引文中“刘邦”的称谓一律为“汉王”,具体内容如下:
又曰:汉王与诸侯兵共击项羽,决胜垓下。韩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汉王在后。绛侯、柴将军在汉王后。项羽之卒可十万。韩信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退。信复乘之,大败垓下。[7]1313-1314
《太平御览·机略二》全部选用“汉王”和我们的观点一致,但是《汉书·高帝纪》中没有相对应的内容。从《汉书·高帝纪》称谓使用的情况来看,如果《汉书·高帝纪》有这段内容的话,指称刘邦时可能选用的也都是“汉王”。否则这段材料是否为《史记》原文的可靠性就有问题。
按《太平御览》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史记》最早的刻本完成于公元997年,所以《太平御览》所引《史记》很大程度出自宋以前的写本。考虑到同一经典文本的不同版本在不同时期会产生大量的异文,我们无法回避《史记》文本书写、内容等问题。《史记》版本之间文字内容上存在差异,不同版本之间校订窜改也会造成文字上的讹误。所以有必要考察《史记》的不同版本对其中的人物称谓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循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我们参校北宋景祐年间刊本(简称“景祐本”),宋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简称“川郡斋本”),宋乾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简称“蔡梦弼”),蒙古正统二年段子成刻明修本(简称“段子成本”),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刻本(简称“崇道本”),明崇祯汲古阁刊《史记索隐》本(简称“单索隐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三家注合刻本(简称“殿本”),清同治五年金陵书局刊本(简称“金陵书局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史记·高祖本纪》旧抄本(简称“宫内厅本”)等,发现以上无论是唐写本还是宋代及宋代以后的刻本,《史记·高祖本纪》都有与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高祖本纪》“高祖、皇帝、汉王”同时并用的语段,说明唐人看到的《史记》就有这段话。故笔者大胆推测“高祖、皇帝、汉王”不同称谓,同时并用的语段应当是司马迁的原文无误,只是后来只有《太平御览》引用,其他类书和史书等文献则不曾引用。
通过比较《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两个文本中刘邦的称谓,《汉书·高帝纪》中的使用内部更为统一。为了进一步说明篇章实体称谓选用的内在规律性,我们对“项羽”“韩信”的称谓也进行讨论。
有关项羽的称谓。《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的称谓依次是项籍、籍—项羽—项王。从鸿门宴开始选用“项王”,但篇章中选用“项王”时,并没有项羽获得这个身份的语言信息。《史记·高祖本纪》中“项羽”和“项王”混同使用,没有明确的选用标准。《汉书·陈胜项籍传》中主要使用到的称谓是“羽”和“籍”,“项王”只出现了3次,2次在对话中,1次是在叙事中。而且也没有说明封为项王的时间,称谓“项王”似是突然之间出现。
有关韩信的称谓。《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称谓出现的顺序是:韩信、信—齐王信—楚王信—淮阴侯,其中“韩信”和“信”贯穿整个篇章,在使用“齐王信、楚王信、淮阴侯”的语段中同时使用“信”以指称“韩信”。但是“齐王信、楚王信、淮阴侯”这些称谓的使用非常严格,都是在韩信拥有了相应的社会身份以后才开始使用的。具体为: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韩信请求立自己为假王。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齐王信)
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楚王信)
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淮阴侯)
《史记·高祖本纪》中韩信称谓为:韩信—淮阴侯—齐王信—楚王。《高祖本纪》中韩信的称谓也出现了例外,封为淮阴侯时间是汉六年,齐王信是在汉四年,也就是其还不是淮阴侯时,已经使用淮阴侯来指称了。《汉书·淮阴侯列传》全部使用的都是“韩信”和“信”,即使是拥有了齐王、楚王、淮阴侯这样的社会身份地位,指称中也没有选用。可见,在指称“韩信”的称谓中,两个文本的处理方式不同。《史记》更加注重对不同称谓的选用,但未能保证称谓内部的统一性。《汉书》的处理则比较极端,没有选用韩信的社会身份指称,单纯选用“韩信”和“信”,似乎是为了确保篇章整体称谓的一致性。
比较刘邦、项羽、韩信不同称谓的选用情况可以看出,刘邦和韩信称谓选用比较严格,项羽的称谓比较混乱。两个文本相比较,《史记》人物称谓的选用相对有规律,但常出现例外的情况。《汉书》中人物称谓内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有时为了追求一致性,仅仅选用个别称谓,而对于社会称谓弃之不用。从名词回指的角度来看,《汉书》中这些个别称谓选用的是人物称谓中最节省的名词形式,主要是人物的名和字,如“籍、羽、信”,所以称谓中的姓氏称谓使用更加普遍和稳定。
《汉书》文本中人物称谓的处理比较刻意,规范化痕迹明显,《史记》称谓的选用则显得相对随意一点。通过观察人物称谓的选用,可以看到从《史记》到《汉书》文本内部语言形式的处理方式。
三、篇章人物指称与社会性直指
根据以上分析,似乎可以认为古汉语篇章中人物称谓选用存在一定的模式,模式中称谓内部存在从一个称谓到另外一个称谓变化的过程。《史记》中不同实体的称谓是“情景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也是称谓变化的原因。从语言学的角度,同一个实体选用不同的称谓和社会性直指有关。称呼语和社会性直指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称呼语关乎说话人和被称呼方之间的社会性参照关系。社会性参照关系表现为人物称谓选用中的社会指称。
篇章人物指称选用存在从情景指称向社会指称的转换。刘邦称谓中的“沛公、汉王、皇帝”,项羽称谓中的“项王”,韩信称谓中的“齐王信、楚王信、淮阴侯”,这些表示社会身份的称谓第一次出现为情景指称,是情景语境影响的结果。篇章后文再次使用这些称谓来指称实体时,指称形式是相对的社会关系,而不再是情境关系,这些称谓称为“社会指称”。
情景指称依赖于篇章语境,所以情景指称是短暂的、突发的指称。以上三个实体的指称选用中都有所体现,《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齐王信”使用了4次,“楚王信”1次,“淮阴侯”1次,这些情景指称出现以后很快又继续使用“信”来指称。《汉书·陈胜项籍传》“项王”出现以后,叙事语段中只选用了1次,然后指称又回到选用“羽”和“籍”。可见这些情景指称的使用比较短暂。
社会指称是稳定的、持久的社会关系,不依赖于上下文语境,是一种社会直指。社会指称不是一个单纯的指称性代词,而是包含了社会性和指称性融合的直指语。当刘邦的称谓“沛公、汉王、皇帝”,项羽的称谓“项王”,韩信称谓“齐王信、楚王信、淮阴侯”这些指称再次出现时就从短暂的情景转换为稳定的社会关系。
从情景指称和社会指称来看《高祖本纪》中的例外,“高祖、皇帝、汉王”并用确实不符合指称选用模式。因为按照《史记》实体称谓选用的体例,先有情景指称,再有社会指称,此时刘邦还没有皇帝的身份,所以就不能选用“皇帝”来指称。其中“高祖”已经从情景指称转化为社会指称,所以这个地方选用“高祖”勉强还可以解释。但是严格按照称谓使用的纯粹性,“高祖”也应该是“汉王”。选用哪种人物称谓不仅是描写客观世界中的实体,还体现了自然语言中的主观因素、意向因素。具体为什么《史记·高祖本纪》中会出现“高祖”“皇帝”“汉王”并用的情况,很可能是作者司马迁主观因素的表现,目的在于体现人物之间的尊卑,同时表达对所指称人物的尊敬。人物称谓的社会性直指体现了更普遍的语言特征,同时又具有复杂性。“高祖”“皇帝”“汉王”都是直接指称,选用哪种称谓,围绕作者的视角展开。作者参引上下文语境因素,主要是事件发生的直示情境,涉及的是非语言因素。称谓选用属于语义解释,语义解释过程中必须能够在至少两种参数下评估表达式,即语境参数和时间算子所必需的时间参数。由此得知,在称谓选用评估过程中,我们就需要从这些方面入手。从语境参数和时间参数来看,“高祖”在上文中已经出现过,可以继续使用。此时刘邦并非皇帝,使用“皇帝”显然是为了表达对刘邦的尊敬,“皇帝”和周围人物“孔将军、费将军、绛侯、柴将军”社会身份尊卑之间进行区分。由于《汉书》中没有这段材料,所以我们暂时也只能对此作出上述解释。
《高祖本纪》中的例外,也可以用社会指称来进行解释。指称形式“高祖”中出现了1次“刘季”,上文虽然没有出现“刘季”,但是篇章首句“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说明“刘季”和“高祖”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固有的关系。至于为什么“刘季”出现在“高祖”中,破坏到了指称选用的模式,从语段整体来看,可能是受到同一语段对话内容中称谓的影响。相同语段中萧何、吕公、吕媪在对话中都称“刘邦”为“刘季”,从人物之间的社会身份来看,这满足语境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叙事部分使用的都是“高祖”,却同时出现了“刘季”。这说明人物称谓的选用除了“社会指称”的影响外,篇章中叙事部分的指称可能会受到对话内容的作用而变化。所以篇章中人物指称选用模式会根据不同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整。
指称语的选用体现了语言编码的社会维度。《史记》篇章叙事中用一个人的职业、官职、封号等信息来指称实体,而不是第三人称代词,是属于敬语(honorific)范畴。因为这些职位类名词赋予了被称方的荣誉,荣誉可以强化其社会性价值。任何涉及honorific的形式一般都有避开使用无标记第三人称代词的倾向。古代社会体系中比较注重人物的社会身份,所以有用社会关系来指称实体的传统。任何一种语言中群体社会关系都是典型的关系。所以称谓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司马迁选用“高祖”和“上”就表示相对级别和尊敬。指称选用依赖于叙述者和描写对象两者之间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司马迁选用“高祖”是因为考虑自身的社会身份,以及“高祖”已经去世了的事实。选用“上”就是尊称。语言使用的许多方面都与社会直指有关,依赖于社会关系。
四、结语
称谓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物社会身份地位的变化。本文认为对不同称谓的指示性解释可用以说明称谓选用的内部原因。我们主要是为了说明下面几个内容:一是《史记·高祖本纪》篇章中“刘邦”的称谓选用形成了统一模式,可以将这种统一模式概括总结为:一个实体有不同的称谓,篇章中可以选用不同的称谓来指称这个实体。但是在选定了某个具体的称谓后,语段中称谓的使用就很单纯,往往只选用这一个称谓,不会多个称谓混杂使用。出现例外主要表现为,上文中出现的称谓转化成了社会指称再次出现在后文语段中,这种例外可以接受。还有一种称谓是情景指称,情景指称只有在语境建立后才可以使用,当情景指称未建立而出现在上文中时这种指称是不符合《史记》篇章称谓选用体例的。二是篇章中实体的称谓如果是从情景指称转换为社会指称而来,这种称谓的选用没有人称姓氏称谓稳定。即便是社会指称获得了稳定性,再次出现时已经不依赖篇章语境。但是这种称谓的使用频率不高,篇章叙事中重提实体时还是会大量选择稳定性更高的姓氏称谓。姓氏一般在表现形式上是比较固定的,也有比较稳定的时间性,可供发话者经常调用。
——以《红楼梦》译本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