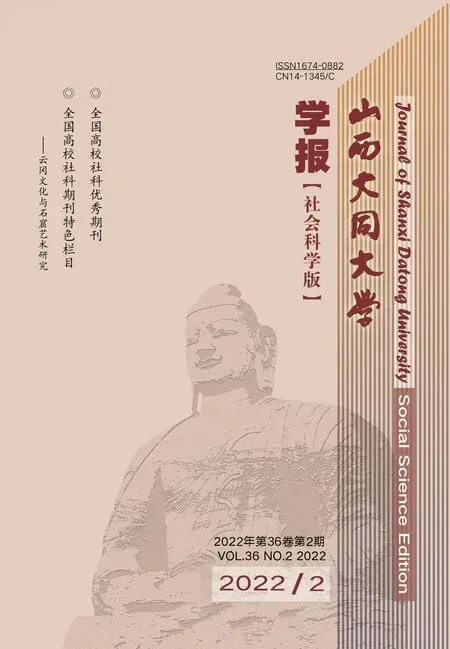文学地理学视野下“人”的生存困境
杨 虹,彭栓红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邹建军指出:“文学地理学提倡从空间的角度特别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研究文学,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法和手段,体现了自己独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文学地理学将人物与景观、实物、事件共同作为构成文学作品地理空间的显性要素。其中,人物要素是“情感和思想的载体与触媒。”[2](P152)文学地理学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关注具体的人与景观直接相互作用,捕捉个人生活之中的文化细节。一个文学作品的空间营造离不开人,必须要以人为中心,人具有主体意义。同时,人具有普遍的共性特征,同时,因为时代、性别、民族、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又呈现出个体差异。一方面,不同的地域环境塑造不一样的地域性格,会表现在体质、气质、价值观和生活习性等方面。另一方面,人的思想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所在的地理空间。从文学地理学视野来审视王祥夫小说,就会发现王祥夫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空间意识,体现为乡土空间、城市空间和仪式空间。通过不同空间下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景的设置,王祥夫小说揭示出人的生存焦虑和困惑,展现出作家对乡村人物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一、农村乡土空间对人物的束缚
“乡土性”是中国社会基层的集中特点。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3](P4)文学中的乡土空间,往往与农村、农业、土地相关联。土地是赖以生存的空间,农业是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是乡土空间内的主角。在王祥夫的小说当中,刻画了大量存在于乡土空间中的人物。展现了农民真实的生活状态。随着时代变迁,乡土空间在发生变化。面对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乡土空间中的人物徘徊在进步与落后之间,乡土这一传统空间,对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王祥夫小说就阐释了这类因乡土空间的束缚所导致的人物命运的变化和生存的困境。
(一)农村权力下人的生存焦虑 在乡村,地方干部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对农民发展造成阻挠,使得农民陷入人为设置的困境而命运多舛。例如《愤怒的苹果》中,亮气承包果园经营渐好,引发为了一己私利的王红旗书记的阻挠,进而造成系列矛盾。王红旗试图以自己的权力压榨果园的收益,从无视果园的承包合同,干预果园的种植,到靠打白条获取苹果谋私利等情节,一步步将脚踏实地经营果园的亮气逼到绝境。故事最后,正值中秋时节,村里闻不到月饼的香气,反而是亮气果园苹果腐烂的臭气“排山倒海地播散到村子里来,把村子盖住,遮得严严实实。”[4](P312)遮蔽农村这一乡土空间的表面是苹果腐烂的臭气,深层的是村书记王红旗的权力压迫,使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他的权势之下。农村权力滥用,普通村民的不觉悟,亮气生产变革遇到的强大阻力,发人深省。小说中亮气的果园是一个更为具体的乡土空间,本质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但这个独特的果园空间也是作家构建的审美空间,承载了一种农村变革的思想,由传统粮食作物经济,变为一种果园经济。亮气对土地的经营模式,从传统的农耕生活走向承包果园。然而勇于探索的勇气为乡土农村空间内书记思想的狭隘、自私的“小农”意识和传统的权力思想所束缚,始终无法逃脱村书记个人私利的压榨。王祥夫将人物矛盾限定在乡村这一地理空间,限定在亮起承包的个体果园这一典型空间中,将村书记狭隘、偏激、独断专权的权力思想与农民积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置于乡土空间之中,将这场较量表达的淋漓精致。
同样,在《腊月谣》也涉及农村权力与村民认知程度的矛盾问题。麻子玉乡政府财政发生问题,工人发不了工资只能向开煤窑的冯敢死借款。冯敢死利用这一点,试图把给妻子张粉菊入党作为借款条件与乡政府进行交易,政府财政发生困难不得不向个人借钱的举措。但是在小说最后,乡政府并没有对冯敢死做出妥协,在乡村这一独特的空间内,村民的小农意识、自私特点,在冯敢死利用借款一事谋求妻子张粉菊入党上突显出来。入党如此庄重的事情,在冯敢死眼里都成了交易。乡土空间对于村民群体本身存在一定的制约性,王祥夫曾说:“多会儿,我北方的农民兄弟才能在北方的黄土地上表现出他们超越社会制约的光芒四射的生命情致。”[5]这正是王祥夫在他的众多小说里塑造乡土空间与人物冲突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这一乡土空间内村民思想、生产经营方式也发生深刻的变革,如农村中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也有工业发展,也有承包制等,但乡土空间的新变革与传统的小农思想、农村权力的冲突造成人物发展的束缚,也是阻碍了农村良性发展,这是中国乡土农村可能遇到的共性问题。
(二)家庭伦理下的人物生存焦虑 王祥夫对乡村以及村民的亲切与熟悉,令其作品始终能原生态的真实书写。乡土空间之下的家庭生活,常常受传统伦理、封建道德束缚,不仅仅背负家庭压力,而且也有乡村社会的邻里压力。比如《怀孕》,主人公小柔因为婚后一直未怀孕,为了避免再遭受邻居的非议,她想到假装怀孕的主意。经过一系列伪装、演戏,在避免露出马脚的过程里,小柔却在这场谎言里怀孕。小说将故事设置在乡土空间,“怀孕”这件事从私密的个人之事变成了邻里间的众人皆知的新闻事。小柔原本充满爱与温馨的家庭生活,由于背负传宗接代的封建伦理压力,才不得不有了假怀孕的闹剧。黑格尔曾谈到:“作为主体,人固然是从这外在的客观存在分离开来而独立自在。但是纵然在这种自己与自己的主体的统一中,人还是要和外在世界发生关系。人要有现实客观存在,就必须有一个周围的世界,正如神像不能没有一座庙宇来安顿一样。”[6](P209)身在农村,人无法摆脱乡土空间而独立存在,必然受农村思想文化影响。这种乡土空间下客观存在的对人的传宗接代的伦理要求、伦理约束造成人物不能违背传统的纲常。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才有假怀孕的荒诞行为,导致正常的人物生活变得不正常,他们无法拥有真正自由的幸福。
乡土空间不仅存在乡村家庭伦理、社会舆论的束缚,而且乡村的传统思想已经融入到个体生命中,成为对自身行为的一种约束。《上边》讲述了农民刘子瑞夫妇住在一个叫“上边”的废弃村庄,当村子里的人都搬到“下边”去住的时候,他们依然守着“上边”的生活。下边人由于生活空间的转变,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刘子瑞的女人依然围绕着牲口棚晒玉米、喂驴喂鸡喂狗,烧火做饭,日子一成不变,毫无波澜。刘子瑞夫妇的儿子从省城归来,他试图在短期内改变上边的生活状况,于是修理房屋,重整院落,这既是一种孝道,伦理要求,也是自我的家庭责任,但是他终究还是会回到省城去。“上边”的生活对儿子来说是短暂的停歇,他将“下边”的生活带到“上边”,却又无法让两种生活真正相融。“上边”既是一个村庄的名字,一个自然地理空间,又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已经衰败的、闭塞的地方文化空间,和“下边”的开放的、变化的、丰富的文化空间构成截然不同的地理空间。刘子瑞夫妇守着旧生活,守着传统,不愿改变自身生活,体现出了乡土空间“人”的自我约束,思想上的保守反映到日常的行为当中,始终保持日复一日的重复性生活。这种恋乡守旧的特质,让他们始终无法放下村子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对这片土地的记忆,这也成为束缚他们走向“下边”的根源。
二、城市空间对人物的压迫
城市空间与农村乡土空间相比较,代表着更开放的思想,更优越的生活方式。王祥夫在他的小说世界里,讲述城市人物故事,常结合特定城市空间描写,塑造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王祥夫善于捕捉人物细节,展现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城市空间人物群像,以此表达在城市空间下“人”的压迫。
(一)务工者的变与不变 王祥夫笔下的务工者,大多是农村涌入城市的人,这部分人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都存在原有生活方式的调整和思想的变化。他们的变与不变既存在客观因素,又存在主观因素。客观上来说,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使得务工者面临在城市空间下的生活选择。主观上来说,是务工者对城市生活的接受心态和接受能力不同,从而导致他们的生活产生变与不变。一部分务工者是主动放弃农村生活,试图在城市中寻求自我多样的发展而大量涌入城市,这种改变是积极的、乐观的,带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迈入新的生活环境。另一部分是由于经济发展,农村生活发生改变而被迫放弃原有的耕地,放弃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得不接受城市所带来的新变化。这种被迫的改变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改变,被迫变的务工者内心是焦躁不安的。这是一个数量巨大的社会群体,被迫选择离开农村走向城市,他们的生存状态始终是边缘化的,不仅在城市的边缘也在农村的边缘,他们是“城里人眼中的乡下人,乡下人眼里的城市。”[7](P19)这类务工者既无法像一个彻底的城市人一样生活,又无法重新接受农村的生活方式。当现代化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农耕文明碰撞交织的时候,这个群体的蜕变无疑是一种痛苦的蜕变,他们的痛苦根源不仅在于难以适应城市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更来源于内心无法融入到城市群体中,由此带来的便是心无所依的心灵困境和穷苦挣扎的生存困境。
当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小说中的人物存在试图适应新环境的自我转变,也存在转变之后的结果问题。《流言》讲到主人公桃花在村子的土地被城市占领后,她积极地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最后却因开车时遭到侵犯,最终选择自杀。小说提到桃花所居住的“刘家甸子紧傍着城市,聪明的桃花就看准了这一点,离城近进城就方便,这就是一种进步,简直就像是一种战略进攻,一步一步,从她娘家的村子,一步一步往城里靠近。”生活空间一步步被吞噬,更加决定了桃花要成为一个城里人的决心,但是面对复杂的城市生活,她无力抵抗。遭到侵犯的桃花,失去信心又重建希望,但周围人的流言、家人的言语像是匕首,深深刺伤了桃花,也彻底将桃花推进深渊。桃花沦为追求城市生活改变命运的“变”中的牺牲品,也有几分可怜无奈。务工者处在“变”与“不变”之间,不仅在于自身主动求“变”,更在于要获得城市的认可。然而他们的生活始终处于一种被压迫的状态,无论是生活空间的压迫,“村子竟然不存在了”,还是精神上对桃花流言蜚语的压迫,都加重了桃花在城市空间内生存的困难。
与桃花不同,王祥夫也写到被迫改变生活成为务工者的五张犁。短篇小说《五张犁》讲述了五张犁这个种田的好手,他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后成为了园林工人。五张犁在农村土地空间丧失后,进城置于城市中园林空间内生存,赖以谋生的生存空间变了,而原有乡土空间的生存技能又成为城市空间的谋生手段。五张犁从农村到城市,变的是空间,不变的是源于“乡土”的生存技能。他总是目光灼灼,守望着自己的土地。一个失去土地的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对城市改革变迁的无奈,但坚守着土地的梦想已深深扎在五张犁的灵魂中。土地,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空间,更是五张犁的精神寄托空间。由农民蜕变为城市园林工的过程中,五张犁的生存空间发生转换,这种转换以土地被吞没为代价,深刻影响了五张犁的现实生活。他不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城市园林工的身份让他彻底成为了城市中的务工者。失去土地更是影响了他的精神世界,以土地为根的农民,土地就是他们的精神的依托,在他们骨子里有着深深的土地情结。土地是与故乡联系在一起的,失去土地,也意味着再也回不去故乡。但五张犁依然不愿意离开已经变为花圃的土地,保留种田的习惯打理花草,种种的细节都体现着他内心对原有生活的渴望,对故乡的怀念与眷恋。
(二)市民的无奈与艰辛 在城市空间下王祥夫也经常涉及到生活在城市的中小市民。《客人》《花生地》《狂奔》等在不同的具体的城市空间内,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生存困境。市民的生活与城市外来务工者不同,他们是原本就生活在城市空间下的群体,对于城市空间的生活有一定的归属感。但是王祥夫笔下小市民的生活也有几分无奈,体现在无法迅速改变不够富裕的物质生活,所以只能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例如《客人》里刘桂珍逼仄的两间屋子:“刘桂珍的两间屋子,是一楼,光线有些暗淡。刘桂珍住的是老房子,格局是一进走廊门就是一个细细长长的走廊,左手的地方是个厨房,挨着厨房是厕所,过了厕所朝北是一间屋,朝南又是一间屋。屋子都不大,却是当年分给市里干部住的最好的房子。刘桂珍的孩子都是在这屋里长大的。”[7](P108)这样的描写,一方面写出了以刘桂珍为代表的一部分在城市生活的小市民群体,艰难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小说中乡下亲戚来城后,挤在刘桂珍屋子里的逼仄做好铺垫,原本狭小的生活空间加剧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矛盾,也将城市与乡下的差距聚焦在了这一个屋子内。刘桂珍城市生活的不易,又不得不应对人情世故,中国传统的情感、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在现实物质条件:两间老屋子的狭小空间内城乡文化、情与理的碰撞下又是那样的必然和无奈。
同样,在一个具体的狭小局促生活空间内展现一家人生活困境的《花生地》,写到在车棚生活的老赵一家。他们住在原本种过花生,现在只剩下一片灰色水泥楼的小区车棚里。在这零零碎碎的生活里,老赵一家却过得有滋有味。人们时常居高临下望着老赵,心存质疑:“那棚子,那乱糟糟的各种破烂,让人们无端端觉得老赵的生活零零碎碎,是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会有前途吗?或者是,会有明天吗?”[7](P103)在邻居们的质疑中,老赵的儿子考上清华大学,打破了这一家一贯的琐碎状况。王祥夫小说描写将一个小的家庭生活,看似聚焦,又是一种放大。他将故事集中在车棚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在暗淡的生活里,老赵一家展现了生命力极强的勃勃生机。正是独特的城市空间的营造,让小说显得小而精。偌大的城市空间下,他们的生存空间只有一个拥挤的角落,对于小市民这一群体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艰难的生活,而无奈改变这一现状,更是加重了在他们身上的压迫感。于是寄希望于孩子考大学,寄希望于下一代改变这种“空间”生存困境。
三、仪式空间展现民俗中的“人”
地域文化的彰显离不开民俗,民俗赋予仪式空间文化意义。“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8](P1)地域与民俗始终是相伴相生的,独特的地域特征孕育出符合自身特点的民俗文化,而民俗文化又构成地域文化的重要部分。王祥夫的小说善于捕捉地方的民俗特色,为读者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原生态面貌。他将人物置于婚俗、丧葬等仪式空间之下,在特殊仪式空间中探讨人的生存困境。
(一)婚俗仪式空间中的“人” 王祥夫小说反映现实生活,往往具有乡土文化气息,“揭示多种民俗事项的深层意蕴,进而揭示了‘偏远地带’乡土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积淀及乡土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9]王祥夫小说中描写的婚俗仪式集中展示了地域民俗文化,在这种富有民俗仪式空间内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变化。在现实世界中的婚俗,其存在方式和形式内容都隐含着仪式空间内人的价值观念和情感诉求。比如《好峁杂录》中提到好峁村的“女儿招”风俗。所谓的“女儿招”就是在结婚之夜用一块一尺宽二尺长的白布来检验新妇的贞操。“招子”一般是挂在酒馆或是饭店的门口迎客,但是好峁村的“女儿招”也成为了一种晾在墙头供人欣赏的传统。好峁村里的姐姐月香已与周禄川自由恋爱,因为不愿与周大货结亲而被拉扯着强迫印刷“女儿招”。后来,在姐姐逃跑之后,好峁村人众说纷纭“月香真是条贱母狗”“该给贱货月香脸上烫印才好”。他们一时说不清月香究竟错在哪里,只是好峁村的传统向来如此。最终月香的父亲迫于压力,将妹妹桂香以同样的方式推给了周大货作为交代。好峁村姐妹俩的命运都被锁在好峁村这一特殊的乡村空间内,传统的牢笼之中,这种贞洁意识在婚俗仪式空间当中被放大。婚俗仪式本是一件喜事,但在好峁村婚俗仪式的底色却更多的是无奈与悲凉。女性在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的双重压力下,难以逾越这种精神桎梏最终导致悲惨的命运。
《婚宴》中还提到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冥婚。冥婚指的是男女双方生前未结成婚姻关系,死后由双方父母做主,按照正常的婚嫁仪式操办婚礼。小说对河边村武国权家的冥婚仪式从种种细节层层铺垫,包括对于婚宴上“侉炖骨头、扒肉条、乳腐肉方”等菜色的描述,到独特的烹饪习惯“打蒸锅”以及烹饪过程等细节都做了详尽的描写。随后画面转向鼓匠们举着各自的乐器,一路边走边吹,一直迎到村外。对面的人马护送着一个彩棚,“彩棚上绣了大朵的牡丹和小小的凤凰鸟,还有黄黄的流苏”,直到进到院子里,两个牌位才露面,用红线绾在一起,放在前院南房的正面桌子上,原来这是武国权为14岁的儿子办的冥婚。这场有声有色又排场的冥婚仪式仍旧借鉴的是传统的婚俗仪式,这体现出传统的婚嫁观念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武国权出于对死去儿子的思念和疼爱,试图以这种方式抚慰亡灵。小说中的人物在热闹阔绰的婚俗中,精神得到了补偿和满足。《婚宴》故事空间限定在河边村这一传统的村落中,聚焦乡村空间独特的婚俗仪式“冥婚”,从而揭示出武国权另类的对儿子的“爱”以及民众的愚昧,给人以警醒。
(二)丧葬仪式空间中的“人” 丧葬仪式是人从生到死的一场重要的仪式,民间认为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点,只是人从“阳世”走向了“阴世”,“丧葬被看作是将死者的灵魂送往死者世界必经的手续”。[8]基于对“灵魂不灭”的观念,于是出现了各样的丧葬仪式以满足后人对亡者的怀念、尊重等复杂的情感需求。《归来》涉及较多丧葬仪式细节:画有西番莲和牡丹的彩画棺材;供桌上摆有花花绿绿的馒头、梨,还有香烟,供客人点烟,就算是与亡者吴婆婆道别;棺材四周铺上秸草,孝子要在晚上睡在秸草上等。另外还有“领牲”,[9]这是丧事出殡前的一段高潮。牵一头脾性温顺的羊,亲人对着羊磕过头后,羊便成了已故的吴婆婆。羊几次亲近吴婆婆的儿子三小,意味着对三小的挂念,羊抖激灵就表示高兴和满意。小说中将人的情感寄托在羊的身上,羊的一举一动就是已故亲人的一举一动。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连接,体现出万物有灵的思想和朴素的民间信仰。“文学地理学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关注本源于生命的发生发展与体验认知。”[10](P64)这种丧葬仪式空间下,生者与死者的情感沟通,渗透着民众对生死的一种理解,侍死如生,孝道、魂灵等传统思想。
在丧葬仪式空间中的人,他们总在试图借由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来表达对人的寄托,这种寄托虽然是“迷信”的,但是这种观念是最直接、最自然的民间表达方式。安东尼·布奇泰利指出“民俗提供通向文化的重量感、气息或扎根性的情感链接,使得它能够成为制造意义的重要场所和有用的工具。”[11]丧葬仪式文化传承不息,一方面是对亲人的依恋、思念,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是人对生死的一种理解,是一种孝道、伦理文化的内在的要求,虽然是传统的,但也指向了当下,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民俗仪式,在仪式空间内彰显生命的诉求和情思的表达。
综上所述,从现实具体的乡土空间和城市空间,到特定的仪式空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王祥夫的小说作品试图搭建起城乡、现实与理想的桥梁。面临着生存的困境,王祥夫关注到人的生存焦虑与困惑,尤其是精神世界的细腻变化。乡土空间对人的束缚以及城市空间对人的压迫,让人挣扎在现实生存困境当中。仪式空间内人物为传统文化所左右,但也是现实生存的一种生存要求,也有几分无奈,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人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是特定空间内束缚的人。小说对人的表达,正是在特定空间内对人生存的思考与读者共同探寻人真正的人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