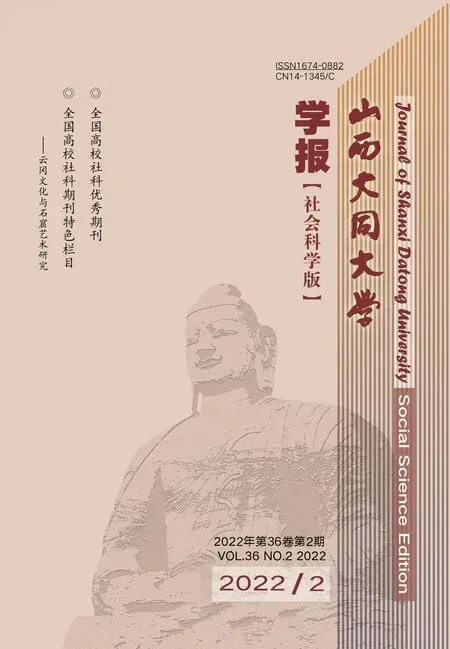草根性:清代花部戏的民间审美情趣
段友文,董亚丽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清代戏曲声腔与剧种发展大势是由雅而趋俗,明衰亡以后,许多文人志士将家国之痛寄托于戏曲艺术中,抒发悲愤与哀思,因此清代戏曲延续了明传奇创作的繁荣景象,《桃花扇》《长生殿》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清中叶以后,文人戏曲创作因其晦涩难懂、远离世俗生活而式微,作为“花部”的地方戏曲以乡土民间为表演场域、以底层民众为欣赏主体,格调粗放,形式多变,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与“雅部”戏曲形成了声腔剧种上的博弈,史称“花雅之争”。其大多是以歌舞为主、情节简单、生活气息浓厚的民间小戏,或是昆曲和其他传统剧作的改编本。在语言上,这些地方戏曲与称为“雅部”的昆剧相比,显得粗糙杂乱,甚至是逻辑混乱、句法错误。这与剧本创作者有关,花部戏的作者大都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民间艺术创作者,与经历过诗词格律训练、系统学习过传统经典作品的文人作家不同。然而,他们熟悉民间艺术和大众语言,了解处于同一阶层的普通观众的社会心理,知道剧本应该如何创作才能抓住观众的眼球,引起观众共鸣。因而,这些地方戏曲贴近生活、贴近观众,展示出朴质真淳、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草根”一般指相对于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的弱势阶层,在这里指平民阶层、大众阶层,而“草根性”指的是一种由自然、自由、自发繁荣的原生性经验出发而形成的具有民众主体性的创作与创造,花部戏在其产生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不论是演出亦或观赏,都与民众紧密相连,蕴含着生生不息的草根力量,这是地方戏曲能在花雅之争中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戏曲演出的生活化
(一)剧目的生活创造 剧目是戏曲表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整个戏曲表演的蓝本。民间戏曲的创作者多来源于乡村田野,且流传方式为口耳相传,导致绝大多数剧目难以考证出作者及产生的年代。口头性是民间文学流传的重要特征,民间戏曲在流传中不断被修饰加工,并根据地域特色产生多种变体,花部戏的剧本创作就具有显著的口头性特征。正因如此,花部戏剧作才能扎根于民间,凝聚更多的集体智慧和思想内涵,取得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
清前期地方戏曲的刻印本较少,现存最早的地方戏曲刻印本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印的《缀白裘》六集和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印的《缀白裘》三十一集。《缀白裘》收录了许多当时剧坛流行的昆曲折子戏和花部短剧,与明代臧晋叔的《元曲选》、毛晋的《六十种曲》等,同为戏曲史上著名的戏曲剧本集。这部剧本集里花部的篇幅大约占十分之二,主要收录了《借靴》《打面缸》《挡马》《花鼓》《看灯》等三十一个剧本。这些剧目主角大多为微不足道的市井阶层,如走江湖的,强盗,妓女等,戏曲的表现形式清新可喜、灵活多变,“有时以鄙俚之俗情,入当场之科白”,[1](P1)也有戏中串戏、戏中插入连厢词以及花鼓的表演等。这些花部短剧对现实有着大胆的批判与讽刺,例如《借靴》中张三向刘二借靴时二人的种种周旋与矛盾冲突、《打面缸》中周腊梅对王书吏、四老爷、县太爷三人的捉弄。除《缀白裘》外,还有叶堂《纳书楹曲谱》的“外集”及“补录”收录了乾隆五十年的时调以及《楚曲》《祭风台》《青石岭》等刻本。另外还有抄本、清人笔记、梨园史料中记述的地方戏曲剧目。抄本有同州梆子《画中人》(嘉庆十年抄本)、《刺中山》(嘉庆十三年抄本)等;笔记有焦循《花部农谭》;梨园史料有杨静亭《都门纪略》(道光三十五年刻本)。对这些地方戏曲的剧目及史料进行研究,可以洞悉其蕴含的历史兴废与伦理人情。
在内容上,各类型的剧目要贴近民众生活,表现普通大众的思想。一方面,古代戏曲中有大量剧目依据少量史实加以想象改造而成,内容丰富生动、引人入胜,不仅反映政治生活,还掺杂了神仙鬼怪之事,目的是引起观众的注意,间接表达民众思想意愿。例如在杨家将故事戏中,不仅着重表现人物的爱国思想与行为,还着重表现其悲惨遭遇,《李陵碑》通过杨继业兵困两狼山,奸佞潘仁美不发援兵,杨被迫碰碑而亡的惨景,来表现奸佞当道对国家社稷的危害,寄寓民众的爱国情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地方戏曲大多活跃于广大乡镇农村,最多的观众是农民,戏班以艺谋生就得迎合观众的需求,农民的爱憎与戏曲剧本内容互构共生。戏曲人物、情节、事件能打动人心的是生活实际所给予人们的爱憎与是非的判断,赵山林曾论述剧目的选择:“李渔不赞成把冷热作为选择剧目的标准,他提出了一个更为本质、因而也更为合理的标准,即‘合人情’。他说:‘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只要能写出‘离合悲欢’,写出‘人情所必至’,就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发冲冠,能使人惊魂欲绝。’”[2](P150)因此,在平民阶层中产生的地方戏曲,剧目内容所要表达的伦理人情就略显复杂,涉及广泛的生活面相与不同的思想倾向,例如《清风亭》中张元秀唱道:“只指望养儿来待老,谁想积谷今朝防不得饥?养儿须要亲骨血,恩养他人总是虚!”[1](P73)体现了人民群众为人处世的情理、是非、道德观念。再如《赛琵琶》《买胭脂》等剧目对抗击恶势力的顽强斗争精神、男女爱情的真挚追求以及家庭生活无私奉献的赞扬。另外,剧目的创作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即要满足祀神节庆和世俗百姓娱乐的双重需求。
综上,地方戏曲的这些剧目深深植根于民间,在创作上更多地体现广大农民群众的时代感受、现实需求,在内容上反映的是他们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愿望。
(二)演员的舞台表演 演员的表现是戏曲展演的重要一环,花部戏唱词说白采用白话文,曲调由板式变化构成,这对创作者文化水平的要求有所下降,演员有能力参加剧本文学和音乐的再创造,演员在舞台实践中,能够直接获取观众的信息反馈,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二次创造,以达到更好的表演效果。发展至清代逐渐形成以演员为主体的风尚。“京剧和地方戏兴起,表演艺术发达,形成戏曲‘角儿制’,演员至上,名角称王。从‘同光十三绝’到梅兰芳,扩及地方戏的各路‘诸侯’,表演艺术达到炉火纯青。‘角儿制’在产生和中兴阶段,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对中国戏曲功德无量。”[3](P74-75)这一时期的表演更加强调演员个人的艺术创新与独特成就。
乾隆以后,花部戏演员群英荟萃,魏长生、高朗亭、米喜子、程长庚、余三胜等著名演员为戏曲的发展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许多演员来自于平民阶层,大部分是农民艺人和农村半职业艺人,他们对于民众的现实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了解观众的所思所想。花部戏曲的演出中,民间艺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演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演出面向农民、小商户等劳动群众;演出场所具有流动性,艺人们在哪里谋生,演出场所就在哪里,例如乡镇、庙会、村头,乃至庆生贺寿的院落等。有时会坐地演出,有时在小戏馆、茶楼等。人们围坐观看,十分随意,不受舞台限制;演出活动与季节密切相关,演出的多少视农忙农闲而定,艺人们既是表演者,又是劳动者;演出的内容与观众生活水乳交融,除观众点戏外,有时要注意迎合观众的心理,安排适合特定观众对象的剧目。
演员表演的内容或是师傅传授,或是在观赏其他艺人的演出时学来。剧情的主干内容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在枝节、语言和唱段方面,常常有变体,剧情的唱段、唱词的多少都是艺人本领的体现。表演的内容或是师傅传授,或是在观赏其他艺人的演出时学来。这些变体常常是艺人根据自身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积累,再结合具体的场合和观剧对象即兴改编,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规律和变化方式:摘挂,即从其他剧目里摘下一些部分放到所演出的剧目里,如唱景、唱花名、唱历史古人等;加词,出现在剧目较短需要拉长演出时间、同台演出时为竞争而即兴加词以吸引观众等情况中;搬家词儿,即甲剧目的词搬到乙剧目中唱;扔词,有三种情况,一是演出时间不够,二是妇女儿童在场,不便于唱粉词,三是观众对某唱段不感兴趣;编加故事,在表演时添加小段内容,内容可以从民间故事中找到押韵部分改编,或是见景生情、即兴发挥,或是从大鼓书中搬来故事;添加小曲,演唱简单活泼的歌曲烘托气氛;大扒皮,抽出许多段词往一段上加。以上的变化主要呈现两个趋势:一是地方化,例如演唱某位人物时,籍贯、时间根据当地情况灵活变动,二是民间化,演唱时的语言、口音、人物形象都与本土民众生活一致。
(三)演出场所的变迁 戏曲的演出场所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变迁。歌舞百戏是戏曲形成之前的雏形,演出场所大都利用自然地形举行。汉代形成了建筑性的演出场所,山西运城、安徽涡阳和河南项城都出土了陶制的百戏楼模型,在《西京赋》《隋书·音乐志》中有相关史料记载。唐代出现了专供歌舞杂剧演出的乐棚、乐楼、歌台、舞台等建筑,在唐代诗文和敦煌壁画中有相关描述。宋代随着戏曲艺术的成熟,演出场所逐步完善,城市出现了瓦舍勾栏式的演出场所,中小城镇和乡村出现了供迎神赛会演出的乐楼、露台、舞亭等演出场所。在宋金交替的北杂剧形成之时舞亭演变为戏楼,山西侯马董村戏楼模型就展现了这一时期戏楼的形制。元代形成了具有上下场定位的三面观戏楼,此时,戏楼也在北方农村广泛兴建,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庙宇碑刻里都有建筑戏楼的记载。明代戏曲发展繁荣,各地为适应观戏需求建造了大量的戏楼,而昆山腔的兴起使得厅堂和家庭小戏楼成为其演出场所,红氍毹就是这一时期舞台的代名词。
在清前期,戏曲观演的主要场所是公私院宅、会馆戏楼以及酒馆戏园,主要满足较高阶层观众的赏剧需要。到了清中后期花部戏兴起之后,戏曲的演出场所随之发生了变化。茶园剧场取代了酒馆戏楼,并在道光以后开始增多,在经营模式和观剧方式上有了很大的转变。道光间张际亮《金台残泪记》中提到北京的茶园“园同名异,凡十数区,而大栅栏为盛”,[4](P248)同治年间,上海的茶园戏馆也越来越多,成为观剧的主要场所。在茶园演剧,戏曲演出的剧目都是事先规定,与电影院类似,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是否观看。每一位看戏的观众都要支付茶费,将原先酒馆演剧中由少部分人承担的演出费用分摊到每一位观众,不仅使看戏成本降低,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也体现了观剧地位的平等,使戏班演出更加职业化、专业化,向独立经济体发展。这种演剧方式使平民大众成为观剧的主体,观众席大致分为“池子(普通看客)”“散座(次于官座)”“官座(富豪或达官贵人)”,虽然有阶层之分,但在演出的欣赏和需求上,大家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且由于池子看客的数量优势,使戏班的演出更加考虑这部分听众的审美需求。王梦生在《梨园佳话》“京师最讲皮黄声调”条就称皮黄“优人在京,不以贵官巨富之独誉为荣,反以短衣座客之舆论为辱”,[5](P126)体现出这一时期平民百姓的主体地位。与这种职业戏班相对的是在广大乡村和城镇由农民业余爱好者和半职业艺人组成的“土班”,他们常常在各种节令赛会中登场表演,也会在日常闲暇时聚集演唱,是一种群众化的演戏活动。在演出内容和形式方面,农村艺人的表演有很多技艺、内容上的不足,这一缺憾随着花部戏曲的兴盛得以弥补,他们积极寻求城市戏班的帮助以提升自身的演戏水平。在演出场地上,他们大都经历了由“唱门子”(指逃荒行乞时站在东家门口的演唱)。“撂地摊”(指在村头街尾以摆摊式的行为演唱)到茶馆和小戏园,再到正式戏园的曲折过程。
演唱场所随戏曲艺术的发展、观众群体的需求而变革,经历了由简单到多样的衍变过程,不断靠近平民阶层。花部戏以强大的市场占领了观剧舞台,推动戏曲演剧传统转变,使得戏曲演出跃入新的阶段。
二、观戏行为的平民化
(一)观剧主体的迁移 乾嘉时期的花雅之争到咸同年间胜负已见分晓,昆曲的市场远不如新兴的花部乱弹繁荣,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观剧主体也由文人士大夫下移至平民百姓,戏曲的审美趣味、思想内容也随之变化。陆萼庭曾指出:昆剧的“文人阶层观众,清代中叶以后,逐渐销声匿迹。”[6](P3)昆曲的兴盛主要由文人士大夫蓄养的家班作为支撑,随着这一风气被遏制,观众越来越少,昆曲的衰落势在必然。《梨园外史》就有这样的分析:“明朝戏班,都是阔人自家拴的……自从我朝桐城张文端公崇尚俭节,不蓄家伶,士大夫人人效法,不拴班子,单靠内府和王府。虽是天家势力,到底养不了那许多的人。戏园内只论挣钱,所以昆曲渐渐少了。”[7](P97)事实确是如此。入清之后,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官员蓄养家班。到清中期后,文人蓄养家班的风气得到遏制,加之实学的兴盛、文人地位下降等原因,家班逐渐衰落,花部戏观众跃升为观剧主体。
市井世俗百姓对戏曲的爱好,直接影响戏曲创作者对剧种、剧目的选择,成为演员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戏馆的开设与商业戏班的发展,使城乡居民成为观戏的主要群体,这就要求戏曲的内容表现他们的生活,形式适合他们的欣赏趣味,满足时代与群众的需要。焦循在《花部农谭》描述:
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自西蜀魏三儿倡为淫哇鄙谑之词,市井中如樊八,郝天秀之辈,转相效法,染及乡隅。近年渐反于旧。余特喜之,每携老妇、幼孙,乘驾小舟,沿湖观阅。天既炎暑,田事余闲,群坐柳阴豆棚之下,侈谭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余因略为解说,莫不鼓掌解颐。[8](P225)
这里呈现了花部戏演出的盛况,明确指出其观众为“农叟、渔父”“老妇、幼孙”等。另董耻夫《扬州竹枝词》中有一首云:“丰乐朝元又永和,乱弹班戏看人多。就中花面孙呆子,一出传神《借老婆》。”[9](P264)描述出花部戏在扬州观者云集之盛况。地方戏的新编剧目更是备受青睐,有“巴人下里,举国和之”[10](P11)之记载,城乡居民成为戏曲观赏的主要群体。
(二)观众的审美理念 审美观点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审美过程所持的态度与看法,由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审美地位所决定,具有时代性和主观性。平民阶层的审美观念与实用性相关,是一种劳动美,“劳动创造了美的世界,劳动成为美的鉴赏的重要尺度。劳动要求健壮美,劳动要求力的美。”[11](P18)民间的艺术创作大多都体现了这种劳动美的思想,发挥着教化、娱乐等实用功能,形成了质朴、简约、大胆、有趣的艺术风格。不论是北杂剧,还是南传奇,或是清代的花部地方戏曲,从诞生起就植根于民俗文化、通俗艺术的土壤,表现世俗性的审美特点,这种特点是其拥有广大接受者的根本原因。
花部戏的返璞归真与素朴本色,符合民众求新、求变、求美的审美情趣。首先,在题材内容、主题倾向和人物形象方面,体现了社会底层百姓的感情倾向、是非观念与审美心理。例如戏曲行当中人物形象的美学塑造,“北杂剧、南戏、传奇、花部乱弹的剧本都标明了剧中各色人物由何种行当扮演,这就涉及塑造人物如何发挥戏曲行当的作用的问题,戏曲行当是一种人物类型,首先在类别的划分中显示了美学的评价。三国戏中,诸葛亮的智慧、周瑜的狭隘、曹操的奸诈、关羽的义勇、张飞的威猛,在不同行当的扮相和唱念做打中都得到突出表现。”[10](P101)可见,行当是一种刻画人物的程式体系。其次,语言、结构和表现方式虽然简单,却呈现出开放性,对各种戏曲艺术营养能兼收并蓄,舞台表演强烈的写意性和虚拟性、角色行当的类型划分及深刻的表现力、程式的广泛应用,都取得了空前成功。
戏曲要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走向民众,声腔上必须通俗易懂,王骥德《曲律》提到的义乌、青阳、徽州、乐平、石台、太平梨园等戏曲声腔,接近当地群众的语言、音乐、欣赏习惯,是弋阳腔地方化的成果。与昆曲相比,更具有观众优势。昆曲风靡二百年,不仅是普通百姓,文人士大夫阶层也对其产生了“审美疲劳”,加上缺乏新剧,他们热情大不如前。这时兴起的戏馆把戏剧文化推向了市民阶层,人们早已对文雅的词文、细腻的声腔失去了兴趣,更热衷于能满足审美需求的花部声腔。在音乐体制方面花部戏曲生动活泼、变化丰富的板式体,代替了传统戏曲的曲牌联曲体,加上“接地气”的故事情节,打败了雅部的戏坛霸主地位。它简单易学、倜傥不羁,富含娱乐性、通俗性,使大众和民间艺人的情感得以抒发和流露,这种由繁至简的回归,正是清代花部戏审美精神与美学风格的呈现。
(三)观剧行为的功能性 观剧行为的功能性体现在花部戏曲与传统节日庆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过年、端午、中秋、新庙庆成、佛像开光以及迎神赛事等活动中,都有民俗色彩浓厚的戏曲表演。这类表演将滑稽与通俗结合、庄严与诙谐相融,以鲜明浓烈的民风、民情表现生活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从而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接受和喜爱,几乎存在于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每一种仪式或应酬活动中。一年四季,逢节日要庆祝,逢节令要祭祀神佛,逢喜事要祝福,逢灾病要祈福消灾等,其间,演戏必不可少,不同地区的节日节令有同有异,供奉的神灵因地域不同也有差异。因而,与这些民俗活动相联系的民间演戏,是常年不断的,归结起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节令祭神演戏,清代节庆演剧蔚然成风,“时剧”《看灯》《闹灯》即为元宵演出剧;每年七月十五盂兰盆会演目连戏,是宋代就有的习俗;春社和秋社祭祀土神演戏,春、秋两季对土神的祭祀演变成了大众参与的、包括各种文艺节目表演的娱乐性很强的活动;五月,祈雨酬神,演青苗戏;土地神诞辰演戏;庆火星诞辰演戏;城隍赛会以及各种重要的节日场合也演戏。二是生活中某个团体、家庭逢婚娶、添丁、寿辰之类的喜事,或逢丧事都要宴客演戏,是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戏行为的功能性还体现在娱乐性。戏曲艺术的娱乐性在众多文化艺术门类中尤其显著,其母体“巫”“优”两种形式的本质是娱乐的,王国维在论述中国戏曲与“巫”“优”关系时指出:“要之,巫与优之别: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13](P3-4)不管是“乐神”还是“乐人”,本质都在“乐”,即娱乐性。花部戏源于民间,体现的是草根文化、民间信仰和百姓的审美情趣,是不加掩饰、毫无顾忌的乡村娱乐。来自民间,娱乐百姓,是花部戏曲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生命力绵延不绝的动力所在。花部戏曲的演出,有时在于娱神、酬神,是出于宗教和民俗的目的,但是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娱人,所以多在逢年过节、社火、庙会或喜庆活动中举行,表现出平民阶层在休息或农闲时对娱乐活动的需要。如《堆仙》中的八仙戏,是旧时浙江地区春节必不可少的演出内容,祈愿祝祷,欢庆娱乐。
教化性也是观戏行为的功能所在,这种功能是多方面的。花部戏中的历史戏、爱情戏、生活戏都在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夫妻争吵、邻里不和、孩童教育等生活问题都会借助戏曲的力量加以规劝、引导,得到解决。花部戏曲中的事理人情与处事方法,是人们吸收经验的便捷渠道,例如闹剧《花鼓》《看灯》《磨坊串戏》等,通过表现家长里短、人物生活、内心情感,利用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生活环境的反差,制造矛盾冲突,刻画出丑公子、恶婆婆、恶作剧的小市民等栩栩如生的形象,让人们看到众生百态,在生活中引以为戒。
三、观演双方的戏曲接受
戏曲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演员与观众的“面对面”是其显著特征,相应地拥有了广泛的参与者与接受者,因此,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较,更加适合运用接受理论来阐释这种现象。戏曲舞台从统治者的深宫到文人士大夫的庭院再到平民的市井村落,广泛的观剧群体在接受戏曲的过程中得到娱乐与享受,感受社会整体的生活状态与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与戏曲舞台表演产生多重互动的体验,感知艺术所表达的精神力量与生命启示。清中期花部戏曲能够发展起来,关键是有效地抓住了平民阶层这一观戏群体的口味与心理,实现了演剧方与观剧方的良性互动。
(一)演剧层面的艺术输送 演剧方要想有效地让观众接受戏曲表演,首先是作品要与观众在感情上产生共鸣。演员在表演时传达了真实的感情,观众看戏时才能感同身受。明汤显祖评价《焚香记》时指出:“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14](P1486)戏曲的这种感染力是以情感为媒介的演员表演与观众接受之间的情感交流为基础的,强调观众情感体验的真实性与可信性。花部戏的演出以切入生活的现实性品质和真实生动的表演方式,获得广大民众的喜爱。清焦循记述:“‘花部’者,其曲文俚直……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9](P225)由此可知,农村乡镇的平民阶层喜欢戏曲,主要因为其题材具有“忠、孝、节、义”的审美特点,舞台表演也具有“其词直质”“其音慷慨”“足以动人”的艺术魅力,从而使人们进人了一个“血气为之动荡”“莫不鼓掌解颐”的接受境界。
其次,戏曲作品的通俗易懂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体现在语言上,王骥德说:“作剧戏,亦须令老妪解得,方入众耳。”[15](P154)强调戏曲语言必须“老妪解得”,才能达到入耳的程度。花部戏的文辞直白,少有文采甚至俚俗,更多的是为角色表演服务,如《打渔杀家》的唱词“我这里咬牙关急往家奔”“将身儿来至在草堂内坐”。[15](P288)另一方面体现在唱曲上,花部戏的唱词重在辙口,少于营造意境,基本上都是押韵和辙的流水词,如著名的《苏三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奴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来言我心好惨,那过往的君子听我言。”[16](P289)花部戏的观众为平民阶层,因此花部戏的通俗易懂不仅仅是编写者文化层次不高的原因,更是为适应观众而形成的表演取向。另外,花部戏由曲牌体变为板腔体的音乐体制,也使唱词发生了变化。
最后,演剧方需要营造多重感官的审美体验。戏曲是一种融合了音乐、舞蹈、歌唱等多种艺术的形式,能够使观众通过视听感觉,接受演员在舞台表演中传达的情感,获得审美愉悦。学者么书仪指出:“光绪中叶以前,京师观众听戏更看重伶人的唱,后来舞台的照明条件逐渐改善,听戏变成了看戏,伶人的神情、做派、念白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也就是说,观众的审美逐渐偏向于表演的‘戏理’”。[17](P270)花部戏对于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舞台艺术等方面都十分重视,更能满足民众的观戏审美需求。
(二)观演双方的交流互动 在戏曲的表演过程中,传达与接受的双方在舞台表演的视听感受、情感共鸣、击节称赏以及艺术回味等方面形成了多层次的互动体验,这里面涉及了感受与感染、认可与接受、思考与评判等活动。焦循《花部农谭》中的《赛琵琶》,论及观演双方的互动交流,描述陈世美“名优演此,不难摹其薄情,全在摹其追悔。当面诟王相,昏夜谋杀子女,未尝不自恨失足。计无可出,一时之错,遂为终身之咎。”[11](P226)“一时之错”即“皆一时艳羨郡马之贵所致。盖既为郡马,则断不容有妻,有儿女也。”[9](P226)同时引导观众“于其极可恶处,看他原有悔心”,[9](P226)即理解陈世美人物性格来源的复杂性,以及造成他堕落的主客观等原因,这个戏才能“古寺晨钟,发人深省。”[9](P226)观众观看《赛琵琶》时,一方面感情随着剧中人物秦香莲的喜怒哀乐而产生情感共鸣,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对这一社会悲剧进行人生思考与切身感悟。
同时,观众的表现对演出的效果、演员的发挥也有影响。赵山林提到“程长庚被尊称为‘伶圣’‘京剧鼻祖’,彼有‘叫天’之誉。但他‘性独矜严雅,不喜狂叫’,常对观众说:‘吾曲豪,无待喝采,狂叫奚为?声繁,则音节无能入四座,寂,吾乃独叫天耳。’有的观众看戏时喝采狂叫,程‘则径去’。于是‘王公大臣见其出,举座肃然’。即使在咸丰帝面前演出时,他也提出‘毋喝采’的要求。”[2](P218)程长庚对于观众的要求,不是表面的的喝采与追捧,而是欣赏艺术时的全身心交流与艺术感知,这样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其艺术表演才能,展现最好的水准。
花部戏在表演的过程中,演员与观众、演员与演员、观众与观众之间都处于一个互动的过程。在演员与演员之间,有农村业余戏班向专业戏班的学习,演员之间相互学习,来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并向更高的舞台迈进。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观众存在审美品位的差异,产生了交融与影响。有时他们之间的信息反馈不仅仅是场上氛围感的营造,也有台下的交流切磋,增强了戏曲的欣赏效果。
(三)戏曲接受的心理分析 在戏曲表演的过程中,观演双方都有各自的心理活动。余秋雨将艺术心理分析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对作品内角色的心理分析,其次是对创作心理的研究,第三层次是对接受心理的深入。[18](P27)在此我们主要分析第三个层面,即花部戏曲为实现“被接受”及观众的接受心理。
戏曲欣赏时需要观众在演戏的真实场景下加以心理想象,进入虚拟时空与情境。在时间上往事可以再现、死者可以复生、千年弹指一挥间等;空间上三四步行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人物的美丑也由演员的表演发生幻化。戏曲要吸引人们的注意,不仅是表现生活日常,带给观众熟悉感,也要满足人们求新求异的心理,“人情厌常喜新”“耳目无久玩,新者入我怀”[2](P192)是人们常有的心理状态,开场时的自报家门、第二折的“冲场”就是引起观众兴趣的手段。另外,戏曲演出是一个需要长时间保持注意力的过程,在主线即核心剧情的基础上,需要出现多种变化使观众全神贯注,花部戏曲演员在演出过程中的变体就是这样而形成的。戏曲的表演不能完全做真实性的展现,而要留给观众一定的想象空间,以虚带实,似真似幻,例如《借妻》中主要用宾白表现生活,塑造人物形象,同时利用戏剧时空和插科打诨揭示人物内心活动,使观众留下了想象余地。观众在观看戏曲时,也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情感经历与剧中人物比照联想,进而产生共鸣,这首先取决于剧目对于情感的发掘,如《铡美案》包拯排除万难怒铡陈世美,舞台上正义的伸张,与劳苦大众渴望公正的心愿不谋而合,观众得以解怒泄愤。其次好的演出,演员的动作神态总能达到令观众触目生情的效果,拨动观众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例如《打金枝》虽是描写帝王将相的家庭关系,但是语言的质朴自然与动作的栩栩如生使民众倍感亲切,从而联想到自身的家长里短。另外语言、戏曲结构、唱词等方面也要为观众理解接受而调整,但不应过度创造,要给观众留下广泛的想象空间。
戏曲不同于小说、诗歌等文学形式可以脱离观众而存在,因此让观众接受这一目的贯穿了从剧本创作到舞台表演的整个过程。昆曲因为文辞典雅、缺少新变而丧失了大部分听众,花部戏以贴近民众生活、清新明快的表演风格而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并产生亲和力,精准把握住观众的戏曲接受心理,产生了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结语
花部戏曲植根于人民,生于斯,长于斯,存在于岁时节日庆典、宗教祭祀、民间仪式、日常衣食住行以及商业消费活动中,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丰富了下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具有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企及的亲和力,同时戏曲观众的喜爱又是花部戏曲不断生长繁荣的不竭动力。本文主要从演戏行为的生活化、观戏行为的平民化以及观演双方的戏曲接受来分析花部戏的草根性。演戏从基本的剧目、演员的组成及表演活动、演出场所等方面,无一不是在向民众靠拢、为观众服务;观戏从主体地位的变迁、观众的审美观念、戏曲的功能所在都体现了与民众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花部戏曲为适应观众而形成的独特表演体制,彰显了生活化、平民化的演出形式,演员与观众在戏曲欣赏这一层面达到了互动,彼此影响又彼此成就,体现了草根性这一明显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