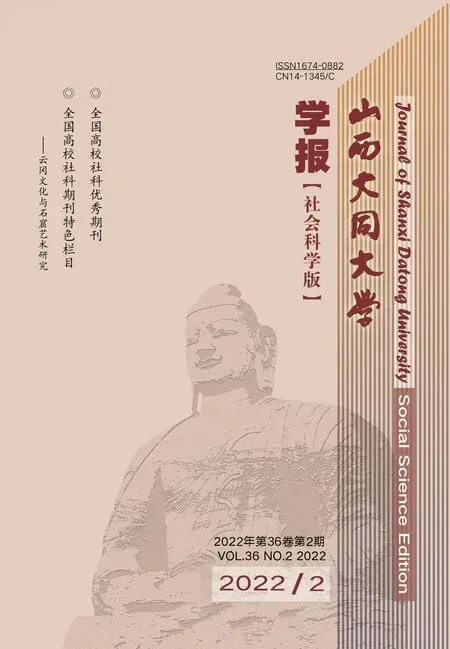布迪厄理论下大同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资源激活
石凤珍,常 虹
(1.山西大同大学现代社区文化研究中心;2.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2008年4月,国务院公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将“历史文化街区”定义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有一定规模的区域。[1]由此可见,我国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一是原有文物丰富;二是历史建筑集中成规模;三是能够体现历史风貌,展现文化内涵的区域。
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因为其文化资源丰富,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精神面貌,且能给予街区居民乃至整个城市的居民无与伦比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比如:苏州的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天津的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以及成都的宽窄巷子等历史文化街区,这些历史文化街区,散发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有的中西结合,有的清新雅致,有的古韵悠长。这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模式也将会给大同本土的鼓楼历史文化街区带来启发,时代在迅猛发展,然而大同鼓楼文化街区及其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激活却没有很好地与时俱进。本文将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审视并指导本土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激活。
一、大同鼓楼文化街区的历史与现状
历史文化社区,其历史性不言而喻。大同位于塞北咽喉要地,处于古代农牧业分界线、各民族的交界处,多种文化于此荟萃,使大同文化的历史性与地方性互为表里。大同的历史文化跨越多个朝代、多个民族。自北魏,经辽金,至于明清,北魏时建都于此,辽金时大同为西京,繁荣的政治文化为现在丰富的文化资源打下了基础,且传统的皇家建造使得大同古城纵横分明,整齐划一;明清时,人口增多,民族融合,这也得益于大同独特的地理位置。作为大同古城中心的突出地标——鼓楼社区是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社区,具有以下特殊性:
(一)以明清之际为历史背景 大同的历史文化别具一格,有着强烈的历史厚重感。大同是明代“九边”之一,处于战争的前沿。这一时期,城市的军事功能和军事文化紧密相连。明清之际,这座城市经由战乱而重回和平。随着移民的增多,城市教化功能逐渐回归。在这样一部特殊的“战争与和平”的剧目中,在当代承平之时,如能通过历史社区文化资源的建设来激活人们对于历史过往的兴趣,无疑也是具有传承与教化意义的。
(二)民族融合伴随始终 中华民族文化既有传承,更有包容,地方文化也是如此。就历史文化社区而言,有很多活灵活现的实例。如大同的鼓楼西街和广府角。在鼓楼西街的街道上,能感受“声闻四达”的报更声;在广府角,明代皇族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空余街巷上的寻常百姓,能感受到社区文化的背后就是农牧分界线进退间的历史融合。在历史文化社区资源激活的过程中,必须重现这种历史感和文化感的整体性。
(三)教化生活一体无间 清道光《大同县志》在第五卷《营建》的开篇就是一段关于城市建设与教化互为表里的论述:“官如传舍,兴废听之于时,此士大夫之过也。若夫入其境而城廓完,祠庙肃,仓廪缮,传置不稽程,行旅不病涉,则长吏之无废事也可知矣。表厥宅里,绰楔相望,则风俗之茂美可知矣。况在冲途,邮政綦重;通商惠工,桥梁尤要。是以志及于此,而不胜惶然也。卷中刍荛所及,诚数年以来所惓惓于兹者。‘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今将次第举之,益兢兢之。”[2]该地方志编者认识到“风俗之茂美”离不开城市规划的教化功能,怀着崇高的情怀描述着城池,甚至感到“不胜惶然”,继而引用《论语》中的警句来强调城市与教化是统一的。
社区与城市在旧时代是一个教化的整体。但现代社会城市化之后,历史文化社区就成了一座孤岛。没有了旧时代教化的氛围,很难对旧时代文化资源的教化功能有切身的感受。所以,历史文化资源的功能激活,就是要在新时代和旧时代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身处新时代的年轻人最大程度感受到街区“新文化”的活力和“旧文化”的厚重。新媒体是连接大同年轻人与大同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重要工具,应当合理运用,取其长处。“在运用新媒体建设社区文化中,还要避免对其技术上的过度依赖,而忽视其他多种媒体形式的运用”。[3]传统文化的教化功能,通过历史文化社区的资源激活得以延续,也对文艺学的西方话语方式产生了一种东方式的新的指引。此时,激活历史文化街区乃至社区的文化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是要重现过去,还是表现当下?历史文化街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种种文化观念随着由他们所映照的世界的改变而改变”。[4]
大同鼓楼西街历史文化街区和大同广府角历史文化街区已被列入《山西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第三批)》。政府层面的重视和投入,使得对此二条历史文化街区文化资源功能激活的研究显得既有利又迫切。重建一片社区不易,激活海量文化资源更难。即便百分之百复现一块昔日的社区,也不得不面对一种尴尬的境地:时移世易,在城市化的汪洋大海中,历史文化社区作为一座文化孤岛,其文化资源很难引起年轻人的共鸣。历史文化社区求古求雅,年轻人则求新求异。现有的对历史文化社区的研究已相当丰富,跨学科、多专业、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成果不断更新。“历史街区功能性问题的解决不能圈于静态保护的思维,简单地延续固有的历史属性,采用‘博物馆’式的保护方法,必须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新的功能内涵”。[5]
二、布迪厄“实践理论”
理论归根结底是由人来运用的,理论也不是静止的,理论前进的方向,最终是靠实践来推动的。法国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对于大同历史文化社区资源激活有重要参考价值。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场域”和“惯习”。虽然这些概念起源于法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研究相关文化街区的问题。布迪厄不仅作为一位文化大师为人所熟知,他的理论在建筑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也有很重要的地位。
(一)场域概念 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人们也可能会提及“隔行如隔山”或“潜规则”这样的俗语。但“场域”更多地是基于社会活动者之间的共识来发挥效用的。场域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客观”的,也就是说,利益的形成是建立在稳定的“倾向产生机制”之上的。虽然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前提,“场域”的效用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为现实中的社会群体有着取得优势的内在动力。当下流行的“抱团取暖”、“内卷”之类的流行语恰是对几十年前布迪厄“场域”概念的最好注脚。人们一方面慨叹“内卷”是一种无意义的低效之举,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不“卷”是不可能的。“场域”既非先验的,也非经验的,如果分析地看这个概念,关系恰恰能说明“场域”在时间上紧凑的生成模式,构型则说明“场域”在空间上庞大的规模尺度。
(二)惯习概念 一定历史时期内某地的居民,其所受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具有一致性,因此其习俗就是行为相似性固化下来的产物,也就是呈一定规律性和统一性的惯习。虽然人群是分阶层的,但惯习的统一性把人们整合起来。惯习是一连串行动,但本身却没有意图和目的。惯习产生于某个固定的社会阶层,并在沿袭的过程中加强了这种结构,使得已有的社群更加稳固。居住在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和精神文化,这些惯习反之也影响着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惯习本身是自由的,是不能被强加的。反过来讲也许更恰当一点,古城历史性和地域性塑造了本地人的惯习,惯习的自由的演化则赋予了历史文化街区各种资源以特别的意义。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历史文化街区的结构化又是一个惯习作用的自由过程,这就产生了一种冲突。惯习长期影响着人们对历史文化街区的评判,是有其倾向性和滞后性的。因此,激活历史文化街区文化资源的功能,既是对居民现有惯习的纠正,也是对居民现有惯习的利用。惯习并不意味着某一阶层所有成员千人一面,观点一致。相反,每一个人的所思所想都是个性化的,只不过这种个性化在这一阶层中具有同源性,因此在平稳发展的过程中是互相协调的。惯习的结构化是递进的,就好比家庭教育的方式决定着学生在学校里吸收知识的方式,进而影响到其工作后的处事方式。惯习形成过程中的效果是在阶层中不断经受验证的。
三、大同历史文化街区文化资源的激活措施
无论是从传承与保护,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大同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资源激活都势在必行,具体而言,可采取如下措施:
(一)打通“场域”的壁垒 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资源的激活过程中,打破街区居民和游客的关系间隔,建立一种互相需要的关系。居民不仅仅是街区的主人,更是街区发展的内在动力,鼓励街区居民参与到街区文化发展中来,提高居民参与度:地摊经济,当地向导,民居体验等都是可操作的措施,与相关部门倡导的一些“高大上”的旅游项目相比,更能拉近游客与街区居民的距离,更能叫参观者有“参与感”,游客不再是局外人,他们能真切感受到大同历史文化街区居民的普通生活。
(二)“惯习”激活与传承 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遗产丰富,形式多样,这是街区代代相传的技艺和习惯,然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保留的层面上——在展厅展览或是让一些传承者坐在历史文化街区的门店中,亦或是兜售一些文创作品,应该创新动态的“惯习”传承模式,如通过提供活动与表现场所和空间的方式让人们和非遗传承人“面对面”“零距离”体验,亲自感受。此外,“惯习”和文化的传承,最需要的是青年人的加入,加强学校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合作,公益活动也好,科普教育亦可,都是传承本土文化切实可行的方法。
(三)公开凝视场景,沉浸式文化体验 国内其他历史文化街区文化资源激活的成功案例,如平遥古城的“又见平遥”沉浸式情景大剧和南京秦淮区“金陵文化”“民国文化”体验剧,就是大型沉浸式文化体验,公开凝视场景。大同是一座文化包容、崇尚礼义的传统古城,将文化沉浸式体验借鉴到历史文化街区,可把古城的元素和演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突出大同的塞外特色,使观众在有限的时间里参与到表演当中:步行穿过几个不同形态的主题空间,可设置风云商场、古堡战场、农间耕作、婚丧嫁娶等主题各异的场景,同“又见平遥”类似,观众可以游走在各个场域之间,化身商人、战士和普通人等,捡拾祖先生活的片段,与演员深度互动。参与实景演出就是“穿越”,观众有时是看客,有时是亲历者,这又与“场域”概念相贯通。通过表达对祖先的敬重感、对传承人的认知感、对他人的礼义诚信的认同感,可使游客身临其境,沉浸式体验大同本土的惯习文化。
结语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对历史文化社区资源激活问题的参考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直击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动机。中国各地之所以掀起大建文化古城的热潮,就是主办者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争夺文化资本,赢得话语权力,打造城市名片。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一定要凭借古城社街文化的视觉效果展示其文化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即建筑风格在时间尺度上的复古特点和在空间尺度上的特异性。这体现了历史文化街区资源的稀缺性。这些均可以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解释。第二,揭示历史文化街区的资源激活困境。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属于限量生产领域,城市整体建设属于大量生产领域。不同场域之间话语的争夺使得历史文化街区资源的激活吸引不到足够的社会资本进行文化再生产。第三,为将来历史文化街区资源激活提供了指引。在研究中,要重视访谈、拍摄、类比,打通各个“场域”之间的区隔。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仍需结合大同本土街区的特点作出以下纠偏。第一,历史地来讲,大同古代城市的变迁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变革,远非布迪厄所观察的阿尔及利亚平静的单线历史可比。第二,现实地来讲,中国当代城市化还没有完成,整个社会阶层处于激烈的动态变化当中。大同历史文化社区的建设和古城的发展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布迪厄实践理论时,要结合实践,强调动态,调整研究思路。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应该得到保留和发扬,在保持其思辨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运用到大同历史文化街区资源激活的实践中,可以有效地克服理论的局限性,纠正实践的盲目性,使理论接地气,实践有条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与大同历史文化街区资源的激活本身就是一体的,是一种从小处、实处着手的理论指导,是有实际指导用处的“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