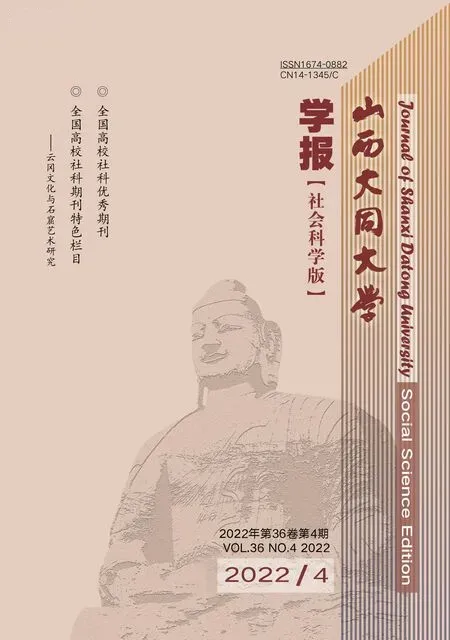“为人生”与“在人间”:陈彦的小说创作论
李一雷,韩伟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128)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陈彦在剧作和小说方面都进行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包括现代剧“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和“长篇小说三部曲”(《主角》《装台》《西京故事》)及于今年面世的长篇小说《喜剧》,这些优秀的作品无疑奠定了其在当代戏剧与小说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从创作之初,陈彦一直恪守“以现实主义精神回应时代的精神疑难”[1]的创作初心,并不断实践着对当代“恒常价值”[2]的坚守与担当,以温情质朴的叙事努力拨亮“人类精神的微光”,彰显了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据此,我们可以从对文学思想传统的“古”“今”融通、对“小人物”的“众生相”的细微刻画,以及赓续“有态度”的现实主义创作三方面来着重挖掘陈彦的小说创作经验,从而为当代的文学书写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为人生”:思想传统的古今融通
“五四”以降文学的信仰观念与“恒常价值”的表达一直是文学和理论界经久不衰的重要探讨问题,在中华民族赓续流传的文化传统中,一直有主张“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文艺观,[3]一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提出的“为人生”与“在人间”的文学创作观,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显然,陈彦充满现实主义底色的文学创作是对这一中国文学思想传统的极大继承与弘扬。
陈彦曾担任过陕西省剧协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多年的戏剧创作经历,让他以戏剧创作为基础,同时凭借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经验,逐步建构起他独一无二的小说世界。由于陈彦多年来对戏剧艺术的接触、熟悉,对戏剧剧本的精神内核——儒家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把握,其作品中体现的文学思想传统的“古”“今”一脉传承与融通不言而喻。在《西京故事》里,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可以是罗天福仁厚又豁达的处世哲学;在《装台》里,可以是刁顺子身上不自觉外显的“侠义观”;在《主角》里,可以是忆秦娥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生活勇气;在《喜剧》里,也可以是老一辈丑角艺术家火烧天对舞台火一般的表演热情。
细观陈彦已出版的4部长篇小说,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几乎都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精神,读者在书中随处可见一幕幕温暖人心的场景。《装台》里,主人公顺子在困窘生活下仍然不灭“生”的担当与责任,彰显古典社会的侠义精神,小说中多次描写到他对于渺小生命蚂蚁的悲悯与同情,这源于他们有着相同的处境——都在奔命、辛劳地生活着,对蝼蚁尚且如此关怀,更不必说顺子是如何善待身边的亲人及朋友,这是顺子“侠义”品格的第一个维度:“仁”;刁大顺的第一任老婆跟别人跑了,只留下一个张扬跋扈、尖酸刻薄的女儿刁菊花,处处刁难他的第二任老婆赵兰香和继女韩梅。无论是包容亲女刁菊花、继女韩梅,善待第三任妻子蔡素芬也好,还是帮助大吊的遗孀周桂荣和她年幼毁容的女儿也罢,顺子以自己的善良、包容为这些苦命的女人们撑起了一方小小的容身之所,供她们治愈受伤的心灵,即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甚至不得不重操旧业“装”更多的“台”,他也毫无怨言,这是第二个维度“义”;其三是“信”,顺子一直秉承着儒家文化中“人无信不立”的诚信品格,无论顺子艰难地讨要了多少装台钱,他都会一五一十地明账分给装台弟兄们,整个装台团队虽然整体揽着又苦又累的活却心甘情愿一直跟着顺子谋营生;第四个维度则是“孝”,顺子父母早亡,只留下两个哥哥与他相依为命,在得知远在珠海的赌徒刁大军病倒后,他二话不说,亲自到珠海把哥哥接回家聘请名医细心照料,陪伴大军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对朱老师和师娘,顺子更是远超师生之情,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孝顺二位老人,这样至情、至真、至善的人伦之情向生活在底层的普通老百姓投去一抹温暖和光明,让读者自觉跟随主人公顺子一道在西京城体会世间人情冷暖、五味杂陈,这便是陈彦小说创作的成功所在。陈彦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身上挖掘出传统中赓续至今的仁爱、善良、诚信、孝悌等美德内核,借助文学作品里的小人物完美展示出来,将这些美德与品格内化为自己小说创作的精神脉络,自觉进行接续与弘扬。
陈彦延续了同为陕西籍作家柳青、路遥对于个人的生存境遇与时代之间复杂关系的现实关切和思考,并将这一点内化为他的创作动力。从人物、时代、家国种种现实难题的解决为切入点展开叙述,进行全景式、整体性地观照,以反映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社会总体变迁的基本脉络和历史意义,证明了个人自身命运的沉浮并不能完全脱离时代力量所造成的影响。
《主角》围绕忆秦娥四十余年个人命运的起伏转折展开故事叙述,连同四十年间时代政治、经济和其影响下秦腔戏剧的兴衰浮沉一并包含其中。忆秦娥自十一岁起学戏历经四十余年刻苦修习,在经历了痛失爱子、丈夫刘红兵残疾、爱人石怀玉离世等一系列人生变故和打击后,饱尝人世间酸甜苦辣,却仍能顶住压力、不灭斗志,“要风里能来得;雨里能去得;眼里能揉沙子;心上能插刀子”,[4]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之境地,终成一代秦腔名伶,可以说忆秦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例证,她以充满力量、催人奋进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书写着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奋斗力量。当忆秦娥不得不面对一代“主角”退场的历史命运之时,她毅然选择了如同当年忠、孝、仁、义四位老秦腔艺人培养她一样的方式,将自己的毕生所学技艺倾囊相授给养女宋雨,她将个人的理想与价值追求融入时代、家国的事业之中,如灯塔一样照亮了秦腔赓续流传的文脉,让秦腔能够代代传承,后继有人。新时代民族精神的传承正是通过千千万万个“忆秦娥”们的书写,才能使我们的民族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二、“在人间”:小人物的众生相
在《装台》中反反复复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物象——蚂蚁,小说开篇就写到蔡素芬刚来到刁家发现了正浩浩荡荡搬家的蚂蚁大军,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蚂蚁暗喻现实生活中工作辛苦、过得卑微、价值渺小却又充满坚韧的刁大顺。因为顺子的形象常常是“活得如此卑微,见谁都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5]这些生存在墙缝边、房门下的“蝼蚁”们,他们怀揣着梦想来到城市,融入轰轰烈烈的时代浪潮,却四处碰壁、举步维艰,如树叶一般轻飘飘寻不到依靠,散落在城乡交界的边缘。
刁大顺日复一日、勤勤恳恳为了生存而奔波,却最终也没能过上片刻只忙于下棋、打牌、喝茶看报纸的“小康生活”。从这个层面上观照顺子的生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当幸福来敲门时”总是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但顺子总是以自己的淳朴、善良向生活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小说的最后又是以蚂蚁的暗喻来作为结尾,“蚂蚁们,是托举着比自己身体还沉重几倍的东西,在有条不紊的行进的。他突然觉得,他们行进得很自尊、很庄严,尤其是很坚定。”[5]毫无疑问,陈彦热切注视着城市与乡村交界地带的以刁顺子为代表的农民工这一群体,展现虽身处社会底层、过得艰难的劳动者,依然用自己的勤劳、诚实的双手为自己挣来自尊、庄严、坚定、幸福的生活。陈彦对底层劳动者们的成功塑造,令他的小说中充满着为小人物发声、现实主义文学的温情与亮色,[6]彰显着人间真情在的美好光辉。
统观陈彦的小说可以发现,陈彦作品的主题都展现了琐碎、细微的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创作多从微小的侧面为切入口阐释主人公独特的生命哲学,以及我国社会近二十年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虽然如蝼蚁一样渺小的人也会有梦想,也会有追求生活美满幸福的权利。《西京故事》中农民罗天福带着生病的妻子进城打工,饱受磨难依然善良淳朴,《喜剧》里常常念叨“福在丑人边”上的唱丑名角火烧天,不忘从艺的初心仍身体力行精进着“扮丑”艺术。在“人”的意义上,在生命的意义上,他们和所有拥有“奋斗”“向上”力量的国人一样,这是他们面对未知的生活艰险做出的最本真的回应。“人是有尊严的高级动物,无论职位高低,贫富贵贱,在生命面前是平等的。”[7]《装台》里公正厚道的瞿团,对艺术精益求精、刀子嘴豆腐心的靳导,为了给孩子植皮卖力干活却不幸早逝的大吊;《主角》里呕心沥血的忠、孝、仁、义四位老秦腔艺人,对司鼓艺术如痴如醉的胡三元等等,“他们都是生活在西京城里的芸芸众生,是一群被现实裹挟着随波逐流的社会底层普通百姓。他们遵循着各自的生活逻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守着彼此内心的责任和担当,折射出当今社会的‘工匠精神’”。[8]陈彦努力将自己的创作真正“下沉”到平民生活中去,透过他笔下这些温柔敦厚的“小人物”——社会底层普通老百姓的视角,去观照、去展示这座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西京城”里,所有劳动者的价值坚守、责任与担当、善良与美丽。
三、重塑生活经验:对现实主义写作的赓续
陈彦的小说质朴平实,读来亲切、余味悠长,恰恰是这种看似毫无突破、老实本分的守“拙”写法,却能最大程度上再现文学创作记录的根本要义。所谓“文学”,究其本源还是“人学”,文学作品要想能够表现出丰盈的人性,就应当将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重返到文学创作现场。他十分愿意、也非常想写作出为读者相信“人世间一抹亮色”的东西,他坚信,只有作品充满“真实”,才会有深刻地吸引力和感染力,在《装台》一书的后记中陈彦曾坦言:“我的写作,就是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与其说为他人,不如说为自己,其实生命都需要诉说,都需要舔伤,都需要爱。”[5]在依然艰辛的社会现实中,时刻关切关注“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重要特征,陈彦通过为生活在城乡夹缝中的底层群体立人生传记,自觉承担起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担当。
“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把自己的童年经验看成是巨大而珍贵的馈赠,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的源泉。”[9]一如老舍笔下对北平日子的眷恋,路遥对生他、养他的黄土高原的热忱,贾平凹小说中陕南乡村生活深刻烙印,毫无疑问,故土生活将在作家创作中转换为所有的心灵寄托、情感归处。陈彦在西安生活了近三十年,他对于这座城市的感情全部化为文字保留在他的作品中,写起来也得心应手,他温情脉脉地注视着西安这座城、注视着这座城里每一个拼尽全力、吃苦耐劳的“小人物”。“温润如玉、充满情义”是陈彦对古都长安的高度评价,也是对所有挣扎于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夹缝中的“下苦人”们的高度赞扬。同时,陈彦在小说中大量、广泛地加入了陕西方言以及口语化的对白,使得作品非常“接地气儿”,例如,用“瓜不唧唧”四字将忆秦娥刚入门当“烧火丫头”时做事憨、傻的可爱跃然纸上;“克利麻擦”在陕西方言里是快点儿做某事的意思,《主角》里常常出现用来反映胡彩香性格的急躁。“咥”是陕西方言里“吃”的意思,《装台》里主人公刁大顺在出苦力干完活后最幸福的事也不过能美美地“咥一碗面”等等。方言俚语恰到好处的运用,裹挟着浓浓的西北乡土人情,带领着读者的感情自然而然进入到陈彦的小说世界之中。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陕西文学的创作一直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从20世纪脍炙人口的《创业史》,到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人生》,再到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陈彦延续了陕西乡土文学创作中对挣扎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小人物命运的现实关切与思考,并巧妙融入传统戏剧艺术,将传统文化重新镀亮,以典型的“中国式讲法”叙述了一个个鲜活、温暖的“中国故事”,彰显着对城市底层奋斗向上的劳动者的赞美和讴歌,这种典型的“中国式讲法”也全部来自于陈彦对于西安城市宝贵的生活经验的珍视。“现实主义创作永远魅力无穷。真正震撼人心、打动人心之作,仍是那些直接从现实生活中压榨而出的琼浆玉液。这种逼人的人性真实与情感真实力量,是文艺接通受众思想和精神光缆的最有效手段。”[10]可以说,陈彦的现实主义创作,是一种有态度的、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的现实主义创作。而这种创作态度被高度凝练为他的小说创作观,陈彦用他的创作疗愈人心,[3]使得文学创作的社会功用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从这个层面上观照,陈彦也在以自身的创作努力回应与赓续着鲁迅“为人生”与“在人间”的文艺创作观。现实主义永远都有意义,因为文学无论再怎么变,永远都反映了客观世界,反映人类的生存与思考。
鲁迅曾指出文艺是照亮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在当今,文艺作家勇于承担起文学书写的使命,努力为时代发声,为人民发声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就应该最真实地表现出人民群众对真、善、美的追求与愿望,使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充分的显现。”[11]陈彦曾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是坚持弘扬中国精神的根本。总书记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灵魂。我们时常感叹世风日下,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处处体现一种善良、正直、宽厚、持守正道的朴素美德,这些美德一经文艺的拨亮放大,便产生一种以石击水的正能量。”[12]显然,他已用自己的作品践行着“重构文化中国,弘扬中国精神”的时代要求,并在千年文明连续统一的意义上铸就中国道路的文化自信”[13]作品中对文学思想传统的古今融通、对小人物众生相的细微刻画,也必将催生出更包容和凝练的现实史诗的文学创造。善于发现和书写人性的些许亮光,让微光照亮微光,最终成为客观存在,这便是陈彦小说创作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