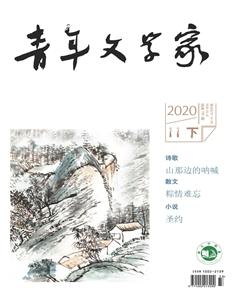《装台》的存在主义解读
何朋达
摘 要:作家陈彦长篇小说《装台》虚构了“西京”这一具有西北地域色彩的城市,塑造了刁顺子、蔡素芬、刁菊花和大吊等各异的人物形象。主人公刁顺子一次次陷入命运的轮回中,无法摆脱存在性孤独和西西弗斯式的无意义抗争。而其女刁菊花也陷入自我主体性消解的悲剧之中,西京百态人物的隔膜和西京这一和谐整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关键词:装台;陈彦;存在主义;海德格尔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3-0-02
前言:
海德格尔在评论荷尔德林的诗歌时提出了“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和“返乡就是返回到本源近旁”的观点[1]。《装台》所描绘的主人公刁顺子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图景,无疑存在于作者铺设的某种类底层的叙事背景之中。但比起对底层文学真实性的探讨,《装台》这部小说更多展示的是具有“西京”地域色彩的边缘化职业视野下的“返乡”故事。这种“返乡”并不是人物形象的物理返乡,而是文本在地域和人的本真性的双重返乡。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在散文《西西弗斯的神话》中通过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不断推石上山,石头又不断滚下的永恒劳作的故事,提出一种形而上的悲观存在论。而不论作者是否刻意在作品中注入了存在主义哲学观,《装台》主人公刁顺子那种类似西西弗斯的人生轮回模式都展示出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语境下的无所依托的流放者,而刁菊花这一女性形象也蕴含着“他者”这一消极的存在论女性主义因素。此外,纵观《装台》描绘的诸多人物形象和小场景小故事,这些事物融合在一起展示了“西京”这一古都的众生相,对一种存在主义视角下苍凉的命运感给予了观照。
1.边缘化职业
《装台》以主人公刁顺子的职业“装台”为标题,而整个故事也正是从装台人生活的几处横切面入手的。装台是一个离艺术既遥远又亲近的职业,它是如此“底层”,却又和艺术表演息息相关。和靳导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相比,以刁顺子为代表的装台人干的是艺术的活,但却又自称“下苦”,和艺术实际上是疏离开来的。既参与艺术又自称下苦,没有接受过艺术科班训练却被要求具备匠人品质,这一有趣的矛盾共同体就是顺子的事业。而实际上,这一事业不仅在艺术上是边缘的,在社会上也是边缘的。它不起眼,从装台经历中看还容易被人瞧不起,稍不注意就有上顿没下顿。《装台》的人物形象却是从这个边缘化的职业展开的,职业的边缘造就人格的边缘。刁顺子和他的装台团队就总是处在边缘,只能按照“大师”的指点安排工作,演出取得成功也不过是保证收入,沾不到多少艺术的光荣,他们就是这样处在幕后和边缘。
这种边缘化和不稳定的职业让刁顺子处在一种存在性孤独的境地之中,在表面上刁顺子要和很多人和事打交道,但就其存在性而言,刁顺子是无比孤独的。蔡素芬代表着家庭关系的缓和因素,但刁顺子和她仍然有不可逾越的隔膜。在躲避复杂的家庭关系而投身于工作中时,刁顺子面对瞿团长、靳导演等服务对象时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隔膜。这种隔膜,最终让他陷入了表面热闹却摆脱不了的存在性孤独的处境之中。就像萨特所思考的那样,这种边缘化的人物因他人注视而觉得自己成为客体时,他就处在无法克服的异化之中。
2.西西弗斯式的“英雄”——刁顺子
刁顺子是《装台》的主人公,故事开头他已经历两次婚姻,迎来蔡素芬后却与大女儿刁菊花产生矛盾。故事中回顾的这两段婚姻,一次又一次的装台工作和矛盾,以及故事结尾和周桂荣的种种可能,顺子像是陷入了那种西西弗斯的轮回。刁顺子的家庭和事业,总是从有起色到崩解,一次次下来就像把石头推上山而石头又滚回去。但顺子却又不得不继续着这种轮回,像西西弗斯一样追求某种微弱的光芒,并默认了这种无助的软弱。对读者来说,一股绝望的命运感和疼痛感扑面而来。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让刁顺子再难以得到任何内在的自我拯救的可能性,只能陷入一种永恒的无意义的轮回之中。此处的“英雄”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传统的英雄行为,他只需做自己人生轮回的一种悲剧性的英雄。而在存在的荒诞性面前,生活的意义已经瓦解,悲剧性的英雄行为也是刁顺子这样逆来顺受的人主宰自己命运的方式,一次次的轮回也是刁顺子一次次力图克服这种荒诞的努力过程。故事中后期刁顺子一心放弃装台事业而去玩虫子,小说节奏骤然舒缓,但矛盾却未解决,只能给这一悲剧英雄带来更多的悲凉感和无助感。李敬泽在评论中写道:“这个刁顺子,他岂止是坚韧地活着,他要善好地活着,兀自在人间。这就又不是喜剧了,这是俗世中的艰难修行,在它的深处埋伏着一个圣徒,世界戏剧背面的英雄。”[2]
3.刁菊花与女性主义
小说中略顯病态的刁菊花是故事家庭线索中矛盾的重心,她是刁顺子第一个妻子的女儿,从故事一开始就和蔡素芬不和甚至故意排挤,后又和继妹韩梅不和使其被迫出走,可以说是故事中制造不稳定的关键因素。波伏娃的《第二性》是存在论女性主义的代表作,阐述了女性作为“他者”的性别身份和“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的女性主义观点,并把症结归结到父权制文化之上。[3]《装台》中的刁菊花相貌丑陋,自觉出身低微,看不起父亲刁顺子,又榨取他的下苦钱。这个人物正是波伏娃视野中困在自我构造的“他者”恐惧之中的女性,她在自我和人际关系中都丧失了本体性。这既体现在她对父亲、继母、继妹、乌格格和谭胖子的厌恶中,也体现在对宠物狗好了的虐杀中。刁菊花已经自在地接受了这种内在化的他性认识,虽然她是作为个体的女性形象接受的。而在萨特“反思的我思”语境下,即她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只是游离在这些关系中,然后通过厌恶和排斥来找寻丢失的“自为的存在”。[4]
4.“返乡”的西京与众生相
在海德格尔眼中,“返乡”就是要回到西方视野中前苏格拉时代的本真存在,但在返乡之途中现代性的人“无力消除自我内部的矛盾冲突和自我主体与世界客体的二元对立”,他将“诗意的栖居”看成人回返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径。[5]但在《装台》的类底层叙事之中,作者也在潜在地追寻这种“返乡”。主人公刁顺子和周遭事物存在隔膜,而他近乎悲壮的人生轮回则将自身规定在了主体消解的现代性视野之中。《装台》展示的人物形象如刁顺子家庭、剧团人物、寺院僧侣以及各类商业人士数量众多,方言词句和关于西京的风物描写也比较丰富,这些加起来就将西京这一有现实指向的虚构地域描绘得极具真实性。同时《装台》又有年代感,如“不在服务区”[6]等话语带有本世纪前十多年的色彩,显得具有生活质感。这样,《装台》中的百态人物虽然有隔膜,但在西京这一地域中却又有某种同一性。这些陷入绝望命运感的人物在西京这一审美和谐的诗性空间实现了某种外在的人性与自然的统一。这种同一性就如同海德格尔“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的回归人的本源的理想状态。也如李敬泽对《装台》的评论:“此处是盛大人间,有人沉沦,有人修行”。
尽管西京整体可以说是和谐的,诗意的,但人物主体和世界客体的冲突并未得到解决。诸如刁顺子、蔡素芬和大多数故事里的人物总是有着苦多乐少的悲剧色彩,作者长篇叙述刁顺子人生横切面的故事,但刁顺子却无可挽回地继续陷入绝望的命运轮回之中。这样下苦的人存在于世间经历悲欢离合,却不得不继续接受隔膜和存在性孤独。对个体来说,唯我主义的返乡之途仍然虚无缥缈,无益于解决具体的生存困境,最终仍将陷入无法摆脱的现实的命运轮回之中。
结语:
装台是在艺术和社会上均处于边缘的职业,装台人干的是艺术的活,却又被称为下苦而与艺术疏离。刁顺子虽然和很多人打交道,但却处在不可避免的存在性孤独之中,在家庭和事业两条线中挣扎但却难见起色。一次次装台经历和家庭变迁后,刁顺子只能选择轮回,成为西西弗斯式的圣徒。刁菊花则自己代入了他者身份,自卑本性掩藏在暴戾之后,丢失掉自为的存在后,渐渐走向了扭曲。西京这一地域具有诗意的和谐性,其中的百态人物却难以解决具体的生存困境,纷纷陷入无可挽回的悲剧宿命之中,最终成为了存在主义视野下主体与客体对立的流放者。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 孙周兴.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 商务印书馆, 2000:24.
[2]李敬泽. 修行在人间——陈彦《装台》[J]. 西部大开发, 2016(8):134-136.
[3]方珏. 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哲学的归宿——略论波伏娃《第二性》的当代意义[J].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6, 23(2):34-38.
[4]谭裘麒. 萨特"自我意识"理论初探[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1):5-13.
[5]赵静蓉. 诗意栖居的本真性——论海德格尔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返乡之途"[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1):113-117.
[6]陈彦. 装台[M]. 作家出版社, 201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