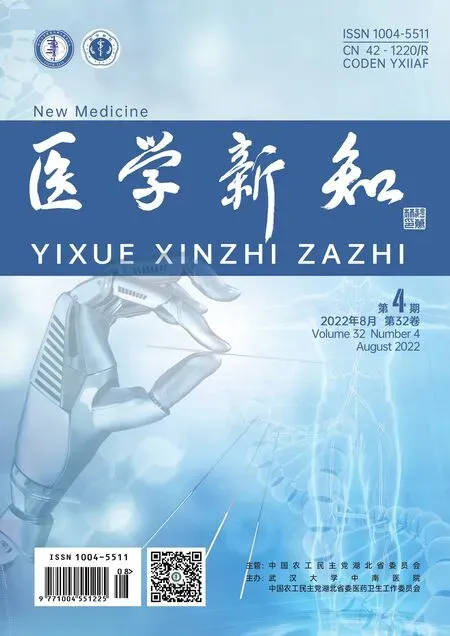炎症性肠病与妊娠及生育力评估
朱 芮,文韵玲,缪应雷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昆明 650032)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种病因不明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疾病,可由遗传、环境、免疫及肠道微生物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引起,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便血。在欧洲,IBD患病率普遍呈上升趋势,过去的三十年间,丹麦CD患病率从5.2/10万增至9.1/10万,UC从10.7/10万增至18.6/10万[1]。在我国,2005—2014年间IBD患者约为35万,至2025年,预计患者人数将达到150万[2]。有研究显示,IBD患者中主动避孕的比例高达17%,是普通人群的3倍[3]。对生育力的担忧及治疗方案存在的潜在风险均可成为患者主动放弃生育的原因。目前IBD患者生育率的下降,将会进一步加剧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给家庭及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此外,在保证病情稳定的条件下,降低不良妊娠风险是临床工作者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总结IBD患者妊娠及生育力的评估要点,为临床工作者制定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1 炎症性肠病对生育力的影响
因IBD发病高峰年龄与生育年龄重叠,疾病可能对患者的生育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研究显示,处于静止期且无盆腔手术史的IBD患者生育力与健康人群一致[4]。IBD患者生育率的降低可能与生育意愿降低有关[3]。血清抗米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作为评估卵巢储备的标志物,是评估育龄期女性生育力的指标之一。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发现,活动期CD患者AMH平均水平(1.34±1.39 ng/mL)明显低于缓解期CD组(3.52±2.09 ng/mL)和对照组(3.87±1.96 ng/mL)[5]。另一项研究显示,缓解期和轻度活动IBD患者的活产率与未患IBD者相似,而中重度活动IBD患者的活产率较未患IBD者下降了21%,表明处于活动期的IBD患者生育力降低[6]。此外,抑郁、焦虑、肛周疾病、住院次数的增加同样与生育力下降有关[4,7]。研究显示,疾病活动期与男性患者生育力下降相关,烟草、酒精在加重病情的同时也会使男性的精子质量降低[8-9]。因此,欧洲克罗恩病与结肠炎组织(European Crohn's and Colitis Organization,ECCO)共识及我国专家共识均建议IBD患者在缓解期进行妊娠,尤其在内镜黏膜愈合状态下的妊娠可获得更佳的妊娠结局[10-11]。
生物制剂的研发应用使得IBD患者的治疗方案不断革新,但仍有60%~80%的CD患者和10%~30%的UC患者最终需要手术治疗。全结直肠切除回肠储袋肛管吻合术(ileal pouch-anal anastomosis,IPAA)是目前UC患者手术治疗的标准方式[12]。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UC患者在IPAA术后生育率下降了46.5%,这可能与术后造成的输卵管阻塞、输卵管与盆腔粘连等术后后遗症有关[13]。虽然手术治疗后的UC患者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人数是未行手术治疗UC患者的3倍,但其婴儿出生率仍下降了40%以上[14]。此外,在男性患者中,IPAA术后可能会出现逆行射精或勃起功能障碍[15]。柳氮磺吡啶(sulfasalazine,SASP)、甲氨蝶呤(methotrexate,MTX)等药物的使用可能导致精子减少,因此,建议暴露于SASP的男性IBD患者在备孕期间用其他5-氨基水杨酸(5-aminosalicylic acid,5-ASA)进行替代治疗,暴露于MTX的男性患者在备孕前停药3个月[16]。综上,IBD患者的生育力与疾病活动度及治疗方案息息相关。
2 药物治疗
因妊娠期的特殊性,部分患者服用药物的依从性会因对药物的担忧而降低,不仅导致病情的加重,还增加了自发性流产、早产、低体重儿等不良妊娠事件发生的风险。事实上,除了MTX和沙利度胺外,大多数IBD药物在妊娠期服用的风险均相对较低。对于多数IBD患者来说,妊娠期服用药物以维持病情稳定所获得的益处远超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
2.1 5-氨基水杨酸
5-ASA是轻、中度UC患者诱导缓解和维持治疗的传统药物,包括SASP、美沙拉嗪等。目前尚无证据证明5-ASA与不良妊娠结局相关[17]。因此,妊娠期间病情复发时,5-ASA可作为首选用药[11,15]。由于SASP会干扰叶酸的吸收,因此需同时服用叶酸(2 mg/d),以减少神经管缺陷风险[11]。此外,对于美沙拉嗪缓释片,因其含有在动物实验中证实对生殖系统发育有不良影响的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故建议妊娠期间改用不含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的5-ASA[11,18]。
2.2 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常用于急性发作及对足量5-ASA治疗无效的IBD患者,其可通过胎盘转换成无活性的代谢产物。一项针对1 490名IBD患者的研究发现,妊娠期暴露于糖皮质激素增加新生儿早产、低出生体重的发生风险,但并未排除疾病活动度对妊娠结局的影响[19]。另一项Meta分析则显示并未发现孕期暴露于糖皮质激素将增加唇腭裂的发生风险[20]。对于中重度活动期IBD孕妇而言,服用糖皮质激素诱导缓解的益处远超其潜在风险[10]。因此,在妊娠期病情复发时,糖皮质激素可作为首选用药,但不能用于长期维持治疗,且在使用糖皮质激素时,应密切监测孕妇血压、血糖等指标,以便及时发现不良反应,降低不良妊娠风险[11]。
2.3 免疫调节剂
免疫调节剂已成为IBD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常用的免疫调节剂包括硫嘌呤类、沙利度胺及MTX等,适用于对激素依赖或无效以及诱导缓解后维持治疗的患者。有研究发现,妊娠期服用硫嘌呤类药物增加患者早产发生风险,但也并未排除疾病活动造成早产的可能[21-22]。另有研究表明,硫嘌呤类药物不会影响妊娠结局,且对后代的长期随访(5年)发现健康状况并未受到影响[23-25]。综上,建议备孕期及妊娠期间可继续服用硫嘌呤类药物以维持病情稳定[10]。现已明确沙利度胺及MTX的致畸性,因此,建议女性在怀孕前6个月停止服用MTX[16]。对于沙利度胺,则建议男性和女性在妊娠前都停用6个月以上[10]。虽然环孢素和他克莫司无致畸性,但是其会增加妊娠期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26-27]。此外,关于环孢素和他克莫司在IBD患者妊娠期的使用数据仍然稀缺,因此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其在IBD患者妊娠期的安全性。
2.4 生物制剂
生物制剂可用于IBD的诱导及维持缓解治疗。一项网状Meta分析结果显示,生物制剂组临床缓解率(17.7% vs. 10.0%)、内镜缓解率(40.4%vs. 30.0%)均显著高于对照组[28]。目前常用于临床的生物制剂有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IFX)、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ADA)、维得利珠单抗(Vedolizumab,VDZ)、乌司奴单抗(Ustekinumab,UST)等。
IFX、ADA为较常见的抗TNF-α的生物制剂。IFX为IgG1单克隆抗体,随着妊娠中期胎儿滋养细胞中Fc受体表达的增加,其穿过胎盘的数量也逐渐增加[29]。此外,妊娠中晚期暴露于IFX的患者,其体内IFX的清除率明显低于妊娠早期和非妊娠期,在其孩子6个月大时的血液中仍能检测到IFX的存在[30-31]。另有研究显示,母亲妊娠期暴露于IFX的儿童感染率较高[32]。因此,建议对于达到临床缓解的IBD患者在妊娠22~24周暂停使用IFX[33]。研究显示,妊娠期暴露于ADA并不会增加孕妇的不良妊娠风险,且其孩子出生第一年发生严重或机会性感染的可能性较小[34-35]。因此,妊娠期间可全程使用ADA[33]。
VDZ是一种针对整合素α4β7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对于其在妊娠期使用的安全性,有研究显示妊娠期暴露于VDZ与不良妊娠风险增加无关[36-37]。但是,一项Meta分析发现,妊娠期暴露于VDZ的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的风险显著高于暴露于抗TNF- α的孕妇[38]。因此,建议VDZ治疗期间严格避孕,治疗结束后至少18周内仍继续采用避孕措施[33]。但若病情需要在妊娠期间进行VDZ治疗时,建议在分娩前6~8周给药,在顺利分娩48 h后恢复给药[27]。目前,VDZ在我国临床上使用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其是否会导致后代发生严重感染、恶性肿瘤等不良事件仍需长期随访观察。
UST是抗白细胞介素12和23的全人源化IgG1单克隆抗体。有研究显示UST治疗不会增加妊娠不良事件的风险[31]。Geldhof等研究发现,暴露于UST的孕妇其胎儿活产、自发性流产、先天性异常占比与一般人群一致,分别为71.3%、18.4%、3.8%[39]。目前关于妊娠期暴露于UST后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仅有个别病例报告[40],因此,仍需收集更多关于IBD患者在妊娠期UST使用的数据,以便更加精确的评估其在妊娠期使用的安全性。综上,对于UST维持治疗的患者,可在妊娠期全程使用,因其在妊娠后期可通过胎盘,故最后一次使用应在预产期前6~10周[33]。
2.5 小分子药物
最近,小分子药物用于IBD的治疗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托法替布是一种口服的小分子Janus激酶抑制剂,主要用于对常规治疗不耐受或无效的中重度UC患者[41-42]。托法替布的无免疫原性和口服食用性,不仅大大提升了患者的依从性,而且还提高了治疗效果,使其具有较大的临床应用潜力[43]。作为一种小分子物质,托法替布可能会跨越胎盘屏障,动物实验已证明了其具有致畸性[41]。但是,一项针对11例女性和14例男性在孕前或孕中暴露于托法替布(剂量为5 mg或10 mg,每日两次)的研究显示,妊娠结果包括15名健康新生儿、2例自然流产、2例药物终止妊娠,无胎儿死亡、新生儿死亡、先天性畸形等情况,与一般人群结果相似[44]。目前关于IBD患者妊娠期使用托法替布的研究有限,因此,建议停用托法替布4周后再进行备孕,并避免在妊娠期间使用[45-46]。
3 其他治疗
随着对疾病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新型技术的出现,推动了IBD治疗的发展。选择性吸附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疗法(granulocytes and monocytes absorption,GMA)为一种减少炎症性白细胞并抑制其在肠道浸润的非药物治疗方式,适用于糖皮质激素依赖或难治型的中重度UC患者,其治疗IBD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已在日本及欧洲国家的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47]。但是关于GMA在IBD患者妊娠期的运用,目前仅有较少的病例报告显示在治疗中并未增加不良妊娠事件发生风险[48-49]。因GMA价格昂贵,其在我国临床实践中并未得到广泛的应用,导致GMA治疗IBD患者的数据非常有限,尤其针对于IBD妊娠期的治疗。因此,GMA在IBD患者妊娠期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还有待研究。此外,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为目前IBD治疗的热点之一,其已成功运用于一般人群复发性艰难梭菌的治疗中。研究显示,临床缓解的UC患者维持FMT治疗有助于维持内镜、组织学及临床缓解[50]。一项个案研究显示,一名抗生素治疗后仍反复发生艰难梭菌感染的女性,在妊娠18周时停用抗生素并进行了FMT治疗,随后该患者未再发生艰难梭菌感染,且在产后4个月的随访中,产妇及婴儿无不良事件发生[51]。FMT作为新技术,在IBD的治疗中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还需开展大量的前瞻性临床研究以证实其在妊娠期使用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4 结语
IBD的发病高峰年龄段与育龄期相重叠,导致众多育龄期患者因对疾病认识不全面而不得不放弃生育。事实上,静止期且无盆腔手术史的IBD患者生育力与健康人群相似,而且通过治疗维持疾病稳定所获得的益处远超过治疗产生的不良反应。除MTX、沙利度胺及小分子药物外,大多数IBD药物在妊娠期服用的风险都相对较低。硫嘌呤类药物可用于妊娠维持治疗;糖皮质激素及5-ASA可作为妊娠期疾病复发的首选用药;抗TNF-α的生物制剂在妊娠期间可选用,但是IFX应在妊娠22~24周暂停使用;VDA、GMA等新型治疗方式仍需大量的临床数据以验证其在妊娠期的安全性及对后代的远期影响,故在妊娠期应慎重使用。做好IBD患者的孕前宣教、孕中产检、产后随诊,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至关重要。同时,多学科团队合作必不可少,应全面、科学地评估患者的生育力,根据患者孕周及病情变化不断优化治疗方案。最后,面对不断推出的新型药物及技术,其在妊娠期的运用经验尚不足,还需进行大量临床研究验证其安全性及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