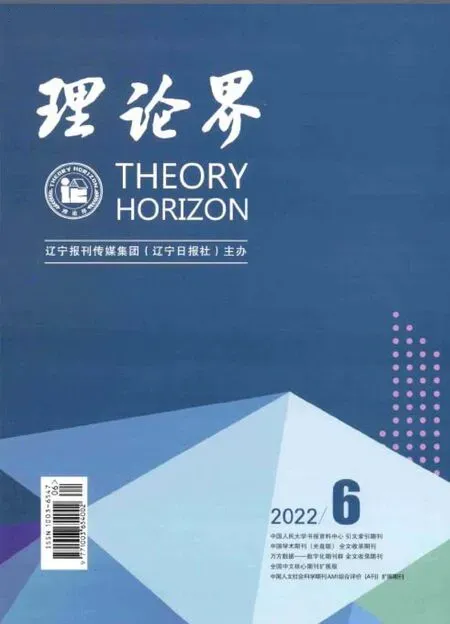试论《礼记》中的情—礼关系
邓 青
情—礼关系在儒家哲学中是一个基本论题。其中,情关涉儒家对于人之性情的理解,而礼则指向伦理规范与政治秩序的建构;两者构成的文质、本末关系,说明儒家的伦理—政治秩序是以人的内在性情为基础与始源构建起来的,同时也以情感陶冶、气质变化、德性进修为归宿,从而礼制乃成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教化成德之道,而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刑政统御之术(《论语·为政》)。质言之,此论题旨在阐明礼制的根据、起源及合理性,同时也涉及礼教在人心中的铺展与内化,干系甚大。
孔子并举仁、礼,是对此论题的发端回答。孔子之教重“直道而行”,而以“诈”与“隐”为耻,如曰:“今之愚也诈而已矣。”(《阳货》)又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述而》)所谓“直”者,为纯天机的开张,真性情的流淌,而并无一毫私曲邪诈介乎思虑动作之间。故其言“仁”,以孝悌、亲亲之爱为先,首出乎血亲之间的天然情感。本诸此情而泛爱博施,则“仁”不远而自至。此为孔子重情一面。然而,孔子亦言“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朴质本真的情气发动须辅之以礼而为之节文。此为孔子重礼一面。
就情礼两者之本末而言,礼以内在的真诚情意为根基,情以见诸物事的礼器、礼节等为文饰,故孔子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阳货》)又云:“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即言礼非徒饰虚文,而必以内心之诚为其本实。如以丧礼为例,孔子以为三年之丧制乃出乎子女对父母的哀戚与不安(《阳货》)。“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丧致乎哀而止”(《子张》),内在的哀戚之情是为“礼之本”;而衣衾棺椁之礼器、哭踊祭奠之礼节之类,孔子亦未全然否弃。故礼贵得不奢不俭之中,使其内外相协、本末兼尽。
以上为孔子论情礼之大较。要之,孔子之说贴切于个人平常践履,以为礼文履行须以真情动发为本,行则从容中规,内则温良笃厚,表里一体,遂达于成德之鹄的。孔子本人便是动情履礼、即心即道的至圣楷模,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者。其言约旨远,以身行为世范,而于精细之思辨不甚着力。而《礼记》所载之记说,则在孔子所提挈的纲领之下,对情礼二者及其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现象探析和更详密的义理发挥,这主要体现于两点:其一,对人情的体察趋于细致,在情之来源、样态等方面皆有阐发;其二,立足于人情的疏导与裁成,论说礼制的起源、本质、功用等,揭示出礼制与礼教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下文即以《礼记》为主、并适当参酌《五行》等郭店楚简儒书相关篇章,稍为详述儒家的情礼论题及此中内蕴的哲学精神。
一、何谓人情
《礼记·礼运》言:“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1〕此回答给出了作为人情表现的七种样态,且指明此七情乃人所本具、不待修习的天然素质与能力。该篇又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2〕孙希旦以为:“情虽有七,而喜也、爱也,皆欲之别也;怒也、哀也、惧也,皆恶之别也。故情七而欲恶可以该之。”〔3〕即言七情可化约为欲、恶这相对的两端;反推之,欲与恶作为基本情感,衍生了其他各种具体情绪。
欲恶即好恶,《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4〕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亦言:“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5〕学者于此区分人性的潜伏与发见状态,以为:喜怒哀悲之气指好恶的内在倾向,而好恶的具体活动则是人性面对事物之感动而生发的当下反应,是人性内容的生动呈露。〔6〕所谓内在倾向或“天之性”,乃一种天赋素质;以之为静,则强调其为人生而禀有,赋命于天之本源。及其感于事物而引起活动,则生发、形见出各种欲求与情绪,如好恶、喜怒哀悲等心理。进言之,情之好恶悲喜实则导源于欲之得或不得,故情即“性之欲”。这是人性活动的一面,呈现为好恶之情,并具体展开为现实生命的原初生存活动,构成生命的基本存在样态。
以情说性或以气说性,并以此开拓人的心灵世界,体现了儒家重视生命情感和现世人生的基本精神。但仅以好恶之情说性,着实将性之含义狭隘化了。这和宋明理学将《中庸》“天命之谓性”一句解释为天命赋予人以纯善之性,是同样的“失误”,尽管其自有理据。实际上,在先秦天命人继的架构中,性为天所降命于人之生命全体,近乎告子“生之谓性”的含义,如《乐记》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7〕此便明言性统括了人的血气和心知。因此,性不只是归属于血气的情欲,也不单指至善的良知良能,而是生命之全具质素。感性的情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虽说它构成了生命的底色,成为生命得以表达自身的基本形式,但它自身并非尽善尽美。唯当人性中其他能力要素(如属于心知的智性或理性)参与到情感的形塑与培植中来,人的德性生命才能够趋向完满。
总而言之,情乃人心感应外物而生发的各种心理情感的集合,欲作为情之发源,析而为好恶或欲恶,再可分别为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等等。人情万端,心术非一。对于古代的礼制、礼仪来说,人内中生发而诚悫无伪的爱、敬、哀、乐等情感具有根本重要性。倘若没有真情实感作为基础,礼之制定践履便失却了意义。
二、礼“顺人情”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言:“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8〕此情乃真情的发动,而非虚伪狡诈之情。真情相感,则不待言语造作而相信。礼即发源、因顺于此原初本真的情感,故《语丛一》云:“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者也。”〔9〕《语丛二》亦云:“情生于性,礼生于情。”〔10〕《五行》则曰:“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11〕一般认为,礼原本是规范言行的方圆规矩,见诸人之动容周旋,而内心不可能行礼。“礼形于内”的说法则欲指明,礼不单是一种善行,而更应有内在的笃实充沛之情感作为支撑。内外配合,善行方才进阶为德行。如是行之由之,方为“君子道”。
如上诸篇注目于人之内心世界的开掘,发扬了孔子之师说,并与《礼记》相辉映。《礼器》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12〕孔颖达谓:“忠者内尽于心也,信者外不欺于物也。”〔13〕忠信意谓人不自欺,亦不欺物,如实对待内中情感,并将之诚实且充沛地表达出来。这成为制礼、学礼与行礼的根本与基础,故《乐记》亦言:“著诚去伪,礼之经也。”〔14〕倘若动容造作皆是巧诈伪饰,而无内在真实情感的维系,那么人事便终成浮幻,而礼亦沦落为空洞的形式与外在的强制。《曾子问》曰“君子礼以饰情”,〔15〕即言内有至敬哀痛之质,则一定的礼仪方可附丽于情而成为情之华彩文饰;且又有以兴发感动其情志,使之充沛饱满而得畅遂,由之增加个人的生命情感体验与人际的和谐圆融。能如此,礼便不为无情实的赘行与牵累。
因为内具人之诚意与真情,礼仪、礼会、礼文之发作便不再为虚而有可敬可信之实。此内在之实,若从人的天然质性来说,也便是仁(爱)。《丧服四制》曰:“仁者可以观其爱焉。”〔16〕仁首先便落实为爱人,特别是爱亲人之情,这贯彻了孔子的“仁”说。此情乃人道之端本,是礼制所凭依的情感基础。《大传》曰:“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17〕于一人而言,与自己血统最近、恩泽最深的乃父母(与之相对的则是子女);自然,人对于双亲的爱最为深厚。上推至祖先,下延及孙辈,血统愈淡远,亲情愈轻薄。根据血缘之远近、亲情之厚薄,古人方才制定丧服轻重之礼。
父母祖先对子孙的仁恩慈爱深厚广远,所以孝子孝孙对父母祖先“生则敬养,死则敬享”,具体而言:父母生时,孝子出乎深爱厚敬,“亨、孰、羶、芗,尝而荐之”以养父母;“先意承志”而待父母以“和气”“愉色”“婉容”;号泣随之而谏,“以谕父母于道”;及乎父母之丧没,此至深之爱便化为最浓重的悲哀,如《杂记下》县子所言“三年之丧如斩”,其时为子之心乃痛似刀斩。儿女悼念思求之深,遂至于有终身之丧、终身之忧,每逢父母忌日既不娱乐,亦不用事。《祭义》云: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声不绝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爱则存,致悫则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18〕
祭者在祭祀之前,经由散斋、致斋整齐思虑,存想所斋者的形象,遂至于志意恍惚,而所祭者直如神明降临,音容宛在,祭祀也就成为“与神明交”之过程,恭敬挚诚,肃肃雍雍。此是孝敬之心达于极致,如《祭义》所言:“孝子之祭也,尽其悫而悫焉,尽其信而信焉,尽其敬而敬焉,尽其礼而不过失焉。”〔19〕在此孝享之中,混合着哀乐的情绪,《祭义》云:“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20〕神灵降临而能享用祭品,祭者感到欢喜;而飨祭之后神灵又将离去,哀戚便生发于心。
此一时之哀乐并出于孝子孝孙对父母祖先始终如一的爱敬,而此爱敬之心的根源在于人始终无法忘怀自身所由来之处,且思以报答之,故《祭义》云:“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敬也。”〔21〕礼(尤其是葬礼、祭礼)的制定和践行,便依托人的这种天然情感或心理。在孔子看来,原始时代的先民即使生存艰苦,资财简陋,亦要致敬鬼神;只此“敬”心便是礼的起源。后来生存境遇得到改善,人们依然准备各种器物“以事鬼神上帝”。从“礼之初”到“礼之大成”,器物由寡少而盛美,然而先民行礼之初心却未改易——此初心便是致敬鬼神上帝。〔22〕其因无他,乃在于鬼神上帝为人所从出之本源:我生自父母,父母生自祖先,祖先死而为鬼神;推而上之,众生、鬼神莫不源出于天地,而天地乃本于太一或上帝(或曰天)。
通过礼仪的演习与施行,人报本反始的心理与情感得以表达,故《乐记》曰:“礼自外作,故文。”〔23〕礼仪这种文饰性的外表姿态与兴作,又有以反作用于人之内心,培厚人的内在情感,由此而对之施行教化。据《祭义》的相关论述,众生死而化为鬼神:骨肉归土,下化为魄;精气发扬于上,是为魂神。鬼神之名使万民产生敬服与畏惧,然则:
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二端既立,报以二礼……教民相爱,上下用情,礼之至也。〔24〕
礼之极致,在于教民相爱,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出之渊源而内尽其情;如此履礼便成为一种仁的教化方式,即在践行祀神之礼的过程中,民众的报恩、仁爱、敬畏、服从等情感得以深化。《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25〕人效法天之四时变化而作息,取资于大地之物财而生存,所以先王制定郊天祀社之礼以报答天地的馈赠,目的在于教化“天民”报本反始,终归于民心之笃厚。
这也意味着,尽管情感之发动是一种自然事实,但通过礼的教化来催发人心民情仍属必要。《檀弓下》中子游言及礼“有以故兴物者”,孙希旦谓:
以故兴物,若荀卿言“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食,所以使之睹物思哀,而不至于怠而忘之也”。〔26〕
这是说,借由礼仪之中的各种器事安排,人的真情实意得以感动兴发,由此固结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浸润人之心地,使之温良朴厚。礼仪、礼器背后蕴含着情感的本质要求,在礼的履行之中,“不肖者”之情得以企而及之,遂不至于怠忽忘恩。
综上所论,人之诚意与真情乃是礼得以制定和践履的内在要素与基本要求,否则礼便失去其实质。人的爱、敬、哀、乐等情感,尤其显著地发见于孝养、丧祭之礼中。一旦情不真、意不诚,那么作为情之发、仁之末的礼便沦落为外在的、虚伪的文饰,随之对礼仪的践履也仅是徒具其表地循规蹈矩而已,不能够作用于人之内心,以培固人的道德情感、启发人的道德意识。
要之,真正的礼发源于人之真情,同时亦表现情、文饰情,又还以培植情。人通过情与外物产生感应与联系,此乃基本的生命情实;礼唯有随顺之,而不能与之违拗。故《礼运》以礼义为“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27〕《丧服四制》亦云:“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28〕言礼虽可上达天之经、地之义,然其切实的铺展与发用,则在乎“顺人情”而已。
三、礼“治人之情”
如《礼运》所言,礼义有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29〕这已揭示出礼并不仅是顺人情而已,而含有约束规范之意。《礼运》亦言:“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30〕孙希旦谓:“治人之情者,示以一定之仪则。”〔31〕即言礼将人情纳入一定轨则之中,如此礼便非任人直情径行、率意而为。此点在有子与子游的辩说中显发出来,《檀弓下》载:
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品节斯,斯之谓礼。”〔32〕
有子以为丧礼若表达出孝子孝孙之哀情便足,如同孺子直率其号慕迫切之真情,而不须立“踊”(顿足)这一夸张的礼规;子游则以为,有子主张的直情径行乃戎狄之道。子游亦不否定情,然则主张礼乃品节人情,对此孙希旦解释道:
然情不可以径行,故先王因人情而立制,为之品而使之有等级,为之节而使之有裁限,故情得其所止而不过,是乃所谓礼也。〔33〕
此品节、裁制即“微情”,“所以使之杀其情而不至于过哀也”。〔34〕具体就哭踊之礼规而言,丧礼中的抚心顿足具有一定次数,以防生者因哀毁而伤性。此即所谓“毁不危身”者。
《檀弓上》记载子路为其姊服丧,因为亲情深厚而不忍除服,然而孔子以为先王制礼之本意正在于使人节制其哀戚而“顺变”。〔35〕“顺”意谓不矫揉、不造作,那么此“顺变”,既指生者当顺应亲人离世而造成的生活巨变,亦指生者应顺承其哀戚之情的流变衰减。因之,礼对人情之品节并非强行阻遏人情流露,反倒有以体察人情自身发作变化的节限。如前所论,亲亲有杀,由父母上至祖先,由子女下及孙辈,由亲生同胞旁及从兄弟、从姐妹,血缘渐远而亲情递减,因而丧服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之等,丧期有三年、期、九月、七月、五月、三月之别。即便对于父母之丧,在整个服丧期间,子女的哀情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退。顺应着情感的自然节度,故丧礼立有变服、除服之渐。人情本身具有自然之节次,礼乃承顺情之节次以治情;就此而论,“治人之情”与“顺人情”并不相矛盾,因而可说是顺人情而治之。
在整个时间过程中,情有自然的增减,礼制亦相应地随之变革。然而,当人猝临变故如丧亲失友之时,其情绪变动毕竟有过或不及。《檀弓上》曰:
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36〕
先王制定礼的标准,在于节制人的过盛之情,又有以兴发人的不足之心;要之,各种礼节的意义就在于使人情之发动达乎合宜适当的状态,《礼运》言:
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37〕
此将“人情”喻为田地,而礼义则为耕种之器械,用意无非在于形著礼“治人情”之义。人遭遇事物及其剧变,情欲之发动每每有过或不及;礼便依托情并裁制之,目的在于使情合宜适当而归于“义”。“义”乃礼之实质,礼乃“义”之形式表现,为“义”所结之果。“义”乃“仁之节”,即爱心亲疏厚薄之适当;“义”还指“艺之分”,即行事大小轻重之宜。总之,内发情感与外在事物若皆能处于适宜的状态,便是“义”。
万事、万物、万情皆合于“义”,则有“序”;典礼之行的目的正在于秩序之实现。所谓“序”,意指每一事物所处的角色、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等级与秩序,如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各有其名位,并各有其分异的制度与典礼规模,据之而各安其次。《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38〕“序”体现了万物所处所存之地位、角色的种种分别,如尊卑、上下、贵贱、男女等等。礼便效仿天地万物的自然秩序(所谓天经地义)而制作,故可说礼体现并强化了万物等位之“别”。
宏观地看,作为人道之礼的最高意义在于:名分相别的人各依其位、各行其道,由此形成的和谐人伦是天地秩序的投影。因之,天地秩序与人伦秩序皆建立在差别(“别”)和等级(“序”)的基础上。自微妙处言之,礼所要求的差别与等级端赖于人之内心情感加以维系。这种特殊的心理情感便是“敬”,楚简《五行》将此情释作:“以其外心与人交,远也。”〔39〕心远、见外而不亵狎,是为“敬”。敬心形于外而成乎礼的过程则为:“不远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尊,不尊不恭,不恭无礼。”〔40〕
“敬”作为情之异端表现在两点:其一,唯有在“别”之前提下,“敬”方才得以发于人心:如男女有别,两者方能相敬而不亵玩;上下有别,下方能敬上,臣民方能敬君,而不相僭越。不同于人之亲爱努力拉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距离,“敬”反倒推开距离以保持彼此之间的差异(即“别”)。礼重名分之“别”,因之亦主远心之“敬”。其二,“敬”之情可以有效地克制甚至涤除人之嗜欲,从而将人之情欲限定于适宜分限之内,由此维持事物之“别”,《郊特牲》曰:
笾、豆荐之,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义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荐,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车,可陈也,而不可好也。《武》,壮而不可乐也。宗庙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庙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以同于所安乐之义也。〔41〕
献于神明之物不同于世俗所惯用便利之物,这是因为天地神明“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42〕故而着重于在人之内心致其诚敬而已。人间的事物永远不能与创造它的事物相称,万物注定无法匹配于天地神明。人与天地神明之间存在不可逾越之“别”,产生人对天地神明最高的“敬”,此“敬”超出了物欲私利的范围。同样,人对于异性、尊长等对象之“敬”,也是一种斥逐了爱恶私欲的情感。由此论之,“敬”是越于一般情欲之上的高级情感,因其有以遏止甚至荡涤人之私心乱情,故特为礼所重视。“敬”情的培养与生发,构成礼“治人之情”的主要方式,因此,也是修身的首要门径与工夫。细味之,培养“敬”情以“治人之情”的方式颇为高妙,因为它是以情治情,其间含有“顺人情”之意,而不纯粹依靠外在的礼仪礼规对人情进行限制。
质言之,“敬”意味着人于内在心理上意识到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与等级,并予以承可;相应地,启发人之“敬”情可以外在的、等级化的、别异化的礼仪礼规为辅助方式。概括地说,礼要通过强调天地之序、人伦之别而深入人对“别”与“序”的认识,如尊卑、男女之别等等。具体而言,如《王制》篇所云,自天子贯于庶人,在爵禄、服制、祭祀等方面皆有不同的等第与规模,天子最尊,逐次递减,等级之间不可僭越。这种严格的等级差异性可以较为强力地抑制个人无限的热情与欲望,从而构建起稳定的伦理—政治秩序。在伦理—政治性的礼秩礼序中,人绝不能肆意地将自己的情欲宣发于外,即便情感是真诚的、善意的。举例言之,凡人对于天皆怀有最高的崇敬之情,然而只有天子才能郊天。
综上所论,就礼的道德意义而言,礼治理人情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人情之发动处于合理适宜的程度;简言之,礼使情止于“义”。借助礼义之规定,人情发动之过盛者有以自我节制,不至于伤及现实人生之幸福;而人情之不足者亦可以在礼仪礼规的践行中培养内在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从而使其心其德归于淳厚仁慈。
就礼的伦理—政治意义而言,礼乃国家的伦理—政治制度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礼仪的安排划分使人安止于各自分位,由此强化人的差别与等级,进而构建起稳定的伦理—政治秩序。在此意义上,礼治人之情意味着通过种种严格的礼制礼规遏止人的私欲乱情,使之不相僭越;但这样的礼并非完全沦落为钳制人情的暴力工具或僵化教条,因为其间以内在的诚“敬”之情作为支撑。内在的诚敬与外在的礼规相互配合,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便可牢固建立;再加以个人道德意识与品质的完善,“小康”便能达致。《礼运》将“礼义以为纪”归于“小康”,正此之谓。
四、结语
由上所论,礼顺人情意味着礼之制定与践履须以人之诚意与真情为基础,因此可以说礼本于仁,或者说礼发乎情;然则人情之动每有过与不及,过则伤人伤己,不及则情味浇薄,故须以礼治人之情,或节制之,或兴发之,终使之归于合宜适中,并基于此建立稳定和谐的秩序。礼对于人情的治理与安排,体现出人的理智对于自身情感的顺应和控制。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礼是人对情欲的一种理性安排,《檀弓上》述孔子之言曰:
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43〕
对此,冯友兰先生论云:
专从理智之观点待死者,断其无知,则为不仁。专从情感之观点待死者,断其有知,则为不智。折衷于二者,为死者“备物而不可用”。为之“备物”者,冀其能用,所以副吾人情感之期望也。“不可用”者,吾人理智明知死者之不能用之也。〔44〕
理智之观点,乃以为人死不可复生,死后是否化为鬼魂亦难知晓;而以凡人之情感论,则又希望死者泉下有知,如同在生之时。理智依凭经验事实,而情感则附着人之想象与期望。既然理智与情感不可偏废,皆为人生在世之情实,那么孔子认为对待死者的“可为”方式在于:理智上虽承认死者确已死去,但在充沛的情感之中,依然觉得死者宛然若存。情感的充沛可以使生者自尽其哀毁之心而得到安慰,而理智上的承认与接受又使得生者不必铺张送死,而能自制其哀。
此一小例说明礼之制作必然兼顾人之理智与情感,礼也便成为既仁且智之人道。前已论及,人性为血气心知之全具,感性之情处其一,理性之智又处其一。礼则循此两者而制作:礼发乎情,本诸仁,是为礼顺人情;礼又止乎义,依于智,是为礼治人情。此便是礼制与礼教的起源、本质与功用所在,即“礼义”所在。此中表明儒家特重本真之情,体现其入世情怀与现实格调;然而出于对理想的生命情态、人伦秩序、政治秩序与天地秩序之追求,而亦表现出理性的修习与克治。两者不可偏废,盖皆出于人性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