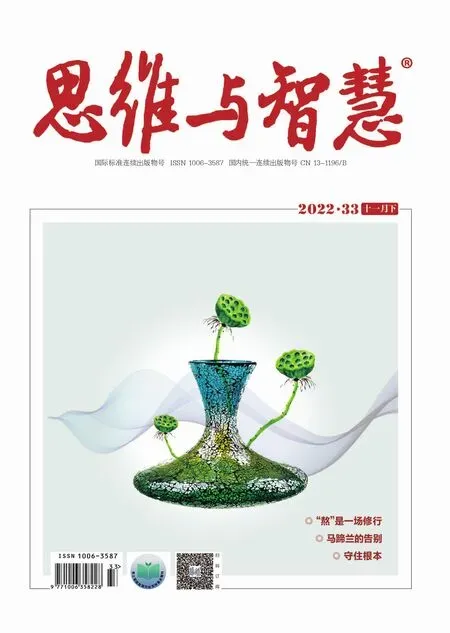思念爬上篱笆
◎ 刘玺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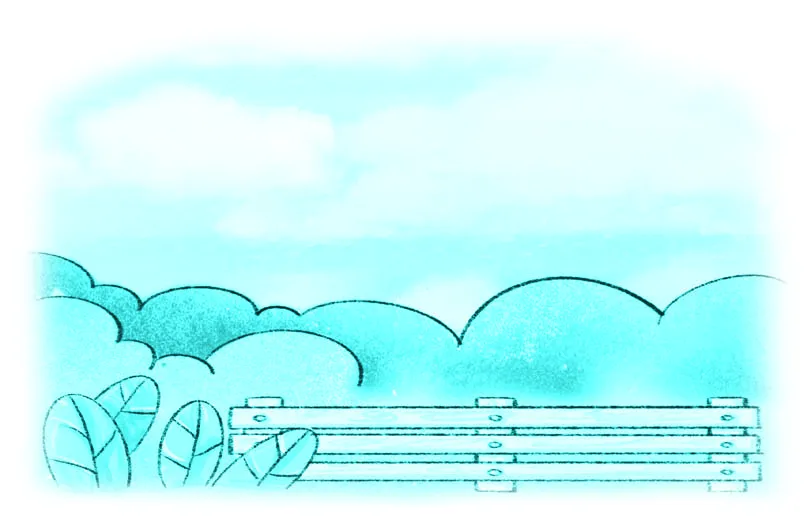
常言道:“什么谷子脱什么米,什么娘生什么女。”可到我和我娘身上,这句话便是空谈。
我娘勤劳能干,家里、地里的活儿,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到我身上就不行了。我念书识字后,觉得自己大可以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来形容。
娘有一个小菜园。里面的菜究竟有多少种,我没数过,反正想吃啥,饭桌上就会有啥:丝瓜、豆角、黄瓜、西红柿、辣椒、韭菜……整个菜园包括边边角角,到处都挤着这样或那样的蔬菜。就连四周的篱笆娘也不放过,上面曲曲弯弯,爬满了绿色、紫色的扁豆角,那豆角在风里摇着小手,如一枚枚弯月。牵牛花也赶来凑热闹,它们缠绕着,努力地擎着身子,吹出一个个小喇叭。
人勤地不懒。娘种的菜都是见风长,一棵棵,一簇簇,绿汪汪、水灵灵的。春夏时,菜多得吃不完,娘就摘了它们送给亲戚、邻居。收到菜的人都很高兴,娘也高兴,整天乐呵呵的。
一有空,娘就忙碌在她的小菜园里。那菜园晨有露,冬有雪,阴有雨,夏有风。那里有她的汗水,还有她的欢喜。
一个中午,蝉在绿荫里噪鸣,我正躺在炕上午睡。下地前,娘嘱咐我:傍晚给菜园里的茄子施点儿化肥。我含糊地应着,翻了个身就又睡去了。疯玩了一下午后,忽然想起菜园施肥的事儿,便抓着化肥袋子,迅速向菜园里跑去。
做晚饭时,娘从地里回来,嗔怪道:“这个孩子!瞧你干的好事儿。”扭身就拿着铁锨,往菜园子的方向走去。我疾跑着去看,不由得大吃一惊,我在每一棵茄子的根部都施了化肥,可能是离得太近,茄秧子受不住,从下到上,很多叶子竟然都被化肥烧得干枯、焦黄。尽管娘及时给菜畦浇水做了补救,茄子还是因此元气大伤,一直耷拉着脑袋,不愿意长。很久以后,茄子才缓过劲儿来,蹿出新芽。
这件事虽已过去多年,但我仍记忆犹新,偶尔回忆,时常为自己的愚笨懊悔。想想这许多年,娘对我这个“傻”孩子从来没有嫌弃过,对待我就像对待菜园里的菜一样,细细耕耘,默默守候,温暖陪伴,数十年如一日,给了我无限的爱。
今天早晨,我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位老人守着菜摊。那菜摊明显是临时摆的,破旧的三轮车上,不多几样菜,一捆捆摆放很整齐。那菜绿汪汪、水灵灵的。看着看着,我就想起了娘,想起了娘的菜园子。
本来已经走过菜摊了,我却在无意中看到老人踱了几步。我注意到,他腿瘸了。我扭头朝他望去,他那满是褶皱的脸上写满了风霜。他可能70岁或是80岁,他的家里可能还有一个同样上了年纪的老伴儿,等着他卖完菜回家,他可能也有一个小菜园,跟我娘的菜园一样。
我的手赶紧伸进兜里找钱,还好,有钱。我知道,现在许多卖菜的老人没有微信,不能手机支付。我买了两捆青菜,夸青菜品质好,他咧开缺了门牙的嘴笑了。
望着这两捆菜,我在心里想着它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播种、发芽、抽茎、展叶的过程,每当晨曦初露或夜幕四合的时候,老人又是怎样躬身忙碌于菜园,除草、施肥、浇水、捉虫,精心打理。他可能对待每一棵菜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没有过一点儿不耐烦。多温馨的画面!只是我,故乡已远,亲人也早已不在了。
多想有一个小菜园。那菜园晨有露,冬有雪,阴有雨,夏有风。菜园的篱笆上,曲曲弯弯,爬满了一个女儿所有的思念。
(谁与争锋摘自《春城晚报》2022年6月24日 图/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