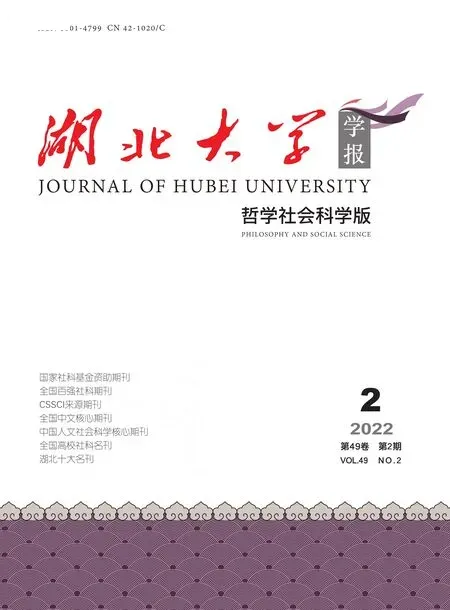“在两界来回的人”:丽塔·达夫《母爱》对“冥后”神话故事原型的改写
曾 巍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暨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丽塔·达夫(Rita Dove),1952年生,是目前依然活跃于美国诗坛的非裔女诗人,其作品曾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她还于1993年、1995年两度当选美国桂冠诗人(1)达夫的文学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出版诗集《街角的黄房子》(The Yellow House on the Corner,1980)、《博物馆》(Museum,1983)、《托马斯与比尤拉》(Thomas and Beulah,1986)、《花音》(Grace Notes,1989)、《母爱》(Mother Love,1995)、《与罗莎·帕克斯坐巴士》(On the Bus with Rosa Parks,1999)、《美式狐步》(American Smooth,2004)、《穆拉提克奏鸣曲》(Sonata Mulattica,2009),短篇小说集《第五个星期天》(Fifth Sunday,1985),小说《穿过象牙门》(Through the Ivory Gate,1992),戏剧《地球较暗的脸》(The Darker Face of the Earth,1996)等。她曾于2015年访问中国,领取“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目前国内只出版过一本达夫诗歌的选集《骑马穿过发光的树:丽塔·达夫诗选》,宋子江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达夫的诗作,将神话、历史与个人经验巧妙地融合,同时广泛吸收美术、音乐、舞蹈等其他艺术形式的丰富资源,生动展现了黑人女性诗人观察当代生活的独特视角,以及思考性别问题、种族问题、文化问题、人类命运问题的广度与深度。在她的作品中,《母爱》(MotherLove)(2)Rita Dove,Mother Love:Poem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95.在《骑马穿过发光的树:丽塔·达夫诗选》中选译了其中的10首。本文中涉及的诗歌译文,均由笔者自译。凡涉及诗歌原文引用,一律在诗后注明诗题及诗行。是一部主题集中、构思精巧,具有鲜明特质的诗集。整部诗集由35首诗组成,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形式感很强的十四行诗,或者由多个十四行诗节构成的诗作。在类似于“前言”的短文《完整的世界》(“An Intact World”)中,达夫意味深长地复述了一则古希腊神话,那就是冥王哈得斯(Hades)掳走农神得墨忒耳(Demeter)之女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并强娶之为冥后的故事。而集子中的诗,一些直接将故事中的三个主要角色纳入诗题,一些则移用了神话中的人物与情节。就整体而言,35首诗的编排顺序,暗含了一条情感线索,也和神话故事的情节发展吻合。虽然诗集中的许多诗融入了创作者的个人经验和现实生活轨迹,但这显然是诗人的写作策略所欲呈现的丰富性和现代性。毋宁说,诗集《母爱》在整体构思上,是对希腊神话中冥后故事的改写。我们感兴趣的,正是通过将具体的现代文本与远古故事原型进行比较与互文性解读,发掘当代文本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改写,并进而产生出全新的意义和价值。
一、地上/地下:生冥两界的穿行
诗集《母爱》诗歌文本中的种种迹象,表明了和古希腊“冥后”神话的“脐带式”关联。用神话学的术语来说,“冥后”神话是神话原型,诗集《母爱》则是神话的移位,在诗集的深层结构中嵌有神话的母题、模式或功能;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冥后”神话是“源文”、是“现象文本”,而诗集《母爱》则是“异文”或“仿文”、是“生成文本”,两者之间构成“对话”关系。两个文本之间的关联,不仅表现为叙事结构上的相似,也体现在文本内部,诸种要素如语言、形象、情节等也彼此关联,仿文的生成过程,也就成为“从一个意指系统向另一个意指系统的转换”(3)Julia Kristeva,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trans. Margaret Walk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60.,从而构成“由引语、指涉、回应、先前和当代的文化语言编织而成”(4)Roland Barthes,Image—Music—Text,trans. Stephon Heath,London:Fontana Press,1977,p.159.的开放式网络系统。反过来,对仿文的阅读,也会引起对源文的记忆,召唤它共同参与意义的建构。可以看出,“冥后”神话与诗集《母爱》,构成了一种“图—底”结构关系:“当下的、现实的文本存在(戏仿文本)就是它的‘前景’,即‘图’;历史的、被幻化为记忆的源文本就是它的‘远景’,即‘底’。”(5)赵宪章:《超文性戏仿文体解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那么,对诗集《母爱》的分析,就不能仅仅停留于单一的语言平面上,而应由仿文中的线索探入历史和文化的纵深,追索原型与“源文”,并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冥后”神话最早的文字记载,出自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Hesoid)的《神谱》(Theogony):“宙斯也和丰产的德墨特尔同床共枕,生下白臂女神珀耳塞福涅;哈德斯把她从其母身旁带走,英明的宙斯将她许配了他。”(6)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2页。原文中的三行,交代了德墨忒耳、珀耳塞福涅、哈德斯的关系,以及三者在神的谱系中的位置。公元前7世纪的《德墨忒耳的荷马式赞歌》(HomericHymntoDemeter),故事情节要丰满得多,更多的笔墨集中在德墨忒耳,讲述了大地母亲神在失去女儿后如何四处寻找她并在寻亲过程中创立了宗教密仪的故事(7)参见Helene P. Foley ed.,The Homeric Hymn to Demeter:Translation,Commentary,and Interpretive Essay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2-27.。关于这一故事的记载流传最广的,来自于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其中第五卷叙述了这个故事,只不过神祇的称谓换作了她们的罗马名字——刻瑞斯(Ceres)、普洛塞庇娜(Proserpina)、普路托(Pluto),分别对应德墨忒耳、珀耳塞福涅与哈德斯。相对而言,这个版本中的细节比较丰富:冥王因为中了爱神之箭,爱上了正在西西里岛的野外采花的普洛塞庇娜,并强行将其掳走立为冥后。刻瑞斯发现女儿失踪,遍寻大地无果,于是去往天庭询问天神朱庇特(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朱庇特答应如果普洛塞庇娜未尝地府之食即可回到母亲身边,可是她却因为吞食了地府的石榴无法如愿。最后,朱庇特给出了折中的办法:将一年分为两半,春暖花开时节普洛塞庇娜回到大地和母亲在一起,而万物萧瑟时则去到地下陪伴冥王(8)参见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97-103页。。天神的裁决让普洛塞庇娜(珀耳塞福涅)必须每年在生冥两界间穿行,这个故事也成为了对大自然季节更替的神话解释。
如果以珀耳塞福涅为中心,上面的故事可以梳理出比较清晰的发展线索:三个主要神话人物,她们之间是通过珀耳塞福涅联系起来的,随着故事的进程,彼此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考虑到这个故事随着珀耳塞福涅的复归呈现出循环结构,她们的关系也会相应回到起点重复演绎。珀耳塞福涅在两界的穿行,可以分别由冥王的劫持与宙斯的裁决为界,分割为两段行程,按凯勒(Keller)的说法是一个“双向旅行”,是“灵魂穿过生与穿过死亡的旅行”;在这样的旅行中,徳墨忒耳与珀耳塞福涅母女,经历了“从最初的亲情的欢乐,经过一段分离与痛苦的时期,最后是团聚的喜悦”的过程(9)Mara Lynn Keller,“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of Demeter and Persephone:Fertility,Sexuality,and Rebirth”,Journal of Feminist Studies in Religion,Vol.4,No.1,1988.。依照神话的演绎,母女久别重逢也让其情感纽带仿如当初,直到冥王再次现身将她们拖入宿命的循环旅行之中。显然,提纲挈领式的抽绎有助于“找出故事讲述的法则,并通过这种叙事法则,构建出具有普遍性的故事模型”(10)陈建宪:《元故事的构拟与激活——从民间叙事法则到“好莱坞圣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从而找到仿文与源文共同的深层结构。但我们也同样要注意到这一“循环模式”中的重要转捩点,尤其是冥王的强力介入,他与珀耳塞福涅建立了婚姻关系,这也必将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影响母女关系,进而导致看似圆满的循环不一定能够回到原点。这也是达夫在神话改写中所遵循的思路:“徳墨忒耳/珀耳塞福涅之间的情感背叛与情感重建的循环十分适合于这个结构,这三者——母亲—女神、女儿—伴侣、诗人都在这条发展线索中奋力歌唱。”(11)Rita Dove,Mother Love:Poems,p.2.因此,对《母爱》这部作品,不妨先聚焦其与故事原型的同构关系,再关注其中变化的因素以发掘仿文的意义生成。
诗集《母爱》共收录诗歌35首,达夫将其明确划分为7个部分,每个部分诗歌数量不一。第一部分只有题为《英雄》(“Heroes”)的诗1首,以一个男性人物的摘花事件切入主题,可以看作整部诗集的“引子”。第二部分有诗12首,从数量上看,应是诗集的重点。这些诗,在简要勾勒一个少女的童年生活后,马上聚焦于神话的中心事件:冥王劫持珀耳塞福涅。故事在《珀耳塞福涅的坠落》(“Persephone,Falling”)、《水仙花》(“The Narcissus Flower”)、《被劫持的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 Abducted”)中均有复述,而《寻人》(“The Search”)、《保护》(“Protection”)、《母爱》(“Mother Love”)则将目光投向了失去女儿的母亲,渲染她的悲愁与痛苦。第三部分是一首长诗,标题《冥府里的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 in Hell”)即挑明将描述冥后的地下生活。第四部分有诗4首,此时冥王占据了一定篇幅,主要书写成为冥后的珀耳塞福涅与哈德斯在地下的二人世界。第五部分的7首诗,则由“向下的旅行”掉头向上,珀耳塞福涅找到了“出口”(“Exit”),回到了“野外”(“Afield”),与母亲团聚。至此,一个完整的循环已经完成。可是,达夫还在其后增加了由9首诗组成的第六部分和一首长诗单独构成的第七部分。这里,故事中的三个主角不仅同时出场并构成对话,《德墨忒耳对冥王的祈求》(“Demeter’s Prayer to Hades”)中冥后的母亲与丈夫甚至直接互动,体现出更明显的想象性创造,而长诗《伊人之岛》(“Her Island”)讲述诗人与丈夫同游西西里岛的故事,并将“冥后”神话穿插于自传叙事之中。可见,这两个部分既内嵌于循环结构之中,又在一定程度上跳脱于神话模式之外,是对主题的进一步升华。通过梳理诗集的编排顺序可以发现,《母爱》展现了一个完整的叙事,其发展线索与“冥后”神话是对应的,神话故事“提供了结构上的一致性,每个部分所包含的诗则具有内部的张力”,达夫不仅通过诗的分列、梳理满足了读者对秩序的期待,同时,她也在总体结构的主干上丰富了细节,甚至进行了大胆改编,从而“拓宽了我们的视域,让我们去发现超越边界之外的一致性与关联性”(12)Lotta Lofgren,“Partial Horror:Fragmentation and Healing in Rita Dove’s Mother Love”,Callaloo,Vol.19,No.1,1996.。
珀耳塞福涅的双向旅行,两个端点分别是“地上”与“地下”,在这两处,分别有一个陪伴者,即徳墨忒耳与哈德斯,“地上生活”与“地下生活”也分别对应着母女关系与夫妻关系。达夫在诗歌《失踪》(“Missing”)中曾模仿了珀耳塞福涅的独白,承认“我就是和姑娘们一起出去的女儿,/再也没回来,也没有什么标记出我/‘确切的下落’,没有一片闪光的花瓣”(1-3),“让你一直在找。一个/走失的孩子,就是围绕着缺席的强化的事实,/胸口的一个结”(4-6),总之“我就是在两界来回的人。/我就是在空中悬着的足球”(13-14),这表明女儿的内心也一直徘徊于两种力量之间,“地上”或是“地下”的选择让她十分纠结。
在“地上”,母亲给了珀耳塞福涅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德墨忒耳眼中,女儿既是她悉心呵护的生命体,犹如植物,“在花园的每个地方我都看见你的颈子/那细长的藤蔓,倔强的婴儿的卷发”(《保护》,3-4),也如同珍宝,“像打磨过的象牙/高悬而闪耀”(《保护》,7-8);母亲也是女儿的避风港和定心丸,“当我朝母亲跑去,她神采奕奕/像田野尽头的玉米秆等着我,/什么都不重要了:世界还站在那里”(《给长女的礼服》,6-8);母亲也时常叮嘱女儿小心来自外部世界的危险,让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有陷阱/张开,一不小心脚就会陷到地下”(《珀耳塞福涅的坠落》,13-14)。可是,这种相依为命的平静生活还是遭到了外来者的撄犯,冥王“从地心里跳出来/坐着金闪闪的可怖的/马车,他计谋得逞”(《珀耳塞福涅的坠落》,4-6),他“如此坚决,像一把刀子插入//最恭顺的沟罅”(《水仙花》,7-8)。母亲则开始了她的寻女之旅,她“因失去而气炸了”(《寻人》,1),并发誓“我要走遍这失信的大地”,“一直走到//青碧的忘川”(《死亡统计数字:目击者》,13-17),最后“已走遍半球,/从花瓣和阳光中辟出路来/找到适合悲悼的地方”(《胜利者的早餐》,1-3)。在达夫的诗中,地上生活与田野、天空、阳光、植物等明亮的意象关联,主要是为了烘托两代女性之间的骨肉深情,尤其当母亲失去女儿之后,她的失落、焦虑、哀伤等情绪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珀耳塞福涅的“地下”生活是在幽暗、阴森的环境之中,冥府是“暮光之城的石窟”(《冥府里的珀耳塞福涅》,2)。在《冥王的情话》(“Hades’ Pitch”)一诗的描述中,出现了神话中并未展开的细节:珀耳塞福涅被“幽闭在这唯有卑屈的地下”,周围是“暗送秋波的石滴水兽,火舌舔过的绣幔”(9-10);只有冥王与她相处,并赤裸裸地表白,“当我摸到你的脚踝……我就决心向你求爱”(1-4);两人朝夕相处,加上冥王“能说会道,/那些话直抵她的心房”(6-7),也让珀耳塞福涅“暗自有些激动”(5),她的内心里漾起爱情的火苗,开始回应冥王的直视,“去注视这笑容/从眼睛开始/在他的双目/吻过的唇上结束”(《归来》,4-7);珀耳塞福涅接受了成为冥后的命运,并与冥王产生了夫妻之情,这也为她日后回到“地上”之后怀念“地下”生活埋下了伏笔。在《遗失的美好》(“Lost Brilliance”)中,珀耳塞福涅承认自己“怀念那淹没在阴影中的长廊”(1),她认为冥府里的“石柱子也很友善,它们的微光/就像顾盼的眼睛光洁的表面”(7-8),而她也习惯了“地下”的生活,甚至产生了幻觉,认为她的居所是“舒适与幽暗的/混合体”(16-17),仿佛可以代替“地上”生活。每天晚上她会从旋梯上走下来和冥王相会,并称其为“我的伴侣,我的另一半”(24),两人产生了相濡以沫的依恋:“从此永远只有/我们两个:/一个受伤的人,/和一个服侍者”(31-34)。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到,达夫笔下的珀耳塞福涅接受了成为妻子的命运,地上、地下都有她牵挂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当德墨忒耳来到地府,女儿叹息“我失去了/决定的能力”(26-27),选择的两难也决定了她的命运——只能在生冥两界之间来回穿行。
二、神话/现实:虚实二境的交织
冥后的故事,构成了诗集《母爱》的情节发展主线,然而,诗集中的叙事并不仅仅是对神话故事简单僵化的复述,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诗集中的故事叙述者不是固定的,不同诗歌中的“我”有时是珀耳塞福涅,有时是德墨忒耳,有时是独立于神话之外的另一个叙述者,叙事视角的变换会导致对同一情节不同的认知和阐释;其二,神话之外的叙述者还会讲述看似与神话无关的事件,从情节上来看,这些事件的亲历者是“我”,如果将“我”看作诗的创作者本人,诗歌中就植入了诗人的自传成分;其三,如《冥府中的珀耳塞福涅》、《冥河酒馆》(“The Bistro Styx”)、《伊人之岛》等诗中所展现的,虽然诗题都与神话元素有关,但故事却被置于当代环境之中,仿佛是将神话人物请入了现实生活,在新的时空维度开启具有现代性的人生。这些都表明,《母爱》是在用新的方式讲述老故事,是对神话的重新阐释。按照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的说法,“人们在神话中搜寻着不同的美和价值,而在对它们进行有意识的诠释过程中,人们从中提炼出许多种不同的真理”(13)吉尔伯特·海厄特:《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王晨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430页。。叶·莫·梅列金斯基则将这样的创作方式称为“神话化诗艺”,并指出“神话化诗艺不仅负有对叙事进行处理的功用,而且是诉诸源于传统神话的种种对应者对现代社会的情景予以隐喻性描述的手段”(14)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97页。。我们不妨从具体诗作入手,辨指出诗集中的虚构与写实的成分,再分析来自故事原型的要素、对故事原型的改编、对现实世界的状写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以及诗人创造性阐释与改写的用意。
如果将神话元素暂时搁在一边,诗集中可以看出另外一条叙事线索,这是一个女性的个人成长经历,而每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都围绕她和她的母亲展开。叙事的起点设定在她的童年时期,《第一课》(“Primer”)以第一人称回忆了“我”在学校里遭到同学欺负的场景,是及时赶来的母亲平息了冲突,但小女孩并不领情,“我怎么也不愿意坐到车上去。/路再远我也走回家,并发誓/证明给他们所有人看:我会长大的”(12-14)。出现在《给长女的礼服》(“Party Dress for a First Born”)中的则是一个参加聚会的少女,面对男性的搭讪和不怀好意的“一瞥”,她想起母亲的叮嘱,保持着警惕和个人尊严。《寻人》的主角是一个失去女儿的黑人母亲,她心焦意乱,“在常去的沿河路上徘徊”(11),根本不理会他人好奇打量的或歧视的眼光。诗集第二部分的几首诗暗示出,这对母女的情感关系并不简单,在亲情之外,两人之间分明存在隔阂,而“低落、沮丧的语调”也传递出“分离、破裂、疏远的信号”(15)Lotta Lofgren,“Partial Horror:Fragmentation and Healing in Rita Dove’s Mother Love”.,不免让人猜测,女儿将要出走,从母亲的世界抽身离去。
《冥府里的珀耳塞福涅》印证了这种猜测。依诗题提示,这首第一人称叙事诗的讲述者应该是珀耳塞福涅,可是,出现在诗中的主人公却是个孤身闯荡大都市巴黎的黑人姑娘。巴黎被叙述者描绘成一座阴暗、冰冷的城市,塞纳河、圣母院、玛黑区、蓬皮杜中心的文化氛围在冷风中荡然无存,街上仿佛到处是陷阱,昏暗的走廊、地铁的入口等则喻指地狱般的环境。这座城市对姑娘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在诗中数次抱怨听不懂法语,这表明她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外来的“他者”,此时身处另一个世界。这让她想起母亲,她“给我钱,让我每天给家里打电话”(II,6),但又旋即表示“可她并不明白我的感受;/她不需要了解我在做什么”(II,7-8)。可见,母女之间一定存在着情感的裂缝,或者,是渴求独立、摆脱依附关系的叛逆女儿选择了远离“母体”,主动投身于能带给她新奇感、充满吸引力的“异质性”世界。当读者随着姑娘的脚步在巴黎游荡,接着会发现她渴望爱情,似乎有意从街头的偶遇者中寻找意中人:“我就这样等着——他们白皙的眼皮、前额/转向我,欣喜不见踪影”(II,27-28);“或者我是否只等一个人/从人群之中分离出来/勇敢抬起下巴,要把/他果敢的,迷惑的面容/置于我的关注之下”(V,23-28)。也就是说,她离开母亲时,“冥王”并没有出现,她来到这个让她感觉“我不属于这里”(VI,6)的地方,并非因为受到了劫持或诱拐,而是她的主动逃离——也许是对母亲的排斥,让她选择了陌生的世界。
《冥河酒馆》采用了同样的“托名”技巧,珀耳塞福涅式的女儿迎来了德墨忒耳式母亲的探访。酒馆的名称别有意味,既与神话呼应,也以生冥的分界隐喻空间和情感上的区隔。叙述者此时是一个在巴黎小酒馆等待女儿来见面的母亲,她十分关心女儿在异乡的生活,嘘寒问暖,留意她在身形、衣着上的变化。两人的谈话终于涉及了女儿的私生活,这时引出了冥王式的男友。从母亲的疑虑可以看出她是不满意的——“把你的生活经营得如此颓废,你/难道还心安理得?还有更糟/更老套的吗,忧郁艺术家的交际花?”(17-19),但她忍住了愤怒,只是佯装关心他俩的生意。女儿于是介绍男友是一个生活没有保障的艺术家,这是在母亲眼里无法给女儿带来幸福的对象。母亲于是委婉提出见见“这位新朋友”(42),却被顾左右而言他的女儿搪塞过去。女儿回避着她的眼神,“她不吭声了,有礼貌地/垂下双眼。她看上去那么美,/幽魂般虚幻”(48-50),母亲所期望的毫无芥蒂的倾心长谈根本无法继续下去。当女儿将注意力完全放到面前的美食上,即使母亲询问“可你快乐吗”(67)她的回答也只是天气和食物时,母亲终于意识到“我已失去了她”(71),过去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已一去不返。在这首诗中,达夫“通过空间置换将人物送到陌生地域,并在相聚中着力刻画她们情感上的不断疏离过程,语言层面则以新异的创造突破语义的束缚”(16)曾巍:《丽塔·达夫〈冥河酒馆〉的陌生化书写》,《山东外语教学》2020年第5期。,将神话故事榫接到消费社会和都市文化的现代景观之中。
至此,诗集《母爱》中神话之外的另一个脉络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它来自于现实的叙述声音,讲述着自我的故事。它仿佛与神话故事平行发展,是文本整体中的一个子文本。或者说,神话文本提供了一个框架,而它“展现的是可阐释的结构”(17)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6页。,既为整体文本贡献了自足性,同时也向创作者开放,允许甚至激发她发挥想象力另外生成文本织入现象文本之中,与之构成互文性,从而,“一部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文本互相交汇与中和”(18)Julia Kristeva,“The Bounded Text”,in D. H. Richter ed.,The Critical Tradit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9,p.989.。神话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仿佛合为一体:珀耳塞福涅的故事也是现实世界中“我”的故事;“我”的现实遭遇,也是珀耳塞福涅的投射。所以,在后面的诗中,这种交织更为紧密:《蓝色的日子》(“Blue Days”)中以现实场景开场展开一段日常对话,收尾却将母亲式的人物称呼为“徳墨忒耳”(13);《出口》(“Exit”)通向外部世界的既是一扇门,也可能是大地上的一个裂口;《政治的》(“Political”)一诗中“在地狱之环中待了七年”(1)既指神话中的地下生活,也暗喻现代婚姻中的七年之痒;《历史》(“History”)的隐喻与象征则既可能关乎只在神话中存在的怪物,也关乎如餐点一类的日常琐事……神话与现实的“虚”“实”交织,丰富了作品的层次,扩展了文本的空间。由此不难推测,《徳墨忒耳向冥王的祈求》也是现实叙事文本中母亲对女儿的伴侣要说的话:“我只希望你有此一物:常识”(1),“因此我也只能放弃这种命运。/相信你自己,/坚持下去——看它带你去何方”(13-15)。随着这两个人物展开交流,“我”或者说珀耳塞福涅的双重身份——既是女儿也是妻子——得以在文本之中确立,而双重身份能否得以协调,也随着神话主线推进到由地下到地上的旅行成为不断审视与讨论的话题。
从诗集的第五部分开始,叙述者的另一重身份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声部加入进来,那就是“女性诗人”。这位“女性诗人”在诗中讲述亲身经历的诗歌活动,也探讨艺术问题与语言问题。如《大自然的行程表》(“Nature’s Itinerary”)写到自己“一路从科隆到墨西哥”,“盛装出席国际诗歌节”(6-7)时,不巧遇上了月经周期,她将女性的生理经验与自然的规律性活动联系起来,也与语言实践联系起来,“隐喻性的出血”(8)因此既是身体的征候,也是符号的镜像。在《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中,叙述者随着诗人旅行团游览墨西哥的名胜,古迹的外观以及导游对阿兹特克神话和历史的介绍,让诗人感叹黏土墙上的虫洞,“像雪花,围绕着仙人掌的刺/堆起来”(3-4),成为了宏大叙事的牺牲者,而掌权者的象征则是“羽蛇神”,他的模样“是高个白人男子,有金色的头发”(12),诗人的思考已经超越了现实之中的个体境遇,进入到历史和文化的纵深,追问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性别压迫的根源。《三原色的十四行》(“Sonnet in Primary Colors”)则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一位当代女性艺术家——弗里达(Frida),这位才华横溢、特立独行同时也颇多争议的墨西哥女画家的命运。诗人将其称为“镜子传奇中的女祭司”(7),赞扬她对艺术的执着与献身精神。诗中描写了弗里达在脊椎受损的情况下如何强忍病痛坚持作画,“在鹦鹉簇拥中直起身子,/为她自己画一件礼物”(3-4),“每个夜晚她在痛苦中躺下,又起身/画挚爱已逝者的赛璐珞蝴蝶”(8-9),肯定她的坚韧;同时也在结尾肯定了她对丈夫迭戈爱情的真挚,在她的自画像中,她画上了迭戈,“一个头像,出现在拇指纹印/圆形的窗子里,烙在她至死不变的眉毛上”(13-14)。这既是为遭到世俗眼光污名化的弗里达的正名,也是为爱情的正名。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女性诗人”声部的加入并不是干扰主题的“噪音”,而是随着在《历史》、《政治的》等诗中融入具有充分价值的意识形态多样化视角,从而将“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19)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29页。,另一种语言现实与神话的共鸣,共同构成诗集的“复调”特征。
总体而论,神话与现实构成了诗集中时而平行、时而交织的两个维度。也许对诗人来说,神话意味着虚构,但也是流淌于人类文化血脉之中的古典传统:古希腊罗马时代虽然逝去了,但它并没有变成僵死、封闭的精神遗产,每一次对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都会推动近代文明的革新。革新的手段,就包括“部分通过模仿,部分通过将其改编运用到其他媒介,部分通过受其强烈刺激而创造出新的艺术和思想”(20)吉尔伯特·海厄特:《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第1页。。随着向现实敞开,向创作者敞开,神话也就处于变动之中,“通过内在的发展、自我修正以及自我增长的过程,取得某种更加纯粹的精神和某种新的更高的形式”(21)查尔斯·米尔斯·盖雷编著:《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北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页。。达夫的诗歌实践即《母爱》的创作通过对“冥后”神话的改编,将丰富的言说方式汇入文化传统之中,从而建构了一个崭新的多维度文本空间。在这个话语系统中,“每一个词语(文本)都是词语与词语(文本与文本)的交汇”,“至少有一个他语词(他文本)在交汇处被读出”(22)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史忠义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指向神话的文本与指向现实的文本,通过换喻与隐喻彼此投射、互相观照,从而进一步延伸了文本空间。在这个神话浑融体和多元体中,“仪典—神话之周而复始的复现性对普遍原始型加以表述,并对叙事之作本身加以构拟”,“有助于现代生活素材的整饬及内部(微观心理)活动的构拟之比拟和象征”(23)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第362页。,进而完成了对集体意识和普遍历程的独立创造。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诗集的诗体形式,体现出另一种文学传统的开放性:形式整饬、在韵律和节奏上十分讲究的十四行诗,是达夫有意识选择的诗体形式,但是在写作中,诗人却经常打破规则,不仅运用多种变体来突破严格的限制,还将自由体的风格植入其中,体现出“对格律与破格、匀齐与参差、规则与特例都给予了足够重视”(24)Stephen Cushman,“And the Dove Returned”, Callaloo,Vol.19,No.1,1996.,文本因此成为对十四行诗的创造性改造。这样,从神话和文学传统的“完整世界”中脱胎而出的仿文,也必定不拘囿于源文静止和清晰的意义,而将转化为如克里斯蒂娃所言的“生产力”,在写作者的现实参与中生产出全新的意义,迸发出诗歌语言的“潜在无限性”(25)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第195页。。
三、罂粟/水仙:性别对立的调和
诗集《母爱》与“冥后”神话的文本互涉,显示出当代诗人所受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在传统中彰显自我在场的强烈愿望。诗人的改编,使“源文”与“仿文”既有同源性,也存在异质性。类似于生物学领域中的“共生现象”催生出文本有机体,传统与现实都带着各自的符号及其意指,“这些文化、符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文本网络”(26)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第69页。,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既让神话照亮了现实,也用现实激发出神话的活力。从互文性的角度来考察,如果说“冥后”神话是《母爱》的“源文”,似有笼统之嫌。前面提到的三部神话文献,《神谱》中相关内容失之简略,《德墨忒耳的荷马式赞歌》和《变形记》在人名地名、故事情节上存在较大差异,但都在《母爱》中有其对应符号。可见,三者恐怕都不是“源文”,不是故事原型,它们和《母爱》一样,也只能看作一个异文,只不过在林林总总的“冥后”神话的“家族谱系”中更接近源头,是故事原型较早的亚型。
神话学者曾从比较神话学的视角考察过与德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类似的故事,并在克里特、埃及、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传说中发现了对应的女神。人类初民对德墨忒耳式的大地女神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或者更早的新石器时期,在其后几千年里,不同地区的宗教和文化由于贸易、旅行、迁徙和军事扩张互相联系起来(27)参见Mara Lynn Keller,“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of Demeter and Persephone:Fertility,Sexuality,and Rebirth”.。也就是说,徳墨忒耳母女的故事是多元文化的混合物。而女神崇拜的原始仪式,可以看作一种文化符号,在初民的不断重复中,成为一种集体活动,“它的反复和约定俗成就是一种原型”(28)程金城:《原型的内涵与外延》,叶舒宪编选:《神话—原型批评(增订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29页。。弗雷泽在《金枝》中认为,德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是“宗教成长的晚期产物”,其原型可见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神话中都有的“五谷妈妈”,两位女神都是“植物的拟人化”:首先被人格化的是“五谷妈妈”,然后她的生产物才作为“收获闺女”被创造出来(29)参见J. G. 弗雷泽:《金枝》,徐育新、张泽石、汪培基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412-424页。。这一神话体现了以农业为主、女神崇拜占统治地位的母系社会的价值观念,所以,母女关系被描述为和平而亲密的。而哈得斯的劫持,则是父系社会兴起之后对神话的一次改写,宣告着男性以近乎战争的方式实现对女性的统治(30)参见Mara Lynn Keller,“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of Demeter and Persephone:Fertility,Sexuality,and Rebirth”.。这一时期,两性的地位、关系也通过神话中的暴力事件呈示出来,“地上”和“地下”的空间区隔,同样象征着两种性别的心理距离:“地上”生活与母女关系联系在一起,常被渲染为田园牧歌式的;“地下生活”则对应着夫妻关系,由于不平等而气氛紧张。
从这个原型的演变过程中可以分离出几组对立性的因素:母权制与父权制、地上生活与地下生活、上升运动与下降运动等。而母女关系与夫妻关系,由于分别与相互对立的两极形成对应关系,也被看作相矛盾、相抵牾的。故事中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圆融模式被搁置一旁,或者说被拉成了指向两个端点的两条逆向直线。而这恰好和另外一套故事原型形成了默契,那就是源自犹太—基督教文化的“双生对立体”:一极是天堂,一极是地狱。源自这一原型的仿文,讲述着人类生活朝着正向或反向发展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分析过这类故事的情节与主题的类型:
在讲述堕落的故事里,我们从天堂坠入凡尘,从人间堕入恶魔道,而在讲述上升的故事中,我们从地狱升入人间(比如,从牢狱中被放出去),或者从人间升入天堂。所有与堕落有关的作品都有生离死别、深重的苦难、牢狱之灾、折磨、模仿生命的机器生物、失败、灭绝人性和死亡。而一切与向上有关的则是与亲朋团聚、鲸口逃生,大病初愈,风和日丽,富裕美满,新生与繁衍。(31)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其他的世界:科幻小说与人类想象》,蔡希苑、吴厚平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9页。
在诗集《母爱》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二元对立的戏剧性冲突,以及双向运动的泾渭之别。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性别视角的观照下,也会存在迥异的阐释,具有截然相反的性质。显然,文学改编呈现出特定的审美形态,取决于改编者的心理动机,它“根植在改编者的个人历史中和他们写作的政治时刻里”(32)琳达·哈琴、西沃恩·奥弗林:《改编理论》,任传霞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3页。,由作者的意向性决定,其中一定包含着作者的态度。如对神话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冥王劫持事件,多首诗都有所涉及,达夫采用了对比鲜明的喻指来凸显两种对峙的态度。
诗集的开卷之作《英雄》的叙述者,目睹了一个匿名者的“摘花”事件。联想到珀耳塞福涅也是由于摘花而坠入地下,此诗中“采花大盗”行为的所指,极可能是对女性的劫持。在他眼中,他所看上的花“就算是枝罂粟吧”(2),这显然别有深意:罂粟色彩鲜艳,气味芳香,是制取毒品鸦片的主要原料,对人有麻醉性,而且易上瘾。这种植物的印象,与男性臆想的女性特质十分贴合:美丽迷人,但却有害——极具观赏价值和利用价值,同时十分危险。而采花理由却被描述为“它开始枯萎”(3),意谓将它摘下来并非伤害而是要延续它的生命,而这也可能是冥王劫持珀耳塞福涅的借口。当他跑向最近的房子寻找水和瓶子,却碰到花的主人——一个母亲式的人物,这朵花是她的精神寄托:“每个清晨/它给她注入了起床的/气力”(7-9)。故尔,无论肇事者编造什么理由,在“写下的历史中加上装饰和生动的情节”(12),也无法平息主人的愤怒。而摘花人却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攻击了主人,带着抢来的瓶子潜逃,一路上还要留意“不要留下证据”(21),并在“故事就要真相大白”(22)时,面对激愤的村民辩解说这朵花“它就要死了”(27)。显然,诗题采用的“Heroes”指向男性英雄,而且指向群体,这意味着,这起劫持事件在男性视角下是合理的,鲜花、女人都是他们的战利品,暴力则是他们获得声名的必要手段。
珀耳塞福涅摘花则是劫持事件的导火索,诗集中多首诗都有涉及,这些诗是从女性视角来观察的,也明确指出珀耳塞福涅喜欢的是一株水仙。《珀耳塞福涅的坠落》即以“水仙”开篇:“水仙,寻常的娇花丛中的/一株,如此与众不同!”(1-2)强调这朵花对珀耳塞福涅有特殊意义,促使“她拔呀,/弯起腰来使劲儿拔”,并引起大地开裂,冥王跳出。从外观形态来说,水仙显然与罂粟区别甚大:色彩单纯素雅,柔弱多姿。在希腊神话中,水仙花是自恋的象征:沉醉于自我的镜像,冷落来自他者的爱(33)参见Max Nelson,“Narcissus:Myth and Magic”,The Classical Journal,Vol.95,No.4,2000.。珀耳塞福涅摘花,是出于对镜像中的女性自我的喜爱,在《水仙花》一诗中,她就以水仙自况,两者的命运缠绕在一起,“当花朵焚灰,我还能看见/自己的手指,听见自己的尖叫”(3-4),与之一道坠入冥府。在地下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思念故乡和母亲,《归心似箭》(“Wiring Home”)是她心中对回家旅程的一种想象:她小心翼翼,“不要惊起狼群嗥叫/也不要招来店家盘问”(1-2);她不畏艰难,“继续走吧;虽然你的双膝/发红,如两个裂口的苹果”(3-4);她心无旁骛,“不去管乞讨者的冷炙,//不去管火堆上的板栗”(6-7)。她尤其对“好说大话的报摊”(8)所代表的男性视角所讲述的流浪与爱情故事置若罔闻,一鼓作气走到了家附近的转角,看到了“那一窗鹅黄//亮如千枝/金灿灿的水仙”(12-14)。这里,水仙花成了她向上的旅行的终点,所指的不仅是明亮美好的生活,更是女性重新找到了自我。
“罂粟”与“水仙”所代表的,是两种凝视下的女性形象。一种来自外部,是男性中心主义居高临下的俯视。统治了人类历史数千年的父权制,造成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男性通过对女性的身体、性的剥削和歧视,获取权力和利益,并将其依附在自己的欲望上塑造女性形象。这是违背女性意愿的“劫持”,也造成了性别对立,它赤裸裸地干涉女性世界,以暴力劈开一条裂缝将其切割为“地上”与“地下”的对立两极。反过来看,女性眼中的男性则是暴君,来自对立世界,而他“穿过两个地方、两种时间、两种时空中的隔断、区别、划分、翻转,从而确证了他的幽灵身份”(34)露西·伊利格瑞:《他者女人的窥镜》,屈雅君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62页。。这样一种固执、排他的视角,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另一种来自女性自身,其特征是自我欣赏并排斥他者,因此也就将自我局限于私人范围而拒绝公共领域,拒绝与他者建立关系。这种形象是女性的自我建构,这个世界虽然完整,但却封闭。显然,对于前者,达夫在《母爱》中持否定态度,这从她以反讽的语调“塑造”男性英雄中即可看出,也见之于诗集中珀耳塞福涅对冥王的控诉。后者的情形则要复杂一些,这种那喀索斯式的自恋发生在女性个体身上,对他者的排斥不仅意味着排斥异性,也可能排斥同性群体中的其他个体。也就是说,在女性群体内部出现了四分五裂的状况,其中的个体彼此疏离。诗集中呈现出的母女关系就是这样:血缘与相同的性别,并不意味着一定形成共识和理解,每个个体都在诗中争取“第一人称”叙述权来表达诉求,因此造成了诗集中“声音的混乱”,甚至“在一首诗中,读者都需要努力辨认出谁是发声者”(35)Alison Booth,“Abduction and Other Severe Pleasures:Rita Dove’s Mother Love”,Callaloo,Vol.19,No.1,1996.。而达夫的诗,就是通过将现实的女性自我置入神话之中,置入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女性中心”和“男性中心”的社会形态之中,正视男性与女性以及女性内部出现的种种对立与冲突,倾听他者的声音,也倾听自我内心的声音,并在当代语境中探寻化解矛盾可能的途径。
因此,诗集《母爱》中清晰的两条互相交织的发展线索——德墨忒耳与珀耳塞福涅的聚散离合,现实的“我”的成长历程——反映的是人生不同阶段女性的自我认识。由此我们不难领会,诗集后半部分一些诗篇看似旁逸斜出的现实书写,不仅没有偏离主题,反而是作者在社会的宏阔和历史的纵深中的深刻省思。诗人不仅探问当代女性现实生存境况的根源,而且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冥府中的珀耳塞福涅》中母女之间的深情呼唤,《蓝色的日子》中男性与女性的日常对话,《德墨忒耳的哀伤》(“Demeter Mourning”)中的女性独白,《伊人之岛》中的夫妻同行等,都表明性别之间的沟通、不同女性个体的相互理解正在成为可能,而这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洞察,以及对自我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
18世纪以来,觉醒的女性认识到在社会中所处的屈从地位,主动争取独立,并努力将自我塑造为更自信的当代女性形象,她们提出“男人只要肯慷慨地打断我们的枷锁,并且满意于和一个有理性的伙伴相处,而不是奴性的服从”,就会发现女性将回报以“更规矩的女儿,更热情的姐妹,更忠实的妻子,更明白道理的母亲”(36)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王蓁/汪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3页。,这就是与冥王式的男性掌权者的交流与沟通。20世纪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女性要求政治权力、经济机会,并以抗争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只要男性与女性互相将对方作为对立面看待,两性之间的鸿沟就难以弥合,偏见与歧视就无法削除,“地上”与“地下”仍将争论不休。而女性意识的觉醒如果走向自恋的极端,又会导致内部的分崩离析。达夫所塑造的冥后,则试图化解种种对立,她的方式是主动走向他者:走向哈得斯,理解男性,两者通过成为各自的“另一半”结合为整体;走向德墨忒耳,如《使用过的》(“Used”)中通过生育,自己成为母亲而成为徳墨忒耳。这样,女性就不会满足于自我沉溺与自我封闭,她通过向他者敞开,“面临一项双重任务:在自身中和自身之外感知并消除分裂与控制”(37)E. M. 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39页。。而冥后在两界之间的旅行,也就由被迫的举动转化为主动的选择,她成为了“地上”和“地下”的信使,拉近了人物之间的距离,并将两个世界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达夫的诗集《母爱》,将两条平行的线性旅程还原为循环结构,神话与现实交织成一个完整的文本世界,并将流派众多的女性主义“追求多样性和差异的压力与追求整体性和同一性的压力协调在一起”(38)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这也是身为非裔女诗人的达夫,其诗歌中的常见主题:不仅书写自我在现实社会中的疏离与分裂之感,而且“继续探寻自我与世界的整体性、平衡、联系、连续性、和谐,同时也努力重新定义自我与历史,并复兴文化价值”(39)Ekaterini Georgoudaki,“Rita Dove:Crossing Boundries”,Callaloo,Vol.14,No.2,1991.——这或许就是评论家将其称为“后女性主义诗人”(40)参见Lotta Lofgren,“Partial Horror:Fragmentation and Healing in Rita Dove’s Mother Love”.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