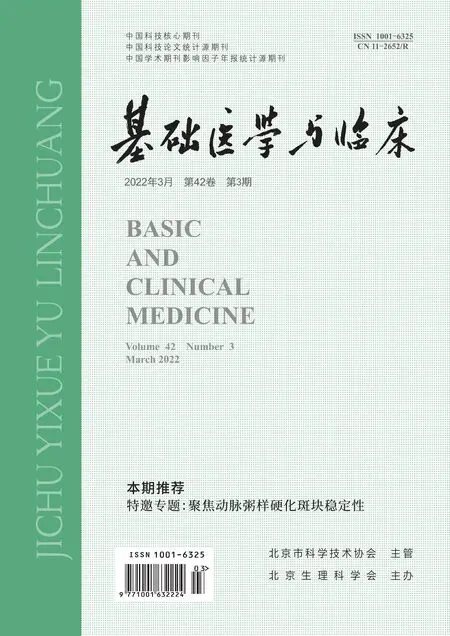肠道菌群在妊娠期糖尿病发病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胡贤良,万 燕,冯 霁*
(1.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临床营养科,江西 南昌 330006;2.南昌大学 江西医学院 研究生部,江西 南昌 330006)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孕妇妊娠期间常见的并发症,国内的发病率已达14%。GDM是导致不良妊娠结局(早产、巨大儿、剖宫产等)的主要原因之一[1],而且可以影响母体及胎儿的远期健康。肠道菌群(gut microbiota)稳态失衡是引发GDM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临床研究显示GDM患者妊娠期间补充调节肠道微生物制剂可以有效改善妊娠不良结局[2],说明肠道菌群在GDM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肠道菌群在GDM的发病中的作用仍不十分清楚,本文就近年相关研究作进一步综述以期阐明肠道菌群在GDM发病中的作用。
1 肠道菌群
人体肠道微生态系统对于维持肠道环境稳态具有重要作用,它是由细菌、真菌、病毒和古细菌组成,其中细菌占了绝大部分,肠道菌群约有2 000余种,目前按门类分型已经鉴别出100余种,主要类别包括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放线菌门及疣微菌门[3],其中厚壁菌门及拟杆菌门占到90%以上。此外按细菌对人体作用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及中性菌,肠道微生物群大多数是厌氧菌。肠道菌群易受饮食、肥胖及药物等因素影响,肠道菌群稳态失衡后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机体内环境的稳态、肠道黏膜屏障功能及免疫功能,发生糖代谢紊乱引起GDM。
2 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的肠道菌群不同分类下丰度比较
GDM患者肠道菌群丰度与健康未孕人群比较:厚壁菌门、放线菌门、变形菌门、疣微菌门升高,拟杆菌门下降。GDM患者肠道菌群丰度与健康妊娠人群比较:在门分类下,厚壁菌门、放线菌门、变形菌门偏高,拟杆菌门低;目分类下,伯克氏菌目、乳杆菌目、芽孢菌目更低;科分类下,疣微菌科、普雷沃氏菌科[4]、拟杆菌科、毛罗菌科显示更低[5];属分类下,GDM患者肠道菌群与健康孕妇比较嫩梭菌属为优势菌属,瘤胃球菌属、普雷沃菌属[6]、副拟杆菌属、巨单胞菌属、考拉杆菌属[7]、毛螺菌属、罗斯氏菌属丰度偏高而拟杆菌属丰度则偏低[8]。GDM患者与健康孕妇不同孕期肠道菌群的研究显示在孕晚期GDM患者肠道γ-变形杆菌比例升高,GDM患者的球形梭菌及多形拟杆菌表达水平在20周时明显升高[9],但 GDM患者肠道菌群α多样性及β多样性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布劳特氏菌及普拉梭菌丰度偏高,艾克曼菌、内脏臭气杆菌和丁酸弧菌偏低。厚壁菌门、放线菌门与体内胰岛素抵抗呈明显正相关,而与拟杆菌门及变形菌门则呈负相关。
3 肠道菌群在妊娠期糖尿病(GDM)发病中的作用
肠道菌群稳态失衡后可通过引起肠道黏膜破坏、代谢产物释放、免疫功能下降以及脂代谢紊乱等多种途径引起糖利用障碍引发糖耐量异常。
3.1 肠道黏膜破坏和代谢产物释放
肠道黏膜是肠道的生物屏障,肠道菌群发生改变可以引起肠道黏膜中紧密连接蛋白ZO-1、occludin的变化,肠道通透性增加,导致更多的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被吸收入血[10],LPS的受体(Toll样受体)被认为是普遍存在于免疫细胞表面的受体,它们的结合激活细胞信号通路NF-κB及IL-1β引发慢性炎性反应,使得机体处于炎性反应状态。此外肠道菌群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主要为乙酸、丁酸和丙酸)对维持正常脂代谢及肠道黏膜功能有重要作用。GDM患者产短链脂肪酸菌群丰度下降导致血中游离长链脂肪酸(free fatty acid,FFA)数量上升,肝蛋白胎球蛋白与FFA大量结合激活Toll样受体通路,可以导致蛋白炎性反应,引起NF-κB通路的激活,从而引起慢性炎性反应。而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可与G蛋白耦联受体(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GPCRs)相结合,促进肠道激素如胰高素样肽[11],5-羟色胺的释放,从而维持血糖的稳定,短链脂肪酸数量下降可引起肠道激素分泌下降,引起糖耐量异常。可能存在肠道菌群-脑-β细胞轴,乙酸在该轴中扮演重要角色[12]。妊娠晚期GDM患者产短链脂肪酸的肠道菌群数量下降[13],由于短链脂肪酸生成下降导致胰岛β细胞损伤进一步加重,胰岛素分泌水平下降,导致血糖进一步升高,加重对胰岛β细胞的损伤。
3.2 免疫功能下降和炎性因子释放
肠道黏膜上皮的免疫细胞维持肠道正常免疫功能。动物试验表明益生菌补充可以有效降低Tregs、Breg细胞及Tfr细胞,减轻肠道炎性反应。说明肠道菌群存在通过调节免疫功能对肠道稳态发挥作用。GDM患者肠道黏膜免疫相关抗原CD4+、CD8+、CD4+/CD8+比例下降与肠道菌群丰度改变有明显相关。也有研究指出肠道菌群能够明显诱导黏蛋白(mucoprotein2,MUC2)及抗菌基因(REG3γ)的表达,而且能够诱导B细胞SIgA的合成与释放,而SIgA是肠道菌群影响宿主的主要关键因子,对维护肠道黏膜屏障功能具有重要作用[14]。当肠道免疫功能下降时,肠道细菌由于失去监控,会出现过度繁殖、细菌移位等。如在严重创伤后可因肠道细菌移位及释放大量内毒素从而引发大量的炎性反应[15]。机体的炎性因子大量释放加重胰岛β细胞功能紊乱,胰岛素分泌下降,导致血糖水平紊乱。肠球菌与炎性因子IL-6、TNF-α等呈正相关;肠杆菌属与IL-6、TNF-α、CRP呈正相关,说明肠球菌属与拟杆菌属为引起妊娠期糖尿病的致病因素,肠杆菌属与拟杆菌属与炎性因子TNF-α、IL-6E的升高均呈正相关。大肠杆菌作为条件致病菌,其与CRP、TNF、IL-6均呈正相关。由此可见部分可致炎性反应的肠道菌群丰度上升可引起肠道发生炎性反应,释放炎性因子引起胰腺β细胞的损伤,引起血糖紊乱[16]。
3.3 脂代谢紊乱
肠道菌群在维持能量摄入及糖脂代谢平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无菌小鼠与有菌小鼠比较体质量明显减低,证明肠道菌群在增加能量摄入与维持脂代谢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肥胖者肠道菌群与瘦型者比较厚壁菌门上升,拟杆菌门下降,说明厚壁菌门可能在引起脂代谢紊乱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外短链脂肪酸的数量下降会增加能量的消耗,引起脂肪酸吸收的增加,导致血中游离脂肪酸数量增加导致脂代谢紊乱,无法氧化分解的三酰甘油以脂肪的形式储存于脂肪细胞,导致机体慢性炎性反应。无菌小鼠体内禁食诱导脂肪因子(fasting induced adipose factor,FIAF)的表达降低,使得血中循环脂蛋白脂肪酶升高,最终导致肝脏中脂肪酸代谢升高及脂肪细胞的三酰甘油储存量升高。此外肠道菌群通过胰高素样肽1(glucagon-like peptide 1,GLP-1)胃肠肽类激素酪酪肽(peptide tyrosine tyrosine,PYY)调控内源性大麻素系统、胆汁酸以及调控FIAF基因的表达来调节糖脂的代谢[17]。而当肠道菌群稳态发生紊乱则会导致脂肪分解代谢下降引起体内吸收脂肪增多,进一步引起脂代谢的紊乱,从而使脂肪因子水平升高,影响了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的抗炎活性、内皮功能以及炎性反应。
3.4 遗传因素
肠道菌群的组成在不同种族人群存在差异,蒙古族的GDM发病率低于汉族与其更加合理的肠道菌群结构相关,蒙古族人群肠道中丰度升高的疣微菌门与空腹胰岛素、总胆固醇呈现负相关,为GDM保护因素,而瘤胃球菌属丰度降低,与空腹血糖呈正相关,为GDM危险因素。芬兰人肠道中丰度更高的产丁酸菌,更加不容易导致脂代谢紊乱,引起胰岛素抵抗和糖耐量异常。但这一点也可能与当地饮食结构及文化相关。对发生GDM的高危孕妇进行5年跟踪的临床研究显示部分GDM母亲的胎儿肠道微生物组(microbiome)与母体肠道微生物组在β多样性上分析相类似,提示可能存在潜在的胎儿对母体肠道微生物组的继承[18],但其具体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4 问题与展望
肠道菌群的稳态对维持机体免疫功能、抵抗疾病起到重要作用。虽然肠道菌群易受到饮食、肥胖等因素的影响,但其总体始终保持在稳定的状态。饮食不合理、不规律,家族糖尿病病史等是引起GDM发病的高危因素,GDM患者在与健康妊娠人群比较肠道菌群丰度及构成发生明显改变,胰岛素抵抗指数也明显升高,孕期血糖出现明显波动,导致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甚至影响母体及婴儿远期健康。近年肠道菌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均显示益生菌能够有效改善GDM患者妊娠结局[19],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然而肠道菌群引起GDM的作用是复杂的,既有菌群通过直接影响机体引发血糖紊乱,也存在菌群通过影响其他菌群或者通过移位而引发血糖紊乱,不同菌群在发挥维持肠道黏膜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所以针对不同肠道菌群在调节机体糖耐量能力方面的作用仍值得进一步研究,这对优化益生菌产品的功能和效果都具有帮助,对益生菌在妊娠期糖尿病的治疗应用中起到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