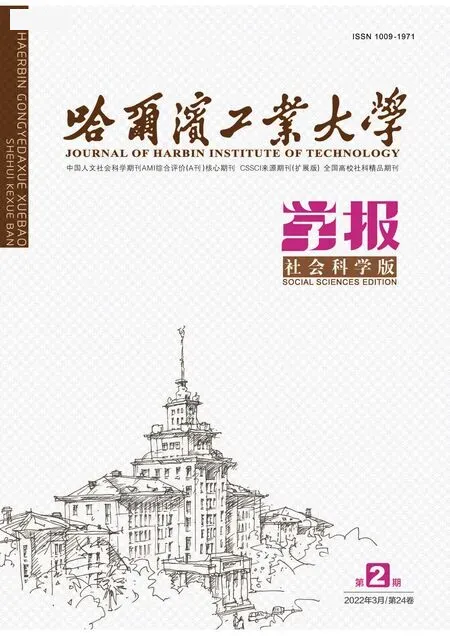从声律节奏到生命之喻
——论古典诗韵的设计美学意义
王秀君
(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哈尔滨 150080)
一、审美视域下的诗歌语言省察
语言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实施思想与情感交流的主要表达形式,也是人类历史活动与存在意义的载体。 自19 世纪哲学思想经历语言学转向以来,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注意到语言本身复杂的意义结构与生成机制,并借由语言重思人类生存的本质。 如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即认为“存在是在词语中成其本质的”,语言是“存在之家”[1]。 在此基础上,作为形式与意义上的“凝炼的语言”[2],诗歌则被视作人类生存情感的结晶体,具有深远的形式美学与生存美学意义。 事实上,后期的海德格尔亦肯定了诗思所具有的本质性语言力量,认为“原始的语言即是诗”[3]。 借由新型的语言观念,我们或能重新发现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审美价值与现代启示。 而对古典诗歌的语言进行立体反思,探讨诗歌语言从形式设计到生存表达的内在肌理,正是本文的初衷。
自《诗经》时代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历代的发展与繁荣,在韵律、内容、艺术手法和生命表达等层面都取得了超凡的成就,在世界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上具有章法整饬、韵律工整、节奏和谐的特点,呈现出“集则有势有事,而散则有纵有横”[4]的形式美感。而在艺术表现上,不论是抒情表意、塑景造境还是作品内在的生命情态,都内蕴着玄妙精微的风味与意蕴。 形式与表意的辩证统一为我们解释了中国古典诗歌体用兼容、表里谐融的整体风貌,也证实了人类语言所具备的横跨形式结构与生存本质的纵深感。
在本文看来,古典诗歌形式建构与生命表达的互涉,可解释为中国古典美学中“诗韵”这一范畴的一体两面。 甘玲指出,“韵”有两个含义:一个指由声律形成的“神韵”,另一个指隐藏于文字之后的“意韵”[5]。 需要指明,“韵”这一美学范畴的多面性并非是割裂的。 易言之,声律节奏的灵活多变与诗歌内容上的蕴藉深沉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抵牾。 从“韵”的统一性来看,两者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肌理和思想传统。 如何在系统理解古典诗歌声律节奏的基础上,将诗歌形式上的美学传统与文辞上的构思传统,上升到诗歌形式与内容辩证统一的整体美学认知,并由此联系到当下中国美学的建设发展,是当今尤需思考的问题。
在全面理解古典诗韵的整体性与当代启示性这一语境下,本文拟提出一个新的理解视角,尝试从古典诗“韵”的构思感与设计感出发,考究古典诗歌从形式到内容在布排表达上的设计考究,并由此揭示“诗韵”美学对当下美学的启示意义。事实证明,关注诗歌在结构设计上的创作心理问题,在诗学史上并不陌生。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就指出,诗歌由语音、词汇构成的异域奇特的诗学特质和意义结构,是诗人为摆脱语言的日常化和自动化而“特意创作”的,其目的是为了使诗的视感“达到最大的强度和尽可能地持久”[6]。 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的文学批评亦格外重视作诗过程中的构思行为与设计意识。 如说“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7],“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炼意魄”[8],都绘声绘色地摹写了诗人在构设辞句时奇幻迷离的状态。 因此,透过构思布排的视角,窥探古典诗歌的生命意识如何从酝酿至成型,最终沉淀为有规律的美学样态,并嵌合诗歌的形式表达,可以使我们立体地感知古典诗韵中丰富的设计感,并将这些复杂灵活的人类设计遗产付诸当代美学实践中。
二、古典诗歌声韵之美与设计美学意蕴
从声律节奏的结构性到生命意识的灵活性,古典诗歌呈现了富有设计美学意蕴的有机整体。在这里,“设计”的意识既外化为格律诗森严复杂的形式结构,也与艺术表达的本体密切相关,呈现出一条贯穿整个有机体系的脉络。 借由“诗韵”这一美学范畴的统一性,本文将分别从声韵美及意韵美两个角度入手,从声律的整饬性、节奏的和谐性、本体的自律性、诗心的丰富性的内容探讨古典诗歌的设计美学意蕴。
(一)平仄相间:古典诗歌声律的设计美
自沈约提出“四声八病”说以来,对诗歌音律听觉美的追求,逐渐成为诗人构思诗歌时格外重视的问题。 李唐一代,格律诗逐渐成型,五言、七言的律诗一跃为诗歌创作中受众面的体裁,不仅成为文人雅集时常写的类型,也逐渐被用诸科场。“克谐音律,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9]严格的格律形式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具备特有的音乐美,在古语吟诵中,吟者能很好地感受诗人情绪的跌宕起伏。 在沈约定义的四声之中,后世普遍流行“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 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10]的认知,而这一认知也直接影响了读者对诗句音律的原初感受。 而基于听感的差异性,后人又将阴平声与阳平声归为平声部,将上声、去声、入声归并为仄声部,由此奠定格律诗平仄声分布有致的结构形式。 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情绪状态以及句子位置淬炼不同声调的字,使之形成抑扬顿挫、强弱有致的听感,既是近体诗创作者必备的功夫,也是近体诗审美的一个基本原则。 事实上,早在沈约奠定“四声说”时,其对于四声韵律的理解,恰恰是建构在创造音律抑扬协调感的理念上。 在沈约为谢灵运撰写的传记中,就已提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11]的看法。 而对这种声律美的诗学追求,自唐代全面成型后,又在宋以后不断求变成为近体诗学体系中的本质规律。 毫不夸张地说,李唐以后,“平仄”已然成为“传统学问里的原子理论”[12]。
从古典诗歌平仄相间的规则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其形式美感,亦能从这一规则的背后窥见丰富的韵律设计理念。 概言之,律诗的平仄规则大体遵循着稳中有变、变中有法的设计原理。 试以李商隐七律《锦瑟》为例予以分析:
仄仄平平仄仄平①格律诗遵循“一三不论”的原则,故在标注时,一、三字分别随二、四字的声调予以标明。 但与此同时,受制于“孤平”原则,在“仄仄平平仄仄平”这一类句式中,第三字若为仄,则犯“孤平”,因此第三字必须为平声。 本诗的第四句、第八句同理。,平平仄仄仄平平。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被公认为近体诗创作者中最恪守格律规范的诗人。 《锦瑟》诗以“仄起平收”句式起句,恰属七言律诗之正格。 从该诗中,我们能一窥近体诗声律布排的基本规则,即一联之内,遵守“相对”原则;联与联之间,遵守“相粘”原则。 “相粘”“相对”原则使得全诗的每一个句子与上下句皆有着各异的平仄格式。 然而细究可发现,每隔四句,同一平仄格式的句型则又反复出现,使每四句形成一个音律格式的循环。 呈现出严谨的结构性与规律性,吟诵起来跌宕起伏。 此即所谓稳中有变,变则有法。 除此之外,该诗对于四声的灵活运用亦不可忽略。 其一展现在半数以上的句子皆同时出现平、上、去、入四声,其二展现在韵脚处阴平、阳平字的平衡运用。 李畯《诗筏橐说》指出:“律有音律之义,声调要亮,音韵要谐。 须按法成章,依谱用韵。”[13]不难发现,李商隐诗在构思设计上不仅严格地展示了“按法成章”的作诗,亦切实地呈现出“声调要亮,音韵要谐”的美学追求,其本质上实际展现的是“参差”的设计美学观。有清一代,对于“参差变化”的追求发展至更为丰富的境地。 相比前朝,其规则要求更为严格,甚至苛刻到“凡喉、舌、齿、牙、唇五音,俱忌单从一音连下多字”[14]595的境地。 可以说,对于平仄相间的追求自南北朝至清代,实际为我们摹画出一个古典诗歌对“参差变化”这一设计美感的发展成熟史。
(二)急缓有致:古典诗歌节奏的设计美
除了平仄声调的错综感,古典诗歌对声韵美的追求亦体现在诗歌节奏上。 概而言之,影响诗歌节奏的重要因素,一在于韵脚字的处理,二在于力量感的平衡。 其中前者关涉韵字的甄选,其内在原理与上文所论述的声律体系息息相关;而后者则涉及句法与遣字等层面,其内蕴着一个关于“正体”与“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并牵扯到具体诗人写作风格的问题。 究其本质,古典诗歌的节奏处理同样关涉诗法主“变化”的传统观念。
用韵层面上,古典诗歌大体遵循“稳当妥帖”“自然浑成”的原则。 “稳当妥帖”即是说韵字要下得稳、下得牢,既可推动情绪的变化,又能充当节奏的顿点。 由于韵脚字总是出现于每句的句尾,因此从结构上看,尾字的字位不仅是音律上重要的节奏点,亦是句式上重要的节奏点,故该字的节奏显得特别鲜明与强烈。 正因为如此,韵字自然被肩负了整合音律结眼与句式结眼的功能[15],被历代诗人格外重视。 胡震亨《唐音癸签》即指出:“夫韵,歌诗之轮,失之一字,全舆有所不行,职此故矣。”[16]沈德潜《说诗晬语》亦说:“诗中韵脚,如大厦之柱石,此处不牢,倾折立见。”[17]由此可见,在韵字的处理上,普遍认为须有“立定”句式的效果,方为上乘。
至于“自然浑成”的理念,则可分两种类型予以阐释:其一,若诗作一韵到底,则韵字与韵字之间要布排有序,层次得当,无紊乱之感,无凑韵之嫌。 一韵到底虽为近体诗的基本特征,却同样存在于大量古体诗中,且古体诗更为注重韵字的处理,要以押韵水到渠成,不涉凑泊为宜。与此同时,基于不同的情感表达和诗歌篇幅,诗人亦须对韵部的甄选予以考究。 譬如就诗歌篇幅而言,平水韵的上平三江韵与下平十五咸韵为公认的窄韵,不宜用于写篇幅较长的古体。此外,由于一韵到底之故,韵字之间亦须注意声调的阴阳,不得流于板滞;其二,若诗作有转韵情况,则韵部的变化须与表意的变化形成同步,不得拖泥带水,亦不得比例失调。 试以王安石《明妃曲》前八句为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18]
此一段落由两个部分组成。 其中,押四支韵的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所述为明妃出塞时,众人惋惜不舍的场景。 押二十五有韵的后四句为第二部分,所述为元帝悔恨并迁怒于画家。 不难发现,该诗的韵部变化是随着内容的“转笔”而发生改变的,由“归来”二字提领韵部的转换,其跌宕感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纵览《明妃曲》全诗,可以发现韵部的转换基本上遵循了“平(四支)—仄(二十五有)—平(五微)—仄(十三职)”相间的规律,且每一次转韵都宕开新的一层意思,其节奏显得从容不迫、徐缓有致。 事实上,唐以后的大部分古体诗、歌行体皆遵循此原则,可见韵字充当着调和节奏的重要工具。
古典诗歌节奏变化的另一影响因素来自句法内部或是篇章内部力量的处理。 换句话说,发力点的位置、发力点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诗节奏是舒缓还是拗峭。 就句式而言,古体诗中不乏诗人刻意设计的声律格式。 如李商隐《韩碑》“封狼生貙貙生罴”“帝得圣相相曰度”二句,前者七字为平,吟诵起来迂回缓慢,后者七字为仄,吟诵起来急切短促,即呈现了不同的力量听感。 有宋一代,即便在律句中,亦不乏诗人刻意为之的节奏,此多体现为拗句的广泛运用。 如苏轼“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陆游“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前者为三仄尾句式,后者为“一字救三字”的经典案例,皆是展现独异节奏的刻意处理。 需要指明,即便是有意破除常规节奏,展现新奇的力量听感,古典诗歌的力量处理仍恪守着平衡协调原则。 即是说,有“拗”必有“救”,有“多字为仄”必有“多字为平”,以此调和全诗的声律,使之成为一个浑圆的整体,此为历代诗人关于句法节奏的设计共识。
就字眼来看,所谓“发力字”“吃紧处”的位置设计,亦影响着全诗的节奏。 以近体诗为例,多数诗人在创作中皆注意到“中二联句法不宜重复”[19]的问题。 营造句法错综变化、纵横跌宕的秘诀,即是使每句的发力点位置错开。 或言之,使每句的动词位置错开。 一般来说,五言律句的发力点常在第三字,七言律句的发力点常在第四字或第五字。 然而考虑到节奏的多样性,不乏有诗人尝试较为新奇的发力位置,以产生陌生的律句节奏,如陈与义“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角晦还明”(第二字,节奏为“一三三”)、黄景仁“不学耕偏愁岁俭,欲归樵却怕山贫”(第一字,节奏为“一二四”)、陈三立“狎玩三千六百钓,归去七十二峰居”(第二字,节奏为“二五”)等,皆使得中二联句法纵横多姿。 此外,除去发力点的考究,虚字与实字之间的协调亦能影响节奏感。 概言之,若一句之内实词过多,则节奏显阻塞板滞;若一句之内虚词过多,则节奏显虚廓油滑。 要须虚实相间,松紧结合,“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工”[20],方可使得节奏平衡有序,通体流畅。 关于诗歌节奏的具体学问尚有很多,限于篇幅,此不再展开。 需要指明的是,较之声律,古典诗歌在节奏上更凸显出明显的设计意识。 如果说声律系统是历代音韵家不断探索并沉淀下来的精华,那么节奏的变化处理则完全可以诉诸诗人具体的写作情境。 苦心经营诗歌的节奏美感,不仅能在通体稳当的情况下凸显诗句的瘦硬拗峭感,更能展现诗歌形式本身的多种可能。
三、古典诗歌意韵之美与设计美学意蕴
(一)思与境偕:古典诗歌表意的设计美
“诗韵”的美学范畴不仅指向诗歌声律节奏的形式呈现上,也指向由此形式所呈现的表意上,也即所谓的意韵美。 事实上,由声韵美到意韵美的过渡并非两个话语体系的平行滑动,意韵作为古典诗歌的存在旨归,本身就是附着于形式呈现的。 声律与节奏的变化要求使得诗人不得不从声韵的角度精心裁字,从而使得字面的观感与字音的听感形成同步。 因此可以说,意韵美的出现本身就涵纳了声韵美的概念。 同样的,意韵美的表述方式也包含了肌理丰富的设计理念。
普遍认为,古典诗歌在表意美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着重关注“意象”到“意境”的变化过程。 自王弼提出“意象”论以来,如何通过有限的形象传递无限的情志,成为诗人孜孜不倦探讨的问题。 在“意象”论与“兴象”论愈发成熟的唐代,关于“意境”“境界”的论述开始广泛流传[21]。究其本质,所谓“意境”论不外乎在“意象”论的基础上加入了情思与形象双向对话的互动机制,即司空图所谓的“思与境偕”[22],其所指向的是一种不可言喻的诗意统一体。 有意思的是,对于“意境”或“境界”的论述,历来被诗人视作纯粹神秘的灵感造物,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然而细究之,我们仍然能在表意方式的处理上,窥见某些“意境”的设计原理。 《文心雕龙·神思》所言“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23],吕温《联句诗序》所言“研精比象,造境皆会”[24],恰恰肯定了实践性在兴象表意中的重要性。 要之,古典诗歌表意的设计学问,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情语与景语的互渗协调。 其中一种设计方式为情语与景语交错出现,互相穿插,“或前景 后 情,或 前 情 后 景,或 情 境 齐 到,相 间 相融”[14]577,方为上佳。 倘若景语与情语比例失衡,则易出现“景多则堆垛,情多则暗弱”[25]的诗病,损害诗歌的整体韵致。 在近体诗的中二联处理上,多数诗人为了避开“呆板”或是“合掌”的诗病,常常用出句和对句表达相异的东西,或上景下情,或上情下景,如“远路应悲春晼晚,残霄犹得梦依稀”“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等,使之不仅宕开意脉,还能深化意境。 另外一种设计方式,为情语渗于景语之中,“情与景会,情与景合”,使之营造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关于情与景的互渗,按《南濠诗话》之说法,又可分为两种情况:“‘芳草伴人还易老,落花流水亦东流’,此情与景合也。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此景与情合也。”[26]然而不论是情合景还是景合情,较之情语与景语交错出现的设计处理,情语与景语的互渗更为精妙高超,其不仅可以有效地规避诗句出现说理谈玄的怪病,亦可以使得诗的每一个字词包含更多的意义叠层,使之更为精炼,更具滋味。 如陈与义的名句“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濛濛细雨中”“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角晦还明”,即充分将情致溶散于景色描绘中,丝毫不见生硬感。 在这里,前者的“海棠”充当了陈与义士人人格的拟物化,后者所描绘的雨景则充当了陈与义境遇的象征。 不难发现,景语与情语的互渗使诗句拓开了丰富的意旨系统,使得诗句本身独具风韵,婀娜多姿。
第二,化用典事来抒情表意。 从意境论上看,用典作为一种特殊的表意方式,实际上可归并为一种“造境”的变式。 如果说情境对话的交互机制营造出了超越空间的意境美,则运用历朝典事可被视作一种对超越时间的意境的营造,盖因为典故背后蕴藏着强大的文化心理系统,能够勾连起历代文人共同的情感旨向,以形成“使闻‘退避三舍’,必若见晋文之鼓;闻‘莼鲈之思’,必如寄江南之旅”[27]的奇特效应。 本文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用典表意,并不能完全被视为一种修辞的技术,事实上,“从《诗》开始,运用古事,已是一种创作手段”[28]。 盖因为典故又分为事典与语典,诗中或可不存在事典,但几乎不存在任何一首诗不包含语言。 换言之,用典作为诗歌的一种基本的表达方式,基本上通行于历朝所有诗作中,几乎是诗歌世界的“行话”。 因此,如何在典事的基础上裁剪化用、夺胎换骨,便成为构思诗作的重要过程。 在此基础上,用典是否含蓄隐蔽,是否曲折幽微,直接决定了诗句在表意设计上功力的深浅。黄庭坚诗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四句皆含典事,却既赋予了熟典以新意,又在字面上不留痕迹,可以说倾注了大量锻造诗句的心血。 因此可见,创作技法上的设计学问,完全可以用于扩充诗歌的意义叠层,增强诗歌的意蕴厚度。 而这些细致精微的设计过程,本身即展现了一种追求自然浑成的美学心理。
(二)独抱诗心:古典诗歌生命意识的设计美
就古典诗歌的存在本质来看,不论是声律节奏还是写意造境,其最终旨归皆指向诗歌所内蕴的诗人生命。 在意韵论的范围内,倘若说声律与技法使意义获取了表达的途径,那么诗歌中鲜活的生命意识,即是意义的泉源,也是中国诗韵的内核所在。 葛兆光先生指出,中国古典诗歌所表现出的错综、堆成与和谐的语音节奏,其最终所显示出的是“人心与天道的同律搏动”[29],此论断恰恰注意到了古典诗歌在声韵美学背后的意义世界——诗人在世的生命体验。 易言之,唯有诗人本身的生命体验能够激活诗的语言,反过来,诗的语言也是因为诗心才得以被赋义,作为诗人高贵生命的记忆与凝萃而被沉淀下来。 清人乔亿《剑溪说诗》所言“道途跋涉之苦,山水奇崛之区,所感非一,情不能已。 至若绝塞边徼,輶轩不到,人物异形,草木殊状,过其地者,莫不悄焉动容,因之嘅然成咏”[30],即解释了诗歌存在的根本缘由。因此“韵”范畴的本质,本就是一个诗歌生命与诗人生命共契的统一体——对生生万物的“悄焉动容”。 诗既是诗人生活的镜照,又是诗人心灵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故说“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31]。
在古典诗歌生命意识这一命题上,我们亦能发现更为宏观的设计理念。 其一,诗人乐于将自身诗歌摹画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在此基础上,诗人不仅能在诗中镜照自身的理念,也能与诗歌本身产生灵魂的交流。 将诗歌解释为生命体的做法具体呈现为将诗的形式内容拟人化。 如归庄《玉山诗集序》指出:“余尝论诗,气、格、声、华,四者缺一不可。 譬之于人,气犹人之气,人所赖以声者也。 一肢不贯,则成死肌,全体不贯,形神离矣。”[32]关于这一种潜意识的设计心理,钱钟书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在统论中国文学批评特征时,有更为理论化的解释。 他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譬如说“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以为皮肤”等[33]。 而这恰恰反映出将诗歌类人化本身就是诗人一种无意识的潜在设计,即将诗歌幻想为能够倾吐生命体验的他者。 其二,诗人乐于将诗歌调适为对日常生活进行加工的结晶物。 有清一代,将诗歌与生活体验密切联系的做法可谓蔚然成风。 较之前朝,由于生活内容变得愈发丰富,诗歌体系内部也相应被诗人开拓出分类更为琐碎的题材,以适应生活的多姿,呈现出“在廊庙台阁,则有应奉经进、颂祷密勿之诗;在军旅封圻,则有赠酬告谕、纪述扬厉之诗;在山林田野,则有言情咏物、闲适光景之诗”[34]的景观。 蒋寅先生将之解释为清诗写作的“日常化”,并认为其深层的意旨,在于清人已然“视诗歌写作为生命意义的寄托”[35]。 概言之,不论是将诗歌视为生命本体,还是将诗歌视为日常生活的加工,其本质都指向发掘诗与人生命意识之共相。 只不过前者的解释具有生存论色彩,而后者则是工具论的视角。
通过梳理以上的设计心理,不难发现所谓“设计”在诗歌生命意识的本体论层面上,实际并不具有具象的操作,而更多是形而上的理念。 而这恰恰指明了诗韵设计理念从形而下层面(声律节奏)到形而上层面(生命意识),所呈现的是一个由术及道、由具体精微到大象无形的过程。 而这一设计理念所折射的美学意蕴,也相应地由形式上的错落有致回归到精神大道的浑融统一。 因而从诗韵的视角来看,诗人构思锻造,恰恰也经历着一个由操演艺术形式到“返精神实体之正大”的过程。①原文所论述的是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提出的“文道”观。 胡晓明认为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以“道”来充实、挺立士人的精神主体,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文化生命意识”。 参见胡晓明《中国诗学的精神》第二版,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79 页。这一过程展现出中国古典诗歌系统的独特的内部逻辑与有机属性。
四、古典诗歌对当代设计美学的启示
毋容置疑,中国古典诗歌的构思体系与创作传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的遗产。 就设计美学的视角看,古典诗歌的创作体系不仅展现了丰富的设计美学思想原型,更为当下中国设计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养分。 就广义的设计美学概念而言,设计美学从来不是封闭的技术系统,它更与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有着紧密联系。 而文化传统所包含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文化心理结构,总是悄然地在设计实践中表现出来[36]。 考察古典诗歌声韵设计与意韵设计对于当代设计美学的无意识影响,既具备学理上的合理性,也能切实地为当代设计艺术提供诸多思想上的灵感。 在本文看来,古典诗韵对于当代设计美学的启示意义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古典诗歌声律节奏设计所蕴含的空间思想
古典诗歌在形式上呈现出平仄相间、轻重有序、定中有变、变中有法的特征,实际贯彻着一种鲜明的空间意识。 汉学家高友工指出,律诗的“二重结构创造出一种复杂而有对称的、层叠的雕塑”,进而使得读者“徘徊于一个封闭的空间,形成一个圆圈”[37]。 此论断最有价值的一点即指明了律诗空间的圆融特性。 倘若将一首完整的诗作视为一个自律的空间,可以看见空间内部的布排不仅遵守着阴阳并行的哲学规律(平仄相间),也符合守变有序的传统审美(节奏有序)。 与此同时,多样的表意方式使得诗歌的语言脱胎于日常,其意旨的叠层却比日常语言更为深厚,一首诗歌亦是一个具有精神弹性的空间。 除去物理意义上的位置占有,它更为我们揭示出时空体空间与情感空间的维度。
就此来看,古典诗歌的空间思想至少为当代设计美学提供了两种启示:一即空间设计不可僵化板滞,而须流动变化;二即空间设计不可扁平单调,而须有人的生存经验流溢其中。 关于前者,其设计美学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已有论文指出:“一切不同要素有秩序、有规律的变化均可产生节奏的韵律美。 设计美构成中的节奏韵律主要表现在重复律、渐变律、起伏律与回旋律四个方面。”[38]这也即意味着,遵守秩序规律的变化可以使得设计成品既具备层次感,又具备回环感,而这种设计理念可广泛用于当代建筑的室内设计与家具设计上,使之呈现出宽窄得当、比例自然等空间美感。 值得一提的是后者。 事实上,关于生存空间与生存体验之共契的当代探讨,海德格尔的《筑·居·思》与巴什拉《空间的诗学》等论文已然具备雏形[39]。 然而较之海氏与巴氏的论断,中国古典诗歌的空间思想还有一个无可比拟的“间性”维度。 也即是说,中国古典诗歌在表现意韵时,其呈现出一种恍惚迷离、朦胧虚廓的美感。 法国学者朱利安对这种间性的空间设计情有独钟。 其认为在中国意韵空间的“之间感”中,固有的实体松动、游弋,坠入虚浮的状态,思绪可以在这种间性的内部肆意逍遥,在有与无之间发现新的生机[40]。
在这种游离的空间状态中,无限的意蕴美充满了诞生的可能,这不得不说具有重大的设计启示意义。 以当代设计美学的视角来看,如何在设计作品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拓开更广大的时空体,是每个具有空间情结的设计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而“之间”的空间思想就原理上看,实际就是将文化记忆作为空间内部的标记表现出来,并对其本有的意旨进行一种含蓄化的加工,使空间内部点与点的间距变得神秘而富有吸引力。 这一设计思路将深刻激发当今传统园林、水域景观、古镇重建、浮雕设计等领域的反思与探索。
(二)古典诗歌抒情表意背后的生命创造力
不难发现,古典诗歌的造境表意在遵循定则的同时,亦包含了诗人个体诸多适性的选择。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泥于法而为之,则撑柱对待,四方八角,无圆活生动之意。”[41]此恰恰佐证了历代诗人求新求变的诗学心理。 而诗韵的变化不仅与诗人生命意识的鲜活息息相关,还与天人合一、适性逍遥的文化传统有所关系。 古典诗歌的声韵与意韵即便看似面临着诸多的规则限制,却也同样折射出非凡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古典诗歌的“韵美”所能呈现的高级状态,恰如前人所言“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42],是一个无限生成的境域。 换句话说,古典诗歌的设计原理的至高境界,即是由有技遁入无技、由技法的淬炼终而迈入完全适性自由的纯灵感境界,迈入宇宙自然的“大设计”母体。 而完成这一过程,既需要设计者有纯熟的设计技巧,也需要设计主体有“游心逍遥”的意识。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即明言:“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就是他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象,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43]这恰恰启示当代设计者需有游心天地、驰怀宇宙的胸襟与格局。 与此同时,在与天地人神共舞的状态下,设计者同样需要在此一过程中完全激活自身的创造驱力,将游神所获的精华倾泻在作品创造上,使之呈现出一种浩瀚浑然却又不落痕迹的天然设计感。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国自身的迅猛发展,当代艺术设计的天才力与创造力已然较早前有质的飞跃。 然而在面临如何脱离当代西方艺术窠臼、展现中国民族自身的源初想象力这一问题上,中国的设计艺术仍有较长的探索历程。 而古典诗学作为一个鲜活却又丰富的民族想象力贮存地,理应受到前沿设计者的关注与重视。不论是实体的建筑设计、广告设计,还是虚拟的软件设计、网络设计,中国古典诗歌的设计美学遗产将有助于推动当代人设计出既有传统记忆、又有时代情调的艺术品。
结语
不论是声律节奏层面还是缘情表意层面,古典诗歌的体系由外至里地为后人呈现了丰富的创造构思理念,对当今的设计美学而言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启发力量。 需要补充的是,从声韵到意韵,古典诗歌的“韵美”范畴不仅内蕴了整全立体、环环递进的内部设计肌理,更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人文精神的凝萃与衍化。 分析与理解古典诗歌的“韵美”范畴,亦能使我们借由诗歌的大道,窥见中国传统精神之崖略。 对于当代设计领域而言,从古典诗歌的风韵中汲取设计灵感,也恰恰能领略到本民族在不同时空情境下的文化精神。 事实上,不仅是设计领域,对于当下中国大部分文化建设而言,中国古典诗歌都有着不可撼动的源初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