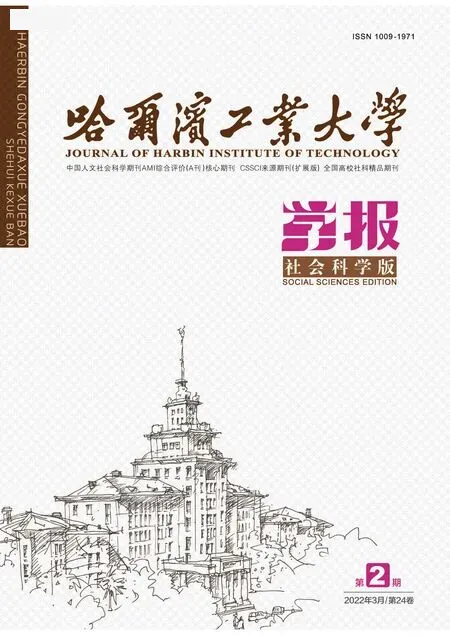“青牛”与老子形象的神仙化
——以老子“出关”故事为考察中心
邓 国 均
(1.贵州大学a.中国文化书院;b.阳明文化研究院,贵阳 550025;2.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贵阳 550025)
道教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既有对《老子》《庄子》等道家诸子思想的吸收,也有对老聃、庄周等道家人物神仙化的改造。 这种改造主要是通过对其生平事迹的改编、对某些重要故事情节的虚构及某些独特文化事象的增加等方式来实现的,如对于老子形象的神仙化,就在《庄子》《史记》等书所载老子故事的基础上,增添了“早慧”“化胡”等情节,以及“青牛”“紫气”等文化事象,实现了对老子形象的重塑。 从《史记·老子传》到《列仙传》《神仙传》等书,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老子在汉代以来逐渐被神仙化的历程。 本文以老子“出关”故事及其演变为中心,对“青牛”事象在老子形象神仙化过程中的意义,及其对汉代以后关涉道教的文学创作之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青牛”与早期神话的动物叙事
《史记·老子传》云:“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1]2141其下文又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1]2142《史记·老子传》叙事的这种模糊状况,为后来道教人士和小说家对老子形象的重塑,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西汉后期刘向所撰《列仙传》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 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 好养精气,接而不施。 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 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上下经二卷”[2]18。 同书所载关令尹喜故事又云:“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 善内学,常服精华,隐德修行,时人莫知。 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迹之(“迹”一本作“遮”,据王叔岷《列仙传校笺》改),果得老子。”[2]21上述故事两称老子为“真人”,尤其是“好养精气,接而不施”、“善内学,常服精华”等描述,实与汉晋道教所推重的服食、行气之术相合,显然是对老子、关令尹喜进行神仙化的具体体现。 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列异传》则云:“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3]92东晋时期葛洪所撰《神仙传》则载:“老子恬淡无欲,专以长生为务者,故在周虽久,而名位不迁者,盖欲和光同尘,内实自然,道成乃去,盖仙人也。”[4]3又云:“老子将去,而西出关,以升昆仑。 关令尹喜占风气,逆知当有神人来过,乃扫道四十里,见老子而知是也。”[4]4该书或称老子为“神人”,或称其为“仙人”,表明老子神仙化的历程,至东晋时期已经基本完成。
在老子“出关”故事的演变过程中,“青牛”“紫气”等文化事象的增加,对于老子形象的神仙化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尤其是“青牛”事象的叙事旨趣,不但深受《山海经》《楚辞》等书神话内容的影响,体现了汉晋道教对于某些原始宗教观念的继承,同时亦与其对《老子》《庄子》思想的吸收和转化大有关系。
《列仙传》《列异传》对老子骑乘“青牛”的描述受早期神话的影响颇为明显。 在《山海经》所载神话故事中,其四方之神,如“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5]206;“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5]227;“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5]265,“乘两龙”似乎是此类神人身份和形象的重要标志。 同书《海外西经》亦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5]209;又云“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鲤,一曰鰕,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5]224。 由此可见,所谓“两龙”“龙鱼”等事象,实与“神人”“神圣”的行游活动密切相关。 类似记载亦见于《庄子》,如该书《逍遥游》所载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即“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6]28。 《齐物论》所云“至人”,亦“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6]96。《庄子》书中的“神人”“至人”所骑乘的“云气”“飞龙”等,亦皆与其行游活动相关。
《楚辞》中这类记载亦为数不少。 如《离骚》“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7]25-26;“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7]42;“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 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7]46。 又如《九歌·云中君》“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7]58;《九歌·河伯》“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7]77-78;《九歌·山鬼》“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7]79;《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7]128。 虽然《离骚》的抒情主人公与《九歌》《九章》等篇所载诸神的活动空间有天空、陆地和河渚的区别,但其所驾乘的“鹥鸟”“玉虬”“飞龙”“白鼋”“赤豹”等,则都是与其“神游”活动密切相关的。 从这些描述来看,《楚辞》所写各类动物,与《山海经》《庄子》等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多以“玉虬”“飞龙”等为主,在神人活动中具有较强的佐助作用,尤其具有较为明显的“先驱”“导引”等文化功能。
《列仙传》《神仙传》等所载仙道故事,虽然某些情节比《山海经》《庄子》书中的神话内容更为曲折,但其动物叙事模式则与之一脉相承。 在《列仙传》中,葛由“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2]50;琴高“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弟子依其言而“设祠”,“(琴高)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2]60;王子乔“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2]65;陶安公仙去时“赤龙到,大雨,而安公骑之东南上”[2]144;呼子先升仙时“夜有仙人,持二茅狗来至,呼子先。 子先持一与酒家妪,得而骑之,乃龙也”[2]148。 《神仙传》所载仙道故事,其情节与《列仙传》亦多有相似之处,如王方平出城时,“唯乘一黄麟,将十数侍人”[4]12;刘根“如华阳山,见一人乘白鹿车,从者十余人”[4]19;鲁女生“去后五十年,先相识者逢女生华山庙前,乘白鹿”[4]82。 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仙人骑乘“赤鲤”“白鹤”“赤龙”“黄麟”“白鹿”等动物,往往发生在其即将仙去之时,或已经成仙之后,与老子乘“青牛”而“出关”的时间节点大体一致。 由此种故事情节的内在关联,可知《列仙传》《列异传》等书所写“老子乘青牛”情节,应是对早期神话中神人形象描写模式的继承和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神话所记述的各类动物,不止是作为“神人”形象点缀,还与其“神威”“神力”有关。 《山海经》对于神人操持、践履、役使、啖食动物的记载,更是其“神力”的直接体现。 如《中山经》所载夫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同篇洞庭之山“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5]176;《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5]370;《大荒西经》:“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5]401有关役使鸟类的记载,则如《海外东经》:“玄股之国在其北。 其为人衣鱼食鸥,使两鸟夹之”[5]263;《海内西经》“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5]306。 对于役使“虎豹”等猛兽的描述,则如《大荒东经》“有蒍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5]343;“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5]344。 上古鸟兽同名,此处所谓“使四鸟”,也即“使四兽”。 对于“啖食”动物的记载,则如《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5]351;《海内经》“又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5]455。 《山海经》中有关“神人”与动物关系的这类记述,表明动物在上古宗教秩序和宗教观念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列仙传》《神仙传》中的各类神仙所役使的动物,亦有一部分与《山海经》等上古神话相同。如《列仙传》所载彭祖故事云:“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祷请风雨,莫不辄应。 常有两虎在祠左右,祠讫,地即有虎迹。”[2]38《神仙传》中的这类情节则更为丰富,如该书所载“淮南八仙”,有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龙,使役鬼神”[4]26;张道陵于西蜀鹄鸣山中精思炼志时“忽有天人下,千骑万乘,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4]29;茅君成仙时“乃登羽盖车而去,麾幡蓊郁,骖虬驾虎,飞禽翔兽,跃覆其上”[4]67;东郭延仙去时“有数十人乘虎豹来迎,比邻尽见之,与亲友辞别而去”[4]82。 在这些故事中,不同神仙对于虬龙、虎豹等大型动物的驾乘与役使,无疑也是其神威、神力之体现,可见这也是汉晋仙道小说塑造神仙形象的一种特定模式。
《山海经》《楚辞》等书的动物叙事所体现的宗教观念,还可以在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中得到佐证。 近代以来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大多具有极为丰富的动物纹饰。 近人容庚所著《商周彝器通考》,将其归类为数十种。 李泽厚从美学角度指出,商周青铜器上的怪异动物形象,“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8]。 张光直则结合动物在上古祭祀活动中的作用,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神话性的动物花纹,主要是“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而存在的[9]。 这些商周青铜器上所铸的动物花纹,与《山海经》《楚辞》等书所载龟蛇、虎豹等动物的宗教文化功能是大体一致的。
从这些方面来看,《列仙传》所载老子“出关”时骑乘的“青牛”,亦可能具有与之相似的宗教文化意蕴。 不同之处在于,见载于《山海经》《楚辞》等书的动物,多具有神秘、凶猛等特点,更多一层作为神人仪仗、羽卫的文化功能,而老子所骑乘的“青牛”,则给人一种温顺、驯良、稳健的印象。 这种差异,应当与老子原有的哲人身份以及早期道教的价值取向有关。
二、“青牛”事象的思想文化意蕴解析
汉晋时期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道教,其理论体系和价值取向固然与道家思想有别,但对老子进行神仙化的改造,其原有的哲人身份和周代社会背景,亦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文化因素。 从《山海经》《周礼》等书的记载来看,牛在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产、生活中,其实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山海经》所记载的高山、大山,其祭祀多以“太牢”为礼具。 如《西山经》“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郭璞注云“牛、羊、豕为太牢”[5]32-33。《中山经》:“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婴以吉玉。”[5]150《礼记·曲礼》亦载“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 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10]1268。 这些记载表明,牛在上古祭礼中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 牛与上古先民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则更为密切,《世本·作篇》云“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11]。 《山海经·大荒东经》亦云:“王亥讬于有易、河伯仆牛。”[5]351类似记载亦见于《楚辞·天问》《吕览·勿躬》等篇,“胲”又作“亥”“该”等。 近人王国维考证说:“‘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12]。据此可知在早期的社会生活中,牛主要用于驾车。随着牛耕的发明和推广,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东汉应劭所著《风俗通义》说:“牛乃农耕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13]无论驾车还是耕作,牛的使用均与土地相关,更兼其独有的性格特点,因此又有牛为“土畜”之说,被看作“土德”“地德”的象征。
《周易》经、传内容,已将牛与“地德”相联系。该书《说卦》云“乾为马,坤为牛”;“乾,天也,故称乎父。 坤,地也,故称乎母”;“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10]94-95。《礼记·月令》亦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天子于是月“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郑玄注云“牛,土畜也”[10]1371-1372。 古人之所以将牛看作“土畜”,可能与其对牛的性格之认识有关。 《孟子·告子上》云:“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宋人孙奭解释说:“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顺。”[10]2748明人彭大翼所著《山堂肆考》亦云:“牛,土畜也。 马,火畜也。 土缓而和,火健而燥,故《易》乾为马,坤为牛。”[14]牛所具有的这种沉静、和缓和驯顺的性格,使人很容易将其与“土德”“地德”联系起来。
《周易·坤卦》传文对“土德”“地德”的含蕴做了较为集中的论述。 《坤卦·彖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10]18《坤卦·象传》则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0]18《坤卦·文言》则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10]18《坤卦》传文的这些内容,不但指出“含弘广大”的大地,具有“德合无疆”的内涵,亦表明“土德”“地德”具有含化、生养、载育万物的文化功能;其在物理形态方面,则具有厚重、广大、承顺等特点。 《周易》传文有关“土德”“地德”的论述,与《老子》思想是高度相通的。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道”“德”也具有近似于大地的文化功能,如该书第三十四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15]405-406;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5]29;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15]69-73。 由此可见,《老子》所谓“道”“德”,与《周易》经、传所谓“土德”“地德”等在化生、养育万物方面是高度一致的。
从《周易》传文看,不但牛所表征的“土德”“地德”具有化生、长养万物的功能,而且牛自身也可以看作生命和繁育的表征。 如《周易·说卦》以《坤》为“子母牛”,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即云:“为子母牛,取其多蕃育而顺之也。”[10]95此种认识应有古老的文化渊源,现存的某些远古文化遗迹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今人饶恒久通过对宁夏、新疆等地发现的“牛形岩画”的分析,认为牛不仅与人类物质生活有悠久而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原始先民的“生殖(生产)崇拜”,也有“极为明显而普遍的联系”[16]。 除此种生殖、生命观念的联系外,《老子》主“慈柔”、尚“虚静”的思想倾向,也与牛的行动和性格特征有不少相通之处,如该书三十六章“柔弱胜刚强”[15]419;第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15]35;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15]160。 又如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静曰复命”[15]301;四十五章“躁胜寒,静胜热。 清静为天下正”[15]45。 这些论述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与牛的沉静、和缓、驯顺的性格特征亦是有不少相合之处的。
因此,就牛与《周易》等早期典籍所谓“地德”的关联而言,致力于“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老子,在“出关”神游过程中所驾乘的“青牛”,确实不但可以看作“五行”观念中的“土德”和道家思想中的“道德”的象征,亦可以看作汉代以来兼具道家哲人和道教神仙双重身份的老子的“德性”之象征。
就“青牛”与汉晋时期道教教义的关联看,则其又是“长寿”的象征。 追求长寿、长生可说是道教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因此对老子形象进行神仙化的改造,关键的一点即是突出其具有超越常人的“非凡之寿”。 《史记·老子传》已表现出这种思想倾向,其称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1]2141。 《列仙传》则云老子“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2]18,实已隐含一层老子长生不老、与世长存的意思。 不仅如此,老子“出关”时所骑乘的“青牛”,从战国、秦汉时期某些民间信仰看,其不但与古人的生命观念有密切关系,而且亦具有极为丰富的长寿文化内涵。
在先秦以来的“五色”观念中,“青”被视为“东方之色”。 《左传·昭公元年》云:“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近人杨伯峻解释“五色”说:“白,青,黑,赤,黄。”[17]《周礼·春官》所载“大宗伯”职掌云:“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10]762《墨子·贵义》篇亦载:“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18]448《说文解字·青部》云:“青,东方色也。 木生火,从生、丹。”[19]这些记述表明,五色中的“青色”,很早就与五方中的“东方”建立了联系。 因此,青色又往往被视为东方之色、生命之色、生长之色。
东汉刘熙《释名·释采帛》云:“青,生也。 象物生时色也。”[20]《说文解字·生部》:“生,进也,象艸木生出土上。”[18]127《楚辞·大招》“青春受谢,白日昭只”,王逸注云“青,东方春位,其色青也”[7]216。 草木于春夏时节长势健旺,故《尔雅·释天》说“春为青阳,夏为朱明”[10]2607,正可与《楚辞·大招》王逸注相印证。 由此看来,“青”作为“五色”之一,乃是得名于草木等植物的色彩。 因为草木在春季生长较快,故而“青”与“春”遂有密切关联。 在“青”的几层含义中,“青”与“生”的关系应该是最为密切的。 “青”与生命、生长的此种深切关联,与道教崇尚长寿、长生的价值观念可谓高度契合。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神仙传》所写仙道故事,有不少内容皆与青色相关,如左慈故事“或不识慈者问其状,言眇一目,着青葛巾、青单衣”[4]37;所载壶公与费长房故事“房忧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与之”,“房所骑竹杖,弃葛陂中,视之,乃青龙耳”[4]39;王烈于太行山中“见山破石裂数百丈,两畔皆是青石”,“中有青泥流出,如髓”[4]45;孙博能以“一赤丸子掷军门,须臾火起”,“复以一青丸子掷之,火即灭”[4]61-62;沈羲“诣子妇卓孔宁家,还逢白鹿车一乘、青龙车一乘”[4]63。 这些故事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早期道教对于青色的崇尚。
由于“青”所具的上述文化含蕴,因此在秦汉以来的某些民间故事和传说中,又有“青牛”为“木精”的说法。 如葛洪《抱朴子·对俗》引《玉策记》和《昌宇经》之说云:“千岁松树,四边披越,上杪不长,望而视之,有如偃盖,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寿万岁。”[21]梁代任昉《述异记》亦云:“千年木精为青牛。”[22]《玄中记》则云“千岁树精为青羊,万岁树精为青牛,多出游人间”;同书又载“汉桓帝时,出游河上,忽有一青牛从河中出,直走荡桓帝边,人皆惊走”,独太尉何公“以右手持斧斫牛头而杀之,此青牛是万年木精也”[3]237-238。 在有关“木精”与“青牛”的故事中,干宝《搜神记》所载《怒特祠》尤为特别,是篇云:“秦时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树。 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辄有大风雨,树创随合,经日不断。”后伐树士卒因伤足而卧树下,闻听鬼与树神之语,遂依“鬼语”而以“朱丝绕树,赭衣灰坌”而伐之:“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 其后青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 有骑堕地复上,髻解被发,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23]《玄中记》所载内容与此略同。 《史记·秦本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数句,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录异传》文字,其故事情节与二书所载亦大体相合[1]180-181。 可见,这一故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颇广。
《抱朴子》《玄中记》等书“千年木精”“万岁树精”为“青牛”的说法,清楚地表明“青牛”事象与道教长寿、长生观念的密切关系。 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作为老子“出关”座驾的“青牛”,确实可以看作是“长寿的象征物”[24]。 尤其是《搜神记》等书所载《怒特祠》故事的细节,更是从两个方面具体地反映了“青牛”与道教“长生”观念的联系:首先,伐树时“树创随合,经日不断”,从表面看是凸显梓树“顽强而令人震撼的生命力”,其实体现的乃是一种“‘生命不死’(不止)的内涵”,“是在追求长生久视的过程中对树木年寿、生命的神化”[25]。 其次,“树断”而“青牛”出,还与道教文化中的“变化”观念有关。 《山海经》所载“女娲”“颛顼”之类的“神人”,大都具有“变化”形体的功能;《列仙传》《神仙传》等书所载仙道故事,亦大多以“神仙”自身形体的“变化”,或驱使外物发生“变化”,作为其“神通”与“道术”的体现,这类情节在实质上皆可以看作是一种表现生命永在的形式,是道教“长寿”“长生”观念的具体而形象的体现。 由此而言,《列仙传》等小说将拥有“千岁”“万岁”之寿而又能“变化”形体的“青牛”作为老子出关过程中的骑乘之物,不但与《老子》哲学思想高度相合,而且对于老子形象的神仙化,确实具有关键意义。
三、“青牛”事象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老子形象神仙化的过程中,由于“青牛”事象所具的丰富文化内涵,使其在汉代以来进一步为道教人士所接纳,成为道教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至迟在东汉末期,陇西和关中地区便出现了道教人士模仿老子骑乘“青牛”的现象,此种现象与《列仙传》等书所载老子“出关”故事一起,成为后世关涉道教的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特殊题材,并在不同文体中表现出各异其趣的审美取向。
汉魏时期骑乘“青牛”的道教人士中,陇西封君达的事迹颇为典型。 西晋张华《博物志》载:“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达,其论养性法,即可放用,大略云:‘体欲尝少劳,无过虚;食去肥浓,节酸碱;灭思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施泄,秋冬闭藏。’”[26]《神仙传》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封衡字君达,陇西人也。 幼学道,通老、庄学。 勤访真诀,初服黄连。 五十年后,入鸟兽山采药,又服术百余年。 还乡里,如二十许人。 闻有病死者,识与不识,便以腰间竹管药与之,或下针,应手立愈,爱啬精气,不疾视大言”,“常驾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号‘青牛道士’”[4]83。 此外《后汉书·方术列传》亦载“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者,皆方士也”,“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 甘始、元放、延年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 君达号‘青牛师’”[27]。 综合《博物志》《神仙传》及《后汉书·方术传》等记载,可知封君达“学道”“养性”故事,在历史上应当实有其事,只不过《神仙传》的记述更为夸张、更多一层传奇色彩而已。
封君达故事在汉晋时期并非个别现象,《三国志·管宁传》所附胡昭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亦云:“初平中,山东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辅。 晓知星历、风角、鸟情,常食青葙芫华。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亲识之,谓其已百余岁矣。”[28]此外,唐人陆羽所著《茶经》引王浮《神异记》亦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 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 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3]245王浮为西晋惠帝时人,其所记丹丘子故事,与封君达所处的时代相去不远。 《魏略》所载“青牛先生”,与《博物志》等书所载“青牛道士”,在行为方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由此可知,在东汉至魏晋时期,以“青牛”作为自己形象和身份的标志,已是部分道士的自觉意识。 此类故事虽然见诸史书记载较少,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可能更多。
汉晋道士之所以选择骑乘“青牛”,应与老子“出关”故事的流传,以及“青牛”事象所具的宗教文化意蕴密切相关。 封君达等人的宗教和社会活动,实际上在《列仙传》《列异传》等书所载老子“出关”故事的基础上,将“青牛”与道教的关系进一步固化了。 魏晋以来的文学作品对于“青牛”事象的书写,即主要是从“老子乘青牛”和“青牛道士”这两个角度展开的。
辞赋、诗歌等文学作品以“青牛”象征仙道文化,大概始于南北朝中后期。 徐陵《玉台新咏序》“灵飞太甲,高擅玉函。 鸿烈仙方,长推丹枕。 至如青牛帐里,余曲既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竞”[29],便已将“青牛”与“仙方”相关联。 庾信《枯树赋》亦云:“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30]47赋文虽主要取“青牛”为“木精”之义,但与道教“长生”思想亦不无关系。 庾信所作《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亦云:“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将尽之命;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30]575其便是对“青牛道士”这一典实的直接运用。 陈朝张正见所作诗歌《神仙篇》云“六龙骧首起云阁,万里一别何寥廓。 玄都府内驾青牛,紫盖山中乘白鹤”[31],已明确地将“青牛”作为表现仙道文化的素材,并创造出一种玄远清幽的诗歌意境,实可看作唐诗中类似作品的先声。
唐代是诗歌兴盛的时代,也是道教文化盛行的时代,“青牛紫气”“青牛道士”遂成为诗人笔下的常见题材。 如王勃《散关晨度》“关山凌旦开,石路无尘埃。 白马高谭去,青牛真气来”[32]674;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青牛紫气度灵关,尺素赩鳞去不还。 连苔上砌无穷绿,修竹临坛几处斑”[32]838;岑参《函谷关歌送刘评事使关西》“寂寞无人空旧山,圣朝无事不须关。 白马公孙何处去,青牛老子更不还”[32]2053;陈元光《真人操》“青牛出关避世纷,招呼鸾鹤引霞樽。 秦王汉武心尘土,欲求真仙恶得覩”[33]758;无名氏(或说此诗为唐太宗李世民所作)《题焚经台》“门径萧萧长绿苔,一回登此一徘徊。 青牛谩说函关去,白马亲从印土来”[32]8869。 这些诗多用“青牛”意象歌咏老子“出关”故事,以表达对老子玄踪哲影、仙风道骨的怀想,传递出一种玄远、清幽的审美意趣。
另一些诗作,如骆宾王《秋日饯陆道士陈文林》“青牛游华岳,赤马走吴宫”[32]843;杨衡《宿青牛谷》“随云步入青牛谷,青牛道士留我宿。 可怜夜久月明中,唯有坛边一枝竹”[32]5289;曹邺《偶题》“白玉先生多在市,青牛道士不居山。 但能共得丹田语,正是忙时身亦闲”[32]6866;储嗣宗《和茅山高拾遗忆山中杂题五首·山邻》“石桥春涧已归迟,梦入仙山山不知。 柱史从来非俗吏,青牛道士莫相疑”[32]6883;皮日休《道院迎仙》“百尺丹台倚翠华,洞门迢递隔烟霞。 雨中白鹿眠芳草,松下青牛卧落花”[33]1180,则多将“青牛”与“道士”并称,以表达对道教文化的喜爱与向往,营造出一种平和、宁静的诗歌意境。 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自唐代以来,“青牛紫气”或“青牛道士”,在诗歌创作中已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组合意象,并具有了较为稳定的文化意蕴和抒情指向。
宋代诗人对于“青牛”事象的叙写,既有继承唐诗风格与意境的一面,但在某些方面又有其独特之处。 以“青牛”意象歌咏老子“出关”故事,这一传统题材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有时并与书、画等艺术形式相结合,如李纲《题李伯时画老子岀关图》云“请说常无众妙门,当时关尹意何勤。青牛西去连沙漠,紫气东来见瑞氛”[34]17608;白玉蟾《李伯阳赞》其三“蓬莱三万里,道德五千言。一自青牛去,函关烟雨昏”[34]37634。 以词体形式歌咏其事的,则如曹勋《法曲·歌头》“柱史乘车,青牛驾轭,紫云覆顶,函关令已前知”[35]1207;刘克庄《最高楼》“白驹恰则来空谷,青牛早已出函关”[35]2636,等等。 在两宋时期的诗歌作品中,大部分则将“青牛”事象从老子“出关”故事中独立出来,或用以抒发仕途失意的引退之志,或表现一种远离现世的隐逸情怀,如黄诰《三峡桥》“隐士闲行随白鹿,道人长往驾青牛”[34]10217;黄庭坚《书石牛溪旁大石上》“石盆之中有甘露,青牛驾我山谷路”[34]11507;张耒《感遇二十五首》其五“我师青牛书,不争忌处先”[34]13324;王安中《送徐干臣》“趣驾青牛寻尹喜,著书方便设津梁”[34]16001;王十朋《游石门洞》 “欲向故乡寻白鹿,先来仙隐访青牛”[34]22738;刘克庄《送杨休文》“自从黄鹤仙人去,谁遣青牛道士来”[34]36254;何梦桂《和徐榷院唐佐见寄七首》其二“何当赋招隐,共驾青牛车”[34]42138,可见宋人对于这一特殊题材的喜爱。 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们进一步拓展了“青牛”事象所具的“言志”与“抒情”功能,体现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除此以外,某些作品还将“青牛”与道教建筑、道士生活联系在一起,形成宋代诗歌中同类题材的一个特色。 如洪咨夔《挽元寂王道士》“院静桃开落,林深鹤去留。 翛然风露表,无处觅青牛”[34]34562-34563;施枢《通真观》其一“不到凝安二十年,丹青一幅尚依然。 青牛已去仙踪远,却有山禽下玉田”[34]39097;陈允平《林道士故庐》“青城道士跨青牛,去作清都汗漫游。 朝扣九关朝玉阙,暮回三岛宴金楼”[34]42006;连文凤《送王道士入燕》“学跨青牛朝玉阙,语留白鹤守金丹。 洞门无钥须归早,莫待桃花落石坛”[34]43364;刘方《玉虚观》“南台旧观再焚修,鸾凤徘徊无树留。 芳草满时迷白鹿,落花深处卧青牛”[34]45225,等等。 这些作品清楚地表明,“青牛”不仅是一个常见于诗人笔下的文学意象,而且还应当实际存在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从两宋时期的诗词创作来看,“青牛”事象在这个时期与道教文化的结合更加紧密,其不但在相当程度上成为道教文化的象征符号,而且在某些诗词中甚至被当作道士、道教或老子的代名词。 宋代以后,虽然这类文学作品还有不少,但其所表达的思想主旨、抒情意趣和所构建的诗歌意境,则似乎没有在根本上超越唐宋诗词的范围。
明清时期,随着神魔小说的兴起,“青牛”事象再次获得其特有的文学生命力,成为小说家表现道教文化的重要题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当数《西游记》了。 《西游记》第五十至五十二回,写唐僧师徒行至金兜山界,遇到一个“独角兕”妖怪,将唐僧、八戒、沙僧等一起捉走。 它在交战时数次手持一个“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把孙悟空及其搬请的天神“哪咤太子”“火德星君”等所使用的兵器,全都“唿喇一声”“套将了去”[36]608-640。 后经如来佛指点,孙悟空到“离恨天兜率宫”寻求“太上老君”的帮助[36]641。原来,唐僧师徒所遇到的这个“独角兕”妖怪,正是太上老君的著名坐骑“青牛”;而其所使用的白色圈子,乃是太上老君的宝物“金刚琢”。 老君向孙悟空讲述其来历说:“我那‘金刚琢’,乃是我过函关化胡之器,自幼炼成之宝。 凭你什么兵器、水火,俱莫能近他。”[36]641老君于是和悟空一起来到地界,使用一把“芭蕉扇儿”降服了“独角兕”,再次“辞了众神,跨上青牛”而去[36]642。 《西游记》对于“青牛精”及其兵器“金刚琢”强大“法力”的描写,从一个侧面衬托、凸显了太上老君的无上神力,同时也与《列仙传》等书所写老子驾乘“青牛”而“出关”的故事遥相呼应。
结语
老子形象的神仙化,是早期道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列仙传》《列异传》等小说,继承《山海经》《楚辞》等书的动物叙事模式,在老子“出关”故事中增加了“青牛”“紫气”等文化事象,基本上完成了对老子形象的重塑。 就其与道家、道教思想的关联而言,老子“出关”过程中所骑乘的“青牛”,实可以看作“德性”与“长寿”的象征。 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诗人和小说家们或用“青牛”营造玄远、清幽的诗歌意境,或用其衬托、凸显“太上老君”的无上神力。 尤其是《西游记》对于“青牛精”的人格化叙事,在唐宋诗人将“青牛”作为道教、道士或老子代名词的基础上,将“青牛”与道教文化的关系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列仙传》《神仙传》《西游记》等小说作品和唐宋诗词对于“青牛”事象的书写,既显示了不同文体各异其趣的审美取向,也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深化了“青牛”事象的宗教意蕴和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