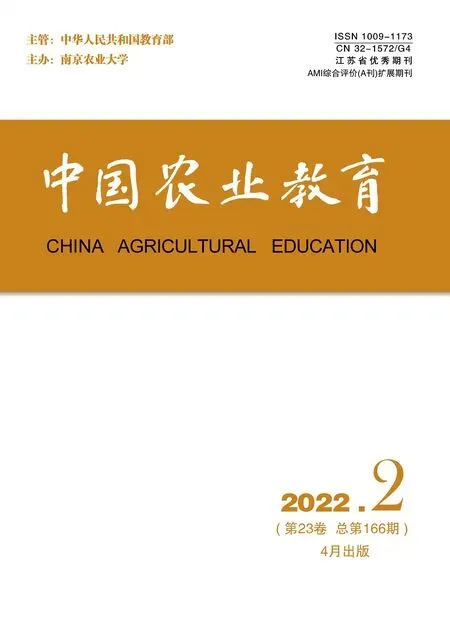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内在要求
——基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经验分析
王建英,李剑富
(江西农业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5)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高质量发展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教育发展当然也不例外。高等教育担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职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显著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关乎到国家的发展前途。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历经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五次转移,虽然与其国内外的环境密切相关,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达到了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水平,使其有能力扛起世界高等教育引领者的大旗,成为世界标杆。
“高等教育强国是完全从中国本土情境中生长出来的概念”[1],作为中国本土化的名词,高等教育强国除了包含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所蕴含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之外,还含有较强的本土文化特征和国际竞争力,“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绝非字面的含义,“高等教育强国”概念强调“赶超”,强调“强国梦”,当与世界高等教育相比较时具备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由于高等教育强国概念源生于中国本土情境,外国学者很少使用,当前学界对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是否是高等教育强国并未做出明确的区分,邬大光认为高等教育强国具有“时代性”的特征,认为“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都曾是世界的高等教育中心或高等教育强国,但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它们,恐怕谁也算不上真正的高等教育中心或高等教育强国。”[2],周光礼指出,“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的标志是拥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大学”[3],而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特征之一,“就是国家拥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4]。因此,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曾是或者说现在仍然是高等教育强国,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5],高等教育强国离不开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强国本身就蕴含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四次更迭蕴含着一定的规律和经验,且都有迹可循,总结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一般规律,归纳出高等教育强国的高质量高等教育基本特征,对于我国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具有一定导向性作用。
一、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路径
自文艺复兴以来,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沿着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轨迹经历了四次转移形成了五个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影响力和辐射力[6],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每一次转移,都发生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都展现着更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教育升级,都代表着引领高等教育旗帜的转移,都反映着世界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发展趋势。
(一)意大利(14世纪—16世纪):文化的觉醒及大学的建立
14至15世纪的意大利政局动荡,国土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政权,资本主义最先在这片土地上萌芽,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处于东西方交通要道上的意大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一度成为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城市也随之兴起。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摆脱教会束缚和封建社会,随即文艺复兴运动爆发,为人们意识觉醒提供了条件。由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需要具备相关知识的人才,思想觉醒的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发展起着莫大的促进作用,他们倡导教育培养人才,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最早的大学在意大利得以建立,虽然没有完备的大学形式,但其具有现代创新性的办学模式成为了后来英法德等国创办大学的模型和范本,到14世纪末,意大利共有大学18所,而整个欧洲也才有60多所,意大利占比接近30%,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人才,譬如“文坛三杰”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艺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大学的兴盛和大批成功学者的涌现吸引了各国学者和学生来此交流和学习,并进行文化思想传播。
(二)英国(17世纪—18世纪):经济的发展及制度的支撑
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成功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确立君主立宪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经济也随之繁荣,被称之为“日不落帝国”。新航路开辟后英国成为大西洋航运的中心,海外贸易、殖民掠夺、黑奴贸易等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渠道,英国经济地位逐步上升,欧洲的经济中心也从意大利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西欧沿海国家,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地位的变化,高等教育的中心也逐步开始转移。随着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一系列高等教育制度得到了实践和发展,为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奠定了基础。英国高等教育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在波谲云诡的社会变迁中主动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开展大学自治和自由教育,17世纪的英国高等教育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最具特色的是学院制、导师制,对现代大学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吸引着大量留学生前来学习。到18世纪,培根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牛顿的实验研究成果纷纷进入大学校园,自然科学讲座大受欢迎,高等教育表现出近代化教育的趋势,产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如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莫尔所著的《乌托邦》、培根的《学术的进展》,以及戏剧作家马洛和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等,群英荟萃,师生云集,一时间英国高等教育占据世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英国资本主义建立和经济繁荣成就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而正是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了人才,提供了智力支撑。
(三)法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中叶):思想的解放及实用主义的加持
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拿破仑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激进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执政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革命的推进使得资本主义在法国土地上遍地开花,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海外殖民掠夺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法国对科技人才需求更加迫切,于是由执政党派带领的法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拉开了序幕,改革下的法国高等教育欣欣向荣,建立了新型的、高水平的大学,多所高等专科学校致力于培养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大革命时期通过《公共教育组织法》决定建设专门化的学院,以专业教育为主,培养实用性人才,“大学校”与其他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层层选拔的精英教育新模式。在国家发展需求迫切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事业被确定为国家事业,兴办各类科学技术学院和新型大学被作为法国基本国策,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对近代德国、美国建立近代教育行政体制和发展国民教育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加之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思想解放,产生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科学文化成果,诸如数学家拉格朗日和柯西、物理学家库仑、化学家吕萨克、生物学家居维叶等,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近百年间,法国的教育名家人数超越同期世界各国水平而到达巅峰,法国逐步成为新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政府的加持使得法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充满了活力与生机,走在社会需求前列的高等教育以培养社会发展需求人才为终极目标,重点培养军事科技人才和实用性人才,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人才、科技保证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源泉。反过来,高等教育以培养出实用型人才、探究出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方式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引领作用。
(四)德国(19世纪—20世纪初):政府的重视与战争的影响
相比而言,19世纪初期的德国经济实力并不是很强,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胜普鲁士的刺激,德国政府认为必须用脑力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德意志民族寄希望于教育兴国,于是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席卷而来。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具备超强发展活力的先进新型大学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探究真理,倡导学术自由,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此外,政府官员兼任大学校长,政府对大学的责任明确,为师生的学术自由提供条件保障,并聘请了一批一流的学者任教,颠覆了以往传统大学模式的柏林大学树立了现代大学的完美典范,德国高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柏林大学模式的成功吸引了大批外来学者,就美国而言,19世纪中期美国赴德国留学的学生达一万多人次,与此同时也产出了大批世界顶尖的学术成果,德国的人文和自然科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德国高等教育的吸引力所向披靡,产生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李比希、高斯等。据统计,自诺贝尔奖设立(1900年)至1920年,德国有19人获奖。此外,19世纪的德国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涌现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和思想,如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其成就至今无人能及。
政府参与和支持下的德国高等教育主动积极地寻求自身发展道路,采用全新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发展知识水平,培养具备独立研究能力的学者。德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证明,教育的繁荣不一定非要有强有力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反的,合适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就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教育改革建立新型大学,吸引外来学者,从而促进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德国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高等教育发展的。
(五)美国(一战后—至今):经济的引领与机制的创新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工业经济迅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加上政府对于教育的大力支持,美国高等教育很快便以乘风破浪之势超越德国。美国高等教育源起于殖民地学院,19世纪大批赴德国留学回来的学者想要按照新理念建立本国的新型大学,通过学习借鉴他国大学发展模式来建设本国高等教育,最先出现的就是哈佛学院。同时美国政府非常注重人才培养,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指明要动用所有条件培养高级人才。高校是人才培养基地的不二选择,研究生教育也成为许多大学的主要任务,科学技术人才在社会上的地位得以提升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投身到教育事业,美国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美国的大学具有多样化的特点,研究型大学、专业院校、文理学院等涵盖多个学历层次的多类型大学构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结合美国实际情况建设具有美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开创了服务社会的大学新模式,创立了学分制和选修制,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了保障。为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美国高校开创了专业认证制度和同行评价制度等,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引入到课堂教学中,翻转课堂和慕课等新的教学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传统教学方式和形式。目前美国的高校多达3500多所,在世界综合实力名列前茅的大学中,美国大学占了一半以上,截至2018年,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得人数均位列世界首位。
美国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教育方面,都切切实实地成为了世界霸主和强国,作为高等教育强国的美国,高质量高等教育不仅是教育系统多样化,而且拥有符合大学发展规律的创新制度,与时俱进的教学改革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领跑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还引领了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
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和政策等因素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最直观的外部因素,但影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最根本因素是高等教育是否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改革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前述五国的高等教育改革都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与时俱进地谋求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最终使高等教育发挥出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基本特征分析
观察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兴衰历程可以发现,高等教育从最开始的迫于经济社会变化,不得不为了适应社会需求而被动做出改变,到后来为了带动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而主动谋求改革创新发展,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由被动改变到主动发展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建设优质的高等教育,培养高质量人才,从而发挥引领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始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各高等教育强国都有着相对独立的特点,总结归纳起来,主要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
在不同的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模式都是所属时代最适宜的。最早的大学创建于意大利,英国在意大利办学模式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了现代大学的雏形,法国则依据时代的需求,建立新型高水平的大学,德国则集他国优势于一身树立了现代大学的完美典范,而美国则在制度、教学方式等方面全方位地为树立世界大学典范添砖加瓦,经过不停地升级变换,从片面的改革到全方位整体地融入时代发展的元素,历经三百多年,才出现了诸多的世界一流高等学府。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每经历一次转移,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经历一次进步,在跌宕起伏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不断完善,与时俱进,逐步茁壮成长为生命力顽强的时代最优的高等教育。
(二)重特色化发展,坚持与时俱进
时代的变迁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保持特色化发展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适应经济社会变化的关键。意大利高校数量繁多、英国拥有别具一格的学院制和导师制、法国开创了专业教育和精英教育模式、德国建立了柏林大学模式,还有美国倡导自由和自治之下的多类型高校,各国的高等教育不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亦或者管理方法,都不相同。自19世纪开创专业教育和精英教育以来,各国便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特色化发展,譬如德国和美国都在建设具有自己本国特色的大学,以特色化发展走向世界高等教育舞台的中心。中国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既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尊重自身的高等教育文化,与时俱进,适应本土生长环境,又要形成大学的独特个性,凝练出中国特色,借鉴他国发展经验,实现优势互补。
(三)注重人才培养,推动社会发展
培养什么人始终是教育发展的首要问题,不论是何种教育,最终的结果都表现在人的身上。高质量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最主要的目标,高质量人才必须要技术够硬、素质够高、品质够好,符合人自由发展的需求和时代发展的需要,能够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最开始,意大利等国的高质量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为了适应社会变化发展做出改变之后带来的结果,自19世纪法国提出专业教育和德国“教育兴国”政策出台之后,高质量人才培养便成为了高等教育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主要任务,培育出诸如柯西、高斯、黑格尔、马克思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而后来的美国则以“出类拔萃的毕业生培养质量、卓越的大学理念以及超凡的科研实力”闻名世界[7],具有世界代表性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得主大多出自高等教育强国。无论是在哲学、教育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还是在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方面,高等教育强国都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代表人物,这些高质量高水平人才不仅推动了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世界各国都影响深远。
(四)力争自主创新,引领时代发展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新的因素和新的需求,高等教育系统也会随之显示出不适应,只有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主动将新的因素吸纳到教育系统中,让新因素对高等教育系统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让旧的高等教育系统发生改变,保持发展活力与生机,才能发挥出高等教育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如英国通过不断创新与变革,形成了“古典大学、近代大学、多科技术学院、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和开放大学等多种形式并能有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8];再如美国具有多元化和创新性的教育系统,不仅开创了研究型大学模式、服务社会发展的高校新模式、通识教育模式等,还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兴趣发展,建立学分制和选修制。教育展现出的蓬勃生命力不仅仅关乎教育本身,也会关乎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是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自主创新是教育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关键,也是高等教育自身保持发展活力必不可少的元素,“优质”的高等教育应当是主动进行变革创新去适应新社会的需求变化,主动保持自身的发展活力,适应新时代对教育的要求,甚至以教育的超前性引领这个时代。
三、未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然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需要探索高等教育新的特色化发展思路,以满足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9]。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要求我们必须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挑战[10],所以我们提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强调要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追求优质的行动理念、过程[11],“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强调高等教育活动的整体性,指向高等教育的未来和理想[12],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仅是为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贡献力量,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人”的优质发展,即实现自身的自由发展,同时又具备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
有学者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回归世界教育中心地位,且中国具备重回世界教育发展中心的优势和潜力[13]。我们能不能在2030年成功回归世界教育中心当前并不可知,但我们提倡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五大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题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要让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发展,发挥出高等教育引领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需坚持与时俱进,实现内外统一的发展
提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身就是因应社会需求变化而适时提出的,但高质量的建设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工程,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应当结合经济社会出现的新变化,与时俱进地丰富其内涵。此外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还应注重发展的内外统一,首先是要坚持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发展需求内外统一。学校是高等教育孕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阵地,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不仅要在学生培养、知识创新、学术活动等方面强调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还应满足学校外部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不可分割,社会发展需要教育的助力,教育发展也需要社会的支持。但高等教育的发展也需要守住本心,历史已经证明,不顾及社会发展需求的教育会被淘汰,完全沦为社会奴隶的教育也会自取灭亡,就像19世纪末沦为战争工具的德国高等教育那样。其次是要坚持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中西方的内外统一。不得不承认,目前西方高等教育在某些方面的内容确实比我们丰富,我们不得不向其学习。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是教育沟通与交流的最终目的。现代大学模式起源于意大利,经过英国和德国的升级,完美树立起了现代大学的典范,学院制和导师制虽源起于英国,却也能走向世界,诸如此类,靠的便是教育的交流与沟通。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即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我国高等教育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主动寻求国际交流与合作,与时俱进地加强产学研融合,推动知识体系创新与协同育人,培养我国社会发展所需的创新型人才,有能力和条件的高等学府要主动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与标准的制订当中去,为国际高等教育的评价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二)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需注重人才培养,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泉和动力
高质量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高质量人才,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人才能够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能够为时代的发展贡献力量。人才培养是国之大计,力求从国家层面进行引导,19世纪法国和德国的教育改革就明确提出要培养各类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20世纪中期的美国更是将人才培养的目标写进了教育法,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高质量人才又为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实现了有机的内循环,所以我国的高质量高等教育必须要重视高质量人才的培养。为了更好地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学府,我国提出了“双一流”建设计划,“双一流”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准,我国要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就必须继续坚持以“双一流”建设为目标导向。我国要建设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14],不仅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还要建成文化强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我国拥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是我国未来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力量源泉。因此,在未来,我国各大高校更应当秉承文化传承的理念,结合时代变化,有机地将中华文化精髓与世界先进文化相结合,将文化强国建设落到实处,所培养出的高质量人才必须要具备将知识转为力量的能力,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三)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需强调自主创新,引领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进步就会被赶超,不创新就会被淘汰。如今的世界,科技在多样化发展、产业在多样化升级、人的需求和发展也在发生着变化,承担高质量高等教育建设发展任务的高校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多样化发展,以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例如美国最先依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引入到课堂教育中,翻转课堂和慕课等新的先进教学方式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给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自身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在大数据空前繁荣的时代,在教育领域将会大量应用人工智能、VR技术、大数据乃至未来智能机器人[15],充分运用网络超时空的优势,给高等教育插上信息技术的翅膀,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共享新模式,开发多元特色的优质教育资源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多元化需求[16]。技术进步催生了新产业、新科技领域对高质量人才的新需求,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应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业的形势,走在时代需求的前端,预见性地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质量人才。高校需要主动推进教学理念、管理方式和体制机制等的创新,实施教学内容、办学模式、管理制度等的改革,只有走在时代发展前沿的高等教育,才能够引领时代的发展。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构建新的发展格局,置身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的高等教育,也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新发展格局,优化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调整教育机构与结构布局,提升教育创新服务能力,形成新的教育评价机制,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并开拓开放合作新局面,整体提升高等教育高质量,最终实现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