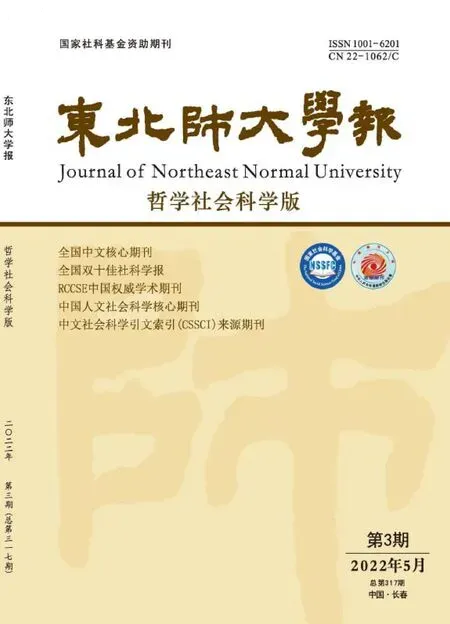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社会力量及其协同
张宝予,高 地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一、问题的提出
价值观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协同联动。其中,社会主体是世界各国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力量。新时代,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意识形态新态势、超级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如何运用社会力量不断提升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是党和国家多年来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统筹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深入到群众生产和生活中去”。可见,建立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协同教育格局已经成为价值观教育创新的重要方略。此外,“构建政府、社会、学校协同联动的‘实践育人共同体’”“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等重要理念均充分体现出党和国家在认识价值观教育社会协同发展和建设规律上的理论创新与思想突破。
环顾世界,价值观教育究竟该如何激活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力量、拓展参与渠道、形成教育合力,是各国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议题。国内学者主要从协同论视角探讨价值观教育的多元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有学者认为,在价值观教育的社会协同中,“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协同的领导者,政府是主导者,社会组织是传播机制的协作主体,人民群众是整体协同机制的受众主体”(1)周利生、汤舒俊:《红色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102—103页。。还有学者认为,多元主体协作方式既有学校内部协同,也有学校与社会教育组织、文化机构、社会团体等组织的多元主体协同(2)王丽萍、郑百易:《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学校德育协同实践与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42页。。也有学者强调,虽然目前政府、社会组织、学校等多元协同主体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进一步凸显,但仍面临价值观教育目标偏离、形式主义、教育有效性不足等问题(3)洪晓畅,毛玲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协同优化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0期。。国外学者则更注重实证调查和案例分析。在价值观教育社会协同的实证探究中,影响较大的要属施瓦茨(Schwartz)建构的个体基本价值观模型。巴迪(Bardi)和施瓦茨依托自我督导、刺激、享乐、成就、权力、安全、遵从、传统、博爱以及仁慈这十种价值观类型(4)Shalom H Schwartz,“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92,pp.5-13.,比较分析不同价值观与各自相应的价值表达行为之间系统的联系,结果发现大部分个体价值观与其对应的行为具有高相关性(5)Anat Bardi and Shalom H Schwartz,“Values and behavior:Strength and structure of relations”,Pers Soc Psychol Bull,Vol.29,No.10,2003,pp.1207-1220.。2000年,菲尼(Phinney)等人将家庭结构和社会环境作为自变量,考察家庭结构变化和社会环境迁移对个体价值观的影响,发现相较于非移民同龄人,移民儿童受父母的价值观影响更大(6)Jean S Phinney,Anthony Ong and Tanya Madden,“Cultural valu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value discrepancies in immigrant and non-immigrant families”,Child Dev,Vol.71,2000,pp.528-539.。其他关于父母等家庭成员对个体价值观影响的讨论也可见于库欣斯基(Kuczynski)(7)Leon Kuczynski,Sheila Marshall and Kathleen Schell,“Value socialization in a bidirectional context”,Parenting and the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s: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Theory,ed.J C Grusec,L Kuzynski,.New York:Wiley.、克纳福(Knafo)(8)Ariel Knafo-Noam and Shalom H Schwartz,“Value socialization in families of Israeli-born and Soviet born adolescents in Israel”,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Vol.32,No.2,2001,pp.213-228.的调查研究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关于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实证研究体系目前还处于建设之中,有关社会力量参与价值观教育的社会调查仍处在探索阶段。但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就现代价值观教育来说,其与传统价值观教育的一个重要分野就在于,学校等教学研究机构不再是单一的价值观教育主体,社会人员、社会资源已经成为影响价值观教育效果的主要因素,这些社会力量逐渐建构出紧密合作的服务网络,极好地体现了现代价值观教育的理念和要求。换言之,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价值观教育,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观教育社会协同发展导向,不断助力并提升我国价值观教育层次和水平,是推进现代价值观教育体系建设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
有鉴于此,本文着眼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现实基础和总体状况,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共抽取美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以色列、加拿大、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巴西十国受访者调查问卷6 491份,其中有效问卷6 274份,样本有效率为96.66%。针对上述有效样本,我们围绕社会人员、社会资源等影响个体价值观养成和发展的核心问题,采用频次分布等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十国数据的平均数、标准差、百分比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十国受访者对“谁来协同”“用什么协同”“如何协同”等问题的评价;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方法,对不同国家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与问题评价之间的差异性进行检验,进而描绘当前国外价值观教育中社会协同的总体状况和客观评价。
二、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社会人员协同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价值观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的教育。因此,价值观教育研究应回归到具体的社会交往之中,从社会交往主体——社会人员的分类构成入手,进一步考察价值观教育中社会人员的协同参与过程及建设机制。综观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发展历程,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开始了社会人员参与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探索。国外价值观教育涉及的社会人员众多,其中既有基于血缘、姻缘联结而具有世俗权利义务关系的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又有基于地缘、业缘联系而参与共同公共事务治理的社区人员,还有基于神缘、亲缘基础而具有相同信仰的宗教团体成员。
(一)发挥家庭成员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先发优势
正如瑞士教育学家裴斯泰洛奇(Pestalozzi)所言,“家庭是每个人自然教育的基础,是每个国家教授社会道德和生活的学校”(10)布律迈尔:《裴斯泰洛奇选集》第1卷,尹德新组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97页。。从个体角度来看,家庭是个体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过渡的最初场所,家长的言传身教、家庭的生活氛围、家族的习俗传统都深深地印刻在人的头脑和行动之中,对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先发性、奠基性、全方位的影响和作用。从历史发展来看,家庭在漫长的人类历史演化中一直承担开展知识传承、价值塑造、社会维系的重要责任,直到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家庭的教育功能才逐步让位于公共学校教育(11)Lilia Halim,Norshariani Abd Rahman and Ria Zamri,et al.,“The roles of parents in cultivating children’s interest towards science learning and careers”,Kasetsart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No.39,2018,pp.190-196.。为检验家庭成员在价值观教育协同中的重要性,我们调查了国外民众对“影响个体价值观养成和发展的人员因素”的总体评价,分别以1—4(“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表示受访者对测量问题态度的强弱程度。调查结果显示,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是影响个体价值观养成的重要因素,其中对父母影响个体价值观养成的评价最高(3.63),且在十国受访者的评价中均排名第一。可以说,国外绝大多数民众都认为家庭成员正在价值观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应该探索家庭成员的价值观教育功能,以实现家庭、学校的协同联动。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彰显家庭的价值观教育功能,各国纷纷以颁布法律政策的形式明确家庭的价值观教育职能,要求父母等家庭成员将道德养成和价值培育带入日常生活中。例如,新加坡政府在1991年颁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明确提出了“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并要求通过婚丧嫁娶、岁时节日、家庭聚会等多样化方式传播重视家庭的价值观,不断增强家庭凝聚力(12)Shared Values (Singapore:Singapore National Printers,1991),1,http:// nus.academia.edu/LiannThio/Teaching/24015/White_paper_on_shared_values_1991_,2021年1月10日。。日本《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提出,教育的基本点在于家庭(13)文部科学省:《21世紀教育新生プラン》,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ugai/21plan/p0.htm,2021年1月10日。。近年来,日本以父母—教师协会(Parents Teachers Association)为载体,大力通过家庭教育讲座、座谈会、学习交流会等方式不断强化父母的德育意识和德育能力,鼓励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积极围绕礼仪规范、家风家规开展价值观教育,以培养子女成为遵守社会规范的合格公民。家庭在英国也是主流价值观培育的重要主体。英国的父母通常将子女的“生存教育”同“绅士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建设良好的家庭环境、丰富的实践体验、统一的家校教育目标等促进子女的健康成长,意在将子女培养成身体、道德、文化、精神、情感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
(二)通过社区人员推动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发展
社区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与社会结合的社会文化现象和社会实践活动,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开展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作为一种社会教育载体,社区能够从价值体验和价值实践维度发挥着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所不能及的重要功能,使学生在社区服务和社区工作中形成“利他价值观”,通过亲身社会体验提升共情和帮助他人的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社区教育往往并不呈现为自发的独立教育活动,而是在与学校的协同合作中共同实施的。正如新品格教育代表人物里克纳(Lickona)所言,“新式价值观教育要取得长久成功,必须依赖学校之外的力量,即学校和社区应当共同努力,来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并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14)Aynur Pala,“The need for character education”,Int.j.social Sci.humanity Studies,No.3,2011,pp.23-32.。
社区人员作为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决策实施的重要主体,是各国开展价值观教育的主要社会力量。由于通过社区人员开展的价值观教育主要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过程,因此国外社区人员较为注重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挖掘价值观教育元素,并将其融入社区生活以及社区活动之中,让学生在多样化、实践性、综合性的社区服务中感受作为公民的意义,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一些学校同社区一起选择价值观教育主题、制定价值观教育计划,地区媒体、公民组织、青年团体等社区机构参与组织价值观教育计划的实施。比如,有的学校聘请律师、法官、军人、警察、立法者、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等,就法治价值观及其践行中的问题向学生进行讲解和阐释。同时,社区会为学生提供福利院或养老院、特殊学校、医院、图书馆或博物馆等公共场所从事社会公益或志愿服务活动的学习机会。通过这些活动,引导学生关注公民参与和公民学习,发展个体对各种公共价值问题的理解、阐释和分析能力。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许多社区都组织了服务学习、志愿服务等社区活动,这些活动都负载着丰富的价值意蕴,包含很多公共价值议题和社会问题,成为拓展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加拿大安大略省约克地区教育委员会开展的“品德问题”项目调查,就将社区人员提升到了同家长、教师一样的高度(15)罗洁、时龙:《新时期青少年德育的探索与创新 北京2006年青少年学生公民教育国际论坛文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3—84页。。可见,社区人员作为帮助学生习得良好品格的重要主体,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开展价值观教育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三)发挥宗教人员在价值观教育中的教化功能
宗教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具有宗教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传播精神价值的重要载体。中世纪时期,宗教教育俨然成为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形式。近代以后,虽然宗教势力逐步让位于资本与技术力量,但宗教依然在个人精神慰藉、社会心态调节、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其中,宗教人员是连接宗教与社会民众的桥梁。宗教人员不仅是传播宗教教规和宗教知识的人员,同时也承载着传递宗教价值观的教化功能,注重引导社会民众认识和认同宗教世界中的超验性、终极性价值理念。宗教教职人员包含各宗教专门从事教务活动的人员,如主教、牧师、阿訇、毛拉等,为社会民众提供宗教信仰、智慧福祉等教义相关内容。主教、牧师、副牧师、长老、教士传播的是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天堂地狱说等耶稣思想和基督信仰,阿訇、毛拉传播的是穆斯林必须尊重、履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公益义务,等等。不同宗教、宗教团体具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人们内在情感、心理状态及其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导致人们在思想观念、生活态度以及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目前世界很多国家的宗教信仰都在日渐衰弱(16)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全球化视域下宗教信仰的兴衰及其发展趋势》,叶丽娟译,《国外社会科学前言》2020年第12期。。在我们调研的9种影响价值观养成的人员因素中,“宗教团体人员”排名倒数第一(得分2.39)。且除巴西以外,宗教人员在其他九国受访者的重要性评价中均位列倒数第一。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表明,宗教对国外民众价值观的影响已经有所减弱。纵观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历程,宗教与世俗之争可谓一条主线,贯穿于现代国家兴衰成败演进之中。聚焦价值观教育领域,对于很多国家而言,拥有宗教信仰是其公民的普遍特征。价值观教育作为一种具有国家意识形态属性的,兼具政治学和阶级性的世俗教育,在推行过程中难免会引发民众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价值矛盾和冲突。如何使具有宗教信仰的公民能够对国家价值观与价值观教育形成真切认知与深刻认同,是国外价值观教育在历史和现实发展中始终绕不开的一个重要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价值观教育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各国通过家庭成员、社区人员和宗教人员开展价值观教育在教育目标上是相互协同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家庭成员、社区人员、宗教人员实施价值观教育的出发点和整体定位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都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培育公民精神、塑造公民性格、建立公民文化,从而造就具有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社区人员、宗教人员在具体的价值观教育目标上已经形成差异化协同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家庭成员开展价值观教育,主要是在家庭成员互动中帮助孩子养成责任意识、增强自理能力,成为知礼守礼讲理、独立自主的文明人;通过社区人员开展价值观教育主要是在社会实践活动和社区服务活动中培养具有公民权责意识、社会参与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的社会人;而通过宗教人员开展价值观教育则是在布道、传教及相关宗教活动中培养具有超验性、终极性价值理念的宗教信徒。三者彼此呼应、相互支撑、紧密相连,共同助力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总体布局和丰富发展。
三、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社会资源协同
发挥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体的重要力量,离不开各类社会资源的协同支撑。就国外而言,有三类资源在价值观教育实践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政治资源,即价值观教育的制度保障;二是经济资源,即价值观教育的资金保障;三是文化资源,即价值观教育的精神保障。
(一)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政治资源
所谓政治资源,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将政党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并加以贯彻实施的资源。政治资源是一个包含许多因素的集合体,对政治资源的分类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和探讨。当前,国外学者大多采取“三分法”透视政治资源的结构,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埃齐翁尼(Etzioni),他将政治资源分为实用性资源、强制性资源和说服性资源三类(17)Etzioni,“The active society:A theory of societal and political processe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8,pp.357-358.。基于对政治资源概念的界定,我国学者陈文新按政治资源表现形态不同,将政治资源划分为实体性政治资源和规范性政治资源两类(18)陈文新:《当代中国政治资源配置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32页。。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政治资源表征着国家对于价值观教育的总体设计和根本要求,决定着价值观教育的本质和目标,往往表现为政府和执政党对价值观教育的顶层设计。本研究运用政治资源类型划分的基本方法,立足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社会协同情况,将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政治资源划分为以下三类,即实体性政治资源、强制性政治资源和说服性政治资源。所谓实体性政治资源,是指为价值观教育制定制度、颁发政策、提供保障的部门或机构,可分为象征国家政权、贯彻国家意志的组织实体,和保障教育改革、教育发展计划顺利进行的经济实体。例如,美国的众议院与参议院、英国的上院与下院、法国的参议院与国民议会、荷兰的第一院和第二院等组织实体,以及各国财政部、地方政府等经济实体是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典型代表,为学校价值观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而由实体性政治组织颁布的教育政策、教育法律、教育法规等则构成了价值观教育的强制性政治资源。在我们的调研中,针对“法律法规”影响个体价值观养成和发展的问题,十国民众给出了较高的认可度,平均值达到了3.18。除日本外,其他九国的态度评分也均达到了3分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各国民众普遍赞同法律法规对价值观教育的积极作用,并期待政府能够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价值观教育施以正向的影响。以澳大利亚为例,自1989年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连续出台《积极公民教育》《霍巴特宣言》《再论积极公民身份》等相关报告,成立议会教育局、宪法百年基金会等教育机构,为价值观教育计划的顺利推行奠定前期政策基础。1999年起,澳大利亚又先后出台《学校价值观教育国家框架》《国家青少年发展战略》等政策法规,实施“四年价值观教育计划”,通过对价值观教育的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形成了对价值观教育巨大的推动力和强大的号召力。相较于实体性政治资源和强制性政治资源显在性、统治性的特征,说服性政治资源最大的特点便在于其旨在通过间接性、柔和性的教育方式,将价值观培育融入各项实践活动中,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其中,英国的BBC,美国的FOX、MSNBC,加拿大的CBC和半岛电视台等社会媒体是国外价值观教育中典型的说服性政治资源。
(二)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经济资源
经济资源是价值观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物质保障。虽然价值观教育的经济资源来源是多方面的,但在我们调查十国受访者对政府价值观教育举措的态度问题上,88.8%的受访者赞成或非常赞成“政府应为价值观教育提供政策、人员、资金等支持”,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政府作为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最大权力主体,应该予以价值观教育最大的经济资源支持,以建构起价值观教育的经济保障体系。而聚焦到各国具体的教育计划和经费资助上,各国政府都竭力为价值观教育提供最大限度的经济资源支持,包括活动经费支持、教学资源支持、教师经费支持等。在美国实施品格教育时期,美国国会于1994年向品格教育研究项目划拨3 000万美元经费,专门用以资助品格教育相关研究。此外,自1996年起,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拨款270万美元,资助全美数十所中小学创立青少年“品格教育”样板,供全国中小学效仿。教育部还专门设立“蓝带奖”用以奖励每年对青少年品格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群体。在澳大利亚霍德华政府实施的“发现民主”公民教育课程改革计划中,政府分两个阶段(1997—2000年和2000—2004年)分别资助1 800万澳元和1 360澳元,推动了该计划的切实实施。2004年,澳大利亚政府又宣布在财政预算中拨款2 970万澳元,用于建立和发展国家教育计划。该计划推动了一系列重要项目的开展,其中最大的项目要属价值观教育优秀试点学校计划,影响了澳大利亚316所学校、51个集群,共计10万名学生。此外,日本政府为加强中小学价值观教育,还专门增加2亿日元预算,用于修订中小学“心灵笔记”、选派校外道德教育专业人士、帮助该地区学校和学生家长构建特色道德教育共同体等,全力推进日本德育工作。再如,俄罗斯政府为有效施行《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要》,从2001年开始至今每年都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专项拨款,在2016—2020年间更是高达17亿卢布,这些经费被用来开展与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的活动,以及为相关执行单位提供资金保障。
(三)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在价值观教育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价值观教育内容的重要来源,是保障价值观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文化资源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具体可分为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两类。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括记录和承载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关文献资料,各发展历程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凸显实践性、沉浸式价值体验的国家博物馆、历史遗迹、古建筑、宗教类雕塑等,是各国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资源。在教育资源影响价值观养成和发展问题上,十国受访者普遍赞同“书籍、电影、电视剧等文学艺术作品”(3.08)和“博物馆和历史遗迹”(2.80)在价值观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该类资源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有史密森人类历史资源库、美国自由女神像、以色列圣殿博物馆等,分别指征着各个国家、民族最渴求的政治诉求和核心价值理念,为学校价值观教育提供了信息丰富、形式多样、类型众多的物质文化资源。相较于物质文化资源有形性、显在性的特征,精神文化资源是以不可见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活动与社会交往之中的。精神文化资源是社会精神财富的总称,是以语言、宗教、科学等为符号传播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化科学知识,助力形成世界观和精神结构的资源。思想价值观念类精神资源,重在培养个体成为尊重伦理价值共识、维护社会公德、具有人文价值理性的人。该类资源既包含满足人日常生活基本道德要求的世俗道德,又包含具有超验性、抽象性原则规范的宗教道德。前者涉及家国社会、日常生活的举止应对、规范要求等立足于现实此岸世俗生活的道德范型,多在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中体现。例如,国际流行的握手礼,日本、韩国、朝鲜等东方国家的鞠躬礼,伊拉克的贴面礼,欧美上层社会的吻手礼,东非男士之间触碰肩膀以表示欢迎和亲切,这些行为方式的差异究其根本就是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后者涉及引导公民在世俗生活中追求“神圣性”宗教道德等立足于彼岸理想世界的道德范型,多在《圣经》《古兰经》等宗教经典中体现。相较于思想道德观念类精神资源,文化科学知识类精神资源更加凸显培养个体对客观世界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和理解能力。文化科学知识类精神资源,重在培养个体成为尊重客观规律的具有工具理性的人。该类资源主要依托具有代表性成果的科学人才、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成果和交叉融合的科学平台。
综观世界各国价值观教育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各国价值观教育的社会资源协同,重点在于实现政治保障、经济保障和文化保障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政治保障的关键是在国家层面完善协同机制,建立全国性法律法规、教育政策、政府报告、教育计划,明确价值观教育责任、目标和内容,建立具体可操作的决策方法,确保政策机制的落实。经济保障的关键是要以经济资助支持并保障教育资源的充沛和政策实施的实效,使价值观教育的社会力量协同得到执行实现。文化保障的关键在于文化资源可以为价值观教育内容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供给,对价值观教育起到了导向和动力的重要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总的来看,社会力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主体。国外价值观教育涉及的社会人员众多,其中既有基于血缘、姻缘联结而具有世俗权利义务关系的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又有基于地缘、业缘联系而参与共同公共事务治理的社区人员,还有基于神缘、亲缘基础而具有相同信仰的宗教团体成员。国外价值观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十分丰富,在这方面集中体现为涵盖法律法规、教育政策、教育计划等政治资源,政府拨款等经济资源和物质及精神文化资源,三者同学校价值观教育相互协同、共同发展,从整体上实现了价值观教育的协同创新和结对共建。
当前,伴随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和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学校价值观教育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观渗透,这容易带来青少年思想观念变化加快、差异化加剧、价值观教育目标不断调整变动等问题。在传统的价值观教育体系中,教育者、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开始出现难以跟上客观现实发展变化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仅依靠教师群体不能满足新时代学生多样性、个性化发展的需求;课堂讲授的教育方式与新时代对青少年价值判断能力提升的要求相冲突;价值观教育内容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国家安全新内容、新趋势的发展变化;等等。这些问题都对价值观教育的亲和力、感染力、针对性和实效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因而,在价值观教育中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一方面将社会协同的理念贯彻进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力量的活力和创造力,促成主体多元、资源多样、活动丰富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同时,紧密结合各国社会人员与社会资源协同参与价值观教育体系建设的有益经验,从而为提升我国价值观教育理念与实践水平提供借鉴。
首先,学校价值观教育与社会力量要在具体的教育目标上做到差异化定位与协同化发展相结合。所谓差异化定位,是指以教育主体、教育载体、教育内容为考量推动价值观教育目标、教育发展定位的差异化,有利于价值观教育定位的鲜明与精准。就其差异化来讲,学校价值观教育主要是在各类课程的知识阐释和校园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回应社会现实问题,而社会力量参与价值观教育是让学生在具体的社会观察和社会体验中学习社会文化、内化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培养他们的健全人格。与差异化定位不同的是,协同化发展是指价值观教育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同步、协调,以实现教育目标互补性互动和和谐式发展。就教育目标的协同来讲,其关键在于必须坚持社会协同理念,建立好价值观教育社会协同机制,做到各种力量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协作配合,进而形成价值观教育的育人合力。
其次,还要做好全面的价值观教育资源部署。在国家层面,制定与价值观教育需求相一致的法律法规、教育政策、教育计划,做好价值观教育整体建设规划的统筹考虑、统一部署和统一落实;建立健全政府与其他社会力量的文化捐赠和资助的相关立法,保障价值观教育专项发展经费的合法、合理和有效使用;组建管理价值观教育社会力量的实体性政治组织和实体性经济组织,为价值观教育社会协同提供政治资源保障和经济资源保障。在社区层面,扶持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团队建设,为价值观教育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助力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理论与实践、想象与现实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家庭层面,家长既要提高自身素质、亲身示范,努力让自己成为孩子的榜样和偶像,又要与学校加强沟通、积极配合、优势互补,还要鼓励学生从学校走入社区,将价值观教育融入社区活动之中,进而助力形成家校社共育的适恰模式和有效途径。
最后,还应积极探索建立价值观教育社会力量协同的多元化评估体系。学校作为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应立足学校和学生发展需要,把握社会人员与社会资源协同规律,承担起制定评估细则、管理评估程序、反馈教育效果的工作责任,淡化单一性、结果性评估方法,强化过程性、发展性评估策略:一方面,提升专家学者、授课教师、学生代表等评估主体对社会人员、社会资源参与价值观教育的参与度、满意度情况;另一方面,加强对人力、物力、时间和经费投入等便于量化的数据统计与分析,进而精准把握价值观教育社会力量协同的程度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