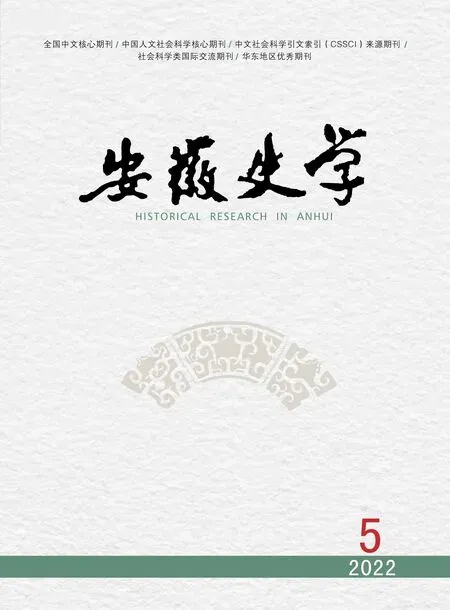明代驾帖制度考论
唐佳红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关于明代驾帖制度的研究,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其在明代司法体系中的特殊作用(1)参见栾成显:《论厂卫制度》,《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82年版;怀效锋:《明代中叶的宦官与司法》,《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赵晓耕、时晨:《平衡与牵制:明代厂卫与法司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专门的研究也已经开始(2)张金奎:《明代的驾帖与精微批》,《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4期。,但是对驾帖的渊源、性质与制度设计的初旨缺少深入剖析。笔者专就这一问题粗发议论,冀可加深对驾帖及明代司法体制与政治的认识。
一、驾帖之起源与其性质
驾帖是明代史料中常见的一个名词。唐宋时期已经称官府文告为“帖”,明代也常以“帖子”指称各种公文,凡发出律令、文券、奏疏之类,如御帖、奏帖、传帖、札(劄)帖、票帖、印帖等,是以皇帝所发出的文书命令甚至圣旨,也可称为帖子。如靖难间赵清为建文帝守彰德:“上(成祖)兵至城下,遣人招之,清对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许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3)《明太宗实录》卷178,永乐十四年七月丁未,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941页。而“驾”即指“圣驾”,如锦衣卫之牌照称“驾牌”,皆因“锦衣卫校尉专为直驾而设”(4)《明武宗实录》卷1,弘治十八年五月壬寅,第11页。,其义类似。驾帖,则是专指皇帝之帖子。目前所见,驾帖一词最早见于史籍在永乐十年(5)参见黄佐:《南廱志》卷2《事纪二》,《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但使用驾帖事例的记载则更早。据《立斋闲录》转录:“(永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该校尉刘通等赍帖一将科,引犯人张鸟子等男妇六名为奸恶事;又引犯人杨文寿等男妇五百五十一名为奸恶事。”(6)宋端仪:《立斋闲录》卷2,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40,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48页。校尉刘通等所取都是建文罪臣练安的姻戚,当是奉成祖旨意,取人进京治罪,其所赍之帖,即当是驾帖。
明代使用驾帖所赍者多为锦衣卫、内监等宫禁近臣,其行使与诏旨相似,驾帖行文形式也与诏旨相去无几。如广东布政使彭韶奏议云:“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奉到驾帖,该司礼监太监怀恩等于文华殿钦奉圣旨,恁写帖子:去说与总镇两广太监顾恒并都布按三司等官知道,彼处地方所产一应土物及各样药饵等项,递年委令精通人员,依时采取办验,真至如法造办,装盛封记,陆续差委的当人员管送来京。毋得指此为由,因而扰害下人,违者治罪不饶。钦此。钦遵。”(7)彭韶:《为陈言进贡事》,《彭惠安集》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页。奏议中所言帖子,显系彭韶所奉到的“驾帖”,“去说与……钦此。钦遵”一语,为抄录驾帖上的全部文字,行文与诏旨已无区别。再如《弘治问刑条例》所注事例:“孙三郎系上直校尉,听候宣官赍送驾帖人数,比与上直官军,尤为紧要。”(8)黄彰健编:《明代律例汇编》卷13《兵例一·宫卫·胡琼集解附例》,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第617页。上直校尉即锦衣卫上直校尉,宣官即锦衣卫宣官,职事奔走奉宣。锦衣卫系内卫,所赍驾帖即“奉旨”而往。又据《皇明条法事类纂》:“宣德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该御马监太监鲁安奏:本监勇士小斯每来告,常川在里头上宿骑马,外厢兵马司又叫他坐铺巡更。奉宣宗皇帝圣旨:免他坐铺,着他上宿骑马,着锦衣卫批驾帖,说与五城兵马司知道。钦此。”(9)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7《吏部类·禁约云南土吏不许父子兄弟相继营充》,刘海年、杨一凡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这正是《大明会典》中所言“旨意一出,即差该直校尉领驾帖,备批旨意于上”的“旨意”。(10)万历《明会典》卷178《刑部二十·伸冤》,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05页。不仅如此,驾帖到目的地后还当如诏旨一样当众开敕,宣读全文。由此可见,驾帖的行文、格式、颁宣已绝类于诏旨。
另外,从法律上对差官所赍文书的明文要求来看,也可证明驾帖实为有别于诏旨的皇帝文帖,洪武十五年定各司文移往来,有云:“凡差使人员,既有所赍公文,其差帖上止写去某处公干,不必云写圣旨。”(11)万历《明会典》卷76《吏部三十四·行移署押体式》,第445页。显然此处所赍“差帖”出自圣驾,但不写圣旨。《大明会典》又云:“凡差使人员,不许接受词状、审理罪囚,违者以不应论罪。”(12)万历《明会典》卷177《刑部十九·问拟刑名》,第901页。此“差使人员”,必有干涉提勘人犯之事,后来形成的专用于差遣办事、提人取物的“驾帖”规制,应即源于此,唯其多承皇帝派遣,不必以程序繁琐的诏旨之名下宣。
在明确了驾帖作为一种诏旨文书的前提下,试从明代诏旨颁发形式入手,进一步讨论驾帖在性质上更近于哪一种诏旨。据《大明会典》:“朝廷颁命四方,有诏书,有赦书,有敕符、丹符,有制谕、手诏。诏赦先于阙廷宣读,然后颁行;敕符等项,则使者赍付所授官员,秘不敢发。”(13)万历《明会典》卷74《礼部三十二·开读仪》,第435页。可见明代诏令就颁宣形式分为两类,一为诏书、赦书,当宣读公开后再颁行;而敕符、丹符、制谕、手诏则为密封下发。据谈迁所言:“先是,山东巡抚上虞李懋芳忧去,颜继祖代镇,论其侵牟坐逮。懋芳在道,缇骑先候于杭州,议开敕于藩司。右辖黄鸣俊曰:‘某宦河南,驾帖开自臬司,重在刑名也。’二司互执,竟开读佑圣观。”(14)谈迁:《枣林杂俎·佑圣观开敕》,《续修四库全书》第1134册,第772页。从这一则史料来看,驾帖为密敕,正属于前述“秘不敢发”的诏旨之类。《大明会典》还详细规定了敕符的颁布、开敕以及宣读地点、迎接礼仪等细节(15)万历《明会典》卷74《礼部三十二·迎接诏敕仪》,第436页。,而驾帖行文、格式、颁宣方式等已经与敕符极其相似。如“《传信录》言:景帝未崩时,有驾帖取楚世子入继,世子欲行,有长史伍姓者止之曰:‘事虽如此,宜待金牌敕书来,然后行未晩。’”(16)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4《史乘考误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6页。敕书即敕符,可见驾帖与敕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的功能,因此常被相提并论。
事实上,驾帖与诏谕圣旨的使用形式也甚为相似,部分场合两者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成化十九年,王恕上疏云:“祖宗时,差内臣出外公干,或赍敕书,或赍圣旨帖子,必明开所干公事缘由,或所取物件数目。”(17)王恕:《论中使扰人因乞休奏状》,《王端毅奏议》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第550页。这里的“敕书”,是指成化十四年郭景赍敕书往安南国与钱能收受贿赂、交通外国之事;而“圣旨帖子”即指王敬同年赍驾帖“前往常州府、苏州府采取药饵,收买书籍”,借机“拘大户,索要银两借采药饵”之事。王恕径以“圣旨帖子”一词指称驾帖,可见在明人心中,驾帖在某些场合甚至已经等同于圣旨。又据明律一条:“诈称御史,赍驾帖拿人,比依诈传诏旨律。”(18)黄彰健编:《明代律例汇编》卷末《附录》,第1055页。亦可见在当时官方意识中也早已将驾帖比于诏旨。
由此可以推见,早期“驾帖”一词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并不拘其用于提人、取物、勘事或是径作为圣旨传达圣意,不过表明其为秉承皇帝旨意的文帖。永乐时尚不为常例,似尚未有专名,称帖、帖子、驾帖者俱有。驾帖与正式诏旨有别,其所承载的事务多不关涉经纬大典,颁发形式亦从简从便,其实质系简约化的诏旨,类似于明中后期文书行政中的“手本”“札帖”等便捷文移体式。其颁发、执行与功能与敕符诏谕相似。驾帖因出令及执行的私人化及随意性,缺乏制度上的合理性和严格的规制,加之多为差遣厂卫所用,并不如诏旨具有皇帝诏书的全部威严和法律效力,这种性质为明代君臣对驾帖合法性的争论埋下了隐患。
二、驾帖制度化历程
驾帖在明代厂卫刑事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几成锦衣卫奉旨拿人的代名词,此处仅对刑事类驾帖的发展史进行专门论述。
锦衣卫奉驾帖捕人,参与刑事之始,当在成祖靖难以后。前引锦衣卫刘通赍帖事例,即为这一时期的事情。永乐时内官出使、分镇成为常态,是以驾帖开始用于内官差遣采办、出使、巡查等事务。内官承行旨意,防检较甚,因而查继佐评论宣德时“内侍犹不至如逆振时气焰也,宣庙刘宁之遣,出独制,且以宁清谨,始与御史同奉驾帖行”。(19)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5上《清介诸臣列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8页。
但是,为了有效制衡缺乏制度监管的锦衣卫,避免其脱离皇权掌控而恣行非法,开始实施六科签批驾帖制度。“凡锦衣卫奉旨提取罪犯,从本(刑)科批驾帖”(20)万历《大明会典》卷213《六科·刑科》,第1065页。刑科签批的驾帖只是关涉如决囚、捕拿、提人等刑事,如果驾帖差遣事情关乎其他情况,则相应由其他科臣负责,如事关虏获蛮夷、罪犯充军等事由兵科负责签批,关于草场、工料等事则由工科负责。,规定驾帖下发必须从刑科签批方才生效。征之《明会典》:“洪武元年,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后又移置于长安右门外,令六科给事中并锦衣卫官各一员,轮流直鼓,收状类进,候旨意一出,即差该直校尉,领驾帖,备批旨意于上,连状并原告押送各该衙门问理。”(21)万历《大明会典》卷178《刑部二十·伸冤》,第905页。此条规定与洪武时期最大的区别就是,驾帖兼涉锦衣卫、六科、皇帝三方,锦衣卫与六科共同预事,已略见驾帖由六科签批之制的雏形,后来驾帖拿人必须赴刑科签批的制度,应与此有相当的联系。洪武时期,凡受鼓下词状的案件,召取原告、批捕被告等,皆以六科给出的精微批作为凭据,刑部或都察院差人履行职责。到了永乐时,直鼓下为锦衣校尉与六科官,捕人则为校尉以驾帖而行,可见驾帖已渐用于处理刑事事务。至迟到正统时,刑科在驾帖的使用程式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如正统元年规定:“凡击登闻鼓诉冤、并锦衣卫等衙门捉获人犯、三法司处决罪囚奉钦依者,俱该锦衣卫直日官,将原给驾帖,填写缘由并人犯姓名。除鼓下词状从各科直鼓官批送外,其余俱送本(刑)科,列名批钤,以凭送问处决。”(22)万历《明会典》卷213《六科·刑科》,第1064页这是对永乐时登闻鼓受状的补充,驾帖已经可用于送问“锦衣卫等衙门捉获人犯”及“处决罪囚”。这一条例在实际上承认了长久以来驾帖专用于刑事事务的事实。
自正统以后,厂卫在刑事事务中的话语权剧增,事关厂卫逮治提拿等刑事的驾帖大量见于史籍,为人熟习。锦衣卫甚或无视法司不请驾帖径行逮捕,驾帖作为厂卫行事的主要法理依据,成为了明代朝野诟病的焦点。文官集团开始尝试对驾帖进行规范,冀图通过严格的制度化措施来防范驾帖的滥用、伪用。
成化时汪直捕拿兵部武选司主事仕伟,竟“不用驾帖,令数较(校)捽仕伟至,拷掠如之,即捉掠其妻孥”。(23)何乔远:《名山藏》卷95《宦者杂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84页。大学士商辂劾奏西厂“事皆出于风闻,暮夜搜捡家财,不见有无驾帖”,而中官“自言亲承密旨,得专予夺,百官进退,尽在掌握,擅作威福,虚张声势”,为害深远,因此强调“旨意必经于六科,防将来之假冒”,并请求革去西厂。(24)商辂:《请革西厂疏》,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38,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4—295页。商辂的上疏促成了刑科签批驾帖制度的规范化,他的制度依据即是将驾帖视为“圣旨”,强调六科在诏旨下达程序中的封驳职能。
成化十三年,云南巡抚王恕劾奏云南镇守太监钱能等人与郭景勾通安南事有牵连,都察院复奏后,随即差刑部郎中钟蕃等前往云南,逮捕钱能等人还京治罪。五天后云南中卫百户汪清又“来自京师赍捧驾帖”前往干涉,前后事体相悖,王恕上疏质疑道:“伏见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公文,及给批差官公干或提取犯人,俱于所在官司比号相同,然后行事。又闻驾帖下各衙门,则用司礼监印信,该科挂号,皇城各门印照出关防,所以防诈伪也,今赍来驾帖,既无监科印信字号,又无各门关防,此臣之不能无疑者。”(25)王恕:《驾帖不可无印信疏》,《王端毅奏议》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第507页。在这一事件中,王恕借机讨论长久以来驾帖伪滥,惊扰官民朘削地方的时弊,还严申驾帖必须由各科签批,强调“不可无印信”,以防止内官矫命。
王恕所说的给批,即后来所称的“精微批”,全称“精微印信勘合批文”,实系明代勘合的一种,因系司礼监精微科职理,盖精微印,故名。(26)伍跃认为,精微勘合与精微批文是为两种文书,参见伍跃:《关于明代勘合形制的再探讨》,《史学集刊》2021年第2期。但《大明会典》详述精微簿的使用,有勘合字号,在无更多证据的情况下,本文仍将精微批视为勘合文书。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已规定,一部分特殊案件由刑科或都察院给批差人提取犯人。(27)分见《诸司职掌》之《刑部·问拟刑名》及《都察院·问拟刑名》,《续修四库全书》第748册,第735、768—769页。永乐十九年,明成祖诏敕强调了精微批文的使用:“今后五府六部等衙门差人出外干办公事,务要办验有精微印信勘合,方许奉行。若无精微印信勘合,即系诈伪,所在官司就便擒挐赴京。”(28)傅凤翔编:《皇明诏令》卷4《成祖文皇帝上·殿灾宽恤诏》,刘海年、杨一凡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176页。内府六科廊存有印有特殊字号与骑缝印章的精微批文底薄,一式两份,一份分送各省府州县,一份由府部院等在京衙门向六科关领,领批者由此领相应事务的勘合批文后,该科签批,赴司礼监盖精微印,根据差遣内容赴目的地,比对勘合字号无误后方得行事,事毕后还需在期限内将批文送科回销,一应程式,俱有明文。(29)万历《明会典》卷206《工部二十六·杂行》,第1029页。精微批与驾帖在职能上均为出京公干之“差帖”,由六科给出,区别在于精微批为政府部门之公差所用,而驾帖为厂卫、中官等皇帝差遣所用,王恕将二者相提并论,为弘治年间对精微批与驾帖的讨论提供了先例。
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就此上言:“旧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员,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所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执送京师,此祖宗防微杜渐之深意也。而京城内外提人,乃用驾帖,既不合符,真伪莫辨,倘有奸人矫命,谁则拒之?请自今遣官出外,仍给批文以防奸伪。”(30)《明孝宗实录》卷18,弘治元年九月壬午,第437—438页。内官、校尉以驾帖出遣外地,多借此沿途需索,扰害地方,如天顺二年,李贤谈到锦衣卫官校“一出于外,如狼如虎,贪财无厌”,英宗遂下令“今后非大故重事不遣”(31)李贤:《天顺日录》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433册,第 204页。,但积习已成,始终未能矫正。何乔新正因驾帖易于作伪,遂援引故事,请今后凡差人出京办事,无论提人取物,悉以精微批代替。
何乔新要求锦衣卫在京可用驾帖,在外则必须与府部衙门一样同赍精微批,一则确保其秉承圣意,一则使其与法司相衡。但他所说的“旧制”,并无故事可援,如前文王恕认为驾帖出京当有京师城门关防印记,并不提及“驾帖不出京”。何乔新所据当是成化十九年议定事例:“两京各衙门斟酌,事重路远的,给与精微批文;事轻的,不拘远近,只给与札帖。”由于精微批制度过于繁琐,文移往来牵涉多方,繁琐不便,故在实际行政程序中,亦多不给批,径以札付、手本、帖下等简易公文代替之。(32)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1《吏部类·制书有违》,第464页。何乔新将驾帖比于“札帖”等简便公文,以为驾帖出京拿人“事重路远”,必须以精微批代替。
何乔新的建议得到孝宗的支持,他当即敕令,今后提人勘事“所司其如例行之,应给批时,毋得稽误”。(33)《明孝宗实录》卷18,弘治元年九月壬午,第437—438页。自此以后,“驾帖不出京”这一制度通例屡被后人援用。然而驾帖捕人,由来已久,已难遽改。故而这道诏令发布以后,旗校提人,仍旧“率赍驾帖”。(34)《明史》卷94《刑法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12页。弘治十一年,五府六部等应诏言事又强调:“今后差官给精微批,锦衣卫官校不许仍赍驾帖,为害非细。”(35)《明孝宗实录》卷18,弘治元年九月壬午,第437—438页。十三年,五府六部条陈再次言及驾帖伪命:“近年以来,官校差出,止赍驾帖,少有给批目。”(36)《明孝宗实录》卷162,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第2925页。可见,弘治初年的敕令执行并不顺畅。另外,驾帖以简便高效为胜,兼具诏旨的权威,本身难以受公共法律约束。弘治十四年,五府六部提议:“今后叛逆等事,方差锦衣卫官校赍驾帖。其余俱下法司转行巡抚、巡按官勘问,有应解京者,就彼差官押解。”(37)《明孝宗实录》卷175,弘治十四年六月丙午,第3202页。该提议准许在特定情况下使用驾帖勘事,相对于先前的规定已经有一定松动,且已经不再提及精微批。孝宗以此议关涉地方,令地方“具奏定夺”,未能准行。
尽管精微批在两京府部衙门和厂卫之间的推行都遭到了阻力,朝官们仍旧坚持用精微批来取代驾帖。正德元年,六科给事中陈言再次重申弘治旧例,请“自今差人出外,止如旧例,以精微批给之。”(38)《明武宗实录》卷9,正德元年正月乙巳,第287页。然而武宗屡屡纵容宗室借用驾帖捕杀庄佃,已是滥逾前代。内阁大学士刘健即上疏言:“皇亲家人,妄奏畿民侵占田土,辄为出给驾帖,提解来京。镇抚司鞫问,俱与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处官司问理。”(39)刘健:《再具自劾疏》,《皇明经世文编》卷52《刘文靖公奏疏二》,第413页。嘉靖以后,世宗乾纲独断,使得驾帖逐渐朝向“突从内降”的中旨发展。嘉靖二年,栾州民赵纪向东厂讦告临洮府知府郭九皋,世宗遂差官校解拿郭九皋至京,陕西御史刘翀言,“东厂之设,专主缉访在京奸伪,无受理词状、远差官拿人之例”,六科及御史亦言其非法(40)《明世宗实录》卷32,嘉靖二年十月甲辰,第836—837页。,刑科左给事中汪思援引故事上疏曰:“朝廷成法,谓东厂不得受状,驾帖不得出京,郭九皋不可提问也。”(41)汪思:《容狂直广听纳疏》,孙旬辑:《皇明疏钞》卷35,《续修四库全书》第464册,第137页。世宗不听,并严斥科道官多事。可见弘治以来“驾帖不出京”的制度已经被皇帝破坏了。
综上,弘治时期驾帖的制度化是在孝宗有意弹压厂卫的背景下进行的(42)《锦衣志》云:“帝(孝宗)仁圣,委法秋官、御史台、廷尉,尝曰:‘与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以故缇骑逆自敛,不敢有所为。”王世贞:《锦衣志》,《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第665页。,官员提出以精微批代驾帖,其意是以恢复“祖制”为名,通过驾帖行用的规范化来限制厂卫。然对驾帖的限制亦限制了皇权,王恕在首次提出针对驾帖的各类关防限制时,其实已有借此限制明宪宗依靠镇守内官在外肆意掠夺的用意。弘治十八年,孝宗违反常例,给驾帖特遣锦衣卫赴南京勘事,引起举朝震动。科道官及刑部奏请停止以驾帖差遣勘事,孝宗反命“锦衣卫仍查累朝有无用驾帖出外提人事例以闻”。这预示了成化以来对驾帖制度化尝试的失败。
三、驾帖的中旨化
嘉靖时,驾帖滥用的状况愈加严重,使得驾帖逐渐朝“突从内降”的中旨发展。(43)中旨是一种不经内阁六科抄发而径自从禁中下发执行的旨意。“夫所谓中旨者,必其纤毫无与于外廷,而突从内降者也。”李应昇:《落落斋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48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45页。驾帖的中旨化,表现为其非但用于差遣执法,更可秉承皇帝意志裁断案件,干涉司法程序。这种趋势在正德年间就已显现,马文升指出:“累朝刑政,移于厂卫多矣,以顾命老臣及部院之九卿,不能得之圣天子之转圜,一武弁安知国法?往往窃之内降之旨,而能使人生,能使人死,为法司者,不亦难乎?”(44)尹守衡:《明史窃》卷13《刑法志》,《四库禁毁书丛刊》第6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其中已隐含着对皇帝以旨意参与法司事务的委婉批评。
明代君臣在驾帖问题上的矛盾在嘉靖朝愈加突显。嘉靖二年,礼科给事中张翀借灾异言事,指出监局以诏旨干涉政务,且“驾帖批钤,坏累朝旧规,而不计真赝”(45)张翀:《严天戒以保治安疏》,贾三近辑:《皇明两朝疏钞》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465册,第197页。,其所谓“不计真赝”实即暗指驾帖批钤不遵轨式,径出皇帝独制而不与有司相闻。嘉靖二年发生的李阳凤案则直接将法司与驾帖的冲突推上了前台。中官崔文家人李阳凤犯法被捕,崔文竟请得驾帖直接从法司取人至镇抚司鞫问,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任刑部尚书林俊强争之,以为锦衣卫夺法司之守,为越轨行为,拒绝承认驾帖的合法性,世宗不听,反以“违旨”之名究问林俊等人。明臣抗论其事,都将驾帖以“中旨”称之,并掀起了对中旨大规模的批评。(46)关于此事的梳理,参见唐佳红:《诏法之争与嘉靖初年政治——以李阳凤案为中心的考察》,《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皇帝以诏旨之威加于国法之上,使得法司进退失据,无怪乎林俊感慨朝臣处境“奉诏则废法,守法则违诏。悬命利刃,无复存身之地”云云。(47)林俊:《乞寝内降以正法守疏》,《见素集·奏议》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7册,第434—435页。驾帖得到皇权庇护,在与法司对抗时有恃无恐。嘉靖七年,刑部尚书胡世宁上疏指出“差官校赍驾帖出外,所过地方无不惊扰”,请“今后官民有犯,在内责之法司,在外责之抚按、按察司等官,作急提问完报,不许淹滞。遇有事体重大,合提在外关人犯到京问理者,行令各该巡按御史严限责差的当人员提解来京,以凭问理。非有事干机密,十分紧急重情,近在畿甸地方,不须再差官校”,世宗以“自有酌处”为名敷衍回应。(48)胡世宁:《应制陈言以弭灾变疏》,《胡端敏奏议》卷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8册,第 686页。
随着世宗取得“大礼议”的胜利,“朝廷之大事,皆出于中旨”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49)毛纪:《乞休疏》,《皇明经世文编》卷129《毛石二公集》,第1239页。,驾帖的专制色彩得到空前加强。刘最以劾奏内监崔文得罪,世宗命校尉逮下镇抚司,刑科给事中刘济直接指出当朝士大夫“缉执于宦寺之门,锻炼于武夫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的不合理现象(50)《明史》卷94《刑法志二》,第2332页。,将驾帖、厂卫与法司之间的关系对立了起来。嘉靖六年,南京礼部右侍郎顾清再次上疏请停差遣:“锦衣职侍卫,祖宗朝非机密不遣。正德间,营差四出,海内骚然,陛下所亲见。近乃遣千户勘扬州高瀹争私财事,囚其女归,惨毒备加,请自今悉付所司,停旗校无遣。”(51)《明史》卷182《顾清传》,第4889页。朝臣多次面折廷争,仍旧无法改变厂卫以驾帖参预行政事务的现状。
万历时,矿监税使四出,借驾帖肆意征敛,诬指良善,以至“谤书一闻,驾帖立下”。(52)《明史》卷237《王正志传》,第6180页。迨至天启、崇祯两朝,获罪者多,驾帖轻出四方,甚或不请径行(53)李应昇:《朝廷纲纪不可不惜谨据法以祈圣断疏》,《落落斋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48册,第445页。,驾帖在史料中的使用记录达到了顶峰,甚至成为中官奸法谋私的工具,以至“此辈一捧驾帖,不知如何索诈,如何惊扰”。(54)汪楫:《崇祯长编》卷32,崇祯三年三月癸卯,第 1885页。大珰甚至“风影诏狱,于是矫旨,缇骑四出”(55)朱长祚:《玉镜新谭》卷6《缇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8页。,权宦借用“不经内阁之票拟”的驾帖大兴党狱,造成了“缇骑遍天下”的局面。(56)毛奇龄:《西河集》卷76《明左都御史蕺山刘先生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699页。驾帖使用之滥、校尉差遣之烦,已远过于先朝。天启四年,内阁中书汪文言及东林党人以参劾魏党被逮下诏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掀起了针对魏忠贤及其附党的弹劾,其中即以宦官借厂卫专擅司法为一大罪,“片语违忤,驾帖立下”,逮捕汪文言等人之驾帖也“不从阁票,不令阁知,不理阁救”,在刑事司法领域对魏忠贤借驾帖倾轧异党进行了批判。(57)杨涟:《二十四大罪疏》,《皇明经世文编》卷496,第5495页。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也上疏声援:“驾帖之佥,北司之拷,非所以示天下公,宜以罪犯付法司,内外章奏还内阁职掌,无使辅臣失职。”(58)嘉庆《太仓州志》卷27《人物》,《续修四库全书》第697册,第450页。首辅叶向高亦上疏曰:“驾帖之拿人,渐不可长。”(59)蒋平阶:《东林始末》,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福建道御史李应昇疏请“敕谕内监,钤束驾帖,金吾职掌,毋听内使纵横”。(60)李应昇:《朝廷纲纪不可不惜谨据法以祈圣断疏》,《落落斋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48册,第445页。这次轰轰烈烈的反魏斗争最后以东林党人被削职禁锢而告终,一些主要人物则以驾帖被逮系诏狱,可见驾帖已经成为权宦打击异己的专权工具,而六科及内阁已经无法对其产生制衡力。
崇祯三年,户科给事中许世荩再次借“公法”之名上疏请“停驾帖”(61)《崇祯实录》卷3,崇祯三年正月戊申,第86页。,未被采纳。思宗在位期间,反而十分热衷派遣锦衣卫使用驾帖捕拿人犯,刑科签批稍迟,甚而获罪降谪(62)《明熹宗实录》卷21,天启二年四月丙寅,第1041页。,至于科臣,对签批驾帖“仅作承行”。(63)李清:《三垣笔记》,《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9册,第 338页。崇祯五年,思宗从提督司房内监所请,下令“自后驾帖径发锦衣卫,若就近密速拿人,不必候科签”(64)汪楫:《崇祯长编》卷62,崇祯五年八月丁丑,第3572页。,成化以来确认的驾帖与六科相衡的制度被彻底废止,驾帖遂成名副其实不与外廷相涉、径自断自宸衷的“中旨”“内降”。至于明季北兵起,明廷偏安南京时,马士英倾轧异党,仍以驾帖付校尉逮问复社党人,然而“驾帖未出而南都亡”(65)徐鼒:《小腆纪传》卷53《儒林一》,《续修四库全书》第333册,第124页。,驾帖也随着明朝的覆亡而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结 语
明代驾帖的设计,一为皇权的制度延伸,表达的是皇权意志,厂卫治狱皆“取诏行,得毋经法曹”(66)王世贞:《锦衣志》,《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第661页。,这是驾帖“私”的因素;一为司法权的平衡维制,是明初皇帝针对锦衣卫的关防之制,又经过历代朝臣不断法制化、规范化,这是驾帖“公”的因素。驾帖所具有的这两种性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和皇权意志。在明代中后期,由于宦官得势和皇帝有意识地袒护,法司在与厂卫的博弈中落败,驾帖已经起不到平衡二者的作用,反而成为内监和厂卫济私自肥的工具。
从厂卫的司法权发展的角度看来,自锦衣卫与宦官互相倚重后,竟称“表里衙门”。明代朝臣试图将驾帖进行法制化,以作为限制厂卫权力的制度措施,但在皇权肆意表达的背景下,驾帖反而逐渐演变为皇权合法控制国家司法的工具,驾帖的中旨化,便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晚明公共政治意识的兴起,掀起了对驾帖合法性的批评,驾帖所具有的“公”的色彩渐渐为明臣所重,他们试图借此将旗校内官差遣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之内,这是对锦衣卫参与司法的制度规范。驾帖的中旨化,体现了制度规范对皇权“法外用刑”的约束是有限的,宦官等近臣更得借此分享皇权,以私夺公。崇祯十五年廷对,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对厂卫司法提出了批判:“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有私刑也。”崇祯帝反问:“东厂、锦衣卫俱为朝廷问刑,何公何私?”(67)《崇祯实录》卷15,崇祯十五年十一月甲子,第456页。可见对皇帝而言,厂卫与法司本无所谓公私,为皇帝问刑即为朝廷问刑,也是传统帝制中国“朕即国家”君主理念下司法生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