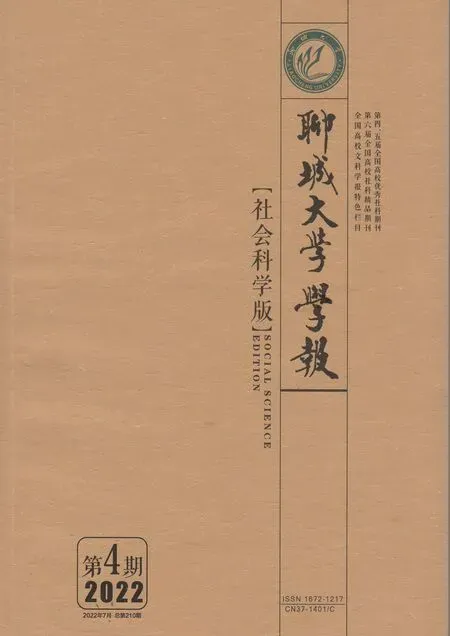《尘埃落定》与《秦腔》中的傻子形象比较论
王俊虎,廖 慧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阿来与贾平凹都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他们各自笔下的藏地色彩和西北风情在文学世界相映生辉,受到文艺评论界与学术界的颇多关注,尤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与《秦腔》两部作品更是广大读者与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自两部作品问世以来,形式的创新与叙事的独特便引发了众说纷纭的研究与评论之声,有对叙事结构的解析、审美意义的透视、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等,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只是以单篇作品作为对象,将两部作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也仅仅是注重对叙述视角的分析,对两个傻子人物形象的对比研究尚有可以探究的空间。傻子形象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其存在具有重要的言说意义,而阿来与贾平凹相继选择在作品中塑造傻子形象,其承载的自然是作家对于社会文化以及生命内涵的深思熟虑,因而傻子形象虽作为边缘人物存在却蕴含着极大的隐喻,并且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与贾平凹《秦腔》中的引生又体现出一种探索创新的尝试与开拓,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与时俱进。
阿来的《尘埃落定》与贾平凹的《秦腔》均选择以傻子形象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虽然傻子视角的采用颇为相似,但是由于两位作家受到不同民族、文化和地域环境的熏染,在各自作品中对傻子形象的描摹又各有侧重。本文将通过比较傻子少爷和引生这两个典型形象悬殊的身份地位、不同的形象刻画、迥异的结局隐喻三个方面,探究表象之下叙事功能、人物意义、作品意旨的差异,从而阐述两部作品殊途同归的价值主题,挖掘傻子形象塑造的当代意义,分析两位作家选用傻子形象叙事的良苦用心,体会作家对现实社会和虚伪人性共同的反思态度,既表现出作家社会责任感的担当,也引来了发人深省的人性叩问。
一、身份地位之别:土司少爷与乡土农民
《尘埃落定》与《秦腔》中的傻子形象最为明显的不同便体现在两者身份地位的云泥,一个是生活在土司家族享受锦衣玉食生活的少爷,另一个却是穿行于清风街上人人调侃、奚落的孤儿,这样的设置事实上是阿来与贾平凹在对自己耳濡目染的文化历史进行深刻体察之后别出心裁的匠心运用,人物形象身份的选择背后承载的是各自小说叙事功能的展开。人物作为小说的三要素之一,其刻画不仅要符合小说的主题和艺术基调,还要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能够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凸显生动的创作风格,例如鲁迅小说中塑造的阿Q、祥林嫂、涓生、吕纬甫等一系列经典的人物形象。在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鲁迅先生着眼于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等底层人物身份的构筑,并借助这些人物形象实现揭露现实和启蒙民众的社会功用。因此,人物形象在作家精心雕琢之后释放出来的丰富而复杂的表现力往往有着强大的叙事功能。傻子形象相较于正常人往往不会受到严苛的社会伦理和精神道德的桎梏,他们从现实生活中抽离进入到另一重世界,以一种洒脱的姿态超越文明的藩篱,在他们身上作者更能实现相对的话语自由表述。但是更加自由的话语表述却也带来了傻子形象塑造上的挑战,诸如如何完成角色的意义指向、如何把傻子身上的叙事功能转化为深刻的文化内涵等,都会为傻子形象的塑造增添难度。而身份作为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标识,融合着丰富的文化内蕴,解读傻子的身份之别,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作者文化态度的探究。
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生活在藏族土司家族中,身为土司的儿子,虽然他是一个傻子,但是他的少爷身份让他并不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傻子和少爷这样的身份组合形成一种悖谬的存在,这悖谬恰是作者的刻意为之,其指向的不仅是生命存在的思考,更是对看似稳固的土司制度的反讽和对一群所谓正常人的嘲弄。
首先,傻子作为麦其土司家的二少爷,本该与才华横溢、风流多情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在古往今来的文人佳话中公子配佳人,自然是应该抱得美人归的,可是这位傻子少爷对爱情的真心换来的却是挚爱之人的冷漠和背叛。傻子对蓉贡土司的女儿塔娜一见钟情,为了迎娶塔娜,他不顾别人劝说毫不犹豫地将粮食借给蓉贡土司,帮助其家族解决粮食短缺的燃眉之急。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在塔娜看来完全是利益的交换,而她正是这场交换中的牺牲品,并且这个行动决定者还是一个众人眼中的傻子。因此,塔娜轻视傻子,几度背叛傻子,将傻子的一片真心任意践踏。塔娜对傻子二少爷的不忠、不爱归根结底是对傻子形象的嫌憎,这正是傻子少爷身份的悖谬之一。虽然地位尊贵,但是形象与地位的不对称让他依旧被人看不起,甚至还在勇敢追爱的过程中伤痕累累。傻子少爷悲凉的爱情也是对土司制度的讽刺,以利益为目的的各个土司家族终归是没有人情与真爱的,他们的命运也将和傻子少爷的爱情一样走向破灭。其次,傻子少爷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低下,只是因为他异于常人的表现而被周围人视作傻子,事实上他有着旁观者清的超脱与从容。小说中,被当作傻子的“我”常常说一些傻言傻语,可是这些话却又多次帮助麦其土司家族做出正确的决定。比如当其他土司都种植罂粟时,傻子少爷建议种植粮食;当哥哥在南方挑起事端发动战争时,傻子少爷却把坚固的堡垒变成开放的市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土司之间的冲突。结果是种植罂粟的土司家族都不得不来求助于麦其土司,使得麦其土司家族实力大增,而哥哥的好战也让他最终命丧仇人之手。以傻子之“智”对比智者之“愚”,这也是傻子少爷身份的悖谬之二,傻子作出的决定却往往是正确的,荒唐却真实,愚者之智的反差更凸显讽刺之意。
与阿来赋予傻子少爷身份的讽刺功能不同,贾平凹《秦腔》中引生的乡土农民身份则体现的是一种观照反思。《秦腔》文如其名,犹如一曲宛转悠扬又喑哑不言的挽歌,以傻子引生之眼,审视了现代文明入侵下清风街上人们精神文化裂变、道德伦理沦丧、人情趋于泯灭的现象,揭示了宗法制乡村在被现代性罪恶蚕食过程中举步维艰的生存状况。引生作为一个底层的农民形象,他生活在贾平凹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书写中,是作者将其对故乡的复杂体验和悲悯情怀诉诸于读者的真情表达。
首先,在清风街上,引生和所有人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土农民,其身份不显突兀因而能够很好地融入清风街民众这一社会群体,四处游荡的他可以深入观照世俗的现实。从村委会到赵宏声的药店,从砖厂到果园,从万宝楼酒店到七里沟,清风街大大小小的地方都有引生身影的逗留,好好坏坏的事情都留下了引生疯眼的见证。其次,引生是带着正常人鄙视的卑微而存在的,由于不懂人情世故被定位为傻子的他更处在了底层中的末端,引生在周遭人眼中的可有可无、地位的卑下能让所有人放下防备、卸下伪装,将自己虚伪、狡猾和丑恶的内心在他面前展露无遗,而引生也能够做出自己最本真的判断,带给读者直指人心的真实感受。当村支书夏君亭力排众议要在三角地修建农贸市场以拉动经济增长拯救清风街的衰败时,从地下挖出了土地神的石像,打消了村里人对于修建市场的疑虑,大家把这一现象看作是一种预示市场成功的祥瑞。但引生竟语惊四座:“说不定是君亭事先埋在那里的!”①贾平凹:《秦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98页。随口之言令周围的人群包括夏天智都意想不到,而大家却只当他说的是没有根据的疯言疯语。事实上,引生的语出惊人道出了他对夏君亭人品的本能体察,抵达事物本质却不被人们接受,毕竟人们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谁又会相信一个傻子的胡言乱语呢。通过引生乡土农民的身份,贾平凹把对世纪末乡土中国的观照和反思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形象刻画侧重不同:智慧的傻子与清醒的疯子
虽然《尘埃落定》与《秦腔》都是以傻子人物为中心,但是在傻子形象刻画上又各有侧重,人物痴傻行为的表现也各有千秋。“《尘埃落定》中的土司二少爷是傻子与智者的结合体,是人性和神性的化身,是‘两体合一式’的人物形象。”②邬婷婷:《“不可靠”的叙述者——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傻子”形象的符号意义》,《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54页。阿来不拘囿于对傻子之傻展开描绘,更多地关注着傻子身上闪烁着的与众不同的智慧之光,将理性、反思、追求等多元内容融入其中,由傻子带领我们走进辽阔的精神世界,一种苛酷却真挚的美感个性始终笼罩在傻子的身上。傻子的智慧首先体现在他对傻子形象的坦然接受,他不会流于表面地在意别人把他视作傻子,相反他用一种知傻装傻的态度突破世俗的狭隘目光,从心所欲,率性而为,潇洒无拘。正因如此,他往往比那些所谓的正常人、聪明人更能洞见迷雾中显现出来的真相,触摸事物纠缠背后的根本,而这也为他自己获得了旁人难以企及的生命的欢乐和痛快的体验。同时,心甘情愿地作为一个傻子让他在父亲、母亲、哥哥等人眼中没有任何威胁,从而放松对他的警惕,少了勾心斗角的残害,可以说在别人眼中他的愚钝事实上成为了他性命无虞的保护伞,这也正是最后仇人多吉罗布打消杀掉傻子念头的重要原因。此外傻子的智慧还体现在对他人心思的明了洞悉和处事态度的宽容豁达上。傻子与现实生活的格格不入让旁人忽视他的存在,自然不能注意到傻子那双细致观察的眼睛,这双眼睛让他轻松地捕捉常人所不能发现的细节和感情。如母亲对于权利的享受过程,不加掩饰地映入傻子之眼:“办了一会儿公事,母亲平常总挂在脸上的倦怠神情消失了。她的脸像有一盏灯在里面点着似的闪烁着光彩。”③阿来:《尘埃落定》,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7页,第9页。当索郎泽郎故意把雪踢到傻子脸上愚弄他时,傻子却不加以怪罪,反而体恤地想“即使是奴隶,有人也有权更被宠爱一点。”④阿来:《尘埃落定》,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7页,第9页。傻子虽然宽和,但他也不会让自己吃亏,他知道让奴仆感到畏惧,展现自己作为主子不可侵犯的一面,他会在侍女不给他穿衣服时故意大声叫喊以此引起侍女担心被土司太太惩罚的恐惧,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知人情而不世故,这恰是傻子少爷的智慧使然。我们从傻子二少爷身上感受到他那看似疯狂的话语、巧合的直觉、离奇的顿悟、怪异的行为,其实这些表现都是在一定基础的理性智慧上迸发而出的,傻与智的对峙让傻子的形象充满了荒诞和神秘色彩。
贾平凹《秦腔》中被视作疯子的引生,却是清风街上最能看透生活本质、领悟生命真谛的人,在他身上疯傻表象下的清醒内在、非理性躯体下的理性思考才是作者刻画这一人物形象的意图所在。虽不是风云人物,但引生眼中的风景却气象万千,而他于这风景中表现出来的清醒认识,事实上是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压抑起来的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与性情。引生的清醒最直白地体现在他的爱情观念中。文章一开篇就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引生对白雪的喜欢,引生喜欢着白雪的一切,即使白雪嫁为人妇也没能斩断引生对她的爱恋。在引生的眼中白雪是纯洁的,他对白雪的爱也是纯粹的,因此在内衣事件之后,引生毫不犹豫地选择挥刀自宫来捍卫这份爱的神圣。虽然荒诞且并不被人认可,却不失为一次对理性的挑战、对真理的探求。引生对待爱情的清醒态度就在于他清楚地明白对白雪的爱是神圣不可玷污的,他也并不奢求得到白雪的回应,因此才会用一种极端并且不被人理解的方式去守护这份真情,反映了引生作为一个疯癫者心灵的本真。对于清风街上人与事的解读也反映出引生异于常人的清醒。比如夏天礼因为银元被人殴打致死后迟迟不肯闭眼,而引生说“用银元按按他的眼皮,眼睛就合闭上了”①贾平凹:《秦腔》,第242页,第237页。,一句不可靠的疯话却真的让夏天礼的眼睛闭上了,令大家匪夷所思。其实这是引生作为一个置身其中而又超然物外的观察者拥有的接近真实的清醒。在引生看来,夏天礼的死“都是银元惹的祸”。“夏天礼一辈子都喜欢收藏钱,其实钱一直在收藏他,现在他死了,钱还在流通。”②贾平凹:《秦腔》,第242页,第237页。疯亦非疯、无知又无不知的引生,将清风街上的人情世态尽收眼底,因而能够一语中的,“用聪明人最始料不及的简单破解一切复杂的机关”③林建法,乔阳:《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接近事物的真相,从而获得清醒的认识。而引生那疯傻的清醒背后,最终意义是为读者展现以清风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精神的异化与农民无奈的妥协让步的现实。
《尘埃落定》与《秦腔》傻子形象刻画的侧重便体现在智慧的傻子与清醒的疯子之间的区别,从而体现出人物各自代表的意义。《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阿来着重笔墨展现的是他智慧之光的闪烁,用来观照的是土司制度下民族与历史的多元复杂。而在《秦腔》中,贾平凹则更多地书写着疯子引生身上清醒的一面,透过引生的清醒苦苦追索着农民与土地、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物质等伴随着时代发展变化产生的难题之解。
三、结局隐喻迥异:孤独的终结者与游走的见证者
《尘埃落定》与《秦腔》两部作品中傻子形象的结局也有着显著的不同:一个随着土司时代的谢幕豁达地结束了生命,一个在见证乡土文明的凋敝之后继续游荡在迷失的困境中。两者不同的结局隐喻着阿来与贾平凹两位作家在对历史进行回顾之后,对各自文化土地所寄予的深刻的理性思考,是作品意旨的突出强调。
文学作品是我们构建的有效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作为一部成功描绘了藏地历史风云变幻的文字画卷,《尘埃落定》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互动,随着时代的更迭显出意义的宏大与主题的深刻,而傻子二少爷这个人物也因作家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书写在文学画廊中光芒四射。傻子二少爷作为麦其土司家的最后一位土司,见证了土司时代由盛到衰、由存到亡的历史过程。傻子以一个孤独的终结者姿态用他的双眼凝视着这片土地,他既看见了土司家族最后的繁荣稳定,也洞悉了这浮华表象之下深刻的腐朽;他既体验了权力的至高无上并萌生了争夺土司之位的想法,却也因此陷入了权力的困惑;他既预言了时代潮流滚滚向前的不可阻挡,也冷静地观察着在这潮流裹挟之下的亲情、爱情、欲望与人性。最后,傻子让仇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慷慨赴死,亲手拉下了历史舞台上土司制度的帷幕,终结了权力的争夺和土司的存在。傻子二少爷的结局展现了阿来对于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土司制度存在的藏民族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一种封闭的环境中,其发展受到地域、宗教、封建农奴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正因如此土司制度下的藏地经济落后,等级森严,思想保守,早已呈现出一种没落颓废的态势。当先进的异质文明,无论是外来者带来的罂粟花、枪炮、梅毒,还是黄特派员为代表的国民党或者是红色汉人代表的解放军,这些现代文明无论优劣都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进入土司管辖的世界,加剧着土司体制的内部消解。落后与先进的对立体现了文明的辩证关系,弱势地位之下的土司文化在与先进的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将自己的缺点暴露无遗,面对人类历史发展步伐的势不可挡,如果不能进步则只能走向灭亡。傻子的结局隐喻着土司制度被取缔的必然,落后的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必然只能化为历史的尘埃,其中隐含了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以及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民族文化应当如何进步的思索。
“如果说取材地位显赫的土司氏族的《尘埃落定》是基于宏大背景之下的有关大人物的大历史、大叙事,是星辰大海,与我们存在一定的距离。”①鲁淼:《论阿来<尘埃落定>和<空山>的史诗性》,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2021年,第12页。那么,取材于当代农村生活的《秦腔》则是以小人物来写大历史,通过疯子引生第一视角的叙述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民在传统文化日趋衰落、乡村生活面临困境背景下挣扎迷茫的生存状态,引生形象本身具有的象征意味使得其最后的结局也体现出丰富的内涵隐喻。相比于《尘埃落定》中傻子的死象征着土司制度的灰飞烟灭,《秦腔》里引生与清风街的终身相伴则象征着乡土文明还有一片栖息之地。在贾平凹的笔下,引生无疑是特殊的,他身上有着对传统文化的追寻,例如他对秦腔的精灵化身白雪的爱慕,对夏天义为代表的乡土文明的追随;同时,他身上表现出对清风街上人与事的神秘预言,例如白雪离婚之前引生便有预感,他梦见掉牙,想到亲人有难,而白雪对于他来说就是他的亲人;此外,引生的身上还有对客观生活的清醒认识,他会灵魂出窍去到果园看夏天义和新生他们忘记年龄和悲伤的打鼓,实际上是在向我们传递着传统文化兴盛和没落的讯息。引生身上的种种象征蕴含着贾平凹对故乡的深情眷恋和守望,他借用疯子引生这个在清风街上无孔不入的游荡者形象,见证了清风街二十年的变迁和人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在小说结尾,引生选择和夏天义到七里沟淤地,实际上是选择了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当夏天义死后,引生继续独自守着他的无字碑,见证着清风街的荣辱兴衰,见证着传统民间文化在现代文明挤压下的没落与颓败、挣扎与努力。引生的结局带来的是贾平凹对乡土文明的深思,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两者的存在如何能够并行不悖?现代社会能否包容多元文化的存在?乡土精神、乡土文化的生存空间又该在何处寻觅?或许这些问题没有准确的答案,但是引生最后留在清风街,继续深爱着、坚守着这片土地,实际上是作者给思想躁动、惶惑无依的诸如夏风一般的城市人诗意的留存。乡土文明并未像阿来笔下的土司制度那样陨落,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中它该何去何从,作者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考。
四、价值主题的殊途同归
小说价值主题的选择与书写是作家对于一个时代文化表象的记述、描绘与创造,它表达着书写主体精神性的思考。阿来与贾平凹在小说中均选择通过傻子形象的描绘来折射社会现实,整个书写空间弥漫着浓郁的文化精神,引发人们去探索隐藏在傻子形象背后的深层意蕴以及傻子载体指向的价值主题。
阿来是一位藏族作家,《尘埃落定》也是一部关于藏族土司制度的故事,字里行间流淌着藏族的风土人情和神秘的藏文化色彩。人们都说这是阿来笔下一部关于藏族的史诗,但是在阿来的眼中,这是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作品,“我并不认为《尘埃落定》只体现了我们藏民族或那片特别的地理状况的外在景观。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 是要在人性层面上寻找共性, 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也是不同特质的人类文化沟通的基础。”②阿来:《大地的阶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586-587页。傻子与正常人的背道而驰实际上观照了傻子不傻的通透品质,傻子二少爷悖谬的存在担负的意义和使命正是作者关于普遍人性的思考。现代性的袭来将土司制度土崩瓦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被利益所扭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兄弟反目、父子嫌隙、爱人背叛等等,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让傻子二少爷的存在更显突兀。但是傻子却是正视人本能欲望以及人性弱点的参照物,傻子挣脱规则的束缚和道德的标尺,用他的真实、真诚、智慧消解了虚伪、荒芜、异化的人性。此外,傻子二少爷对自我的追问和思考,更将作品主题提高到了人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等人生终极问题的层面,是哲理思辨的叩问,从而摆脱现实的窠臼,阐明了深刻的哲学理念。而《秦腔》何尝不是这样一部具有探究人生普遍性特征的作品。同样是傻子的第一视角叙述,同样因天马行空的主人公引生不被周围人理解而被当作傻子,但同样傻子有着敏锐的大智慧和先知先觉的预言能力。引生他孤独地活在这个被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世界中,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没有人能理解,甚至被单纯地否定,但是他却是七里沟最善良、最清醒、最热心、最风趣、也最执着的存在,他有着自己的追求和信仰并为之付出行动和努力。贾平凹用引生不向世俗社会屈服的坚定,不被道德压抑的本能将真实的人性展露无遗,以此揭开被金钱扭曲的人性虚伪、丑恶、阴暗的面纱,在引生这个小人物身上表现出深邃主题的思想含量。
《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与《秦腔》中的引生,他们茕茕孑立于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新旧时代的交错处,用他们看破前尘往事的神秘迎来一段新的历史,在他们的身上充溢着颠覆与启蒙、自我与他者的矛盾,他们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着生活中的世俗丑态,揭露和讽刺着人性的虚伪。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但是精神世界却越来越空虚,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充斥的是物质欲望的膨胀,精神追求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于是道德文明滑坡、价值观念失范,人性、人心功利而虚伪。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两位有责任和良知的作家忧心忡忡,他们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阿来与贾平凹通过傻子形象的刻画,说出了常人所不敢言说的真相与事实,表达了一种对人类世界中日渐空泛模糊的真善美情感的向往,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在缅怀各自的民族文化或者乡土文明的同时,用傻子的智慧与清醒、疯子的豁达与坚守传递了对现代社会中人性纯真、善良、诚实等品质的呼吁和追求。
阿来笔下的傻子二少爷与贾平凹笔下的引生虽然刻画各有侧重,书写也各具特色,但是两位对文学秉承赤子之心的作家却通过傻子形象表达了共同的文学诉求。傻子二少爷与引生身上的单纯快乐反衬着现代社会人性的悲凉,体现出两位作家对生命的思考,凸显了他们对自由灵魂与丑恶现实格格不入的反省,张扬着他们对人类真诚心灵的渴望。阿来与贾平凹在各自作品中关于傻子的书写是非常厚重的,他们用一种理性的目光回望各自民族历史与时代文化的更迭变迁,通过对傻子形象的深入刻画,探寻共同的人性主题,蕴含着两位有深度、有理想的作家对历史、文化、命运、人性、现代性等问题的审视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