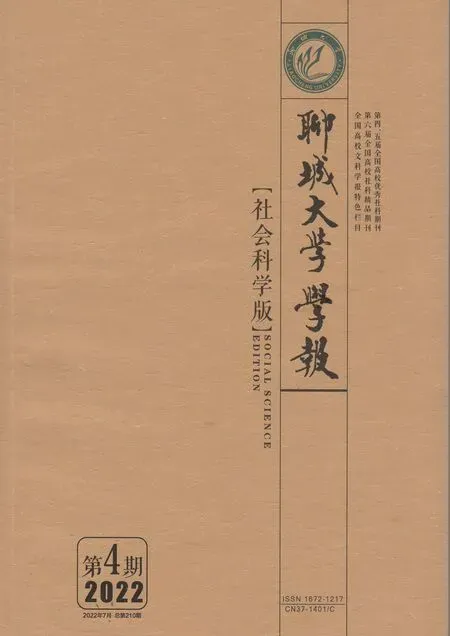论列宁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开拓
——为纪念苏联百年而作
刘长明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天津 300071)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在垄断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打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和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列宁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因而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复杂多变的实际问题,并在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形成列宁主义理论。列宁在长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开拓中形成的一系列丰硕成果,铸就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永远熠熠生辉的里程碑,由此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承前启后的崭新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经过百年历史风云的洗礼,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在苏联建立百年之际,纪念这位苏联的缔造者,无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一、战斗哲学 复活革命
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大行其道,第二国际逐渐走上一条去革命化的道路。充满机会主义者的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拒斥革命,醉心于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俄国的经济派蔑视革命理论,反对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迷信自发的工人运动。孟什维克继承经济派的衣钵,弱化党的领导,试图建立一个没有定型的、成分复杂的、涣散的党,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公开抛弃党的革命纲领,要求取消党,堕落成为取消派。托洛茨基同取消派一唱一和,肯定机会主义派别在党内的活动自由。
一时间,乌云滚滚,“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一国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①《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4页。。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徘徊在一个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无产阶级如果容忍这样不成体统的党作领导,无异于自废武功。关键时刻,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拨云去雾,矫正了前进的方向。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普选除了是强化统治秩序合法性和调节社会矛盾的工具之外,什么都不是。资产阶级议会是垄断集团操控的木偶,资产阶级政府首长是资本集团的大管家,资产阶级军警和司法系统是资产阶级维持统治的暴力工具——有没有普选、怎样普选、选出谁当政府首长,都不会改变这些基本事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工人阶级都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普选夺取政权并向社会主义过渡。资产阶级政府枪杀3万多名公社社员的枪声余音未散;1917年十月革命后,英、法、日、美等14国联军与国内反动势力组成的白军,更是杀人无数。所以列宁认为,革命在关键时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列宁敏锐而精准地把握时代变化的革命本质,深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革命家的非凡气魄,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经济派、孟什维克、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在复活革命真谛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战斗哲学。
列宁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页。鉴于此,列宁从建构战斗哲学入手,在《帝国主义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中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特质得以复活。
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诚然,马克思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创始人和得心应手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宗师,然而,却没有建构起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针对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端攻击和肆意歪曲,列宁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一系列论著中,对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实践观等,都进行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从而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界定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给出关于“物质”的经典定义,堪称列宁在唯物论领域的突出贡献;对真理、客观真理、相对真理、绝对真理等范畴,以及认识的实践基础、真理标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的系统阐述,则彰显了列宁在认识论领域的慧眼如炬;在辩证法领域,列宁条清缕析出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严密逻辑结构,从而矗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独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大厦。
奏响时代主旋律——无产阶级革命。19世纪末,殖民体系得以确立的资本主义世界,开始高歌步入帝国主义阶段。在此背景下,考茨基提出“超帝国主义论”,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极力主张在帝国主义框架内即不改变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劝说、敦促帝国主义调整个别政策,反对用暴力革命推翻帝国主义。曾经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一个是恩格斯的学生和满腹经纶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一个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但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横加指责,对近在咫尺的工人起义百般阻挠。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叶公好龙”成语的最好注释:平日里对社会主义理论夸夸其谈,但社会主义真的来临时却怕得要死。在他们看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条件是:资本主义必须充分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中小生产者完全破产,沦为了无牵挂的彻底无产者。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即在无产阶级还没有经受惨无人道的剥削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还没有被榨干血汗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应当也必须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静静地等待自己的血汗被榨干,尔后再按部就班地开始计划中的革命行动。为了澄清认识,列宁深入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走势,推出鸿篇巨制——《帝国主义论》,增补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同时,破天荒地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精准定义:所谓帝国主义,就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②《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1页。。列宁将垄断作为剖析帝国主义的切入点,建构了经典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强调:“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①《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0页,第426页。从总体运行趋势看,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腐朽因素已越来越明显,虽然垂死不等于死亡,但已“无可奈何花落去”,开始走下坡路。列宁在对帝国主义社会经济特征深入分析后指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时代的主旋律是无产阶级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是其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一个世纪过去了,帝国主义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但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没有丝毫改变,由垄断所决定的帝国主义本性也“涛声依旧”。在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新帝国主义”②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第52页。阶段的今天,垄断仍然是今天世界经济的常态,金融寡头对全球的控制更加强化。服务于垄断资本的投资银行更像是一个金融恐龙,利用颇具诱惑力的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和杠杆工具,呼风唤雨,将诈骗伎俩演绎得出神入化,魔术般撬动全球经济,掠夺全球资源。美其名曰的金融创新,成了垄断财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垄断,是统治——而且是恐怖统治!今天的美国及其垄断资本,越来越表现出黑社会性质。如今的金融寡头已经从列宁所说的“向全社会征收贡赋”发展到向全世界征收贡赋;从控制本国政府发展到控制各国政府。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已经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量身定做了套在脖颈上的“辔头”——这个或隐或显的“辔头”,使各国政府不得不屈从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为了维持垄断地位,金融寡头转而用超额利润收买本国工人阶级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培植控制全球的社会基础。于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新常态”屡屡上演: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完全站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寡头一边,不惜与自己的祖国为敌,蜕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当代的垄断已经登峰造极,越来越走向极致——威胁到全人类生存的极致。列宁以垄断为理论主轴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垄断依然是列宁早年揭示的、今天我们仍然要面对的经济生态,《帝国主义论》依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提出“两个承认”——既承认阶级斗争,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③《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0页,第426页。但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够。当是时,取得政权的途径及取得政权后的施政,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焦点。考茨基流派天真地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也能够进行合法斗争,经由渐进温和的法律框架内的竞斗,完全能够不经任何阵痛而和平接收政权,并在接收政权后保留原有民主制度。列宁则警告指出,长期痴迷于合法合规竞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必然逐渐修正主义化;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可靠手段;夺得政权后的无产阶级,必须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留情地废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资产阶级已经联合起来的国际环境中,率先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国家,也必须用专政的方式保卫本国的无产阶级政权。据此,列宁提出了“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论断。而且,“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④《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首倡“一国胜利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6页。其立论依据是:在资本主义迅速向世界范围内扩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国际现象的背景下,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或至少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然而,革命导师的理论是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考茨基之流无视形势的变化,警告“蠢蠢欲动”的落后国家的革命者:按照历史演进程序,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目的只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拓展道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仅仅因为胜利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按照考茨基的顶层设计进行,十月革命之后,考茨基同伯恩施坦等人一起加入了国际资产阶级攻击苏维埃俄国的大合唱,指责列宁在尚未对社会主义作好准备的国家发动革命。如果不突破第二国际庸人们设置的这个理论禁区,就会葬送生机勃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列宁以伟大的革命气魄指出,当越来越多的东方国家卷入革命运动的时候,就应该“丢掉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①《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8页,第776页,第777-778页。。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普列汉诺夫等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指责,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列宁在《论我国革命》等著述中,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论证了俄国革命无可置疑的正确性。基于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深刻把握,列宁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完全能够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的少数几个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科学结论: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国面临的特殊形势,使它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整个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一时没有联合镇压无产阶级的可能;人民面对战争灾难,除奋起革命别无选择,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结合的条件在俄国业已成熟。列宁由此认为,俄国生产力落后是无可争辩的,但以此为借口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攻击和否定,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②《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8页,第776页,第777-778页。既然历史给俄国无产阶级以极为有利的革命机会,“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建立政权,“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③《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8页,第776页,第777-778页。俄国把历史顺序颠倒一下,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恰恰是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科学理论依据,坚定了取得革命胜利的信心。当然,列宁也不忘谆谆教导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相反,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④《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3页。
明确党的革命性原则。列宁在1901~1902年撰写的《怎么办?》一书中,提出了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观点。在列宁看来,党必须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以“职业革命家”为组织核心的坚强机构,落后群体应当也必须接受先进群体的领导。列宁特别强调组织的重大意义,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⑤《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6页,第406页,第342页。;“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⑥《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6页,第406页,第342页。只有把党组织起来,才能完成其革命彻底性使命。列宁说:“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⑦《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6页,第406页,第342页。列宁强调,只要还有阶级存在,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在回答关于“一党专政”的指责时,列宁回答:“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⑧《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6页。列宁给马克思主义补充的先锋队政党学说,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
确立哲学的党性原则。对哲学领域甚嚣尘上的所谓“无党派”、“超党派”论调,列宁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亮出哲学上的党性原则。所谓哲学的党性原则,指的是所有哲学和哲学家,要么归属于唯物主义阵营,要么滑向唯心主义泥潭,绝无中间道路可走,试图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中间派或超越派,无异于痴人说梦。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超阶级、无党性的哲学派别。列宁说:“阶级和等级相反,阶级总是使个人保持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的完全自由。”①《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3页。但是,在私有制社会中,阶级身份的转化仅仅是个人身份的转化,并不是整个阶级的身份转化,更不会改变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阶级意义上区分的客观事实。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②《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6页。
重建哲学的战斗性原则。生活和战斗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历史时代的列宁,面对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消解,面对资产阶级学者的诘难,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全新使命,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哲学,恢复了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强大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磨砺马克思主义的剑锋,充分焕发出哲学的战斗性活力。列宁根据战斗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与革命任务,高扬哲学的战斗性和革命性,讴歌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革命:“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③《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6页。
列宁的战斗哲学彰显了革命家宽广的理论视野、博大的思想情怀,在充满战斗精神的理论世界里,树立起了震慑资本统治的思想旗帜。倡导战斗哲学的列宁与高扬人民史观的毛泽东,堪称集伟大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君师合一者,是西方世界最忌惮也最敬畏的世界革命领袖。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主义被处心积虑地边缘化,那么,列宁及其主义、毛泽东及其思想简直就是被丧心病狂地妖魔化。尽管当代世界与列宁面对的社会历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无论历史风云怎样变幻,列宁的战斗哲学思想大旗仍然猎猎飘扬,没有一丝一毫的褪色。
二、十月革命 震撼世界
1917年爆发的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旧的专制皇权,却保留了资本的统治,以社会革命党和宪政民主党为主的各党派联盟俄国临时政府成立,新的“民主共和国”继续坚决地参加为争夺世界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从而使俄国面临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形势:要么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是将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临时政府,埋葬二月革命。
作为二次革命论者的孟什维克,认为俄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俯首听命于临时政府。改良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下了一道“圣旨”:目前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异于自寻死路。1917年4月17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四月提纲》矛头直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指明了革命发展的前途,那就是——俄国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在8月完成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论证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意义,指出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机器重建方面的任务。10月25日晚(公历1917年11月7日),列宁发动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巡洋舰一声炮响轰击冬宫,宣告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在接下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选举成立人民委员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人民自己的政府,列宁众望所归,当选人民委员会主席。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全世界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并颁布《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1917年11月9日清晨,大会胜利闭幕,向全世界宣告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十月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继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给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添加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内容。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开始变成实践。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历史上最深刻的改革:摧毁旧的国家机器;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大会同意将布尔什维克党更名为俄国共产党——这就是我们通常简称的俄共(布);在同年颁行的宪法中,规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为新政权的正式名称;在列宁的倡议和领导下,1922年12月30日,苏俄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简称:苏联。
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逐渐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是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共产党领导广大劳动者进行的铲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制度的深刻的社会革命,颠倒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逻辑,打碎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写进了世界政治版图,在占世界1/6的土地上推翻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旧世界,开创出社会主义新天地,由此标志着人类进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世界历史由此改写,进入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时代,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就中国而言,十月革命唤醒了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毛泽东高度评价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虽然20世纪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社会革命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真正称得上世纪地标的,无疑是也只能是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尽管20世纪末出现了苏东剧变,致使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开低走,但这只是历史前进主旋律中的一个小插曲,历史波浪回旋时激起的一朵小浪花,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航向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完全可以预言,经过震荡整理和力量积蓄,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冲击波将更有力量,波及面更广。
三、伟大设计 两个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3页。为了实现理论的自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萌生过进一步划分共产主义社会为初级阶段和发达阶段的构思。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或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虽然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阶段,但没有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未来社会,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为理论支点、以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致同时发动并取得共同胜利为理论指归的。事实上,社会主义没有在西欧而是出人意料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率先突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走势大大超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既有构想。关键时刻,屹立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潮头的列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明确将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冠之以社会主义社会之名,进而凝练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列宁分析指出,社会主义是夹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社会形态,换言之,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早期阶段。后来明确将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第一个阶段,属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第二个阶段。
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是从资本主义母体中刚刚脱胎而来的新生儿,因而在经济、文化、习俗、道德等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根据列宁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归整个社会公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两种具体的公有制形式,从而消灭了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
实行按劳分配,但按劳分配的实现须借助于商品货币关系和贸易。由于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但却无法相应迅速消灭另一种不公平现象。这表明,按劳分配同时意味着,不同个人能力和不同赡养人口必然导致收入水平的一定差异。问题在于,按劳分配衍生的不公平又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
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列宁尖锐批评机会主义“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②《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第140页,第140页,第594-595页。。
还需要强化而不是弱化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资本集团祭起的法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③《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第140页,第140页,第594-595页。。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也必须针锋相对,拿起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一样,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全新的——“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④《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第140页,第140页,第594-595页。。1975年,毛泽东组织全党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意味深长。
无产阶级专政与法治建设相得益彰。将无产阶级专政牢牢压在法治的“五行山”下,无疑是法律党瓦解社会主义的阴谋。历史上的所有专政都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当然也不例外,“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⑤《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第140页,第140页,第594-595页。当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法治建设。对二者的关系,列宁的态度很明朗:既不迷信法治,也不轻视法治!
四、直接迂回 殊途同归
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结合俄国国情,探索和开创落后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大道,从而开显出历史新元,成为列宁必须解决的首要时代课题。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实践,在不同的形势下,先后实行了两种内容迥异的政策:一种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种是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后,苏俄内战爆发,帝国主义联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粮食、煤炭、石油和钢铁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处境十分困难。为把仅有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战胜敌人,同时也尝试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于1918年6月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上得以通过。这项实施了近三年的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所有制领域,对关涉国计民生的土地、银行和大工业等推行渐进国有化,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由国家集中统计和监督;在生产领域,直接监督、管理经济的国家,还肩负着直接组织、指挥生产的职能,通过“国家的生产”运作,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工厂,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和调整;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国家垄断所有外贸活动;禁止商品交易,实行计划配给制;在分配方面,国家对居民消费按计划实行统一分配。在当时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证了军民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对于平息国内白卫军的叛乱、击败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功不可没。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由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所创立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理论发生了冲突。1921年3月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俄共(布)顺势而为,决定采取断然措施,通过“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决议案。决议的核心内容包括: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允许商品买卖,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企经济,取消实物配给制。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苏俄社会主义政权进一步巩固。新经济政策解决了小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最大难题,开辟了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
从当时的背景看,“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都是立足于现实的最佳选择,都是列宁在走向社会主义大方向下合乎逻辑的伟大探索。两大政策均抓住了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因而拯救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应该说,列宁关于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计划是审慎的。事实也有力地证明,在赢得国内战争胜利和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过程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虽然“战时共产主义”“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但“‘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①《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2页,第502页,第623页,第364页。当机会主义者迫不急待地借新经济政策攻击“战时共产主义”时,列宁痛斥道:“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②《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2页,第502页,第623页,第364页。至于新经济政策,也并非如人们所说的是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新思考,而是对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让步政策,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由于遇到不利的国内外条件而选择的暂时退却,是从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到迂回过渡的退却,是两次进攻之间的喘息之机为了积蓄重新进攻力量的一种退却,即列宁说的“后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两步”。新经济政策是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更不是布哈林认为的那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③《布哈林文选》上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59-260页。,它本身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对此,列宁解释到:“这个政策之所以叫做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象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④《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6页。退却固然是为了前进,但退却本身不是前进。列宁告诫我们,退却不能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如果只讲退却不“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就会混淆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与资本主义改革观的界限。如果不承认新经济政策的退却性质,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所做的那样,错把退却当成前进,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指鹿为马,最终必然把本来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
必须说明的是,不管是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抑或迂回过渡的新经济政策,其终极目标指向应当也必须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利用资本主义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终究不过是权宜之计,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迫不得已的策略权衡,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为此,列宁强调,只有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控制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国家牢牢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和一切最主要的工业部门,使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才不会葬送苏维埃政权。
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无论是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是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都牢牢咬定生产力不放松。在列宁看来,“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把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在俄国最终胜利的唯一保证。因此,“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⑤《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2页,第502页,第623页,第364页。1920年,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⑥《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2页,第502页,第623页,第364页。这一著名公式。列宁把他亲自领导制定的全国电气化计划称为“第二个党纲”。
1923年1月2日至3月2日,病中的列宁仍然关注着社会主义第一胎的健康成长,先后口授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在这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五篇文章中,通过总结五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其基本内容是:进行农业合作化;实行工业化和电气化;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在艰辛探索中,列宁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曲折性和长期性的认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目的是利用资本主义成果为成长中的社会主义参天大树施肥——利用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复辟资本主义!
五、国家学说 系统阐发
恩格斯逝世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学说,自然成为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攻击、歪曲和篡改的对象,生生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革命灵魂,国家与革命问题被弄得混乱不堪。同在其他领域一样,他们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不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不能前进一步。列宁根据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需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完成的划时代巨著《国家与革命》中,从国家的起源、作用、特征和消亡等方面条清缕析,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工具,阐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同时也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及时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俄国革命的新经验,深刻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在国家和革命问题上的恶意篡改和歪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100多年后,我们再度翻开《国家与革命》,更加叹服革命导师有关暴力革命和国家职能的思想之精辟、论述之辩证、方法之科学。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一般说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首先从原点问题——国家起源和本质问题制造混乱开始。为了揭批风行一时的国家是“超阶级”的、“调和阶级矛盾”的机关等谬论,列宁首先从国家起源方面论证了国家的本质:“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①《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第150页。阶级矛盾在客观上无法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国家应运而生。列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国家问题上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批判,无情揭露了机会主义分子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丑恶本质和罪恶目的,不过是用来欺骗工人阶级放弃武装斗争,为资产阶级充当说客。
迄今为止的任何国家都不是人民的。列宁根据恩格斯反复强调的原则——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明确指出,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机会主义者为之倾倒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代议民主,与人民大众不相干,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群来自资产阶级或者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客,一帮为政客出谋划策的竞选团队,一批提供选举资金的财团,一曲资本集团的大合唱。如果一个候选人没有足够的资金,就意味着他无法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因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②《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第150页。至于普选制,列宁嘲讽道,它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何况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为了艰难地生存,通常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①《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第126页,第190页。即使现代雇佣奴隶在艰难度日之余偶尔关注一下选举,那也不过是在资本集团圈定的两个或三个流氓中选一个。在这个纷纷扬扬的选举闹剧中,现代雇佣奴隶的权利在于也仅仅在于——你可以行使选举权,也可以放弃选举权;如果你想在喘息之机按捺不住寂寞行使一下自己的选举权,那么,你完全可以在政客甲、政客乙、政客丙中任选一个;任何一个选项都不会改变自身雇佣奴隶地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代雇佣奴隶所选择的,是代表资本集团统治自己的代言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你有选择谁来统治你的权利,却没有改变这种统治的权利!
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消灭。列宁指出,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是由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的——既然任何国家都是作为镇压机关存在的,那么,暴力机关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摧毁,而不能靠温情脉脉的说教。作为一小撮富人对千百万劳动者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资产阶级国家只能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即无产阶级国家来取代。醉心于“和平过渡”,借口时代变化妖魔化暴力革命,把无产阶级的斗争聚焦于“取得议会多数”进而改良为“无产阶级议会”的说教,纯粹是梦呓,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他们恰恰忘记了,“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②《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第126页,第190页。。
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存在,决定了还不能立即取消国家,暂时还需要“国家”这个“寄生机体”,而且,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不能取消和削弱,还必须加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才真正是人民的国家。诚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③《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第126页,第190页。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国家绝不能自废武功,放弃镇压的机器,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在通往共产主义的曲折道路上,从镇压不甘心失败的剥削者到彻底消灭阶级,必须借助无产阶级专政,别无他途。
“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才有爱国的权利。在无产阶级没有“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以前,换言之,无产阶级依然处在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时,工人阶级无论拥有怎样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都不能改变自己悲惨的阶级地位,反而会为人作嫁衣——替资产阶级巩固其统治基础,最终掉进资产阶级在国家问题上设置的陷阱。没有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不可能有“热爱祖国”的权利。工人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才有资格讨论“爱国主义”问题。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高歌的那样:“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就是护国派了,我们赢得了保卫祖国的权利。……我们维护的不是大国地位,不是民族利益,我们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的利益,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我们是社会主义祖国的护国派。”④《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8-319页。
无产阶级国家只能自行消亡。作为历史范畴的国家,既非古已有之,亦非万世永存,随着阶级产生而出世的国家,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最终走向消亡。到共产主义的发达阶段,已经没有需要镇压的阶级,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国家,势将丧失作用,自然而然走向消亡。
国家的阶级职能决定社会职能。国家既具有阶级压迫职能,同时也兼具社会职能。两种职能并非等量齐观,国家的社会职能是由阶级职能决定的,社会职能服务于、服从于阶级职能。随着时代演进和社会变迁,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存在渐次扩大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阶级职能的自我否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6页。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有镇压职能,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如果以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扩大的公共管理职能讳言乃至否定阶级职能,以“全民国家”自诩,如此论调无疑是捧杀社会主义国家的绞索——一个美丽的绞索!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描述是粗线条的大写意,是远景规划,而在列宁笔下,一个有血有肉、体魂兼具、形象丰满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跃然纸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堪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之作,不仅为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光明的道路。
六、民族理论 助力世界
在领导十月革命的同时,列宁敏锐地觉察到即将在亚洲出现的必定波及世界的革命风暴:“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②《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7页。被压迫民族的命运及革命前途,牵动着革命导师的心。列宁断言,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情况下,民族解放已成为时代的伟大主题。正是在东西方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历史背景中,在殖民与反殖民的民族运动激流中,列宁形成了引领时代的世界历史观。从这样的世界历史观出发,早在1912年列宁就起草过《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继而在《亚洲的觉醒》《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一系列文献中,讴歌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以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为主题的世界历史观理论体系。新的世界历史观必然催生新的世界革命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振臂一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合乎逻辑地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发展成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今天重新翻阅列宁的上百篇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著,仍然能够强烈感受到列宁主义中包含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的强劲时代脉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的两大集团在战争中相互削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在此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与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处于矛盾纠结中。一方面,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长远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又有直接的共同利益——从对外掠夺的高额利润中分得一杯羹,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待遇,成为带血的高额利润的分赃者,并因这种分赃而滋长机会主义,放松或放弃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甚至堕落为恩格斯所讲的“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和“剥削全世界的民族”。在帝国主义国家国内阶级矛盾因“无产阶级参与掠夺后的分赃”而获得缓和的同时,落后国家的国内阶级矛盾则因遭受外来压迫而被搁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团结各国的革命左派,支持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1919年3月2日,列宁在莫斯科主持召开有3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代表出席的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纲领性文献,决定总部设在莫斯科。在列宁指导下,新建立的共产国际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范畴,予以特别关注。仅以1923~1927年五年为例,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过728个决议。共产国际对中国、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帮助。尽管其中有些决议、指示脱离中国实际,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
作为伟大的国际主义典范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总是以全球视野考量未来。譬如,在中国问题上,他就显示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胸怀。1900年,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一针见血地揭露沙皇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水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①《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9页。1911年,在得知中国腐朽的清王朝被推翻后,列宁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新生的中国》。在《致捷尔任斯基》时,列宁尖锐地指责沙皇侵占中国领土:“沙皇政府在对待邻邦中国时,总是力图不付出战争费用,不冒战争风险而获得成功,他们总是趁中国局势混乱时疯狂讹诈中国领土,这是帝国主义最丑陋的行径。”②《列宁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1919年7月25日,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通称《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首次正式表示要归还中国被占领土。一年之后的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再次表示归还中国领土,废除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列宁无疑是站在时代制高点和全人类的视阈看待主权问题,是个纯洁且纯粹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是,忙于寻找洋人做靠山进行内战的中国北洋政府没有任何呼应,甚至不予理睬。
列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用毕生精力和浩然正气将人类文明列车推离了压榨劳动者的轨道,开始驶向光明的未来。他缔造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创立社会主义俄国,推动建立社会主义苏联,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列宁主义,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巨大的鼓舞。李大钊在《列宁不死》的演说中,盛赞“列宁的功业”“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高度评价这位“弱小民族的良朋”、“被压迫者的忠仆”、“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躯干虽死”,但“精神不死”。③《李大钊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09页。